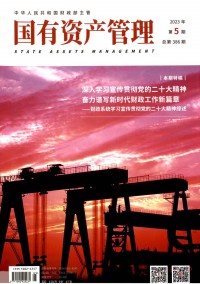国有经济学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国有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国有经济比重分析
一、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值
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大低于乡镇企业、国内私人企业与外资独资的私人企业的经济发展速度,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这个客观事实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理论工作者的关注。这方面的讨论就其内容来说,不外是两类:一是属于规范经济学的范围,即国有企业在什么意义上是必要的?如果它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它在什么样的产业部门中必须存在?其存在所依赖的条件又是什么?第二类问题是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围,即客观上国有企业是如何运行的?国有企业究竟在国民经济中会趋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国有企业的产值在某一个产业中的比重最终会趋于一个什么样的均衡值?是否在所有产业中国有企业产值的比重都会下降?若下降则会降至一个什么样的均衡值?该均衡值是否为零?在什么条件下,当允许私人企业进入时,国有企业产值的相对比重会急剧下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在某产业中的相对优势会继续得以保持?最后,从社会主义生产目标(即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出发,在国有经济与私人经济“合资”的条件下,为了保持国有企业的产值的相对比率,国有经济成份究竟占多大控制比例才是合适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在量上应当如何确定?“主导”是否一定等同于“50%”以上?本文的写作动机是试图从理论上回答上述两类问题。撇开政治上社会主义国家从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与实现控制这一层考虑,本文仅仅是从经济当事人决策与行为的分析层面上考察,当国有企业在一定的目标函数驱动下遵循约束条件求最优解时,国有经济的相对比例会趋向于什么样的均衡值?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所讨论的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是内生地决定的,即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值是国有企业最优决策与非国有企业最优决策的互动过程的一个均衡解。
本文试图讨论的是,在不同的生产条件(成本条件)与市场需求条件外生地给定时,这个内生决定的均衡可能具有若干特殊形式与特殊数值。我们的讨论所要揭示的是,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实质上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有关,甚至可以说,是依赖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的。从80年代后期开始的近10年来国有经济相对地位的下降,与私有企业进入有关,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国有企业改变目标函数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国有经济地位的下降是国有企业自己找的。这种讨论的动机是由国内文献与国外文献两方面激发的。樊纲(2000)最近论证,无论非国有经济在开始时多么弱小,只要其效率及增长率比国有部门高,则Jt作为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在时期t)将趋于缩小,当t→∞时,Jt→0。当然,在同一篇论文中,樊纲也指出,Jt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就趋于0,而是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Jt是否一定趋于零?二是如果Jt趋近于一个大于零的均衡值,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描述与刻画这个均衡机制?在国外的经济学文献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国有经济在混合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有不少讨论。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是P.Beato和A.Mas-colell(1984)的模型。这是一个特殊的古诺双头寡头竞争模型,它在边际成本MC为正,需求函数为一线性函数(p=a-bx,这里p为价格,x为产量,a>0,b>0)的假定下,把国有企业视为一个斯塔克伯格(Stackelberg)领导者,并指出,如国有企业背离纳什均衡点,引非国有企业进入,是会增进社会福利的。1989年,G.Defraja与F.Delbono在《牛津经济文汇》上,从Beato-Mas-Collel的环境里引入了二次成本函数,并分析比较了国有企业继续国有或者私有的不同方案对于市场结构均衡结果的影响。这实质上给出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双头博弈的混合寡头模型。C.Fershtman(1990)给出了一个“合营”企业或部分国有化企业与另一个私人企业双头博弈的模型,正是这个模型实质上讨论了国有成份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的内生性。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K.Basu(1993)综述了混合寡头模型的主要论点。
他这份于1989—199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讲稿是启发本文作者思考这一问题的直接思想资料。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这里我首先考察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是如何作为一个限制非国有企业进入的手段而发生作用的。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当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发生了变动时是如何启动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的?因此,国有企业是否应当存在?国有经济是否应当保持相对优势?其根本的经济学论证,应当从是否应追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福利这一目标的论证中去寻找。如果这一目标在相当程度上仍应当坚持,则在等边际成本函数条件下,国有企业就不会趋于消亡,国有企业的相对地位(比重)也不会趋于零。其次,本文扩展了Fershtman的模型,论证了在由两个部分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国有企业的双寡头模型里,纳什均衡解是回归于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的。因此,如果只就国有企业内部进行渐进式的体制转换,改革是不会有出路的。这是本文的一个主要贡献。本文的第三项工作是,试图将企业目标函数与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S)联系起来,并在双寡头模型中建立了s与国有化在生产目标中的权数θ之间的函数关系。本文基本上是一种静态分析,即在技术条件、市场需求函数给定的前提下,在一个同时求解的古诺模型中来讨论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市场结构。但这里的分析对于动态分析也是有意义的,即它指出了国有经济相对地位的动态趋势是有条件的,我们应该引入决策当事人的决策优化过程。在下述行文里,第二节专门分析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与国有企业存在理由的内在一致性,这实质上是对国有经济必要性的重新论证。第三节给出两个局部追求利润的国有企业双头寡头博弈的模型,并会推导出作者分析中发现的三个结论(命题)。最后,在第四节,总结本文并阐述其政策含义。
二、社会福利极大化与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
我们的讨论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出发。国有企业既然由政府掌握其产权,其目标函数当然也应是政府的目标函数。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多维的,我们只能就每一个所讨论的问题来澄清政府的某一维目标。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视政府在策略意义上的角色与经济当事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样,国有企业的目标,也即是政府在定位国有企业时的目标,应会与私有企业有所区别。在这里,我们沿用Niskanen(1975),Bos(1988),Delbono与DeFraja(1987),Rees(1988)的假定,认为国有企业是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的,而社会福利被定义为是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与利润之和。尽管上述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是西方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的目标,但由于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事实上已处于非国有私人企业的包围之中,又由于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事实上与我们传统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有着一致性,所以运用这样的假定有其合宜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对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可以进行改革。相反,我们在下一节的分析会澄清,讨论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变化正是本文的重要之点,并且,今天国有企业的地位也是与在目标函数上的改革有关的。一旦确定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为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就会引出两个结论:一是,若市场需求函数为线性,边际成本为常数,则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便不会动摇;二是,在二次成本函数的生产条件下,追求社会福利极大化的国有企业不可能阻止住私有企业的进入;但若社会坚持福利极大化的目标,则国有企业在集中度高的产业不会趋于零。显然,第二个结论(定理)比第一个结论(定理)要微弱得多。这说明,生产成本函数是我们讨论国有企业地位时不应忽视的条件。
国企改革理论的未来走向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产权论;竞争论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进行国有经济改革,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产权论、竞争论、结构调整论等理论,本文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演进与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改革开放以后,旧有的国有经济模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为了使我国经济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1979年,我国开始进行国有经济的改革。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探索,我国的国有经济改革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国有经济改革的“产权论”
从中国国有经济改革开始以来,有关“什么是国有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的争议就一直存在。在主流经济学家中,一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即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中国经济学界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论理论源于科斯开创的产权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根据这一理论结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和根本就是改变国有制。因此,诸多经济学都针对国有制的弊病提出产权改革,认为对国有制进行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核心。持这一观点和改革思路的包括了蒋一苇、董辅轫、厉以宁、刘伟、张维迎、樊纲等经济学家。
金融抑制理论研究讨论
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对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约束理论的简要回顾,说明了信贷配给的形成及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然后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信贷配给现象予以考察,对中国信贷配给的双重性进行了说明和解释并提出了结论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贷配给;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信贷配给双重性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渐进式改革国有银行改革
摘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担保代替注资的特殊性,其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应首先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再生机制,二是国有银行投机行为形成的不良资产再生机制。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国有银行改革
摘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国家担保代替注资的特殊性,其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应首先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再生机制,二是国有银行投机行为形成的不良资产再生机制。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