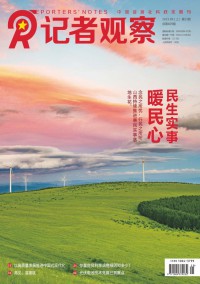情乱夜中环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情乱夜中环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情乱夜中环范文第1篇
上海的房价在中国属于最贵的一档,外国人内环线,港台人中环线,上海人外环线。
上海中心城区的三环(内环,中环,外环)是城市快速干道的三个环体。由于其位置地域的多重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性和人文景观。
可以说,中环是城市的骨骼,内环是血肉,外环则是发肤。中环骨骼需要做到的是疏通,继而显达;内环血肉重要的不只是商业显贵,更要注重文化显雅;而外环发肤是城市形象,需要传达齐整亲和,进而细节显美。
上海,观之风姿卓约,妩媚动人,与之生活,则需用足智慧,精打细算。好在生活在此的人,都有着与这座城市的分区格局和谐共处的天分。
内环,中环,外环的物理概念
上海内环线――以中山环路为基础,是采用高架道路组成的一条交通快速干道,穿插于城市中心,也穿插于众多高层建筑群之间。其边沿距建筑物外沿最近处仅咫尺之遥。上海内环线高架道路全长48公里,由三部分组成:浦西段29公里连续高架道路,浦东段8公里地面道路,通过浦江双桥(二桥长11公里)连成一体。
上海中环线――介于外环线和内环线之间,是中心城区中心区发展的边界。中环线没有采取封闭交通干道的形式,而是开放的形式服务于城市和两侧用地。其区域在浦西段由虹梅路、虹许路、真北路、汶水路、邯郸路、殷翔路和军工路组成;浦东段由金桥路、张江路、华夏路和上中路为主,总长约71公里。中环线快速干道穿越于众多的优秀居住区和科研教育机构之间,其中不乏上海著名的住宅群体和著名院校。同时也与许多绿地、公园和商业设施相连。
上海外环线――上海中心城区的发展界限。它的建成标志着城市生态缓冲空间的建立。上海外环线工程全长99公里,全线设8车道。外环线位于上海城乡结合部,环内城区面积680平方公里。它连接10条快速干道、10座大型全互通立交和徐浦大桥、外环隧道2座越江工程。
内环,中环,外环与上海楼市
业内人士分析,2007年会是楼市较稳的一年,在房价的走势上应该会有结构性的区别,那就是“内环稳涨、中环趋缓、外环下跌”。
事实上,上海楼市“三重天”的大格局正初露端倪:内环线以内由于土地稀缺、供应量日渐减少,造成地段的保值升值,成交量和成交价格也止跌回涨;中环线由于地段和配套达到了一个均衡点,只要价格适当下调,就会成为以婚房为主的刚性需求的释放点;而外环以外地区由于配套欠缺、交通不便,不少楼盘自调控以来成交量直线下降,成交状况一直不能好转。外环的楼市有一个规律,就是在涨的时候领涨,在跌的时候领跌。外环的土地供应量是最大的,但是它的需求却没有那么大,因此市场趋势向下是很有可能的。
内环,中环,外环的感性碎片
文/何菲
一位在上海失败过的台商感慨:“上海是人间天堂,也是人间炼狱。”
这些年,进入上海的门槛已非常高。如今在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的大部分不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们早搬出了上海的内环线,散居到了中环线、外环线两侧。
想在上海捞世界的新移民很快会发现:上海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触手可及,尽管外滩能让人魂牵梦萦,陆家嘴能让人心潮澎湃。
真正的上海在静安寺,在徐家汇,那才是真正的中西文化的融合。衡山路的梧桐总是透着一种文明,那叫做“舶来”。鲁迅公园也只能羞涩地躲在大气的虹口足球场东南。明珠线以它特有的轻灵告诉中国其他城市:什么叫差距。
你能漫步于淮海路南京路的霓虹灯之下,然而从高级商务楼里走出的男女小资告诉你:梅陇才是他们的生活。尽管这个位于中环线外环线之间的社区从前只能叫做梅陇镇。开着车,谈笑间你就走到了松江……那里高新的企业告诉你,欧美的融资聚集地其实在松江,佘山的豪华别墅群告诉你,那里是新贵的新一轮投资所在。
回到内环,上流社会和底层生活是如此近在咫尺。里弄只是豪华高楼下陈旧的花园,零乱的竹杆和飘零的晒衣告诉你上海底层的艰辛。内环之内,真是上海社会的冰火两重天。
外环以外,嘉定赛车场轰鸣的 F1带来的文明又有多少人能承受之重,同样在城市边缘,宝钢上汽宏大而壮丽,而中心区正大广场的外华内空,也不代表上海的虚荣。
也许一座蓬勃的城市并不能叫做一座完美的城市,但它给人的启示和感触真的很多,很深。
如今,上海人在街上最大的感受是,似乎一夜宝马遍天下。尤其是在浦东,街道宽阔得多,各种型号的宝马成为驾乘者的财富标签,经常会看见它们窜进楼价在每平方米2万元的社区,比如香梅花园、新世纪花园等,这些社区有着庞大的园林面积,但白天很少见人,晚上也很少有灯。
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城市居住分区格局是与城市郊区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在郊区化的最初阶段,最先搬入郊区的是富有阶层,此后,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相反,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不断衰落,公共设施陈旧,治安环境恶化,成为穷人居住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中国看起来正在运作的是一个与之反向的过程。经济适用房和拆迁房的修建,实际上也加剧了这个过程。事实上,人们来到城市,是因为城市能提供更加美好的生活。尽管西方出现过逆城市化的运动,但那不过是主流中的逆流,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中国城市空间正在被市场化。建国以来,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相应的是,人们的居住地点实际上也是计划控制的产物。因此,一个人住在哪里――哪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哪一个区域,基本上是一种偶然。一个下岗工人,说不定家住繁华的南京西路旁,一个腰缠万贯的新贵,说不定还住在空气污染、治安很差的某个中部城市。显然,这种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长期维持,货币之手必然引导多级别的城市化,在一个城市内部,则是外、中、内环的重新划分。如今在上海,已经有一种通用的说法,内环里住说英语的,内环和外环之间住说普通话的,外环以外住说上海话的。
上海不是能随便进入的。
上海的房价在中国属于最贵的一档,外国人内环线,港台人中环线,上海人外环线。北京人先买车后买房,上海人先买房后买车。有个安心的房子是每个男青年人结婚的必备,上海女孩除了丑的没法要的(外国人品味很奇怪)才会找一个外国人,嫁个港台人倒是蛮多的事,毕竟家住中环又有车,去新天地很方便。
赚钱,买房,结婚,生子,长大,赚钱,买房,结婚,生子……这样的循环会让有些人觉得幸福,有些人觉得厌倦,有趣的人永远会从生命的枯燥循环中找到快乐。有的人也许会觉得上海人缺乏对上海生活方式的自醒,但我觉得上海人的乖巧和聪明正在于:他们在人生的自由和幸福,忙碌和压抑之中找到自我平衡点的生活方式,也许是适应上海这座城市的最好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喜欢安家上海,它让人有家的感觉。这里少了许多漂泊悲壮之感,这里白天需要紧绷神经,而夜晚却是美轮美奂。每个普通人可以在黄浦江边吹着暖湿的江风,牵着家人的手,看百年的忧郁与急促,做自己狭小的梦,为身边的几个人。
内环情结
内环内,老城区,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地域概念,而是有着悠久绵厚的历史积淀的区域――成熟的社区架构、深厚的文化底蕴、兴旺的商业氛围、发达的交通系统。这里有着大多数上海人刻骨铭心的私人记忆和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难舍内环的原因。
上海人之“怒”
文/凌惠芬
上海人的务实是众所周知的。市区的基本建设给市民带来极大的实惠,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旧房拆迁。
本来这是件非常欣慰的事情。但以精明能干著称的上海人突然发现,市中心那些动辄几百万一套的公寓的主人,不是外国人,台湾人,就是外地人,当然还有海归。而他们这些老上海却大都因拆迁被安置到远离市区的外环线居住。原先上海人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之说,虽然现在老观念已经大为改变,但是,老上海人的心里总感到难以平衡。
不过,上海人的这个“怒”毕竟是“喜中之怒”。毕竟自已也已经住上宽敞的新房子了,自然界还有阴晴圆缺呢,何况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内环的老虎窗
文/郑树林
上海的弄堂出名,上海的老虎窗更出名。现在有许多老式公房平改坡,也是延续了老上海石库门平房开老虎窗的设计理念。
那时,我住在私房,没有机会领略老虎窗的风采。因此,我常常到同学家,当石库门天井的大门关上后,我一溜小跑和同学来到三层阁,从那扇小小的老虎天窗看天上飞机小鸟,星星,月亮,我觉得我离天很近,近到甚至可以摘到星星,真羡慕极了。后来,家中翻造私房,我就向父亲提出,翻造的房一定要有老虎窗,而且自己要住在有老虎窗的房间里。房子落成后,那老虎窗与石库门的老虎窗不一样,无高耸入云之势,却有视野开阔之态。我站在小凳子上,抬头可见蓝天,低头可看弄堂里男男女女,进进出出,风光无限的就是这老虎窗。幼小天真无知的少年在老虎窗看到的各种故事,男女“绯闻”就从我们这些小孩的口中说出去了,老虎窗就像一个弄堂里的观察哨,监视岗加喇叭口。
小时候不懂事,每次在老虎窗看见弄堂底邻居的叔叔或阿姨,领着个不熟悉的阿姨或叔叔时,还大声问候,弄得这些叔叔阿姨那头抬起来看我们时,脸上红红的像西瓜瓤,不过很开心。这么一打招呼他或她会从口袋里摸出糖果,从弄堂的小道上扔上老虎窗口,这大概就算是封口的小费吧,如果不小心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把事情泄密,一场家庭纠纷整个弄堂都会知道,这泄密的我们虽说童言无忌,但在父母面前还免不了一道美味的“竹笋烤肉”,长没长记性要看自己的聪不聪明了。
住在老房子久了老虎窗的功能看到的就越来越多,记得有一部电影是赵丹、周璇主演的,两个人在各自的老虎窗里观望,还唱起了情歌。我们那时候在老虎窗前抛来抛去的小纸团,不知道有多少因为手力不够,小纸团从屋顶瓦片上滚落到天井,让大人惊动拣到后打开,后悔也没用了,就等“竹笋”上身。
随着年龄的慢慢长大,家里住房显得有点紧,父母双方单位的领导曾多次来过我家,就是为了解决住房。记得最清楚刚刚粉碎“”后,父亲调到浦东分厂上班,单位里可以分配很大的新房,但要将这间带有老虎窗的老房子交出去。不知什么原因,父亲没有同意,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有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虽然挤在一起,三层楼的空间经过新的开发,老虎窗下成了我和哥哥的独立空间。
春夏秋冬四季我喜欢看下雨时,雨水打在屋顶的瓦片上,然后汇聚在瓦片链缝之间,滴在屋檐的天井里,瓦片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瓦片中也会生出许多不知名的小草,四季中可以看着小草长大,开花结果,枯萎来年再生的生命力。最喜欢的是冬天下雪以后,推开老虎窗,看见的是白雪皑皑,屋顶上偶见几块黑瓦片露出,黑白分明煞是好看。弄堂口被大人们铲起堆起的雪堆,被同学少年做出了一个个的雪人,老虎窗口的小雪球变成了打雪仗的子弹,弄堂口下的雪球不停地向老虎窗击,弄得地板上雪迹斑斑。
老虎窗是童年看大世界的窗口,有着许许多多磨不去的回忆。现在再看见老虎窗几个天真的小脑袋在窗口探头探脑出现,总让人想起那难忘的往事。
内环以内,最“上海”的生活方式
文/凌惠芬
曾经有一段时间对老房子特别有兴趣,带着相机穿街走巷拍老式房子的砖墙、大门、老虎天窗。
身在这样一个城市几十年,分为住内环以内和中环附近的两个阶段。如今一走进小弄堂,就好比进入了人体的毛细血管,既陌生又熟悉。
前几天偶尔路过山阴路,不自觉地就往里走。山阴路靠市中心四川路的街口,洋房边摆了很多小摊,卖水果、卖杂志、配钥匙,和中环线附近的成熟社区没什么不同。但看上去确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差别在于:没有急躁,没有喧嚣。虽然有点杂乱,可也掩不住一种从容,一切都不紧不慢。
内环以内的老房子就是这样慢条斯理。小摊的摊主好比拉家常一样做生意,客人散漫地边走边看。放慢你的节奏,一切都显得这样安详自如。
穿过短短的街市,立即显得非常的宁静。浓密的绿树后面隐隐透出红瓦坡顶,天窗下的女孩在坡顶下惬意地看闲书。转到大陆新村,看到了鲁迅故居,那样犀利的文字来自于那样的平和的环境,真是让人奇怪。
溧阳路、山阴路、四达路、长春路一带,是这个城市走弄堂的好去处,也是无目的散漫的好去处。当你看到过街楼上写着1914的时候,看到墙头上一溜的各种花盆的时候,看到爬满青藤的砖墙的时候,也许能演绎出那个年代的故事。
身边熟悉的城市正一天天在消失,代表着一个年代的石库门也在消亡。内环线以内,最“上海”的生活方式也会消失吗?
难舍内环
文/张萍
“阿拉屋里就住勒内环呀!”能这样说的上海人,多少有着一点“自得”的。毕竟,在如今的上海,内环内的民居,较之20年之前,已是少了很多。这其中,有旧区改造必须拆了的危棚简屋,也有市政规划而需要重新布局的老区旧街。离了旧居的原住民,大部分都把新家安在了市郊结合部,也就是现在的中环或外环。尽管新家是那么的宽敞明亮,但在他们的内心,对内环内的旧居,却是那么地难舍难弃。
所以,就有这么一些人,是宁弃“大”家而甘居“小”家的,深究起来,也不无可取之处,算是求仁得仁之别解吧。
一好友,三口之家,在市区住得好好的,只因婆家动迁,丈夫是独子,二老需要照顾,就合二为一,在浦东买了房,足够三代人起居的了,但却留了后手,没把自己的小房子卖了,赚点小钱――出租了。
新家的环境,自是与原来的没得比,不说其他,单是站在阳台,放眼望去,那还真的就是舒心养眼:花草馥郁,树木葱茏,更有人造湖水,中立假山,把二老高兴的,直说,今后都不用逛公园了!
老人高兴,小辈自是也高兴啊,一片孝心没白费嘛。可没过了几个月,好友心里就不乐意了。其实,也难怪妻子,夫妻俩工作在浦西,女儿读书也在浦西,这每天来回跑,搭上的时间、金钱,可以忽略,那多耗费的精神,实在是有点吃不消了。尤其是孩子,天天早出晚归,少了睡眠,还影响了读书的精力。转学吧,浪费了重点中学的名额;没了好的师资,孩子的前途难保。虽说之前对这些也有顾虑,但总觉得还能克服。如今发现问题还挺麻烦,经反复商议、权衡,跟老人说明了难处,一家三口重又打道回蜗居,收回了出租屋,过起了如常的日子。只是每逢节假日或双休天,他们是必回浦东陪伴老人的,也可享受大房子的舒畅啊。
电聊好友,听得出:那叫一个称心啊,哈哈!
内环内,老城区,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地域概念,而是有着悠久绵厚的历史积淀的区域――成熟的社区架构、深厚的文化底蕴、兴旺的商业氛围、发达的交通系统;这里还有着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大剧院、新天地、修缮一新的音乐厅、苏州河沿岸的创意园区,以及世博会将会给老城区带来的崭新面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爱在内环的理由,也都成了难舍内环的借口!
一张钢丝床
文/郑自华
女儿曾经在她的作文里写到:“什么时候才能拥有我自己的一张床?”每当看到这里,我的心里就一阵痛楚。
女儿生于1980年,从她出生开始,我们就给她备了一张小床。小床伴她度过她的孩提时代,以后就开始用折叠式的钢丝床。那时家中房子不大,16平米,除了必要的家具,还放着一张写字台。每天晚上到睡觉的时候,就要将那张折叠式的钢丝床打开,放在我们床的边上。这时家中已经没有可以走动的地方了。钢丝床的位置在大床和方桌的中间,狭窄的空间里要放钢丝床,绝对相当于搬场公司到老式公房搬大橱走曲直的楼梯一样,难度很高。放钢丝床的任务是由我承担的,一个大男人既然不能给妻女舒适的住家,只能天天晚上放床了。床有10多斤重,既不能碰到家具的漆水,还要小心翼翼,免得将地面弄坏。如果晚上有事不能回家,这任务就由妻子担当。有几次,妻子中班,我又不在家,女儿就睡在大床上,待我们回家,女儿已经睡得很熟了。我又不敢睡钢丝床,怕将床睡坏,只能三人挤在一张床上。我缩在角落里,个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了。记得一次,我晚上10点多回家,妻子中班尚未下班,只见钢丝床放好了,而女儿在一旁却哭泣着,原来女儿一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床放好了,但由于力气小,钢丝将她的小手划出血来。我心痛得掉下眼泪来,要知道那时她才10多岁啊。
1997年,女儿18岁的时候,我们终于搬家了。虽然面积不算大,才50多平米,可女儿毕竟有了自己的一张固定的单人床,当女儿第一次在自己的单人床上蹦跳翻滚的时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今年我们第二次搬家,面积换成了100多平米,女儿有了自己的一间闺房,小床也换成了6尺的大床,上面是厚厚的席梦丝。
上海房地产走过了18年,女儿为有自己的一张床也经过了18年。没有上海房地产这18年,我的女儿可能至今还在睡钢丝床。
中环,快捷生活升级版
中环这一承载着上海新一轮经济发展期望,肩负“完善路网、均衡车流、服务世博”职能的城市快速干道,历经39个月的日夜兼程,鲜活地出现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中,上海人的快捷生活又再次被升级。
中环线工程是上海城市快速干道中,首个引用了景观设计的理念,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融,穿越于众多的优秀居住区和科研教育机构之间,同时也与许多绿地、公园和商业设施相连。
在“围城”外逍遥
文/茅永民
女儿真的大了,再也“屏”不住了,那十几平方的小屋里,见到她要换衣服,我就马上“识相”地走到厨房里抽烟,还不时地催促着“好了伐?好了伐”,看来,这日子确实难以持续下去了。
1997年我准备买房了,这在当时可是个“重大决策”,朋友们听了都傻忽忽地看着我。大概觉得我很有钱,可捂着并不“饱满”的口袋,买环内的力不从心,买环外……说真的,是有点下不了决心。就像一个拥有私家车的让他骑自行车了,用北京话说,那是下了档次;用阿拉上海话讲是“脱了西装穿长裳”,肯定要下大决心的。
两老同学来找我,说他们都买房了。“在哪里?”我急切地问。“五角场”。那是什么地方,我记得,小时候去过,那不就是“农村”嘛!拗不过他们的“热情”,去看了那新房,我就动摇了,且不说那80几平米的宽敞,就是那绿树成荫的小区环境,让我乖乖地掏出了钱。几年后,我这2500元的房价陡升到了近万元,难怪有人说,其实过些年就有财富的机会,看来我还是把握住了。
本来荒凉偏僻的地方,就看着它一天天地变化,我此刻是在被高架“围”着的“内环围城”外面逍遥着,我看着门口的马路在挖着地铁,对面的大卖场刚刚建成就涌满了喜气的人们。今年,五角场商业圈一建成,我在徐家汇的朋友那天驾车来我家,跟我讲了那中环线的“彩蛋”,巴黎春天、万达广场、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沃尔玛……他说五角场已成了徐家汇第二了,而同样的商品比徐家汇同样的商店里价钱又便宜,所以他们一家今天采购了一车子东西……我笑着和他调侃道:那应该将徐家汇改为“五角场第二”了,否则你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说得都大笑起来……
星期天,我和娘子逛了整整一天“商业圈”,在家门口,散步似地就去了,多潇洒啊!中午,我们吃了25元一碗的面条,娘子不舍得,说过去这里的大排面只要4元钱,我说:档次上去了嘛!你没听说过?地段的价值就在这面条的价格上!回家路上,我又在“创智天地”里的咖啡厅里请娘子喝了“爱尔兰咖啡”,我们像绅士公主般地慢慢品着香浓的咖啡,一句广告语伴着幽雅的音乐“味道好极了”……
晚上,我失眠了,因为,有朋友说,松江那里的带花园的复式房太好了,我的心又动了……
家住中环的真实感受
文/管琴
我觉得,中环是城市的骨骼,内环是血肉,外环则是发肤。中环骨骼需要做到的是疏通,继而显达;内环血肉重要的不只是商业显贵,更要注重文化显雅;而外环发肤是城市形象,需要传达齐整亲和,进而细节显美。
我家住中环,现在家住中环的上海人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对于大多数的上海人来说,其深刻的家居变迁的印象就是随着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广大市民也是逐步逐步往城市的迁移。把中心让给了规划,让给了商业,让给了地标。当然,根本上说,我们的家居环境是改善了,宽敞了,明亮了……可是,一有机会,我们记忆深处的光荣史还是会冒出来闪回闪回。比如,“小时候,我家可是住市中心呢!”那时候,小朋友做完功课相互一照应,十分钟后就出现在人民广场的小三角公园里。一玩,就玩到黄昏才一溜小跑着回家,从不耽误吃饭时间。那是一段人有我有,不用攀比的岁月。
现在,闲时去淮海路走走,坐车的话,起码要半个小时。倘若逛得尽兴,买了一手东西回家,傍晚时分打车的话,那就更磨了。家住中环而上班较远的上班族,早出晚归是辛苦的。每天先与交通工具作战,再与革命工作作战。打惯车的人,也惹了一身“打车病”。自己开车吧,想想是最无后顾之忧了的,可惜实际操作下来的人都心知肚明,那也是有苦说不出来的活计。现在问题凸现的“绿标”一说,就是实例。记忆里,我的姨、舅他们上下班,走走也就几条街的光景,羡煞吾人呐。真希望随着卢浦大桥、中环线、轨道交通的完善,让中环骨骼架构彻底地清晰起来,能够真正做到四通八达,给城市的加速运转提供方便,给城市人提供方便。
除了上班、购物出行之外,一些家居用品的购置,上学,看医,银行,邮局等关切到民生的问题,还是不必担忧产生困扰的。家附近除了家乐福、乐购、九百超市,一家家小型超市也比比皆是。还有特色的书店、服饰店、音像商店、美容院、健身俱乐部鳞次栉比;大中规模的饭店,大众小吃店,也是很可以挑挑拣拣的。
住在中环的尴尬是有的,好像它虽然有影院 K 歌房,但比不上正大、钱柜来得赏心悦目;有书店,图书馆,但肯定没有上图的敞亮,季风的品调;虽然也有吃的玩的地儿,但过不了多久,你还是想着去新天地溜达溜达,好沾染潮流感觉;然而,住在中环的心理优势也是明显的,它没有内环的热闹,也就少了很多纷杂;不像外环那般遥远,毕竟我们还要正常上下班么。“适中的距离,产生适当的美”,是我这个家住中环人的真实感受。
外环,刚性需求的释放源
外环楼市一向为“百姓楼市”或“低价房”的代名词,目前已形成五大特点:一是已然成为上海楼市刚性需求的释放源;二是催生了百姓楼市多元化价格体系的发展;三是成为一大批“新上海人”怡然乐居的首选之地;四是“截流价值”的潜在行情表现仍十分可人;五是快捷交通顶推的择居思路已发生了悄然变化。
外环群体的生活主张:价格不高,品位不低;远离喧嚣,不离时尚;拒绝豪华,拥抱温馨。
内环、外环的本质区别
文/惠芬
但凡你在上海住过,一定会发现上海的内环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城市。狭窄但是安全的街道,美丽的行道树,遍布街边的小商店和饮食店,传统的高档百货公司,穿着打扮时尚的人群,丰富的夜生活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构成的一个城市。内环的土地供应相当有限(浦东地区除外)。内环的住房以平方米计算比郊区要小很多,不过,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安全的夜生活则是什么都不可比拟的,这也是为什么内环的有些地区房价出奇的高,但是仍有人愿意接盘。
内环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安全,很多外地朋友喜欢津津乐道他们家乡动不动就动刀子的传奇。不过,发生这种传奇的地方,一定不是大家所向往的居住地。上海能够有那么大的台湾社区,安全的居住环境应该是居第一功的。
内环内现在的房价究竟贵不贵呢?可以说也贵也不贵,取决于对谁而言。动辙200万的房价可能对上海大多数工薪阶层而言是不小的数目,但是现阶段内环内豪宅的主要对象并不是传统上海人,外籍人士、海归和中国各地的富裕人群才是内环内楼盘的主要对象。如果是上海人,设想夫妻都工作,年薪如果都是30万以上的话,供这样一套房子应该是没有问题,但这样的人士在传统上海人群中占极小比例。
情乱夜中环范文第2篇
《沉香屑第一炉香》:
以香港来找寻失去的上海
张爱玲最喜欢的是上海人,但她最成功的小说写的却是香港,献给上海人的也是一部“香港传奇”:“写它(《传奇》)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2]可见张爱玲的上海情意结与香港意识是分不开的,两个城市的关系在于“参差对照”。
香港和上海的对照就是如此,从外在看,她们都有孤岛与世隔绝的特点,而内在上,她们都是摩登时代、物质挂帅的心性。张爱玲反复强调自己是“拜金主义者”,对享乐非常热衷。张爱玲从不讳言自己的“俗”,并对“俗”津津乐道,甚至于她在《烬余录》中写战争前后和发生时自己与同伴的行事与感受,竟然一点也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情怀,还是唠唠叨叨地谈吃谈玩谈恋爱,她对物质文化的极致崇拜从中可见一斑。
香港的另一个特点是新与旧、中与西的撞和交融,在张爱玲的年代,撞的情况远比交融多,就造成了香港“不中不西”的杂种文化。对于这种混合文化,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3]小说表现得最用力的是梁太太的房屋建筑、布置及宴会场面,一言以蔽之,就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中西混杂的建筑除了是给远道而来的西方人瞧瞧外,也是上海的一种潮流――外滩的西式建筑就是如此。
“人人(香港)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难学样,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早已翻花样。”[4]上海走在潮流尖端,香港那时候只是跟屁虫,张爱玲想必在上海看过一些新鲜物事,很快就被淘汰了,来到香港后,又重新发现这些“潮流旧物”,不免感触良多,电影院就是一个好例子:“中环一家电影院,香港这一个类型的古旧建筑物有点像影片中的早期澳洲式,有一种阴暗污秽大而无当的感觉,相形之下街道相当狭窄拥挤……老式电影院,楼上既大又坡斜得厉害,真还没看见过这样险陡的角度。”[5]回忆上海的过程中发现上海和香港的相似性,去沪日久,张爱玲对上海的热情依旧,可是对上海的回忆却日渐模糊,她只会求助于香港来找寻她失去的上海。
《沉香屑第一炉香》有个耐人寻味的结尾,讲述乔琪和薇龙在新年逛湾仔遇到一群雏妓的事情,这个安排固然是以雏妓来响应薇龙的堕落,可是从城市书写的角度看来,她们的相遇可以看作是“双城”的对照。从上海来港的薇龙象征上海,而湾仔街头的雏妓则代表那个时期的香港,寓言着上海和香港城市命运的重叠。一个是孤岛租界,一个是殖民地,她们受人蹂躏的遭遇是相同的,可是上海毕竟还是中国,外国还给她“几分薄面”,如同薇龙是高级交际花,虽然干的仍是“长三堂子”的勾当,但至少衣着光鲜,出入贵地,堕落得有派场;香港是殖民地,居民都是“殖民”,自然不会受到尊重。殖民者对香港的开采是不留情面的,情形就如同那些英国兵挟住那个雏妓准备去泄欲一样,相对于薇龙,湾仔雏妓的命运自然更悲惨。张爱玲刻意安排的这个结尾就意味深长地交代了“双城记”的内容和原因,亦表达出她对上海前途的忧虑:“后面又拥来一大帮水兵,都喝醉了,四面八方的乱掷花炮。瞥见了薇龙,不约而同地把她做了目的物,那花炮像流星赶月似的飞过来。”既然香港和上海的命运有宿命似的一致,上海会否“沦落”为另一个殖民地?而香港成为殖民地是“被迫”的,受西方资本主义侵蚀至麻木的上海却是“自愿”,甚至享受去当殖民地,如果是这样,她的上海还会在吗?
有了“溯源”和“未来”的概念,我们就能明白《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作者为何不断提到上海了――她提醒读者,她是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和眼光去“看”香港,从而对照出记忆中的上海:“香港的深宅大院,比起上海的紧凑、摩登、经济空间的房间,又有另一番气象。”[6]对照的目的,不是文化推崇,而是借反复强调来说服自己仍是上海人。
张爱玲口口声声称“到底是上海人”,但她留在香港的那几年,创作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也得到香港文学文化永远的纪念和研读,正如梁太太所说:“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你现在又是一个人。你变了,你的家也得跟着变。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7]或许张爱玲本身真的只是想为上海人写一部传奇,可是香港死里逃生的经历让香港在无意识间成为她思想中无法取缔的一部分,使“创作渐渐背离她的意思”,成为一部“双城记”。
《香港1960》:
作为台北避难之所和城市寓言的香港
与张爱玲一样在香港看出末日意识和身份焦虑的是白先勇。白先勇最成功的小说是“台北人”,这些“台北人”中,很多都有着“上海身份”或“上海记忆”。如《永远的尹雪艳》等等,白先勇直言不讳他对上海的喜爱:“在上海住了两年半,直到1948年的深秋离开。可是那一段童年,对我一生,却意义非凡……战后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8]台北人的“上海籍”绝非偶然:“虽然短短的一段时间,脑海还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9]“最后的一抹繁华”,不就正像白先勇笔下恋恋往昔的台北人吗?可见,白先勇的“双城记”是有意识的,只是在他笔下,上海变成了客体而已。
在“双城记”的意义上,白先勇是张爱玲的延续。他们的香港命运是连续的――张爱玲从薇龙身上寄寓香港奇货可居,略一调教就可大红大紫,白先勇的薇龙却已经年老色衰,末日将至,二人对香港的感觉也一脉相通,《沉香屑第一炉香》是“活到那里算到哪里罢!”,《香港1960》是“我没有将来”。张爱玲在香港看出中西文化的冲击,白先勇则看出香港在时间定位上的模糊性:“教书的人总是要讲将来,但是我可没有为明天打算,我没有将来,我甚至于没有去想下一分钟。明天――太远了,我累得很,我想不了那么些。”[10]香港没有历史,仿佛也没有将来,他生存在一个“第四空间”,身份、优劣都得不重要,不管你是前朝遗老还是民国将军:“你害怕?害怕我是个在湾仔阁楼顶的吸毒犯?因为你做过师长夫人?用过勤务兵?可是在床上我们可没有高低之分啊!”[11]
白先勇以香港来对照台北,1960年代的台湾政局混乱,许多权威人士被迫害,使白先勇对自己的贵族身份产生了危机意识,他一方面沉溺于自己的过去:“至少你得想想你的身份,你的过去啊,你该想想你的家世哪。”另一方面又害怕这种身份:“你是说师长夫人?用过勤务兵的,是吧?可是我也没有过去,我只晓得目前。”香港这个埋葬身份的地方,为白先勇的认同危机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让他暂时不去想台湾的政治风云,可是他又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任由香港埋葬自己:“姐姐,嗳姐姐!你一定要救你自己,一定要救”他始终要寻回自己的身份,在白先勇和张爱玲心中,香港模棱两可的身份是没有未来的,但却可作为暂时的休息,等他们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就能回上海和台湾。
如果说《香港1960》中的余丽卿象征台湾,那么她的情夫――湾仔阁楼顶的吸毒贩,代表的就是香港。而余丽卿和情夫的“命中注定”就像在预言台北和香港遭际的重叠。《香港1960》以意识流方式写作,给我们一个混乱的印象,也塑造出一个杂乱的香港形象,单就小说开头的家居布置来说,绿与粉红的配搭已经给人一种绮丽而不协调的感觉,连海绵枕都是“肥胖”的,就有一种粗俗的感觉,加上庸俗的香水,整个环境显得奢华而缺乏品味,这种附庸风雅的态度是旁人对香港的普遍鄙夷,但正如东方主义者以建构东方来映射西方社会,白先勇也是想象一个香港来对照台北:“或许是我的偏见,这些新与的咖啡馆,豪华是豪华,但太过炫耀了,有点暴发户。”[12]白先勇惊见台北发展的一日千里,对这个充满依恋的城市感到陌生,让人回想起余丽卿的梦:“蒙间,余丽卿以为还睡在她山顶翠峰园的公寓里,蜷卧在她那张软绵绵的沙发床上。”[13]对现实中自己身处的湾仔阁楼、身旁的男人、对面夜来香的广东音乐和窗外的夜市叫卖感到“喘不过气来”,我们将发现余丽卿和白先勇“无所适从”的感觉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只是白先勇为进步而惊,余丽卿为退步而怵――白先勇以作家敏感的心,害怕台北虽然现在正在攀升,但终有一天会像香港般毁灭――“香港就快完结了,东方之珠。嗯,这颗珠子迟早总会爆炸得四分五裂。”[14]如此一来,香港岂止是台北的城市寓言,更是城市“预言”,白先勇表达了他对台北前途的忧虑,在“去与留”之间挣扎:选择清醒,离开台北或是改善台北“趁现在还不太迟离开这里吧”[15];还是“我只有眼前这一刻”[16],得过且过?
上海与香港的“双城记”在学界已是一个热点,可是台湾、香港的双城记却没有被认真探讨,仔细一想,就不难发现台湾作家多有“香港渊源”,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感谢香港给了他们丰富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环境,余光中是如此,施叔青亦然。乡土情结是台湾作家的一个共同心结,在台湾他们感觉有切身之痛,在创作中往往有所顾忌,然而在香港这个“奉旨自由”的城市,他们找到熟悉的“家乡味”,另一方面又因香港与台湾的距离而感到放心,安于他们的边缘书写,台湾和上海都看出这个城市与她们本质上的相近,亦利用了香港“无王管”的地域特色,以香港做幌子来书写自己的“故城”。
白先勇以香港写台湾,表达了他的身份焦虑,同时也反映出香特的政治无意识:末日意识,没有过去和未来,余丽卿如梦般的呢喃就是对香港纸醉金迷的反映,表现了白先勇侨居香港时感受到的香港印象,《香港1960》以香港写台湾,又由台湾反观香港,成为台湾上海的“双城记”。白先勇和张爱玲都对香港作出“凝视”,他们把香港作为“他者”来观照台湾及上海。这种“他者化”行为是由“凝视”来实现的。当然,白先勇和张爱玲对香港的批评有一种自身优越感的情结在内,他们眼中的香港是台湾和上海的参照物,让他们从“他者”更了解“自身”,这种方法透过“凝视”来实现,凝视既可以是轻蔑的,也可以是妒羡的,可以是他者,也可以是自身。因此,当香港文化工作者认同了自己的香港身份,承认了香港身份的独立性,他们就能把张白的“他者”凝视转化为对“自身”的凝视。
《候鸟》:书写一个完整的香港
城市生活多彩多姿,物质丰裕,城市的“摩登”暗示了她与世界的接触,正因为如此,城市人才能有属于城市的“国际视野”,并为自己的见识而自豪,张爱玲爱的是上海人的“通”与“坏”,而“通”与“坏”又不限于上海这个城市,作为上海的参照物,香港也不遑多让,香港作家每每以香港为题材,透露了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迷恋,对香港花费得最多笔墨,也最脍炙人口的香港作家非西西莫属。
西西生于上海,五岁移居香港,在香港接受教育在进行创作,她自认是个地道的香港人。香港文学史把西西列为香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绝不是以她的成就来壮大自己的声势,而是由于西西对香港的关切确定了她作为“香港作家”的地位,她的作品自然成为“书写香港”最具权威性的文本。一般认为,西西最代表“香港性”的作品是长篇小说《我城》,可是讲到城与城之间的对照想象,《我城》就不及《候鸟》适合了。《沉香屑第一炉香》与《香港1960》均有一个“出城”的背景――薇龙从上海到香港,余丽卿由台北到香港,《候鸟》也有着一个“出城”的过程,主人公素素由上海逃难至苏州,再辗转到了香港,“流徙”经历让作家以他者想象自身成为可能,并促使他们站在不同的视点观察相同的问题。
作为“外来者”,台湾和上海作家对城市的“惊”又不局限于其事实上有多“光怪陆离”,或多或少含有“这个妹妹,我见过的”的熟悉感在内。假如要用一个意象去形容这种“熟悉的荒诞”,“哈哈镜”是最佳的选择:“看到镜里反映出扭曲变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的奇形怪状,笑不可止。童年看世界,大就像‘哈哈镜’折射出来的印象,夸大了许多倍。”[17]外来者看城市就像是看哈哈镜,照出来的影像不管如何奇形怪状,终归是自己。张爱玲和白先勇让我们看到上海台北的侧面,却没有让我们在“寻常”的角度去考察这两个城市,西西的《候鸟》却让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城市一同出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香港。
“候鸟”一词本身就是“向南方迁徙”的意思,南与北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上海虽是南方,但与更南的香港相比,她便是北方了。《候鸟》讲述的就是主人公林素素因躲避战乱,由上海移居到香港的过程。《候鸟》中,素素叔叔的生活环境才像李欧梵描述的上海:“叔叔和我们不同,我想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每天上学去,总要经过叔叔的房子,那是一幢很高的楼房……除了叔叔住的地方,我只在百货公司里见过电梯”[18]。叔叔住的是像“外国蛋糕”的房子,由外观到家具都充满洋气,活脱是上海的“摩登建筑”。而素素与叔叔一家进行的活动也比较接近李欧梵和张爱玲的上海:叔母会和素素及素素妈妈去看戏看电影,熨头发,缝旗袍,吃冰淇淋,讨论首饰――是阔太名媛专有的优哉游哉的上海,这或许代表了香港繁华的一面――如前所说,以前香港的潮流都是上海的重复,但这绝对不是完整的香港。
早期香港人感觉自己与中国的相连就是通过与大陆“移民”接触而发现的,这些移民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香港人建构他们的中国想象。在众多移民中,香港最感兴趣的是上海,一来是由于上海移民多,从北角“小上海”的称号就可见一斑。香港电影也不乏上海元素,如《金枝玉叶》的开场音乐就是上海的旧歌曲,电视剧《上海滩》就更是以上海为背景的。在这些媒体中,上海成为怀旧的代表,可见香港对上海的感情是一种“寻根”式的中国情结,既然香港惯于把上海作为“怀旧”的形式,香港文学中的上海不过是现今香港人的历史记忆,她指代的不是真实的上海,而是香港本身。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研究上海都市文化不外乎是一种消费、物质的文化,这些文化必须在消费场所林立的情况才能出现。李欧梵在第一部分“重绘上海”中列举当时上海的消费场所包括:外滩的西式高楼、百货大楼、咖啡馆、餐厅、公园和跑马场,而在白先勇和张爱玲的“小说上海”中,这些场景都是反复出现的,可见它们组成了上海都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西西笔下的上海却没有任何一个这些场景:“店铺永远是一个样子,只有一、二间店铺一年中才有些微的变化”,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完全看不出上海的繁华,这个平民化的上海与《候鸟》的叙述角度密切相关,这种视觉是张爱玲和白先勇的香港传奇所没有用过的。事实上,在香港人的记忆中,香港才不是张爱玲和白先勇描写得那么糜烂,一直以来,香港的贫富悬殊是非常严重的,贫者的数目远远超过富者,尤其在上世纪70、80年代之前,香港平民百姓很多住在环境恶劣的“天棚”。平常的日子无肉可吃,也无新衣可穿,父母赚钱养家,年长的孩子负责弟妹的起居,最大的已经打工或学徒去帮补家计,孩子就是这样拉扯着长大,哪有心情和时间像葛薇龙去想堕落?一块糖、一片肉就足以让他们兴奋老半天,西西笔下的林素素,才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提到上海作家的“亭子间”生活,他们活在“象牙塔”一类封闭的空间,与外界没有接触,他们对外界的认识和接触在于“想象”,而不是实质上的交流,因此,考察上海作家的小说,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主人公生活在象征意义上的“亭子间”,与外界的接触几近于零。张爱玲的小说就特别喜欢写一座房子发生的事,所有事件都压缩在这栋建筑中发生,而主角也没有“其它人”与她交流沟通,《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主要在姑母梁太太的家活动,没有“洋房”以外的朋友,父母远在上海,在开头略略交代就没有再出现,仿佛跟薇龙也没有什么关系。白先勇的《香港1960》就更为极端:小说是余丽卿的“意识流”,她根本就没有踏出卧室一步,与世隔绝得让人窒息。然而,西西的上海却不是这么一个“孤岛”般的生存环境。素素的生活空间是开放的,从上海到香港也是如此,在上海,她与叔父一家和姑母交往频繁,而到了香港后,她也有了一班朋友,她一家与校长也有不少的接触,作品中洋溢着浓厚的“人情味”,这是张爱玲和白先勇所没有的,素素到香港后,经济拮据,交不起学费和杂费。假如是张爱玲的话,这个情节已经可以借题发挥到半篇小说,以借钱失败来强调人的势利和冷漠,换作是白先勇,大概就会加上他“没落贵族”的多愁善感,慨叹今非昔比,像西西这般朴实道来,实在是他们没有想象过的。由此可见,西西写的不是典型的上海,而是香港的成功传奇――香港人刻苦耐劳,确信未来会更好,团结一致地为创造更好的香港而努力。如果《夜上海》是上海的主题曲,那么香港的主题曲就是《狮子山下》:“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 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作为香港人的故事,《候鸟》以一种似乎并未完成的结局成全了一个开放的空间,让香港以自身的传奇继续完成西西的寓言,迁徙可以是地域上,可以是心理上,更可以是处境上,由沪到港,本身已是处境的迁徙,上海代表香港的繁荣,香港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盛极而衰,在金融风暴下、“非典”爆发后,香港都曾经受到重大打击,面临危机,情况有如林家由沪到港的过程,然而香港人每次都能迅速地在“危”中发现“机”,即便未能迅速恢复,但至少能在另一个范畴“重新来过”,西西的《候鸟》,实际上是有关香港处境循环的城市寓言。
如果张爱玲因香港而觉得自己“到底是上海人”,那么白先勇则于香港“蓦然回首”自己的台北身份,而西西是以上海来映衬“我城”,为上海、台北、香港的“三城记”画上一个圆――毕竟,他们所身处的“不光是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还是一种植根于大都会的都市文化感性”[19],一处不同时代的城市寓言和身份记忆。
注释:
[1]梁秉钧:《书与城市代序》,香港香江出版社,1985年版
[2]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3]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典藏全集短篇小说卷一》,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29-130页。
[4]施叔青:《寂寞云园》,广东: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5]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89-90页。
[6]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第143页。
[7]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第177页。
[8]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四卷》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166页。
[9]白先勇:《上海童年》,《白先勇文集第四卷》广东: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10]白先勇:《香港1960》,《白先勇文集第一卷》,广东: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
[11]白先勇:《香港1960》,第227页。
[12]白先勇:《明星咖啡馆》,《白先勇文集第四卷》广东: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13]白先勇:《香港1960》,第224页。
[14]白先勇:《香港1960》,第231页。
[15]白先勇:《香港1960》,第228页。
[16]白先勇:《香港1960》,第228页。
[17]白先勇:《上海童年》,第166页。
[18]西西:《候鸟》,台湾:洪范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