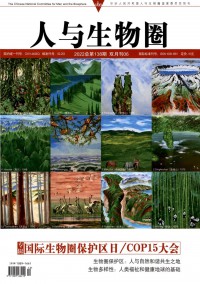柏拉图的永恒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柏拉图的永恒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柏拉图的永恒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10
尼采将查拉图斯特拉第一次下山时的情形比喻为即将溢出的杯子,而这一时刻即是查拉图斯特拉人形与神形的临界。这可以说是尼采精心设计的沙漏,因为根据权力意志,灵魂与肉体(生命)以一种内在的抽象形式往返于“高山”与“深渊”之间,“重力之神”在这一系统中彻底失效。亚里士多德以限制——有限——可分割——存在建立了存在物的单向“分聚”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成物处于存在物与非存在物之间,处于中间的存在物必然有一个终结,并且可以逆转,也就是这一个生成,那一个消灭,一个东西只有通过最初的东西才能生成,所以它不是永恒的。如果不能期求达到某一界限,人就不会有所作为,在世界上就没有理智这个东西,凡是有理智的东西,永远是有所为而为。所有的东西就是界限,所有目的就是界限。(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苗立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4-35.),相反,尼采将任何一个存在物存在的本身纳入了权力意志的范畴,存在者通过其最初形式的重新生成构成了永恒返复的条件。与其说权力意志与永恒返复的结合是颠覆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原子论的一种结果,毋宁说是一种必然的原因。海德格尔将二者的结合称之为“最艰难的思想”和“观察的顶峰”,“如果谁没有把永恒轮回的思想与强力意志联系起来,把前者思考为真正的要在哲学上思考的东西,那么他也就不能充分理解强力意志学说的形而上学内涵的全部意义。”[1]
一、超越与被超越
查拉图斯特拉下山的原因在于对人类的爱,然而众所周知,尼采撒谎的本领不在柏拉图之下
从根本上讲,尼采与柏拉图一样深刻地看到:真理对个人及共同体的生命来说都是致命的,因此必须用谎言掩盖起来。因此,正如柏拉图强调一个完美的城邦需要“高贵的谎言”一样,尼采也认为一种健康的生命需要希腊悲剧这样高贵的艺术。(参见: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5.),我们完全可以将此时的查拉图斯特拉当作尼采的雅努斯面孔,譬如尼采一方面如康德、黑格尔等传统哲学家一样沉思,将宗教界定为哲学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又如迷狂的政治哲学试验者一般,将“未来哲学”、“大政治”等统统设定为“未来宗教”的元素。我们可以大胆地将潜藏在尼采隐微术面具之内在矛盾性发展为一种内在的超越性,查拉图斯特拉对于人类的爱其实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类最致命的毒药。尼采为人类的前路预设了两个方向,亦即将人类按未来视角划分为两类。一类人最终能够在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的鸿沟之间建立桥梁,在伟大的“正午时刻”最终实现超人超人是尼采对未来人的设计。他部分是诗人,部分是哲学家,部分是圣人。他是诗人因为他是创造性的,但他高于当今的诗人,尼采批评后者撒谎(他们歪曲、篡改无意义的既成事物)、不能创造新价值而毋宁说充当传统道德的奴仆,超人将创造新价值并且在这方面将类似于传统哲学家,但他的创造将是自我意识的创造。最后,超人将类似于圣人,因为他的灵魂将包容基督教赋予人的全部深度。超人将是具有基督灵魂的凯撒。(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下)[M].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974.);第二类人在进路中逐渐衍变为消解了一切内在矛盾的人类形态,随着矛盾与冲突的彻底平息,人类本身也滞于一种归寂的、固化的、腐朽的形式,这就是尼采所谓的“再也无法鄙视自己的最可鄙的”
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对末人的讽刺表达了对“最大上限的最大幸福”、“兄弟情谊”、“人人平等”等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及社会主义口号的讽刺。(参见:彼珀.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义疏[M].李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69-73.)末人形象。末人是必然会被超越的,于是“超人”与末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就此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逻辑:查拉图斯特拉本身并不是“超人”,而是超人的导师、教人超人之人,牧羊人所最为关注的对象必然是羊群,而人类只有一部分可以成人超人(亦即超越了另一部分即将成为末人之人),因此,查拉图斯特拉下山的目的是出于可能超越之人类而非所有的人类。
柏拉图的永恒范文第2篇
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美学思想,虽然“同我们的观点相距很远,但是,他的美学观点同我们的美学观点毕竟存在着有益的和重要的联系。柏拉图没有编纂出一个美学问题的系统汇编和基本原理,然而在他的著作中,他涉及了美学的全部问题。总而言之,柏拉图“美是什么”的严肃提问和“美是难的”的庄严回答,为西方美学规定了一种先在范式的逻辑:美学以回答“美是什么”为宗旨,开启了西方美学史对美的本体的探索和美的本质的追问的艰难历程,可谓执中西美学之牛耳。如果说两千年来的西方美学就是不断重答柏拉图之问的历史,似乎也不为过。
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借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的一系列对话,提出并阐释论证了“美是什么”这一关于美的本质的命题。柏拉图从对各种具体审美实践现象的批判切入,经过精致的类比论证,提出了“什么是美”就是“美是什么”的著名论断,而且还通过试探性的诘难式的讨论方式对美是“有用的”“恰当”“有益的”“视觉和听觉产生的”等一系列概念进行了阐释和论证,最后得出只有“美本身把它的特质传给一件东西,才使那件东西成其为美”的形而上的结论。柏拉图提出并论证“美是什么”的逻辑过程是:“在一个讨论会里,我指责某些东西丑,赞扬某些东西美”。于是引出“你怎样才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你能替美下一个定义么?”的美本质论问题。“有正义的人之所以是有正义的……是由于正义。”“有学问的人之所以有学问,是由于学问;一切善的东西之所以善,是由于善”。 因此,“美的东西之所以美……是由于美”。进而推论出“美即美本身”或“美本身即美”的论断。
柏拉图提出“美是什么”的问题是源于对“指责某些东西丑,赞扬某些东西美”的具体的审美实践和美的现象的。就是说,他的美本质论的提出完全不是臆想出来的,更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其现实根基和历史意义的。这充分证实美的现象的客观存在和审美实践的现实性。即使是在他对“美是什么”的推演论证过程中一味地无视甚至否定审美实践和美的现象的存在意义而狭隘地从纯粹理性的抽象思辨层面进行逻辑求证的现象中,依然可以看出柏拉图没有否定审美实践和美的现象,只是从反面以一种更加曲折隐晦的方式对其予以承认和肯定。因为肯定不只是否定的对象,更是其得以存在和运演的根基。柏拉图美本质论的诞生是与古希腊崇尚理性,追求真知的社会人文背景偶合的。它的提出标志着人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开辟了新的知识领域,尽管论证的过程、方法还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不科学甚至是错误之处。而在阐述“美是什么”这一命题的过程中,柏拉图展示了自己对“美”的特殊理解,构筑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理式”是柏拉图整个美学思想大厦的根本支柱,要进入这座辉煌耀目的美学宫殿,我们就有必要开启“理式”的千寻铁锁。
鲍桑葵在《美学史》中概括出古希腊美学的三条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和审美原则。理性精神与道德实践相结合是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理式(ideal)的提出是对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原则的绝对化和道德主义原则的形而上学化。从寻求定义到寻求普遍的本质,从寻求各种德行的特殊本质到一切事物的共同本质,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经过柏拉图向这两个方向扩展,最后都在“理式”这个核心概念上着陆。
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十中提出:“我们经常用一个理式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现实世界中的每一类事物,都有一个相应的理式,譬如,床有床的理式,桌有桌的理式。各种理式就组成了理式世界。虽然“理式”并非柏拉图的首创,在当时的古希腊已是一个日常词语,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把它作为“种”“属”的意义来使用。“种”“属”是人作为主体对客体进行抽象的产物,也就是哲学上的“共相”(或“普遍”“一般”),与“殊相”( 或“特殊”“个别”) 相对应。但正如黑格尔所说:“柏拉图是第一个对哲学研究提出更深刻的要求的人,他要求哲学对于对象(事物)应该认识的不是他们的特殊性而是它们的普遍性,它们的类性,它们的自在自为的本体。”柏拉图赋予“理式”以超验的、永恒的、派生万物的范型的特性,“工匠制造每一件用具,床,桌,或是其他东西,都各按照那件用具的理式来制造”。而床与桌的理式本身, 并非工匠所造, 是宇宙中永恒、普遍的法则。作为万物之“共相”:理式是原因,它是事物的模型,其构造具有永恒的性质。对实物来说,理念乃是“原型”、根据、范本。因此,可感觉的事物乃是超感觉的理念的影像。
即是说,理式是“一种派生世界万物的客观精神实体,即共相模式和理性范型”。柏拉图理式论的提出是有其理论渊源的。他对德谟克利特的反映论和普罗泰哥拉的“知识即知觉”的感觉论表示怀疑,而求助于巴门尼德的“存在”:变动不居、捉摸不定的世界万物即非存在之外的本源的、纯然的、恒定的世界,借助于苏格拉底的知识产生于概念的思想,创立了他的唯心主义的理式论。而理式论的核心就是要人爱理性,成为理性的人。在柏拉图看来,人的本质是分裂的,主要表现为人的灵魂与肉体、理性和欲望、人性和神性的矛盾和二元对立。灵魂的本质是自动的、永生的、不朽的。他力图证明,人之为人根植于生命内部的理性,理性是人的故里。人的本质就是追求理性、爱理性,就是向理性的生成,最终就是要人作理性的人――理想国中的合格的公民。做理性的人,就是要靠理智去获得知识。但理式世界不同于可感的现象世界,知觉不包含理式,人就不能在知觉的内容中去人是理式。但知觉可以给我们以暗示,灵魂从而可以回忆起理式,获得对理式的知识,柏拉图坚信灵魂不朽。
柏拉图对美的绝对性可谓情有独钟,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终极意义和普遍意义的美本身。但后来,他意识到:美的事物虽斑驳陆离、千姿百态,而万变不离其宗,美的本质只有一个,并且美的本质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有机统一体。美不是具有美的属性的美的事物,而是超出美的事物之上的一种东西。这些流行的美的概念,只抓住美的本质的某一方面、某一因素、某一层次,但是进一步推演下去,普遍适应性与真理性的不足,概念的单一性、片面性就暴露出来,终被否定。但拨乱却未反正,最后只好宣布:“美是难的”。
古希腊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在现象千变万化的背后应如何思考统一的、永恒不变的存在”,许多哲人也就普遍相信永恒绝对的本体美是存在的。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哲学家们都在执著地探寻着美的本体,除亚里士多德较为重视艺术理论外,几乎所有美学家的兴趣与成就都集中美的本体理论上。具体的美的事物又是何以为美的?柏拉图在其具有哲学高度的理式世界统摄现实世界宇宙观的规定下,从上到下,演绎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美本身”概念,对此做出了回答。他在思想日趋成熟的学园时期的著作《斐德若篇》中提出:如果在美自身之外还有美的事物,那么它之所以美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分有了美本身。
现实世界中的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分有了“美本身”。具体的美的事物不是真实的、绝对的,是“时而生,时而灭的”,而“美本身”却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这种“美本身”即美的理式。相应于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理式,美的事物也有统摄杂多的美的理式。在柏拉图看来,现实事物的美的形成过程,是对理式的分有过程,是天国之美、彼岸之美向人间由高到低,从学问的学问、学问知识、行为制度、所有形体,到两个形体、单个形体,逐渐流动、扩展的过程,而对美的把握与观照则要由高到低,从单个美的形体开始,依次经过两个美的形体、全体美的形体、美的行为制度,最终“彻悟美的本体”,“沿波讨源”,理式之美也就“虽幽必现”。 这一概念的提出,把美的探讨从感性领域推进到概念和超验领域,标志着美学史上新的里程碑――本体论美学的萌生。
柏拉图的永恒范文第3篇
话说老师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离开了雅典,开始了长达10年(或许是12年)的漫游,先后游历了小亚细亚、埃及、昔兰尼(今利比亚)、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途中柏拉图接触了多位数学家,并亲自钻研了数学。返回雅典之后,柏拉图创办了一所颇似现代私立大学的学园(Academy,这个词现在的意思是科学院或高等学府)。学园里有教室、饭厅、礼堂、花园和宿舍,柏拉图自任园(校)长,他和他的助手们讲授各门课程。除了几次应邀赴西西里讲学以外,他在学园里度过了生命的后40年,而学园本身则奇迹般地存在了九百年,比剑桥大学还要悠久100年。
作为大哲学家,柏拉图对欧洲的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一生共撰写了36本著作,大部分用对话的形式写成。内容主要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也有的涉及形而上学和神学。例如,在《国家篇》里他提出,所有的人,不论男女,都应该有机会展示才能,进入管理机构。在《会饮篇》里这位终生未娶的智者也谈到了,“是从灵魂出发,达到渴求的善,对象是永恒的美。”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爱一个美人,实际上是通过美人的身体和后嗣,求得生命的不朽。
虽然柏拉图本人并没有在数学研究方面作出特别突出的贡献(有人将分析法和归谬法归功于他),却是那个时代希腊数学活动的中心,大多数重要的数学成就均由他的弟子取得。例如,一般整数的平方根或高次方根的无理性研究(包括由无理数的发现导致的第一次数学危机的解脱),正8面体和正20面体的构造,圆锥曲线和穷竭法的发明(前者的发明是为了解决倍立方体问题),等等。甚至连大数学家欧几里得也来阿卡德米攻读几何学,这一切使得柏拉图及其学园赢得了“数学家的缔造者”的美名。
对数学哲学的探究,也起始于柏拉图。在他看来,数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理念世界中永恒不变的关系,而不是感觉的物质世界的变化无常。他不仅把数学概念和现实中相应的实体区分开来,也把它和在讨论中用以代表它们的几何图形严格区分。举例来说,三角形的理念是唯一的,但存在许多三角形,也存在相应于这些三角形的各种不完善的摹本,即具有各种三角形形状的现实物体。这样一来,就把起始于毕达哥拉斯的对数学概念的抽象化定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影响的无疑要数《理想国》了。这部书由10篇对话组成,核心部分勾勒出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哲学。其中第6篇谈及数学假设和证明。他写到,“研究几何、算术这类学问的人,首先要假定奇数、偶数、三种类型的角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已知的。……从已知的假设出发,以前后一致的方式向下推,直至得到所要的结论。”由此可见,演绎推理在学园里已经盛行。柏拉图还严格把数学作图工具限制为直尺和圆规,这对于后来欧几里得几何公理体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柏拉图的永恒范文第4篇
关键词:奥古斯丁;美学;柏拉图主义;“反”艺术
中图分类号:J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4-0114-01
奥古斯丁是中世纪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是西方基督教美学的创立者。①由于他人生历程的复杂性,导致了他思想在不断地转变和发展,其中在其艺术观、美学观的转变和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的看见时代思想和不同流派的痕迹。奥古斯丁先后接受了摩尼教,柏拉图主义,最后皈依基督教,每一种思想都在他的美学历程上留下了痕迹,并且被他吸收到了以后的基督教美学体系之中。虽然奥古斯丁的艺术观是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中的,但是最终他的对于艺术评价的态度上是停留在“反”艺术上。
奥古斯丁生活于公元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前半叶,正是古代社会向中世纪转型的时期,此时基督教虽已被确立为国教,但是由于理论还不成熟,尚未站稳脚跟,其他的一些神秘主义宗教也在大肆的流行,奥古斯丁正是在这时信仰了摩尼教。这种宗教文化虽与基督教文化大相径庭,但是奥古斯丁并不认为它全部是糟粕,而是在吸收的同时进行自己哲学的思考,并且还写了一部著作《美与适宜》来阐述美的问题。此时的他沉醉于物质美的层次,虽然奥古斯丁将自己关注的对象停留在物质美,但是他已经开始对美的本体和本质进行了自己的探讨,这正是古希腊的美学思想。在这里,其注重的是从内在来阐释美,而不是从外部来寻找美的本源。
后来,奥古斯丁脱离摩尼教改信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是众多流派中对基督教影响最大的。他将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中的“理念说”、“灵魂论”、“流溢说”等思想稍加改造借鉴到自己的基督教神学体系中,为基督教所服务。柏拉图哲学体系集中探讨了与不完美现实世界相对而言的绝对永恒的“理念”。柏拉图哲学认为人分为“聪明”和“愚笨”两种,不同的认识能力有着不同的认识对象,不同的认识对象必然要求不同的认识能力。在这两种人所代表的感觉和理智两种能力背后也必然指向着两种不同的存在,一类是“理念”,另一类是和它们同名的具体事物,二者之间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是理智的对象,而后者则是感觉的对象。前者是单一存在而不是组合而成的永恒不变,后者则是由组合而成不是单一的不断变化。“理念”虽然无数,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某种秩序,最高的理念是“善”,它是认识和真理的源泉,各种“理念”在“善”的理念指导之下,形成了一个有序的“理念”的世界,“善”也就成了其他“理念”的规则。后来新柏拉图主义将“善”演化为“太一”,并认为它处于一切范畴化的语言和思想之外。奥古斯丁看到了这种“理念”和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永恒存在、不变的,因此,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进行了改变,上帝是通过永恒不变的“理念”来创造可感、可知的世界。柏拉图主义“理念说”中的客观唯心主义被奥古斯丁的主观主义思想所取代,由以前的独立存在变成了基督教神学体系的一部分,成为了依附上帝而存在的造物模式。
奥古斯丁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歌颂上帝和为教会服务。以奥古斯丁对于文学的评价为例,“文学是为了教会神学服务的,一切美的文字和话语都是为了歌颂真善美的统一体——上帝的”。奥古斯丁所接受的柏拉图主义中有一个关于绘画的理论。柏拉图以床为例,认为床有三种,第一个是床之所以为床的那个“理式”,其次是木匠以床的“理式”为标准创作出来的个别的床,三是画家临摹个别床的样子所画的床。第一种床的“理式”是永恒不变的,床的本体存在,他存在于上帝那里,是上帝的“真”。木匠所创作的床虽然是按照上帝床的“理式”进行的创作,但是由于受到物质材料和思想的偏颇必然会对那种永恒不变的“理式”进行改变,也就是一个个体。此床并不一定适合彼床,它已经缺失了床的“理式”的永恒性和普遍性。因此,木匠所创作的床只是一个床理式的摹本。而画家所画的床虽然是对木匠所创作床的本真的还原,但是由于所绘角度和方向的不同,导致了画面和实体的不同,因此,画家所画的床成了摹本的摹本,和真实的世界隔着三层。柏拉图的三层世界:“理式世界、感性的现实世界、艺术的世界”理论的区分,使得“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的信条被打破,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都是对于“理式世界”的模仿,“艺术世界”依附于“理式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存在,因此,“艺术世界”也就存在了更多的不真实,这和上帝所代表的“真善美”大相径庭,艺术的不真实也就是对“真善美”的破坏。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奥古斯丁后期对于艺术价值的评价。
在奥古斯丁后期,宗教意识支配了他的所有的思想,包括对于艺术的评价。奥古斯丁从“艺术服务于宗教”到“反”艺术思想,所有的一切都是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痴狂。奥古斯丁认为戏剧艺术完全就是过眼云烟,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可以留存下来影响人们对于“理式世界”的认识和理解。音乐则会使人们沉溺于自身的享乐而忽略了心灵的思考。
奥古斯丁对于艺术的声讨源于以下几个原因:一、艺术亵渎了神灵,破坏了神的“真善美”的统一体的完美性。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有很多对于神的描写,并且众多的神都是各司其职,有自己的管辖领域,同时这些神都有缺点,有的是沉迷于美色,有的是妒忌,有的是狂妄自大等等,神成了人们超人形象的化身。但是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唯一的真神,是“真善美”的统一体,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化身,没有任何的缺点的存在。因此,奥古斯丁认为古希腊罗马神话中,众多神的存在是对于上帝这个唯一真神的不恭,而那些神身上存在的缺点只可能存在于人类身上,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真善美”的统一体,不可能存在自身的缺点。那些神话是对于人类自身缺点的掩饰,这是对于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亵渎。二、艺术容易引起感性的欲望,从而破坏人类本身存在的“理式”和道德观念,艺术中包含的七情六欲侵蚀了人们的灵魂。以戏剧为例,悲剧是以虚构的故事来唤起人们内心的同情来达到自己艺术的成就,而这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虚假而不是真实,也就是说悲剧是在用一个虚假的故事来骗取人们的同情心,是不“真”的行为。而喜剧则是以一个小人物猥琐的行为和事迹来博取观众的开心,这种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是不“善”的行为。戏剧一方面燃起了人们欲望的篝火,一方面虚假的骗取人们的同情,这是不“美”的。这与基督教所要求的人们的行为以及上帝的“真善美”是相悖的。三、艺术是虚假的存在和存在的虚假。首先,本身艺术就是对于感性的现实世界的模仿,而这个现实世界又是对于上帝所代表的“理性世界”的模仿,也就是说艺术和上帝之间隔着三层,本身就是虚假的。不管是绘画还是诗歌或者其他艺术都是对于“理式世界”的一个不“真”的表现,同时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有混杂了很多创作者本身的思想和情感,或为达到艺术的目的进行虚假的构造,这些都是与基督教所倡导的思想不符的。
在奥古斯丁眼里,艺术要想存在于现实世界必须克服他们自身所存在的缺点,并且将基督教教义作为艺术创作的准绳。我们可以看出,奥古斯丁摒弃的并不是整个艺术,而是那些对于“真善美”进行破坏的艺术。艺术可以通过自身的功用来为基督教服务。在对艺术和宗教的思考之上,奥古斯丁吸收了柏拉图主义的很多认识,最终确立了自己对于艺术价值和评价的观点。其“反”艺术思想不仅深深地影响着其以后基督教艺术的发展,同时对于后世的很多思想的诞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严家强.从奥古斯丁宗教哲学思想看永恒的现实性[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
[2]胡万年.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的辨正[J].理论界,2009,(12).
[3]徐彦婷.用艺术来解释奥古斯丁的困惑[J].艺术研究,2009,(03).
柏拉图的永恒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柏拉图假说;二元价值;解构;超越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有一个著名的假说:最早时人是双性同体的……后来,神把人从中间劈开,就有了男人和女人。于是每个人诞生世间都有一种神秘的渴望,希望找到未被神分开之前,那个最相契的另一半。这一假说在柏拉图“理式”的最高范畴体系中,与人最接近“理式”的神性部分――精神、心灵相结合,后被解释为“柏拉图式恋爱”。
古今具有开创性的大哲学家都意识到,人类除了暂时的、局部的苦闷,还有诸多“永恒的苦闷”,来自外在的未知与人自身的不完整性,无法消除、永劫回归,而“柏拉图的假说”正属其中之一。
时间进入当代,米兰•昆德拉率先对“柏拉图女人”提出挑战。在他所追求的小说“终极悖论”“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从形而上的层面入手,以充分自觉的姿态,怀疑一切、拷问一切,解构传统“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揭示世界混淆、模棱的虚无。作为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先驱,米兰•昆德拉认为:“既然上帝已去,人又不再是主人,那么究竟谁是主人呢?这颗行星正在没有任何主人的情况下穿过虚空。”[1]42为了探索“所有的可能性”和个人化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托马斯一方面对“柏拉图女人”充满期待,另一方面无休止地猎艳,他要背叛爱情的“非如此不可”。包括最后对“柏拉图女人”的摈弃,实际上是托马斯对“非如此不可”本身的再次背叛。在这一摈弃与背叛中,现实来到台前――妻子特丽莎为此痛苦万分,为摆脱这一被动处境,使自己真正成为独立的灵肉合一的主体,实现爱情的纯粹和专一,她主动接近托马斯的情人,使自己与托马斯共同面对其情人而与托马斯成为一体;为了检验对灵与肉分离的怀疑,特丽莎试着与一个陌生的工程师,结论使她恐惧:没有爱情同样可以,人的灵与肉竟然可以分离。理想的爱情被瓦解,她由痛苦堕入比托马斯还要矛盾的空虚。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成功实践了他的否定美学,摆脱、破坏“非此即彼”“善恶分明”的二元价值公式,毁掉确定性,把一切肯定变换成疑问,与所谓必然性、终极价值背道而驰,“被迫不是面对单一的绝对真理,而是面对种种相互矛盾的真理混乱状态”[1]5,他以探究性而非道德性立场反叛“永恒的苦闷”,善与恶、灵与肉、美与丑、轻与重、性与政治……二元对立界限被取消,一切还原到存在本身,描绘世界的本来面目,即谜和悖论,[2]深刻的怀疑主义浸透其作品和思想。可是当怀疑和否定走到这个世界边缘时,我们却发现最终一切都是虚无。最后作者也不能揭示托马斯和特丽莎在轻与重、灵与肉的无所归依中走向何处,他制造了一场车祸,让二人忽然死去。最终,怀疑和虚无成为一场大而无当的宏大叙事,一切都失去归属、失去根基、包括情感、价值、永恒……将背叛和藐视的对象、解构以后的碎片、将“柏拉图女人”一起留在了荒原上,残酷、真切而冷漠。既然一切都破碎,就没有什么值得注意和关心的了。
2009年央视播出了一部由九年编剧、余明生导演、焦恩俊、林湘萍主演的电视剧《宝莲灯前传》,“柏拉图女人”再次出现,该剧在昆德拉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对其造就的解构、终极悖论后现代传统作出了新的质疑与反驳,以大胆再造的神话爱情故事打动了许多人。另一个“柏拉图女人”之外的女人――寸心来到观众的视野中。特丽莎让人同情、给人冷静的智性的启迪,寸心则让人振奋、感动、泪如泉涌。这位让她的丈夫二郎神杨戬郁闷发疯、万般无聊却欲罢不能的女子再也无法被虚无地解构,无法被柏拉图式的幻想掩盖,她浓墨重彩、如火如荼。
和托马斯的假想不同,初次驾云的杨戬在空中迷失方向,竟然见到一位在月中跳舞的仙子――嫦娥,从此再也不能忘怀。可是,和托马斯一样,命运将另一个女人送到了他的身边,就如托马斯出于对特丽莎的生病的同情,杨戬出于对寸心搭救过他的报恩,很负责地将妻子的位置赐给了她。寸心太爱二郎,欣然地屈辱地接受了这个职位,但是从此嫦娥,这个“柏拉图女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寸心的头顶。二郎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被天上的月亮吸引,每个人都看月亮,可是寸心觉得杨戬看的就是不一样。她在婚姻中感受到的只是责任、没有爱情。但是和特丽莎的委曲无望、暧昧惶惑不一样,仿佛要刻意地和昆德拉作对,理想主义者寸心不允许混乱、不允许荒诞、不允许“可能性”,一定要在终极悖反的世界里挣出个所以然,不是真就是假、不是轻就是重……为了争取二郎全心的爱,寸心采用了所有的办法,愚蠢的、荒谬的无所不用。一哭二闹砸东西、隔断二郎与妹妹、兄弟、师父、哮天犬之间的联系,追究与嫦娥有关的所有蛛丝马迹、发展到将二郎领养的孩子当作其私生子扔掉,最后上天杀嫦娥。和假想敌作战的傻寸心,摧毁了昆德拉后现代的模棱两可与混乱。宁可决绝去把这种表面、勉强、虚假的关系毁灭,用两败俱伤的方式把一切打回原形。全心的爱或者一点也不爱。只要最好的,否则就不!一点也不爱比仿佛有点爱更让人轻松,就像真的比假的更让人信任。违背了后现代真理的寸心让二郎忍无可忍,终于发展为中国式离婚,以昆德拉式的悖反而告终。
然而,《宝莲灯前传》并未就此陷入昆德拉虚无的怪圈,而是展开了宝贵的下一步。在西海的岸边,那个曾经第一次遇见二郎的地点,已解除婚约的孤独的寸心在沉思。正如老子所言:“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当幻象如镜花水月般失去、消失,欲望被拆去了婚姻的平台和蒙蔽,一些纯真、美好的点滴反而晶莹地显露出来……寸心透过、摈弃求不得的欲念,开始远距离地审视二郎本身,体会到二郎心中超越于她的大爱。当二郎为反抗陈腐天条被天庭质问时,寸心出现在南天门,帮二郎顶下所有的罪过,让他继续担任司法天神,继续为大家造福。寸心受到责罚,削去公主称号,永世不得离开西海。西海诀别让许多人难以忘怀,已经不奢望能够再次感受二郎怀抱温暖的寸心再次和二郎拥抱,“有些事情,错过了,就不再有弥补的机会。我现在只是希望,能为你多做一些事情。”“保住你司法天神的位置,把你的爱,你的遗憾,都留给大家吧。”寸心抽身离去,走向西海……寸心,在你的手指从他的手中抽出的一瞬,你有没有看见二郎那茫然不舍的空握,寸心,他爱你!不知道从前的一千年他是否爱你,但是,在这一刻,他爱你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无题》)错过的已经错过,即使是西海不舍的离别也一样可以体验到那种莫名地将两人越拉越远、往而不返的力量,是什么呢?是嫦娥?是往昔的时光?是彻悟后的通达还是冷漠?有所求却求不得,是不是有什么超过我们的事物在左右我们?来自世界还是来自内心?为什么会如此隐匿而又如此巨大,非有非无、不增不减,仿佛命中注定的无可奈何,却又似乎从来就永恒不灭。给人类的情感下定义从来就是虚幻难凭的。面对未知的力量,即便无可奈何,即便无效,寸心体现出的却是一种心灵悲壮的奋斗。那就是,在虚无的荒原上,在终极悖反的捉弄当中,在失意的被否定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坚持理想?
人生在世,总想追求一些完美的真正让自己满足的东西,而且觉得宇宙间应该有这种最完美的东西。这种事物越是高远、渺茫,就越容易引人追求和向往……以前寸心以为是二郎,是二郎对自己惟一的爱,她为此艰苦卓绝、不遗余力地奋斗过,可是越努力却越快速地陷入命运悬置的落网,最终失去了二郎。但是,即便意志无成,生命落空,对精神上和心目中最完美的理想的追求却依然存在。也许,它不仅仅是二郎或者从来就不是二郎,而是一种比二郎更高远的事物。“保住你司法天神的位置,把你的爱,你的遗憾,都留给大家吧。”是追求本身,是超越小我的更博大的爱。这份绝望中强自挣扎的苦心,立志更坚的追寻,已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情感,而成为一种高贵坚贞的德操!经过一种肃杀、凄凉、零落,所有的二元悖反都摆脱了,人生境界忽然升华了,对世界有了更超脱更高远的看法。回首寸心在婚姻中一系列偏激、不良的表现,也不再是真正的不堪与堕落,而只是人生歧路上的徘徊。即便求之难得,依然弃之不舍,这一精神上的飞动,让现实与未来之间蓦地有了一种回旋起舞的空灵之态,让心灵与他者、与未知、茫茫世事结合起来,没有在犹豫疑惑处戛然而止。
昆德拉的讨论止于怀疑与悬置,人物到最后常常成为与谁也不相干的局外人。个体的自由反叛走向极端的终点,最终陷入的是关于“自我”的确信。《宝莲灯前传》再次颠覆了这一“自我”的基点,较之昆德拉的个体性探索,较之特丽莎对托马斯个体小天地的执拗、二人对于被颠覆的亲情、世情的冷漠已经截然不同。对美好理想的追寻和生命无常的遗憾总是并存,终于得知为什么特丽莎让人同情、清醒,而寸心让人尊敬、落泪,只有关涉他人的永世忧伤才是仁慈的,只有在最孤绝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心灵升腾的自由才是尊贵的。面对永恒的苦闷,寸心用心灵的升华与超越,打破了昆德拉怀疑、悬置的世界。让轻与重、善与恶、高与低的二元价值在更高的意义上再次回归。
在这个多元文化和相对性的时代,一切意识形态,包括传统价值判断似乎都已失去了真理的垄断地位,遭到相对、解构的命运。如昆德拉所言,确信世上没有确信之事是奇妙欢悦的。[3]昆德拉的颠覆的确具有为一个时代代言的意义与智慧。可是我们即便知道了所有可能性也无法选择所有可能性,只能在我们可以做到的范围中作出选择。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类可能性”的检验,必然包含着作家本人的选择性意向,包含作者某种生发的道德前景。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仍然必须作出“非此即彼”“善恶分明”的价值判断。真与假的二元价值结构必然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破碎泛化、似是而非中有一个新的前进,即辨证扬弃二元中的另一元、心怀他者的美与道德自由的新突破。
[参考文献]
[1]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唐晓波,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2] [捷克]安托万•德•戈德马尔.米兰•昆德拉访谈录[M]//李亮,李艳.对话的灵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507.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