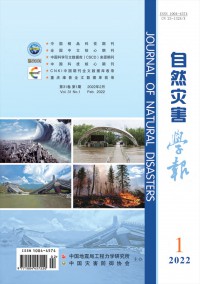雨天是放声哭泣的时间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雨天是放声哭泣的时间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雨天是放声哭泣的时间范文第1篇
看到这组日期,回忆便像潮水般涌上了心头,记得在外婆去世前的那天晚上,还沉溺在甜甜的睡梦中的我,被依稀的哭泣声所吵醒,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渐渐看清了,趴在我床头已经哭的泣不成声的女人,那便是——我的母亲,我被惊得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捧起母亲那张挂满泪水的脸,心疼的望向她那双因哭泣而充满了些许血丝的眼睛,问道,妈!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将头依偎到我的肩膀上,抱着我,默默地流着泪,我透过门缝看去,也只见父亲正踱着碎步在客厅里满是思绪的抽着烟,烟雾早已笼罩了他的脸庞,让人已浑然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那时的我似乎已经意识到了某件事情的发生,可还是不愿往那一面去想,最后,母亲终于哽咽着对我说,我刚刚接到你舅舅的电话他说…他说,你外婆由于手术失败已经走了……其实我已经听清母亲所说的话,可我还是不敢相信的问她,走了?什么走了?她去哪儿了?母亲终于再也忍不住的放声哭起来,走了,你外婆因为手术失败去世了,她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了!那时的我顿时像只被雷击中了的鸡,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当泪水也不知何时流下滴到了我的手上时,我才恢复了清醒的状态,确定这件事情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我低头看向哭得像孩子一样无助的母亲,更加心疼不已,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般往下掉,那时,心里除了有失去外婆的哀痛,也有了让我以后要保护妈妈,不再让她流泪的念头,将心比心啊…只想着妈妈没有了妈妈的疼爱,所以以后我要更爱她。因为过去的我是那么的不懂事,那么一味的自私,无论做什么事从来都不曾考虑她的感受,当我还沉静在这些思绪当中时,爸妈已经匆匆忙忙的准备出门前往医院去见外婆临终前的最后一眼了,我赶紧的光着脚丫,跑到他们的身边对他们说了,我也想要去见外婆的打算,可最终,他们并没有能够让我如愿,因为当时已经是深夜,而明天的我还要早起去上学。可谁又能知,那夜,我注定无眠。
天色终于渐渐亮了起来,我第一次觉得等待黑夜过去是如此的漫长!看着枕头上的大片泪迹,揉了揉哭肿了的眼睛,就赶紧上学去向老师请假,参加外婆的葬礼了…那天,天空中有些冷雨在飘飞,虽然天气不是很冷,但我却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凉意。妈妈已经没有了力气,在旁人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向着殡仪馆走去。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很吃力的往前走,但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尽头。我的泪水已经迷糊了我的眼睛,一脸茫然的在这条路上寻找着这最后的回忆,重温往日的亲情。当见到屏风后的外婆,一直静静的躺在那儿,知道她再也不能对着我微笑,再也不能在我耳边给我像小时候那样讲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的时候,一时间全身的所有悲伤情绪主宰了我,我终于放声痛哭了起来,曾一度有过认为哭得大声,躺在那儿的人就会回来的可笑念头。那一瞬,只觉得天昏地暗。
看着一点一点被推进那个火炉中将要承受剧烈疼痛的你,过去那一幕幕温馨的画面,就又如电影放映般映入我的眼帘,外婆,你知道吗?往日里,你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其实那是我雨天里的阳光;往日里,你的微笑洒在我的身上,其实那是我成功的力量;往日里,你那份豁达,其实那使我学会宽容……我不敢再往下想下去,我仰望着天,长长的两行泪,在我两腮滑落了。我知道此时分别就意味着永远的分开了,但我相信外婆对我的爱却永远都不会被这一层黄土所隔绝……
雨天是放声哭泣的时间范文第2篇
我的生活太正常。从来都是优等生,从小学到大学、MBA,然后顺理成章进一间国际知名机构做事――这样的顺当,连家人都感觉无惊亦无喜。
我想不出不快乐的理由,同样感觉不到快乐。那吉说,快乐是件深奥的事,是意外之喜。天上白白掉下来的,不曾花过半分力气的,一跤跌在青云里的,都是快乐。
然后,她盯住我额头,食指逼近:“如你,这样辛苦读书,获得文凭,是份内之事,当然无快乐可言。”
我笑,做势去咬竖在鼻前她的食指:“那你教我如何得到快乐?”
那吉是我女友。追她的时候费尽了周折,那时,我才顿悟,学业与情事相比,后者更为艰辛。大三那一年,我所有的心思全花在她身上,抗外敌,博芳心,一年下来整个人瘦掉5公斤。仿佛是某个下雨天,两人只有一把雨伞,撑开来,整个世界便只有我与她。飒飒的雨中,她注视我的眼睛也蒙了雾气,她的手抚过我的下巴,叹息:“你对我太好。”
我不太记得起是先握住她的手,还是先吻住她的嘴。四五年过去了,唯一清晰的记忆是她在我怀里用拳头轻捶我胸口,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平静?”
平静。真是平静。心跳不加速,呼吸不急促,甚至连吻都温和安静。
DAY说:“列详细的计划,经过百般迁就千思万想梦寐以求才到手的东西,因过程太艰涩,当然不会快乐。”
是不是替我感觉可悲――二十七八岁高职高薪高学历的男人,还得打电话到电台的热线向主持人取经。
DAY是本城某电台直播节目“对她说”的主持人,一个声音模糊年龄的女人。开始,我只是她的听众,每天听她安慰或痛斥打热线电话的观众。问题花样层出不穷,她的回答也无公式可循,有这样的一档节目,也算给我平淡的生活添多意外之喜。我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有打电话给她这一天,握着电话的手心居然会紧张得出汗。
DAY轻轻笑了一下:“你还在听吗?”
换只手握听筒,将手心的汗在身上抹干,我说:“在,我想知道,如何才能感到快乐?”
她又是一声细微的轻笑:“很容易――与一个危险的女人谈恋爱。”
周末,阳光不错。
我打电话约那吉一同去淘碟。
那吉的声音半睡半醒:“啊?哦,好,你来接我,半小时后。”
坐进车里,那吉一个哈欠连一个哈欠。我问她是否没睡够,她边用手掌捺下嘴里呼之欲出的又一个哈欠,边说:“昨天晚上加班一个通宵啦,最多睡了3小时。”
“那你为何还要陪我?”
那吉奇怪地看着我:“你是我男友啊,为何不陪你?”
红灯时,我伸头去吻她脸,她咭咭笑,躲闪到一边,指指车窗外相邻的车辆:“不要啦,会被别人看到。”
我看着她,脑中却不合时宜地响起DAY的声音。某次节目中,她感叹:“真是怕了你们,为何不懂得爱情最美丽之处是可以任性,来去自若,不受俗礼常理所拘,拒绝其他因素影响?”
我说:“吉,什么样的女人是危险的?”
那吉很认真地去想,掰着指头数给我看:“像张爱玲《红玫瑰白玫瑰》里的娇蕊,像《原罪》里的安茱丽亚・朱丽叶,像……”
她忽然打住话头,拉我的手,让我向车窗外看:“喏,那个女人,便是危险女人。”
一个白衣女人正旁若无人地横穿马路。我没有看清她的脸,只看到她耳边两枚巨大的白色圆形耳环灵活地随着她头的转动左甩右甩。
“她为何危险?”白衣女人的身影被车抛远后,我问那吉。
那吉边摇晃着趿着凉拖鞋的脚,闲闲地说:“看她的打扮就知,良家女人谁会将白衬衫的扣子松至,谁会戴那样夸张的耳环。”
晚上,我打电台的热线――
“你还记得我吗?那个不知道快乐的男人。”
“哦,你还没有去找危险女人吗?”
“没有。不过,今天我开车带女友外出时,看到一个危险的女人。”
“你怎么知道她危险?”
“我女友说的。她说,没有良家女人会将白衬衫的纽扣松至,会戴那样夸张的白色耳环。”
DAY愣了一下,肆意地笑了起来:“就这样吗?你与她搭话了吗?”
“没有,我有女朋友的,而且,我连她的脸都没有看清。”
“你打电话来想问我什么?”
“我,我买了《原罪》的DVD。我,我是说,如果我真遇上了一个危险的女人,却不想做对不住我女友的事情,怎么办?”
DAY笑:“到时候再说呗,没有发生的事情,想那样周全做什么?记住,时间总是会过的,到时不妥之事一定全部妥当。”
夜里做梦,梦里便是那个连面孔都没看清的白衣女郎,她的耳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她说:“有了我,你快乐吗?”
从梦中笑醒。那白衣女郎,居然是DAY的声音。
那吉拖我去登记结婚时,我有意外,却无喜――恋爱六七年,不需动脑也知结局一定是走入婚姻。电影里有过求婚的各种画面,多是男人求,女人应,男人坚定,女人惊喜。求婚时应该有香槟、玫瑰、指环、吻、音乐,甚至直升飞机、豪车、名宝,男人女人喜极而泣。我对我的婚姻发生做过种种设想,偏偏没有想到这一出:那吉所在的银行要盖楼,已婚部门经理可以享受百平方米以上的福利分房待遇。那吉通知我结婚时,像换算兑率似的不停算给我听,这套房如果按市场价会是多少万,虽然我已买房,但是,房子多一处不嫌多,转手卖掉的话,可以让我们提前七八年退休去某国某海滨或某农场闲逸百年……她说了太多太多,兴奋得声音都略略走调。
她说了半个小时,忽然停顿下来:“糟糕,我忘记很重要的事情!”
这话让我心一紧,以为她会问:“我忘记问你是不是愿意娶我。”谁知道她却说:“我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项目要开会研究,我去安排一下,你马上开车接我,去民政局的路这个时段怕会有堵车……”
在夏日滚烫的空气中两人开车向民政局赶。那吉一路上不停地催我开快点儿,我脚下的油门却越踩越轻。你们不会明白这种糟糕的感觉――不像去结婚登记,而是去参与某次减价大抢购。
那吉到登记处取表格,我看着表情麻木的登记人员、墙上明码标价的登记收费表,忽然有些心酸。走到门口吸烟,看到对门半掩的房门中写着“离婚处”3个大字时,忙将眼睛调转。走廊的尽头是一扇油漆斑驳的淡黄色木窗,一个女人站在阴影中吸烟。
我忘记去掸指间的烟灰,怔怔地看着她身上那片白。
她扔掉烟头。
她向我走来。
我的心陡然乱跳,脸上有了血液的温度。
“快来填表,我要在4点半之前赶回银行。”那吉的手将我拉回到登记处。
手被她拖动,身体被脚拖动。我回头看,只看到女人推开离婚处木门时的背影――白色无袖长衫,细小的镂空中隐约可见蜜色的皮肤,头发在脑后被一根碧玉簪固定,头两侧两串垂到肩头的红珊瑚耳环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摇摆。
“我结婚了。”
“好啊,恭喜你。”
“我在登记处看到了那个女人。”
“什么?”
“我上次在电话里和你讲过,那个白衣女郎,危险的女人。”
“你,认识她?”
“我没有看见她的脸,这次,她戴着一副鲜艳夸张的红珊瑚耳环,直觉告诉我,上次我看到的女人就是她。”
“你与她说话了没有?”
“没有。我只看到她的背影,她走进了离婚登记处。”
“你打电话来,想问我什么?”
“没有什么,只是,我结婚了……你以前说的,与危险女人恋爱,不可能再发生在我身上……我想知道……感到快乐,能不能通过另外的方式……”
“你在哭吗?”
“……”
我放下电话,关上收音机。
我的生活太正常。从来都是优等生,毕业后顺理成章进一间国际知名机构做事,毫无波折地娶回相处6年的恋人,加赚一套小型复式楼――这样的顺当,连家人和朋友都感觉无惊亦无喜。
我想不出不快乐的理由,但是,也同样感觉不到快乐。妻子说,快乐是件深奥的事,是意外之喜。天上白白掉下来的,不曾花过半分力气的,一跤跌在青云里的,都是快乐。
然后,她盯住我额头,食指逼近:“娶我几乎不花半分力气,还平白多了一幢房,天上白白掉下来这样省心省力的好太太,你还敢说自己不快乐?”
我笑,无声的笑从嘴角漫延成模糊的表情。
电台里,有男人在喋喋倾诉:“她总是希望我透明成一杯水,但是,我做不到,虽然我爱她,但是,总有些事情,是没有必要告诉她的吧……每次看她追询的眼睛,我都会心慌压抑……她说我不是一个好男人,至少,我不像她对我那样开诚布公……”
DAY说:“女人们常说这样的一句话:爱人就是脚上的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但是,作为鞋子本身,它没有义务告诉脚,之前有过多少双脚来试穿过,之前有过多少双手将它加工过。当你良心不安的时候,可以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世界上有那样多脚,每双鞋却只给一个人,对鞋子来说,它已做到最好!”
我将车里的电台换了频道,现在,我不能再听她在电波里说话,就像这席话,分明是她在宽慰我,她知道,有些事情,我是瞒着那吉的。
那日。我打去电话问她除却与危险女人恋爱之外还能不能有别的获得快乐的方式的那日,一个人啜泣挂掉电话关上收音机的那日,接到了她的电话。
她问我:“你现在说话方不方便?”
她的声音像熨斗,仅是一句话便将我心上郁闷的纹淡化。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是,我骗不过自己――那时,我比任何时候都心悸。
我说:“我很想见你。”
“那你接我下班,地址我告诉你。”
短头发的女人,随着我心跳的节奏坐到我身边。我不能判断她是不是那个危险女人,但是,她那袭白衣让我不能把持自己。
我去吻她脸,她将头调转了过去,嘴唇便在她发梢耳轮处停留。仿佛短短的头发扎进了眼睛,我忽然放声哭了起来。整个人伏在她膝上,像是童年搬家告别伙伴,像是丢失了最心爱的集邮册,毫无目的,只是哭,仿佛要等眼泪将过去的记忆冲远,只想哭到累,然后休息。
“希望,没有吓到你。”漫长的哭泣结束后,我低着头,不敢去看她的表情。
她用手仔细地将裙子扯平,慢吞吞地说:“你两次见到的女人都是我。戴白耳环走在马路上那天,是我刚离开前夫的家。他与一个女人在一起。”
“她,会比你更好吗?”我像十几岁的男童,幼稚地发问。
“她比我更危险。”她笑,“确切地说,她比我更新鲜。当苹果是禁果时,亚当认为它危险而诱人。可是,当危险的东西习以为常,他便不能再从苹果身上得到快乐了。在他郁郁寡欢的时候,出现了一只番茄――苹果已是普通水果,番茄此时成为禁果,食它,更危险。”
我辩解:“那吉从来都不是危险女人。”
“所有新鲜的,都是危险的。”她打断我,有些不耐烦,“你第二次见到我时,我与前夫办完离婚手续。”
“你很落寞,一个人到角落里吸烟。”我说。
“不,是他在离婚登记处泣不成声,我嫌烦,索性出去吸烟。”
我点一支烟,拧开电台,用音乐掩饰情绪:“他哭?怎么会?”
“他害怕,因为我虽不危险了,但是也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他害怕打破。而且,他后悔。人总是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充满向往与渴求,我不再属于他,于是,我在他心里重新变得新鲜、危险……”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说,一个男人一生多半会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他的白玫瑰,娶了红玫瑰的,那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而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我今天见到了“明月光”。她在书店签售她的书《对她说》。
我依然没有看清她的脸。
她低着头,两串黑珠子缀成的长耳环不停地晃动。她在一本本递到面前的书上龙飞凤舞地写自己的名字:DAY。
那吉推我:“发什么呆!”
我将她揽进怀中,手抚摸着她日渐隆起的肚子说:“这里挤,我们到楼上去。”
其实,我想问DAY一个问题――别误会,我已经不再去想快乐不快乐这个问题。
我是已婚男人,可以用一副过来人的姿态取笑开解患婚前恐惧症的同事,告诉他们,结婚的好处是自己可以变成女人眼中的危险男人,生活更多新鲜刺激。
我晚上不再听收音机,如果没有酒会,固定节目便是与妻子一起畅想我们的孩子会念什么样的小学,长成什么样子,遇上什么样的爱情……而且我现在挺快乐,特别是最近接到通知,调我去加拿大总部工作,可以携家属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