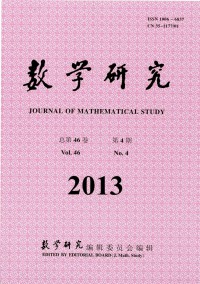零容忍纪录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零容忍纪录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零容忍纪录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独立纪录片;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社会透明程度的提高,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氛围正在形成。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整个社会对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可以容忍了。因此出现了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在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这种现状已经是不容置疑的现实。就属于影视艺术的独立纪录片来说,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许多怀有艺术理想的人在先锋艺术领域“独立和自由精神”的倡导下,自愿脱离公职,专注于自己的创作,成为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自由艺术家”或文化“盲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实现个人化的影像写作和表述的一种渴望。这是由早期独立纪录片的作者的特殊身份决定的,他们多少都曾与电视台有过某种工作或合作关系,但是在为电视台制作(纪录片)节目的过程中,他们感到了相当程度的束缚与制约。于是,独立创作纪录片成为他们实现艺术理想的最好选择。
独立纪录片是从“个人立场”出发,透视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生存诉求及其情感方式。它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和校正。他们的创作没有商业化和播出的压力,往往把镜头对准中国社会体制之外的边缘人,倾听他们的隐蔽心声与情感陈述,贯注着人道关怀精神和个性特征。尊重自由表达的权利,象征着个人化创作方式。独立纪录片创作者往往兼具导演和制片人双重的身份,一般不属于体制内。独立纪录片的作者挑战传统的表现手法和表达题材,想在平常中寻觅新奇。比如英未未的《盒子》,大胆的把镜头对准了一对女同性恋,观众对此充满好奇心,作者通过对内部的深入挖掘,使同性恋的成因呈现出完美的社会学意义。
我国现在的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属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生存在体制中有一种尴尬。中国大陆的独立纪录片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诞生:1988~1993年,主要有吴文光、温普林、蒋樾等人早期的“记录”行为,80年代末期,在北京出现了一个流浪的艺术家群体;1991年6月成立了“结构.浪潮.青年.电影小组”,即SWYC小组,并在12月举办了“北京新纪录片作品研讨会”。中国大陆的第一部独立纪录片是吴文光的《流浪北京》(1990),记录了五位自由艺术家80年代末在北京的一段生活。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以前的工作不同,但是他们的目的大致相似,即为了在北京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他们活在自己的梦想里面,在艺术的海洋里他们看到的都是阳光,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他们在生活的巨轮前无力的挣扎并最终选择了不同的生活。
发展与探寻:1993~1999年,1993年参加山形电影节后,大陆的独立纪录片作者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纪录片;1994年广电部下发通知,就一批导演私自参加鹿特丹电影节举办的中国电影专题展一事予以处罚,1994年多少有些孤寂与落寞,这年不甘寂寞的张元与段锦川合作拍摄了一部35毫米的胶片作品《广场》;1995年,蒋樾历经两年的《彼岸》拍完;1996年,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由文化交流公司出品;1998年,李红的《回到凤凰桥》(曾获1997年山形电影节“小川绅介奖”)被英国BBC公司以25000英镑的价格收购,这是大陆独立纪录片中首次被国外电视媒体购买的作品;1999年,由“疯狂英语”发明者李阳出资,张元创作完成《疯狂英语》,这是一部艺术水准和商业利益双赢的纪录片。
蓬勃兴盛:1999年以后。1999年,《老头》和《北京弹匠》双双获得日本山形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2000年2月,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雎安奇的作品《北京的风很大》获青年论坛单元大奖;2001年9月下旬,由北京实践社和《南方周末》报联合发起的首届民间独立映像展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此次映像展,堪称独立纪录片的一个狂欢式盛会,五十余部长期散居民间的独立纪录片作品同观众见面,实现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会师,在参与竞赛的纪录片中,杜海滨的《铁路沿线》因对铁路沿途流浪群体的平视与深入荣获最佳纪录片奖,英未未的《盒子》和朱传明的《群众演员》也以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受到了关注。
一、创作上自主意识加强
(一)主动参与
独立纪录片产生前片子大都是体制内的,专题的倾向比较大,在这里面的创作者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物质条件的完备,人们有了越来越多自主选择的权利,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将自己的声音记录下来,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在独立纪录片的创作中有很多的作者都没有受到过专业的训练。
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杨天乙的《老头》、朱传明的《北京弹匠》、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赵亮的《纸飞机》等等,这些纪录片在短短几年内不断涌现并在国内外名目繁多的纪录片奖项中得奖。其中有好多制作人都是第一次拍纪录片,而且不是专门的纪录片工作者。和1990年早期的“独立纪录片运动”不同的是,当时的纪录片工作者,无论是吴文光、段锦川还是蒋樾等人,大都有在电视台工作的背景,他们是苦于不能在传统体制内进行真实的表达,才选择了独立制片的道路。而当下年轻的纪录片创作者们则多半不在专业影视从业人员之列,他们或者是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学生(如朱传明与杜海滨,拍片那时尚未毕业),或者是流浪北京的青年,甚至是像杨天乙那样原本对影视制作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杨天乙的《家庭录像带》是从自己想要知道的问题出发,20年前父母为什么要离婚,通过镜头,我们看到的是20年后的平静,而且母亲弟弟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愿意将家庭暴力这事说出来。独立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将镜头对准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生活,而且很主动的将这些东西表达出来,而不再是直到被迫表达。拍《姐妹》和《邝丹的秘密》的章桦,她曾经是发廊妹,这可能让她有了低人一等的感觉。刚开始是为了生活才拿起摄像机,希望有一技之长,但是久而久之,她爱上了摄像,而且积极主动的拿起摄像机来记录自己与身边朋友的生活。
(二)关注自己
独立纪录片是将视线转入了自己身上,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把发生在自己身边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都记录下来,通过这些,人们对日常的事物有了新的看法,引起社会上有相同问题人们的关注。
《盒子》记录的是一对同性恋的生活思想,通过对她们的挖掘,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并不是对她们的歧视,相反有了社会学的意义。又比如唐丹鸿的《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这部独立纪录片记录了在中国四川成都的三个人在1999年末到2000年初这段时间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他们中的崔莺是一位画家,她感到自我正在遭到践踏而痛苦不解;尹晓峰的油画曾经充满了力量和激情,现在他一直做着与盲人有关的行为艺术;唐丹鸿是一位诗人,她在严重的抑郁症里挣扎着,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当遇到心理医生张血曦女士后,在治疗过程中,作为对那段时间的清理,拍摄了这部片子。唐丹鸿通过对自己的关注,通过对小人物的关注,将人真实的内心展示在观众的面前,他们的苦恼,抑郁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作者关注的是父母的生活。宋田的《天里》通过关注农村改换村主任的事件把中国普通的一个村庄村民的日常生活呈现在观众面前,作者在这里面贴近了村民,把自己融入在这当中。我们从这些独立纪录片小人物边缘人物的身上看到作者所关心的问题,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自己的身上,拍出来的不是历史片或者是政论片,而是大多数人们所关心的题材。
(三)理性写意
2001年9月22日首届独立影响展组织者说过:“我们不仅是在自觉的展示作品,更为主要的是想介入理论思考、充满反思精神的学术评论,从而让本次影展上升到学术层面上进行。”而独立纪录片从理性写实转向理性写意,指的是通过写实的手段来表意。纪录片的特点是要完完全全的真实,不带有任何的感彩。作为纪录片一种的独立纪录片一开始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套路,但是随着独立纪录片逐步的发展,人们的目光更加的开阔,拍摄更加的自由,拍摄的局限被打破,用独立纪录片来写意的作品越来越多。比如说杜海滨《铁路沿线》中的十几位盲流,作者用一种平视的眼光看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物,对他们的关注没有只停留在生活现象的层面,而是直入精神世界,并且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对话,片中的“小新疆”、“李小龙”等人通过他们真诚的讲述呈现了丰富的个性,赢得了观众的尊重。还有《盒子》,作者通过与她们精神世界的沟通让人们看见的是美。陈晓卿的《沙与海》写的是内蒙与宁夏交界处沙漠边缘的农民的生活状态,人们看到的是长期封闭带给他们的一种状态。
二、资金上自行筹措
目前中国唯一一家专业纪录片商零频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郑琼认为国内独立纪录片制作人的生存状态比起外国同行要差许多,这归因于中国纪录片仍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方案预售机制,同时又没有来自国家、社会的纪录片的基金,独立纪录片的制作者们无法靠记录片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吴文光认为:“你可以在某个领域是一个专业的人,所以你必须做其他工作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结果拍记录片就像业余去做一样。”吴文光的独立纪录片《电影》是他2000拍的素材,但是到了2005年才拿出来剪辑完成。
体制以外的独立纪录片人拍摄时的资金需要自行筹措,拍摄资源无从获得,加上国内相关政策不明朗,只有少数幸运者能得到在电视台播放的机会,或在国际大赛中有所斩获而在海外市场销售,更多的则可能因为不能通过审查,或找不到适合的电视台播放而被彻底湮没。
旅日人士张丽玲自行筹资、策划并组织拍摄的《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历时四年,跟踪拍摄66人,采访数百人,用尽1000多盘素材磁带,斥资6400多万日元。不过在发行上,这部独立纪录片比较成功,先后在上海、重庆、南京、香港等地播放,并引发收视热潮。王兵在制作《铁西区》的过程中,常常很窘迫。他的资金来源是不固定的,并且由于《铁西区》片长达九个小时,没有音乐,没有故事,现代很少有人能够完整的看下来,艺术价值高,但是发行很不成功。张以庆的《幼儿园》花费了大量的资金,要是没有强大的资金做后盾,他根本没有办法获得成功,在艺术上,他是成功了,可是在盈利上,他是失败的。像他这么幸运的人可以说是很少的。资金上的自行筹措导致了很多的导演一闪即逝以及拍摄者身份界定等问题。
文章对独立纪录片的特点进行了论证。不管公众对独立纪录片持什么样的态度,它已经浮出水面了,虽然说它现在的处境很艰难,但是独立纪录片肯定会有一片属于它的市场,并且最终会走进公众的视野。
参考文献:
1、张明博.她们的声音——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独立纪录片女导演创作概述[J].新闻大学,2007(6).
2、孙霁,张爱华.DV纪录片的题材[J].新闻传播,2007(6).
零容忍纪录片范文第2篇
2011年,《看见》之《专访药家鑫案双方父母》,在采访受害者张妙的父亲时,隔壁传来张妙母亲的哭声。柴静起身,“我去看看”,并示意摄像师留在帘子外……
对于这些曾被外界热议的举动,柴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人之常情”。不过,在心态上,她觉得现在与过去还是不同:“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有的悲伤太直接的抚慰是一种冒犯、傲慢,不可安慰的时候你再去呈现它,就有点消费别人的悲伤,我特别害怕这个。另外,30多岁的人对悲伤也有一种克制,语言没有用,我能做的就只是一种陪伴。”
非典那年,白色防护服下柴静娇小的身影,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让她在新闻界声名鹊起。随后在《新闻调查》,柴静屡次与黑暗势力交锋,绵里藏刀,甚至咄咄逼人;她也曾安静倾听伤痛者的诉说,不掩饰自己的柔情,让观众感知节目的温暖。
《看见》制片人李伦说,柴静在《新闻调查》的采访更多是对抗性的,现在更多是体察、温良,用沉静的方式去采访。
现在的柴静,会在采访李阳妻子KIM时送她一束花,她认为这束花代表“你仍然美丽,值得尊重,世界上仍然有美好无损的东西”。同时,面对这样一个内心压抑太久的受访者,她会扔掉提前准备好的提纲,跟随对方进入她的感受,哪怕采访看上去不那么严丝合缝。
她还会在采访结束后与编导一起写稿子,且稿子时常改到八九稿。她不觉得这是分外的工作,因为她干这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一个主持人”。她的兴趣在于认识世界,稿子的形成决定如何认识这个人物。
2012年,36岁的柴静说,采访是一种双方的完成,要尽量做到“不伤害任何人,帮助任何人”。“我原来博客叫‘柴静・观察’,现在改成了‘柴静・看见’,‘观察’还有一种审视的刻意,‘看见’特别寻常,看见就是看见了,我描述给你看。”
工作起来的柴静经常会有一种“沉醉”的美妙感,也似乎从来不知道疲倦,总是在不断地反思。“有时候做这行时间长了会容易油滑,这个油滑就叫把玩,知道怎么玩弄语言观众就会比较HIGH,或者就把这个事给糊弄过去了。”她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种笨拙,在对事实的了解上不偷一次懒。
对于明天,柴静从不规划,“未来不迎,过往不恋,当下专注,就够了,这样会觉得活着特别饱满。”
对话柴静对事要苛刻 对人要宽容
《综艺》:就你个人而言,《看见》与《新闻调查》《面对面》有何不同?
柴静:做《新闻调查》时,面对复杂的新闻事件,经常一期节目要采访20个人,要调查真伪,孰是孰非;在《看见》需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是这个人在这个事件中做出这个选择。《看见》与《面对面》也不同,《面对面》往往是在演播室采访一个人;《看见》即使是人物节目,也要穷尽一切努力去接近他生活的土壤,去发现他跟其他人物之间的结构,弄清楚是什么左右了他。同样是周播节目,《面对面》要比《看见》人物专访时长长很多,可是我现在的工作量几乎是《面对面》时的三倍。
《综艺》:人物节目应该是什么样子?
柴静:我们做叶德娴的时候,那么多媒体都在做《桃姐》,制片人说你要不要采访许鞍华,我说不要,我只要叶德娴。其实我只了解她唱过一首歌《赤子》。为什么对她感兴趣?一是她唱《赤子》时那么动感情,就可以想象她的人生是怎样的。第二个因素是刘德华的存在。我个人对做娱乐明星有些谨慎,但这次人与电影的呼应有戏剧性。相关信息媒体都知道,但没有很清晰地把人生的百味杂陈说出来,我们就要做这样的选题。我们做的不是电影,是人生。以前在《新闻调查》,一个选题有90%的把握我才去做,现在大概60%,给生活的多种可能保留了30%,也是对现实保留一种未知的谦恭吧。叶德娴采访最后,她让我喝水,我们把它放在节目中,这是她性格的延伸,也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呼应。《看见》是个人物节目,我们会更注重用细节和瞬间来勾勒人物。
《综艺》:《看见》中哪期节目对你来说难度最大?如何克服?
柴静:《熊之辩》相对来讲难度大一点,因为要周日播,周四才开始采访,而且我们去的时候现场有两百多个记者,要很准确,知道拍什么不拍什么。进场时我是最后一拨,按号我是排在第一位,就在我回头看我同事的时候,已经有三位同行插在我前面了。我能理解,因为熊肚子那儿只有一个机位能拍到。但对我来讲这不重要,就算用他的素材也没关系。进去也是,同行们还没开拍就已经串场了,越是身在漩涡中越要有等的沉静。所以第一天我们什么都没做,第二天同时采访两方,我清楚我要的是什么。采访完在回来的飞机上我和编导就基本把稿子写完了,当天晚上回来编,周日播,过程比其他节目还要顺。
做这期节目我有一个感受:对事要苛刻,对人要宽容,这是对观众智力的一种尊重。这期节目你会看到价值观的剧烈撞击,我们让每一方都有充分讲话的机会。作为记者,我们做的是让大家明白这件事,而不用替观众去审判这个人。这种客观或者平衡的取向不是通过后期剪辑能做到的,而应渗透进思维方式中。文如其人,还是应该从做人开始,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综艺》:你曾说过“我也是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面对镜头,怎样才算是“平常说话”?
柴静:主持人会有一个误区:老怕观众把自己忘掉,实际上这都是把自我凌驾于报道和对方之上。主持人所做的只是把每一个事实都问到,而不是玩弄语言把对方推到极致,被观众嬉笑怒骂,也不要去秀自己,要让观众自己做出判断。
但我也不是总能保持住,杨丽萍那期就忍不住用了偏艺术的语言。润色是最要不得的,要拉回地面,回到特别真实哪怕是粗糙的状态去体会人性,用最白描最扎实的事实来叙述一个人。采访一定是心里曾经滚热过,但写的时候要沉静下来,放凉了再写,不用自己的情绪去激动别人的情绪。我们做药家鑫那期节目时只是陈述,陈述是最有力量的一种状态,不需大声叫喊,也不要过度煽动。
《综艺》:面对有伤痛感的采访对象,问与不问如何平衡?
柴静:这种揣摩来自一种直觉,问与不问和怎么问之间细如蛛丝,失之毫厘就不对了。我的方式是不对自己有任何约束。刚做记者时,觉得要对别人的伤口感到痛苦、同情,到下一阶段会告诫自己不要那么滥情,要有分寸感,不可以流眼泪。现在我说一切都回到寻常,把自己放进他的感受里会自然而然做出反应,要像他一样活一遍,好感和反感,不管如何掩饰,他都能感觉到。以前会强调主持人要公正。我现在会有一个习惯,把采访提纲放在旁边,沉静在采访对象中,忘掉我的问题,这种感受力很重要。采访KIM时就是这样,我设想如果我是她,我会很抵触一个记者拿着一个准备好的提纲来采访我――他已经想好了要如何运用我的人生,我不要这样。
《综艺》:从广播到电视,从湖南台到央视,再到在央视的几次栏目调整,每一次改变,有共同的原因吗?
柴静:我自己的调换大部分是被动的。真是我憋着一股劲儿非干不可的有两次,一次是广播电台,一次是《看见》。我来《看见》时也有一种少年的冲动,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就是想与我喜爱的人做点我们高兴的事儿。这个团队有新闻评论部的人文传统、纪录片的情节,我希望在一个业务气氛非常浓的气氛中工作。那时候还没有周末版,我跟李伦说,就让我做你们普通的记者,在日播节目中每周播出一次,根本不会想到把它放到周末版或作为一个特别节目推出。我们开播前连一次会都没开过。我给李伦发短信说我要做药家鑫,他说做吧,就两个字,这是一种共识。一个团队最怕说服和解释,这对我来讲特别重要,几乎没有别的损耗。
《综艺》:你采访的逻辑是怎么形成的?
柴静:《新闻调查》,我可能会在出发前先写好策划案,然后一二三四五去采访,刚来《看见》时也有过这样的状况。后来我调整了,就像刚刚结束的这期采访,一开始也困惑,到现场后也不知道会做成什么样,但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所以我现在的方式就是踏踏实实采访,一个人物采访三个小时,回到原点去说,水落石才出。前几天采访魏德圣也是,采访时发现了一个我们之前都没有发现的线索――导演和他塑造的主角之间紧密又反叛的血肉关系,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他,他自己都不自知不自觉,只有通过摸索才能看到。
《综艺》:相比过去,你对自己现在的采访状态满意么?
柴静:我很少看以前的节目,重要的不是我到底比过去进步了多少,而是我有对自己的生命诚实吗?我并不认为我20多岁时候的表现比现在差。那时候我去给孩子擦眼泪,或者在对抗性采访中咄咄逼人,也是恰如其分的诚实,也没有逾越职业伦理的界限。但现在我变化了,我适应它,我尊重自己对人生的思考,最有意思的也许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诚实,不撒谎。我小的时候老想特别宏大的事,现在觉得做一个记者诚实最重要。有人说《看见》不是一个新闻栏目,更多带有文学性,文学和新闻的区别在于文学讲的都是最寻常的,它要的是人内心的共鸣。把新闻变成文学后,视野会有很大的变化,也不会想刻意创新。
《综艺》:采访中你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
柴静:我不能容忍对采访对象的干预。因为他的任何一个状态都非常有价值,而且是属于他本人的,干预他就表明不能理解他。第二不能容忍的是粗暴地对待采访对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第三,我希望有一种判断,判断来自人生的全部经验,采访、摄像、编导所有的信息都不丢失,才有可能保留一种别人看起来会轻易丢掉的东西。
《综艺》:每期节目播出后你都会在博客中做出反思,你是个挑剔的人吗?
柴静:我每期都有反思,也有同事批评我反思过度了。我不这么觉得――没这个劲儿就别干这行了。多写、多总结、多反思是这个职业唯一能够进步的根源。相反,我经常在采访对象面前觉得很惭愧,杨丽萍对自己是什么要求,王迪是个小伙子,但彩排的时候都跳不动了,她要一连跳五遍,她身体是什么感觉?她非如此不可,那是她的命。传播力和影响力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看完自己做的节目能不能面无愧色。
柴静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