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的诗句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春分的诗句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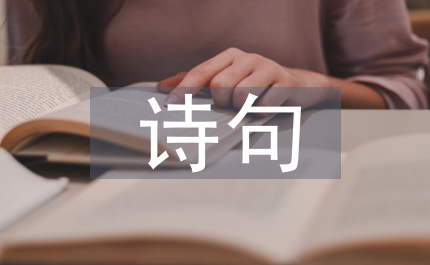
春分的诗句范文第1篇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分布格局;变迁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6-0154-07
西周末年,因幽王废申后和太子,申后之父联合缯、犬戎攻破镐京,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平王继立以后,于公元前770年,东迁雒邑,这样历史进入到春秋时期。春秋以降,王室衰微,诸侯坐大。但“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1](《万章下》)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当时各诸侯国的疆域还没有联成一片,各国之间还有许多的隙地。少数民族尤其是戎、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纷纷进入中原,形成了与诸夏交错杂处的分布格局。中经春秋战国时期民族间的战争与经济文化交流,内迁的少数民族最终与诸夏融合,并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华夏族居中,戎狄蛮夷居于四边的分布格局。
春秋时期少数民族的分布
宋人永亨在其《搜采异闻录》中云:“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之戎、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用夷。” 这是对当时民族与诸侯国分布情况较为明确的概述。因为春秋时期内迁的主要是戎、狄,所以对活跃在中原一带的戎、狄分布是介绍的重点。
《史记・匈奴列传》曰:秦穆公时,“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x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可见戎族支系甚多。下面把活动在中原的戎人分布作一考证: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云:“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在陆浑之戎被迁至伊川以前,伊洛地区就有戎人居住了。《后汉书・西羌传》载:“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吕思勉先生云:“其以戎称者:曰扬拒、泉皋、蛮氏之戎,曰骊戎,皆在今河南、陕西境。”[2](P33)
并注曰:“扬拒,在河南偃师附近。泉皋,在今河南洛阳附近。”蛮氏之戎,吕氏注云:“今河南临汝。本居茅津。亦称茅戎,《公羊传》作贸戎。地入于晋。”
在河渭交汇处,也生活着戎人的分支。《后汉书・西羌传》又载:“后九年……允姓之戎迁于渭I;东至S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S辕,在今河南偃师东南,登封东北[3](P88);而河南山北,即指陕西商县以东,河南嵩县、陕县一带。这些地方都在中原地区。《左传》闵公二年:“春,虢公败犬戎于渭I。”《史记・秦本纪》云:“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唐张守节《正义》注“茅津”引刘庄伯云:“戎号也。”《括地志》云:“茅津及茅城在陕州河北县西二十里。”《左传》僖公二年:秋“虢公败戎于桑田”。桑田在今河南灵宝境内。《左传》成公元年:“春……刘康公徼戎……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宋元人注曰:“茅戎,戎别种也,《括地志》云:‘茅戎,在河北县西二十里。’徐吾氏,茅戎别种。” 此外,骊戎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在晋南一带[4](P54);卢戎,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九南漳县条载:南漳县东北五十里有中庐城,是春秋时卢戎国故地。另《水经注・沔水》也载:“过中庐县东……。县即春秋庐戎之国也。”即在今湖北南漳县境;戎州己氏戎,《左传》隐公二年杜注:“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春秋大事表・四夷表》:“在今山东曹州府之曹县与河南兰阳县接界。”即在今山东曹县东南;山戎(又称北戎、无终),《春秋大事表・四夷表》:“今直隶永平府玉田县治西有古无终城。”即在今河北卢龙、迁安县境。由此看出,当时内迁的戎族主要生活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等地。
北狄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个支系。据《史记・匈奴列传》载:晋文公时,“赤翟、白翟居于河西簟⒙逯间。”《集解》引徐广曰:“簦在西河,音银。洛在上郡、冯翊间。”《括地志》云:“近延、绥、银三州,本春秋时白狄所居。”白狄先在陕西延安、山西介休境,后徙至河北境内,分为三支:鲜虞,建有中山国,都城在今河北新乐;肥,在藁城县西南;鼓,在晋县以西地。赤狄首先活动在山西南部,后有支系向东迁徙。《左传》闵公二年:“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皋落氏就是赤狄的别种,在山西垣曲县西北五十里。《左传》文公十一年载:“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潞国也是赤狄的别种。赤狄共六支:潞氏,在山西潞城县东北;东山皋落氏,一说在今山西垣曲县。《水经注・河水》说:“河水东过平阴县北,清水从西北来注之。清水东流迳皋落城北,服虔曰:‘赤狄之都也……《春秋左传》所谓晋侯使太子申生伐皋落者也’”一说在今山西长治县一带。《后汉书?郡国志》上党郡壶关刘昭《注》引《上党记》说:“东山在城东南,申生所伐,今名平皋”;一说在今山西昔阳,宋《乐史》说乐平县有皋落镇,“即古东山皋落氏之地”[5](卷五十);留吁,春秋初期居地不祥,据《水经・浊漳水注》,其春秋中叶居于今山西屯留;Z咎如,在山西太原附近,一说初在晋国之西,后徙至河北境内[6](P5);铎辰氏,春秋中居地在今山西长治境内;甲氏,依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四夷表》的考证:“甲氏在今直隶广平府鸡泽县”,即今河北鸡泽县一带。其地在太行山以东,今河北邢台以南,可能是狄人占据邢国故地以后迁居之地。长狄和赤狄曾先后活动在山西、河北乃至山东海滨之地[3](P119)。依《左传》与《史记》的有关记载,知长狄支系n瞒则分布齐、鲁、宋、卫之间,相当于今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
春秋时期,南方蛮族种类繁多,有群蛮、百濮、百越等,统称为南蛮。一般地说,群蛮分布在今湖北北部,百濮分布在湖北西南部及湖南境内。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四夷表》云:时人“往往不能举其号第,称蛮曰‘群蛮’,称濮曰‘百濮’,以概之。其实种繁,其地为今某州县亦难为深考”。南方的江汉流域及西南部,当时为楚地,境内多为群蛮,还有巴、濮、邓、庸等,后融合于楚族。越族分布在东南沿海及岭南之地。
东夷主要指居住在山东半岛、淮河中下游今安徽、江苏一带的夷人,包括舒夷、淮夷、徐夷、莱夷。舒夷在今安微中部;淮夷分布于今淮河下游苏北、皖北境内;徐夷在今安徽泗县北;莱夷在今山东半岛;任、宿、须句、颛叟、莱、邾、莒、郯、、介、根牟等都是莱夷建立的小国。其中,莒在今山东莒县;根牟在今山东莒县东南沂水流域;牟在今山东莱芜;郯在今山东郯城;介在今山东半岛南部;莱在今山东半岛北部;舒夷在今安徽舒城、庐江、霍山、桐城一带[7](P16)。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戎狄蛮夷与诸夏出现了分布上的交错杂处的局面。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列国疆域的扩展,诸夏与戎狄蛮夷之间的战争就因对资源的争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同时,诸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进行之中。这些都大大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而就是这种民族间的融合,最终使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间的斗争与融合
从民族斗争发展总的趋势来考察,华夏与四方诸族的关系中,以北方戎、狄之族和南方楚族的活动,对华夏产生的影响最大。《公羊传》僖公四年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就是对这一形势的概括表述。
春秋初期,犬戎依然是威胁着周王室的主要力量。《左传》闵公二年载:“虢公败犬戎于渭I”;二年后,“虢公败犬戎于桑田”[8](僖公二年)。犬戎力量被削弱以后,继之而起与周王室对抗的是杨拒、泉皋、伊雒之戎。周襄王三年(前650),王子带勾结“杨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8](僖公十一年),以至秦晋出兵“伐戎救周”,直到周襄王十七(前664)年,“取太叔(王子带)于温,杀之于隰城”[8](僖公二十五年),才告结束。后来,晋楚争霸时,陆浑戎和蛮氏戎成为双方争夺的目标。《左传》宣公三年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周简王元年(前586),陆浑戎随同晋国“侵宋”[8](成公六年),后来,晋国却以陆浑戎“贰于楚”为借口,灭了陆浑。随后,晋楚又对蛮氏戎进行争夺。周景王十九年(前526),楚国“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8](昭公十六年)。其后,蛮氏戎又勉强维持了三十余年。《左传》哀公四年曰:楚“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蛮氏戎灭亡。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在戎夏关系中,西戎与秦国的关系尤为密切。春秋之初,《史记・秦本纪》载,周平王二十一年(前750),“秦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于是秦国在西戎的势力大为发展。一个多世纪后,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4),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国乃成为春秋时期我国西部地区民族融合的巨大中心。
早在春秋初期,狄族便是诸夏来自北方的重要威胁。《左传》隐公九年载:“北戎侵郑”。从此,揭开了北狄与诸夏斗争的序幕;周桓王十四年(前706),“北戎侵齐”[8](桓公六年)据《史记・齐太伯世家》载:齐桓公两次发兵救燕,出击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在此后的数十年内,狄族又先后“灭卫”、“灭邢”、“灭温”,而以齐国为首的诸夏则进行了“救邢”、“封卫”的斗争。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7),晋国“败狄于箕……获白狄子”[8](僖公三十三年)。自此以后,狄族发生了严重分裂:《左传》宣公七年载:“赤狄侵晋”;《左传》宣公十三年云:“赤狄伐晋及清”。与此相反的是,《左传》宣公八年记载:“白狄及晋平”,晋国利用狄族内部的矛盾,于周定王九年(前598),“晋……求成于众狄产;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8](宣公十一年)。《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晋国“败赤狄于曲梁……灭潞。”《春秋大事表・四夷表》云:“诸狄之中,赤狄为最;赤狄诸种族,潞氏为最。”潞氏的灭亡,对赤狄打击之大。接着,《左传》宣公十八年又载:“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留吁、铎辰”。周定王十九年(前588),“晋s克、卫孙良父伐Z如,讨赤狄之余焉”[8](成公三年)。《左传》文公十一年曰:“齐襄公之二年,n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卫人获其季弟简如,n瞒由是遂亡。”《左传》昭公元年:“晋国申行穆子败无终于太原”,与山戎的和好关系结束。无终败后,乃东北去,从此一蹶不振。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晋国又结束了与白狄的结盟,出兵“灭肥”。接着,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晋灭鼓 [8](昭公二十二年)。历史的发展,使晋国成为春秋时期北方各族融合的中心。至此,北狄之中,仅存白狄鲜虞一支。
在东方夷族中,淮夷是较强的一支,西周中后期,淮夷不断进扰周室[8](《大雅・江汉》),双方不断发生战争。这在西周时期的《簋》、《明公簋》、《禹鼎》、《生S》等铭文中均有记载。春秋中叶,淮夷再度强大起来。《左传》僖公十三年载:“淮夷病杞,且谋王室也”。此后,诸夏基本上制止了淮夷的进扰。春秋后期,淮夷与诸夏关系已十分密切了,经常参与各国的会盟和征伐。例如:《左传》昭公四年载:淮夷与各国“会于申”;又参与各国“伐吴”。莱夷是东方夷族中较强的一支。《左传》宣公七年曰:鲁国会同齐国“伐莱”。在齐鲁的连连打击下,莱夷元气大伤。《左传》襄公六年云: “齐侯灭莱”。西周末年,周宣王攻打淮夷时,徐夷也受到很大打击[8](《大雅・常武》)。春秋中期,徐夷力量得到恢复,并先后打败舒夷和莒国,经常参与各国的会盟。周敬王八年(前512),徐夷被吴国所灭。春秋中期以前,舒夷已被楚国征服。但在春秋中期以后,众舒与楚国进行了六七十年的斗争。《左传》宣公八年载:“楚……伐舒蓼,灭之。”舒庸于周简王十二年(前574),利用吴楚矛盾,“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但舒庸终为楚师所灭[8](成公七年)。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舒鸠灭于楚。东方夷族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如纪、J、谭。遂等,均先后为齐所灭。齐国成了东方民族融合的一个中心。
《左传》桓公三年载:周桓王二十一年,“楚屈瑕伐罗”,罗与卢戎大败楚军,致使其主帅自尽。其后,在近一个世纪中,随着楚国在经济军事方面的迅速发展,楚在与蛮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约当鄢陵之战前,大部分蛮族已被楚国征服,故在鄢陵之战中,蛮军成为楚军的一个组成部分[8](成公十六年)。此外,据《左传》桓公十八年、十九年记载,在“伐罗”之后,楚国先后征服了西南方的巴人和南方的濮人,又先后灭掉了“汉阳诸姬”。由于与夷、蛮、戎各族均有较多的联系,楚国成了沟通南方蛮族和中原华夏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巨大桥梁。
各族的长期斗争,进一步了打破他们之间的地域界限,与此相伴的是,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进行之中,且联系日益加强。
政治上主要表现于会盟。春秋时期,少数民族与诸夏举行多次会盟,其主要会盟有:
鲁隐公“会戎于潜”,“秋,盟于唐,复修旧好也。”[8](隐公二年)
鲁桓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8](桓公二年)
“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8](僖公十二年)
“卫人及狄盟。”[8](僖公三十二年)
鲁公子遂“会雒戎,盟于暴。”[8](文公八年)
“白狄及晋平。”[8](宣公八年)
“晋s成子求成于众狄……会于绾。”[8](宣公十一年)
晋悼公“使魏绛盟诸戎。”[8](襄公四年)
各国诸侯与淮夷“会于申。”[8](昭公四年)
楚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8](哀公十九年)
同时,各族间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融也日渐深化。《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晋惠公时,迁姜戎至晋的“南鄙之田”。《左传》襄公五年:齐悼公时,“选定莱于\”。《国语・齐语》云:齐桓公时“通齐国渔盐于莱”。晋悼公时,魏绛“和戎”的目的之一是因为戎狄“贵货易土,土可贾焉”[8](襄公四年)。据《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晋景公赏荀林父“狄臣千室”,并“献狄俘于周”,《左传》哀公四年也有楚昭王灭蛮氏戎,“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的记载,这些少数民族直接被投入到生产部门。少数民族的一些农作物也随之传到诸夏各国。周惠王十五年,齐败山戎,献“戎菽”于鲁[9](庄公三十一年)。管仲亦云: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戒篇》)。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华夏化进程加快。《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晋国范宣子同姜戎驹支发生争执。驹支在回顾了晋戎的关系后,乃赋《青蝇》而退;周景王二十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有人问郯子:“少氏鸟名官,何故也?”[10]郯子对答如流,并讲了许多历史典故。《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的周王子朝等“奉周人之典籍以奔楚”,是为周文化南下入楚的重要事例。而鲜虞所建的中山国,其主要特征已与诸夏无异。春秋战国时期各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发展已达到的令人惊叹的高度。
民族间的通婚则把各族融合推进到更高的阶段。《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后晋献公伐骊戎,“骊戎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姊生卓子”。《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又载:重耳奔狄时,“狄伐Z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同时,晋国也嫁女于戎狄,如晋景公的姐姐便是“潞子婴儿之妇人”[8](宣公十五年)。《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所载的鲁僖公夫人风氏也是东夷的女子。此外,诸夏与少数民族的下层民众之间的通婚想必当会更多。
战国时期,“攘夷”的任务已告结束,各诸侯国为了能一统天下,兼并战争不但继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经过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斗争融合,今陕甘豫晋冀一带的戎狄族已无迹可寻。在南方,楚国灭越灭鲁,势力发展到云南滇池一带;秦国兼并了巴蜀,又夺取了楚的巴黔中郡。中原的诸夏和东南沿海的越族、西南方的西南夷的融合也加速了。民族斗争和融合的结果,大大促进了华夏族群的发展,并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大帝国创造了条件。
民族认同与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
所谓民族认同,首先是诸夏的认同,然后是秦、楚、吴、越的华夏认同。经过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韩、魏复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F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11](《西羌传》)自此,中原地区诸戎已经与华夏族融合了。已经华夏化的中山国最终被赵国所灭,中原地区狄人也不复存在。秦、楚、吴、越也逐渐认同于华夏。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华夏居中,戎狄蛮夷居于四边的分布格局。
进入春秋以后,民族矛盾激化,使诸夏民族意识得到强烈的发展。《左传》闵公元年载,齐桓公二十五年,“狄人伐邢”,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诗经・鲁颂・s宫》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歌颂鲁僖公追随齐桓公北伐狄,南服楚、舒,认为“诸夏亲昵”,则“天下无敢御也”[12]。孔子时,对于夷夏关系,主要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8](定公十年)。孟子则提出以“用夏变夷”而反对“变于夷”[1](《滕文公上》)。儒家的民族观有歧视夷狄的一面,又认为夷狄只要接受华夏的文化礼俗,即可视为兄弟。孔子本人虽感叹“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13](《八佾》),同时还“欲居九夷”[13](《季氏)》,并不认为蛮夷戎狄是一无足取的。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3](《子罕》),即对夷狄要用文德使之归服,他收徒“有教无类”,他的高足子夏说:“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3](《颜渊》)。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观的演进,是当时民族融合的历史大趋势已明朗化的反映。孟子尽管反对兼并战争,当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时,但他明确地回答“定于一”[1](《梁惠王上》)。荀子与韩非等人,则更积极主张中央集权制下的君主专制,全国统一,“一断于法”。
在春秋时期,秦、楚、吴、越等当时仍为夷蛮戎狄的国家,则积极吸收诸夏的文化,尽可能使自己与中原诸夏发展水平接近。楚原是南蛮的一部分,《史记・楚世家》就有国君熊渠“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记载,《诗经・大雅・采芑》也斥之为“蠢尔蛮荆”。前659年始与中原诸侯会盟,称楚,成王十六年与齐桓公等有召陵之盟,虽仍被中原当作蛮夷,实际上已列于诸侯之林,为诸夏所重视。自庄王到平王近一个世纪,为晋楚争霸的时期。也是楚由蛮夷转而为华夏的关键时期。春秋中晚叶,楚已经是“夷狄进至于爵”,被诸夏所接受,《史记・楚世家》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则是楚人被认同为华夏的重要标志。战国的两个多世纪,楚境民族融合进展非常迅速。春秋中后期,吴、越的华夏化进程也加快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吴季札来观周乐,尽知乐所为。”由此看来,当时吴国贵族的华夏化程度已很深了。《吴太伯世家》载:“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越王勾践世家》也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则是吴越民族认同于华夏的标志。后,越灭吴,越又被楚所灭,更加快了他们华夏化的进程。秦在建国之初因行“戎狄之教”14](《商君列传》),一直被诸夏视为“秦戎”、“狄秦”[10](《小匡》)、(僖公三十二年),“不与中国诸候之会盟”[14](《秦本纪》),据《史记・秦本记》载:直到秦文公十六年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将中心稳定地迁居“F渭之会”。此后秦人脱离游牧转向定居农业,并在周文化影响下向华夏化发展。民族融合的过程,在秦国进展迅速。秦穆公时,即已经以“诗书礼乐”自居,而“秦灵公作吴阳上,祭黄帝;作下,祭炎帝”。祭黄帝、炎帝是秦人华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战国时期,华夷统一的学说形成。《公羊传》对《春秋》所记242年历史,以大一统为宗旨总结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的三世说。认为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诸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所见世为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15](隐公元年及何休注)已实现“王者无外”,天下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公羊派是从大一统出发看到了并且肯定当时的民族大融合、诸夏大认同的事实。《禹贡》已打破当时国界划分天下为九州,又根据各州民族远近与民族特点划分为五服,从而创立了根据各地土壤高下与物产不同来确定赋税等级,根据民族特点来确定管辖政策,这样一种华夷统一的地理学说与政治理想。《周礼・夏官・职方氏》说:“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职方氏根据战国七雄形势,划分天下为九州。《礼记・王制》也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纹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通过翻译“达其志,通其欲”,而天子对各民族“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于是中国与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的统一格局形成了。
战国时期形成的这种华夷五方格局,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地理分布上对后世中国的民族分布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持正统史观的学者则都有汉族居中,少数民族居于四夷的思想观念。后世王朝虽都有民族间的迁徙,但内迁的少数民族则大都后来同化为汉族了。所以,其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直到现在,虽然我国是“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但汉族主要居住在中原,而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则主要居住于四边的格局仍是一个基本事实。
参考文献:
[1] 孟子[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M]. 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3]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A], 古族甄微[C].成都:巴蜀书社,,1993.
[4] 顾颉刚.骊戎不在骊山[A], 史林杂识[C]. 北京:中华书局,1963.
[5] 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M].北京:三联书店,1962.
[7] 邱树森,匡裕彻.中国少数民族简史[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8] 左丘明.春秋左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9] 春秋谷梁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黎翔凤.管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 范 晔.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 诗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 论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春分的诗句范文第2篇
关键词:活性炭负载氧化锆 聚乙烯醇 包埋
Abstract: I embeded activated carbon loaded with zirconium oxide with polyvinyl alcohol and sodium alginat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and pH on its phosphorus removal effect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8% polyvinyl alcohol and 1% sodium alginate embedding zirconium oxide have higher phosphorus adsorption rate, and it mechanical strength is strong, permeability is good. At 25℃, pH of 5,the phosphorus adsorption rate is best.
Key words: activated carbon loaded with zirconium oxide , polyvinyl alcohol, immobilization中图分类号:G424.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氮、磷是引发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元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增高,更加注重精神享受,人们为了美化和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在城市内修建了大量的人工湖。但是由于人工湖汇水面积小,汇水量小,交换水量调节能力小,而且人们缺乏对人工湖的定期检测,造成人工湖营养失调,氮、磷引发水体富营养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笔者希望通过模拟废水磷去除的研究,对以后水体的除磷能够提供些许建议;通过控制、破坏水体中COD、氮、磷的比例,来控制水体的富营养化,保持水体的洁净,提高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国内外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四价金属锆的水合氧化物对水中的磷具有较好的吸附效
果[1、2]。朱格仙、张建民[3]等对负载氧化锆除磷的制备条件做了研究。国外近年也有人将氧化锆负载在纤维材料中以提高水中微量磷的去除[4],可见采用氧化锆除磷具有一定发展前景。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发现当负载氧化锆的活性炭吸附一段时间后,氧化锆会从载体活性炭上脱落,降低磷去除效果,而且浪费材料。现笔者将参考前人研究成果,采用包埋法,即在原物质表面包裹一层有空隙、能使氧化锆与水中的含磷化合物自由接触但不产生泄露的方法,用聚乙烯醇和海藻酸钠对负载氧化锆的活性炭进行包埋固化。对其包埋前后除磷效果做比较,并研究温度、pH对其处理效果的影响。
1 实验部分
1.1 试剂与仪器
实验试剂包括:氧氯化锆、八水、无水氯化钙 、海藻酸钠、氨水、磷酸二氢钾、酒石酸锑钾、钼酸铵、盐酸等均为分析纯、硼酸(化学纯)、活性炭颗粒、聚乙烯醇(1750±50)。
实验仪器包括:可见分光光度计(N722),万用电炉(一联),六连同步电动搅拌器(JJ—4),水浴恒温摇床(SHY-100),新飞冰箱(BCD—185K),医用一次性注射器(20ml、10ml、1ml), 快、慢速定量滤纸(9.0cm、11cm、12.5cm) ,0.45µm针孔滤膜等等。
1.2 模拟废水的制备
磷酸盐储备液:将优级纯磷酸二氢钾(KHPO)于110℃干燥2 h,在干燥器中放冷,称取0.2197 g溶于水,移入1000mL容量瓶中,加(1+1)硫酸5mL,用水稀释至标线,此溶液每升含磷50.0 mg(以P计)。
1.3 固定化细胞的制备
将一定配比的聚乙烯醇和海藻酸钠混合加热溶解约15 min ,随即加入负载氧化锆的活性炭搅拌均匀,冷却后用注射器均匀连续地将悬浮液滴到含2% CaCl的饱和硼酸溶液中固化,利用注射器将混合液滴入硼酸溶液时需用搅拌器不停地、均匀地搅拌以防颗粒间交联,滴液结束可停止搅拌。固化20 h后滤出小球,用去离子水冲洗3次后备用。
1.4 溶液测定与计算
实验测定步骤[5]:①分别取经滤膜过滤水样,加入50mL比色管中,用水稀释至标线。②显色:向比色管中加入1mL10%的抗坏血酸溶液,混合30s加入2mL钼酸铵溶液充分混合,放置15min。③测量:用10mL比色皿于700nm波长处,以零溶液为参比测量吸光度。④计算:磷酸盐(P,m/L)=m/v。
实验计算:除磷率 P=(C-C)/ C吸附量 Q=(C-C)×V/m
式中 Q—— 吸附量,mg/g C——溶液的初始浓度,mg/L
C——吸附后溶液的浓度,mg/L V——溶液的体积,L
m—— 吸附剂的质量,g
结果与讨论
2.1 聚乙烯醇和海藻酸钠的最佳配比
聚乙烯醇具有机械强度高、化学稳定性好、价格低廉等优点,但它是一种高粘度的物质,与硼酸反应较慢,溶液滴下时容易黏在一起,即聚乙烯醇有强的附聚趋向。而海藻酸钠作为一种多糖类天然高分子化合物,成型方便,通透性好,但其机械强度弱。结合以上两种材料特点,我们将聚乙烯醇和海藻酸钠按一定比例混合对负载氧化锆的活性炭进行包埋固化。有研究表明当加入0.5%的海藻酸钠时[6],就能有效地克服附聚现象。为了提高传质性能在本实验中加入1%的海藻酸钠。分别配制聚乙烯醇与海藻酸钠浓度比分为6:1、7:1、8:1、9:1、10:1载体溶液进行实验。
综合考虑,本实验中我们采取8%聚乙烯醇和1%海藻酸钠的混合液进行包埋固化。其包埋后的小球直径约为4mm。如下图:
2.2 负载氧化锆的活性炭和聚乙烯醇包埋对比实验
分别称取0.2g活性炭颗粒,0.2g负载氧化锆的活性炭和包埋了0.2g负载氧化锆的活性炭聚乙烯醇小球。放入浓度为50mg/L的50mL磷溶液中,在25℃、150r/min恒温振荡器中振荡。用0.45µm滤膜过滤溶液后,用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磷溶液的含量,计算其吸附量。
图1不同情况下除磷效率
结论:活性炭吸附除磷的效果最差,负载氧化锆后磷的去除率明显上升,但是当把负载氧化锆的活性炭用聚乙烯醇和海藻酸钠包埋后磷的去除效果更好。说明氧化锆具有良好的除磷效果,且在吸附过程中确实有氧化锆从活性炭上脱落、泄漏,包埋固化负载氧化锆的活性炭后能够提高氧化锆的利用。
春分的诗句范文第3篇
春分过后,油菜花竞相开放,清明时节,油菜花漫山遍野。她花期不长,却开得热烈,她风姿不妖,却子实丰盈。
我家门前是广袤的田野,清明回家,正赶上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怒放。在和煦的阳光照射下,亮晶晶的,黄灿灿的,令人心绪惬意,目光发亮。近前,还可看见蜂儿起舞,蝶儿彷徨,微风吹来,香气袭人。经意或不经意间,将那些难以捉见的花粉吸入鼻孔,湿湿的,痒痒的,那感觉十分舒坦。姑娘们掩不住内心的喜悦,纷纷钻到花丛中,有人还摘取一朵插在发间,嬉笑连连。春日的田畴被油菜花浸染得的确让人陶醉。
单个的油菜花,其实也不是特别好看,很普通的黄色花而已,那形状也不是很别致,每一朵油菜花由四个萼片组成,辐射对称,十字形排列,萼片内收外展,就像一把把小扇子。仔细看那萼片,其实是双层的,每个大萼片的下面都忖着一个小萼片,实则就是花托吧?被萼片包括的是六雄一雌七个花蕊,雄蕊还算有特色:四长二短,故有“四强花蕊”的说法。其实,绝大多数蔬菜类都属十字花科,也就都是油菜花的亲戚,花序为总状,只是颜色不同罢了。也许正是因为“太普遍”这一特点,所以很少有人特别是名人关注,自然也就少有人对其赋诗作文唱赞歌了。
但是,油菜花是美丽的。她的美不在争奇斗艳,不在妩媚妖娆,而在以小见大、温馨耀眼、气势滂沱,当她们簇拥在一起连成片形成遍地金黄一望无际的海了,那才是油菜花蔚为壮观的美。
春分的诗句范文第4篇
第一次读灵均的作品,是在记忆深处的十八年前,那时我们都在南湖之畔读书,与一些梦想同行而不务正业。他写了一首关于月亮印象的长诗,用长袂飘逸的句式和回环往复的结构挥霍自己的热情与才气。那首新体“回文诗” 有一百多行,用复写纸周正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它所进行的语言猎奇和文体冒险,当时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日月忽其不淹”,十八年恍然如梦。十八年不能改变月亮阴晴圆缺的运行,十八年却足以让热情倦怠,让梦想泯灭,让淡蓝色的字迹模糊,让浅白色的纸张焦黄,更何况这十八年间我们经历了许多对文学颠覆、对记忆修改的公众事件及个人遭遇。十八年后,在春分与清明之间,集中读了灵均的一组散文,感觉到时光不但没剥蚀他诗意的感知,而且使之更加丰盈充沛,不但没有让他梦中的憩园、泊地堕入红尘,而且他精神的漫游走得更远更从容。
从《古村夜境》的张谷英到《沱江之水》的凤凰城,从《巫山夜雨》云雨笼罩的船头到《索溪,索溪》梦里水乡一般的潭中,他总是以行走的方式找着都市背面的世界,悄然一人与古人、溪流和雨水彻夜长谈,“给灵魂以最充盈的慰藉和抚摸”。在此,他也以个人的语言创造汇入了当代文化散文的表意流程:“寻找景物背后没有凝聚成实体的精神”(余秋雨语)、“在灰烬中摸到历史远去的余温”(黑格尔语)、“为散文重新进入自然与历史找到一条秘密通道”(谢有顺语)。我想,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写作者须才情、文蕴、睿智三者兼备。纵观灵均的这几篇散文,才情是充溢的,故索溪的至美能在他笔下得到充分表现,巫山夜雨被他赋予了狂草的气势,沱江之水也由着他牵引,“一寸一寸地深入梦的腹地”。文蕴是含而不露的,我很欣赏他对张谷英的文化阐释:“与其说男人张谷英创造了一个村落,让后人或游人把一段历史翻出来数点,还不如说,这是中国湘北民俗中一段无法睡去的章节,鲜活了延绵一脉600年的正统血缘。” 如果《巫山夜雨》不是在李商隐的诗句前浅尝辄止,而是沿着这一文脉深入,引发意蕴更悠长的文化感悟,那么,该篇就会更厚实一些。景致虽然可以当早点,但还不是大餐,丰盛的文化大餐需要文火慢慢熬出的原汤原汁。融入思考的睿智是他的追求,他总是在字里行间进行着意义的探究和思绪的放飞。在疑惑发生的地方,人文关怀和心灵重建总会悄然生成:“古村人丁兴旺或许与一床暖被相关联。不然,村民为何这么早便入睡?”读到这些句子,我会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我感到平日话语从容、有些发福、爱抽烟喝酒的灵均在精神上是一位永远的游子,一位秉烛夜游的诗人,和十八年前一样,只是少了一些才情挥霍,多了一些“凝聚人生与文明的内力”。应该说, 这样更好一些, 更能“ 在繁华的尽处,在思念与泪水交识之处,在疲惫与困顿挣扎之处”,凭自己的意念之力和精神之火拨亮“那盏亮在黑暗深处的暖光”。每一个给自己“星星点灯” 的人是有福的,他能借此给精神导航,穿越迷雾,避开暗礁,迎着浪头朝着家园的方向行驶,不论旅程有多远,他的灵魂都会回家,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
灵均生长在楚辞滥觞的地方,他的家学渊源,这与一根须十分发达的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连他的名字也来自《离骚》,楚文化已经流淌在他的血脉里,他写作中的美文倾向十分强烈,贯穿了整个青春期,使我相信,风格来源于血液。他的散文,意象的色彩美、动态美和语言的流动美、纯粹美及观念的唯美是合一的,美得乱人心智也好,美得一塌糊涂也好,美是他文本里的实体,而不是概念,他总是在审美化的体验里完成自己的精神游历,由此,很自然就想到了屈原开创文学的传统:让思绪和灵魂一起优美地飞翔——这也是我拿《山鬼》里的一句辞作这篇印象记标题的缘由。
春分的诗句范文第5篇
——摘自援疆干部、原兵团兵团日报社副总编辑田百春诗歌《我们来援疆》
2013年3月20日,春分,北京大雪。
这天上午,援疆干部、原兵团日报社副总编辑田百春的妻子梁文欣来到求是杂志社副总编朱铁志的办公室,向他谈了田百春捐献眼角膜的愿望。
梁文欣离开后,朱铁志有些感伤,但他怎么也没料到,没等到办理好捐献眼角膜的手续,这天夜里,田百春的病情就急剧恶化。
3月21日凌晨5时,“优秀援疆干部”、文化援疆干将田百春永远地离开了。
三年,10省市文化援建兵团的事业可谓如火如荼,兵团文化事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切正是因为有以田百春为代表的文化援疆者的辛勤劳动。
他们是心灵的纽带,合力编织着兵团人的文化之梦。
用先进文化温暖人心
2011年7月下旬,《梨园春》栏目组走进十三师,展开《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新疆赛区的选拔。同时,还为十三师各族职工群众献上了精美的文化大餐——明星璀璨、阵容豪华的“豫疆情”大型联欢晚会,点燃了职工群众的文化热情。
8月7日,《梨园春》栏目组在红星一场万亩葡萄园中录制的戏迷擂台赛在河南卫视播出,红星一场职工赵翠莲躺在病床上看完了整场比赛。
继“豫疆情”晚会后,2012年10月,河南电视台品牌栏目《华豫之门》又走进十三师,举办“情鉴豫疆”大型鉴宝活动,一批珍贵的军垦文物登上了珍宝台,为兵团精神的发扬和传承作出了精彩的诠释。
今年年初,河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获得兵团“文化援疆突出贡献奖”,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河南省文化援建方式不断创新,内容异彩纷呈,成为援疆工作的一大亮点。
用文化实力夯实基础
用文化“软”实力夯实发展“硬”基础,三年来,兵团文化援疆工作蓬勃发展——
山西省先后组织大型历史话剧《立秋》、“黄河情韵 放歌天山”等专场文艺节目在乌鲁木齐、昌吉、阜康等地演出。
河北省开展“燕赵媒体二师行”活动,全方位、多角度采访二师工业企业。
十四师四十七团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沙漠研究中心、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教育部直属重点实验室等实验室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先进的科研设备,在团场投资建设防沙治沙试验示范基地,为几十万亩沙地安全、持续、高效利用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促进团场职工稳定增产增收、快速致富。
让兵团文化蓬勃发展
4月24日,八师、石河子市中影文化广场城市文化综合体项目在石河子总场北泉镇开工建设。该项目汇集了电影院线、文化产业基地、超市、酒楼、动漫城、精品商业街、美食酒吧街等商业形态,预计将于2014年年底建成,2015年投入运营。
作为城市文化商业综合体,中影文化广场将文化、商业、生活组合形成良性的互动,它的建成,不仅能提升石河子的城市旅游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的活力,更将对八师、石河子市乃至兵团的文化生活全面升级和优化起到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