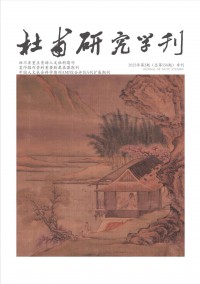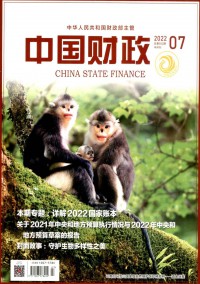三十年是什么婚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三十年是什么婚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三十年是什么婚范文第1篇
结婚23年是绿玉婚。绿玉婚含义:绿玉,牡丹名品之一。绿色花系,绣球型。初开绿色,盛开粉绿色。茎短。梗长。叶大而尖。株型半开张,分枝力强,花期中。因此形容婚姻坚强而独立,稳固而永久。
结婚23年周年祝福语:
1、装满一车幸福,让平安开道;抛弃一切烦恼,让快乐与您环绕;存储所有温暖,将寒冷赶跑;释放一 生真情,让幸福永远对你微笑。
2、在这喜庆祝福的时刻,愿神引导你们的婚姻,如河水流归大海,成为一体,不再是二,并且奔腾 不已,生生不息。
(来源:文章屋网 )
三十年是什么婚范文第2篇
宋玉说:“我们登记。”男的没抬头,问:“你们登多少钱的记?”宋玉和孟倩倩疑惑不解。男的指指窗口玻璃上贴的一张纸。纸上写着:一千元、五百元、一百元、五十元、免费、奖励一百元。金额后分别写着: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孟倩倩问:“这是什么意思?”窗口里那个女的抹一把脸上的汗说:“你们也看到了,来我们这里的人非常多。现在的人好像都喜欢结了婚就离婚,离了婚又结婚,不瞒你说,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工作的。经常有同志累得在岗位上吐血。所以,为了尽可能维护我们的健康,有关部门新出台了这项规定,结婚时间短的收费就高些,反之,就低些。如果二十年不离婚,那就免费,如果三十年不离婚,我们还会额外奖励一百元。你们俩准备几年后离婚?”
宋玉说:“我说几年就几年吗?这事情谁也说不清楚啊。”男的说:“是这样,我们实行多退少补、违约加罚的原则。如果你登记五年的婚姻,结果三年就来离婚,那么我们不仅要加收差额,而且要加倍罚款。现在你们明白了吗?”宋玉和孟倩倩同时说:“明白了。”窗口里的两个工作人员也同时说:“好,你们商量一下,别急着做决定。”
宋玉和孟倩倩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登记五年的婚姻。窗口里的那个男的冲着旁边的一个门指指:“好,你们去那个屋,宣一下誓。”
宋玉和孟倩倩离开窗口,推开宣誓室的门,屋里坐着一个老太太,很庄严。老太太说:“我们也知道宣誓这东西没什么用,但还是搞一下好。调查表明,宣过誓的夫妻与没宣过誓的夫妻相比,婚姻解体的时间大约可以延迟五至六个月。”
老太太问:“你们的姓名?”宋玉和孟倩倩说了。老太太说:“首先请你们俩如实回答下面的问题。你们是自愿结婚的吗?”宋玉和孟倩倩刚要回答,老太太摆摆手:“有三个答案供你们选择。A、自愿。B、不自愿。C、说不清楚。”宋玉和孟倩倩同时选择了C。
老太太问:“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你们能做到吗?A、能做到。B、做不到。C、看情况而定。”宋玉和孟倩倩同时选择了C。
老太太问:“夫妻双方有互相扶养、照顾的义务,你们能做到吗?A、能做到。B、做不到。C、到时候再说。”宋玉和孟倩倩同时选择了C。
老太太问:“你们能自始至终地善待双方的老人吗?A、能。B、不能。C、给钱就能,不给钱不能。”宋玉和孟倩倩同时选择了C。
老太太问:“你们能忠于对方吗?A、能。B、不能。C、不知道。”宋玉和孟倩倩同时选择了C。
老太太问:“你们信仰上帝吗?”宋玉和孟倩倩点点头。
三十年是什么婚范文第3篇
比如,她会把放在你面前的一碗肉换到她儿子面前。我发誓,我对那盘肉不感兴趣,只是忍不住会叹息一个女人的爱为何这样狭小。
这种事情在某一段时间内频频发生,那时我刚刚进入婚姻第二年。我安抚自己说这其实无所谓,可失落感日复一日地浸润进来。婆婆的举动告诉我,她和她的儿子有共同生活亲密无间的三十年。我是外来者,是一只被主人遗落的小狗,在餐桌上看着他们相亲相爱,无法逃避。
可是,我的爱情在这里开花结果,我为什么要那么自觉地让开。
有段时间我非常想回家,想爸爸妈妈。他们会把餐桌上的一切决定权都交给我,我爱吃什么,桌上摆的就是什么。他们会相当积极地洗我的衣服。脸色有一点倦怠就到处给我找药吃,还会为了让我吃什么药产生争执。
我安心地接受着父母的照顾,和别人的爸妈住一起时的孤独感与之形成巨大落差。我开始觉得自己命苦,如果再次选择我一定不会再结婚。向老公倾吐这种感受后,他把这个问题看作我与他之间的事,永远不会往父母那处去想。
他是我最亲密的人,却没法理解我。我开始讨厌回家,回家是一种负罪,我超越常人地喜欢工作,巴不得天天都上班。上班让我觉得更加轻松自在。
有一次在一个同学会的饭桌上,女同学们都在讲自己的婆婆,个个苦大仇深,彼此抱团求安慰。我坐在旁边一声没吭,看着身边这些曾经那么可爱的ABCDE的表情,突然觉得很狰狞。这种狰狞的面目让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
当我三十年媳妇熬成婆后,会不会重复上演对儿子独占欲的戏码?我的内心与她们相差无几,也曾如此狰狞地声讨过另一个母亲。
我发现我们容不下的不是婆婆太爱自己的儿子,而是她怎么不爱我?不关心我?不主动给我添菜?不主动帮我洗衣服?
我们容不下她们为何不先于我们表达爱。这是我们这代人的通病,不太会为别人着想,总想着改变别人,不想着改变自己。
春节带儿子回娘家看父母。母亲很细心地问我生活的各个角落,谁洗衣服?谁做饭?我一一回答。问到儿子晚上跟谁睡觉时,我回答说:“儿子跟我睡。”这时候我发现妈妈的表情,一种被伤害的样子。
第二天,我听到母亲和儿子的对话:“你以后不要跟妈妈睡觉嘛,跟你奶奶睡觉,你看你妈妈上班多累啊?”儿子稚声稚气地拒绝:“不行,我要跟妈妈睡觉!”母亲百折不挠:“你要懂事,你要心疼妈妈。”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感性地讲,为一个母亲的百折不挠有点堕落的爱;理性地讲,我开始理解婆婆。
后来我出差,老公带了全家老小送我到机场。临别时儿子跟我拥抱,老公跟我拥抱,婆婆站在旁边讪讪的样子。我走过去抱了抱她。
她说:路上小心,早点回来。
三十年是什么婚范文第4篇
昨晚,我陪年过八十的父亲喝了点酒,算是过年。――真正隆重的仪式,还要等25天后的农历春节。天冷,父亲在我这里并不冷。我住的楼房里有暖气,不像老家的寒舍。
现居城里,心却总还张望着东南方向的老家。那片熟悉的土地上,不,是土地下,有母亲独居的房子。母亲,正值数九寒天,您那里冷吗?三十个年头了,虽然,只有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十月一,您的子孙才定期来给您打扫卫生,送钱送物,但我们从来就不曾忘记您啊。
还是按农历说吧。四十二年前,四十二岁的母亲开始孕育我。命运无情,我们母子只在一起生活了短暂的十二年。这十二年,包括我有记忆能力前的三四年,也包括母亲患病后直至辞世,神智如小孩的一两年。但四十多年来的生活阅历告诉我,母亲给予我的已足够多。她那温暖的目光,穿越三十年的时光隧道,一直投射到遥远的未来,始终在为我,为她所有的子女探路、护航。
1.母亲的饭桌
母亲的饭桌在哪里?母亲有饭桌吗?有的,有的。母亲的饭桌在忙碌的田间地头,是树荫下,那托着粗瓷大碗的手掌。这本是一双细腻的玉手,却捆扎了太多艰难的日子。它,晒黑了,粗糙如沙石,干裂似旱泥,却是我最好的“痒痒挠”,无指甲的利刃,多催眠的熨帖。
母亲的饭桌是那面烙饼的鏊子。烙出的饼,大的是煎饼,地瓜面的,有时也掺点棒子面,高粱面的好像也有过,但绝少纯棒子面的。小的就是麦子面做的白面饼,在小鏊子上烙的。如果烙白面饼,母亲就有桌无饭了。白面饼都是烙给别人吃的,帮忙杀麻的,盖房的,垒墙的,推土推粪的,干的全是力气活,需要最好的招待,有着最大的饭量。收成好的年月,偶尔也烙过一两回油饼、菜饼,但不多见。
母亲的饭桌是那烟熏火燎的泥巴灶台。仅有的一点饭菜,全端到了堂屋里,供那些苦中作乐的客人们猜拳行令,母亲便在灶前凑合一点了事。
总之,母亲的饭桌不讲条件,不选地点,因陋就简,随处可用,但始终摆满了劳累,一直支在老家那盏昏暗的油灯下,支在三十年前发黄的乡下记忆里。那上面,唯一的一点调味品,就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缕希冀。可是,很快,母亲的饭桌就移到了医院里。三年里,两度脑溢血。多亏一位“德医双馨”的大夫,母亲吃饭的方式才由输液恢复到从前。那位大夫姓秦,是一位手艺精湛的“厨师”啊。但第二次病后的母亲,半身不遂,仅有一只手能拿东西,成了她特有的饭勺和筷子。病床就成了母亲离不开的餐桌。
当生活的春风终于刮来的时候,时令却转向萧瑟的晚秋。母亲的儿女们个个捶胸顿足,不得不把她送出家门,在西南坡族林里,给她建了新房,支起了供桌。此后,母亲就开始享有一个巨大的饭桌――坟前的一片沃野,稳如磐石,已经三十年的风霜。今天,我庆幸母亲有福,不像许多城里人,生前日子过得拥挤,死后还要在公共墓地里排队编号,才住得上一平米的小屋,能安多大的饭桌?特别是环顾皆石碑,多为异乡魂,总缺了叶落归根的安然。
三十年沧桑,母亲的饭桌上不停地变换着饭食,而且越变越好。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而今,跨过不惑之门,又添了两岁的我,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后,忽然又有所悟:其实,母亲的饭桌何曾离开过我。
2.母亲的小脚
母亲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农村,和当时所有的同龄妇女一样,裹一双尖尖小脚是自然的。母亲洗脚时,我蹲在旁边,看得仔细,但我不愿意用语言来形容它。那畸形的小脚,长在母亲身上,却一直是我心底的痛,也有莫名的恨。痛,却无可奈何;恨,又不知恨谁。我好像问过母亲,把好好的脚裹成这样,疼不疼。母亲说,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裹,一开始很疼,得扶着墙走路。后来,慢慢地就不疼了,就长成这个样子了。记忆有些模糊,大体是这样的对话。“很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时母亲有多大?不得而知。但这并没有模糊我对这双小脚的记忆。
脚是用来走路的。走路,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地量自己的人生。这与脚的大小没有关系。再长的人生,用再小的脚也能量完。即使一个人病瘫在床,如母亲。“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说得对极了。
母亲除了瘫在床上的日子,一双小脚始终在追赶生活,一步也没落下。母亲走直线,从家门到田野,来来回回,不记得留下了多少个脚印。母亲也走曲线,上湾西崖的自留地,得沿歪歪斜斜的湾边小路,绕过庙前的石桥,不记得留下了多少个脚印。母亲走的更多的是圆圈,去湾边打场,到街心轧碾,在家里推磨,脚印连着脚印,脚印摞着脚印,有多少个,也不记得。但我记得那急促的脚步声,如出兵的战鼓。因为一双小脚走起路来,主要靠脚跟用力,如棍杵地,所以这面战鼓声音沉重而不够浑厚,无美感而更颤动人心。仅脚跟着地,稳不稳,累不累?人生路上,坎坷多着呢。母亲就用这样一双小脚,急匆匆走完了她五十五年的人生之旅。在她身后,我们学她走直线,一如她的为人;学她走曲线,一如她的处事;学她走圆圈,一如她的毅力。
母亲的小脚迈出的也不全是急促的步伐,也有悠闲的散步,那是照看儿孙的时候。“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此时的母亲,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母亲从没听过这首歌,也从没到过海边。她的身后没有蓝天碧海,白浪逐沙,没有暖暖的澎湖。还有,母亲是不用拐杖的,尽管她是小脚。如果挽儿孙于沙滩上,会留下什么样的脚印呢?也如棍杵地么?如今,她最小的孙子――我的儿子,已上了大学,她的孙辈有的也有了孩子,并上了小学。他们是否愿意再听一听,二十多年前,那首风行大陆的台湾校园歌曲?
3.母亲的大袄
母亲有多少衣服?我不知道。我只记得她的大袄。虽然这是一件经年未拆未洗,积满生活尘土和岁月沧桑的旧式大襟棉袄,失去了当初的新鲜柔软,但在三十年前的十几个春秋里,却一直在为我遮风避雨。它传递的温暖,如同一曲《妈妈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三十年来,这首歌,在我的耳边循环播放,眼前就再现出“老鹰叼小鸡”的游戏。那老母鸡张开的双翅,就是母亲的大袄啊。有了这双翅膀,再凶猛的老鹰也休想叼去那些嗷嗷待哺的孱弱小鸡。
母亲是个勤快的人,手也巧,但就是来不及拆洗自己的大袄。农活如赶集,家务似织梭,还有多少时间,多大精力?何况那么多孩子需要照顾,哪一个不是她的一根手指啊。所以,母亲就只能披着旧大袄拾瓜干,走磨道,在黄昏的门口呼唤儿孙倦鸟归巢。
母亲不识字,当然无从知道孟郊的《游子吟》。我们做子女的,在母亲生前,也从未有过游子般的远行。但我们知道,母亲的针脚,缝补了多少个艰难的日子,缝起了一个虽然贫穷但不失温馨的大家庭。其实,三十年前的少年,长大了后就紧随时代,穿上了西装,根本用不着母亲的针线了。而今,我迈过新年的门槛,依然看见,远隔了三十年的母亲,站在时光的那头,脚踩田塍,手遮额头,还在翘首远望渐行渐远的儿女……
4.母亲的旅行
三哥当工人后,在1976年,或1977年,借了一辆自行车回家,接母亲去他们厂宿舍待过几天。这恐怕是母亲一生唯一的一次远行了。尽管三哥所在的厂子那时还属城郊,离县城还有几里,但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还是了却了一大心愿。近百里的路程(那时老家未通公路,进城要绕很远的道),填补了母亲五十多年的人生空白。感谢三哥,再晚一年,瘫在床上的母亲,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还有别的旅行吗?那次二哥用一辆独轮车,推着母亲和我,或许还有四哥,去二十里外的公社驻地,找在那里干厨师的大哥,算旅行吗?母亲回娘家,或走亲戚,也算旅行吗?母亲的世界就这么大。母亲能否忍受,今天的年轻人看待这段历史的怪异目光?
母亲知道吗,她最小的儿子,我,在她去世后第四个年头,进县城读了高中;第七个年头,到泰山脚下读了大学。此后,虽然一直受制于“孔方兄”和时间老人,但后来毕竟也进过省城,去过青岛,看过威海,到过沈阳,游过微山湖,也在南京、上海、苏州、太湖开过眼界。我知道,凡是我到过的地方,母亲就到过。我就是母亲的眼睛啊!
其实,我与母亲是常见面的,在梦里。阴阳两隔,母亲来看我,她那双小脚要走多少路?这也算是旅行吗?她可是不会骑车,也无车可骑,更未打过“的”。乡下人也能够打“的”,而且如平常事,这在母亲生前,是想也想不到的。
成天“胡思乱想”,我素有的头痛,便痛得更多,更痛。很多时候,是工作劳累、生活挤压引发痼疾,但有时也属“虚病”,多方求医,均不奏效。后来有人指点,是母亲惦记我,看我来了。便试着用了“虚法”,送别了母亲,果然不再头痛了。前段时间,我去北京,参加“复兴之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文学创作研讨会暨颁奖大会,乘机游览了故宫、鸟巢、水立方,登上了长城。不敢说品尝到了“跻身皇城,俯瞰天下”的滋味,但“漫步京华,一睹神圣”,母子两代人八十多年的梦想,实现了。那几天,我又头痛,是母亲又随我来了。母亲,如果您真能来,即便是再头痛,我也愿意陪您到处转转,看看北京的门、北京的桥,看看故宫、颐和园,看看天安门前的像,看看深秋的红叶满香山……
5.母亲的生日
母亲的生日?太陌生了!
母亲的生日,我们谁都没有记住,或许母亲从来没有提过。母亲生前走过的五十多个春秋,不是战乱,就是贫穷,有天灾,也有人祸。再加上我们的家庭和国家一样,人口多,底子薄,天天忙吃忙穿,日子还是过得捉襟见肘。母亲还过什么生日?母亲无暇提起,大家顾不上问,母亲的生日便最终掩埋于一黄土之下,消散于历史的烟雨之中。
其实,母亲说过,孩生日,娘苦日。我一直记着这句话。所以,这些年来,我拒绝流俗,从不给儿子过生日。我告诉他,“孩生日,娘苦日”。你的生日不值得庆贺,而应该感恩。细想想,不是这样吗?可如今还有多少人这样想呢?又想起从前听到的一句“怪话”:“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父母。”怪话不怪哩!
给老人祝寿,我不反对,不仅不反对,还举双手赞成。给老人祝寿,是感恩,其实也是教育孩子。把“恩”字拆开来,不就是“因心”而生吗?我们兄弟轮流养老,父亲在哪,寿宴就在哪。去年中秋夜,望着那轮圆月,我写下一首《中秋的圆桌》:
母亲走了
来不及再看一眼
那轮明月
父亲赶紧过来
支起拜月的圆桌
我们大了
圆桌上射出
一支支箭
落在
我们的小家
反射的目光
却总被月光淹没
父亲老了
一年一度
看这圆桌
在我们中间
来回穿梭
一晃三十年
月光
一直燃着
圆桌上的香火
连月饼都知道
父亲在哪
哪里就有一轮明月
我们给父亲祝寿,其实也是给母亲祝寿。
6.母亲的照片
我从未见过母亲的照片,或许,母亲从来就没照过相。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习以为常的。但如母亲一般年纪的人,即使在三十年前,照张相也并非绝不可能。历史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母亲的照片也能算个谜团吗?三十年过去了,母亲知道照片还能带彩么?知道手机也能拍照么?知道寻常家庭也能够自拍DV么?母亲给我们留下的遗憾太多,太多。可是,她自己认为是遗憾么?
八年前,父亲的生日,我们照“全家福”。二哥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说,给父亲单独照张相。话没说透,但我明白,不能让当时已七十三岁的父亲再留遗憾。我不认为这是在咒父亲。如果有人认为是咒的话,那就“咒一咒,十年寿”。孝顺的方式、形式,有时似乎不合常理。
尽管母亲一生没留下照片,但青春易逝,岁月可流,母亲的音容却永远定格在儿女的心底,清晰不变,直到永远。可是,孙辈呢?母亲去世时,我二哥的儿子才周岁多点,根本不记事;三哥尚未结婚,四哥与我均未成年,我们大家庭后添的新成员,就只能从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母亲的容貌。只是,他们是否有倾听的欲望。先前的故事,能够吹动他们心海微澜吗?
记住自己的先人,就记住了自家的历史。如同牢记祖国的历史,就能更好地把握住现在和未来。不忘记过去,就永远不会“背叛”。责任,不是大而空洞的一个字眼,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番说教,不是人为戴上的一副枷锁。忘了它,就会迷失自我,如断线风筝,水上浮萍。
借助以上文字,一来宣泄一下我的激情,二是给母亲拍个照,送给晚辈。
独轮车
车轮滚滚,似看得见的时光。从骑自行车,到驾驶摩托车、电动车、小汽车,对寻常百姓而言,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如同吃惯了大鱼大肉而觅野菜,久离泥土的双脚,又丈量起宽阔的马路来,连梢头的清风,桥下的流水,都猜得透养生的心情。路,永远走不完。这双脚,还能走到从前吗?
记忆的源头总是泥土。发黄的背景下,土路上,隐约走来一辆独轮推车。两千多年了,你,依然不停地向前走着,走着。老胳膊老腿了,吱吱扭扭,看得出你满怀疲惫。远处,费翔唱着一曲《故乡的云》。你的双臂已经磨得光滑,车襻是你的领带,浸透了汗渍,早不见了往昔的容颜。好在近期你才换了双新鞋――胶轮替下了木轮。抖落肩头层层堆积的战争硝烟,重新沐浴着和平的阳光,你一直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刚刚记事的我面前。推土,推粪,推粮食,推柴火,进进出出,来来往往,从庄户小院到田间地头,日复一日,可曾如诗人一般叹息“年年岁岁花相似”?负重的间隙,你也总闲不住,不是驮着老人小孩悠闲地走亲戚,就是载着病人伤者奔医院。隔一层红被,替一顶旧式花轿沾沾新娘子的“鲜”,估计也是有的,只是不曾亲见。
相传,是诸葛亮生下的你。走遍蜀道之难,黯淡了刀光剑影。替一代贤相出力,理应心甘。但是,这能掐会算的老头儿,可曾料到,你“木牛流马”的使命这么悠长,悠长,而又寂寥,全然不似戴望舒的雨巷,你的主人也从没有那“撑着油纸伞”的闲情。你的大哥是两轮的地排,他从很早的岁月就在部队服役,跟叱咤疆场的将军猛士一起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也曾被改成四轮,伴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共赴秦楼楚馆,笙歌曼舞。后来老了,牵走驾辕的战马,卸去炫耀的装饰,他又走进民间,忙在田间。当然,作为兄长,他比你载得早,载得多,也比你受礼遇,他多次被毛驴拉着,穿梭在乡间,办些应急的事儿。
三十年是什么婚范文第5篇
你幸福吗?你穿着Prada,拎着爱马仕,开着保时捷,住着纳帕,喝着拉菲,你幸福吗?就好像最近网上流传的狗与狼的对话―狗:我有房子你有吗?狼:没有。狗:我有狗粮你有吗?狼:没有。狗:我有户口你有吗?狼:没有。狗:我有医院你有吗?狼:没有。狗:我有干爸你有吗?狼:没有。狗:我有LV包你有吗?狼:没有。狗:我有玛莎拉蒂跑车你有吗?狼:没有。狗:那你有什么呢?狼:自由……
为财富打拼了三十年,温良恭俭让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刚刚全面爆发了对财富的热情,却又在“幸福”二字面前怅然若失。你有很多东西,你有的东西郭美美们也有了,那么,你凭什么说你幸福呢?更架不住的是,郭美美们有的东西,恐怕你还没有,你的幸福又是什么?即使你比郭美美拥有的还多,你的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只狗的幸福呢?
正如欧阳锋,为“天下第一”打拼多年,忽然被普普通通的“你是谁”问得神智昏迷无法自拔。你有很多武功,也可能天下第一,但是天下第一又是谁呢?
你幸福吗?你有房有车有钱有粮,但是你不敢生病,害怕医生乱开药乱开刀;你也不敢帮人治病,害怕病人拿刀来砍你;你不敢结婚,害怕《婚姻法》,害怕太过投入婚姻最后净身出户;你不敢生孩子,害怕成为孩奴,害怕找妇产医院,找学校,找老师,害怕孩子“拼爹”;你甚至不敢想未来,不敢变老,害怕成为无人来扶的老人,不敢设想70年后自己的房子会归谁所有……
与“你幸福吗?”给你带来的不知所措、莫可名状相比,“你痛苦吗?”可能是更现实的一句设问:《福布斯》2011年度“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第二次高居榜眼位置,“痛苦”这个词开始有了更具体的含义。尽管国家税务总局以最高效的方式回应了这条新闻,纳税人的痛苦与困惑并没有得到丝毫消减。
按照“税收技术”的名言,“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哥尔柏),中国的纳税人此次感到痛苦,发出震耳欲聋的“鹅鸣”,并不是因为毛拔多了,而是因为知道毛拔多了,而且不清楚毛的去向。税务部门的人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们一直这样拔毛,以前鹅闭着眼睛,并不叫,或者叫得并不凶,现在突然睁开眼来,突然叫得很凶,真让人很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单纯解释我们并没有拔太多恐怕没有用,因为眼睛睁开了,就很难闭上了,要想减少鹅鸣,两个办法:一是切实减税,二是让鹅们知道每一根拔下来的毛都去了哪里,是不是都利益了众生,是不是让鹅们的幸福不再含糊,看病生孩子养老不再含糊……只要说得清道得明,拔更多的毛,鹅们也会赞成。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