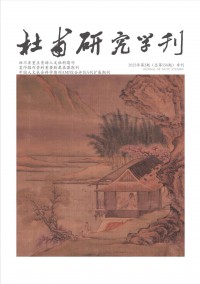写给父亲的诗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写给父亲的诗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写给父亲的诗范文第1篇
1、《父亲写的散文诗》是一首由董玉方作词,许飞作曲、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将父亲对子女的爱与责任,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父亲已老的无奈诠释得丝丝入扣。
2、2017年3月14日,音乐人李健自弹自唱,翻唱了这首歌。同年6月份姚晨在《跨界歌王》半决赛中翻唱该曲。
(来源:文章屋网 )
写给父亲的诗范文第2篇
离乡背井赴京寻梦
唐良超,1985年8月出生于湖北仙桃一个小乡村里,是家里的长子。母亲怀着他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穿着白色长袍摇着扇子的人。她把梦跟村里的民办教师一说。老师想了想,说:“这是古代文士的打扮,你儿子这是文曲星下凡啊!”
唐良超一上学,果然表现出非凡的文学天赋,参加乡里作文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初一那年,唐良超第一次接触到了诗,那是刊登在某本发行量很大的文摘刊物上的一首席慕容的诗。唐良超看完之后怔住了,原来世界上有这么美的文字。从此,唐良超爱诗歌爱得如痴如狂,每当翻开一本书一本杂志,都先去找有没有诗歌。就这样,他慢慢接触到郭沫若、臧克家、艾青这些老一辈诗人的诗作,他也爱看鲁迅的诗,觉得他的诗很有力量。
上高中之后,唐良超又阅读了舒婷、北岛、芒克这些现代诗人的诗,开阔了眼界。有一天,他看到了海子的诗,被深深震撼了。尤其是那首《祖国(或以梦为马)》,他至今都能倒背如流: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
唐良超知道海子是在北京上的大学,从此,北京成为唐良超心目中的诗歌圣地。他一定要去北京。2003年,唐良超考上了大学,可惜不在北京,而是湖北当地的一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唐良超读的是新闻专业,诗歌写作和新闻写作看上去都是文字工作,其实差别很大,甚至可以说是天渊之别。新闻写作要求作者冷静客观,诗歌写作却要求作者追求个性诗情澎湃。
唐良超感受到了撕裂的痛苦。白天他认真地完成学业,晚上追逐他的诗歌梦想,躲在被窝里写诗。他加入了学校的诗歌社,认识了一批诗友,大家一起谈诗论文。
大三的时候,父亲赶到学校,说已经托人在当地电视台给他找了实习的岗位。但唐良超拒绝了,他去找了当地的日报副刊部实习,还在上面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
就在唐良超大学毕业的时候,噩耗传来,母亲因患重病离开了人世。失去了一直关爱自己、十分支持自己写作的母亲,唐良超在学校里大哭了一场,在回家的车上又忍不住泪如雨下。
安葬了母亲之后,对于以后的人生道路,唐良超和父亲有一次正式的对话,父亲希望唐良超能在当地找一份工作,再找机会以后自己出来做生意。
唐良超拒绝了父亲对他的人生安排,他要去北京追逐他的诗歌梦。去北京之前,唐良超在母亲的坟头坐了一天,他把那年母亲节写给母亲的诗《有关我母亲的一切》,工工整整地抄在纸上,烧给母亲,他相信母亲在天上看着他,也看见了他写给她的诗。
2006年9月,唐良超坐上了北上的列车,他激动地想:北京,我终于来了!窗外是北方大地广阔的平原,景色那么新鲜,唐良超心里十分兴奋,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车上的一夜他几乎没有合眼。
唐良超拖着四个包走出北京站。他带着一年四季的衣服,分别装在四个包里,他给四个包取名叫“春、夏、秋、冬”。
唐良超站在北京站口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四个包像四个孤儿一样围在他脚边。首先要解决住的地方,他身上只带了几百块钱,住不起旅馆。他在火车站旁边找了个网吧,上求职网站投了很多份简历。当天晚上就睡在网吧里,他怕“春夏秋冬”丢了,特意解下皮带一头拴着四个包,一头缠在皮带扣上。谁知第二天醒来,包还是丢了——皮带被人剪断了。
唐良超只好和网友联系。有个网友在圆明园旁边的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卖花。唐良超去跟他挤一张床,夜里热得要死。
唐良超在网上找了一个零工,在一个叫Mao的酒吧里做服务员,每天要干到凌晨两三点。回家的公交车早就没有了,唐良超又舍不得打车,他就趴在酒吧的桌子上睡,第二天接着干活,这样也不用回去跟网友挤一张床。
在朋友的介绍下,唐良超还给朱哲琴的演唱会打过零工,干了一晚上杂活,赚了200块钱。唐良超很开心,第二天请他刚刚结识的诗友们吃路边摊。一群人一顿饭就把200块钱吃完了。
2006年底,眼看春节就要来了,唐良超在酒吧拿的工资刚够他付房租吃饭,买不起回家的车票。唐良超不敢给父亲打电话,只发了一条短信拜年,告诉父亲今年就不回家过年了。父亲当天没有回复,唐良超安慰自己说,这是因为父亲不会发短信。第二天一早,父亲的电话就追来了,父亲在电话里严厉地说,今年不回家的话以后也别回家了!
唐良超向朋友借了钱,置办了一身新衣,还特意买了一双皮鞋。父亲喜欢他穿皮鞋,说这样才有气派。
回到家,唐良超发现等待他的是一场劝导会,父亲请了好多亲戚过来,希望他好好想想以后的人生,做什么北漂,没有户口没有身份,将来娶妻生子都成问题。
唐良超有个弟弟,比他小三岁,高中毕业后在家人的帮助下开了个驾校,收入不错。父亲就拿弟弟和他作对比。唐良超很为弟弟的成就感到高兴,他跟父亲还有各位亲戚说,人各有志,强扭的瓜不甜,他这一辈子就是要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做一个诗人!当天晚上,弟弟给唐良超发来一条短信:“哥,你文艺!”唐良超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第二天,唐良超又坐上了北上的列车。
负债几万女友离开
2007年5月,唐良超在诗友的介绍下进了一家杂志社做编辑。主编很器重他,让他负责主要版面,做知名文化人物的访谈。唐良超喜欢热闹,喜欢和人打交道,这份工作他干得风生水起。杂志社的收入不算高,但至少是一份稳定的收入。他在单位附近租了个地下室。
写给父亲的诗范文第3篇
清晰的,
绝望与悲伤
撕裂了四川的大地;
挤压着汶川的楼房。
沉重的,
却又无比伟大,
像那些夜以继日,
不休不眠的救灾者;
像那位放弃了亲情,
却换回了数十个稚幼生命的无私父亲;
还有那位弯身跪地,
以身躯擎起自己孩子生的天空的伟大母亲。
时光,
销蚀着无数生命,
可他们坚持着、坚强着,
创造一个又一个生之奇迹。
在那成为了历史的繁荣里,
蜷曲着一个又一个哭泣的身躯,
可他们却坚韧无比,
在蒙着双目
被抬出一片废墟的那一瞬——
生命之火,
再度激昂地跳跃了。
获得幸运需要幸运
并非每个人都拥有幸福。
于是数以万计的人
永远地逝去了。
死亡在全世界的默哀中,
死亡在全国的泪水中,
死亡在整个四川的悲剧中。
但,这并非是绝望的弥留
在那疼痛无比的呜咽里
看见了,
看见了,那绚烂无比的云雀,
一飞冲天,
又婉转徘徊。
是光明,
带着希冀与笑靥
引领那些无辜纯洁而又苦难流连的灵魂,
向着那
向着那,在没有灾情的天堂。
飞去了……
写给父亲的诗范文第4篇
悲痛的母亲在整理儿子的遗物时,发现了笔记本里面让她心酸的一页。这页纸被王硕用一根竖线分成左右两栏。左边是“死的理由”,有6条,包括:得病、高考、休学、退学、高中乐悲参半,最后一条是“没有追喜欢的女孩,只会偶尔揪她的辫子”。右边是“活的理由”,如燕(我猜应该是他喜欢的女孩名字吧)、NBA、伦敦奥运会、动漫、棋、武林外传、电影……总共有23条之多。让人难过的是,23条“活的理由”终究在内心的天平中没有压倒6条“死的理由”。
也许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想象中的纯洁和完美。1918年11月初,梁济60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11月7日,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后,即民国七年十一月十日,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
父亲的自杀对经年进行人生思考也想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他开始用一生研究“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样一个深奥的人生哲学课题。“人的一生要解决三个关系。首先是,人和物的关系;再次是,人和人的关系;最后是,人和内心的关系。”这是他得出的结论。懂得担当的梁漱溟用95岁的高寿完成了当年对父亲所言 “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的行为证明。1983年,美国学者艾恺教授对梁漱溟进行连续十余次访谈。后来,30多小时的录音被整理成一本书,名字就叫《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书中有这样一段易懂却引人深思的话:吃饭好好吃,睡觉好好睡,走路好好走,说话好好说,去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美,越来越好。
1995年,37岁的几米遇到人生的一个重大事件,罹患血癌,凭借对美好世界的热爱和内心强大的力量,最终战胜病魔,在生命的长河中逆流而上,成为台湾最著名的绘本作家。几米在自己的作品《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里写下这样的话:落入深井,我大声呼喊,等待救援……天黑了,黯然低头,才发现水面满是闪烁的星光。我总在最深的绝望里,遇见最美丽的惊喜。我在冰封的深海,找寻希望的缺口。却在午夜惊醒时,蓦然瞥见绝美的月光。
“我有着向命运挑战的个性,虽是屡经挫败,我决不轻从。我能顽强地活着,活到现在,就在于:相信未来,热爱生命。”上面的诗句是诗人食指写给自己的内心,也是写给世界上每一个追问人生意义的人。
写给父亲的诗范文第5篇
在自己的家中感受不到温暖和爱的柯勒律治羡慕的不仅是这对兄妹之间的亲情,更多的是这对兄妹在诗歌创作上的默契与合力,更准确些说,是多萝茜对诗人兄长的助力。
失去与寻找
多萝茜有两个哥哥,理查德和威廉,两个弟弟,约翰与克里斯托弗。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英国湖区考克茅斯镇上最好的房子是她与兄弟们短暂美好童年的见证。当律师的父亲与富商女儿的母亲给他们提供了优裕的成长环境。
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她不仅受父母宠爱,还得到了兄弟们的爱护。若非家庭变故,这位中产阶级的女孩儿本可以一直过着公主一样的生活直到长大嫁人。她或许也会如简奥斯丁一样,以针线活为遮掩,书写自己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但对于多萝茜而言,在短暂的幸福童年之后,在她与哥哥重聚之前,十几年的时间里都活在这些悲剧与泪水中。
6岁时,母亲病逝,家中无一女眷,父亲把多萝茜送到姨妈家。然而这一别,直到五年后父亲病逝,她也再没回过家中。父亲走后,他所服务的罗德老爷不归还欠发工资的不义行动让这几个孩子不仅失去了父母双亲这片天,而且也失去了获得任何遗产(包括房子)的可能。
多萝茜和兄弟们很长一段时间无家可归。1794年,还未满23岁的多萝茜从亲戚家奔向已经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兄长威廉,他们在湖区、多赛特郡等地漂泊。经济来源多是兄长朋友的资助。他们不停地在寻找家园,又不停地失去家园。成年后的兄妹在不断寻找一个能将他们带回到失去的家园、补偿失去父母之痛的地方。
威廉想成为一名诗人,与舅舅对他投身宗教的期望完全相反,除了梦想,他一无所有。多萝茜在哥哥身边,鼓励他,批评他,他是华兹华斯的作品最早最客观的评论者之一。她与他一起守护着他的诗人梦想,一起寻找与修复华兹华斯在变质的法国大革命中受重创的理想与心。
多萝西曾经在与好友简波拉德的书信中说威廉具备她其他几个兄弟所共有的所有美德,即坚持、真诚,然而最吸引她的是威廉在所喜爱的事物面前所自然流露出的那种爱的力度,他对事物的一种“不安的警觉性”,一种永不褪去的柔情,还有说话、做事时的谨慎。
而华兹华斯在他著名的自传长诗《序曲》回溯妹妹在自己迷茫岁月中的作用时,这样说:“是她/使我保持了与真实自我的联络,/因此将我拯救。”(丁宏为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创作也是兄妹两人重建家园的努力之一。
华兹华斯喜欢他这位唯一的妹妹在诗歌阅读上的品味与鉴赏能力,他欣赏并且羡慕她所具有的异常敏感的诗人一般的眼睛与耳朵。他在妹妹这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创作的灵感,更多的是一种让他坚持做诗人的力量,是一份让他不畏外在世界与言论的安心。
他另一诗作《埃斯威特山谷》(The Vale of Esthwaite),一首国内读者鲜少读到的诗中曾经这样写多萝茜:“我爱着的妹妹/她深深温暖了一位兄长的心。”
这对在苦难中团聚的兄妹最终在诗作、在湖区格拉斯米尔的安稳中慢慢擦干童年的眼泪。有心的读者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寻得淡淡的泪痕。
“她给我一双耳朵,一双眼”
多萝茜对自然万物的敏感,细缜的观察力得到了她的诗人兄长以及他们共同的好友柯勒律治的赞美。他们在英国南部时经常三个人一起散步,一起讨论。多萝茜说他们是三个身体,一个灵魂。他们三个友谊的巅峰也是两位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创作的巅峰时期。
多萝茜写日志,两个大诗人阅读。多萝茜初始记录日志时并未想着出版,她最初写只是为了“给威廉一些乐子”。而多萝茜没有想到的是,无论对于华兹华斯还是对柯勒律治,这渐渐成了他们创作的灵感来源。
读者所熟悉的《咏水仙》中有这样的诗句:“蓦然举目,我望见一丛/金黄的水仙,缤纷茂密;/在湖水之滨,树荫之下,/正随风摇曳,舞姿潇洒……摇颤着(tossing)花冠,轻盈飘舞(dance)。/湖面的涟漪也迎风起舞,/水仙的欢悦却胜似涟漪;有了这样愉快的伴侣,/诗人怎能不心旷神怡(gay)!”(杨德豫 译)华兹华斯早年的《夜景》(A Night-piece)与多萝西在英国南部的日志《埃尔福克斯顿日志》中的记载一一呼应。他的《孤独割麦女》也是c妹妹的《苏格兰游记日志》中的记载呼应。
很多时候真分不清是妹妹参考了哥哥,还是哥哥参考了妹妹。然而,这些或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位心灵都是诗心,所以才可以如此默契与相通。
华兹华斯的诗歌与妹妹的日志似乎成了彼此的注脚。一个是散文化的诗,一个是诗化的散文。华兹华斯在很多场合下表示过他对多萝茜在自然中的观察与回应之敏感与细致的羡慕之情。他在《麻雀窝》中写她还是“口齿不清的小姑娘”时,对鸟窝的“又想接近它,又怕惊动它”的“好心肠”。(杨德豫译)两人在追蝴蝶时,她“生怕碰掉/蝶翅上面的薄粉”。(杨德豫译)《麻雀窝》中准确地概述了她这位妹妹之于他的意义:
我后来的福分,早在童年
便已经与我同在;
她给我一双耳朵,一双眼,
锐敏的忧惧,琐细的挂牵,
一颗心――甜蜜泪水的泉源,
思想,欢乐,还有爱。(杨德豫译)
多萝茜不仅是哥哥创作灵感的来源,在她中年生病之前的二十几年的岁月里,她还是哥哥诗作的誊写员。多萝茜不仅誊写,她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而她的观点,华兹华斯几乎在每次的修改中都采用。
多萝茜是华兹华斯诗歌中“亲爱的,亲爱的妹妹“,是他诗中的“艾米莉”,是他笔下的 “爱玛”,或许还是众多学者与读者莫衷一是的“露西”。他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这位妹妹无处不在。她与哥哥威廉一起旅行,一起安居格拉斯米尔,一起在创作中寻找过去、现在与明天。
生死不渝
多萝茜将一生奉献给了哥哥以及哥哥的孩子,一生未嫁。
关于多萝茜的感情,文学界有些猜测,其实这些文学八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多萝茜没有致力于任何一种自己成家的可能,而是全身心地待在哥哥身边。她照料他的生活,为他誊写诗作,与他一起读诗,为他读诗,兄妹两人给彼此温暖,渐渐重建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家。
如华兹华斯在诗中所言,他们几个孤独地抱在一起,一起面对这无依无靠的世界。华兹华斯也在书信中曾经写过,每失去一个家人,他们余下的人会抱得更近,那是对失去的恐惧,那是对尚存的珍惜。没有经受过这种切肤之痛的生离死别人,是难以体会他们这么紧的拥抱,这么亲的共存的。
1831年她患精神动脉硬化瘫痪后,神智时常混乱,她在轮椅上度过了余生的24年,守着终年不灭的火炉。即使是夏天,她也不允熏壁炉里的火灭掉,神智清醒或不清的她守着那团火,守着那团年轻时的吉普赛女郎式的热情,守着那实实在在的温暖。她常常吟诵哥哥写给她的诗,当她还是他眼中“小多萝茜”的时候。
有人说多萝茜的位置如此重要,华兹华斯对自己的妻子其实没什么感情。这也是无稽之谈。华兹华斯与妻子自幼年便相识,她与多萝茜也是好朋友。两人近半个世纪的婚姻中(1802-1850)始终恩爱不移。他们多年如一日充满浓情蜜意的书信惊煞了所有读者的心。玛丽也并不是没有文化的村妇,她的意见与多萝茜的意见一样被华兹华斯接受和重视。还是那首我们最熟悉的《咏水仙》。那首诗中华兹华斯认为最好的两句:“水仙呵,便在心目中闪烁――/那是我孤寂时分的乐园”(杨德豫译)便是出自妻子玛丽之后。玛丽与她的小姑子同一个屋檐下相处半个世纪之久,两人未曾吵过一句。玛丽在1850年送走了丈夫,在1855年送走了小姑多萝茜,1859年在89岁时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