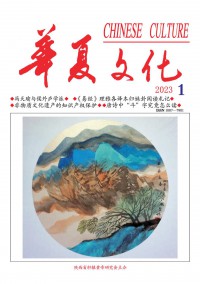清明的诗歌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清明的诗歌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清明的诗歌范文第1篇
清明出自唐代杰出诗人杜牧之手。
杜牧,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理人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
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其诗英发俊爽,多切经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颇高。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来源:文章屋网 )
清明的诗歌范文第2篇
我妈一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很快就和那家主人聊上。后来我妈和我说,那个逝去的人是个年仅24岁的男孩,因为失恋而投江自杀。老父亲紧追其后,但追之不及,一时间竟天人永隔!我闻之非常之惊讶和惋惜!就因为一场恋爱而放弃仅仅24年的灿烂年华,置父母24年养育之恩而不顾?我无法理解,也不赞同!须知生命中最为灿烂的部分并不是如何恋爱结婚,动辄以生命的了断作为对恋爱失败的注释,虽用情至深可感可佩!但作为一个男人,一个肩扛着父母深恩,心担着万千大世界的男人,怎么能就此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在回家的路上,我久久难以释怀,我不止一次看见骨灰坛、灵位、坟茔上,几岁的、十几岁的、二十来岁的早逝的生命,每次看见我都会难以释怀!我是个父亲,我能够深深的领悟失去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撕心裂肺的痛,这种痛会无休无止,每次生死忌日更会痛的难以为继!这种痛不同于其它,会因为时间推移而痊愈。随着时间推移,没有了眼泪不是不痛,而是痛的麻木了!不是痊愈,而是结疤了,痂下依然血泪横流!
想到这,我想起那年女儿因为头发剪得过短而割腕的事情。但是结局和那老父亲却不同,我那时因为隐隐觉得不对劲,暴起翻窗而入,一入眼女儿正拿着一把带锯齿的西餐刀正在割腕。一时间夺刀,然后一巴掌扇在她脸上!瞬间,心痛如刀绞,我至今仍然无法用语言解释当时的心情!但是我想这种心情和那个老父亲气喘吁吁眼看的自己的儿子纵身一跃定格自己生命的心情绝对没两样!同样是父亲,同样目睹自己的孩子自寻死路,不同的是我警觉而有机会,而他年迈体弱没机会!
清明的诗歌范文第3篇
一、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对明清历史重估的理解
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革命”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评价的取向与重点发生重大转移,才有了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居主流的中国观。19世纪60年代后,中日两国学界对此的反应颇为不同。似乎日本学界也有“以我为主”的意识,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对“欧洲中心主义”有所抗争,有“东洋史”等等话题的提出。
同样,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西方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
“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在《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里,通过其写作的长文,发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反诘:“西方是否真的兴起过?或者说西方事实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沉重的病症?它是一项成就,或者是严重的失误?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实现?是不寻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寻常的崩溃?我们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历史系统何以会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加以限制?而这是预先设定好的状态,或者纯粹是意料之外的?(注:卜正民、Blue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二章“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华勒斯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最后一句,特别提醒:对于抑制资本主义出现的文明系统(华氏显然首先是指中国),要另眼相看。这里,华勒斯坦要表达的是有没有可能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条历史通道。至今为止,国内赞同“反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评价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倾向,似是不应有的疏忽。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这种史学思潮可能产生的现实导向,有没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如何明智地应对。
我们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应对,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研讨。
第一,基于事实的层面:“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强烈的重新解读历史的冲动,因此他们在重新解读甚至想颠覆欧洲史旧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欧洲史研究对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样,他们也对中国历史的光明面、积极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遮蔽了的东西,展示于阳光之下。这两者对我们都有历史认识方面纠偏补全的冲击作用。由此启发,若要全面地进行明清史再认识,则需要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双向互动,难度将大大增加。
由于“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提醒,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应该引起警惕的是,不能以一偏纠一偏。对“反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出现的许多新的历史判断,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事实层面上需要独立地省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注重实证,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实证方面,我们应该拥有西人难以替代的本土优势。这种新的西潮,应该成为激励我们更细致全面考察国史的强大动力,而决不是跟风而进,单纯变成另一声音的消极代言人。
第二,基于价值认同的层面:无论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现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经带来的社会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来隐患,“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惊叹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断然丢弃长期学术积淀形成的历史比较“规则”,我们对历史发展的把握,会不会变得无所适从?至于更宏观的道德诉求,诸如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等等的不和谐,恐怕是一个永恒性的难题。在史学上过度的执著,会不会再度激活出新的“乌托邦”倾向?例如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来有些国家找到了较好的内部解决办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贫困包袱甩给别的国家为代价,转换成国际性的困局,从人类历史全局来看,仍然是一个大难题。因此,当我们进入历史评估时,往往需要有历史主义与价值观的平衡,而非执著一端。
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冷峻地“秉笔直书”,需要有一种超乎情感之上的,实证地描述历史变迁的职业意识——不论中西,任何历史都是连续的,是连续中的发展。历史轨迹的明晰,是每个国家发展自己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独立的认识价值,就在于它是为“现在”而提供“过去”的情景,过分注重对“未来”的设计,会使历史学走向“过度诠释”的歧途。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价值观的分歧,必然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史家对历史描述特别是评估的主观取向,这是史学上的一个吊诡。学术上如何处理,也需要史学界进一步研讨。
二、关于明清历史再认识视角的变化
1840年开始,中国一再受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原有“天朝优越”的自信力终于遭遇到了严重的动摇。史学家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有难以自存以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溯明清历史,关注对政治史的批判,认定明清已经走到“前现代”的尽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现在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恰恰是针对着这种史学倾向而来的挑战。
当前,我们对明清史进行再认识,自然就会产生许多新的检讨角度。择其要者,大致有两方面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对“革命”做法的检讨,觉得它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态度——一个国家,不要说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它的存在,总有一种“历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经采取的治国方略,总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当时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否则,它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进,要摆脱困局,也不容易找准入手的路向。推倒一切重来的“革命”不是好办法,后遗症严重。受此苦痛,史家意识到有必要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更深入、更细致地鉴别分析明清历史的实际运作状态,特别是挖掘这些运作的“历史土壤”有否改良的可能,而非脱胎换骨,“只争朝夕”。这种时候,久被压抑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与过去总期望历史突变不同,成为了考察历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视点。
这里,思考的难点,是如何把“合理性”变成动态的概念,由此回答连续性与社会变革的契合关系在哪里?否则,“长期停滞论”很难以从根本上被驱赶出去。易言之,当变革实际上还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长期停滞”的提示,在思考中国长时段历史上,会不会仍然有其认识论上的价值?
其次,与前述相联系,历史考察的视域必然地要有所扩展。近2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等,都逐渐在深入展开。站在历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与人物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以及由规则“丛林”构成的结构性历史。因此在研讨“前现代”或向现代过渡的时候,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来。总体上说,在中国,目前专史、断代研究的力量较强,成果多,而跨朝代的、连贯的研究难度高,一时还跟不上来。但少了这种延续性的通贯研究,就很难准确定位断代史,更难把握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连续而非断裂式发展产生的路向。
在“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曾经有一种意见很受大家重视,那就是“整体的、全面的、协调的同步发展”。其实有哪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转型”过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结果)真正全面协调得那么顺利?西方专家提出的静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太理想,而且也与各国历史实景不是很吻合。在各国现代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凡经济推进的欲求最强,共通性也最大;其次是政治,政治与经济的匹配,恐怕有许多绕不过去的相关性,但其间不仅滞后是经常有的,而且也表现出某种为许多理论家不可思议的妥协性与灵活性,两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点;意识形态的通约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同是走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子的匹配,具体的对应组合方式,实际是相当机灵和多样的,是随机性的,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只有在各种模式的整体效果上,是可以比较甚至评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国家也往往很难“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现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应该被发掘出来的“现代化资源”?假若有,是哪些?但从实际历史运行来观察,又会纠缠于前述三者互动节奏的“合理性”在哪里?实际上却缺乏明晰的判别依据。因为讨论到突破的环节,什么时候以什么最佳,史家多般无从主观下断。在这里,我们只能隐约地感到,历史从来很难服从理论,而理论却必须依据历史来修正。这样,问题又回到需要对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全盘性的总体思考上来。
三、关于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
如果回到长达五六百年明清经济史叙事的角度,确有相当多的史料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工商业者还是农民、手工业者——不缺乏经济理论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经济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偏见。但即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家,也都认为19世纪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了“大分流”,中国沦入了真正的“停滞”。对于后一说法,我们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认真地予以正面回应(注:参见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笔者以为,由于各断代经济史微观研究深入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长期停滞论”撕成了碎片,伤痕累累。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由前清至晚清,乃至晚清至民国,经济都不曾有过真正的停滞。微观或断代研究不足的地方,就是各代说各代的,不能顾此及彼,把连续发展在时段上系统化,用以论证中国经济发展整体状态的趋向,揭示它的发展以及不发展两面。但是,明清经济史的考察,即使发掘的光明面再多,也无法绕过一个巨大的障碍:如何通解过去说的“中国近代的落后”?这是与西方国家、与日本比,要否认也很难。那么这种“落后”与“前现代”的历史有没有关联?可以把这种原因仍然单纯地归咎于“列强侵略”(“反欧洲中心主义”就有类似暗示性的倾向)吗?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认为。
对明清经济发展状态的估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主要谈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上,讨论经济发展的水准,最容易成为观察“社会进步”与历史分期标志的是工具、能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开发、物质增长的速率。它们都是非常醒目的标志,判别上最不容易出现歧见。“前现代”与现代,在这方面的分水岭便是以煤为能源的蒸汽机的使用(所谓“煤铁联合”)。中国“前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人力资源与手工机械。为什么它向现代“煤铁联合”的机械化生产转变反应慢而效率低?这是很需要费心回答的大关节。
与此相关联,笔者以为许多学者对“人口”的正面效应估计不足,不顾国情的不同,片面执著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多,当然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相冲的危机;但人口多,强大的生存欲求,也能促发各种经济开发的努力,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总量的增长。因此,直到清亡为止,从“前现代”经济的特性上衡量,中国是不是到达了“人口危机”的临界点,变成了消极的因素,还是相反,劳动力丰厚与密集恰恰是宋以来经济能长期连续发展的基础?这需要讨论。当然更关键的,被西方视为现代经济转变标志的那种技术进步,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中国,以及即使后来学到的、使用了,发展得也很慢,比日本都差得太多(我曾经比较了19—20世纪中日棉纺织业的不同发展态势(注:参见王家范:《发展与忧患:明清史再认识》,《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思想者”专版。))?这就启示我们需要从经济总量以外的角度思考问题,需要关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其他要素。
其二,不管“反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的中西比较,也不可能取消中西历史比较作为方法论存在的意义。他们中有些人一直认为,那种把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分析,意义不大。例如在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很强,国家对工商的掠夺也很突出。甚至也可以这样发问:发展经济的效率,能说集权制国家一定比分权制国家差吗?但,这些能否构成把政治制度与经济变革截然分开的充足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考察时,两者互相作用的联接点在哪里?国家财政政策的考察是个突破口。说具体些,财政政策,会影响到经济资源的支配与使用状态,国民生产总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终利益格局,特别是政治主体与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都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清明的诗歌范文第4篇
1、清明后的下一个季节是夏季,清明节在春季。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第108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2、清明节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自然节气点,也是传统节日。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清明节的两大礼俗主题,这两大传统礼俗主题在中国自古传承,至今不辍。
3、清明节气在时间和天气物侯特点上为清明节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该节气被看作清明节的源流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清明的诗歌范文第5篇
凡准备申请助学金的新生,来校报到前须在本人户口所在地相关部门开具家庭经济困难证明,一式两份,具体办理如下:
一、农村户口新生只需携带《家庭户口薄》户主页(首页)和本人页复印件各二份即可办理。
二、城镇户口新生(选其一办理):
1、享受“城市低保”家庭的新生,可携带《城市居民低保证》复印件和户口薄户主页及新生户籍页复印件;
2、其他新生,需在社区委员会按以下三类原因开具证明:
(1)长期疾病类
(2)单亲家庭类
(3)父母下岗类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证 明
兹有 (家庭户口所在地首页内的具体地址)居民 (爸爸或妈妈姓名)之子(女) (学生姓名)被xx学院录取,该生家庭主要成员 有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姓名),主要从事 (主要收入来源如种植、工资、买卖生意、低保金、退学金等),家中收入 元(家庭年收入状况),家庭经济困难,开支大,负担重,望相关部门给予该生在校期间的生活补助,资助其顺利完成学业。
特此证明
(村委会或居民委员会)经办人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