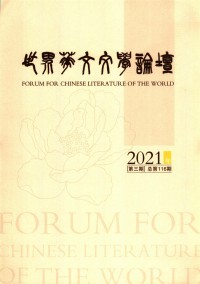解读红楼梦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解读红楼梦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解读红楼梦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语言前景化 视角 《红楼梦》译本 解读
《红楼梦》译本作为一种有着丰富内涵的艺术作品,在整体的运用中能构建出全方位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在整个前景化视角下进行深入分析,能形成整体的艺术魅力,因此,通过采用前景化的翻译方式,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的人物性格、个性化语言等给予综合分析,从而实现对整部作品的风格把握。
一、简述前景化视角的理论运用
(一)概念分析。前景化是功能文体学极其重要的概念。布拉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率先明确提出前景化的概念,后来经由雅各布森、韩礼德、利奇等语言学家对前景化理论做了补充和发展。穆卡洛夫斯基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前景化”的概念,他认为:“前景化,是‘自动化’的对立面,是对一种行为的‘非自动化’;客观地讲,‘自动化’能使事件‘程式化’,而‘前景化’是对‘程式’的违背”。韩礼德认为前景化是“有动因的突出”;利奇则认为“前景化就是一种对艺术的偏离”。前景化把标准语言推到背景位置,从而把对标准语言的种种违反推向前景。由此可见,前景化是将变异的语言表现形式凸现出来,目的是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们感到惊异和陌生,从而产生强烈的美感。
(二)整体作用。“前景化”的概念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经过穆卡罗夫斯基、雅各布森等布拉格学派学者的阐发,后又经过利奇、韩礼德等英国文体学家的加工与发展而最终形成。“前景化”的概念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则是由穆卡罗夫斯基(JanMukarovsky)首先提出,根据他的观点,诗歌语言并不构成标准语言的一种,但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标准语言构成诗歌语言的背景,对标准语言的规则系统的违反使得语言诗意(化)成为可能;如没有这一可能性,就没有诗歌,而否定诗歌作品对标准语言规则的违反的权利就等于否定了诗歌。在文体分析中,“它指一种具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东西的前景化,或从背景中突出的技巧。被突出的特征是语言上的偏离,而背景是人们一致接受的语言系统。语言可看作必须遵守的一套规则,而‘突出’是违反这套规则,是出于艺术目的的偏离。”
二、分析《红楼梦》译本的风格作用
(一)不同译本的特色分析。《红楼梦》在1830年就有了第一个英文译本。在1830-1892年,总共出了4个版本的《红楼梦》英文译本。这些译本不仅不准确,而且显得很荒唐,译者为了渲染这部书的“异国情调”,满足异国读者的猎奇心理,把黛玉翻译成Black Jade,(虽然字面上的翻译还说得过去,但是,却不顾这个名称在英语中的引申意义,给外国读者在理解林黛玉这个人物的时候带来了极大影响。进入20世纪,《红楼梦》又陆续出现了3种英文译本,其中一个是从《红楼梦》德文版转译的。另外两个译本,分别由王良志和王际真翻译。王良志,纽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师,在1927年出版了他的译本;王际真,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在1929年出版了他的译本。
(二)文化艺术的表达方式。这两个译本都有鲜明的特点,就是服从了美国出版界的要求。在美国读者看来,他们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常常集中在两点:一是通过小说去接触异国风情的生活,二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情节,也让美国读者感到好奇。所以,美国的出版商们严格规定两位译者必须按照读者的需求进行翻译。于是,这两个译本就只保留了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故事,删除了一切和宝黛爱情无关的内容,《红楼梦》的主题也被简化为“浪漫的之爱”。两位译者把《红楼梦》中几乎所有描写封建社会生活的内容删掉了。所以,王良志和王际真两位译者,虽然扩大了《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但是他们翻译的《红楼梦》是“西方化”的《红楼梦》,而不是原汁原味的《红楼梦》。直到1973年,才有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红楼梦》面世。这个《红楼梦》才是中国全景的红楼梦,呈现出了全部风采,可是这时距离《红楼梦》开始西传,已经有143年了。也就是说,经过了143年,英语世界的读者们才第一次全面领略《红楼梦》的艺术魅力。
三、探讨语言前景化视角下对《红楼梦》译本的解读
解读红楼梦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互文性 道家文化 《红楼梦》
一 互文性理论与中国典籍英译
互文性理论突破了理论研究和可操作性批评术语的范围,不但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重要的文本理论在中国典籍英译中展示出其对文学传统的包容性和对文学研究视野的可拓展性。互文性将外在的影响和力量文本化,一切语境无论是政治的、历史的、宗教的、社会的、心理的都变成了互文本,使自身在阐释上具有了多向度的可能。译者越来越重视文本本身的语篇衔接,在语篇内有语言的衔接也有语义的衔接,在语篇之外有语篇之间的衔接,从而拓展到与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大文本的衔接,最终让自己的视线扩展到整个文学传统和文化影响的视域之内,即一个从文本的互文性到主体的互文性(即“互射性”或“互涉性”)再到文化的互文性逻辑模式。互文性是从文本(text)到语境(context)再到互文(intertext)的无限衔接的过程,其所关注的文化传统为“先前文化”和“周围文化”。文本被置于一个非文本的历史框架之内,与历史文献、宗教仪式、民俗活动等非文学文本形成相互指涉的互文性描述,历史和文本进入到了一种互文性的运动之中。中国典籍本身与中国本土文化构成大的互文结构,作为中国典籍代表之一的《红楼梦》以其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道家文化,要想让西方读者读懂并且领悟译本中的道家文化,译者不但要考虑语言衔接、语义衔接、语篇衔接,还要考虑文本与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外部衔接,即《红楼梦》与道家文化的互文。冯庆华教授说:“宗教文化牵涉人们的信仰,影响着其他文化成分的作用和发展,理应视作核心文化之一。在文学作品中,核心文化对作品的作用、对读者的导向都是巨大的。”
二 两个《红楼梦》全译本中道家文化英译之比较
1 道家文化语汇英译对比
首先说道家文化中“周天数”的翻译,试看下例:“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第一回)“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霍译为thirty-six thousand,five hundred and one large building blocks;而杨译为thirty-six thousand,five hundred and one blocks of stone.“三万六千五百零一”正合周天度数:即小周天上下升降规则。所谓周天,即以日月为喻,一昼一夜为一日,喻一周天;三十日为一月,亦可喻为一周天;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一十二月,亦可喻为一周天,总之无所不可为喻。周天者,即是一次循环,一次往复,运行一周之义。《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道家文化主张万物都是循环往复,但不是简单的重复。“器”与“象”在变,而“道”不变。“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中“一”出自《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一”生出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之故事,纷繁复杂,绚烂之极又归于平淡,由“一”生出的万物最终要归于“道”。读者看到两个译本对这一文化现象均无注释,因此在体现道家文化“周天数”上还有欠缺,没有译出道家文化的味道,读者便无法理解原文的深刻寓意,在英语读者眼中,无非是机械的、冷冰的数字了,曹雪芹这绝妙的一笔在英语读者眼中只不过是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了。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它的文本;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译者要充分考虑与其互文的文本和文化,使读者充分体会译文的源语文化内涵。
再说道家文化中“魂魄、阴阳、鬼神”的翻译。阴阳是中国文化特有词汇,道家把宇宙万物都视为由阴阳二气构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是辩证的对立统一体。从语言和语义衔接来看,阴阳、魂魄和鬼神作为体现道家文化特色的词汇把《红楼梦》与道家文化纳入大的互文结构。鬼神乃阴阳中之灵也。鬼:归也,阴之灵;神:伸也,阳之灵。一气至而伸者为神,一气反而归者为鬼。魂魄和鬼神也是阴阳。
例1: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的魂飞魄散……。(第七回)
霍译:Terrified out of thEir wits at hearing a fellow-servant utter such enormities…
杨译:These obscenities frightened the servants hail out of thEIr wits…
杨译和霍译都把魂飞魄散译为out of their wits,程度还远远不够。魄主金,金生水,即魄生精,精者魄藏之,属阴,主静,夜隐;魂主木,木生火,即魂生神,神者魂藏之,属阳,主动,昼浮。道家文化中魂魄相离人即死,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魂飞魄散本意指人死不能复生,此处指的是被吓死了或吓得半死,表示程度,笔者认为魂飞魄散译为:feel as if one’s soul had left one’s body或be half dead with fright可能程度更进一层。
例2:湘云笑道:“糊涂东西,越说越放屁。什么‘都是些阴阳’……”(第三十一回)
霍译:‘No,stupid! ’said Xiang-yun.‘The more you say,the sillier you get“Just a lot of Yins and Yangs”
杨译:“What nonsense you do talk, you stupid thing.”Xiangyun couldn’t help laughing. “How could there be so many yins and yangs?”
两个译本把阴阳都用汉语拼音来处理,比较妥当,“阴阳”是事物普遍存在的相互对立的两种属性,阴阳相反相成是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根源。一切具体的概念都无法超越“阴阳”这一表示万物本源的对立统一的概念,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这一概念倍加推崇,而现代科学的发展逐步证明了“阴阳”、“五行”等概念的科学性。作为中国道家文化特有的词汇,英文中就很难找到与之匹配的词汇了,因此只能用汉语拼音来译并且加以注释。
例3: “世人都晓神仙好”。(第一回)
霍译: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解读红楼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接受美学 红楼梦 习语翻译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是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种,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德国诞生。其代表人物为汉斯·罗伯特·尧斯和伊瑟尔。与其他理论不同,接受美学将读者的身份地位放在了一个中心地位,而非被动地位。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对于文本的理解过程是对文学文本的再创造,其功能地位不可忽视。有了读者的参与,一个作品才能称得上是完成的文学作品。
姚斯认为“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一个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具备先在理解结构和先在知识框架,这种先在理解和知识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是读者与文学作品进行对话的前提。一个文学作品需要激发读者的接受趋向,唤醒读者以往的阅读记忆,唤起其期待视野(周宁,金元浦,1987)。伊瑟尔(1987:97)认为,作品的意义只有在读者参与的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接受过程中。因此读者的地位应该受到关注。
一.接受美学对《红楼梦》习语翻译的启示
习语承载着独特的文化特质。与其他语言成分相比,习语是语言的精华,更具典型性。习语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是文化交流过程。所以,是否能解决好习语翻译中的负载文化问题是译作成功与否的标准(文晓华,2006:41-46)。《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书中语言生动形象,具有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
二.接受美学框架内《红楼梦》中的习语翻译分析
《红楼梦》的英译本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两个是杨宪益及夫人戴乃迭的译本和戴维霍克斯及约翰敏福德的译本。本文拟就杨译版《红楼梦》和霍译版《红楼梦》中习语文化特色的处理方法进行分析比较。
1.对译文读者认知心理的关照。
《红楼梦》体现了中华名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红楼梦》的翻译,尤其其中承载着独特文化特质、生动活泼的习语翻译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化,而是文化的交流。不同背景下,读者具有不同的认知心理。对于习语的翻译应该体现出对读者认知心理的关照。
例1 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第二十四回)
Y: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H: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这其实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地方习语,因为荣宁二府在金陵,属南方地区,而南方人以食米为主,因此,贾芸才如此说来。最初是宋代庄季裕《鸡肋篇》中先创此语为“巧手莫为无面饼”(针对主食面粉者)。意指即使是聪明能干的人,做事缺少必要条件,也难以办成。在霍克斯的翻译中,他讲“米”和“粥”翻译成了“flour”和“bread”,这两种是国外常见的主食,因此更加容易被西方读者所接受。
例2 情人眼里出西施。(第七十九回)
Y: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H: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西施天生丽质,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中的“沉鱼”,讲的是西施浣沙的经典传说。而“情人眼里出西施”则指的是比喻由于有感情,觉得对方无一处不美。因为此处“西施”对于国外译文读者来说并不熟悉,因此也无法体会到此习语的内涵,杨和霍将其翻译成英语中的对等习语,使得译文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品。
2.对译文读者文化心理的关照。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历史习俗、审美情趣等也颇为不同。这些差异经常表现在语言文字这一文化的载体之中,同时也表现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当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处理好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信息。
例5 女娲补天:原来在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第一回)
Y:When the goddess Nu Wa melted down rocks to repair the sky… (p.5)
H:…when the goddess Nv-wa was repairing the sky,she melted down a great quantity of rock… (p.1)
该句中的习语涉及到中国古代神话,而在杨,霍的译文中却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背景知识,他们采用了异化的方式来保持了习语原来的字面意思,但是对于目标读者来说则难以理解到这个习语的意思,会对女娲为什么补天而感到疑惑。
例6 千里姻缘一线牵
Y:People a thousand li apart may be linked by marriage.
H:Old folk talk about “the unseen thread that binds”. They say that marriages are decided by an Old Man Under the Moon who joins future couples together by tying the round the ankles with a scarlet thread….
“千里姻缘一线牵”指的是夫妻婚配是命中注定,由月下老人暗中用一红线牵连而成。而月下老人则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主管人间婚嫁之事。在杨的翻译中,其采用了直译的手法,“千里”翻译成了“a thousand li”,“里”是中国的距离单位,在西方没有这个说法,因此如此直译将会是西方读者不解此处到底要表达何种意思,同时在杨的翻译中只译了 “linked by marriage”,也没有提及为何“linked by marriage”。而霍在翻译是对其进行了添加,提及了“月老牵红线”的典故,不仅让译文读者了解了该习语的意思,同时让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的文化,满足了读者的阅读享受。
3.对译文读者审美情趣的关照。
习语语言生动活泼,鲜明立体,能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保持意美,音美甚至改善读者的审美体验。《红楼梦》中的很多习语都采用了比喻或者类比的修辞手法,来使得语言更加生动形象,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对这些修辞带来的美的体验进行传递。
例9 心病终须心药治,解铃还是系铃人 (第九十回)
Y:The cure for a broken heart is heartening news;
The knot must be untied by one who tied it.
H:No remedy but love
Can make the lovesick well;
Only the hand that tied the knot
Can loose the tiger’s bell.
在霍的译文中,“love”和“knot”,“well”和“bell”押韵,句首的两个“Can”重复,同时在句中“tied”和“tiger”押头韵,这一系列的押韵与重复,使得该翻译朗朗上口,在意达之外更创造出了音美,从而使得译文读者有美的享受。相比之下杨的译文则没有霍所创造出来的音美效果。
例10 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 (第二回)
Y:A single chance hiatus
Raised her status
H:Sometimes by chance
A look or a glance
May one’s fortune advance
《红楼梦》中的习语大都工整对仗,此句也是五五相对,较为工整,因此在翻译时如何尽量保持这种形美也是相当重要的。杨和霍对这个习语的翻译保持了原先的形美,同时在句尾“hitatus”和“status”押韵,“”chance“glance”“advance”押韵,创造了音美,关照了译文读者的审美情趣。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是我国语言文化的一个宝库。本文以接受美学为视角,对《红楼梦》中习语翻译的读者关照进行了分析,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对译文读者的认知心理,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进行关照,同时也要给其留有足够的空间,拓展其“期待”视野,宣传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
参考文献:
[1]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London: Penguin Group, 1982.
[2]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
[3]柏钧, 张映先, 古诗英译在《红楼梦》中的审美再现,[J].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4]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文晓华,浅议习语翻译中文化信息的传递[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
[6]游洁,张映先,从目的论看《红楼梦》中俗语的翻译[J].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7]周宁金元浦译姚斯崔拉勃著.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解读红楼梦范文第4篇
最近读到一本书《音乐家眼中的〈红楼梦〉》(孟凡玉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该书是音乐学和红学研究学科交叉的新成果,研究视角独特,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以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为基础,结合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历史,借鉴当代研究理论,对《红楼梦》中的音乐活动情况作了全面的梳理,并对其中的音乐审美、乐人、仪式音乐、音乐术语等音乐文化现象作了深入的解读,不仅为阅读、理解《红楼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中国清代音乐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参考资料。
这本书的风格独特,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1、角度新颖。《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中国清代社会生活的“大百科全书”。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研究者从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园林学、建筑学、语言学等多种角度开展研究工作,以《红楼梦》研究为中心,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红学”,先后出现了“题咏派”、“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等多种红学研究流派。但是,对于书中音乐现象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学术空白,形成了一个学术盲点。作者选择音乐学视角,新颖、独特,填补了红学研究书库中音乐学研究专著的空白,无论是对红学研究还是对音乐学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正如音乐学家乔建中所说,本书“开掘出无论对‘红学’还是对‘音乐学’来说都具有‘补白’意义的一个新领域”(见该书封底)。
2、原创性探索。红学家胡文彬说:“这个选题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填补一个学术空白),同时也有相当的难度”(见该书封底)。确实如此,选择音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由于前人较少涉及这个研究领域,所以能够参考、借鉴的先期成果不多,需要更多的创造性探索。因而,本书选题是有胆有识的举措,本书的研究成果是富有开拓精神的原创性探索。
3、视野开阔。该书内容丰富,广泛涉及到红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学、音乐教育学、表演艺术学、音乐人类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是多学科交叉的学术成果。比如,第一章《〈红楼梦〉中的音乐审美》以贾母、林黛玉、贾宝玉、妙玉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揭示这几位主要人物的音乐审美心理;第二章《〈红楼梦〉中的乐人》深入细致地解析了《红楼梦》中的乐人这一特殊的人物群体,并与古今乐人群体情况对照,阐释乐人群体的职业特点和个性特征;第三章《〈红楼梦〉与中国歌唱文化》、第四章《〈红楼梦〉与中国器乐文化》全面梳理了《红楼梦》中的歌唱和器乐文化现象,深入剖析了中国古代积淀深厚的声乐、器乐文化内涵;第五章《〈红楼梦〉与中国仪式音乐》从仪式音乐的研究视角,对《红楼梦》中的祭祖仪式音乐、丧葬仪式音乐、驱邪仪式音乐、庆典仪式音乐等作了深入透彻地解读;第六章《〈红楼梦〉中的音乐传承》则着眼于音乐的传承活动,重点分析了音乐传承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等等。总体来看,本书视野开阔,是多学科交叉的学术成果。
解读红楼梦范文第5篇
“虚实相生”是中国美学的基本法则和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虚实论的哲学渊源可追溯到老庄道家的“崇无论”。老子从他崇尚的“道”出发,认为“无”是“有”的根本,世界是有和无、虚和实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之上,万物才得以运动、发展以至生生不息。这种“有”和“无”、“虚”和“实”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体现就是“虚实相生”的艺术原则,它认为艺术形象必须虚实结合,才能真实地反映有生命的世界。新版《红楼梦》恰恰背离了这条原则。以下笔者试就此简单谈谈个人看法。
首先,新版《红楼梦》中的演员选择不符合原著的人物刻画。原著中的人物外貌描写和形象刻画可谓句句传神,如形容林黛玉“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而这样刻画薛宝钗的雍容华贵:“只见脸若银盘,眼同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黛玉另是一种妩媚风流。”87版《红楼梦》中的主要演员陈晓旭和张莉,就算不化妆也十分贴近原著的刻画,简直是小说中这两个中心人物的原型。
当然,外形上的差异是可以通过化妆、服饰和演员的演技来弥补的,但遗憾的是,新版林、薛的两个扮演者并未将两个人物演活,至少没有让大多数观众记住她们的姓名和演技。总之,新版演员的选择,或太过重视外形、年龄的真实而忽略气质神韵,如小贾宝玉的扮演者于小彤;或过于注重名气而忽略口音、实际年龄和外形体貌特征的差异,如王夫人的扮演者归亚蕾;或随意安排调换角色致使演员出演了与自己气场不符的角色,如雍容大气、本该扮演薛宝钗的姚笛却扮演了王熙凤。此外,贾宝玉的纯真多情且富有灵气,王熙凤的干练泼辣兼凶悍狠毒,贾母的慈祥富贵和集严厉、溺爱于一身,在新版《红楼梦》中统统走了样。
其次,新版《红楼梦》中的人物造型刻意求新,虽然导演试图从戏曲中寻找人物衣着头饰的古典气韵,只可惜生搬硬套而来的贴片与头饰,再加上颇具程式化的服装造型,使本应符合人物个性特点、形式风格各异的服装头饰变成了很难区分的清一色戏曲装扮,其视觉效果上单调刻板而神采意味全无,结果是“实”未成而“虚”不就。如薛宝钗以白色服装为主,林黛玉多着青色服装,以至于有评论者把二人比作《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和小青。
新版《红楼梦》在人物造型上是比较失败的,过分追求服饰的哲学意味而忽视了人物正值青春年华,试图把小说内在蕴含的悲剧命运和美学观念穿在人物身上,这样人物造型丧失了人物本身的精气神而沦为了一种观念符号,有故作深沉之嫌。剧中还有一些人物造型和相关场景过分追求奢华浓艳,以致视觉上艳俗有余但贵气不足。总之,新版《红楼梦》花费太多精力在外在的东西上而忽视了原著中人物自身的生命活力与风采神韵,正如朱良志在《曲院风荷》中所言:“中国艺术强调,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浓,朴茂沉雄的生命,并不是从艳丽中求得,停留色相之上,而失世界真意。”
再次,背景音乐、画外音的运用上也有缺憾。庞龙的一曲《红楼梦》,虽然在作词作曲上着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追求,但由于对作品深层情感基调体悟不足,可以说精美但不灵动,悦耳但不哀婉;尤其是和87版中那一曲荡气回肠的《枉凝眉》相比,显然缺乏那种诗意隽永、大气悠长的古典情怀。剧中许多烘托气氛的音响加得有些牵强,无法与情境有机契合,反而不如舍弃,追求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新版《红楼梦》采用全文言文的人物对白,又怕影响观众理解,于是大量使用画外音,这种贯穿全剧的“读书式旁白”,时时将观众从入戏的状态中抽离出来,使之无法完全沉入剧中,更谈不上情感共鸣了。
“虚实相生”背后所蕴含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这种深刻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最鲜明的体现是:中国艺术多靠主观想象去领悟自然万物的情趣,其最高原则是“气韵生动”或“象外之象”,这就要求欣赏者心领神会。换言之,艺术作品应该给欣赏者留下一个思考和想象的空间,一如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更能激发欣赏者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促进欣赏者与艺术家、欣赏者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心灵沟通。中国艺术创作虽然讲究虚实相生,但总是指向“虚”,“实”是“虚”得以实现的手段,即画面表现出来的“有”是为了表现画面之外的“无”,“有”是媒介、桥梁,而“无”才是目的。所以,中国传统艺术崇尚含蓄,于有限中追求无限,这才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和精髓。新版《红楼梦》的失败,正是因为背离了中国美学和中国传统艺术的这一核心与精髓。
参考文献:
[1]张同道.艺术理论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朱良志.曲院风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4]陈祥麟.评李少红新版《红楼梦》――兼与黄蕉风先生商榷[J].观察与思考,2009(9).
[5]徐丽莎.新版《红楼梦》:传统经典解读的噩梦[J].社会观察,2010(8).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