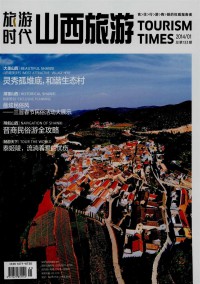旅游人类学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旅游人类学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旅游人类学范文第1篇
一、引言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青睐于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旅游,体验新颖独特的民俗风情,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饮食往往是吸引游客前来参观游览的重要因素。本文将贵州省石阡县坪山乡尧上仡佬民族文化村作为研究对象,从旅游人类学的视角来论述尧上仡佬族的“六和三角宴”,通过对“六和三角宴”的文化解读,从当地仡佬族的社会分层、社会性别以及仡佬族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等方面揭示仡佬族的基本社会结构。力求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发现文化旅游开发的新路径,让旅游者对当地仡佬族文化有更直观的了解。
二、“六和三角宴”的来源及其文化内涵
尧上仡佬族“六和三角宴”由来已久,距今这一习俗已有300多年历史,2013年以前,此项习俗还只是在当地流传,尧上仡佬族民族文化村不为世人所知。自从2013年除夕,央视新闻频道连续三次现场直播尧上仡佬族“六和三角宴・集体过大年”的盛况后,尧上民族文化村和其特色宴席“六和三角宴”开始走进大众的视野。因此,尧上仡佬民族文化村的“六和文化”也成为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据传,尧上民族村村民除夕摆放“六和三角宴”、集体吃团圆饭的习俗缘于仡佬先民崇尚“合和”之故。关于“六和”的来历,世居于此的邓姓仡佬族村民有这样的传说:邓氏家族来到这个地方,原本有八兄弟,不幸有两个夭折,其余六兄弟长大成人,因相互间经常发生纠纷不和,六家人商议每年除夕时聚在一起吃饭,大家握手言和。后来除夕夜聚在一起吃饭成为惯例,并立下训言,六兄弟的后人要永远和睦相处,“六和宴”就这样诞生了。“六和三角宴”传承的文化内涵丰富,“六和”:寓意“六六大顺”,更蕴含着“父母和蔼、夫妻和鸣、家庭和顺、邻里和睦、环境和美、社会和谐”之意,彰显的是仡佬民族团结、忍让、宽容、诚和、善处、礼敬的‘六和’精神。“六和三角宴”这一饮食习俗的意义,在于它所蕴含的“和”文化价值,通过饮食活动过程传递、承载了积极和睦的仡佬族文化。
三、“六和三角宴”的社会功能
(一)宴席座次中体现的社会分层
“六和三角宴”的宴席桌子摆放是很有讲究的,在村民活动广场上所有的六边形的桌子要摆成三角形,全村300多村民按年龄、辈份大小依次围坐,长者坐在三角形的顶端。三角造型,寓含天时、地利、人和之意,以昭示后人传承尊老爱幼的美德。让长者坐在三角形顶端的位置,表示全村人对长者的尊敬,也增进了村民的团结和友爱。
(二)饮食传达的“和”民族价值
作为仡佬饮食化典型物化符号的“六和三角宴”,不仅体现出尧上仡佬族饮食文化的特征和内涵,也体现了仡佬族以“和”为核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完美的诠释了仡佬族的“和”文化。
1、人“和”。“六和三角宴”宴席体现出仡佬族淳朴的品质。六和取“父母和蔼、夫妻和鸣、家庭和顺、邻里和睦、环境和美、社会和谐”之意,彰显的是仡佬民族团结、忍让、宽容、诚和、善处、礼敬的‘六和’精神。“六和三角宴”宴席的设计十分精妙,从“六和三角宴”宴席的菜名设计上看,比如:猪脚老腊肉、苔茶糯米酥、香菇长寿汤等,既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又表达了对长者的祝福;餐桌的设置也独具讲究,六角形的桌子,呈三角形摆放,长者坐前端,传递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全村集体吃“六和三角宴”,充分凸显出了此地仡佬族人民善良淳朴的精神品质。
2、自然“和”。“六和三角宴”宴席食材原料都是绿色健康的农家菜,有美味的山珍:如木耳和丛木菌等时鲜菌类等,还有滋补养生的药材:如冬虫夏草童子鸡等。这些食材的特点就是自然和本真,都是大自然馈赠的美味。
3、自然与人文结合。尧上仡佬族民族文化村坐落在美丽的佛顶山脚下,包溪河流穿而过,山清水秀,景色迷人,而”六和三角宴”本身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则为宴席润色,青山绿水间摆起宴席,吃着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听着仡佬族热情的祝酒歌。游客在饮食的过程中,充分不仅享受到了视觉、味觉方面的盛宴,而且可以切身体会仡佬族的文化习俗,享受精神层面的盛宴。
四、尧上仡佬族饮食文化开发的思路
旅游人类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族旅游;文化再生产;信仰文化;神秘湘西;旅游吸引物
[作者]赵玉燕,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长沙,410081
[中图分类号]F5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2-0184-006
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衡量,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低、厚薄或好坏之分。各类文化之间的不同,在于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并且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同时,任何依然还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都必然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流体存在。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mduction)”理论说明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一方面,文化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维持自身平衡,使社会得以延续。另一方面,被再生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体系,而是在既定时空之内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旅游业比较好组织,又容易在经济上获利,所兜售的旅游吸引物不仅有自然遗产,还具有地方文化和地方色彩,诚如翰・厄里所言的“消费地方”。因而,一地的旅游开发包含着如何理解地方文化、如何理解商品、如何理解地方文化的商品化和旅游者(购买者)的心理以及旅游吸引物在整个商品世界的位置等诸多问题,这就使得这种实践活动并非那么简单易行。在每一个旅游中心,制作吸引游客的吸引物都充满着竞争。对地方、民族文化元素的筛选,就成为一个必要的环节。旅游开发者大都主张,在民族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必须对内容进行精选,其原则就在于旅游吸引力。吸引力又主要决定于当地与游客产生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因而在开发的内容选择上应精选其具有特色的部分。这种特色与差异的效果,会导致两种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时产生文化震撼,文化震撼的强度大小正是旅游部门策划旅游项目、增强旅游吸引力的文化心理依据。
在一定意义上,落足于某地的民族风情旅游中的文化再生产,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能动地获取意义的存在。它不再被视为一种文化形态过去所固有的特性,而是被理解成了一种处于现在、关于现在并与意味深长的过去相联结的弥散的、象征的和阐释的建构。这种实践,就集体层面而言,服务于民族复兴,发挥着宣扬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建构针对国内外游客的旅游与文化表演的基础,确立自我认同的象征物的作用。
“神秘湘西”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由各方力量为了提升“文化势差”,利用本地已有的信仰文化向中外游客打出的旅游口号。这一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建构,反映出旅游场域中各方力量的竞争和合谋关系。神奇的山水风光、独特厚重的地域文化、多姿多彩且浓郁的民族风情以及别具一格的信仰文化,在社会各方不遗余力的炒作、介入下,最终使湘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一、媒介对“神秘湘西”的宣传制作
我们知道,任何已知社区的旅游业都是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能够吸引“外来人”的特殊地理特点和娱乐特点相互联系的综合产品。媒体、政府、文化经纪人和旅游业操作者共同创作出来的湘西“神秘信仰文化”的代表――湘西三怪――即“赶尸”、“落洞女”和“放蛊”,成为湘西苗寨重要的旅游吸引物。
赶尸人们关于赶尸的讨论,在湘西之外流传很盛,游客都带着看“赶尸”的向往来到湘西,但是“赶尸”这回事,就是湘西人自己也讲不出所以然来。我在田野调查期间,总是被游客追问:“你调查到湘西赶尸的事情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真的存在么?”
人们传说“赶尸匠”是湘西民间特有的行业,能够领着一群尸体在夜里赶路,路上有“死尸客店”,店门一年到头都开着供“赶尸匠”和死尸住宿。赶尸匠要通过种种苛刻的考试并学会画符和别的一些技能。有的旅游网站还给出奇奇怪怪的解读,激发大家的好奇心。
从事苗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人倾向于认为苗族的巫师确有“赶尸”的技能。凤凰老洞苗寨的本地导游就这么跟游客介绍:“去年我们寨子刚开发的时候,就有一位法师应了游客之请,表演了一场赶尸法事,半夜时分在一个山洞将他已死去的父亲从墓里赶出来,让他走了几步。后来这个法师被乡邻指责拿自己的先人开玩笑,他就不敢再做表演了。然而,我们苗乡确实有能赶尸的能人。当家里人出去好几年没有音讯时,家中人挂念,就会请法师赶尸。有一个男孩子到浙江打工几年没有回来,爹妈也没有他的信息,因此担心儿子死在外头了,就请了法师在家里赶尸。那个男孩在外地,梦里连续几天都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于是就辞了工往家赶。他赶回自己的寨子时,已经是晚上了。于是他到家门口敲门,喊父母亲开门。父母亲吓得要命,后来让他在门外伸手进来,摸到有热气,才确认是自己的儿子。之后这个儿子再也没有到外面去打工了。他就是在家里作了赶尸的法事才回来的。”
有趣的是,2005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10套两次有摄制组专程到山江苗寨拍摄关于“赶尸”的探秘节目,其中也的确拍摄到了一些至今还不能解释的现象。这些节目的播出,立刻在国内外引起颇大的反响。
神秘现象是否存在不是我在这里想要探讨的主题,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对这些神秘现象的信仰和传播。当我们仔细推敲这些多少有些耸人听闻的宣传材料时,在查无实据的背后,我们能隐隐看出流露于字里行间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合谋关系。
落洞女沈从文的小说中曾经提到过“落洞女”,说的是苗族中上层地主家的女子,读了点汉族的诗书辞赋,在青春萌动的季节,就日日幻想着自己和洞神谈上了恋爱,此后就一日一日地消瘦下去,直到呓语着“洞神要来接我去作他的新娘了”而玉散魂消。“湘西的‘落花洞女’是部落中有一些未婚的女子,能将树叶哭下来;到山洞不吃不喝,几天不死,回来后也不饮不吃,几天后就死去。部落人们认为她去和树神、井神结婚了,因而这些女孩生前没有结婚,但人死后,落花洞女的家人给她们不但不办丧礼,还要办婚事,以示婚礼之喜。”
人们说,凡属落洞的女子,一般都眼睛光亮,性情纯和,聪明而美丽,未婚且喜爱修饰。落洞女子平时镇静自处,情感热烈不外露,但是喜爱幻想。间或出门,即自以为某一时无意中从某处洞穴旁经过,为洞神一瞥见到,欢喜了她。因此更加爱独处,爱静坐,爱清洁,有时且会自言自语,常以为那个洞神已驾云乘虹前来看她,这个抽象的神或为传说中的相貌,或为记忆中庙宇里的偶像
样子,或为常见的又为女子所畏惧的蛇虎形状。女子落洞致死的年龄,年岁不等,大致在16岁到24、25岁左右。病的时间久暂不一,大致是两年到五年。治疗落洞女子最好的方式是结婚,一种正常美满的婚姻将医治好这种女子的病症。
在湘西凤凰为期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中,这里苗乡的人告诉我,“落洞女”实际上是患了一种病,女人只要能够苏醒过来就好了。他们还绘声绘色地告诉我有好几个这种“落洞女”,幸运地被挽救回来了的人。对“落洞女”这一现象的笃信,在当地似有根由。
“落洞女”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在人们生活中比例到底有多高,这似乎已经不成为大家理性思考的对象。在旅游地形象策划时,为了彰显文化的差异与他族群的神秘,落洞女成了“神秘湘西”制作的环节之一。
放蛊对于现代的旅游者而言,“放蛊”现在变成了一种美丽的传说。流言中它过去所拥有的能致人于死地的神奇魔力,在现代化医疗面前已经不攻自破。除去了对人的危害的可能性,“蛊”事的神秘就让人更感到好奇。“爱蛊”“情蛊”的传说,对于处于爱情失意或者不良婚姻状态中的一部分游客来说,几乎成了一种心理慰藉。文化的差异在特定的语境里成了人们共享的东西,激起了人们对他者文化的向往和欣赏。
现在苗族年轻人对待蛊的态度很不一致,也令人玩味。山江博物馆里年轻的工作人员回答游客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苗族人会放蛊是不是真的啊?”由此可见,关于蛊与苗族人的联系对游客们的困扰。每逢这时,人们就会有一个很热烈的讨论。有一种说法这么认为:“苗族人肯定不会放蛊啊。要是能放蛊,我们苗族难道不能住在平原上么?哪用得着住到山区来。过去也用不着三番五次和朝廷打仗了,只管派一些蛊婆去放蛊就是了。你们说呢?”而老洞苗寨的年轻苗族导游却总是这样调戏女性游客:“到了我们苗疆,却不学点蛊回去,真是太划不来了。我们这里的蛊,是一种气,一种意念。如果你喜欢谁,只要对他放爱蛊,他就会一辈子死心塌地跟着你厮守终身。我们苗家离婚率低,也是因为我们苗家女子会爱蛊的缘故,当然喽,各位男士想学的话,照样有效”。
据学者考察,有关“蛊”的话语是苗乡内部原生语态中的“流言和闲话装置”。它一方面使邻里和睦关系有所减弱,另一方面使各种潜在的不和通过这种渠道得到发泄,秩序得以重新确认。
二、地方民众对“神秘文化”的民间再创作
与以上媒介的渲染不同,地方民众或出于以旅游促经济发展的需要,或出于自我或多或少对传统信仰文化的承继,参与了发展湘西旅游的“神秘文化”创作。不同的是,民间的创作重心主要在于对“命运”和“前生后世”的诠释。
以下好几则故事,折射出普通百姓对湘西“神秘文化”的确认和再创作。
故事A:麻冲寨子里有个人离奇失踪了三四年,前不久回来了。大家都问他这些年去了哪里。“唉,别提了。我有一天走在路上,被两个人挟持着,飞到了外面一个煤矿做工,实在很苦啊。后来我趁这两个监督着我的人不注意,就偷偷跑回来了。那天我走的时候,我看到你们走在离我不远的一条路上,我被人挟持着,拼命喊你们,你们没有听见么?你们没有看见我么?”大家都摇头,说确实没有见过。
理性的人推敲这一段文字诉说时,或许会觉得它简直就是一段呓语或者说神话。然而,本地诉说的人、听故事的人以及传播故事的人,在这种梦幻般的叙述中,却多少体验到生存的不易。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而言,这种有着此等叙事方式的人群,不也正成了他们的旅游所要探访的目标么?
故事B:有一个信用社主任是副科级干部,工作业绩很不错,各方面条件也好,但是连续几年在仕途上该升正科级干部的时节却没有得到升迁。他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就到一个算命先生那里去“看屋场”。那个算命先生说:“你家屋场后边被人凿了一个大窟窿,整个家屋都泄了气,你还说什么升官的事情呢!”过了些日子,他回家查看,发现弟弟本来打算在家屋后边挖一个红薯窖,挖了一半,觉得不合适就放弃了,也没有填回土。他见状赶忙让人将这个洞填平,一年过后,他如愿以偿升了官。
这一类型的算命故事,其实在汉族民间流传也很广。我们不妨将之看作人们在面临困惑、不顺又想自我免责时所构想出来的一种有趣的解释体系。不过,在旅游开发“神秘文化”的语境中,这类解释体系的再度喧嚣,总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湘西苗族村寨对前生后世的故事和解读也很耐人寻味:
故事C:人或许真的是有前生后世的吧。一个寨子里有一户人家,他们有一个孩子在九岁时被牛踩死了。隔了十多年以后,另一个寨子里一个小伙子来到这个寨子做工,告诉这家主人,现在他回家了,他自己的前生就是那个被牛踩死的孩子,后来投胎到了别的寨子。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身份,他告诉大家小时候他在哪一棵树下玩耍埋过一些东西,并带着大家去看,刨开表层土,果然就看见了那些他所说的玩具。以后这个小伙子就做了这家的儿子,两家保持来往。
故事D:一个仙娘总是给别人“走阴”。她40岁那年的一天,忽然看到了自己的前生,因此便决意要去找那家人。她找到了那个寨子那户人家,对着主人家就喊哥哥。那个男人吓了一跳,说我自己是有一个妹妹啊,但是死了很久了。仙娘回答说:“哥哥啊,我确实是你的妹妹。我死了以后就投胎到了别的寨子,现在才回来找你呢。”说完,就跑到这家房屋的床底下,拿出一大包封好的东西,告诉哥哥那是什么时候她曾经用过的。之后这户人家就真的把她当作妹妹了,现在两家还保持着亲戚关系。
我和苗家的年轻人以及小学教师一起讨论有关前生后世的这两个故事。我们推测或许是两家穷富不一致,所以需要找理由攀附。但故事讲述者断然拒绝了这种可能性,她知道两边家境都很穷,没有必要为了这一层关系攀亲。而小学老师则认为:后则故事里的女人找哥哥可能有一个动机,即为自己找一个娘家人。在苗乡,有娘家人,尤其是舅舅是非常重要的。夫家因为舅舅的关系,会对这家媳妇特别客气一些。而这些故事之所以流传,会不会是有好事者出于什么目的而故意散播呢?“整个就是些装神弄鬼的东西”,这位老师说,“我也是苗族人,我怎么就没有听说过这些故事啊。”
然而,这些神秘古怪的事情,好比是配合“神秘湘西”旅游的宣传似的,在民间广有流传。创造和流传甚至于评论这些故事的人,在行动的同时,事实上都知道自己的立场所在。无言的山水风光,在各种力量的综合下,就这样披上了一层神秘外衣。
三、旅游开发企业对“神秘文化”的舞台展示
表达山江苗族精神信仰世界的许多仪式和物质载体在旅游的潮流中每天反复出现,这与旅游开发企业对“神秘文化”的舞台制作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当地信仰文化的舞台展示,旅游开发企业成功地满足了游客对于他者精神世界的窥探和对“神秘”湘西的期望与臆想。
“还傩愿”曾经是湘西苗族民间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民俗事项,现在仍有留存。人们对傩神(傩公为东山圣公大帝,傩母为南山圣母娘娘)乞求病痛痊愈、求子嗣生育,求升官发财,一旦愿望达成,就要选择秋、冬时节(春季偶尔也举行,但夏季极少)祭祀傩公傩娘,以表酬谢。傩神没有庙宇,人们往往在家中设置神坛、安放神像祭祀。举行还傩愿时,主人家还一定会请歌师在神
堂唱戏(称为“傩愿戏”)以乐神。“还傩愿”仪式一般会有以下仪式:神坛布置、发鼓请神、神下降后,要举行“和上洞”、“和中洞”、“和下洞”等一系列仪礼,之后是打合同、上马、送神等。我于2004年田野调查期间,参加过三次举办非常隐秘、规模也较小的“还傩愿”,程序大致和石启贵先生上世纪30年代相似。
作为一项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还傩愿无疑是具有开发价值的。然而,由于巫师传人的锐减以及信仰禁忌的束缚,向游客演出“还傩愿”和“傩愿戏”不太可能。事实上,在这种神秘文化的舞台化过程中,湘西少数民族内部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乡村百姓对鬼神仍笃信不疑,认为祭神的巫歌巫舞不能随便唱随便跳,鬼神在无事的情况下随便延请,免得让他们过于劳累而给人们降下灾祸。在乡间有一定威信的法师一般不愿意接受民俗风情园的延请,为游客进行表演。“我不能耍弄我的各路师傅,无事调动我的兵马,请神送神。这是要在真正有事情,为人解难的情况下才作的。他们(风情园)就是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干这种事。”有一位巫师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因此,虽然“还傩愿”仪式是山江苗族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仪式,但由于其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仪式过程繁琐且不具有观赏性,没有成为神秘文化“舞台展示”的内容。有意思的是,在民族内部,乡村巫师倾向于将向游客表演绝技的那些巫师们称为“”,而自诩为“正教”。
因此,傩堂在湘西对外的神秘文化展示中就占据了重要位置。在湘西苗族博物馆的第一馆――“普通农舍”中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傩堂”,向游客讲解还傩愿习俗。这个傩堂据说是博物馆的创办者在做了“还傩愿”法事后专门留下来做为展示的。讲解员就在这个傩堂里每天向游客讲解苗乡的神秘奇特文化:还傩愿。
旅游开发企业将湘西神秘文化搬出展示的还有一些绝技如上刀梯、下火海、踩火犁、摸油锅和吞火、吃火炭、眼提重物等。在过去,这是巫师用来向“鬼”展示自身法术和魔力的一部分,然而现在它被抽离出原生情境,每天都在民俗风情园里应邀向游客上演。
“上刀梯”本来是苗族巫师收徒传法的重大仪式,兼有为凶死者解罪和还愿的功用。一般由巫师来主持仪式,刀梯也是临时搭建、仪式结束后马上拆掉。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参与者很多,通常整村整寨的人都会来给主家帮忙。这是邻里、村寨、族人之间一种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在旅游的背景下,这一部分因其可观赏性而被抽离出来。刀梯和大刀被固定在民俗风情园场地中。人们在场坝上竖一根高约二丈的钢柱,钢柱两边由下而上等距离地横插数十把锋利的钢刀,每把长约一尺五寸,刀口向上。表演者手握刀口,赤脚踩着刀刃,逐级向上攀登,再顺次而下回到地面;在刀梯的前方,固定安放一把锋利的钢刀,表演者赤脚从刀把处出发,走完刀刃。在风情园中,每一次表演这些绝技,都要有法师鸣锣开道做法,祭请祖先鬼和师傅保佑。然而,这些巫师们,其道行法术大都不被乡村生活所认可,我们或许将他们称之为“表演者”更为合适。
四、结语及讨论
民族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信仰文化再生产,使“神秘湘西”这一主题得到确立和传播。在旅游“场域”下,行动者能动的主体性得以凸显。“神秘”一词作为湖南湘西旅游景物的“标志”(marker),语义得以扩展。“落洞女”、“赶尸”、“放蛊”这些文化元素成为湘西象征性的指涉和导向性的预期旅游体验。而我们知道,“在观光中景物并不一定就是重要的因素,比景物更重要的是游客对景物标志的关注”。符号学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随机性原则,能指总是被理解为一个心理存在,而所指总是被理解为一个“外在”的客观事实。湘西的旅游景物最终具有的形状和稳定性,能否被“神秘”所涵括,就像符号一样,由社会而非某个个体所决定。而“神秘湘西”这一“地方特色”和“地方感”的提炼与打造,确保了能体现某一地独特感觉事物的“他者”之展现、保留与再造,彰显出现代语境下独特感和奇异感的与众不同的价值。
同时,我们发现在此案例中充当了一般旅游吸引物的特点:刺激想象的马赛克文化拼图。后现代语境下的旅游吸引物首先需要满足人们的求新、求异体验,因而提供新奇的、虚构的刺激物可以对人们个体想象的虚构情境产生情感影响,使人们不断沉浸在“自我陶醉”的想象性体验之中。而所有一切神圣的东西在离开了特定时空成为一幅大拼贴的碎片之后,都成为对世界的仿真物。
旅游人类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旅游展演艺术;研究现状;艺术人类学
【作 者】魏美仙,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昆明,650101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92-005
Research on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Wei Meixian
Abstract:Bor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s the token of cultural transition in every type of local cultural tourism. Now academe mainly explains it with the view of the Tourism Anthropology and Ethnic Culture. Whether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s viewed a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adition of the invention,or is expressed in ideology and local self-identity,authenticity and mutual negotiation couldn’t show the difference from other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he specific association with the local cultural life. It’s no doubt that the mental method of Behavior Study and double unscrambling of Art or Culture on Back to Life of Art Anthropology has provided study view with great explanation for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Key words: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Actuality of study;Art Anthropology
在各种地方性旅游中,旅游展演艺术被作为旅游地文化展演的主要类别而呈现,主要行使“文化”展示而不是“艺术”表演的功能,因此,很多研究常常不分彼此地统称为文化展演。旅游文化展演是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学界对其关注主要在两个视阈中――以民族文化为焦点的文化变迁视野和立足于两种文化关系的旅游人类学视野,前者以文化传统和创新关系为主要论题,后者在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关系视角中展开研究,论题和取向多样化。
在民族文化变迁视野中,在切入角度、关注点、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呈现中学者对文化展演进行了或集中或分散、或明确或暗含的讨论,主要呈现为两种类型。
一是文化作为实体的传统文化取向。此类研究以全球背景下传统文化变迁为语境,集中关注展演文化的传统性。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开发”、“利用”、“发展”等问题进行不同向度的探讨,以“传统”作为基本支点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或“原汁原味”地保留“传统”,或对展演中文化成为“伪文化”、“伪民俗”的警惕与批判,或“合理”开发利用,或“创造性”地发展等等,都是以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作为现代文化的代表,以旅游冲击下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审视中心的解读方式,是对“传统”“能否变化”以及“怎样变化”这个焦点的不同折射。研究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差甚远,不再是“传统”,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就是“开发利用”中新价值的创造,文化展演活动就是文化传承保护的有利手段等。此类研究大多是全球化冲击下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民族文化的实际生存境遇激发起的感性认识和理解,大多是对民族平等团结、文化多样、民族发展等现实需要的回应,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相似的现实生存状况进行重复性描述,理论阐释的深度还有待于开掘。其中无论对个案描述还是理论阐释,大多并未把艺术展演作为专门的考察对象,只是在研究视角和阐述的脉络中隐约包含着对民族文化成为一种表演性存在的关注。
另一种是文化建构取向。此类研究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矛盾中对民族文化展演在二者互动中的建构进行阐释,超越了第一种对文化事象静态罗列的表述方式,从文化主体的角度出发理解文化展演对地方人群的意义,对文化展演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以文化事象为主的传统、保护、传承等话题,而转向民族文化传统“复兴”、“重构”,在传统复兴与重构现象中,文化艺术展演的生成性成为主要关注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延伸性探讨,对传统“复兴”与特定时期族群身份认同、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再生产等一系列文化发展中不同侧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关注市场、政治权力、民间文化等多种力量的互动,使“开发”与“产业化”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最具吸引力的话语。
旅游展演生存于旅游场域,旅游人类学在其对旅游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探讨中对文化商品化、文化商品的真实性、文化商品的族群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格雷本使用“第四世界”的概念描述传统地方性社会,讨论了旅游影响下民族地区艺术品的变化,文化的经济化以及当地艺术传统的复兴问题。①国内研究集中于国外理论的引介和运用相关理论对国内旅游文化表演进行个案研究。旅游人类学对文化艺术展演的研究,主要在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对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的真实性探讨从客源地大众与旅游地人群的关系视角出发,关涉到本地文化在展演中的真实再现和游客他者的感受两方面,内含了文化展演与地方“传统”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舞台真实”概念的提出。②对旅游展演“真实性”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学者在游客与旅游地关系互动中对“真实”的不同层面进行了区分,指出“真实”的感受不仅与旅游地文化的再现和游客的建构有关,而且游客也非同质化的,不同的个体对旅游展演“真实”的感受和理解有差异。对此问题探讨的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表述,同时,在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刘晖的《旅游民族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和张晓萍主编的《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三本著作中相对集中地对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二是文化展演中的地方性认同。学者大多认为旅游中的文化展演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而被作为地方性文化的表述方式,交织着地方人群的文化认同。“东道主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表达了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地方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解。”“当个人去思考表演中暗含着的、为国家所强调的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就会体现出对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多种建构。”③弗里德曼在谈到日本阿依努人的文化运动时,认为认同策略不是简单的文化差异呈现而是全球位置的问题,旅游业的生产和展示已经变成了阿依努人认同的有意识重构中的核心过程,其整个旅游节目是文化认同的更大构成过程借助商品形式的一种展示。④玛格丽特・萨克西安围绕着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发展,对由国家主办的旅游文化表演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⑤本迪克丝的《旅游和文化表演――发明传统为了谁?》以瑞士旅游胜地的个案为例说明传统发明与展演为当地人身份认同提供了手段。苏珊・露丝也以菲律宾个案为例说明村寨旅游展演对强化民族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⑥相对来说,国内对旅游展演中文化认同的研究无论是个案还是理论阐释都显得较为薄弱。
三是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旅游文化展演是不同文化相遇时的文化呈现,其中充满了不同文化权力关系的互动,与文化认同密切相连的是其意识形态性。霍尔等西方研究者认为,在西方都市博物馆和展览会上的土著文化展示中,展示的分类就是一种文化殖民的体现,⑦民族志博物馆的功效之一就是将“高级”艺术形式和“低级”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永久化。⑧金光亿认为,不同形式的生产和消费的民族艺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艺术特征也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反映。⑨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呈现了后殖民国家的旅游展演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组织者参与其中是对国家多元文化的工作,旅游景点超越了地方空间而成为国家的战场,意义被争论,认同被协商。⑩在国内,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得到了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旅游文化展演某种意义上是主流文化霸权的一种体现。史丹利、萧竞聪在《再现中国文化――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述评》中认为深圳民俗文化村的旅游表现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11]刘晓春认为少数民族的展演是一种权力关系不平等中的被动被看,具有内部殖民色彩,民俗旅游服务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诉求,是现代性话语对民间、边缘文化的政治暴力的一种表述。[12]在“被看”的命运中,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适合主流世界的修改,从而使本地原有文化遭到破坏和异化。
四是文化展演的互动协商性。以文化建构论为出发点,很多学者把旅游场域各种关系互动作为旅游展演生成和存在的关系网络,关注其互动协商中的建构。旅游文化表演作为一种交流行为,参与其中的游客和本地人之间进行着积极的互动协商,在协商中本地人的自我、认同、身份等得以建构。[13]其中有政府力量、民间组织团体、学者、旅游机构、当地人等各种主体力量的参与互动。社会学家科恩对东南亚各国发展“民族旅游”的两难和此过程中少数族群、旅游机构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协商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探索,[14]周星通过对贵州黔东南的民族风情村寨旅游个案研究对旅游中民族文化展示作为文化再生产、文化商品化、民族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关注了建构中主客双方的互动。[15]马炜从多种文化互动视角阐述村寨文化展演的建构,揭示文化展演生成和地方文化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16]
对旅游展演在文化互动中建构进行阐述时,学者关注到了产业化和文化再生产,如对旅游产品和商品的开发模式、措施手段等问题的研究。李蕾蕾等人以个案为基础考察了文化表演的产业化运作模式;[17]宗晓莲对旅游中文化变迁作为再生产的研究;[18]方李莉以个案资料分析了西部民族文化当代构成与生产状况,指出西部民族艺术通过“文化”“重构文化”的再生产图景,其中具体阐述了以地方性文化为再生产的原料,以国家、市场、学界、民间的各种“力”为动力的生产过程,并分析了各种“力”作用的具体方式。[19]以此为基点,学者对旅游展演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格雷本对艺术品涵化的研究涉及到了旅游展演中艺术品的发展变迁即艺术品涵化的生产过程与传统生产不同,他指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肯尼亚的康巴人,都在旅游市场中进行着不同于传统的工艺品生产。同时,他还对艺术品生产的特点、功能、前景等进行了论述。[20]戴琦就旅游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旅游不仅未对旅游地艺术和工艺品制造产生破坏,反而促进了古老的传统得以复兴。[21]李蕾蕾等人在对旅游表演的生产机制进行个案考察的基础上,指出旅游演艺是商业和艺术的混合,对艺术性表演与旅游演艺作了十九项差异划分,其中旅游艺术展演体现了几个明显的特征:表演内容的“混杂的文化主题、将文化碎片拼贴”,演员的“不强调核心演员,关注集体表演的场面效果”,“室外半室外场地”,道具的“人工制作与自然实物”,观众座位的开放、不设座位并多与景区融合,观众参与体验多以视觉和感官的身体体验为主而不是精神和意识体验。[22]徐赣丽以个案考察了旅游歌舞表演的建构手法和原则,认为表演歌舞不属于一种文化复制,而是主要按市场规则和商业化原则进行的文化再生产,其中很多传统文化要素发生了功能性转变,[23]同时她对表演的内涵、形式特征、影响等作了初步论述。[24]
以上立足于研究主旨与取向从问题探寻的不同视角和维度对旅游文化展演研究现状进行简略梳理,从中可以发现,对旅游展演的研究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旅游人类学视野都是聚焦于当代全球文化背景下地方性文化的变迁及其中各种复杂互动关系的分析,国外已进行了个案考察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对旅游展演文化的不同理论关注点。国内旅游业发展较晚,旅游文化展演存现时间较短,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作为民族文化变迁的描述和对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并初步运用于解释国内旅游文化展演实践。在目前研究基础上,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还有待于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拓展。
首先是个案研究中人类学整体观的落实。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奠基于文化整体观的基础上,艺术是一种文化,其实践、功能、结构、意义都与其所处的文化密不可分,应该作为文化的整合部分被研究。旅游文化展演的生成和存在与地方性文化密切相联,只有践行人类学研究的文化整体观,回到地方性文化生活中才能理解它。当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开放度,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旅游文化展演连接着大众消费和地方性文化,是两种文化边界中的关系性生成和存在,在此背景下,文化研究的整体观不仅是地方性文化生活的整体,而且是包含了卷入其中的当代各种权力关系的整体。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是文化书写的基础,在旅游文化展演研究中,虽然有学者对广西南宁民歌节的研究这样突出的个案研究成果,在旅游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及其运用于个案研究方面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对旅游展演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个案的浅层描述上,很多研究虽然关注个案,或称为个案研究,但仍限于对地方特色“材料”的运用以表述自己的主题,在理论和田野之间进行着一种倒转性研究,即个案不是研究的基础和事实,而成为论述或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未把展演放在地方具体人群生活中,只是把它分割为研究所需的文化事象,从而影响了对各种地方性文化展演差异的整体性把握及其不同运作逻辑的揭示。因此,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需要整体观中的个案研究,在扎实的个案支撑中构建相应的理论阐释,整体观的贯通与落实成为实实在在地面向现实生活、回到具体人群鲜活生活流的研究。
其次要明确具体研究对象。在当代民族文化研究中,明确地以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多,大多被包含在林林总总、大而化之的“民族文化”研究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层面或要素,而在对旅游文化展演的专门研究中,不论是集中论述还是略有涉及,又大多集中在共同的文化展演上,很少对其中的展演主体部分――艺术展演――单独进行考察,展演艺术总是被作为文化展演的局部进行研究。部分展演研究对艺术展演的关注已成呼之欲出之势,但总是被放置于笼而统之的文化展演中,而对问题探讨的实际向度又内在地以艺术为对象和参照,艺术展演成为文化展演研究中一根始终不断的暗藏主线,却总是掩盖在“文化”中。在人类学语境中,不论是文化还是艺术展演都包含了两个层面内容并呈现两种生存形态――文本以及文本展演,必须对文本符号与其实践方式即作为“文本”的艺术与作为行为“过程”的艺术双重解读,方能揭示展演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意义。
艺术展演作为明确研究对象的缺乏或含糊源自对艺术本体自身与一般文化符号不同特性的忽略,这种忽略又决定于研究者理论视野的局限,没有把研究对象作为“艺术”来对待,艺术生存的两个层面上的统一性完整性被人为地割离开来,对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展演艺术的关注遮蔽了对作为“文本”的艺术的关注,如对工艺品的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其自身所具有的符号特性。而很多对旅游开发中民族艺术的研究又专注于艺术本体,完全忽略了它是一种文化实践。单纯作为艺术的文本式的研究和作为文化的行为过程的研究都在艺术本体和文化解读之间顾此失彼。解决上述问题除了研究者应该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储备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在于理论视野的转换,注重对艺术展演的“文化”功能及其“艺术”特性的完整性阐述,如此,倡导“回到生活”和“行为研究”以及“艺术”“文化”双重解读的艺术人类学无疑为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科视野。[25]
最后还要关注展演艺术的建构生成性。在地方性旅游文化中催生的展演艺术,是在旅游场域中建构生成的,其中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复杂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性决定了其建构过程的地方性运作,也生成了展演艺术自身的特性。做为一种特殊场域生成的文化,对艺术展演的相关特性的把握不在于其已然存在的结果中,对其探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其生成过程,这样才能对其建构与发展变迁作出符合事实和逻辑的阐述,学界目前对旅游展演进行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化、保护传承、文化互动生产、文化产业等诸多问题的探讨都必须放在该文化自身生成的文化和实践逻辑中。目前研究中的“过程、再生产、建构、表演理论、当代构成、阐释、变迁”等关键词的提出表明学者已注意到了旅游展演艺术作为一个文化过程的动态研究,但总体上仍以展演艺术作为既定的文化事实存在为研究起点展开对其特点、功能、意义等探究,研究者往往从客位观点出发对已然呈现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所作的描述大都建立在对对象静止考察的基础上,只把它看成固定的文本,忽略了展演艺术是一个行为实践过程,所作阐述与旅游艺术展演自身生存实际有着相当的疏离,从而导致理论判断的片面或是武断。
在艺术人类学视野中,对展演艺术生成逻辑的考察就是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从具体层面看,展演一方面指“艺术的行为(Artistic action)”一方面指艺术的情景(Artistic situation)。[26]在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就是展演艺术的主体,它关联着艺术行为和艺术情景。旅游展演与地方人群生活密切相关,是地方社区“现实的”、“活”的文化,对艺术展演主体及其生活的关注成为解读的一个重要视角,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关注游客对文化展演的感受和理解,在文化变迁中对当地人与表演的关系进行研究,都涉及到了“过程”研究。但总体上学者对展演生成过程关注不多,更多的研究是把文化展演当成静态的客体性存在,而不是作为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过程,因此,它与地方人群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阐述,使展演对具体人群的有关价值、意义、感受等全都消失了,只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描述上。有学者认为,乡民艺术在当代逐渐从民族国家意识导引下的抽象化、符号化、工具化的政治价值开掘中走向乡民生活语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彰显被遮蔽的乡民自身主体意识。[27]主体意识是理解文化艺术实践活动的关键,对艺术展演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的关系思考无疑成为人类学回到“主位”视角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对展演艺术生存的生活语境的关注就是以地方人群及其生活作为理解的基础,把展演艺术当作生活过程放入地方人群生活流中去描述,在与地方文化互动生成的关系阐述中揭示当下地方性文化运作逻辑,得出趋近对象的解释。
有学者认为,现代旅游中越来越多地包含着对“艺术品”的审美需求,甚至“艺术之旅”已成为现代旅游中的一种类型。[28]民族旅游中对异文化的向往“实质上是立足于旅游者对自身的文化背景对‘异文化’的审美意象。”[29]而审美意象最典型而集中地体现在艺术产品中,很多旅游地的文化展演主要以艺术展演为中心,“在许多少数民族社区中,人们用具象化的形式,着意恢复和重新创造富有特点的民族文化,阐释文化遗产,并进而以此作为谋求更重要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手段,艺术正在作为表达政治意愿、展现族群性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族群更娴熟地加以运用。”[30]因此,在民族文化学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转换到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把它当作一个实践过程,关注它在地方文化中的运作逻辑,既是人类学研究整体观的践行,也能兼顾到它不同于一般文化的“艺术”特性,从而做出切合其生存实际的解释。
旅游人类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族旅游;符号;象征;解读
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消费的核心,是它构成对民族旅游消费的需求与供给,同时也促使了民族旅游活动的产生与完成。当某一民族文化纳入到旅游开发过程中时,就不再单独作为该民族的生产或生活方式,而被放置于旅游背景和范畴之内,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特殊意义。旅游是一种符号消费,作为人们追求的一种另类生活方式,旅游者对物的消费性质发生了变化,不再从使用角度来对物进行判断和消费,而是从物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价值认定,进而从这样的文化消费中获得身心满足。旅游消费于是成为一种将旅游者的社会地位、身份、品位、情趣、认同区分出来的象征消费。①
一. 民族文化中的象征符号价值解读
民族旅游符号的象征性源于各民族绚烂多姿、个性十足的独特文化魅力。“一个国家的民俗,如果其民族品格越鲜明,原始气味越浓,历史氛围越重,地方差异越大,生活气息越足,那么,正是一种最能吸引异国异域游客的特色旅游资源。”②地理单元的独特性和相对封闭性给予了各民族文化独有的品格,在这样独特神奇的民族文化资源基础上构建的民族旅游符号必然具有其象征性特点,不同民族的符号系统象征着特有的民族,表达、传递着各民族鲜明、特别的民族形象。民族旅游中的象征符号依据民族文化意义表现出能指与所指功能。如游客到一家傣味餐馆用餐,一方面,傣族食物作为一种“物”(符号的能指—signifier)可以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达到填饱肚子的功能)还可以让游客看到食物的外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游客通过这一行为,可以体验另一种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符号的所指—signified),体会到隐藏在食物背后的傣族历史与文化,使得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与旅游吸引物的两种指示功能发生互动关系,从而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要和心智想象。
二.民族旅游消费中的符号价值
在经济进程中,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各个地区所获得的发展的资本是不平等的,作为能够更新改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民族旅游地而言,必然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选择为宗旨,民族旅游地为了增强自身的造血机能,包括经济资本、象征资本的多种投入成为当地发展的关键,在人们的选择不能脱离历史与现实的条件下,经济资本越不足的地方,象征资本所表现的作用越为明显和重要。以云南少数民族节庆活动-----火把节为例,由于经济转型的推动,原生形态和半原生形态的火把节符号的指述、表现功能以及传达功能为了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新式火把节当中,节日的内容由对于祖先和神的崇拜转换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形成了“旧瓶装新酒”式的旅游需要,这体现了民族旅游作为资本的象征符号价值。
旅游过程中对民族旅游产品的消费过程是民族文化商品化过程,也是民族旅游符号化的过程,民族文化的商品化使民族文化成为资本,进入到民族旅游消费物的生产和消费中,极大的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使得旅游目的地发现地域文化的极大价值和作用。在消费社会“物”是一种符号,这是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的观点,物只有成为符号才能成为被消费的物,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消费者从原来单纯的对物的消费转向注重对物所蕴含的意义即象征符号价值的追求。因此旅游者对民族旅游的消费不仅仅是为了单纯的物质需求,更多的是为了体验民族旅游地的文化,民族旅游的象征符号背后隐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比它们本身的实用价值更为重要。作为民族旅游消费物的符号价值具有内在化的意义和外在化的两重象征特性。在旅游消费中,民族旅游消费物作为旅游者社会身份交流的一部分,当旅游者回到住地在他者面前进行展示和馈赠时,是对旅游者自我的呈现,旅游者将民族旅游消费物作为道具,以期待他者对自我的态度。民族旅游消费物在此意义上构建了人们所属阶层的等级和品位,民族旅游消费物成为旅游者自我外在化的象征,旅游者通过此消费物向外部世界确证了“我”的存在。某些时候旅游者消费民族旅游产品只是为了给自己留做纪念,这时它让旅游者确定并认同了民族旅游情景中的“我”的社会身份,获得了自我的确证。
注释:
①张晓萍. 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马晓京. 旅游象征消费对云南石林旅游商品开发的启示[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P205.
②杨慧等.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P286.
参考文献:
[1] 彭兆荣. 旅游人类学[M]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P267-273.
[2] 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p148-190.
[3] 罗康隆.论人文环境变迁对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民族研究,2001(4).
[4] 杨慧等.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P286.
[5] 谢彦君等. 旅游体验研究———走向实证科学[M]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p37-38.
[6] 张晓萍. 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马晓京. 旅游象征消费对云南石林旅游商品开发的启示[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P205.
旅游人类学范文第5篇
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L.Smith)出版了《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一书。作为旅游人类学的先锋之作,该书确定了“主客关系”这一旅游人类学的核心主题。2001年,史密斯和布伦特(Brent)编辑出版了主客关系研究领域的第二部力作《HostsandGuestsRevisi-ted:TourismIssuesofthe21stCentury》。随后,许多学者对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聚焦。Aramberri指出,①在旅游研究中存在三种主要的研究领域,即主客关系领域、②旅游作为非寻常行为的研究③和旅游吸引物的生命周期研究。④Nash特别指出,在所有的人类学研究案例中,研究的中心应该是主客关系。⑤并且Pearce认为,对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关系的研究是个涵盖面广、极富挑战性且越来越有价值的学术领域。⑥正是基于这些认识,McNaughton指出,旅游研究的焦点应实现一个重要转变,即由过去关注旅游和游客本身,转变到关注当地居民(主人)、旅游影响和主客互动上面来。⑦研究表明,民族旅游作为旅游现象的一种,其核心问题是民族旅游中的文化互动,即民族旅游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之间的交往,具体涉及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文化互动。⑧因此,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应是民族旅游研究的核心。尽管学术界对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尤其是在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方面,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
二、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研究述评:基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
从目前国内外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相关研究看,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主客互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正如有学者指出,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动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互动,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微观层面的社会互动。那么,根据微观社会学的理论,应重点关注这种人际互动的过程以及这种互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而研究的现实情况是,目前大部分旅游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游客和当地居民相互作用的结果上。⑨已有关于主客互动的研究内容多数侧重于从宏观的视角对主客相互影响的结果进行测量,即大量的文献聚焦在主客互动的性质及其结果上面。在民族旅游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倾向。①学者们对主客互动结果的研究较多,这种结果表现在主客态度、价值观、行为倾向、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或者由于游客的进入而导致民族地区文化商品化、文化包装、文化瓦解、文化复兴、示范效应、社会矛盾和冲突等文化、社会和经济影响的产生。这些研究往往偏向于对主客互动结果的一种宏观测量,而对主客互动的微观过程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即使有一些研究涉及了主客互动的微观层面,如对于互动内容与互动方式的探讨,但也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仅仅是一些零散的描述。笔者认为,如果要对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动过程进行微观层面的考察,深入探讨主客互动这种现象中互动控制所涉及的主体的角色、地位与权力等问题,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视角。Colton认为,对休闲、娱乐与旅游等相关行为的解释,只有通过符号互动论等社会心理学理论以及整体分析方法才能实现。
布鲁默指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是一种符号互动,人们通过运用符号来解释或确定相互间的意义。符号互动就是一个通过人们对符号意义的相互理解而激发的一个过程,意义构成了人类社会互动的基石。③符号互动论强调主体行为的产生,建立在主体对于符号意义的主观解读基础之上。对于人类行为和事物背后意义的解释,布鲁默强调,在对人类互动行为进行解释时包含了主观的经验,即从行动者的观点来理解事物。在主客互动之前,对于主体来说,客体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意义,客体的意义是主体在互动中赋予的,甚至可以说,客体是在与主体的符号互动中被创造、被肯定或被否定的。他认为,符号互动论的特征在于强调人类对彼此行动的解释和定义。个人被卷入一个巨大的互动过程之中,在这里他们必须对不断变化的行动进行相互的调适。个体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既要向他人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又要对他人的行动进行解释。④当个体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时候,个体会理所当然地对他人的行动进行意义的解读,而且认为对方对自己也同样如此。⑤而问题恰恰在于,已有的关于民族旅游主客互动方面研究,大都停留于互动现象的表面,比如互动的结果、特征、方式以及互动交换的内容,而没有深入到互动行为背后主体对于客体符号意义的解读,以及基于这种解读基础之上对行为的控制。当然,这里所说的“主体”与“客体”并不对应主客互动中的主人与客人。因为站在主人的立场,与其互动的“客体”就是客人;而站在客人的立场,与其互动的“客体”就是主人。并且在民族旅游中,与主体互动的“客体”不仅仅是主人或客人本身,还可以包括一切外在的物质或符号,比如主人的民族服饰、建筑、手工艺品、传统器具、特色美食以及文化符号(如纳西族的东巴文与东巴图画等),或者客人的潮流服饰、高科技装备(相机、手机、摄影机等)、露营设施、消费方式等。因此,对于主客互动的研究,必须关注主人或客人对于各种“客体”背后的符号意义是如何解读的,以及他们的这种对于意义的解读是如何影响他们对于互动行为的控制。此外,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这种“解读”离不开对具体情境的深入分析。这是因为,任何具有意义的符号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具有确切的意义。意义因情境而生,行动者根据他处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重组和改变意义。
也就是说,任何有意义的人际互动,总是在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社会情境中设计并实现的。对于外来游客而言,当他进入民族地区旅游后,就意味着某种特定的主客互动的情境就产生了。这个时候他必须对各种符号进行解释,并对情境进行定义,然后才开始行动。⑦为了理解这些符号并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动,游客首先必须对这些复杂的社会情境进行观察和解释。但也有学者指出,对任何情境的理解,首先必须确定的是参与者自身的角色。⑧因此,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过程中,当地居民和游客在各种境遇(即托马斯所说的“情境”)中的地位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对于理解他们的互动行为十分关键。诚然,主客互动不仅涉及某种具体的旅游情境,而且还将涉及互动过程中双方主体的地位、角色与权力等方面。而民族旅游主客互动双方的角色、地位与权力微观层面的问题,恰恰是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的内核,即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现象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首先,从角色方面来看,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动中,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往往视自己为主人,视外来游客为客人。而这种角色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Aramberri指出,随着民族地区旅游的发展,传统的主客角色关系会发生质的变化。事实上,主人不再是主人,而是服务提供商;游客也不再是客人,而是顾客。①不过Pearce认为,尽管主人的直接目的是获取利益,但他们在与游客的接触过程中,仍然要尊重对方、彼此诚信、开放、友好和真诚。②实际上,这种角色认知的变化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主体对于自己行为的控制,这一点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其次,从地位与权力的角度看,在游客互动的过程中,尽管少数民族居民可以控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以及提供的方式,但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落后的、弱势的。这种看法在很多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Li认为,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即将消亡的种群(dyingbreed),③他们给外界的印象总是停留在过去,并且是欠发展的。④而游客作为来自异地的汉族,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先进的、强势的。他们在民族地区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⑤他们可以控制自己,如何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货币以及如何消磨自己的时间。但现实情况是,有些游客进入民族地区之后,自己的这种“相对优势感”却淡化了,反而觉得自己受东道主的控制。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可以获得新的自我,这种自我就是库利的“反射的我”或“镜中我”(looking-glassself)。⑥即个体会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重新认识自我,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根据这一观点,要深入研究民族旅游中主客双方对于互动过程的控制,就必须考察双方如何通过从对方那里获得自我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三、民族旅游主客互动研究模型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