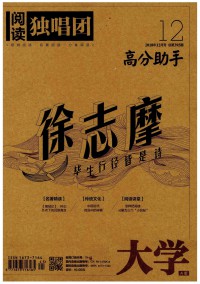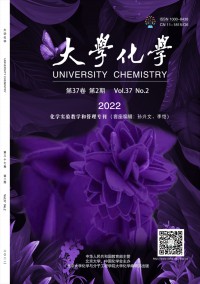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范文第1篇
卫礼贤;典籍翻译;互文性;《大学》;康德
H335.9A006108
在中国典籍外译的历史上,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是个不容忽视的名字。卫氏早年间,以传教士身份来华,在青岛从事传教、办学活动;后,与前清遗老交往密切,结交改良派人士;一战结束后,他退出教会,在德国驻北京公使馆任职,一度任教于北京大学,投身于国学热之中;返回德后,卫氏任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教授,主持成立了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为中西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卫氏一生最大的成就,当属他译介的“中国哲学及宗教经典系列”。这些译著以其卓越的翻译品质,至今畅销全世界,早已成为汉学家的必备书目。遗憾的是,如今无论在汉学界,还是在翻译界,有关卫译本的研究仍旧寥寥无几。有鉴于这一空白,笔者赴德国,搜集各种文献,力图依托真实史料,还原卫氏典籍翻译的原貌,同时从翻译学的角度,对卫氏的翻译思想、理念和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卫氏典籍翻译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构建经典间的互文关系,架起贯通中西哲学的桥梁。在儒家典籍的翻译上,主要表现为以康德哲学的要义诠释儒家学说。本文以卫氏1919/1920年版《大学》译稿为对象,分析研究卫氏对《大学》首章的翻译,阐明他“以经释经,以典释典”的翻译理念及手法。本文是笔者初步的研究成果,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外首次针对卫译稿的研究。笔者希望以此为今后的卫译本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开辟出一条可行的途径,并为典籍翻译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
一、 卫氏《大学》的翻译情况
就卫氏的《大学》翻译,就笔者所见,目前保留的手稿、机打稿、译文、译著中,至少有七个明显不同的版本,还不包括重复、修改、引用和节译,情况非常复杂。译稿残缺、遗失、年份不详等问题,也给文献整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卫氏于1904年首次刊登《大学》节译(Die Welt des Ostens, 1904: 3436),该文于次年再度发表。自那之后,卫氏就没有再公开发表过《大学》译文,直至1930年《礼记》译著(Li Gi. Das Buch der Sitten der lteren u. jüngeren Dai. Aufzeichnungen über Kultur und Religion des alten China)问世。本文分析的是卫氏1919/1920年版《大学》译稿①。这也是卫氏的《大学》首个全译稿。目前保留有:初稿Die hhere Erziehung、修改稿Die hhere Bildung(1919.1.141920.1.6)、机打稿Die hhere Bildung和讲稿Die hhere Erziehung(1919)。根据手稿的情况,可知卫氏初稿,已有三次大的改动,誊抄到修改稿时,与初稿最终译文,又有很大的出入,随后修改稿本身,又经历新一轮修改,机打稿的内容,与修改稿基本一致,不过也有改动,而修改稿之后,也有新的批改,总之前前后后,已经修改过无数次。《大学》讲稿的用途,目前尚不明确,但应该不是课堂材料,可能是卫氏讲演所用,保留的也是原稿,不过后面内容有缺失。根据初稿可知,卫氏所用底稿为朱熹的《大学章句》,包括《大学》全文及《大学章句序》。书名下方注明“据原传本”(Nach der ursprünglichen berlieferung)。卫氏这一版译稿,不但内容最全,修改次数最多,而且有机打稿,可知曾打算出版,虽然未付诸刊印,但许多译法和注释都在终版译文里保留,所以格外重要。以下仅就《大学》首章,依次分析各段译文,说明卫氏典籍翻译的基本思路及方法。
徐若楠:构建中西经典之间的互文性
二、 “明明德”与“理知本性”
原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译文:Die hhere Bildung führt zur Luterung der ursprünglichen guten Anlagen, zur Liebe zur Menschheit und dazu, dass man sich die hchsten Ideale als Ziel setzt.本文所引的译文,全部是第二稿的最终修改版。
《大学》开宗明义,阐明“大学”的宗旨,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朱熹称之为“三纲领”。这是《大学》全书的精髓。在这里,卫氏将“明明德”译作“净化原初善的秉性”(Luterung der ursprünglichen guten Anlagen)。在第一稿中,曾有过“澄明原初清澈的天生秉性”(Klrung der ursprünglichen klaren angeborenen Anlagen)、“澄明清澈的秉性”(Klrung klarer Anlagen)两个译法。无论是哪种表述,意思都是一样的。卫氏说,所谓秉性或天资(die Anlage),指的就是人的本性(die Natur);因人的本性源自天,清澈而透明,故而称为“原初善的秉性”。卫氏在初稿中,解释说:
人的这一天性,是精神的、理知的、理性的,它是神性理性的一部分,因此是纯粹而光明的。原文:Die geistige intelligible, vernünftige Natur des Menschen ist, weil Teil der gttlichen Vernunft rein und leuchtend. Eisler 编的《哲学概念词典》,是最权威的德国哲学概念词典,也是卫礼贤使用的主要工具书。
这番话完全是康德哲学的表述。康德哲学的根本,在道德律观念的确定。康德讲道德律,提出三条原则,即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律。第一条普遍立法,即要求任何时候,人的意志准则同时应是某一普遍立法的原则。而普遍立法成立的前提,就是假设存在“普遍的神性理性”(die allgemeine gttliche Vernunft)。康德借用一系列基督教概念,提出了“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的公设,从而以神学作为其道德哲学的支撑。而康德追求的道德世界,就是一个“超越世俗的、理想的、纯粹的理知世界”。
如果某种认识可全部或部分地通过纯粹的思考来获得,那么就被称为是“理知的”(intelligibel)。认识的方式“合乎理智和理性”(verstandes, vernunftmig),就叫作“理知”。“理知”与“智识”(intellektuell)不同。人通过理性获得某种认识,但这个认识本身也在感官可以抵_的范围内,这叫作“智识”。而当我们认识的对象超出了感官的世界,只能靠理智去想象,这就属于“理知”了。理知无法被认识,也无法被证明,即使理论上也不可能。理知的功能在于,它可以限制人在运用理性时,仅凭自己的经验做出主观臆断。换言之,理知作为纯粹的理性思考本身就是神性的。
卫氏解释说,人的精神本质,原本纯净无瑕,因在物化过程中,与之相连的心灵和外部世界交织,致使人的本性受到了污染。这个物化的过程,卫氏称为“empirische Erscheinung”。这是西方哲学的说法,意思是精神实质具体成形为经验性的事物。“Erscheinung”指的是“现象”,是与本质相对的哲学范畴。康德说:“自身不属于现象的,我称之为是理知的。”(转引自Eisler, 1910: 589)原文:Ich nenne dasjenige an einem Gegenstande der Sinne, was selbst nicht Erscheinung ist, intelligibel.“empirisch”意思是“经验的”,是相对于“先验的”(transzendental)、“超验的”(transzendent)、“先天的”(a priori)这类范畴而言的。所谓“经验认识”(empirische Erkenntnis),是指人通过后天的(a posteriori)感性经验所获得的认识,与“理知的”认识相对。在康德哲学中,原初的、纯粹的理知世界,与后天的、经验的现象世界,构成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
卫氏说,人的天性是善的,可是现实生活中,却常见人性之堕落,这个长久以来的谜题,在宋儒那里得到了解答。朱熹提出了著名的心性论。他认为,心只是一心,或觉于欲,或觉于理,故有人心、道心之异。卫氏在1914年《中庸》译文里,用“期望”(das Wollen)和“应当”(das Sollen)这对康德哲学的范畴翻译“人心”和“道心”。同样地,性也有两类,一为天命之性,一为气质之性。二者同出于天理,但因“气质所秉”不同,有“昏明薄厚”之别,故而有所分殊。说:“本然之性,纯理也,无差别者也。气质之性,则因所禀之气之清浊,而不能元偏。”(,2010: 91)
朱熹注: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卫氏将“天命之性”、“本然之性”译作“人的理知本性”(die intelligible Natur des Menschen),将“气质之性”译作人的“经验本性”(die empirische Natur)。这完全是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格义了朱熹理学的范畴。卫氏说,按宋儒的说法,人的理知本性是善的,经验本性则因人而异,它可能是善的本性,也可能是阴暗的本性,宋儒通过这一区分,解决了人性问题的矛盾。而所谓“明明德”,就是要净化人的天性,使人脱离经验本性,重返人的理知本性,这就是教育的作用。卫氏在《教育哲学讲义》中写道:
性之为说,纷无定论……然人之性,纯以善恶分别之,似俱不妥。盖其所谓性者,起点不同,故所谓善恶亦不同。欲之性质,须先明何谓之性。性可分为二种,一即人类公性,一即个人私性。前者为先天的,后者为后天的……教育作用,即俾后天之恶性,入于先天善性之中,即使人情,变作仁性而已。故教育之说,莫善于大学。所谓在明明德者,即是理也。
三、 “新民”与“另更心性”
卫氏说,人皆有善的天性,只因久在尘世,沾染了恶习受到蒙蔽,人必须通过教育,重拾自身纯净的本性。而教育的使命,不仅在教人净化自己,也在于帮助他人净化自身。故《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卫氏在第二稿中,将“亲民”译作“爱人”(die Liebe zu den Menschen),并一直沿用到最终版中。不过,在初稿中,卫氏曾将“亲民”译作“更新他人”(Erneuerung der anderen Menschen)。“亲民”二字,向来有作“新民”解。朱熹注曰:“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卫氏在初稿中亦解释说:程、朱二人,皆读“新民”,意思不是“爱人”,而是指“更新人性”。而德语“erneuern”一词,既有更新的意思,又有修复的意思,所以“更新人性”,也可理解为朱熹的“以复其性”。卫氏在《教育哲学讲义》中说:
西洋人性论,约有二元:
一即自犹太教入基督教又入于哲学……犹太教经,谓人为上帝所造,亦为性善;及入世后,为外物所诱,即失本性。教育功作,即复其本性是也……基督绝对提倡性善。性虽不能变化,然必须追其己放之性,使复本原。至后世基教。已失基督本意,久而渐变为性恶之说。非特谓个人性恶,且谓自祖宗传来,无法挽回:唯信基督,乃能另更心性。此等说法,于西方思想潮流,颇有影响。
卫氏在这里,将“复其本性”的思想,与基督的“另更心性”相提并论。而基督教的善恶说,正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来源。康德认为,人具有向善的禀赋,可是也有恶的倾向,这倾向不是天生的,不属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自然本性。关于恶的起源,康德采用了基督教的原罪说。康德认为,人要救赎自己,就必须弃恶从善,而弃恶从善的前提,就在于“实践理性”这一道德立法没有腐败。所谓重新向善,康德称之为“重建向善的原初享赋”(转引自李秋零,1997:31)。这重新向善的禀赋,不是人所建立的,所以也不因人的堕落而丧失。换言之,这善的禀赋乃是神赐的。人唯实行道德律,才配领受神恩。在《大学》讲稿中,卫氏说,诚如耶稣所言,纵使人曾经堕落,仍然可以改过自新,重新向善。这正是“新民”二字的真谛。
仍存怀疑者,可再看下面一证。卫氏1904年版《大学》译文中,将“正心”译作“die Rechtbeschaffenheit des Herzens”。德语词“Rechtbeschaffenheit”为基督教神学术语,词根“Beschaffenheit”是性质、质地之意,词缀“recht”原是正确、正当、合理之意,又可引申为权利、资格。“Rechtbeschaffenheit”一语双关,既指人原初的本心之正,又指人有权获得永生。基督教教义认为,人心的基本特性(Grundbeschaffenheit)造就了人的行为。人犯下原罪后,丧失了本心,无法行神的律法,因得不到神的接纳,无法获得永生。但因基督徒的缘故,神对人格外施恩,所谓施恩的意思,不只是说神同情人,还指神放了某样东西在人里面,进而赋予了人某种特质,使人的神性得到了“更新”。在经院哲学术语中,这叫作“神灌注给人一种恩赐的习性(Habitus),可以译成‘一种精神禀赋’”(Joest, 1981: 4)。这一灌注通过圣礼完成,主要是受洗。人获得了新的心质,便可以行神的律法,通过积累功德,使自己有资格领受神恩。现在就看每个人的表现了。如果能守住“恩赐的天赋”,同时认真加以运用,尽量多积德行善,使其还能更加稳固,那么到最终审判时,神便会准他升天堂。反之,若自甘堕落,戴死罪离世,就将万劫不复。因此,基督教所谓“gerecht”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人复归其神性本性;二是指人配受神恩获得永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卫氏将《大学》所谓“亲民”,与基督教所谓“另更心性”相联系。
卫氏说,各种人性论观点,中国先哲都有论述,而各家各派,无论是主性善,还是主性恶,皆认同一点,那就是文化教育之必要性。这一是要相信,人能够改过自新,即在人的本性中,始终有善的天赋,二是要知道,如何能够改过自新,即如何发掘人善的天赋。而恰恰是在这两点上,卫氏感@道,中国哲学体现了其伟大之处。
卫氏说,“爱,或者更新,就是帮人净化他们的天性”。这里有两点,一是人自身如何行为,二是人在社会中如何行为。《大学》讲“明明德”,即谓个人方面,讲“亲民”,即谓社会方面,足见两者并重之意。在《教育哲学讲义》中,卫氏评价道:
自历史上观察教育,约分为两种:一为偏于社会的,一为偏于个人的……偏于社会的教育者,如柏拉图(Plato)、菲西(Fichte)、那他不(Natorp)等及中国法家申不害、韩非等皆是也。偏于个人的教育者,如卢梭(Rousseau)、黑巴(Herbart)等及中国杨朱等皆是也。然二上皆执其两端而言,不适中道,故有两派意见合而统一者,如高德(Goethe)及中国孔子等皆是也。
卫氏解释说,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要有崇高的理想。理想终归是理想,永远不可能达到,但它却是激励人的动力,人必须有高远的目标,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人类的终极的理想,就是至善,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追求的方向。卫氏说,这种坚定不移的实践精神,正是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态度。而至善的理想,是人净化自身和更新他人的共同标准,也是整个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
另值得注意的是,卫氏虽意在构建中西经典的互文性,却也留意避免概念的混同。在译文中,他就有意不用康德的“die hchste Güte”翻译“至善”,而是意译为“最高完满”(die hchste Vollkommenheit),后改为“最高理想”(die hchsten Ideale),把“至善”的涵义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在康德那里,至善理想(Ideale hchste Güte)是“纯粹理性最后目的之规定根据”(邓晓芒,2008:71)。所以在“至善”一词的翻译上,卫氏反倒更加谨慎,并不直接制造语义的对等。
四、 “意志形成”
原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译文:Wenn man sein Ziel kennt, so gibt das Festigkeit des Entschlusses. Ein fester Entschlu allein führt zur Ruhe des Gemüts. Die Ruhe des Gemüts allein führt zum Frieden der Seele. Der Friede der Seele allein ermglicht ernstes und besonnenes Nachdenken. Ernstes und besonnenes Nachdenken allein führt zum Gelingen.
《大学》开篇首句,讲教育之要义,在复自己与他人之本性,以求达到最高的完满。这句承接上文,讲人为何要有目标。卫氏说,一切教育之根本,在于意志的形成,而要形成坚定的意志,就必须要有目标,没有目标,意志就依据心情,起伏不定,有了目标,人就有了追求的方向。卫氏解释说:方向,使人意志坚定;意志坚定了,心境就会安宁;心境安宁,人方可感到满足。所以,最重要的是静,静下来,一切自然井然有序。安宁带来沉思,沉思带来成功。这就是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卫氏将教育的基础归纳为“意志形成”(Willensbildung)。他解释说,人有了坚定的意志,才能把持住自己的心,把持住了自己的心,意志反过来也就坚定了。当意志的方向指向探究世界的法则,便会产生敏锐、准确的思想,通过践行这一思想,原初的善就会得到理解,所以意志形成是一切的基础。“意志形成”也是康德哲学的重要概念。康德认为,道德律是内化的准则,是自律意志形成的一种准则。卫氏说,自古以来,凡智者谈教育,皆认为“坚定的意志和自制的心灵”乃是教育的土壤。康德J为,人天生有善的禀赋,但在后天的生活中,需要通过道德教育,约束自己的动物性,发掘并施展自己的天性,从而形成善良意志。因此,在康德看来,任何一种教育理念或学说,都应该揭示一种教育的理想。卫氏在《教育哲学讲义》中,一再重申“教育须有根本主张”。换句话说,教育归根结底在于意志的形成。卫氏说,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要什么,不懂得运用“期待”(das Wollen)的力量,就永远为外界所困。因之,卫氏在《教育哲学讲义》中说:
怀疑主义,因知识上既无定,行为上亦无准,故有实用主义。所谓实用主义事实上绝无目的,如船在海浪,飘摇无定,但求不沉,无所谓方向也。实则虽暂不沉,终非长久之道。故希腊辩论家,谓“人为万事之标准”。虽能各自谋幸福,然希腊公共文化,因此坏矣!故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盖知止为得之本,即成功之始也。为无行为目的,终于外物役,故康德实践理性之批评考查行为之本,而自法他行为,Heteronomy推及自法行为Autonomy始得真正自由行为之平。
五、 “意志表达”
原文: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译文:Jedes Ding hat Stamm und Verzweigungen, jede Handlung Ende und Anfang. Dadurch, da man erkennt, was zuerst und was nachher kommt, nhert man sich dem rechten Weg.
依照卫氏的解释,上段讲“意志形成”,这段讲“意志表达”(Willensuerung)。上段最后,讲“虑而后能得”,卫氏在初稿中译作“选对手段,目的方能达成”。原文:Kenntnis der angemessenen Mittel zum Zwecke führt zur hchsten Weisheit.到了这段里,他注解说:现实存在“确定的因果次序”(eine feste Anordnung von Ursachen und Wirkungen),这个次序是单向的,即因包含在果里,所以人的行为,也要有相应的次序,先有开始的基础(Grundlagen),后有最终的结果(Konsequenzen)。他在1919/1920年版译稿中,将“本”和“末”分别译作“根”和“枝干”。他在讲义中解释说,万事万物都有根基,此乃先决条件,在此根基上,才生出枝干部分,所以人了解事物,也要抓住事物根本,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智慧。卫氏说,人观察事物,总是先见枝干,绝大多数人,看不到问题的实质,纠缠于细枝末节,最终疲惫不堪,仍然一无所获,若想抵达事物的根本,光靠观察是没用的,还必须通过思考,看透事物的本质,而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其余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分清主次先后,这是一切意志表达的基础。而遵从“确定的因果次序”,就是指人的行为要合乎道德律。卫氏在1904年的译文中,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译作“主导人事的,与自然界一样,是合规则的因果关系”原文:In den menschlichen Angelegenheiten herrscht, ebenso wie in der Natur, ein gesetzmiger Zusammenhang von Ursache und Wirkung.所谓合规则(gesetzmig),即是康德所谓的合道德律。另外,“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译作“要获得最高的智慧,就要懂得以恰当的手段达成目的”原文:Diese richtige Wahl ermglicht Erreichung des Ziels.。我们知道,康德的道德律,强调的正是“目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 der Zwecke),强调不仅达成的目的应当符合道德律的要求,就连达成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也必须是正当的。康德从理论上,驳斥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观念,在哲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卫氏通过翻译,将“本末”、“始终”、“先后”等儒家哲学的范畴,转变为了“因和果”、“手段和目的”这类西方哲学范畴,可以说是对《大学》进行了彻底的脉络化。卫氏在《大学》讲义里写道:
科学的任务,一是要正确地反映世界,反映我们意志表达的任务,二是要找到实践规范,使意志表达和谐且合规则。在实践确认过程中,必须也要考虑到,人乃是群居动物,所以必须有实践规范,让人们能够在目的王国中理性地共同生活。原文:Das Ziel der Wissenschaft ist demnach einerseits sich ein richtiges Bild der Welt zu machen, in der unsere Willensuerungen sich abwickeln und andererseits praktische Normen zu finden, damit diese Willensuerungen einstimmig und gesetzmig werden. Bei der praktischen Besttigung ist aber in Betracht zu ziehen, da der Mensch mit anderen Menschen zusammenlebt und da demnach Normen gefunden werden müen für ein vernunftgemes Zusammenleben der Menschen in einem Reich der Zwecke.
六、 “格物致知”与“实践理性”
原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译文:Da die Alten auf dem ganzen Erdkreis die ursprünglichen guten Anlagen lutern wollten, ordneten sie zuerst ihr Land; um ihr Land zu ordnen, regelten sie zuerst ihr Haus; um ihr Haus zu regeln, veredelten sie erst ihr eigenes Leben; um ihr Leben zu veredeln, strebten sie nach der rechten Gemütsverfassung; um die rechte Gemütsverfassung zu erlangen, strebten sie nach Wahrheit der Gedanken; um wahre Gedanken zu bekommen, strebten sie nach vollkommener Erkenntnis; vollkommene Erkenntnis beruht auf dem Erfassen der Wirklichkeit.
《大W》首章最后一段,卫氏解释说,按照正确的次序构建人事,乃是一切成功的秘密所在。任何人类活动,皆以世界和平为终极目的,而实现世界和平,当以个人的修养为前提。他解释说,人先是自外而内,由末逐本,再是由内而外,按照时间顺序,逐一实现目标。这是双向运动,先是自外而内,是抽象归纳法;再是由内而外,从中心向外推展。换句话说,就自然来说,是先有了根基,然后才是枝干;就人为而言,则是先明确了目标,再反推实现的条件。所以人类社会,从家庭到国家,都是有机的组成,家庭次序的建立,以个人教育为基础,而个人教育的根本,在于健全人格的塑造。在卫氏看来,人格健全完整的人,也就是“理性的人”。他指出,朱熹主张以丰富的理论知识作为正确道德决定的基础,而王阳明则认为,人只要克服自私,行为自然会合乎道德认识。朱熹注重内心的同时,也注重外部的现实,王阳明则是完全的唯心论,与歌德的观点如出一辙。卫氏说,在王阳明看来,所谓“格物”不是说,人要从理论上去研究外物,而是说人要在实践当中,穿透一切自私的遮蔽,直抵人性的核心,直抵“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原文:Erfassen der Wirklichkeit ist für ihn nicht eine theoretische Beschftigung mit den Objekten der Auenwelt, sondern ein praktisches Durchdringen durch alle Hüllen und Hinderungen, die aus dem Egoismus entspringen, zu dem Kern der Natur, der den Menschen im Herzen ist, dem moralischen Gesetz in uns.。他引用王阳明的话说:“理解现实,在于消除一切虚假,使心中的驱动力,只有源于理性者。”原文:Die Erfassung der Wirklichkeit besteht darin, da man alles Falsche wegrumt u. dafür sorgt, da man in seinem Herzen nur davon bewegt wird, was der Vernunft entspricht.
卫氏将“格物”译作“实践地理解现实”(die praktische Erfassung der Wirklichkeit)。在初稿注释中,卫氏解释说,天下根植于国家,国家根植于家庭,家庭根植于个体。个体的主宰是心(Gemüt);主宰内心的,是恒久的意愿(die stetige Willensbereitschaft);诚意的前提,是有充足的知识,这样才有“合乎理性的行为”(ein vernunftgemes Handeln),而知识的完满,是通过对现实的理解达成的。在卫氏看来,这一因果关系层层递进,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实践理性的至上”(das Primat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他解释说,人的认识有误,行为必定失当,只有彻底认清现实,人的认识才会完满,方才能达到“致知”。因此所谓“致知”,卫氏初译作“寻求理性”(suchen sie ihre Vernunft),终译作“完全自己的知识”(vollendeten sie ihre Erkenntnis)。卫氏在《教育哲学讲义》中写道:
盖本身教育,为一切教育之最要者。因恒以有意识的关系,常自督责,故大学特重正心,诚意,致知三步也。本身教育,为一切教育之基础。
卫氏在《大学》译稿中,将人的天赋之德诠释为“理性”,将“知行合一”的境界说成是“以实践理性为动力”,又将“e矩之道”直接译作“理性法则”,这里因篇幅有限,无法进一步加以说明,但总而言之,卫氏从康德的实践理性出发,阐释《大学》要义的思路清晰无疑。他早在1906年,就在青岛讲康德时指出,“在康德看来,哲学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教人以知识,使人成为人。康德在哲学领域的努力,就是为了让人不再沉迷于对外部世界的追求,回归自我”原文:Die wichtigste Aufgabe sah Kant darin, Menschen zu lehren, was er wissen mu, um Mensch zu sein. Seine Tat auf dem Gebiet der Philosophie ist so, da er die Menschen, die im Streben nach der Auenwelt versunken waren, zurückgeführt hat auf sich selbst.。卫氏说,孔子与康德尽管在时间、空间上都相距甚远,背景、经历也大相径庭,却恰如孟子所言:“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可见他贯通孔子与康德的想法早已有之。而据卫氏自己说,他成立尊孔学社的初衷,亦是思拯救中国文化于危难,“遂决定,通过翻译、报告和科研著作,推动东西方在精神领域的联系与合作”。而这一使命的重要工作,就是将康德的著作译成中文,将中国的经典译成德文(Wilhelm, 1926: 172) 。原文:Der Gedanke war, dazu beizutragen, da die Schtze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die damals uerst gefhrdet waren, auf die Zukunft gerettet würden. Anknüpfung und Zusammenarbeit auf geistigem Gebiet zwischen Ost und West sollten durch bersetzungen, Vortrge, wissenschaftliche Verffentlichungen bewirkt werden. Kantsche Schriften wurden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 chinesische Klassiker wurden verdeutscht.
本文针对卫氏1919/1920年版《大学》译稿,通过对《大学》正文首章的分析,说明了卫氏翻译《大学》的基本思路,是用康德哲学的逻辑来诠释儒家思想。他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康德化”,意图构建哲学经典间的互文关系,从而架起贯通中西哲学的桥梁。这种“以经释经,以典释典”,是卫氏典籍翻译的基本理念及方法。但要确定这一点,仅仅依靠卫氏的译著,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切实掌握真实情况,以手稿、讲稿等史料为依据,才能断定卫氏经典互释的背后,确实有着对翻译目的和策略的全盘考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卫氏译稿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卫氏的每一版译稿,都是他后m翻译的铺垫,为学者真正了解卫氏的翻译观,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依据。因此,本文首度尝试译稿研究,依托从未发掘的史料,探究卫氏的典籍翻译过程及思路,相信不仅对卫氏翻译思想研究及中国典籍外译研究将有所贡献,也会为海外汉学研究、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带来有益的启发。
. 中国伦理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 邓晓芒. 康德对道德神学的论证 [J]. 哲学研究, 2008(9): 7075.
[3] 李秋零. 康德论人性根本恶及人的改恶向善[J]. 哲学研究, 1997(1): 2833.
[4] Eisler, Rudolf.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 [M]. Berlin: Ernst Siegfried Mittler und Sohn, 1910.
[5] Wilhelm, Richard.Die Seele Chinas [M]. Berlin: R. Hobbing, 1926.
[6] Wilhelm, Richard, and Dschung Yung. Mass und Mitte [J]. Chinesischdeutscher Almanach, 1930(5): 1335.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太极拳 文化内涵 翻译目的 文本英译
太极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以显著的养生保健功效和精深的文化底蕴,成为很多人健身的重要手段。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一体化,独具民族风格的太极拳已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深得国际友人的青睐。然而由于太极拳的中国特性让许多不同国际文化背景的习练者很难理解和把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太极拳的传播,因此太极拳如何在国际上高质量、高效度地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太极拳的翻译质量。这就要求译者全面透彻地理解太极拳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建立起太极拳习练者能够理解、易于接受的通道,展现原汁原味的太极拳文化,达到准确、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一、太极拳的文化内涵
太极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晶,深受中国古典儒家“天人合一”思想,道家“阴阳相济”思想,以及孙子“以柔克刚”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充满智慧的太极拳文化内涵。
(一)哲学理念
贯穿于太极拳中的“天人合一”是太极拳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太极思维的灵魂。“天人合一”主要是要求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它主要体现在太极拳的名称、动作及外形内气上。首先,太极拳在一些名称上多采用自然界的动物形态命名。例如,“野马分鬃”、“金鸡独立”等,这样的名称更容易让人感受到自然的魅力,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其次,太极拳的动作讲究虚实、开合等转化,旨在让人身体动作和谐统一,最终实现天人合一。最后,太极拳在运动中强调“内外合一,形神兼备”,将人的身体外部形态与内部气、神结合统一,达到主客体的相互融合,是“天人合一”的集中体现。
“阴阳相济”是我国古代道家的核心思想。太极拳经典著作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开篇就说:“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应,动缓而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为一贯。”“阴阳相济”包含了丰富的中国式朴素辩证法:宇宙万物都包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阴阳矛盾,都是阴阳消长和对立统一的。太极拳的阴阳、动静、刚柔、虚实等方法就体现了这种理念,在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生,阴阳互根的中和条件下通过人的意识指挥人体随意机能,使它们按照阴阳互变规律进行运动。
太极拳在攻防上强调“以柔克刚”的根本宗旨正是我国兵家文化核心思想的体现。所谓“柔”与“弱”并非软弱无力,而是一种含蓄、深沉、坚韧不露、外柔内刚的状态。太极拳其应敌原则是以小制大、以静制动、避实就虚、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后发制人、以弱取胜等就是利用意念和智慧,花费小的气力,博取大的成功,展示出了太极拳这种以弱胜强、以小搏大独特的技击思想。
(二)民族特征
创立于中华传统农耕经济文化氛围中的太极拳,其拳理无不映射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中庸之道”。中庸之“中”为适应之谓;中庸之“庸”为经久不渝之谓。中庸又进而演为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之意。作为“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方法论,被应用于太极拳之中,可归纳为行拳走架“求中”、意念动作“守中”、技击原理“用中”:身型的“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太极拳无论是行拳还是站桩,都要求身体上下、前后对准成一条直线,不凹不凸,不偏不倚,节节贯通,自然成直,正是不偏不倚的表现。意念“守中”是太极拳修炼之心法,即练习太极拳注重以意念引导动作,培养“中正之心,平和之气”。动作上强调“发劲上下相随,立身中正不偏,曲中求直”。体现了“无过不及”、“不偏不倚”的顺从自然常规节律的中庸精神。
(三)审美意境
太极拳极具中国古典美学之要素,从名称、动作到姿势,无不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享受。太极拳以内在的含蓄与整体的和谐为特色。内在的含蓄以讲求沉稳凝重,外示安逸之神,加之动作刚柔相济、虚实互换,到达潇洒从容、心地坦然、神态自若的意境之美。太极拳中国古典美学的另一表相是追求“身心合一”整体和谐。太极拳的立身中正安舒,支撑八面,运动时一举动周身俱要轻灵。有上即有下,有前则有后,有左即有右;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相济,表现的就是阴阳调和互补的整体和谐之美。
二、探讨太极拳文本的翻译对策
太极拳以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为理论依据,结合中国传统的哲学、养生学、军事学与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太极拳的这些特点和风格所展现出的民族文化理念,大都在西方文化里缺乏相应的对应物,属于文化的缺省部分,在翻译成英语时最难进行语言转换。要想建立译语受众能够理解、易于接受的通道,把太极拳的精髓和要点有效地传达出来,必然要求译者能够全面、透彻地理解太极拳的拳理和文化,在翻译中根据译文的交际功能进行不同等级的语际转换,在译语中展现原汁原味的太极拳文化。
(一)太极拳文本翻译的目的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翻译目的决定译文是否需要连贯,是否应该忠实于原文。换言之,它决定翻译的具体策略和方法。太极拳语言翻译的目的不仅是传播太极拳的技巧,更是再现太极拳蕴涵的文化内涵,促成太极拳的国际化,达到借助太极拳传播中华文化内在精神之目的。
(二)太极拳文本翻译的策略
1.音译加文化注释
太极拳是以古代阴阳学说为理论依据,采择诸家拳法精华创编而成的。太极拳的这些特点和风格所展现出的东方文化理念,在西方语言里缺乏自然对应物,属于文化的缺省部分,是文化交流中最难翻译或转换的。因此,在太极拳的翻译中,就要补充译语文化中的缺省,应采用音译加注法。例如,“太极”、“无极”和“阴阳”是太极拳的重要哲学术语。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表达,因此对“太极”、“无极”和“阴阳”最好在音译的基础上增加解释的翻译方法,“太极”可以翻译为:Taiji,in terms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refers to the universe-forming essence,it also means the supreme ultimate,hence Taiji quan is the Metaphysical boxing or the Supreme-and-Ultimate boxing;“无极”译为wuji( infinity);“阴阳”译为yin and yang,a term of Taoist cosmology,refers to the two forces through whose essences the universe was produced and universal harmony is maintained. In gereral,Yin has more to do with softness and receptivity,a more emotional energy,and often includes movements that are lower ( of the earth).Yang has more to do with hardness and creativity,a more muscular energy,and includes movements that are higher (representative of the sky).”
2.保留原语文化形象
太极拳拳路名称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形象的思维特点,其中既有动物形象,又有人与动物形态合一的形象。这些形象化的名称使动作富于意向和想象,一方面便于习练者结合想象思维揣摩和体会动作,掌握动作要领,领会技击作用,另一方面能够概括太极拳行云流水、舒展大方的运动特点。对于这些动作的英译一定要注意保存原语文化中的文化特色。对于与动物形象相关的动作,翻译时既要注意原语文化的象形特色又要注意其功能意义。如“揽雀尾”这个动作好似在捋顺孔雀的尾巴,因此可以译作smoothing the peacock’s tails;“白鹤亮翅”可译为white crane spreading wings;“野马分鬃”可译作parting the wild horse’s mane;“金鸡独立”可译为rooster standing on one leg;对于借物拟象、以象导动的动作名称,在翻译时也要尽可能保留原语的文化形象。“玉女穿梭”可译为maiden waving the shuttles;“上步七星”可译为stepping forward and forming the shape of the Dipper;“单鞭”可译为waving single whip。
3.直接借用译入语
太极拳翻译向读者首先要传达的是其技术要领。如果原语中词语的所指与英语文化在语义层次上具有同一性和可理解性,则译者可直接借用译入语约定俗成的名称,更有利于西方读者了解和接受。如太极拳拳谚中的“以柔克刚”可以译为to conquer the rigid with the soft,“四两拨千斤”可译为to move thousand cattle with four tales,再如太极八法的“扌朋”,是以臂向前,承接和化解对方手或臂的来力,可翻译为ward off;“捋”,接扌朋的势头将对方来力送向左侧后方,可译为roll back;“挤”,是用小臂挤击对方身体,可译为forward press;“按”是用单手或双手按对方身体,顺步得势,可译为push;“采”是以手抓住对方手腕或肘部往下沉采,使对方身体前倾,可译为hold and pull down;“扌列”多用在扌朋或捋之后,一手按住对方手臂,另一手用手背斜击对方领际,可译为diagonal cuffing;“肘”是在与对手距离过近而不得势时用肘攻击对方,可译为elbowing;“靠”是用肩部靠顶对手胸部,可译为shouldering。
三、结语
太极拳作为中华武术的杰出代表,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让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是翻译工作者们共同的责任。因此,译者必须准确理解太极拳拳理及文化内涵,提供高质量的汉英翻译,努力推进太极拳文化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
参考文献:
[1]崔建国.《老子》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影响[J].武术科学,2006(3):16.
[2]高丽.太极拳的文化内涵[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8(5):141-143.
[3]顾留馨.山右王宗岳《太极拳论》解[J].体育科技,1980(2):883.
[4]田桂菊.析太极拳的文化价值[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5):44.
[5]吴孟侠、吴兆峰.太极拳九诀八十一式注解[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
[6][清]王宗岳.太极拳谱[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7.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范文第3篇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极为繁荣的时代,不仅有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这三大世界发明,而且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药学、农学、农学等学科很多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触及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①这种“精神力量”在宋代的湖南就是理学。理学是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基础上,把经典的伦理学教义和推理的宇宙理论整合起来而形成新的哲学体系,常被称为“新儒学”②。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理学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天人合一自然观的伦理化倾向与有机性并存理学在湖南的发展主要是由湖湘学派完成的。湖湘理学源于周敦颐,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宇宙图解《太极图说》。《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周敦颐把整个宇宙当作单一的有机体,“极”被认为是有机体的中心,是世界中轴线本身,但任何一个特定的部分都不能被认为居于控制地位。朱熹在继承前人理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将世界本原探讨归于“气”和“理”,他认为这两个术语代表了基本自然世界中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朱熹曰:“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4]朱熹的理气之分可以看作是周敦颐阴阳两极思想的延伸,但他和周敦颐一样,并不把理气对立,而认为是一体浑成,“理未尝离乎气”。([5],pp.32-33)因而认为其存在着有机整体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李约瑟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最好把“理”译为“有机体”或“有机体原则”,表示宇宙的组织原理。[6]如果因为朱熹的有机论倾向就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那又有些牵强。朱汉民就认为,理学家提出的诸如无极太极、理气等学说,最终要证明作为宇宙本体的天理,就是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7],p.8)如朱熹就曾说“,且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8]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朱熹的自然观明显地与伦理思想掺杂在一起,折射出理学中的儒家身影。他的自然观中蕴涵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自然规律和伦理规律是合一的或者一致的。胡宏对“天人合一”做出了新的本体论诠释,提出了“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的本体论,认为天理人欲在形而上的本体中处于同等地位。胡宏的本体论既区别于程朱遵循“天-性-心”逻辑结构的天本体论,也区别于陆王两派遵循“心-性-天”逻辑结构的心本体论,但这种本体论更加反映了天人合一自然观中浓厚的伦理色彩,这表明当时的自然观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唯物自然观,也就不会有助于认识世界的物质本性,这必然对科技活动产生消极影响。李约瑟也认为,儒家对待科学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虽然从根本上注重理性,反对一切迷信,但在另一方面,儒家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使得他们只对“事”进行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这对科学的进展,反而不如神秘主义。
2.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同时指导着道德实践与科学实践格物致知学说,初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在汉唐时期沉寂了几百年后,宋学家对格物致知学说作出了自己独特的阐释。二程认为,人心中本来有知,由于被外物所蔽,使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所以要通过“格物”或“即物究理”而获得知识,认识自己。程颐认为,格物致知是内省的功夫,是德性之知,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治理天下国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格物与致知的学说,他也认为,所谓格物致知,不在于求科学之真,而在于明道德之善。关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过程,朱熹同意一物一物地格,积习多了后,便能“豁然贯通”。有学者认为,朱熹“求理于事物”只是“得君行道”设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0]这与二程格物致知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湖湘学派的胡宏也认为,致知的目的在于认识普遍的、先在的道德规律,而穷理致知是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他在《与张敬夫》中说,“故学必穷极物理为先也。然非亲之,则不能知味。惟不知味也,故终有疑,必待人印证也。”[11]虽然朱熹认为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但是他并不排斥“格一草一木的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一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12]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后人在继承“格物致知”学说时,不仅用于指导道德实践,也用来格物理之理,指导着对自然的探索。这样,格物致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如宋人朱中在研究潮汐中就运用了格物的思想和方法;宋王厚斋依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类推”,将格物致知学说运用到生物知识的发展中。正因为如此,该词与西方“科学”含义最为接近,因而近代学者在引进西方“科学”一词时,最早是将“Science”(科学)翻译为“格物致知”。
3.书院私学成为官方科技教育的重要补充官学中的科技专科学校(如司天监中的天文历法学校)是宋代实施科技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能在官学中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更广泛的科技教育任务,仍然需要私学来补充。宋代是私学科技教育充分发展的年代,书院是私学的高级形式。长沙作为商业发达、商人集中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也较为昌盛,这也符合“富而教之”的传统。宋代书院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被普及开来,尤其是到南宋,书院文化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据统计,宋朝共建书院173所,其中北宋建37所,南宋建136所,占总数的78.61%。[14]湖南书院教育发达,全国四大书院中湖南就占到一半:长沙岳麓书院和衡山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在南宋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书院。湖湘学派开创者之一胡宏在担任碧泉书院、文定书堂和道山书院山长期间,经过长期探索逐渐形成了湖湘书院教育的特色。他认为,创办书院的教育目的是振兴道学,培养有体有用的人才。并且,胡宏强调学贵力行,他认为“力行”既是教学的目的,又是检验学习是否有“真见”的标志。他自己甚至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突破了道德践履的局限。其学生张栻秉承师训,并在其主持岳麓书院工作时将其发扬光大。岳麓书院此后一直将“务实”作为执教理念,尤其体现在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上。正因为这种学风,书院所涉及内容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伦理学科,还有自然科学;不仅对以往的科技史有所研究,还包括对科技的应用与创新的扩展。如朱熹对自然科学和音律学颇有研究,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因而他在岳麓书院讲学时,就曾告诫学生说“:为人子者,医学、地理之书不可不知也。”
4.实学精神对发展实用技术影响深远宋学通过“天人合一”肯定了人格本体与外在宇宙本体相通,但要实现这种内与外、人道与天道的沟通,则必须通过实践。理学的实践精神对湖湘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直接结果是诞生了实学思想,湖湘学派明确标明“务实近本”“、当昭示以用工之实”的实学宗旨。那么,他们这个“实”到底指什么呢?张栻是这样回答的“:于践履中求之。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际,无非实用。(”《性理大全》卷四十九)。这段话包含了两方面内容:第一,湖湘学者所说的践履是“实行”、“实践”的意思,这种实践主要是日用伦常活动,即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第二,实践与实用是紧密相关的。湖湘理学的这种务实思想对宋代长沙商业有较大影响,体现在提倡重视市场、注重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务实作风,以及积极实践、敬业创业的商业思想。按照《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之十二》的记录,古时长沙的潭州所辖各县商税年收入曾一度达到9.2万贯,商业水平位于全国先进行列。除此之外,湖湘学派的实学宗旨对发展实用技术具有深远影响。宋代自开国便外患四立,在统治者尊崇儒学的背景下,宋学家自觉树立“内圣外王”的志向,并通过教育将这种精英文化推向社会。湖南在实现“内圣外王”目标中不断发展“经世致用”的各类实业,不少行业发展水平领先国内其他省份。比如,代表着军事和贸易水平的湖南造船业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潭州能制造载米万石的巨舰,其技术水平之高可想而知。([3],p.481)此外,潭州是宋代有名的产纸地,发达的造纸业又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最终造纸业和印刷业共同推动了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岳麓书院在宋代刊刻有大量书籍保存至今,这是与当时造纸业的发达密不可分的。这种实学精神甚至影响到近代,一大批在政府担任要职的湖南人,如魏源、、左宗棠,在失利后率先开眼看世界,把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引介到中国。综上,在古时科技最为繁荣的宋代,科学与技术作为文化形式在不断交融中相互促进发展,即使在相对偏僻的湖南地区也是如此。当然,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社会文化作为中介完成的,在湖南尤其是受到理学文化的影响。
二、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
1.从区域文化层面看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中国古代文化在特定的区域内,具有各自相似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社会体系,古今学者均对此提出了不同的划分方法。本文沿用中央民族学院徐亦亭的提法,中国古代有四大文化区域:即中原华夏农业文化区域、东南百越稻作文化区域、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区域,以及西部与北方游牧文化区域。古代湖湘文化被归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区域,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说:“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这是春秋时长江中游山地民族游耕文化的一种写照。春秋战国时的楚人发扬了游耕于荆楚山地的火耕传统,在江汉沅湘地区形成独特的荆楚文化。作为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湖湘文化,既不同于东南百越稻作文化区域,乐于四海为家,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也不同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安土重迁的稳持性和逐步向周边拓展的凝聚性。湖南深处内陆,又被长江天险阻断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交通不便,思维顽固。这种地理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导致湖南很少受到外来经济和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文化上的贫瘠。这种贫瘠在两宋之间由于中原文化南迁而有所改观,以理学为特征的湖湘学派逐步形成,在此后湖南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影响着湖南精英知识分子的思维。当然,也顺理成章地影响到湖湘科技文化。如果说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各地都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人们文化水平相差不大,资源禀赋的因素就对地方经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生产的需求又刺激了技术发展。在这一时期,湖南由于地理上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青山绿水,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农耕发达,矿产丰富,加之人们具有较强的勤劳勇敢精神和敢于探索的冒险精神,湖南的技术水平居于国内先进水平。然而从东汉至宋明时期,整个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世界处于先进水平,湖南也加快了发展速度,但却落后于江浙一带。由于这一时期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得到了开发而得到迅速发展,湖南人的开创冒险精神不再是优势,而江浙一带对科学技术的严谨求理、重农重商精神成为时代最需要的精神,这使得江浙一带成为此时中国科技先进地区,湖南只处于国内中等发展水平,尤其表现在科学理论研究与技术发明方面。而清代至民国初期,中国在世界上远落后于西方的科技发展水平,湖南在新技术开发上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但在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发现发明上,处于国内中等水平,明显落后于江浙地区。([3],p.12)尽管在湖南本土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止,湖南的科学发现与发明上并未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一大批在外省担任要职的湖南人,如、左宗棠,却率先开眼看世界,大力推动国外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进行技术开发,实行产业化,商品化,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实业家。这是与湖南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强大的人才储备紧密相关的。然而湖南人在长期封闭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倔强”或称之为“固执”性格,在建国后乃至改革开放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难以解放思想,延误了湖南经济腾飞的时机。总的看来,影响湖南数千年的湖湘文化及其中包含的科技文化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因为湖湘文化的核心在“经世致用”,即使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和张栻等提出的知行合一,主要还是指伦理上的道德实践要求,既包括“内圣”的自我道德实践要求,也包括“外王”的救国救民的政治伦理,即使后来的王船山,杨昌济也没有超出这一传统。比如,王船山的知行观仍然是“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杨昌济留学国外多年,但他提倡的“力行”仍以伦理道德为主,他说:“盖君子之于修身,乃毕生之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这也是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所在。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湖湘科技文化根源的理学之所以能够受到士子和统治阶层的推崇,主要是其“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主张符合了统治阶层的需求,因而被统治阶层引入科举考试,使得古时只能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士子们被迫绑在了理学的架子上。
大学之道翻译及原文范文第4篇
对本文而言,“神学观念”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概念。如果“神学”(Theology)是关于神(God)的理论问题研究的学问[5],那么所谓的“神学观念”(ThoughtofTheology),应该是指在研究关于神的理论问题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这一领域研究应该采取或者抱有的基本态度,及由此态度而展开的思维特征。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神学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神学本身研究的指导,而是逐步深入到了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当然也包括史学研究领域)。换句话说,被观念化的宗教意识使得西方的集体记忆基本都围绕着《圣经》展开,而发端于对神的认识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则具备了博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等特征,两者共同影响了一切与人类历史有关的“事件、人物与时间”。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西方对历史的叙述与对“神”的探索——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神学观念的形成、演化、自我调整及无所不及的影响力对西方史学研究更是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自古希腊到中世纪,西方文明对神的意识逐步进化到神学观念,这一过程使得宗教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更加系统化、全面化。神学既成显学后,神学观念占据了西方社会整个思想体系的统治性地位。神学的道德和被广泛地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从堕落到末日审判,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宗教赎罪的历史。
但是,真正使神学研究系统化、理论化并对史学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应该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时代的神学观念。阿奎那对神的认识上升到了理智的高度。在提出了“上帝的存在”的三个问案后[6],托马斯•阿奎那论证说,神不仅是信仰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理智把握的对象;运用理性对经验材料的思索能力,可以达到对上帝的认识的必要性;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神的认识。这种设问的方式与论证的逻辑,很显然,将问题直接引向了对“历史存在与认识”的哲学根源。正如柯林武德所说的那样,“欧洲曾有两度伟大建设性的时代。在中世纪,思想的中心问题关注于神学,因此哲学问题产生于对神学的反思并且关注上帝与人的关系。”[7]
自近代以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时间何者不受神学观念之影响往往是无从解释的。对于被伏尔泰打上“黑暗”印记的中世纪,在许多历史学家的眼中“也并非满目皆是不毛之地,那里曾有过丰富多彩的技术发明、艺术创造、思想感情和宗教见解,欧洲的经济最早就在那时开始扩张,欧洲的民族主义也萌芽于其间,还有什么理由能在那种荒谬的概括下把那段历史(中世纪)一笔抹杀呢?”[8]从正统神学到危机神学(TheologyofCrisis),神学理论体系的演化充分反映了神学观念的包容性、多元性与危机感。危机神学遵循现代批判主义哲学的原则,使整个神学理论体系不断得以修正与开放,并且学会了与其他观念的共存。而即便是对最具世俗特征的资本主义而言,其兴起也依然无法开脱与新教精神的干系。在这个神权与世俗分离的时代,由神学观念派生的哲学思想与历史观普遍地影响着欧洲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理论与史学理论大师——不论是奥古斯丁、伏尔泰、黑格尔,还是普罗提诺、狄奥尼修斯、埃里金纳、库萨的尼古拉、莱布尼茨、黑格尔、怀特海和海德格尔。在他们的著作中,神学观念的特质无所不及,甚至是“作为神学理论的替论而存在。”[9]因此,正是由于神学观念中“平等、兼容、开放”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西方的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广泛的视野,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从近代到现代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历史哲学的思辩。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一段话最能概括神学观念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与其他文明不同,我们的文明总是与它的过去密切相关,万事万物都追溯到同一源头——基督教和古典遗产。我们的前贤往哲——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就擅长撰写历史,基督教就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宗教体系的信仰和礼仪都源于接近洪荒时期的神话。基督教的圣书包括:史书、礼仪祀典,还包括上帝的现世生活情节、教会纪年、圣徒行传。从另一种更深的意义来说,基督教是历史性的宗教。”[10]
事实上,论证神学观念对西方史学研究所具有的影响,只是本文立论的前提。而要转向本文的立论,需要提出一个似非而是的问题(Paradox):西方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要远远超过中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西方史学观念源起神学观念,这也已经成为众多西方史学理论家的共识。那么,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律?
柯林武德的“历史是思想活动”的观点在西方史学界早已广为人知的。而贝奈戴托•克罗齐在区分历史与编年史的特征时也说:两者不是形式上的差异,而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而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11]且不论这个命题是否为真,但是只要承认思想具有延续性与扩散性,那么就可以判定神学观念对史学观念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史学观念也是在神学观念的耳濡目染下。克罗齐将此归结为这样一种状态,即“一种无法调和的二元论的词被设想为是矛盾的,实则是有关系和统一的。”[12]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西方“新的史学思潮”或者“新史观”,实际上并不是对传统思想、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或者割裂,而是在批判意义上的继承。[13]简单地说,这种新的史学观念只能算是根本性观念的衍生(如果观念能够存在一种先后延续的等级关系的话)。
随着观念趋于多元化,观念体系不断建构、不断开放、不断完善。在此指引下,观念与方法的结合使得史学理论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促使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的扩展与切换。换句话说,从宏观史学到微观史学,从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到语言学、符号学方法的引入,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日益丰富无一不是建立在观念开放与生活实践之基础上。尽管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意识与历史观念是存在显著区别的。他说道:“古代苏美尔人丝毫没有留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学的东西。如果他们有过任何作为历史意识的东西,他们也并没有留下来对它的任何记录。”[14]事实上,这种观点存在一种认知重返的错误。因为所谓的历史观念,只是一个“后化”的概念。前人书写的历史的东西,都是被后加为“历史意识”或者“历史观念”的。但是他也承认,人类对于人的知识是源起于人类对于神的知识的。布洛赫将这种理解推进了一步,认为理解活生生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15]而且“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16]简单地说,正是从活生生的生活中,史学研究不断获得来自观念(不管是神学观念还是世俗观念)的影响与启示。
或许,任何富有逻辑的论证都不及列举几个显而易见的实例更显得有说服力(当然这种例子是接近现实就越具有说服力的):费正清(JohnK.Fairbank)在研究中国的近代史过程中构建了一个“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范式,柯文(PaulA.Cohen)却希望摆脱“以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历史”的框架,于是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17];对于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范式,何伟亚(JamesL.Hevia)则认为,“朝贡体制”具有一定范围内的适用性,但是许多经验事例都打破了这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因此他将研究的视点转向了他所定义的“宾礼”体制。[18]从逻辑上说,“中心主义”价值观需要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作为依撑;与此相反的研究视角则同样应该来自对应的观念的影响。然而,经验事实证明,结论并非如此。萨伊德批判西方“东方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是在伊斯兰的观念体系中完成的,而是在受到西方观念体系的熏陶后才在美国形成的。
“神”的意识及其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神”的概念与意识是显然存在的,而“神学”的概念与观念则是缺失的。如果将产生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的范式选择困境辨言为理论与方法的“纷杂”(DisputationofParadigm),毋宁说是因为我们在根本上缺少了“神学观念”。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早于商代就出现了一个最突出的特征——神学观念。战国以降,中国文化则由神学形态转变为了世俗形态。[19]他的论据取自西周时期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20]但是,“尊神”与“事神”的行为只能判定“神”意识的存在,而不能直接推断“神学观念”之存在,因为只有在对“神”进行了理论思考后,才能称之为“学”。自“子不语怪力乱神”[21]成为儒家之教义后,以“神”为对象的学问就未见于儒士中有集成。当然,此处之“不语”并非不谈论,而更多地是要体现孔子对这些“东西”的不以为然。换句话说,对于“神”的问题,儒家思想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但并未绝对排斥。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盛于中唐时期。[22]及此,“神”(佛)的观念渐入民心。儒释“不同道”的惯例依然拒绝儒士们对佛教的“神”进行深层思考。即便是南北朝时期,儒士们纷纷借用佛教教义来解释儒家传统要义,但是却依然未见对“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神”的起源、本质及缘由进行探讨。“神”只是被作为一种符号、一种普遍性的“理论预设”而为社会接受,可以信奉、包容、抵制甚至唾弃,但鲜遭质疑。在整个过程中,“神”的意识作为政治的附属物得以时隐时现地发挥着教化的功能。
16~18世纪耶稣会士将基督教传入中国。尽管基督教的神学具有强大的理论体系,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政教分离环境之影响,“基督教神学思想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难以填补语言概念和思维习惯方面的鸿沟,甚至多次被政治的变化所中断。”[23]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本应有机会刺激中国神学的复苏或补充中国神学的缺失,但是在当前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的动荡情况虾,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利用政治活动获得民族集体的意识与感情的认同,而不是求助于宗教的力量。”[24]建国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正统性涤荡了“神”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符号和概念。如果说只有系统地研究该领域的理论问题,才能称之为“学”,那么既然作为研究对象的“神”及其理论概念并不存在,也就意味着并不存在以“神”为对象的“神学”;或者说在中国,“神学”从古至今就基本丧失了作为知识或学科的基础。在这种认知力的笼罩下,关于“神”的问题被转化成了“真理”的反问题;并且在意识形态正当性的约束下,神学观念往往被圈囿在极其狭窄的领域,被视同为“迷信”遭以嗤鼻。
由此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应该是可靠的,即受儒家观念体系的浓重的世俗化文化特征的影响,不管是本土的对“神”的意识,抑或是外来的对神的观念都难以被理论化、体系化。而儒家崇尚的“心性之学”和“经世之道”则使得整个观念体系中的宗教神学特质被越来越淡化。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不存在神学研究,中国的学术观念中也并不存在神学观念。反过来,正是由于其自身神学特质的丧失,儒释道之依附于政治权力并随世俗变化而浮沉,使得儒家观念体系的独创性与开放性越来越受到约束,“这导致其超乎世俗社会之上进行独立批判的功能之下降。于此已不难见出神学之阙如或凋零,不但对于学术之健全,而且对于社会之健全,都是一大缺憾。”[25]
直截了当地说,观念缺失所造成的影响是直接性的,也是全面性的。从传统历史研究过程看,由于神学观念未见健全及哲学思辩能力的缺失,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始终未能形成基本的历史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张廷玉的《明史》,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尽管得到了充分发展与延续,但是却从未深度地触及一个根本性问题——历史哲学(伏尔泰提出的概念)。[26]而编年形式的历史记载所提供的历史时间、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无法使我们获得理解历史真实、还原历史进程所需要的详细信息。这种形式究竟能否称之为“历史”确实值得商榷。而从当前的情况看,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倚重使中国的史学观念出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不是靠一种思索它们的思想活动(那会使它们迅速得到充实),而是靠一种意志活动结合在一起和得以支持下来。这种意志活动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认为不论那些字句多么空洞或半空洞,保存它们是有用的。所以,单纯的(历史)叙述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意志活动所维持的空洞字句或公式化的复合物。”[27]或许,引用这段话并不妥当。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根本上就在于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与理解的观念存在偏失。实际上,受神学观念影响的西方史学研究的文本及话语形式都反映着其独特的哲学逻辑[28],也充满了对历史认识与理解的人文主义精神。
如果以史学的现代性为比较标准[29],中国史学研究所遭遇的困境应该是多重的,即首先必须承认中国史学研究存在观念的偏缺;其次还必须承认当下的中国史学研究存在基于观念偏缺而导致的理论贫乏;再次则应当承认存在因史学理论贫乏而引起的史学研究方法的无所适从。由于中国当下的主流史学观念使历史的“真实”被长时期地物化,并且被与精神彻底割裂开来,因此缺少了创造性地转换、完善观念的余地。如若梁启超所言的历史就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30]的论断有些许道理,那么缺乏健全的史学观念与历史精神的指引,就会使这种认识可能带来的创造性无法扩展到整个历史研究的领域,进而出现类似于何伟亚所说的“试图把客观主义的西方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模式用于对非西方材料的分析,恐怕也有些‘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的意味’”的那种局面。[31]当然,从逻辑上说,这句话如果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所谓的“危机”。其产生的根源实际非常简单,即在与西方史学界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往往无法回答诸如历史著作中人的主体作用、史学的独立自主性、史学家的主观意识等深层次的观念性问题[32],因而也无法找到由观念指导的恰当的研究范式(理论与方法)。或者按照黄宗智的说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33]因此,有人采取了规避的方式以摆脱理论选择的困境,仅从事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尽管近二十年来,这些方面已经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但终究无法回避这个“历史哲学”的根本性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史学研究陈旧的理论模式已在事实上形成制约具体研究的束缚和桎梏。[34]按照高华的说法,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现存的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革命叙事范式无疑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特征,其很难与浓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加之革命叙事范式的观念僵化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根深蒂固,因此阻滞了史学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35]
“创造性”地转化[36]观念与走出困境
唯物史观的统治地位源于史学观念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一方面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受历史传统与历史环境的影响。所谓历史传统,是指自春秋“百家争鸣”后,中国文化的观念体系总是以某个思想占统治地位,基本上不存在与之对抗的成分。即便有过某些不兼容的观念,也大多不对主流观念造成影响。所谓历史环境,则是指在当时社会、政治条件下,观念的正统性必须为当时的政治诉求服务。
无论是就历史传统还是就历史环境而言,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史观与占统治地位的唯物史观相比,两者存在显著的区别。神学观念要求公平地对待其他观念的存在,要求增强观念自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且,神学观念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显然要大于唯物史观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此两项特性使得神学观念与学术研究产生了良好的结合效应,也为史学研究开拓了极为广泛的视野。因此,“当代西方产生的具有决定影响的知识大部分是非政治性的,也就是说,纯学术的,不带偏见,超越了具体的派别或狭隘的教条的。”[37]而对当下中国的正统史学观念而言,意识形态的诉求削弱了史学观念的开放性,维持着体系主导观念的独占性,甚至要求不予承认知识的非政治性。这种局面迫使中国的史学研究蜷缩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只为那些是否具备解释的“正确性”字眼进行“论战”,而无法扩张史学(即便仅仅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解释力与影响力,也无法构建起与外部对等交流的观念与话语平台。一如前述,批判别人观念的“非法性”,而又借用这种“非法性”观念引导下产生的研究范式——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在否定自认为确信的观念。
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不能依靠借用理论来弥补,而是必须认识这种不足是由观念的缺少造成的。各种史学理论主张的系统化、史学理论的多样化及史学理论之间的相互整合确实是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但是,这种脱离观念联结的理论是否能够具备应有的创新能力却是值得怀疑的。有人认为,“各种不同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具体见解可能而且可以相互吸收,但最核心的理论主张可以并存,却不可调和。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具有对多样化的史学理论加以整合,以寻求多样化的整体主张,并居于我国史坛主导地位的能力和潜力。”[38]或许,其结论并非不对的,但前提预设则无疑并未真正认识造成“危机”局面的根源。因为史学观念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依靠外部因素(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权威)获得的,而是由其引导下的研究范式通过解释力竞争而获得的。
现实的情况已经显而易见。尽管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许多的史学方法(如比较方法、系统方法、数量方法、模糊方法、跨学科方法等)被引进、被研究、被尝试,但是这终究是一种“跟跑”战术,或者说只能按照别人已设定的研究范式做以尝试性的应用。中国史学研究的前途应该不在于跟跑,而在于构建对等的话语权力,甚至更在于超越。要构建对等的话语权力,要实现超越,首先需要一种突破,那显然不是从方法,也不是从理论,而是从观念。如果我们将史学观念视为中国当代史学的“传统”,那么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史学研究的创新“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39]易言之,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与理解不能局限在必须想方设法地维护其权威,而是要让史学观念具备观念本身应有的开放性因子,具备观念之间相互结合的能力,进而构建起能够与其他观念进行交流、对话的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
总之,走出困境的路径“或是观念、或是理论或是方法”,这需要审定对历史认识的基本态度及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但不管怎么,只要承认历史能够被“无限近似地认识”,就应该承认史学观念、史学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创新”都是有助于实现历史研究视野的拓展与切换的,而三者的序位关系将直接决定这种创新能力的大小。引用史蒂芬•霍金的话来终结本文的论述或许是恰当的——“我们可以预期,自然选择赋予我们的推理能力在探索完整统一的理论仍然有效,并因此不会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有能力选择能够解释现象的理论。”[40]
【注释】
[1]参阅[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4页关于“范式”(Paradigm)的定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载于《世纪中国》2005年3月15日。
[3]类似的观点在国内外的史学理论著作中清晰可辨。参阅[德]威廉•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活表现的理解”,《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注:原文翻译没有斜体字,但是如果缺少这些字眼,则显然不符合中文的表述规范,因此按照笔者理解进行补充。
[5]参阅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香港:香港基督教辅仁出版社,1965年。
[6]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的存在”的三个问案即:(a)上帝存在是否直接自明;(b)上帝存在是否能以表证;(c)上帝果否存在。参阅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香港:香港基督教辅仁出版社,1965年。
[7][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8][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3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9][苏格兰]约翰•麦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想》,第4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8~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1][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2][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3]参阅于沛:“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及史学名著”,载于《光明日报》2001年4月21日。
[14][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15][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6]姚大力:“历史学失去魅力了吗?”,载于《学说中国》,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7][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载于《世纪中国》2005年3月15日。可以进一步参阅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8][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0~1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9]黄玉顺:“中西之间:轴心时期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载于国际易讯网2005年4月30日。(/Article/Class4/Class13/200504/471.html)
[20]《礼记•表记》。
[21]《论语•述而》。
[22]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3]何光沪:“麦奎利与《基督教神学原理》”,载于《世界宗教文化》第4期1997年。
[24][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补本)》,导论第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5]何光沪:“麦奎利与《基督教神学原理》”,载于《世界宗教文化》第4期1997年。当然,此处亦可以添加“对于观念之健全”之表述。
[26]尽管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于历史哲学问题稍有涉及,但是远远达不到理论体系的层次。20世纪初,在广泛接触西方近代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论著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论文才较为系统地对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史学研究方法及史学哲学基础等问题,这才真正出现了中国史学研究过程的“哲学思考”。
[27][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28]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213页;香港:香港基督教辅仁出版社,1965年。
[29]以“现代性”为标准,必然会引起众多方家的异议。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的标准,那么史学研究就会丧失交流的意义与功能,中外史学研究就只能囿于各自的天地,而得不到任何相互有益的借鉴和发展。
[30]梁启超:《新史学》,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32年。
[31][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2]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33]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收录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4]“史学家畅谈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35]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6]此处借用了林毓生的提法,当然也包括了借用他的释义。参阅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37][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1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38]“史学家畅谈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