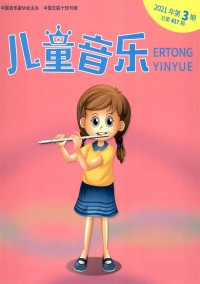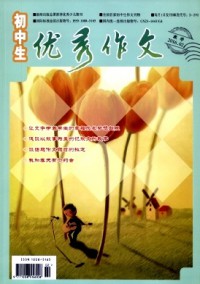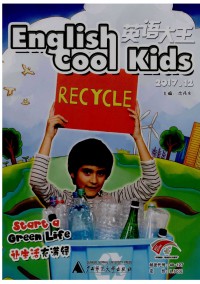我是钢琴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我是钢琴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我是钢琴家范文第1篇
卞萌出生于音乐世家,自幼随父习琴。6岁因会弹琴被市立著名的红旗路小学文艺班提前录取为一年级学生,并参加了接待阿尔巴尼亚外宾的演出活动。1978-1984年,卞萌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88年取得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文学学士,并被学院推荐免试攻读钢琴专业硕士学位。期间先后师从刘爱贤、尤大淳、林恩蓓、李名强等教授,并曾在国内、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
1990年初,卞萌被公派赴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师从“人民艺术家”叶卡捷里娜・穆里娜和钢琴艺术理论家索菲亚・亨托娃教授。1994年5月,被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授予音乐艺术(钢琴)博士学位。同年11月,又被俄罗斯最高学位授证委员会授予哲学(艺术学)博士学位。1996年初,学成归国的卞萌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两场独奏音乐会,琴键上跳动的音符充满灵性,而音乐风格把握的精准到位更让老师们看到了她的变化与进步。求才若渴、广纳贤能的中央音乐学院千方百计地把她留在了北京。这件事在当时国内音乐学院颇为轰动。
1996年,由卞萌所著的《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在北京出版。这本书被国内专家高度评价为“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将中国钢琴艺术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与广度”的专著,卞萌也成为中国钢琴界少有的集演奏、教学和科研于一身的优秀人才。
此外,卞萌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译文,著有《钢琴全面训练基础教程》,并出版了个人钢琴独奏CD《中国钢琴音乐精选》、VCD《钢琴名家教名曲――卞萌专辑》等作品。在学术专研之余,她还经常举办钢琴音乐会,演奏曲目包括从巴罗克到近现代不同风格的作品。
留学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习钢琴的?
卞萌:因为我父亲是钢琴教师,所以家里有钢琴。我从5岁开始学弹琴,起初只是弹着玩而已,总是边唱边弹。当时我家住在南方(安徽安庆),同一个院子里的一位小学音乐老师听说我会弹琴,就说他们学校(当时的红旗路小学,现在叫双莲寺小学)正好有一架钢琴,需要我这样的学生,因而我也就提前上了小学。我第一次上台是6岁多,参加的是当时学校在市政礼堂举办的演出。
留学生:钢琴于你而言的意义是什么?
卞萌:受父亲的影响,学习钢琴于我而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每天都要坚持弹一弹,它就像我生活的一部分。小学的时候,我经常会去参加市里的一些音乐活动或者是演出。后来,我又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大学,再公派留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回来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20年,一直生活在音乐学院的氛围中,始终没有离开过钢琴。
钢琴很像一个“魔术盒”,能够发出各种奇妙的音响:大自然中流水、风声,教堂的钟声,钟楼上的银铃,还有,不同人发出的歌唱的声音,或男声,或女声,或合唱……钢琴就像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每天都要见面。
留学生:俄罗斯的钢琴专业在教学上和国内有什么区别?
卞萌:俄罗斯的钢琴学派可以说是自成一派。虽然与欧洲最早的发源地意大利、法国、德国相比,俄罗斯的钢琴学派起步要晚一些,但是后来者居上。在很多重要国际性的钢琴比赛中俄肴硕加姓季萸凹该大奖。另外,俄罗斯学派的作品非常吸引人,很多获奖者最后一轮与乐队的协奏曲都愿意选用像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等人的作品。我记得前两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钢琴大赛,其中前六名获奖者最后一轮选择的都是俄罗斯作曲家的协奏曲。
俄罗斯钢琴学派有它别具一格的特点,尤其是在演奏方面。安东・鲁宾斯坦是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钢琴家,当时被称为“俄国的李斯特”,因为他的演奏同李斯特的钢琴演奏艺术是一脉相承的,吸收了李斯特感情鲜明、热情奔放、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所演奏的作品等浪漫主义演奏风格特点。安东・鲁宾斯坦的演奏音色特别浑厚,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充满了激情豪放,极具艺术感染力。安东・鲁宾斯坦非常善于把握作品的整体,他的演奏就像是在圣坛上演讲一样,不光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场下的观众。
我在俄罗斯学习了六年,我的老师叶卡捷里娜・穆里娜是前苏联尼古拉耶夫钢琴学派传人。这个学派倡导“深触键”,重视八度与和弦弹奏技巧,整体上力度变化鲜明、具有激情豪放、大气磅礴的演奏特征。同时,它也非常强调如歌(即歌唱性),提倡非常深沉的连奏音响。这个学派的钢琴演奏触键和音色非常干净利落,音色丰满、真挚感人、充满共鸣。2001年10月,我的老师叶卡捷里娜・穆里娜首次访问中国,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独奏音乐会,在当时很是轰动。尼古拉耶夫学派,甚至是整个俄罗斯钢琴学派的特点都是“用音乐带动技术”,就是演奏者首先要内心里充满了音乐,再用音乐来带动演奏技巧的展现。
我当时主要跟叶卡捷里娜・穆里娜教授学习演奏,我个人觉得她在教学上还是跟国内有所不同的。在国内,一般采用的都是“师生一对一”封闭式的传统钢琴教学模式。而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上课的时候,叶卡捷里娜・穆里娜教授借鉴自己在国内外讲学时常用的“专家课”形式,实行一种“用大课形式进行的个别教学课”方式上课。她每周来三天,只要是她班上的学生都可以来,这样,老师主要针对演奏的学生讲课,现场的其他学生也可以一起旁听观摩,通过老师的讲解熟悉曲目、掌握基本的演奏技巧指法规则。真是“一人上课众人受益”。这种上课方式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学生能在不同观众或演奏环境(不同的教室)中进行演奏训练,更有利于他们适应在大演奏厅的表演。有过这样多次舞台环境感体验的学生,一般都不会出现怯场、恐慌等现像。
另外,在上课的时候,叶卡捷里娜・穆里娜老师会亲自示范,因为她有着长期的舞台演奏经验,所以每次上课学生不仅能感受到她的那种演奏家的气场,而且还能够从中获得有效的艺术熏陶。有时候,说一个小时或讲一万句,都比不上一次直观的示范演奏,钢琴课就是这样。
留学生:赴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的这段经历对你今后的艺术生涯有哪些影响呢?
卞萌:俄罗斯的这段学习经历可以说是对我的人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当时是1990年公派赴俄留学的,1991年的时候我回国在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演出,当时我在附中的一些老师也都到了现场,她们对我这一年钢琴演奏的变化很是惊讶,说:“大不一样了!” 比如我弹的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奏鸣曲》,这首曲子我在国内也曾弹过,但是后来在俄罗斯又学习了一番以后,对它的理解又更深入了一些。
因为我当时赴俄主要是学习,所以和学校的老师接触蛮深的。我在俄罗斯留学的第二年,我又学习了一门钢琴理论,当时的老师是索菲亚・亨托娃。她负责辅导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主要是有关中国钢琴文化的论文,后来被编成了一本中文书,名叫《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叶卡捷里娜・穆里娜和索菲亚・亨托娃这两位老师,她们对艺术的热爱,以及专业的精神都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我:在我回国的20年间,叶卡捷里娜・穆里娜老师一直都在弹琴和开各种演奏会,今年3月底又将在中国演出,我觉得她一直都生活在艺术当中;索菲亚・亨托娃老师一生写了40多本书,她这种孜孜不倦的专研精神令我很是折服。
留学生:在众多的俄罗斯钢琴曲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卞萌:俄罗斯著名的钢琴曲实在是太多了,包括众所周知的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等等。这些作品极具俄罗斯音乐特色,但在演奏上也有一定的难度。苏俄作曲家还有很多很好听的中、小型乐曲,像巴拉基列夫的云雀,格林卡的夜莺等。
留学生:你认为俄罗斯音乐文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影响有哪些?
卞萌:中国和俄罗斯是相邻的两个国家,所以在各个方面影响都很深远。因为我主要研究的是钢琴领域,那我就讲一下俄罗斯对中国钢琴方面的影响吧。其实,中国的钢琴与俄罗斯的钢琴文化还是渊源已久的。十月革命时期,一些俄国难民后来流落到中国上海,其中有一位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扎哈罗夫,他是最早对中国的钢琴艺术发展产生影响的音乐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名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创办人萧友梅邀请他到该校任钢琴系主任。由于扎哈罗夫在当时的中国上海培养了一批出色的音乐家,提高了中国在钢琴演奏和教育方面的水平,尤其是在钢琴教育上,使之可以与当时的世界并排,故他被我们称为中国钢琴文化的“一代宗师”。当时还有一位作曲家齐尔品于1934年11月在上海发起了一个“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的创作比赛,无疑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激发了东方作曲家发扬民族音乐的信心。
留学生:俄罗斯钢琴学派无疑是众多钢琴学派中最为耀眼、人才最多的钢琴学派,涌现了许多世界级的钢琴家和教育家。其中你比较欣赏的大师有哪些?怎么评价他们的演奏风格?
卞萌:俄罗斯的钢琴大师有很多,其中一些已经过世了,像涅高兹、索弗罗尼茨基、里赫特尔、吉列尔斯等,只能听传下来的录音或录像了。就在世的钢琴大师而言,我个人比较喜欢格里哥利・索格罗夫,他今年年底(12月份)将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举办个人独奏会。整体上来说,俄罗斯的钢琴演奏风格给我的印像都是很宏伟的、气势磅礴的,而且在弹奏歌唱性旋律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很高贵、很忧郁的、高山仰止的感觉。
留学生:除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以外,俄罗斯还有哪些在钢琴教育方面比较好的学校?
卞萌:俄罗斯在这方面比较有影响力院校有两所:一个是建立于1862年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它是俄罗斯最为古老的音乐学府;另一个是继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之后于1866年建立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原名为莫斯科音乐学院)。这两所院校都是俄罗斯、也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学府,涌现了不少杰出的钢琴家、小提琴家、作曲家等。当然除此之外,俄罗斯还有许多其他比较优秀的音乐学院,诸如格林卡国立音乐学院等。
留学生:你认为中国的钢琴学派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下去?
卞萌:我记得1994年在彼得堡论文答辩的时候,学校的教授肯定地说:显而易见,有一个中国的钢琴学派了,已经正在形成。20年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在中国又出现了新一代钢琴家,如郎朗、李云迪、陈萨、王羽佳、张昊晨等,这成为了中国人的自豪,体现了中国人在钢琴事业上的成绩,让人看到了中国钢琴演奏和教学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根据钢琴音乐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学派的形成除了有一批技艺高强的演奏家,还要有高深度艺术境界的作品支撑。首先,是要学习前人演奏和创作的经验,取其精华所在,然后,是挖掘创造出中国人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对西方作品进行再创造,在保持其原有精神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做到有说服力并使听众能够接受,也要把中国作品弹好,这个就有很多课题要做了,而且是很值得去做的。
留学生:你觉得钢琴对初学者而言最难的地方在于哪里?
卞萌: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说,钢琴也不再是什么特别的奢侈品了。一般经济还可以的家庭都能够买一架钢琴。钢琴的音准是被调好的,手按下去就有声儿了,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难学的。但,它的难度在钢琴是多声部乐器,要掌管多个线条层次,音域最大,最为复杂,钢琴用得好可以代替一个大乐队(当然你也可以弹单旋律)。
在学习弹钢琴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就是拟人化,弹起来要很有韵律。怎么弹得吸引人、有韵味这是钢琴学习中的一大难点。你要学会让钢琴听你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完全地控制它,你还要和它交朋友,让它发出自身最美的声音。
留学生:对于快速提高钢琴水平,你有何好的建议?
我是钢琴家范文第2篇
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那时候,年少无知的我不知道梦想离我们到底有多么遥远,就毫不犹豫地说:“我长大了要当一名钢琴家!”
刚刚接触钢琴后不久,我就知道练钢琴是件多少残酷的事情了。后来,渐渐地,我也明白了钢琴家的梦想离我是多么的遥远,直到有一天……
那是我即将考钢琴五级的时候,受尽钢琴折磨的我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简直快要受不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郑重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再也不想弹琴了!”听了我的话,妈妈脸上的笑容顿时灰飞烟灭:“上幼儿园的时候,不是你嚷嚷着要学钢琴的吗?我花了这么多钱给你买钢琴,给你请辅导老师,还不断地为你加油、鼓气!你说不弹就不弹了,那我为你付出的所有心血……”
“让我静一静!”我打断了妈妈的话,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在房间里,我抱头痛哭,难道追求梦想的路就这么难吗?突然,房间外隐隐约约传来了妈妈的哭泣声。这时,我的脑海里跳跃出了儿时信誓旦旦要成为钢琴家的豪言壮语。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我想通了,打开了房门,径直向钢琴走去,打开,掀起,挥动着手指,练起了考试曲目。顿时,我与音乐融合在一起,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享受的感觉!
“请赵玲艺同学上台领取钢琴五级证书!”伴着欢快的音乐声,我健步走上台去,从评委老师手中接过了份量不轻的证书,泪水瞬间从我的脸颊滑落。而台下,妈妈的眼眶里也满是喜悦的泪水。
我是钢琴家范文第3篇
这注定是断裂的、伤痕累累的描述。从1996年退出钢琴舞台,到今天重返人们的视野,波格莱里奇所传递出的怪异、困惑乃至痛苦感与日俱增,人们并没有听到因年岁而增加的圆融、和解。如果说稍早期的波格莱里奇尚能制造出如涅高兹所说的“天鹅绒上钻石般的音质”的话,那么2011年他留给大多数上海人的印象可谓惊心动魄:虐待钢琴乃至虐待自己,封闭式的演奏,令人错愕的空白,愤懑,夹带着不少失误。傅聪曾有过评语,大体是说听波格莱里奇演奏会感到莫名和愤怒。外媒则不断地扼腕叹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令我们的天才堕落?”当然,这些负面评价乃至“骂名”并未对钢琴家本人产生过多的烦恼,他认为人们不过喜欢拿他当话题谈资罢了,并冷嘲热讽地对《纽约时报》说:“我是世界上被写得最多的钢琴家,哪怕是我为钢琴把灰尘掸去,都会有长篇大论。他们只是不能原谅我长得好看吧!”
无论如何,波格莱里奇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受大众欢迎的钢琴家之一。我更喜欢德国作家、乐评人凯泽(Joachim Kaiser)的说法:“他是一个必须被严肃对待的艺术家,一位极具天赋、散发无穷魅力的钢琴家。简单概括,他让人激动。”任何一种表达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于是,我们有了如下一些关于钢琴家的解构碎片,印象的叠加、不同的向度,或许每个人在这幅立体主义式的拼贴画中都能拼出自己的答案。
一次访谈
――告诉我,他是个好的对话者么?
――一般而言,他很冷漠。如有切中他心思的话题,或许他会有热情解释一番。
2014年12月,波格莱里奇在香港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这是香港乐迷期待已久的盛会,曲目菜单可谓“慷慨”,包括李斯特、舒曼、斯特拉文斯基及勃拉姆斯的作品。与其他会准备大量曲目库供主办方选择的钢琴家不同,波格莱里奇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音乐会曲目都要限定在很少的数量内,以确保演奏保持高水准。于是记者从这个角度开始了战战兢兢的发问。
记者_ 您为香港的观众选择了跨度从浪漫派到二十世纪早期的大作,这背后有什么意味吗?或者说想传递给乐迷怎样的讯息?
波格莱里奇_ 讯息就在曲目里。
记者_ 我浏览过你的官网,通常你每个乐季都会设定很有限的音乐会曲目,包括独奏、协奏曲等。每次挑选时,是否遵循某种逻辑?
波格莱里奇_ 是的,通常我希望能给观众多些展示,通过曲目编排架构之间的逻辑勾勒出某种形象。逻辑既从音乐角度出发,也兼顾钢琴表演。
记者_ 你是否会将肖邦钢琴比赛视作个人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当阿格里奇称你为“天才”并退出评委席为你正名时,你做何感想?
波格莱里奇_ 我当时二十二岁,去问任何一个二十二岁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瞩目对象的年轻人,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吧。
记者_ 你如何定义“天才”这个词?
波格莱里奇_ 我认为这个词被滥用了。
记者_ 有评论将你同伟大的格伦・古尔德相比,你是怎么看待传奇钢琴家古尔德的?
波格莱里奇_ 我不认识他,我从未听过他的音乐会,也从未见过他。
记者_ 据闻你退出舞台表演的那些年一直在从事珠宝设计。是什么令你有这样的改变?你又为何重返舞台?
波格莱里奇_ 你的提问基于并不准确的信息,因此我没有什么好回答的。只能说,我的确有些年不登台演出了,不过业余时候我一直在画画,那是我无数爱好之一。
记者_ 除了音乐,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波格莱里奇_ 在我看来有几种关系很重要,音乐家与作曲家之间,音乐家仿佛是从作曲家手中接过礼物;而对于观众,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忠诚的情感,必定也要将忠诚同等地回馈给他们。
格尔尼卡
记得萨拉热窝吗?记得克罗地亚美丽的古城杜布罗夫尼克吗?记得消失了的南斯拉夫吗?
波格莱里奇记得。
1958年,波格莱里奇生于当时尚存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他的父亲是克罗地亚人,信奉罗马天主教,母亲则来自塞尔维亚。这个家庭很好地诠释了南斯拉夫脆弱不堪的民族势力构成。一直以来,波格莱里奇总在以钢琴家的身份做些力所能及的修补,然而战争的伤痕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何况他的武器仅是一架钢琴。通过在世界各地巡演、发行唱片所得,波格莱里奇帮忙修建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遭受重创的家园,为难民提供有限的医疗帮助。1994年,波格莱里奇在萨拉热窝建立基金会,将善款用于建造一所医院,向当地居民提供医疗照护。他也是首位在科威特举办音乐会的钢琴家,1999年他在科威举行了五场音乐会,只为萨拉热窝母婴医院筹款。
有意味的是,波格莱里奇的个人职业生涯也一直在别人的口水战中忙于“修补”,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依然是无解的谜题,人们对他的描述似乎还停留在年轻时,连同他未曾软化的钢琴技艺:无鉴赏力,甚至粗野不堪(英国媒体)。一个浑身是问题的天才出现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欧洲城市,他的演奏奴役了他的乐迷。不可否认,“戏剧性”一直是波格莱里奇身上抹不掉的关键词。
回到1980年,波格莱里奇在华沙肖邦钢琴比赛第三轮中被淘汰的那一幕。或许是当时冷战环境下的政治需要――赢家必须是莫斯科人,或许也真有评委觉得他不够资格――他被打了零分。评委会成员阿格里奇愤然离席,宣称一位真正的天才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华沙事件的补偿很快来了:一张跻身国际舞台的入场券。那夜,“被淘汰的选手”波格莱里奇身穿丝质套装,脸上带着浪漫主义特有的忧郁,仿佛即将奋身跃入音乐死亡的深渊。
古典乐界常有青年才俊因赢得重大比赛桂冠而星途坦荡,而波格莱里奇则因为出局而成了明星。音乐会引发热烈的浪潮,人们爱极了英俊少年的炫目表演,但也有乐评称,他的技巧与控制力虽堪称完美,却带有浓烈的异端色彩。随着南斯拉夫解体,巴尔干地区陷入疯狂,负面的不和谐声音便愈发明显。关于巴尔干战争、科索沃的话题,波格莱里奇总是很谨慎,仿佛一座等待伤口自我愈合的城,缄默不语。平日里,如果没有演出,他喜欢穿运动套装,把自己打扮成好战的保镖,待人总是冰冷礼貌。他的笑容里没有快乐。 1998年的波格莱里奇
二战期间,他的父亲试图加入抵抗组织,为德军所捕获,险遭厄运,母亲则两度被关入集中营,家中成员多数遭到迫害。对此,波格莱里奇很平静地表示:“一百年来所发生的大规模暴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将影响每一个见证者,而这一切最终使我们的灵魂得以进化。”这或许部分解答了这位怪异的钢琴家灵魂构成中的冰冷、大胆和惊世骇俗。我想起波格莱里奇指着大屠杀纪念馆说:“看啊,它的存在是要令我们知道人类能经受住多大的灾难。”在他的音乐中,这只魔鬼突然跳出来,便是叫耳朵不寒而栗。
忽然,我的脑海中现出格尔尼卡的画面。
“他们突然发现我成熟了”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被忽略了:我是拿着证书的、合格的音乐家。
波格莱里奇极端、过于出位的演奏方式让很多专业人士头疼不已:用虐待钢琴的方式表达“响”,用听不见甚至是空白表达“弱”。果真要这么愤怒、粗鄙地虐待音乐么?人们早先把此归结为年轻音乐家的不成熟。
1998年,波格莱里奇在DG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四首肖邦谐谑曲。肖邦一直是波格莱里奇与听众最亲密的纽带。这一回评论有了些柔和的声音,知名乐评人诺曼・莱布雷希特称:“新专辑不再难以入耳,至少弱的部分听得见,响的部分也不再难以承受。尽管依然有些喧闹,我们还是能感受到钢琴家的观点。”波格莱里奇立刻跳起来反驳,“我讨厌那些胡言乱语,仿佛他们忽然在我的演奏中发现了成熟。……以前,有人叫我钢琴界的弗兰肯斯坦,键盘上的魔鬼,一位穿着皮裤演奏的钢琴家,可我自己连一条皮裤都没见过。他们讨论一切,却对我的演奏只字未提。如今,他们却突然发现我成熟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被忽略了:我是拿着证书的合格的音乐家。我有权依照自己的方式诠释要演奏的作品。我坚信自己是有这样的资格的,今天这些并非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
的确,波格莱里奇七岁开始学习钢琴,五年后应邀前往莫斯科,进莫斯科中央音乐学校学琴,十六岁入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师从蒂玛克希姆、戈尔诺斯塔耶娃、马里宁,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从1976年起,波格莱里奇开始追随格鲁吉亚钢琴家爱莉莎・克扎拉兹(Aliza Kezeradze)学习演奏,继承了李斯特-西洛蒂学派的演奏传统。其间,波格莱里奇获奖无数,包括1978年意大利卡萨格兰德比赛及1980年蒙特利尔国际音乐比赛的大奖。如此漫长的职业生涯必定不是一蹴而就的,波格莱里奇有他的问题,而我们的问题又在哪里?是否我们太过单一地看待一位不可能单一的音乐家?是否我们错过了一些合理的环节,一些具有持续性的、温柔且坚定的声音?
这一辈子,有太多人对波格莱里奇说出不入耳的话,可他欣然接受了其中一位,并信她、爱她到死:爱莉莎・克扎拉兹。
爱莉莎・克扎拉兹
任何一个音乐家都必须信任另一位音乐家。
十六岁的波格莱里奇被邀请去了某苏联科学家家中做客。在当众表演之后,科学家的夫人淡淡地说:“你没好好利用你的天才。”波格莱里奇听了很生气,觉得这位太太无礼得很。后来,他才知道这位点评者是大名鼎鼎的李斯特-西洛蒂学派传人――钢琴家爱莉莎・克扎拉兹。很快,波格莱里奇拜克扎拉兹为师。波格莱里奇坦言自己认识爱莉莎后,钢琴演奏才算步入正途。1980年,在一次钢琴课后,波格莱里奇向年长自己二十一岁的老师爱莉莎求婚。爱莉莎的决定同样让世人震惊:与科学家丈夫离婚,改嫁波格莱里奇。波格莱里奇的父母无法原谅儿子,从此与他断绝联系。1996年,爱莉莎因肝癌逝世。她死前肝出血,与波格莱里奇吻别,在丈夫身上留下了斑斑的血迹。之后的整个葬礼,波格莱里奇一直不肯洗去身上的血迹:“就像杰奎琳・肯尼迪当年不肯换下沾有她丈夫血迹的衣服一样……现在我知道我只能靠自己站起来,但这需要时间,需要很长的时间。”
爱莉莎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张专辑扉页放了两人合照,并刻着这样的字:“这是爱莉莎・克扎拉兹与伊沃・波格莱里奇最后一次合作,我们永远想念爱莉莎,虽然她已不在我们身边。”在世俗的层面,爱莉莎是波格莱里奇的爱情、妻子、家,代表一切安全、温暖、稳定的持续生命力;而在音乐家的层面,爱莉莎又是他追随的老师、对话的合作者。世人认为一位乖张、喜欢“重建”“解构”的音乐家对感情如此专一是匪夷所思的。波格莱里奇敏锐地感受到世界对他和爱莉莎的敌意、质疑,“很奇怪,任何一个音乐家都必须信任另一位音乐家,这种信任甚至可以成为信仰,很遗憾,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少出现这样的关系”。波格莱里奇感慨如今音乐学院并不强调师承的关系,如同爱莉莎・克扎拉兹的离去一样令人伤感。
“首先,完美技巧的至高境界是自然;其次,洞察钢琴声响的发展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钢琴/作曲家是学习的典范,他们往往能理解钢琴同时兼有人声与乐队的功能,可以制造出音色的无限可能;第三,需要不断适应、挖掘现代钢琴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具有更丰富的音响效果的乐器;第四,与他人不同很重要。这是爱莉莎教我的最重要的四件事。”波格莱里奇说。
不论别人怎么说,波格莱里奇坚信自己正走在不断攀升的进化之路上――新的计划、新的曲目以及跨文化领域合作,还有大量等待他花时间筹备的医疗救助机构、难民庇护所。
我是钢琴家范文第4篇
雅:有了好的技术并不等于有了音乐,内心的情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要和别人接触,还要和大自然接触,和一切美好的事物融合在一起,内心才会有音乐。齐迈曼跟我学的时候,我还教他游泳、潜水,平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孩。
我常告诉我的学生:你必须自己教自己,不要指望我告诉你一切。如果学生年纪小,老师可以多教他们,但是学生年纪大起来,老师就不应该再去教许多细节。每个学生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每个人在弹琴时,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弹性节奏(Rubato)。
一个好的钢琴家应该学会让钢琴歌唱。歌唱家、小提琴家都可以把一个音延长,但在钢琴上,一个音弹下去就没有了。所以让钢琴歌唱是最困难的事。钢琴常常会变成一台机器或一台电脑。
我的嗓子不好,但我永远在内心歌唱。
在弹琴的时候,我会马上感到自己是个歌唱家或小提琴家。
在舞台上,我们常常听到的只是音响。我们应该有从心到心的感受。齐迈曼开第一个独奏会时很紧张。但是他演奏完后观众长时间鼓掌,然后寂静无声,没有人动,也没有人走。
所以,钢琴家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并且要把自己和作曲家结合起来,想象作曲家是自己的老师或朋友,想象作曲家是怎么创作这个作品的。当然,这只是那些非常敏感的钢琴家才能做到的。
鲍:这次您听到了许多年轻的中国选手的演奏,能谈谈您的印象和意见吗?
雅:中国的学派非常好,很美也很有内涵。我看到,中国选手在台上都很集中,能很好地控制自己。我想这和中国的“功夫”有关吧!(笑)
中国人弹琴非常认真,但有时候演奏过于夸张。其实可以更自然,不需要做太多。但有时他们对谱上的东西又不太注意,比如作曲家写了P,他们却弹得很响,作曲家写了rit.,他们又弹成了慢得停顿了。
中国选手有时候弹得太“甜”。特别是演奏莫扎特的慢乐章,他们常会把Andante弹成Adagio。这次有一个中国选手把贝多芬的《奏鸣曲》(Op.109)弹得非常慢。
大提琴家卡萨尔斯曾说过:“一个乐旬应该像一条项链,不是一颗颗单独的珠子,而是一颗颗串起来的。”所以说,乐句必须有方向感。你在弹一个句子时,必须“听到”后面的东西。
鲍:慢乐章是非常难演奏的,往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
雅:一个人如果内心真的有很多东西要说、要表达,慢就会慢得很有意思。弹不同作曲家的作品要有不同的弹法。我刚才说了,贝多芬不是那么“甜”的。还有人把莫扎特弹成了德彪西。
俄国作曲家的作品应该是充满了力量去推向。比如拉赫玛尼诺夫、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必须非常重视低音。俄国作品里有很多低音,如宏大的钟声等。俄国有很多教堂,到了星期日,连穷人走进教堂时都会感到一种自尊。所以弹这些作品不光是要“美”。
这次比赛中,那位以色列选手有很好的音乐想象力。但是他演奏的《幻想波兰舞曲》,没有必要做那么多的伸缩。应该像更宁静、更遥远的回忆。肖邦的祖国被沙皇俄国占领了,他的内心是极其悲伤的。他为自己祖国的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这个曲子是个悲剧,不是光辉的结尾。但那位选手弹得像骑马、打枪一样。他弹的声音层次非常好,但是可以弹得更朴素一些。鲁宾斯坦弹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细节”。
中国钢琴选手弹巴赫,风格都不够好。巴赫应该做“阶梯式”的渐强渐弱,而不应该做“波浪式”的。应该把层次更清晰地做出来。
还有贝多芬奏鸣曲,要弹得像乐队。《“热情”奏鸣曲》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都不要太快。第一乐章的三连音一定要平均,不要有重音。就像打木琴、两个手的锤子要打得均匀。第二乐章要有神秘感。
鲍:这次每个选手都必弹肖邦的练习曲,请谈谈您的印象。
雅:练习曲的技术都很好。
Op.25,No.11,左手的旋律不应该按4/4拍的感觉去弹,而应按两大拍的感觉弹。这样会把旋律弹得更有豪气。同时,右手不要做渐弱。
Op.10,No.4,也同样不要弹成每小节四拍的感觉,而要两大拍的感觉。
Op.10,No.8,不要弹成进行曲。其实肖邦有些方面是很像莫扎特的。
Op.10,No.5,左手要像舞蹈一样,把每个切分节奏都认真做好。左手一定要很有力,可以当成旋律来弹。也可以考虑用别的指法来弹。右手的音就像一串项链一样,有几个音不好就使整串都不好。所以如果想弹的好,整个曲子不要太快。
Op.10,No.10,很多人的分句都不够好。
Op.25,No6,大部分人对左手都不够注意,左手一定要有意思。
Op.10,No.12,也一样,左手的旋律是最重要的。
Op.10,No.1有个别地方指法可以用2414241。
鲍:作为肖邦比赛的主席,您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想参加肖邦比赛的年轻人呢?
雅:肖邦比赛不是为炫技的人,而是为敏感的人设置的。不是每个好钢琴家都能弹好肖邦。肖邦是敏感的,但又不能过分。决赛中有一位中国选手弹了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太快了。很多人没有认真按谱子弹,比如波哥雷里奇,他是个好钢琴家,但不适合肖邦。(笑)他弹的《玛祖卡》,只有舞曲,没有内心感觉。
有很多中国钢琴家演奏肖邦时,动作太多了,肖邦的音乐是非常朴素的,就像古典音乐一样。上届肖邦的冠军,他弹肖邦非常自然,一点也不做作,我相信他过几年会更深刻、更成熟。
下次我来中国做大师班讲座时,我会讲如何演奏肖邦的《玛祖卡》和《波兰舞曲》。
鲍:太好了!
雅:还有太多的人用臂和肘部来弹肖邦,这是错误的。其实指尖是特别重要的,手指本身就像一个小榔头。(这时,雅辛斯基教授摊开了翻转的双手,并让我看他指尖上的“肉垫”。)
我是一个热爱钓鱼的人。钢琴家的指尖就要像鱼钩一样。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不是绝对放松的,也要有一点紧张度。你看,像这样,一钓到鱼就马上提起来。护士打针也是一样,要一下子扎进去。发音要有一个点,很敏锐,但不要压死。还有,你看鸟儿在天空中飞翔,它不是不停地扇动翅膀,它扇完后有滑翔的时间(雅辛斯基教授不停地用各种动作来辅助他生动的讲解)。
我是钢琴家范文第5篇
王勇博士作为友情客串,穿了一套黑色的貌似西装的外套,但是我可是很眼尖的哦,外套的领子两边有精细的绣花哦,很低调,很奢侈嘛。
本次“克勒门”的主角是宋思衡、黄蒙拉、薛颖佳三个出生于80年左右的年轻音乐人,与以往的“克勒门”不同,之前的克勒门里我们常常能够见到老克勒们汇聚一堂,一边吃着精美的下午茶,一边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开怀畅谈,在闲聊追溯中摸索窥视曾经的上海文化。而此次《青梦》是属于年青人的故事,将三位80后的音乐界“小克勒”请到一起,为大家讲起了属于现在的上海的克勒精神,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对于音乐的追述、思考和探讨,让人们在音乐中寻找自我,感受真情,在音乐中回归爱美的本性。
陈钢说:这些小克勒体现了一种上海的腔调,他们是上海的希望,上海的骄傲。克勒精神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永远不老。
“我的父亲说我小的时候全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所以等我长大以后,中国一定是在追求艺术的时候。”小提琴家黄蒙拉在“青梦”上回忆说。《从到莫扎特》在经济基础的奠定下,人类会本能追求美好的事物,追求人文艺术的精神世界,而音乐正是以它流淌的旋律抒发了人类对这一需求的向往。而他的黄金搭档,钢琴家薛颖佳也在一旁表示:在欧洲学习的那些年里,你会发现你走过的那些教堂、那些风景、甚至是那些不同的经历都会成为你的一种积累。这些积累会带领你成长,会帮助你对音乐的理解,更会在日后你的音乐里表露出来,让更多的人去聆听、感受、思考……作为多媒体音乐尝试者的宋思衡想必非常赞同他们的这种说法,因为他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宋思衡将原本属于听觉的音乐大胆地创新,添加了属于视觉的绘画,有声的故事描述。他从古典音乐的传统演奏中衍生出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感官体验,将音乐扎扎实实地融入到人类追求艺术精神的本性中去。
黄蒙拉1980年出生,4岁开始学琴,启蒙老师为原上影乐团的张欣老师。曾就读并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 2002年7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被誉为当代最活跃的小提琴家之一。他辉煌的技巧和独特的演绎令欧洲、亚洲和北美的观众为之倾倒。2002年,黄蒙拉荣获第49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并同时获得了这届比赛中的帕格尼尼随想曲演奏奖和纪念马里奥罗明内里奖。著名的英国《留声机》杂志称赞“他的才华正快速的为世人所知”。
据黄蒙拉在“青梦”上的回忆,自己会叫“蒙拉”既不是以传说中的“猛拉”得名,也不是以“懵着瞎拉”而得名,而是他父亲以英文Moonlight的音译而取的名字。我是知道老外有一个姓氏叫Moonlight,但名字就叫月光的似乎也太浪漫了吧。黄蒙拉说起自己参加帕克尼尼比赛时的一些趣事,说自己一路上如何一路辗转地在半夜抵达青年旅社,最后抱着借来的琴谨慎疲劳地睡着的故事,黄蒙拉一边叙述一边感叹。主持人阎华这时问:那比赛的情况呢?黄蒙拉一甩头:“比赛么……那容易多了,那是自己份内的事情了。”原来比起国际大型比赛,旅途更艰难困苦呀。
薛颖佳5岁开始学习钢琴,每天都需要练习4、5个小时。薛颖佳天生一双大手,能爬11、12度。曾经先后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师从丁逢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陈彦新。02年大学毕业后先后赴比利时、意大利学习,在欧洲待了8年,将经历变成了一种累积。分别深造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和被称为钢琴家圣殿的意大利伊莫拉国际钢琴学院。师从于法国钢琴家米歇尔·达尔贝托(Michel Dalberto),加拿大钢琴家路易·洛尔蒂(Louis Lortie)以及俄罗斯钢琴家鲍里斯·彼得鲁尚斯基(Boris Petrushansky)。
另外,薛颖佳还是黄蒙拉的黄金拍档,两人从小一起练琴。据两人回忆,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后,薛颖佳就会到黄蒙拉家里,两个人一起练琴。黄蒙拉拉小提琴,薛颖佳为他钢琴合奏。多年的磨合练习之后,如今两人在演奏时已经能够做到“琴投意合”,光靠耳朵听就能知道对方的需要和意向。
宋思衡出生于1981年中国上海,三岁开始接受父亲的钢琴启蒙。1991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师从李道韫老师。1994年考入上音附中,后直升上海音乐学院。在此期间跟随我国著名钢琴教育家盛一奇教授和艺术家许忠学习钢琴。
宋思衡2002年前往法国,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école Normale de Musique de Paris),跟随马利安-里比斯基(Marian Rybicki)教授学习钢琴。2003年由评委一致通过获得最高演奏家文凭;并成为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华裔教师。之后深造于巴黎音乐学院(CNR de PARIS),其间在国际钢琴大师班上师从多位国际级大师:菲力普-昂特蒙(Phillip Entremont)、米歇尔-达尔伯托(Michel Dalberto)、德米特里-巴什基洛夫(Dmitri Bashikirov),白健宇(Kun-Woo Paik)和许忠等。现师从老一辈法国钢琴大师多梅尼科-墨赫莱(Dominique Merlet)。
2012年6月,宋思衡多媒体音乐工作室在上海正式成立,他和同仁们将继续探索多媒体音乐会的多样可能,为古典音乐走入当代社会拿出自己更多的创意和努力。
在他们三人的身上还有一种相通的共性,他们每个人都有在欧洲学习、生活、参赛的经历,这种经历促使他们能够有一种敞开的胸怀接受不同文化的碰撞,用一种变革性的角度思考自己对音乐的追求。而海派文化也一定需要由拥有这样“世界心”的人才能够包容、理解、交汇出一种特有的属于国际的上海精神,克勒精神,它是一种Open Mind For Different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