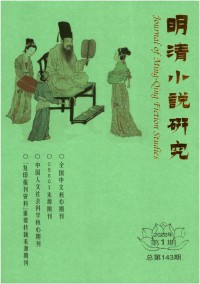水浒传作者资料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水浒传作者资料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水浒传作者资料范文第1篇
Novelist Luo Guanzhong/playwriter Luo Guanzhong 有两个罗贯中,一个是小说家罗贯中(约1280-约1360),山东东平人;一个是杂剧家罗贯中(约1323-约1397),山西太原人。他俩不仅籍贯不同,而且年龄差别很大,小说家罗贯中比杂剧家罗贯中大约年长四十几岁。《水浒》应为罗贯中、施耐庵合著。
【关键词】 小说家罗贯中/杂剧家罗贯中
伟大小说家罗贯中的籍贯在哪?原有山东东原(即东平)、山西太原、江西庐陵、浙江杭州四种说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辨证,江西庐陵说、浙江杭州说已不再有人坚持。罗贯中籍贯东原说、太原说成了《三国演义》研究界双峰并峙的两种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2006年8月,我参加了在山东东平县举行的“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阅读了“泰山名人研究室罗贯中课题组”的调查研究报告《关于罗贯中原籍“东平”说的研究和调查》以及其它有关资料,结合对罗贯中原籍“太原”说的论文和资料进行分析,经过长时间思考,方才发现,原来关于罗贯中籍贯研究的误区在于,把小说家罗贯中的籍贯资料和杂剧家罗贯中的籍贯资料混为一谈(按:过去我也曾进入过这一研究误区),于是相互抵牾,彼此矛盾,怎么也不能统一起来。如今我走出这一研究误区,另辟罗贯中籍贯的研究新思路,于是豁然开朗,柳暗花明,终于解开了罗贯中籍贯之谜:一个是小说家罗贯中,山东东平人;一个是杂剧家罗贯中,山西太原人。他俩不仅籍贯不同,而且年龄差别很大,小说家罗贯中比杂剧家罗贯中大约年长四十几岁。下面,我据事实说话,说明我的罗贯中籍贯研究的新思路是符合两个罗贯中的实际的。
一、杂剧家罗贯中,其籍贯确为太原
说罗贯中的籍贯是山西太原人,虽然资料仅有一则,但这则资料是过硬的。这一资料见于《录鬼簿续编》(《续编》作者一说为贾仲明,一说为无名氏):“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和罗贯中有“忘年交”的《录鬼簿续编》的作者,对罗贯中的籍贯是不会搞错的。古代人见面、相识后,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对方的郡望。因此,杂剧家罗贯中的籍贯为山西太原是否定不了的。“忘年交”,一般相差二十岁以上,如只相差十来岁,可称“师友之间”。我们已知,《续编》作者在永乐二十年(1422)为八十岁,他生于1343年。假定《续编》的作者和罗贯中结为“忘年交”时为17岁(1360),罗贯中为37岁;“天各一方”约四年,那么,“至正甲辰(1364)复会”时,《续编》作者为21岁,罗贯中为41岁。也就是说,《续编》作者生于1343年,杂剧家罗贯中约生于1323年。“别来又六十余年”,《续编》作者,活到八十岁以后。假如杂剧家罗贯中享年七十五岁,他的生卒年月约为1323-1398。到《续编》杀青时(1422)止,《续编》的作者只提及太原的罗贯中有杂剧《风云会》(即《赵(宋)太祖龙虎风云会》、《连环珠》(即《忠正孝子连环谏》)和《蜚虎子》(即《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假如《三国演义》为山西太原人罗贯中所著,作为与罗贯中“忘年交”的他,是一定要提及这一到永乐二十年(1422)已经有一定名气的名著的。《录鬼簿续编》作者只字不提《三国演义》,恰好从另一角度反证杂剧家的罗贯中并无《三国演义》这一著作。(按:《三国志传》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名,直到明嘉靖以后才出现。)
二、小说家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
我们说小说家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是有确凿的证据的。
第一、明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写得很清楚:“若东原(即今东平)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亦庶几乎史。”该序写于明弘治甲寅(1494),而在此以前《三国志通俗演义》已经流行,“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王利器先生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意义〉》上篇(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中说:大多数明刻本《三国》都“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
第二、简本系统的《水浒传》,现存最为完整的是《水浒志传评林》(1594年),题“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编集”。
第三、“明嘉靖间人说《水浒传》的作者,多是施耐庵、罗贯中并提,偏重谓《水浒传》文本出自罗贯中之手,并认为他即为《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本字贯中。”(袁世硕:《水浒志传评林·前言》,东平县人民政府重印本,2006年6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第四、百十五回本《水浒传》署“东原罗贯中编辑”;百十四回本《水浒传》署“东原罗贯中参订”;万历本《三国志传》署“东原罗贯中道本编次”;《三遂平妖传》署“东原罗贯中编次”。这都说明,作为小说家的罗贯中,其籍贯应为东原(今东平)无疑。
那么,东原罗贯中其人找到了没有呢?《关于罗贯中原籍东平说的研究和调查》向我们报告说:找到了!据元代延祐五年(1318)状元霍希贤的后代霍树元、霍衍皆介绍,“霍希贤和罗贯中是同时代人,他有位好友叫罗本,就是写《水浒》的罗贯中。”“罗在宿城罗庄住,也是个大家庭。我祖上为了与他相处,即把他的府第(状元府)建在了宿城,府府相邻。”“我们霍状元曾和罗贯中是很好的把兄弟,两人的关系亲如手足。”我们假定霍希贤于1318年中状元时为35岁,生于1283年,罗贯中小他3岁,那么,小说家罗贯中的生年约为1280年,即生于元至元庚辰年左右。如果他活了八十岁,小说家罗贯中的生卒年约为1280-1360年。小说家罗贯中的年龄比杂剧家罗贯中(1323-1397)的年龄大约年长四十多岁,几乎大了两辈。把《录鬼簿续编》中杂剧家罗贯中的资料与小说家罗贯中的资料“合二而一”,必然扞格不入,难以解释两者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
罗贯中既已找到,他的生卒年已大致确定,那么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的罗本(其生年约在1315-1318之间),是另一个罗本,并非东平罗贯中的罗本,不能把这两个罗本混为一谈。
三、罗贯中于元代末年创作的《三国》原本,是《三国志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祖本,这个原本虽然至今尚未找到,但《三国》原本之谜可解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者,经反复讨论,对《三国演义》原本问题基本上取得这样一些共识:在罗贯中的《三国》原本问世后,其手抄本被后人加工,以两种版本系统出版。一是《三国志传》系统;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这两种版本系统都源自罗贯中的《三国》原本,但有多处异文,说明它们之间是“兄弟”,而非“父子”关系。较多学者还认为,《三国志传》系统据以出版的底本早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据以出版的底本。然而,罗贯中的《三国》原本究竟怎样,因原本早已佚失,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只要我们把见存的《三国志传》系统中的异文加以研究,当可得知罗贯中《三国》底本的大致面貌。
(一)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嘉靖年间的(序中有一日期为嘉靖二十七年,即1548)《三国志传》为十卷(后来的《志传》系统的本子大多分为二十卷)。该书第一卷正文前三十二行的七言诗,自“一从混沌分天地”到“曹刘孙号魏蜀吴,万古流传三国志”,对汉以前和汉代三国历史作了概述,很有说唱文学的特点。多本《三国志传》都有这首歌,并被冠之以《全汉总歌》的名字。这应该是罗贯中《三国》底本所有。
(二)分卷分节不分回,各节题目的字数是不整齐的。
(三)正文前有三国君臣《姓氏附录》(个别后出《三国志传》易《姓氏附录》为《三国志宗寮》,那是因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本已经流行的缘故,如《三国志传评林》,万历年间余象斗刊本,载《三国志宗寮》,那是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本上抄来的)。
(四)无略、表等。
(五)文字比较通俗,如称“宦官”,不称“中涓”。个别地方,文字多于后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如第一节关于十常侍的描写。
(六)某些情节与后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本不一样,且比较合理。从周曰校本《三国志通俗演义》(1591年出版)中得知,该书与其它《演义》本不同,有多种异文,可见该文“显然不是以嘉靖本(即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本文作者注)为底本,而是取自别的底本。”(王长友:《周曰校本与闽建本》,载台湾《小说与戏剧》第6期,1994年)如关羽之死,嘉靖本如此写:“时五更将近,正走之间,喊声举,伏兵又起。背后朱然、潘璋精兵掩至。公与潘璋部将马忠相遇,忽闻空中有人叫曰:‘云长久住下方也,兹玉帝有诏,勿与凡夫较胜负矣。’关公闻言顿悟,遂不恋战,弃却刀马,父子归神。”(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三国志通俗演义》,第739页)回避了关公被擒被斩。而周曰校本写关羽之死,则为:“时五更将近,正走之间,喊声举处,两下伏兵皆用长钩大竿,一齐并出,先把关公座下马绊倒。关公身离雕鞍,已被潘璋部下步将马忠所获。关平听知父已被擒,火速来救。背后潘璋朱然精兵皆至,四下围住,孤身独战,力尽,父子皆受执。吴侯孙权恐不了事,自引诸将直至临沮。时东方已白,闻已擒关公父子,权乃大喜,聚众将于帐中。少时,马忠簇拥关公至前。权曰:‘孤久慕将军盛德,欲结秦晋之好,何相弃?公平昔自以天下无敌,今日何由被我所擒?将军今日伏于孙权否?’关公骂曰:‘碧眼小儿,紫髯鼠辈,听吾一言:吾与刘皇叔义同山海,今日误中奸计,但有死而已,何能伏耶?’权回顾与左右曰:‘云长世之豪杰,孤深爱之,孤欲以厚礼宥之,若何?’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日曹操得此人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爵封汉寿亭侯,赐美女十人,如此恩养,尚留不住,其后五关斩将,曹公怜其才而不忍除之,今日自取其祸,欲迁都以避其锋。况主公乃仇敌乎?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孙权低首良久而言曰:‘斯言是也。’急命推出。是岁十月中旬,关公于临沮而亡。与子关平,一时遇害。”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整理者,以为关羽被擒被斩,有损关公形象,改为“玉帝有诏”,“父子归神”。其实,还是罗贯中写关公就义,虎虎有生气。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将它删却,不当。毛纶、毛宗岗父子加工的《三国演义》,恢复罗贯中《三国》底本对关公就义的描写,正表现了他父子俩的艺术识见。
(七)有关索故事(嘉靖本已删去)。
(八)把《三国志平话》的“七虚三实”,以《三国志》等史书为根据,糅之以民间传说、三国戏等多种资料,改为“七实三虚”,终于将《三国志平话》整理、加工、再创造为不朽的《三国志传》底本。从总体说,罗贯中的《三国》底本,比起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要粗糙些,但某些段落却比嘉靖本写得好。
综上所述,罗贯中及《三国志传》底本之谜可解,作为《三国志传》底本的创作者,罗贯中可以不朽矣!
四、罗贯中创作的是《水浒》简本,比现有《水浒》简本还要“简”;施耐庵在此基础上加工改写为繁本,《水浒》乃罗、施二人合作
根据出土文物施让(施彦端之子)《施氏族谱》谓施彦端即《水浒》作者施耐庵)墓志铭(《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施廷佐(施彦端曾孙)墓志铭(《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我考证出施彦端的生卒年为1332-1406年(详见《去伪存真,施耐庵之谜可解》,载《陈辽文存》第1卷,香港银河出版社1998年出版)。也就是说,《水浒》作者之一的施耐庵比罗贯中小了五十二岁。难怪明人记载中多谓《水浒》的作者是罗贯中。托名“天都外臣”汪道昆、《七修类稿》的作者郎瑛、《癸辛杂识》的作者周密、《续文献通考》的作者王圻、《忠义水浒全书发凡》的作者袁无涯、《西湖游览志余》的作者田汝成、《樗斋漫录》的作者许自昌等人都明确肯定罗贯中是《水浒》的作者。但是,如今印刷出版的《水浒》,都署名施耐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鲁迅目光如炬,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断定,简本《水浒》乃罗贯中所作,繁本《水浒》乃施耐庵所作,所谓《水浒》施作罗续、施是罗的老师的说法是不可靠的。鲁迅的原话如下:“总上五本观之,知现存之《水浒传》实有两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於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须改作也。”“又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周亮工闻於故老者亦第云罗氏,比郭氏(郭勋)本出,始着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时后起,非古本所有。”“后人见繁本题施作罗编,未及悟其依托,遂或意为敷衍,定耐庵与贯中同籍,为钱塘人,(明高儒《百川书志》六)且是其师。”现在,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大致生卒年既已考定,根本不存在施作罗续的问题。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籍贯为东平、靠近梁山泊的罗贯中在晚年撰写了简本《水浒传》,后由施耐庵加工、改写、再创造为繁本《水浒传》,并流传至今。因此,今后如重新出版《水浒传》,署名应为罗贯中、施耐庵合著。但罗贯中撰写的《水浒》,比现存的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本《水浒》还要“简”。其中无“知会”一词,无“里甲”(按:里甲制度始於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十分可惜,原本《水浒》现已无存。
水浒传作者资料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词话 说唱伎艺 通俗小说 口头伎艺 小说文体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2-0122-07
作为中国小说史上重要的文体概念之一,“词话”一词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小说史研究展开之初就已受到学界很大关注。之后,许多学者撰文对其内涵和指称对象进行了详尽考证。80年代,学界又以60年代末发现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为文献依据,对其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番新的探讨。虽然这些研究论著对“词话”的命名内涵、指称对象及其体制特征、渊源流变等基本问题都已做了较全面的论述和界定,但依然存在认识理解不尽一致、许多说法似是而非等诸多问题,特别是材料误读和以偏概全尤为突出。本文试图通过“词话”一词相关文献资料的重新梳理辨析,对前辈学者旧说的主要误识进行深入辨正。
一、“词话”之命名:宋元说唱伎艺演化的结果
“词话”作为伎艺名称最早见于元代,专指当时流行的一种独立的诗赞系讲唱伎艺,这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通常,前辈学者对“词话”命名依据的解释多集中于“词”字之释义,即“词”指诗赞唱词,该伎艺因诗赞唱词而被称为“词话”,如孙楷第《词话考》称:“元明人所谓‘词话’,其‘词’字以文章家及说唱人所云‘词’者考之,可有三种解释:一词调之词;……二偈赞之词;……三骈丽之词。”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所以词话和明清弹词、鼓词的‘词’的意义完全相同。但这称诗赞为‘词’的,也不始于元代词话,唐五代俗讲中的《季布骂阵词文》《后土夫人词》的‘词文’或‘词’,就是指诗赞词而言。”李时人《“词话”新证》:“元明词话之‘词’实因‘唱词’而起。”然而,“词话”之“词”字释义实际上仅仅解决了我们对“词话”词语本身的认识问题,而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词话”伎艺的命名问题。其实,“词话”伎艺的命名如果放置在宋元说唱伎艺及其名称发展演化的历史背景中来看。更应看作宋元说唱伎艺发展演化的结果。
作为诗赞系讲唱伎艺,元之“词话”通常被认为是由唐五代词文,宋代陶真、涯词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宋之“陶真”、“涯词”基本可看作元之“词话”的前身。现存宋代“陶真”、“涯词”的直接相关史料非常稀少,很难说明其伎艺形式,而只能通过一些间接史料作出推测性描述。大多数学者通常将其认定为一种以七言诗赞为主的讲唱伎艺。“陶真”发展到元明时期,依然保持了其原有的称谓,如元末高明《琵琶记》第十七出“义仓”:“激得老夫性发,只得唱个陶真。”“涯词”之名称,元代似乎就失传了(或许被混称作“陶真”)。元代,指称诗赞系讲唱伎艺的名称实际上主要有“陶真”和“词话”两种。从明代相关文献资料来看,“词话”和“陶真”指称的应为同一对象,如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说:“闾阎陶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国初瞿存斋(佑)过汴之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其中,“太祖太宗真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新刻全相说唱张文贵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开头的唱词完全相同。因此,元代“陶真”和“词话”也应为同一种诗赞系讲唱伎艺的两种不同称谓。这实际上表明,“词话”是宋之“陶真”(或“涯词”)发展到元代后新起的别称。那么,“陶真”(或“涯词”)发展到元代之后,为什么会被别称为“词话”呢?
“词话”、“平话”都起源于元代初年,两者大体发生于同一时期,而且,从“词话”指以唱词的方式敷演故事,“平话”指以平说(散说)的方式敷演故事来看,两者在命名上亦具有鲜明的对峙性。可见,“词话”与“平话”一定是相伴而生、并从演说方式角度进行区分的一对伎艺概念。
宋代说唱伎艺主要有“说话”(包括“小说”、“讲史”、“说经”、“说铁骑儿”等)、“鼓子词”、“唱赚”、“覆赚”、“诸宫调”、“涯词”、“陶真”等,元代主要有“陶真”、“词话”、“货郎儿”、“诸宫调”、“平话”、“小说”等。由宋至元,“鼓子词”、“唱赚”、“覆赚”等以宋代词调为韵文的乐曲系讲唱伎艺已基本消亡,盛行一时的诸宫调也已走向衰落,至元末则“罕有人解”;“说话”伎艺中的“说经”、“说铁骑”基本消亡,“小说”也已衰落,“讲史”别称为“平话”,继续盛行。在这些说唱伎艺种类的消长变化中,大多数伎艺沿用着原有的名称,而只有“陶真”、“讲史”出现了新的别称“词话”、“平话”。这应当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偶然。随着“诸宫调”、“鼓子词”、“唱赚”、“覆赚”等乐曲系讲唱伎艺的衰落消亡,更为通俗明白的诗赞系“陶真”日趋兴盛,“陶真”在发展过程中,题材内容不断扩大;同时,“说话”伎艺中的“小说”、“说经”、“说铁骑儿”趋于衰落消亡,而“讲史”成为独秀的一枝继续盛行。这时,人们更需要从演说方式的角度,对这两种最为盛行的主要说唱伎艺进行区分,于是便出现了对举的“词话”、“平话”。另外,“陶真”之名主要流行于南方,很可能,“词话”是“陶真”伎艺从南方流传到北方以后出现的。因此,“词话”之命名应看作宋元说唱伎艺发展演化的结果。
元代还有“诗话”伎艺名称与“词话”非常相近,很可能也是在宋元说唱伎艺发展演化的背景下,受到当时流行的“词话”、“平话”名称影响而昙花一现的一种称谓。“诗话”作为伎艺名称见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现存两种宋元刻本,一本为小字本,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另一本为大字本,题《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通常认为两者源于同一祖本。“诗话”之名仅见于小字本。小字本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一行,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据此认定该书刊刻于南宋,但后来不知何因又改称元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则认为可能刊于元代。综合各家之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刊刻年代应大体在元代初年。近年来,一些学者经深入考辨认为,该书虽刊刻较晚,但成书年代“至迟也该在北宋”,“可能早在晚唐、五代就已成书”。也就是说,现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元代初期之书坊主以晚唐五代或北宋的旧抄本(或刊本)为底本重新刊刻的。那么,题名中的“诗话”一词为原本所有,还是后刻者新题呢?从现存相关文献资料来看,“诗话”更可能属元初后刊者的新题,而且极有可能是刊刻者自创的新词。因为,一、大字本题
《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并无“诗话”之称,可见“诗话”并非祖本原题;二、“诗话”一词并不符合宋代说唱伎艺的命名方式,而与元初流行的“词话”、“平话”相对;三、“诗话”作为伎艺名称仅仅见于此书,其他文献并无记载。许多学者认为,这部作品被称为“诗话”是因其中人物“以诗代话”的诗赞,所谓“以诗代话”,就是每一段结尾处,人物咏诗言志,即以诗赞代替人物的独自或对白。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唐、五代变文话本体制的表现”如果因此而被称为“诗话”则显然属于元初人的一种妄称,而且很可能是根据当时流行的“词话”、“平话”名称而自造的。
二、“词话”之另一种指称:白话通俗小说或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
目前,学界对“词话”一词的理解和界定仅仅限定为“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其话本的专称”。其实,在明后期和清前期,“词话”主要用作白话通俗小说或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
明前期的文献典籍中,关于“词话”的资料并不多,但都非常明确地沿袭元人的用法,指称诗赞系讲唱伎艺及其话本,如都穆《都公谈纂》卷一:“君佐出寻瞽人善词话者十数辈,诈传上命。明日,诸瞽毕集,背负琵琶。”徐渭《徐文长佚稿》卷四《吕布宅诗序》云:“布妻,诸史及与布相关者诸人之传并无姓,又安得有‘貂禅’之名。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善词话者”、“为弹唱词话”中的“词话”显然为讲唱伎艺名称。当然,由这种说唱伎艺转换而来的话本自然也依旧称为“词话”,如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一些作品扉页上明确题写着其文类名称“词话”――《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说唱词话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歪乌盆传》“全相说唱词话”、《新刊全相莺哥孝义传》“新刻说唱足本词话”等。直到明中后期,模拟这种伎艺形式的文人拟作也都命名为“词话”,如杨慎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然而,从相关文献资料来看,“词话”的此类用法实际上主要流行于明中期以前,明代后期和清前期则已很少专指这种具有独特体制的说唱伎艺,而主要作为白话通俗小说或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使用。一些学者在使用明后期和清前期文献中关于“词话”的史料时,依然沿袭元代和明前期“词话”之内涵和指称进行阐释,造成了多种“史料误读”。这种误读遮蔽了“词话”另一种内涵和指称的存在。
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嘉靖三十一年):“武穆王《精忠传》,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辞话”即“词话”之误,所谓“演出辞话”,就是将上文之“意寓文墨,纲由大纪”的著作敷演为“词话”(或以“词话”的形式敷演)。这样做是为了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此处,“词话”既指《大宋武穆王演义》,又泛指此类白话通俗小说作品。李大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嘉靖三十二年):“《唐书演义》书林熊子锺谷编集。书成以视余。逐首末阅之,似有紊乱《通鉴纲目》之非。人或曰:‘若然,则是书不足以行世矣。’余又曰:‘虽出其一臆之见,于坊间《三国志》、《水浒传》相仿,未必无可取。且词话中诗词檄书颇据文理,使俗人骚客披之,自亦得诸欢慕,岂以其全谬而忽之耶?”’“词话中诗词檄书颇据文理”指《唐书演义》中的诗词檄书非常符合为文之道。这里,“词话”显然就指《唐书演义》。《大宋武穆王演义》、《唐书演义》是典型的白话通俗小说,它们被泛称为“词话”无疑属于借用。
万历年间,钱希言在《狯园》、《桐薪》、《戏瑕》等笔记中多次使用“词话”一词,如:《戏瑕》卷一:“词话每本头上有‘请客’一段,权做过(个)‘德(得)胜利市头回’。此正是宋朝人借彼形此,无中生有妙处。游情泛韵,脍炙人口,非深于词家者,不足与道也。微独杂说为然,即《水浒传》一部,逐回有之,全学《史记》体。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书矣。郭固跗注大僚,其于词家风马,故奇文悉被划剃,真施氏之罪人也。”
此处之“词话”相当于其他人所说的宋人“小说”,如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小说起宋仁宗时,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得胜利市头回”应指宋元小说家话本中的“入话”,许多“入话”包含一连串的诗词,特别是宋词,所以钱氏称之“游情泛韵,脍炙人口,非深于词家者,不足与道也”。大概《水浒传》早期刊本也曾逐回包含“入话”,只是后来被郭勋翻刻时删除了。显然,此处之“词话”就是指称宋元小说家话本。称“词话”为“每本”,以“本”为单位,大概指的是单行本,而非话本集。
《狯园》卷十二“二郎庙”条:“宋朝有《紫罗盖头》词语,指此神也。”《桐薪》卷一“灯花婆婆”条:“宋人《灯花婆婆》词话甚奇,然本于段文昌《诺皋记》两段说中来。”
《桐薪》卷二“公赤”条:“考宋朝词话有《灯花婆婆》,第一回载本朝皇宋出三绝。”
“《灯花婆婆》词话”、“《紫罗盖头》词话”曾被晁氏《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其中,《灯花婆婆》还曾作为古本《水浒传》的“致语”之一。两者无疑应为宋元小说家话本。在这两段文字中,“词话”显然也是作为宋代小说家话本的文类概念使用的。
《桐薪》卷三:“逍遥子商调《蝶恋花》十一首,盖宋朝词话中可被弦索者。以后逗露出金人董
解元《北西厢》来,而元人王实父、关汉卿又演作北剧。”
“逍遥子商调《蝶恋花》十一首”指宋代赵令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钱氏认为。该作品属于宋朝“词话”中可由音乐伴奏而歌唱的。它后来发展为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可见,在钱氏看来,宋朝“词话”大多属不可歌唱的,而《蝶恋花》只不过是一种特例。此处之“词话”,也应指称宋代“小说”伎艺或其话本。
《桐薪》卷三:“《金统残唐记》载其(黄巢)事甚祥,而中间极夸李存孝之勇,复其冤。为此书者,全为存孝而作也。后来词话,悉俑于此。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
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今人耽嗜《水浒》、《三国》而不传《金统》,是未尝见其书耳。”
《金统残唐记》应为一部跟《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相类的白话通俗小说。“后来词话,悉俑于此”应指后来的“词话”都以《金统残唐记》为敷演的底本。那么,此处之“词话”无疑指称当时的口头文学伎艺。然而,它到底是指诗赞系讲唱伎艺“词话”还是散说体伎艺“平(评)话”、“说书”呢?这恐怕已难以确指。因为当时“词话”、“平话”混称的情况已相当普遍。不过,从当时一般情形推断,此处之“词话”,更应指“说书”或“评话”。因为,明代中后期的文人普遍认为,当时盛行的“说书”伎艺和“通俗演义”都是由宋代的“小说”(或“说话”)伎艺及其话本发展而来的,钱氏将宋人之
“小说”伎艺及其话本称为“词话”,自然也就可能将当时盛行的“说书”、“评话”也用“词话”指代。而且,像《金统残唐记》这样长篇巨制的历史题材作品,更可能被“平话”伎艺敷演。
有的学者将上述几段引文中的“词话”理解为诗赞系的讲唱伎艺,甚至由《戏瑕》卷一推断出《水浒传词话》的存在,并引证其他材料进行论证,得出《水浒传》由词话本演变为散文本的结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不可不辨。从上述具体考释可见,此段文字中,钱氏所谓“词话”指宋元小说家话本,并不存在所谓的《水浒传词话》,且明代文献中相关的说法也都是指“古本《水浒传》小说”曾含有“入话”或“头回”。现存明刊本《水浒传》中的诗赞之词虽有可能是说唱词话之遗文,但也应是散文本《水浒传》借鉴说唱词话的结果,而非词话本演变为散文本的产物。因为,这些诗赞之词数量极少,而且主要用于状物和咏赞人物,而非叙事,与小说家话本的韵文使用习惯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这些诗赞之词是完全按照小说家话本韵文的使用习惯被借鉴过来的。当然,元明说唱词话的取材广泛,以水浒故事为题材也是很有可能的,也可能存在水浒故事的说唱词话话本,现存《水浒传》刊本中的诗赞之词或许就是借鉴的此类话本。但这并不能说明现存《水浒传》由词话本演化而来。从明代相关文献资料来看,明人多认为《水浒传》源于“说话”,属“通俗演义”系统,而与说唱词话并无多大关系,如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天都外臣《水浒传叙》:“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称为行中第一。”
清初,钱曾《也是园书目》卷十《戏曲小说・宋人词话》著录作品十六种,有《灯花婆婆》、《风吹轿儿》、《冯玉梅团圆》、《种瓜张老》、《错斩崔宁》、《简帖和尚》、《紫罗盖头》、《山亭儿》、《李焕生五阵雨》、《女报冤》、《西湖三塔》、《小金钱》、《宣和遗事》四卷、《烟粉小说》四卷、《奇闻类记》十卷、《湖海奇闻》二卷。其中,《灯花婆婆》、《风吹轿儿》、《冯玉梅团圆》、《种瓜张老》、《错斩崔宁》、《简帖和尚》、《紫罗盖头》、《山亭儿》、《李焕生五阵雨》、《女报冤》、《西湖三塔》、《小金钱》为单篇流行的宋元小说家话本;《宣和遗事》为宋元讲史平话; 《湖海奇闻》被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和《百川书志》卷五《小史类》著录,且《百川书志》称其:“聚人品、脂粉、禽兽、木石、器皿五类灵怪七十二事。”《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和《百川书志》卷五《小史类》多著录通俗小说作品,因此,《湖海奇闻》大概也为通俗小说集。 《烟粉小说》、《奇闻类记》大概与《湖海奇闻》性质相类。这十六种作品还被姚燮《今乐考证・缘起-说书》著录为“宋人说书本目”,可见,这些作品确实为散文本之通俗小说,而非讲唱体的“词话”。此处“词话”被别称为“说书本”,也应泛指宋代的“白话通俗小说”。
此外,还有个别通俗小说被直接冠以“词话”之名,如《金瓶梅词话》、《新编梧桐影词话》等。在这些题名中,“词话”也并非讲唱伎艺概念,而应为“白话通俗小说”类型概念,相当于“演义”等。《金瓶梅词话》名为“词话”,却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体裁完全不同,实际上为诗词曲运用相对较多的白话通俗小说,《续金瓶梅后集凡例》称:“小说类有诗词,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今因题附以新词,参人正论,较之他作,颇多佳句,不至有套腐鄙俚之病。”显然,“小说类有诗词,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实际上把“词话”和“小说”基本看作同一概念;《梧桐影词话》为清初啸花轩刊本,目录页题“新编梧桐影词话目次”,该书名为“词话”,实为一般白话通俗小说。显然,这些题名之“词话”也应作为白话通俗小说的泛称看待。
三、“词话”另一指称之成因:口头伎艺的混称和通俗文学的指称习惯
“词话”被引申为宋代小说家话本或白话通俗小说的泛称,既与“词话”、“平话”、“说书”等口头伎艺名称的混用有关,也与明人指称通俗文学的习惯密不可分。
元代的诗赞系讲唱文学主要以“词话”、“陶真”来指称,而明代则“异常混乱,据文献的记载共有十种不同的名称。而本质都是诗赞系的讲唱。”它们是“陶真”、“词说”、“词话”、“说词”、“唱词”、“文词说唱”、“打谈”、“门词”和“门事”、“盲词”或“瞽词”、“弹词”。明中期以后,“陶真”、“弹词”等名称开始逐渐盛行,如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说:“间阎陶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国初瞿存斋(佑)过汴之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冤狱”条:“畜二瞽妓,教以弹词,博金钱,夜则侍酒。”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弹词小纪》载:“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板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女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明传奇《醉月缘》第九折题名为《弹词》,且提及许多“弹词”作品。这样,“词话”这一名称本身的指称和内涵便逐渐不为人知了,以致于有了“元人弹词”之说,如徐,愎祚《三家村老委谈》:“汤若士……《南柯》、《邯郸》二传,本若士、臧晋叔先生所作元人弹词来。”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侠游录小引》:“余少时,见卢松菊老人云,杨廉夫有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录四种,实足为元人弹词之祖。”于是,便出现了“词话”、“评话”、“说书”等伎艺名称的“混称”现象,如《古今小说》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 “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完全是说书人做场的口吻,“词话”显然是在称呼自己的伎艺。演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应属“评话”伎艺,如《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 “这段评话,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警世通言》卷十七《钝秀才一朝交泰》:“听在下说这段评话。”称为“词话”应为伎艺名称的混用。袁于令《双莺传》杂剧第四折[羽调排歌]云:“(小旦)一面差人去请柳麻子说书,混帐到天明罢了。……(小旦)说词话,间戏嘲,管教胡乱到今宵。”《梅里诗辑》卷四朱一是有《听柳敬亭词话》诗。柳敬亭以散说的评话著名,无说唱词话事,这里的“词话”无疑指“评话”。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卷十六《王行传》:“市药籍,记药物,应对如流。迨晚,为主妪演说稗官词话,背诵至数十本。”从“演说”、“背诵”等搬演方式来看,此处“演说稗官词话”也应指“评话”、“说书”。
水浒传作者资料范文第3篇
一、四大名著阅读状况分析
(一)名著“寂寞”
在四大名著中,对其一无所知的学生人数比例分别是:《三国演义》7.4%;《水浒传》7.4%;《西游记》7.6%;《红楼梦》竟达16.7%。
虽然大部分同学知道四大名著,但“知梗概”的远多于“知全文”:《三国演义》“知梗概”占72.9%,“知全文”19.4%;《水浒传》“知梗概”占73.1%,“知全文”19.5%;《西游记》“知梗概”占30.6%,“知全文”61.8%;《红楼梦》“知梗概”60.7%,“知全文”22.6%。
“知道四部小说”的信息来源,“听来的”和“来自影视媒介”的占了绝大部分:《三国演义》86.8%,《水浒传》84.1%,《西游记》86.7%,《红楼梦》74.8%。
不少同学阅读名著方式是“看连环画”:《三国演义》7.1%,《水浒传》7.2%,《西游记》13.3%,《红楼梦》3.4%。阅读原著的同学却少得可怜:《三国演义》13.29%,《水浒传》7.4%,《西游记》5.8%,《红楼梦》4.5%。
不知名著,已经令人遗憾;知名著却知“梗概”,就难免有些尴尬了;而 “知梗概”,却是绝大部分来自 “快餐”式的图文加工品,这就让语文教师感到无奈了。 “知识爆炸”时代,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通过阅读名著夯实文化“底子”的意义,却被人们忽略了。于是,名著寂寞了!
(二)看热闹
知道四大名著的学生中,喜欢故事情节的占绝大部分:《三国演义》50.9%,《水浒传》49.7%,《西游记》67.9%,《红楼梦》38.8%。喜欢艺术技巧的很少:《三国演义》6.4%,《水浒传》5.9%,《西游记》6.3%,《红楼梦》13.9%。
这一组数据表明,高中生欣赏名著的水平仍然停留在“故事”的浅层次上。情节曲折、生动固然吸引人,但四大名著可看的东西远远不只这些!高中学生对名著的欣赏只是 “看热闹”,水准明显偏低。在这个问题上,为师者应该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毕竟,“知道名著”的学生中,喜欢名著的人数占了大多数。这是值得欣慰的“大多数”,说明名著对学生还有一定的“亲和力”。老师是否充分利用、发挥了这种“亲和力”呢?
(三)雾里看花
同学们对名著的“主要体会”是怎样的呢?体会深刻:《三国演义》18.4%,《水浒传》16.6%,《西游记》43.0%,《红楼梦》19.6%。体会一般:《三国演义》57.2%,《水浒传》61.6%,《西游记》42.4%,《红楼梦》41.4%。没有体会:《三国演义》17.5%,《水浒传》14.4%,《西游记》7.0%,《红楼梦》23.4%。
不难看出,名著在学生面前实际上是“无名”的。四大名著是古典文学的四朵奇葩,但在中学生审美世界里,只是四朵消了颜色、散了芬芳的“无名花”!尽管有些同学也读了原著,却体会一般,甚至没有体会,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交流心得体会时吱吱唔唔,哼哼哈哈,说不出所以然来。尽管大部分中学生能列举小说中5位人物姓名,但分析人物形象,绝大多数学生不能胜任,分析的结果有的只是“贴标签”,甚至有些人物形象张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
(四)“动力”不足
阅读名著是否能提高语文成绩?对这个问题,44.1%的同学说不清(认为“与成绩有关”的占24.5%,“与成绩无关”的占21.9%)。阅读名著与成绩关系真的微妙难说吗?这表明学生阅读名著的动力不足。实际上,那些语文成绩能保持稳定良好的同学大多读过原著,且都有较广泛的阅读面。应当想办法使学生阅读名著变得“有效”,增加学生阅读名著的动力。在中、高考的试卷中设置适量的名著类试题,也不失为一个较现实的办法。当然,可喜是今年福建省高考语文试卷中已经很好的关注这个问题,话题作文中两组人物中“曹操”“宋江”“薛宝钗”等均是四大名著中人物。这个高考指挥棒对中学语文教学无疑起推动作用。
二、古典诗歌阅读状况分析
(一)读过篇数和背诵篇数
读过篇目不少于16篇的学生为38.6%,不少于80篇的为39.9%,不少于160篇的有21.4%。能背诵篇目不少于24篇的为69.6%,不少于120篇的有25.1%,不少于240篇的仅5.3%。
【简评】仅5.3%的人达到新课标的基本要求,可见学生阅读量和记忆量之低。
(二)对古典诗歌的兴趣
兴趣状况:(1)喜欢39.3%;(2)不喜欢6.5%;(3)谈不上喜欢与否54.2%;对古典诗歌的体会:(1)体会深刻22.7%;(2)体会一般68.8%;(3)没有体会8.4%。
对唐诗宋词元曲的了解:(1)很熟悉8.9%;(2)了解一些79.6%;(3)不熟悉11.5%。
对李白、杜甫的了解:(1)很熟悉26.2%;(2)了解一些66.9%;(3)不熟悉6.54%。
【简评】许多同学在古典诗歌面前,或熟视无睹,或敬而远之,或望而却步,或茫然不知所云,或胡乱曲解诗意……甚至有6.54%的学生连李白、杜甫都不知道。这些现象的根源,就是没有形成鉴赏古典诗歌的能力,得不到美感,当然就不会乐在其中了。
(三)与语文成绩关系
(1)认为与成绩有关的,占67.1%;(2)认为与成绩无关的,为9.4%;(3)请不清楚的,占23.5%。
简评:中学语文教师几乎没有不重视古典诗歌教学的,原因是中、高考那分值不低的试题。于是普遍存在只“治标”不“治本”的现象。治标者的拿手戏就是模仿中、高考题型,编选大量标准化试题将学生捺入题海泡浸。这对于培养真正意义的审美素质毫无裨益,反而降低了学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兴趣。新编高中语文课本有多个诗歌单元,我们应充分利用课本引导学生欣赏古典诗词,提高学生品味古典诗词的能力,提升素质,才能真正应对考试。
三、问题与建议
结合座谈和访问的印象,本人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狭隘的学习功利主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习辅导书”就成了学生课外书的代名词,家长、学生、学校都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一本又一本的辅导资料书。不少家长推崇“非辅导不看,非习题不做,非英语不听”的三不规则。毕业班学生为攀登升学的金字塔,一头扎进题山题海,更与经典无缘。尽管高二学生大多数都知道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是什么,但真正读过的没有几个。为什么不读?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还在分数的压力下苦苦挣扎,哪里还有时间去看这些与考试无多大关系的书呢?”
(二)图视 “驱逐”文字
图视类传媒高速发展:各类影碟铺天盖地,互联网与数码影像接踵而至,再接着是摄影图片类书籍及卡通画异军突起……校园周围小书店及市区几家书店这两年最热销的是文娱和足球类画报、绘画本中外名著、卡通等等,而文学名著销量一直不太好。图视传媒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也要警惕“读图时代的阅读危机”。今天的学生大多通过影视录像了解古典名著的原因很简单:读文学作品吃力。然而学生一旦养成阅读图视作品的习惯,今后进入大学、进入社会后也很难改变。
(三)敬畏“经典”与否认“经典”
在繁重的学习负担下,长篇的语言和结构因素成了学生“亲近名著”的又一个障碍。许多学生表示,有时也翻翻名著,只觉眼花缭乱,没看出什么又放下了。一些学生说,现在大部分名著已拍成电视剧或电影,看过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耐心再去看原著。有的学生说自己也知道母语作品重要,但不如影视、数码影像的虚拟世界吸引人。言语之间,他们对名著不敢亵慢,只是“敬而远之”。
另一方面,对名著“不喜欢”的同学也大有人在(《三国演义》6.4%,《水浒传》5.3%,《西游记》5.6%,《红楼梦》14.6%)。这些学生否认“经典”,认为名著部头巨大,情节冗长,描写拖沓,节奏缓慢,书中所写时代距今遥远,时代背景、人物关系难理解,不如读现代武侠、言情、侦探推理小说以及卡通连环画来得轻松。他们对名著了解的微乎其微,却对一个个大碗明星的生肖、爱好甚至婚变的次数能娓娓而谈,如数家珍。
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是否应该自问:怎样才能带领学生进入古典文学的殿堂,领略其中的奥妙,使他们读古典文学也会产生像读流行书、畅销书一样的审美愉悦?
(四)家庭普遍缺少浓厚的文化气氛
父母的文化层次较低,是农村家庭文化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学生档案资料统计,父母务农的占45%,职工13.3%,半农半商的11.67%,个体经营的占12.52%,其余有少量的干部、教师。父母是文盲初小、高小文化的占多数,少数是初高中文化程度,因此在营造家庭文化氛围方面几乎无能为力。多数父母虽然重视儿女的读书,但仅限于关心学习成绩,看重分数,因此反对儿女看课外书,认为这些“闲书”会影响学习,有的父母则忙于生计而放任不管。
多数学生家庭中最有文化气息的活动仅限于看电视。调查中,回答“经常看影视片”的学生占了大多数。近半数的学生是在没有任何一本课外书和报刊杂志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们从小学到高中唯一的“文学读物”就是一本语文书。
语文素质是要从小培养熏陶的,在这样缺乏文化氛围中读到高中的学生,要在高三一年中突然提高语文素质是不太可能的,即使在高中三年中要大踏步提高也是要付出相当艰辛劳动的。
课外阅读历来被不少人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君不见父母谈“课外书”色变,不少班主任(非语文老师)明确规定“不准把课外书带回课室,一经发现,全部没收,还要在班上检讨……”
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没有阅读十本八本中外名著,背诵200首以上的古典诗词,那实在是整个人生的一大憾事!学生对古典文学的“远离”,必然导致精神“钙质”的缺少和欣赏层次的低下,导致“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浅薄。这种“后天不足”对一生的成长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缺陷。这是有识之士的共同的看法,也是实际生活业已证明了的事实。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中学生课外阅读近乎空白的情况呢?本人认为:
第一,学校、家长和社会都要达成这样的共识;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素质。要培养良好的素质,不读书怎么行?我国当代语文学家刘国正先生说过:“书是知识的宝库,智慧的海洋,奋斗的向导,成功的阶梯,学文,学做人,求大发展,大成就,离开读书,不过是缘木求鱼。”而读古典文学应是读之基本!
水浒传作者资料范文第4篇
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源于上世纪40年代初期叶圣陶先生的思想,他在《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中指出:“现在国文教材似乎该用整本的书,而不该用单篇短章……退一步说,也该把整本的书作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建国初期,他总结多年实践经验草拟了《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把上述观点修正和发展成为:“中学语文教材除单篇的文字而外,兼采书本的一章一节,高中阶段兼采现代语的整本的书。”
抗日时期,叶老曾同朱自清先生合编《略读指导举隅》,专供教师参考,从而指导学生读“整本的书”。每部书按具体情况作了五个方面指导:
一、版本指导。简要介绍该书的写作年代和版本变化情况,以突出其历史地位。
二、序目指导。通过序文和目录的介绍,交代该书的写作意图和内容梗概。
三、参考书籍指导。推荐若干有助于读懂该书的参考用书。
四、阅读方法指导。这是指导的重点,结合该书内容和形式的特点提示阅读的门径。
五、问题指导。
这些研究都为我们今天更好地进行名著研究性阅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研究全书结构,读薄整本书
结构是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形式要素,是指各部分之间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在表现形态。结构是一本书鲜明的特色。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只有重视对于名著结构的研究,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尤其是一些外国小说,其作品结构与写作风格本身是相得益彰的。
即使结构看似简单的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细致研究其结构也是一门学问,更是读薄全书的重要路径。如《水浒传》一书,前五十回分为九个结构单元:(一)鲁智深传(三~八回);(二)林冲传(七~十二回);(三)杨志传(十二~十三回、十六~十七回);(四)晁盖、吴用等人合传(十四~十六回、十九~二十回);(五)宋江传(十八~二十三回、三十二~四十二回);(六)武松传(二十三~三十二回);(七)李逵传(三十八、四十三回);(八)石秀、杨雄合传(四十四~四十六回);(九)李应、扈三娘合传(四十七~五十回)。后三十回分为五个结构单元:(一)两赢童贯(七十五~七十七回);(二)三败高俅(七十八~八十回);(三)接受招安(八十一~八十二回);(四)破大辽(八十三~八十九回);(五)征方腊(九十~九十九回)。
茅盾先生在《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中指出:“从整体看来,《水浒》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无割裂之感。但是,从一个人物的故事看来,《水浒》的结构是严密的,甚至是有机的。”李希凡在《水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中提到:“如果从内容的安排来探讨《水浒》的结构,它的长篇结构是有机的”。
但是郑铁生先生在《论水浒传叙事结构》中认为:“《水浒传》前70回是以人物性格为结构形态,而70回以后则又回到了故事情节的结构形态,是一个交叉的多元的叙事结构形态”。而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则认为《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先是折扇式的列传单元,后是群体性的战役板块”。
二、研究重要情节,读通整本书
读一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读通整本书,而重要情节的研究必须放在整本书中来研究。要引导学生在通读全书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精彩片段在全书的特殊作用;引导学生结合作者的创作意图来深入研究作者的匠心;引导学生借助研究资料来丰富对精彩片段的理解。
比如,《汤姆索亚历险记》第二章中《刷墙》是全书中经典的情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作者第二章中是如何写出如此精彩的情节?
引导学生抓住这一章中的重要细节来进行研究。比如汤姆・索亚在此次刷墙中所获得的巨大“物质”财富:“苹果、一只收拾得很好的风筝、一只死老鼠和拴着它甩着玩的小绳子、十二颗石弹、一只破口琴、一块可以透视的蓝玻璃片、一尊苇管做的炮、一把什么锁也不开的钥匙、一截粉笔、一只大酒瓶塞子、一个洋铁做的小兵、一对蝌蚪、六个爆竹、一只独眼的小猫、一个门上的铜把手、一根拴狗的颈圈――却没有狗、一个刀把、四片桔子皮、还有一个坏了的窗框。”汤姆更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舒服而安闲的时光”、“这世界原来并不那么空虚啊”、“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个大法则――为了要使一个大人或是一个小孩极想干某样事情,只需要设法把那件事情弄得不易得手就行了。(工作是一个人不得不做的事情,而玩耍却是一个人所不一定要做的事情)”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物件?这些物件在全书中有没有深刻的意义?
第八章写汤姆“用两个大白石弹换了三张红票,又用其它一些小玩意换了两张蓝票。当其他的孩子走过来时,汤姆又拦住他们,继续收买各色各样的票。”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刷墙的收获,才能用这些物件换取了各色各样的票,才有下面更加精彩的情节:
“这时候只差一件事情,就能使华尔特先生狂喜到极点,那就是他非常想有一个机会给某个学生颁发一本《圣经》,借以展示一下自己。”
“汤姆・索亚却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九张黄票、九张红票和十张蓝票,请求得到一本《圣经》。这真是晴天霹雳。……于是,汤姆有幸与法官和其他几位贵宾们坐在一起,这个重大的消息就从首脑席上公布于众了。这是十年来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全场大为轰动,把这位新英雄的地位抬高得和法官老爷相等。”
汤姆和蓓姬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开始,可以说这就是作者的深刻用意。
这些物件里有一样极其重要:铜把手!汤姆对蓓姬求爱时因为误言而失败时,“汤姆把他最珍贵的宝贝,一个壁炉的柴架顶上的铜把手,拿出来从她背后绕过去给她看”,但是蓓姬“一把把铜把手打翻在地”。而当汤姆“失踪”时,蓓姬“愁眉苦脸地踱来踱去,心里觉得很凄凉”,唯一想到的就是“那只柴架上的铜把手”!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两人的“定情信物”。
所以,刷墙这一章是全书的重要“关节”。更重要的是,这一回仅仅是一个开始,和后面的历次历险是否有更加内在的关联?可以说,正因为汤姆在遇到困难时,有着这样善于思考的习惯,才会在最后的洞中历险中用自己的智慧逢凶化吉。一次又一次的历险中,汤姆的形象不断地成长起来。
三、研究叙述视角,读透整本书
读透整本书,首先要研究作者的用意,尤其是一些讽刺性文学作品。比如,《格列佛游记》在表面上是写实主义的、甚至是“航海日志”式的风格,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假称为格列佛本人的记录,委托亲友发表,书中对日期、地理位置、航行路线、事物的大小和数量均力求显得翔实准确等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一效果。
主人公的叙述时而故作严肃、一本正经,时而显得天真无邪、令人莞尔,时而又过度夸张、难辨真假,从而产生强有力的反讽效果。在《格列佛游记》里,叙述者的态度和作者的真实意图当然不尽一致,却并非一成不变,叙述者扮演的角色在各卷中也各有不同。
例如在小说的第一、二卷中,斯威夫特让读者明显地意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但在第三、四卷中,情况则不那么简单。尤其是在第四卷中,由于格列佛不再扮演佯装者角色,所以我们“很难知道格列佛和斯威夫特之间的距离有多大,确切地说,是很难知道那位旅人对于慧S国的热情中哪一点表现得过分了”。
在什么地方、在何等程度上格列佛表现了作者本人的观点?什么时候格列佛自己也成为了作者反讽的目标? 书中深层面的讽刺对象到底是什么?
水浒传作者资料范文第5篇
一、 得“法”于课内,运用于课外。
新课程下的语文教学,重视语文素养培养,重视语文综合能力的锻炼,强调拓展语文教学的外延,重视学生知识面的拓展,重视课外阅读。语文课堂教学不应仅满足于帮助学生理解“文中之道”,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学有所“得”。叶圣陶先生说过:“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可见,加强课内阅读方法的指导,应用于课外阅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对于提高学生课外独立阅读的能力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在课堂学习中加强和渗透阅读方法的指导,首先,注重朗读与默读相结合,从四年级开始,逐步培养学生的默读能力和习惯,课堂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来进行朗读和默读,让学生用默读来提高阅读速度,用朗读来体验情感。第二,注重精读与略读相结合,在学生具备一定默读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快速浏览,理清文章脉络,了解文章内容梗概,再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地方细细品读:对文中的人物感兴趣就着重品读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心理活动,以及所处环境和细节描写;对事情感兴趣就弄清事情经过,弄清情节,分析环境场所,分析相关人物;对文中的景物感兴趣,就抓住景物特点的细腻描写,身临其境体会意境,体验语言的丰富妙用,从而品味积累吸收。第三,阅读与思考相结合,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一味读书,而不思考,只能受到书本表象的迷惑而不得其解。所以我们主张阅读要边读边想,带着问题去阅读。比如教学《阅读大地的徐霞客》时,就先让学生看题质疑,从中梳理出“徐霞客是一位怎么样的人?”“徐霞客是如何阅读大地的?”让学生带着这两个问题去阅读课文,边读边思考,更快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第四,阅读与想象相结合,想象是智慧的翅膀,引导学生在阅读文本时,展开想象的双翼,一定会给文本带来更多独具特色的个性化解读。
读物众多,方法各异,以上所提仅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的些许感悟,更多的阅读方法还有待大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形成。只要老师们在课堂教学中加强阅读方法的指导和渗透,让学生一课能得一“法”,再把这些阅读方法运用于课外独立阅读上,相信有“法”可依,他们定能“读得更快,读得更多,读得更深,读得更透。”
二、 立足于课内,辐射于课外。
牛顿、爱迪生等伟大科学家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一生所学的知识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学校课内习得,而绝大多数都是在课外学到的。因此,新课程改革后的阅读教学更加注重了课内学习内容的拓展与延伸,老师们要树立“大语文”观,突破僵化的思维模式,突破课堂的禁锢,突破课本的约束,强化课内外联系,引导学生挖掘开辟阅读内容,丰富阅读信息,把学生的阅读从课内辐射到课外。
1、 课前铺垫式阅读。在学习新课之前,布置学生阅读与课文的作者、背景、内容相关联的资料,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在教学《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时,课前布置查找普罗米修斯的相关资料,有的从网上查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英雄事迹,有的从书上了解到与普罗米修斯有关的神话传说,交流时,还有学生提出他找到了与课文内容不同的多个传说版本。虽然学生查找到的资料内容丰富多彩,各不相同,甚至出现争鸣,但无一例外,他们都通过广泛的课外阅读,加深了对普罗米修斯这位英勇顽强、无私奉献的英雄形象的理解。
2、 课中推荐式阅读。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恰到好处地穿插阅读一个或多个与课文内容相关的文本,再以点带面,推荐阅读,既激起了学生阅读的兴趣,又增加了学生的阅读量。如教学冰心的《忆读书》一文时,引导学生感悟“读好书”的好处时,冰心多次提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好书,教师顺势而导:《三国演义》让作者感到“津津有味”,“好听极了”,还“含泪上床”,“哭了一场”;《水浒传》让作者“大加欣赏”,“气愤填胸”;《红楼梦》让作者“尝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你看过这几部作品吗?你是否与作者有相同的感受呢?紧接着教师随手拿出事先准备的《水浒传》,选择“虎松打虎”片断,声情并茂地读起来,处却戛然而止,幽默地说:“欲知下文,请自己看书!”下课后老师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几部名着放在图书角让同学们借阅,老师欣喜地发现,这“虎松打虎”果真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3、 课后延伸式阅读。下课铃声的响起,决不意味着学生阅读的结束,在很多时候,恰恰是新一轮阅读的开始。延伸就是以课文为基点,向更深更远更广的阅读空间扩展。如学习《房兵曹胡马》和《马诗》两首古诗,引导学生发现两首古诗的作者都是唐代诗人,课后向学生推荐《唐诗三百首》;学习了《郑人买履》这则寓言后,老师根据寓言的出处,课后向学生推荐《韩非子》;学习《孔子和学生》后,向学生推荐孔子的《论语》……学生在课本中所学到的课文内容,有时想更加了解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求知欲望极高。这时向学生推荐这方面的课外读物,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这样一来,学生的兴趣由课内迁移到了课外。长此以往,学生就会盼望着读,自觉去读,甚至于手不释卷,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之中。
三、 展示于课内,激趣于课外。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儿童主动积极阅读的基础。两千年前的孔子也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不如乐之者。”兴趣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剂”,它能推动学生从课外有益读物中去探求知识和获得能力。不管是何种课外阅读方式,关键在于课堂上必须要给学生提供舞台,让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阅读成果,激发他们课外继续阅读的兴趣而乐此不疲并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