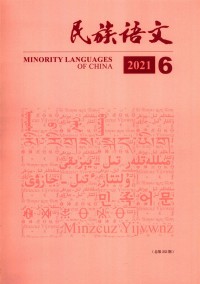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代诗歌;教学策略;资料介入;对比;练笔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7)16-0073-01
《长江之歌》是中央电视台纪录片《话说长江》主题曲的歌词,被编排在苏教版教材六年级上册的开篇。诗歌以简练而富有深情的语言,展现了长江绵延千里的宏伟气势、刚毅博大的精神以及敢于奉献的高贵品质,表达了诗人对长江的依恋和赞美之情。笔者以这篇文本的教学为例,谈谈高年级现代诗歌教学的一些做法。
一、资料介入,明晰内容
诗歌对事物的介绍,并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以独特的表达方式加以呈现。因此,如果不对所描绘的事物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学生也就难以真正读懂文本的核心内容。
鉴于此,教师在教学这首《长江之歌》之前,就引领学生分别从长江的概况、长江的发展以及长江的贡献三个维度进行资料收集,让学生了解长江的具体长度、流经的区域、起点与终点等,了解长江的起源、历史发展的轨迹,了解长江对各种植物的哺育情况以及沿江开发、贸易发展的相关信息。然后,教师将这些信息与文本中的内容进行整合,让学生深入理解诗歌的大意。如将长江终点、起点的知识与诗歌第一段中“你从雪山走来……你向东海奔去……”相结合,感受作者艺术化语言表达所形成的丰富意蕴;将沿江开发和贸易发展的资料与诗歌中“你用磅礴的力量,推动新的时代”相结合,感受在改革开放中,长江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诗歌语言精练而具有跳跃性,仅仅凭借着诗歌自身的语言,学生难以揣摩作者意欲表达的内涵。而广泛的资料收集,为学生拓展补充了相应的知识信息,为解构和感知诗歌的内蕴起到了铺垫性作用,教学效果鲜明。
二、对比感知,洞察思路
相对于一般的现代诗歌而言,歌词的创作有着自身的规律与原则,其中上下段之间的对应联系,就是歌词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教师可以引领学生采用对比、联系、整合的视角进行解读,从而在深入辨析中既明确作者的创作思路,又能感知如此设置的表达效益。
如教学《长江之歌》时,教师组织男女生分别诵读课文的第一、第二自然段,并在对比中明晰两个自然段在语言形式和写作策略上的特点。学生在深入思考之后进行分享。有的学生发现两个自然段在语言形式上有对仗关系。教师相机引领学生紧扣语言形式的特点,深入感知作者分别是从哪些视角来描写长江的。在教师的点拨之下,学生逐步意识到第一段,作者借助长江的起源和终点,以空间概念,展现了长江绵延千里和刚柔相济的特点;而课文的第二自然段则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凸显了长江沧桑的悠久历史和全新的青春活力。
两个语段并列呈现,让学生以立体化、多层次的方式感知了作者表达的内在情韵,不仅深入洞察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基本构思,更促进了学生文本解构能力的有效发展。
三、拓展补充,实践练笔
Z文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阅读教学就应该在学生深入感知与悦纳的基础上,创建真实可感的平台,引领学生在深入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语用能力。
教师在执教完《长江之歌》之后,为学生拓展补充了另一首描写长江的诗歌《长江礼赞》,并引领学生在对比阅读中感受两篇文本在创作上的共有特色:首先,都是借助第二人称“你”的口吻来直接抒情,便于诗人将自己独特的情感和盘托出。其次,两首诗歌都大量使用了拟人、比喻的修辞手法,以艺术化的手法对长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感知,从而促进了表达效果的整体性提升。在这样的基础上,教师则引领学生在自己生活中,选择一个与自己情感最深的事物,并模仿这两首诗歌的写法,尝试写一段诗。教师可以先组织学生讨论,让学生感知诗歌与普通文本之间的区别。然后,再让学生深入实践,进行练笔,从而促进学生语用能力的提升。
在这一案例中,教师始终以语用训练为核心,通过其他类群文本的拓展补充、对比细读,进一步明晰了诗歌的体裁特征,并以一个价值点为范例,对学生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深入指导,为学生的实践练笔奠定了基础。
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李商隐;意象;隐喻
李商隐的诗歌在历史评判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转折,经过实践和无数学者的探究讨论之后,李商隐的诗歌终于在历史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李商隐的诗歌作品采用了大量的意象,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审美情趣、朝代背景等都融合在了诗歌的意象之中,让人读起来能够从表象的事物观察到当时的时代缩影,对现代了解晚唐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李商隐诗歌意象特征
1.客观自然诗歌意象
李商隐诗歌中出现的实体性意象主要是分为植物、动物、人体、气象、地理、天文、无生物等。在李商隐的诗歌中有311个天文意象,主要是日、月、星、辰。在地理意象中主要是水流、山、地的意象,一共是出现了476个。在气象意象中一共有479个,主要是风、云、雨、露雪。时间意象出现了256个,主要是夜、春、秋。人体意象有339个,女性的身体部位、肠、身,主要是体现了女性身体的美妙。动物意象一共是出现了548次,主要是鸟类、昆虫类、马、鱼,在昆虫类的动物意象中,碟、蝉、蜂出现的次数比较多;鱼类、爬行类、兽类出现的次数很少。在植物类的意象中一共出现了738个,花、柳、桂出现较多,荷花和梅花在花类中较多。无生物意象一共是有386个,水、灰尘、波出现较多,冰出现的次数也很多,但是和水属于同种物质,所以,就归结到了水中。
2.历史范畴诗歌意象
历史类的意象主要是人物、建筑物、地理、精神活动、朝代、器物、书籍文章、机构等。其中人物意象主要有两种,在现实中存在的人物有434个,泛指的人物有174个。在人物中主要是历史人物,潘越、宋玉、司马相如、西施、杨朱等出现的次数较多,泛指的人物中客、女子、帝王僧、夫君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在地理中,路、关、池出现较多;在建筑类意象中楼、宫、门、台、殿、阁苑、亭出现的次数较多;在精神活动意象中梦、泪、魂魄出现的次数较多;在器物意象中,女性器物出现的较多;文章典籍中书典、文章出现的次数很多;周、秦朝代出现的比较多,厦、商基本上没有出现;在机构中家、国出现较多。
3.虚拟类的诗歌意象
虚拟意象主要是诗人自身的直接或者是间接的生活经验之上的虚拟事物,在作品中通常占据的比例很小。在李商隐的诗歌中一共是出现了378个虚拟的意象,占据着5%左右的比例。主要是人物、动物、仙境、植物、器物等。泛指的人物主要是神仙人物,动物主要是凤凰、龙,仙境主要是大范围的境地和具体的宫殿。李商隐认为凡人和仙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达到了精神上的自由,所以,他使用的仙人器物很少。
二、李商隐诗歌隐喻基础
1.在物理上存在相似性
物理上的相似性主要是包括功能、形状、外表上的相似性,李商隐的诗歌中有的意象存在物理上的相似性,所以,存在隐喻的现象。如,李商隐在《细雨》中这样写道,“帷飘白玉堂,簟卷碧牙床。”大概意思就是细雨好像是一副延绵细长的帷幕在白玉堂前漂浮着,好像是碧绿的竹席铺展在蓝天下。“白玉堂”“碧牙床”比喻天空,使用“帷帘”“竹席”比喻细雨,主要就是利用了他们在物理上的相似性。帷帘和竹席都是柔软细长的织物,细雨在微风的吹拂下展现的形状与帷帘和竹席非常相像,这就是以物喻物。
同样在《咏史》文章中李商隐主要就是借助历史典故来表达自己对政治的感叹,使用了“琥珀枕”“齐威王”两个历史典故,突出唐文宗的重视贤能、勤俭节约。使用“青海马”来形容能够承担重大责任的人,青海马和为国效忠、辅佐君王的忠诚在功能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为了主人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在心理上存在相似性
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因为文化上的相同或者是同样的心理感官,对两件不同的事物产生了相同的心理感触,这就是意象心理上的相似性。李商隐的诗歌中借助想象或者是实际存在的意象,来和想要表达的寓意进行联系,让读者能够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如,在诗歌《柳》中李商隐写到在春天生机盎然的柳树,怎么到了秋天就变成了一副萧索的模样?李商隐就是借助了柳树在春天的生机勃勃和秋天的萧索进行了对比,从而隐喻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年轻的时候年轻有为,到了老年却是穷困潦倒。在年轻的时候,诗人充满了朝气,想要用凌云壮志朝气蓬勃的抱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却不想经过了人生打击之后,最终变成了穷困潦倒的模样,他的生活经历和柳树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相同之处。
在《蝉》中李商隐给蝉塑造了这样的形象――身居高位,孤高清苦,其身难保,徒劳叫声。自己的命运和蝉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似,自己品德清高,却是面对着穷困潦倒的境界,空有一腔热血,却是打动不了世态炎凉。
三、李商隐诗歌概念隐喻
1.人物的结构隐喻
李商隐诗歌中采用的人物结构隐喻主要是让两种界限不明确的事物进行概念上的叠加,用来代替另一种事物。最常见的主要是:(1)使用祥禽、瑞兽代表贤臣明君。在《重有感》中使用蛟龙、在《楚宫》中使用了长姣、在《咏史》中使用了青海马、在《当句有对》中使用了游蜂等。(2)使用秀木代表着美人、君子。如,在《日高》中出现了药、在《房中曲》中使用了松、在《闲游》中出现了荷花等。李商隐在进行意象隐喻选择的时候,主要是使用松、梅、莲花、猛马、骏马、麒麟、凤凰等,隐喻选择美好的美人、君子、明君等形象。
2.实体隐喻
实体隐喻主要是将我们的思想、情感、行为、事件等无形的概念看成了具象的事物,这样能够生动地传递感情。实体隐喻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应用,如“我在幸福中长醉不醒。”这就是把自己的幸福进行了实体隐喻,好像就是喝醉了酒的感觉,宁愿沉醉其中不能自拔。李商隐在进行描述的时候,采用了很多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在生活、政治中的失意,如在《夜冷》中使用败荷表达了自己的失意,在《滞雨》中使用残灯,在《燕台诗四首》中使用蜡烛,在《夜雨寄北》中使用西窗烛等。诗人在描述自己的感情的时候,对周围的事物就有很多的把握,周围经常出现的事物能够很好地代表着诗人的情感,这就是常说的借物言志。
在实体隐喻中容器隐喻较为常见,主要是因为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容器,对周围的事物也可以看成独立的容器,这样在进行情感表达的时候,就很容易将难以描述的事件进行汇总归纳。李商隐将很多的自然界事物当作了容器,如,在《安定城楼》中的绿杨枝外、《风过伊仆射旧宅》中的败荷、《隋宫》出现的垂柳、无题中出现的重帷深等。
3.空间比喻
空间比喻主要是将空间的事物放在非空间概念中,这样就能够通过空间概念总结非空间概念。空间隐喻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是通过一个一个的空间隐喻作为基础,构建很多的概念,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它的产生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在丰富的文化经验和物理经验的前提下产生的。空间概念主要是在人们现有的理解能力之上,通过对社会地位、生存状况、生活、时间等进行一定的了解之后,将难以表达的抽象概念进行描述,从而表达自己的意思。
如,李商隐使用“上”隐喻时间较早、社会地位较高、理想状态较好。在时间较早中使用“上”主要是在《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世戏赠》中出现的“千骑军翻在上头”。在表达社会地位较高的时候,也经常使用“上”,如,在《韩碑》中出现的“表曰臣愚昧死上”和“誓将上雪列圣耻”,在《访隐》中出现的“泉自上方来”,在《圣女祠》中出现的“天上应无刘威武”等。表达状态较为理想也会使用“上”,例如,在《少将》中出现的“上马即如飞”,在《重过圣女祠》中出现的“上清沦谪得归迟”,在《日高》中出现的“飞香上云春诉天”等。
李商隐的诗歌中以“下”进行隐喻也有所体现,“下”和“上”的状态相反,代表着生活状态不理想、社会地位较低、时间较晚等。在状态不理想中,经常使用“下”。如,在《井泥四十韵》中使用的“一日下马到”,在《闲游》中使用的“强下西楼去”,在《曲江》中使用的“玉殿犹分下苑波”等。表达社会低下的时候,也会使用下,如,《裴明府居止》中出现的“爱君茅屋下”,在《行次西郊一百韵》中出现的“下田长荆榛”“敢问下执事”,在《归来》中出现的“敢问下执事”等。
4.语义结构
在诗歌教学过程中通常都是应该有本体有喻体,但是在诗歌中因为条件的限制,经常是出现本体或者是喻体,从而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1)只有喻体没有本体。这种隐喻是李商隐诗歌中经常出现的隐喻结构,例如,使用美人难以嫁出去表达自己空有政治抱负。在《无题》(八岁偷照镜)中有很好的体现。诗歌中的表面就是写美丽动人的女子,不但情节高尚,勤学好问,而且生性活泼,很有魅力。但是到了出嫁阶段之后,父母却是不想把她嫁出去。随着生活和时间的流逝,姿容美貌的女子对婚姻生活也产生了一些忧虑。李商隐就是用美丽的女子来表达自己不被重用的现实。自己同样具有优秀的文采和高尚的情操,却是难以得到赏识,在政治上一直不顺利。使用黄昏、落花、莺、蝉等表达自己的现实感慨。如,在《桂林路中作》中使用蝉和空花枝表达自己的郁闷,在《乐游原》中使用黄昏表达自己年老不得志等。(2)本体和喻体一起出现。本体和喻体一起出现在李商隐的诗歌中比较少见,我们在进行李商隐诗歌阅读的时候,需要细细品位,才能够体会其中的隐喻。如,在《过伊仆射旧宅》中描写的“幽泪欲干残菊露”,《临发崇让宅紫薇》中的“秋庭暮雨类轻埃”,《赠郑处士》中的“浮云一片是吾身”,《锦瑟》中的“沧海月明珠有泪”,《陈后宫》的“茂苑城如画”等都是本体和喻体共同出现的。
5.喻体特征
李商隐诗歌的隐喻具有典型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喻体大多是哀怨感伤美丽纤柔的。他们高洁美好,但是却是不断地在接受着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严重摧残,它们想要反抗却是无力反抗也不能反抗。主要体现了诗人具有高尚的情操,才华横溢,但是家族、爱情、理想方面都接受了严重的打击,一生坎坷。(2)诗歌充满了多义性和朦胧性。诗歌之间的隐喻主要是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程度,或者是心理相似或者是物理性相似,而这些相似都是主观判断的,可能二者之间相似很少,也可能相似很多。所以,李商隐使用了有本体喻体和没有本体的隐喻,这样就让诗歌充满了多义性和朦胧性,在解读的过程中产生了多种含义。(3)具有新颖性和创新型。李商隐的诗歌在进行隐喻的时候,增加了隐喻的形式和内容,让原本没有关系的事物进行了联系,从而提高了隐喻的新颖性和创新性。
李商隐的诗歌具有很强的特点,是晚唐时期典型的代表。李商隐在选择意象的时候,主要是人物类、建筑类、动物类、自然景观类等,隐喻主要是进行了结构隐喻、实体隐喻、空间隐喻等,丰富了文章意象的内容,提高了隐喻的深度,对现代诗歌具有很深的影响。
描写植物的诗歌现代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风景画;美学;德国观念论;自然象征主义;风景艺术;灵知主义
中图分类号:J20文献标识码:A
在欧洲语言历史中,“风景”一词在中世纪晚期出现,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16世纪末,“风景”一词,和鲱鱼、漂白亚麻布一起,从荷兰输入到英国。其德语词根“Landschaft”,同人类的占有欲望联系在一起。人常说“秀色可餐”,意味着人类对风景的判断,往往同对于一种迷人事物的渴念紧密相连。Landschaft作为一种理念产生于荷兰造堤防洪实践,绝非偶然,将广大自然据为己有本身就是一项伟业。“风景”的意大利语同义词是“parerga”,意为小溪流水,满山金黄,以及田园牧歌的发祥地。“风景”概念广泛流布于17世纪初,“风景画”在17世纪法国和意大利先于诗歌和小说从审美角度发现了万古常新的“自然”。在英语中最早使用“风景”(Landtschap)来描写画面的作家是B.约翰生(B. Johnson),在他的《褐色面具》(Masque Blackness, 1605年)中有这样的句子:“这般场景上首先被画出的是一片小树林构成的风景”。17世纪末期,像德莱顿之类的英国作家已经泛化“风景”概念,直接用它来指代绘画本身了:“将这部分风景移入阴影,以便强化画面的其余部分,让它们显得更美。”
然而,风景不是身外之物,而是宇宙自然通过人的感性生命而塑造出的精神外观。真正将“风景画”作为视觉艺术的一种类型,则在17世纪后期。罗伯特・耀斯断言,17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风景画的审美意义超出了同一时期的田园小说和英雄小说,荷兰日常生活风景画的审美意义也胜过了类似的流浪汉故事。①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自然的经验”和“自我的体验”之互动过程中,一种审美对话与交流的关系在17、18世纪历史中缓慢地展开,一种源自孤独心灵的渴念正在艰难地寻求表达。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诗人、哲人和艺术家将这场精神的剧变推向了一个,漫游小说、“渐进的宇宙诗”以及“情绪风景画”把自然与自我的这场对话呈现为悲剧的场景,而把孤独心灵的渴念提升到了绝对的高度,用风景道出了忧生忧世的无限悲情。
一、浪漫灵异――自然象征主义
自然象征主义,是指以具象的自然事物为符号,去建构象征体系,表现宇宙、人生的奥秘,以及无限的人类精神。这种指向与诉求,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之中得到了经典的理论表述。伴随着异教诸神的复活,人们向内发现了心灵,而向外发现了自然,风景才得以在艺术中登堂入室,取代人物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优先对象。自然是一本书,风景是书中的文字。只有当人打开这部书并倾心读解其中的文字,风景才算是存在,也就是说才被发现了。早期浪漫主义的哲人和诗人就建议人们把“自然”当作“经书”来读。谢林说,“自然”乃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比任何成文的启示都更古老的启示”,而通过解读这部神秘的“启示之书”,人类得以超越一切古老的对立,置身于一切冲突之外去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②诗人诺瓦利斯提示我们,“自然”乃是柔和而伟大的“远古进程”的产物,而一道神圣的面纱将之所由而来的远古遮蔽起来了,凡俗的灵魂藉着诗歌这一“魔镜”窥见了“在神圣美丽之中”的“远古”。③于是,浪漫主义诗人、哲人以及画师眼中,自然之物灵异盎然,甚至还蕴藏着一种非人的诡异的力量。
一如迪福笔下的“孤岛游子”鲁滨逊,浪漫诗人、哲人与画师无不作茧自缚,画地为牢,囚禁自我,影息闹市,远离城邦、世界、文化世界、公共空间。然而,悖论恰恰在于,“孤岛游子无时不在,甚至他还置身在不入时流的鲁滨逊刻意逃离的人群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人群,尤其是栖身城市的现代人群,工业时代城市里的人群,也挤满了孤岛游子。”他们像动物一样渴饮世界的匮乏,“这个匮乏的世界剥夺了孤岛游子的本质,据说还剥夺了那个作为他者的他者,剥夺了他们的一般独异性。”④因此,浪漫主义者都是一些孤岛游子,遭受到一种非人的诡异力量的摆布而无力自拔,心生一种畏惧之情。这种非人的诡异力量,驱动浪漫诗哲建构“新神话”,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将之命名为“实在专制主义”(Absolutismus der Wirklichkeit)。“这个术语是指人类几乎控制不了生存处境,而且尤其自以为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生存处境。” ⑤青年时代的黑格尔就是一个知名的浪漫哲人,他也陷入到这种非人的诡异力量之掌控中,强烈的抱怨之情与激进的反叛之愿如潮涌动:精神欺骗我们,精神玩弄诡计,精神编造谎言,而且精神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精神(Geist),就是我们的主题词“灵知”之“灵”。浪漫主义诗哲同出一辙,都无奈地把“精神”(“灵”)看作是那种非人的诡异力量,巨大若蟒而且凶残如魅,带着阿里斯托芬式的反讽微笑,嘲讽人类总是把自己微不足道的家园建在荒山夕照之中,还自以为那里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结果却发现它只不过是人类灾难的火山。
对于非人的诡异力量的恐惧,将浪漫诗哲一个个变成了偏执狂。整个19世纪主导的精神品格,就是这种偏执情绪浸染的“伦理浪漫主义”(克罗齐语),颓废而又狂热,交织着乐观与悲观,对世界爱到极致,恨到深渊。这种伦理浪漫主义在早期浪漫主义那里涌动,在叔本华那里达到,几乎主宰了瓦格纳的全部音乐剧,直接催生了尼采的悲剧精神和权力意志。到了20世纪,“伦理浪漫主义”蜕变为政治机缘主义决断论,同极权主义同流,在艺术中蔚然成风,弥漫于现代主义思想艺术运动中。不论人们绝命挣扎,偏执狂都徘徊不去,去而欲返。“有些东西已经溃烂,有些东西受到摧残,有些东西使我们陷入沮丧而不能自拔,不论它们是我们意欲根除的人类,还是人类无能为力的非人力量。”⑥恐惧更兼忧惧,惊恐尤其惊艳,那种非人的诡异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却自始至终都无法被定到一个特定的对象上。
其实,这种非人的诡异力量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一个典型母题。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的短篇小说《金发的埃克伯特》就萦绕着恐惧与忧惧,惊恐甚至惊艳。一只金色的鸟在埃克伯特面前出现,唱着“森林的孤寂”(Waldensamkeit),让主人公心烦意乱,难决去留,于是灵魂深处爆发了一场生死搏斗,两个倔强的精灵在灵魂之中绝命相争。他说:“有一瞬间,我觉得宁静的孤独是这样美好,而后对于丰富多彩的新世界的想象又使我如此心醉神迷。”⑦将这场灵魂内两个精灵之争实现于历史,就是一场震荡宇宙、开新天地、涵濡雨露以及唤醒世间罪恶的革命。浪漫与革命的关联,在此显山露水,随后风吹云动,最终咆哮江河。金发埃克伯特先知一般地以诗学方式预演了浪漫与革命的变奏。他在愉悦与恐惧交织的情绪状态下虐杀了金鸟,于是各种灾难接踵而至。他被迫不断地杀戮,不断地破坏,各种非人的诡异力量纠结成巨大的恐怖罗网,他越是挣扎,就越陷越深,杀心越重,杀戮越多,在噩梦之中走向了死亡。而这种噩梦,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中堪称典型。这种噩梦有共同的思想来源,即非人的诡异力量主宰着人的生活,逼良为,助桀为虐,甚至以神圣之名行罪恶之实。非人的诡异力量,涌动于法国革命,诗性地呈现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那里,终于造就了伟大而多难的19世纪,其笼罩所及的时段还包括20世纪,直至今天。好像整个世界被一种自然的超自然力量驱动着,在“苦难与整体偿还”之间凄惨地摇曳,走着上升之路和下降之路,兴衰浮沉,悲剧结局一场比一场更恐怖、更黑暗,直至深不见底,万劫不复。于是,浪漫诗哲的心灵亦如凄风苦雨中飘零的枯叶,在神秘的乐观主义与恐怖的悲观主义两个极端之间震颤。
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留下的精神启示在于,解读“自然”如同解读永恒的经典,揭示“风景”就是暴露自己的灵魂。这就启示我们从接受理论的视角去审视早期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的兴起及其主要特征。如果把“自然”看作是一部神秘而又神圣的经典,那么,历史上生息栖居于自然之中的人对于“风景”的发现,就好像是不同时代读者对这部经典的接受过程。“风景的发现”超越了一般所说的“风景的观赏”,正如接受理论中的“解释”超越了一般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风景本非自古有之,而有待以特殊敏感的心灵为装置去发现、甚至去建构。自然就成为一种表达人性痛苦与欢乐的符号,而成为无限渴望源始象征:一切生命不可破除的沉郁悲哀即由此而来,欢乐必然具有痛苦,痛苦在欢乐中必然萦升。⑧谢林还在他的文章结尾把自然直接看作是神圣在此岸留下的踪迹,“自然是最初的遗约或旧约”,但蕴涵于自然之中的“神言”又只有通过人才能得以解说。自然作为神圣启示,存在于一切成为启示之前,而人又是这一启示的合法阐释者。启示与解释,就是自然与人的对话,对话的最高境界便是“同时存在于真理和自然的完美整体”。这一完美整体就是一种对不可能的激情,一种对无限的渴望,一个浪漫主义的新神话。
浪漫诗作为进化的宇宙诗,乃是一种夸张至极的说法,将文学提升到了一种绝对的高度。虽然声称要把艺术诗与自然诗融合为一,这则断章却预示着一种自然的象征主义――新神话的大地之诗。施莱格尔在《谈诗》的戏剧体对话之中假托对话者的口说道:
养育着万物的大自然生生不息,各种植物、动物和任何种类的构造、形态和颜色无所不有。诗的世界也是这样,其丰富性无法测量,不可探究。那些由人力创造出来的作品或自然的造物,都具有诗歌的形式,背负诗歌的名分,但是,即便是最有概括力的思想也难以将之包容。有一种无形无影无知无觉的诗,它现身于植物中,在阳光中闪烁,在孩童脸上微笑,在青春韶光之中泛起微光,在女性散发着爱的胸襟燃烧。与这种诗相比,那些徒具诗歌形式号称诗歌之名的东西算得什么呢?――这种诗才是原初的、真正的诗。若无这种诗,肯定不会有言辞之诗。的确,除了这首神性的诗之外,我们所有人的所有行动和所有欢乐都永远不会有其他任何对象和任何材料,就连我自己也是这首惟一诗歌的一部分,是它的精华。这首诗――就叫大地。⑨
自然的象征主义,有一个要点,那就是用有机体的隐喻来刻画诗的形式。自然天成,扎根大地,生命与宇宙同流,个体与永恒同在,这便是浪漫主义诗风、艺魄与画魂。
二、美至绝境――德国浪漫主义的绝对美学
18世纪到来,一种新的风景建构缓慢开启,一种新的感受模式渐渐形成。启蒙在一定程度上扫荡了教义思维的阴森迷雾,艺术家渴望将风景从神话、神学、救恩历史等主题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让神话的崇高、神学的尊严服务于风景,而不是相反,从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寄托人的生命理想。风景不应该成为神话、神学主题的背景,而应该成为高尚纯洁的人类部落可居可游的空间。席勒认为,只有与人类生命世界、精神世界建立联系,风景才获得独立的审美价值。此时,风景的审美属性就是崇高:无垠的狂野,高耸的山峰,烟波浩淼的大海,繁星密布的苍穹。崇高之物不可再现,惟有同灵性相联系,才能让个人超越狭隘的实在,冲破肉体的牢笼,而象征人类强大无比的尊严。在风景感受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还不是席勒,而是英国的博克和法国的卢梭,他们分别在《对我们有关崇高和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1758年)和《新爱洛绮斯》(1761年)之第23封信,他们分别以论文和小说的形式表述了新的风景感受模式,将风景从传统的审美惯例中解放出来。此后,人们在绘画中相继发现了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发现了欧洲的湖泊与山脉,诗人也纷纷用风景来寄托自己的梦想。这已经预示着浪漫主义文化对启蒙理性文化的再度颠倒了,“浪漫风景画”运动重启了返回心灵、重访神性的道路。
卢梭的《新爱洛绮斯》之后,成千上万令人惊叹的风景被建构出来,仿佛被置于一座真实的剧院中,以某种超感性和超自然性的魅力冲击人的感官,愉悦人的心灵。对风景之美的耳濡目染,对自然世界的静观默察,人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新天新地,享受着其中无穷的乐趣。这便是卢梭所实现的欧洲自然感受史的巨大转折:科学只对自然世界进行原子论的分割和局部的说明,而审美的想象力承担了将整个自然作为活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任务,诗人与艺术家为这种想象力铸造了合适的表现形式。不过,卢梭给予浪漫主义文化的灵感不只是通过想象建构了风景,而且通过将自我绝对化而建构了孤独的灵魂。一个孤独者在漫步时分的遐想,便是现代主体的典范。他感到,一个孤独的主体是绝对自由的,因为他完全同和平的自然环境分离开来。绝对的分裂因此而产生了忧郁的渴念,分裂与渴念构成了自由的必要条件。这个在分裂和渴念之中执着地寻求自我的漫步者,就是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哲人、艺人心目中存留的一道幽美的神圣剪影――这是一个悲剧的绝对。
1795年,诗人席勒创作诗歌《散步》(Der Spaziergang),祝福褐色的群山、灿烂的太阳、苏醒的原野、宁静的蓝天、碧绿的森林、丰饶的河岸,同时暗示日内瓦那位孤独漫步、寻找自然状态的先驱者:人与自然圆融的状态一去不返了。在人日渐远离和谐的自然怀抱之后,风景正在渐行渐远,成为正在消逝的美丽。同年,席勒写作了《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在古典立场上以理论形态表述了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我们曾经是自然,就像它们一样,而且我们的文化应该使我们在理性和自由的道路上复归于自然。因此,它们同时是我们失去的童年的表现,这种童年永远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因而它们使我们内心充满着某种忧伤。同时,它们是我们理想之最圆满的表现,因而它们使我们得到高尚的感动。”⑩当我们是“自然”时,诗歌是素朴的;当我们行进在理性和自由之路上而同自然分离时,诗歌是感伤的,不仅感伤,而且充满了对自然的渴念,以及再度与自然合一的激情。
在哲学家谢林那里,席勒的命题转化到了另一个维度上。人与自然的分离,就是人与神性的分离。人对自然的渴念,本质上是对神性的渴念。人与自然再度合一的激情,终归是与神性再度合一的激情。而人与神的再度合一,是由艺术来实现的。在专论造型艺术与自然的文章里,谢林提出:当自然使艺术成为展现自然的灵魂的媒介时,自然与艺术之间便产生出最佳的和谐关系。故而,在《先验唯心论体系》的结论中,谢林说自然界“就是一部写在神奇奥秘、严加封存、无人知晓的书卷里的诗”,而只要揭开了自然之谜,我们就能从中认出“精神的漫游”。在谢林的《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之中,这一切之最高境界――阅读自然之书,揭开自然之谜,以及再度与自然合一――都归结为与神性合一的绝对渴念。按照谢林的形而上学玄思,世间万物都有其实存的根据。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根据/本质(Wesen),那它就是“永恒太一感到要把自身生育出来的渴念”,“对神性的渴念,也就是意欲生育出这个深渊一般的统一性”。特别值得注意,谢林使用的这个“渴念”兼有欲望、意志、渴望等多层涵义。渴念源自人的痛苦(Schmachten),痛苦来自人与自然、人与神性的分裂(Unterscheidungen),因这种分裂而渴念格外强烈。如果一个人,因而枯萎憔悴,因思念而忧郁成疾,因爱恋而悲伤痛苦,那么他就是浪漫主义的渴念者。诺瓦利斯的奥夫特丁根就是这个渴念者的化身:他的面孔很苍白,像一朵黑夜之花,在黄昏笼罩的夕土(Abendland)深深地叹息。这种令人憔悴的渴念,是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隐秘动机,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绝对追求(thetragic absolute)。
诺瓦利斯用他的诗歌、诗化小说以及诗性的片段书写方式将这种“悲剧的绝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凝聚为“世界必须浪漫化”的命题。“浪漫化是一种质的强化”,就是给卑贱的事物以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的事物以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的事物以未知事物的庄重,给有限的事物以无限的表象。这种浪漫化的心灵律动就呈现在想象之中,诗人要么将未来的世界置于高处,要么将未来世界置于深处,要么将未来世界在灵魂的转生之中置于我们。不论将未来世界置于何处,诗人都是怀着梦想穿越宇宙,而宇宙在人的心中,自然的真理在自我之内。于是,我们看到,早期德国浪漫主义文化运动之中,诗人、哲人和艺人将一个脆弱的自我提升到了神圣的位置上,从而完成了一次对欧洲文化价值的再度颠倒:不是宇宙世界,不是神圣的上帝,不是外在自然和内在理性,而是以梦为马的自我和灵魂成为艺术探索和哲学探索的中心。
作为一种“悲剧的绝对”,渴念赋予了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艺术以独特的个性。一条神秘的路将孤独的灵魂与茫茫的宇宙沟通,这就是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艺术所表现的“内在性”。德国浪漫主义绘画与它的诗歌和哲学精神一致,而区别于同时期的瑞士、西班牙、英国艺术家,后者即欧洲同时代的艺术家总是将自然幻想化进而使之同现实的生命疏离开来。与这种趋向相反,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家有一种将整个生命浪漫化的强烈渴念,将独一无二的灵魂光亮赋予万物,在平庸中发现神奇,在一切场合遭遇神圣与神秘。同时,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备受歌德为首的古典主义者打压和贬低,它在与古典主义的抗争与妥协中寻找自身的合法性。因而,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同古典主义的区别不是其风格与形式,而是其“精神姿态”(Geisteshaltung)。这种精神姿态源自对包罗万象的宇宙中隐秘意义的探求,而自然就成为神秘或者神圣本身,风景成为神秘或者神圣的符号。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哲人和艺人的这种对于“悲剧绝对的渴念”表现在他们将生命艺术化的姿态中。在他们看来,艺术是人类天然的表现神圣的语言,而神圣本身就毫无分别地表现在宇宙之中。将这份外至宇宙、内达灵魂的隐秘渴望视觉化,就是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家所担负的共同使命。当然,这也是浪漫主义风景画运动所分担的使命。
三、写在风景之中的新神话
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样,浪漫主义诗人、哲人和画师在外部空间无限冒险,最后却驰情入幻,外间万象在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之中彼此反射,互相关联,前后比邻。一切都是正在消逝的环节,而迷人的自然和困惑的自心,都是一些象征而已。通过象征与隐喻,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艺术把风景建构了一种关于自然的新神话――写在风景之中的新神话。
F.施莱格尔断言,诗艺,甚至一切艺术的核心,都可以在神话和古代的神秘剧之中找到。而在一个启蒙之后的时代,即古代异教审美主义复活的时代,浪漫诗人、哲人和画师必须像上帝那样,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世界,一个新神话的世界:“因为新神话将沿着完全不同于古代神话的途径来到我们这里。过去的神话里,遍地都是青年想象力依次绽开的花朵,古代神话与感性世界中最直接、最活泼的一切亲密无间,并且按照这一切的模样来塑造自己。新神话则反其道而行之,人们必须从精神的最深处把它创造出来;它必定是所有人力所为的作品中人为色彩最浓重的,因为它的使命是要囊括一切其他作品,要成为一个新的温床和窗口,以容纳诗的古老而永恒的源泉,甚至包容那首无限的诗,即把所有诗的萌芽全都掩在自己身躯之下的那一首诗。”
这首诗就是“不断进化的宇宙诗”,它不仅囊括所有的艺术,而且呈现人类的精神为“总体艺术作品”,且表现人类无限的可完善性。所以,写在风景之中的新神话,就是“感性的宗教”,是通过浪漫诗风借尸还魂的古代异教多神论审美主义。这种“感性的宗教”乃是一个时代的俗众与哲人的必需。这个时代不仅经受了启蒙的荡涤,而且正在经受文化身份分裂的煎熬。在一个文化紧迫而思想危机深重的时代,观念论与浪漫派的崛起恰恰就是布洛赫所说的“青春、转折和创造时代”的征兆。身姿向前驱动,目光瞥向“尚未”(noch-nicht)之境,此乃浪漫主义的基本姿态。可是,浪漫主义强有力地超越启蒙和狂飙突进,而执着地抒写“对于失去的过去的悲情”。“浪漫主义的创造不仅与冲动、本能水融,而且与隔代遗传的预见能力和深渊的窃窃私语水融……显得悖谬的是,在浪漫主义者那里特别富于创造性,恰恰充满某种期待的特征,而这种创造性和期待感仅仅在古代图像中,在过去中,在远古的东西中,在神话中聚精会神,沉思冥想。”一句话,浪漫主义在还乡途中远游,在幽深莫测的岁月之井中发掘出新神话,复活感性的宗教,从而以审美的方式救赎一个物质化的俗世。
1796年,瓦克罗德创作、蒂克补充和编辑的《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一书匿名出版。这个事件被公认为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与艺术的开端,这部重要著作为龙格、诺瓦利斯、蒂克等艺术家、诗人和作家的闪亮登场做了诗意的铺垫,为浪漫主义艺术的风景神话埋下了深邃的伏笔。在远离尘嚣的修道院里,挚爱艺术的修士在平静与谦卑的心境下,依然还怀藏着“对已逝时代中神圣事物的敬畏”,毅然决断以整个生命和宗教激情去履行艺术家的使命。在瓦克罗德的“倾诉”中,浪漫主义风景艺术的“自然崇拜”主题已经朗然照人了:“我知道有两种神奇的语言,造物主通过它们赐予了人类一种能力,即他可以在受造物可能的范围内(……),不偏不倚地认识和理解那些神圣的事物。它们并非借助话语的帮助,而是通过与之迥异的渠道进入我们的内心;它们会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猛然触动我们的灵魂,渗入我们的每一根神经和每一滴血液里。这两种神奇的语言,其一出自上帝之口;其二则出自为数不多的遴选者之口……我指的是:自然与艺术。――少年时代的我就从宗教那古老的圣书中认识了人类的上帝……自然就是一部解释上帝的本质和特性的最全面最明了的书。树林中树梢的沙沙作响,滚滚的雷声,都向我诉说着造物主神秘的事物,我无法用话语表达它们。一段优美的山谷,为许多千奇百怪的岩石所环绕;或是一条平静的河流,其中倒映着婀娜的树姿;或是一片开阔的绿色草坪,映照在蓝天之下;――啊,所有这些事物,都比任何话语更能神奇地触动我内在的情怀,更能深刻地把上帝万能的力量和他万有的恩泽载入我的精神,更能使我的灵魂变得更纯洁和高贵。”
早期德国浪漫主义为一种自然哲学所启发,又反过来为这种自然哲学推波助澜。这种自然哲学将自然概念与上帝概念联系起来。早期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便是这种万物有生论与万物有机论的视觉表达,从而为表现与超验灵性铸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在C.D.弗里德里希那里,这种新的宗教语言就是“情绪风景画”或者“寓意的风景”;在P.O.龙格那里,这种新的宗教语言就是“风景的神话”。
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年)的风景画是早期德国浪漫派自然象征主义的典范与先驱。作为风景艺术家,他在超验神性的笼罩下以一颗微妙的诗心去触摸风景,艺术地把自然解读为古老的启示语言,解读为传递灵知的象征媒介。《云山雾海浪游人》(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便是早期浪漫主义情绪风景画的典范之作。云雾弥漫的山崖之巅站着一位年轻的浪子,他面朝一片苍茫的背景,背对着看画的观众。我们观众永远也无法知道,这幅苍茫风景是令他欣喜还是令他忧惧。我们只知道他在沉思默想,在用心体验自然浩淼无垠的生命给予他灵魂的激荡。而宇宙的无边动荡和生命的隐秘节奏,提示人们要应目而会心,体察其中活跃着的那种非人的诡异力量。而这幅投射了心灵的风景,便成为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新神话:诗意的形象变成了一种实在,象征负载着主宰经验世界的神奇魔力,作为主体的个体变成了一种通过自然而追求神圣的人。正如A.施莱格尔所说,浪漫主义诗人和画家“为了达到一种神奇而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必须以灵性来主宰物质世界”。其结果便是像诺瓦利斯在《奥夫特丁根》中所做的那样,把故事的主角化为“花朵”、“生灵”、“岩石”和“星辰”,按照林中仙女和山中妖女的形象来构思和描摹风景。在如此构想的风景中,人成为救世主或者“自然的弥赛亚”,而自然也充满了道德感,而成为人类的“女教师”。
在19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艺术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特征在于其对于“属灵维度”的刻意呈现。1808年,C.D.弗里德里希《山上祭坛》(Tetschener Altar)的公开展出及其所引发的戏剧性论争,就是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神话艰难历世的见证。镀金的哥特式拱顶画框上,十字架在岩石山巅挺立,直逼苍茫太空,长青木在四周林立,十字架底座环绕着常春藤,落日残照辉煌,黄昏紫色光辉映照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把祭坛安排在山上,而把风景与祭坛并置,从而产生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样式――风景祭坛。青翠的十字架呼吁拯救,绿色森林之中的圣林传递灵知,常青树象征复活的生命,以及哥特式的教堂建筑风格表现基督教的幽深,这一切乃是浪漫主义艺术与中世纪精神之间传承的历史明证。大卫・弗里德里希生于波罗的海地区,在灵异盎然的丹麦度过了学艺时光,养育了历史精神以及内面精神维度,其接受和传递信仰的方式就是“自然布道”。换言之,他在艺术之中贯彻着自然象征主义。《山上十字架》是典型的祭坛画,然而此作甫一面世,即招来了公众的指摘,说他是如何冒天下之大不韪,僭越风景艺术和宗教艺术之间的森严壁垒。他自我辩解说,这是一种灵知,承袭了森林基督教的古典传统,而画上那棵常青树象征着耶稣复活之后的永生永福。
3年之后,即1812年,弗里德里希又创作了《冬景》(Das Winterszenerie),将自然的象征主义融入基督教神话体系中。自然被描绘为“神性之造物”,“与一切人文化成的造物相对立”。在画面最显著的位置上,触目惊心地伫立着冷杉树。这个植物便成为灵知意象,象征着基督在冬日的死亡之中复活的希望。这种象征的意蕴,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北欧和日耳曼人的历法。根据他们所感知的节序,冬天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像肚脐一样连接着异教灵知与基督教信仰。这个节日就是临近圣诞节的冬至日,其现代形式直到宗教改革前夕才出现在德国的日历中。冬日,准确地说,冬至日,乃是圣诞的呼召之日,一个经过洗礼的异教的圣诞光明节庆之日。冬日寒冷阴霾,到处是死亡的萧瑟。而在厚厚的积雪中,竖立着常青树。常青树乃是圣诞树,象征着救赎主降临的消息,以及他死而无怨、死而复活的希望。拄杖而行的旅行者就是朝圣者,他步履蹒跚地走到了十字架前。他紧紧依偎着岩石,而抛开了拐杖,而岩石上一枝干树在十字架左侧平行伸张。岩石象征着基督教经典,拐杖象征着羸弱扶病的生命,而伸张的干树则象征着因被救赎而复活的生命。青翠十字架传统之中所有的神话和象征体系,都凝缩在冬景画面上了。画面的背景上,哥特式教堂耸立,直逼苍天,启示天堂的居所,灵魂安息之地,漂浮的薄雾笼罩着精神的家园。教堂尖顶线条明晰,与冷杉树孑然独立的形象交相辉映。整个画面烘托出一种人间匆匆节序,将一个时日升华到了神圣的高度:这个日子不是一年之中黑夜渐渐变短而白昼渐渐变长的节点,而是万物死而复生的日子。冬日召唤救赎,如同雪景预兆春天,且希望春天能够永恒,生命得以永生。那一丝新绿,便是春天的一袭温柔,那些无畏雪压而渐渐展露叶尖的小草,预示着不算遥远的春天。冬天的绝望与春天的憧憬纠结在画面上,将一种绝对的悲剧情怀升华在信仰的灵知中。画面上的十字架与冷杉树一起,直面观众,救赎与复活的信息直击观众的眼睛,冲撞观众的心灵。植物与十字架构成了俯视教堂中殿的祭坛装饰,而教堂就是画家弗里德里希树景背后的“灵之圣所”。青翠植物,就是祭坛与唱诗班,它们咏唱着将自然与哥特精神融为一体的赞美诗,一首死而复活的赞美诗。十字架下面,散布在岩石旁的枯木象征着人类的堕落,枯木如羸弱的爪子绝望地伸向基督。天汉分源一般的流水,在十字架下涓涓流淌,最后注入了“治愈之池”,它象征着涤净罪孽获得救赎。于是,弗里德里希以神性为向度,用自然象征主义弱化人的因素,强化风景的神性内涵,从而规避人类中心论的藩篱,把风景建构为一种新的神话,以及感性的宗教。
四、中国形态的自然象征――“一画”与“灵知”
学兼中外而深受浪漫主义灵韵浸润的宗白华先生,将弗里德里希风景画解读为近代欧洲精神的象征,那是控制无限空间的强烈欲望所驱动的一往不返的追求,其结果是彷徨不安,怅望无限,渴念难平。而这同中国古代诗画所呈现的空间迥然异趣。宗先生认为,节奏化的音乐空间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象征,那是亲近自然宇宙的深情韵致所涵养的回旋往复的意趣,其境界是潆洄委曲,往复绸缪,逸韵升腾。欧洲浪漫风景画对无穷空间的爱,是一种生命激情和精神渴念,如此激情与渴念可能会导致一种悲剧感。而中国古典美学有没有这么一种悲剧感呢?
苦瓜和尚石涛就用他的“一画”道说了艺术之美的绝对性,从而呈现了风景审美的悲剧感。“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苦瓜和尚如是发问,而坚执地以“一画”界破天地,收拾乾坤。苦瓜和尚石涛(1641-1707年)原名朱若极,为明藩靖江王朱守谦的后裔,也算不乏王室血统。年少皈依佛门,却始终萦情山水,且为艺独尊自我。宋代之后无中国,明代之后无华夏,清代之后无汉人,这不是肆意贬低历史,共孽显扬而命慧晦蔽使然。江山社稷如此,艺术也难辞宿命。高古苍茫而近古昭明的崇高画境如幻梦如泡影,如风之神如虹之气无奈雪压霜欺,阴风惨雨,而从衰退的民族心灵里消逝了。支持画家艺境的是残山剩水,孤花片叶,虽有飘逸之美,而乏磅礴雄图。以“一画为通变之法”,石涛志在呼唤一阳来复,为艺境之淋漓元气招魂。然而,“一”之于艺境,与其说是画“器”,不若说是画“道”,然器载人灵达入道,便是由艺进道,人灵上行。一幅石涛晚岁自画像,年迈的画家满脸矜持,神态孤傲,疏野干枯之笔墨勾勒出他的心灵世界:悲情而不乏慧心,忧生忧世而又落拓不羁。而且,似乎还有一种文化遗民的心性不知不觉地渲染着他的孤高与脆弱。梅花羸弱却坚韧,显然寄寓着苦瓜和尚微妙隐秘的情性:“怕看人家镜里花,生平摇落思无涯。砚荒笔秃无情性,路远天长有叹差。故国怀人愁塞马,岩城落日动边笳。何当遍绕梅花树,头白依然未有家。”砚荒笔秃,头白无家,整个一副未成正果的德性,然而他以“一画”为笔性师心,沉入杳渺的灵魂深处,直接遭遇一个黑暗的世界,在众沤洪涛之中让黑暗点亮他自己卑微的生命,用这份集悲于慧的微弱光亮去烛照宇宙间的“奇枝怪节”。倾空内府,澡雪精神,乃是苦瓜和尚的一贯姿态。惟其如此,他就可藉着“一画”经天纬地,裁云剪水,吐纳烟霞,用情于笔墨之中,放怀于笔墨之外。
宗白华先生尝试将苦瓜和尚和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荷尔德林捉至一处,而涵濡中外,看东西方艺术精神之汇通。“天地氤氲秀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这是“苦瓜和尚”石涛的题画诗。宗白华比附诺瓦利斯在《奥夫特丁根》第九章中的名句:“混沌的眼,透过秩序的网幕,闪闪地发光。”宗先生的类比逻辑是,中国古代画家与德国浪漫主义诗人都要求在自己的作品里把握到天地境界,而境界就是自由的境界。这一境界类似于石涛的画境:白云笼罩山巅,虎过腥风乍起,“怒猊抉石,渴骥奔泉,风雨欲来,烟云万状,超轶绝尘,沉着痛快”。其中自然涌动着一股淋漓元气,一股渺远而且诡异的精神力量。“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这是诗人杜甫形容诗歌的最高境界的诗句。宗白华紧接着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诗句:“谁沉冥到/那无边际的‘深’,/将热爱着/这最生动的‘生’。”按照他的一贯逻辑,深沉的静观与飞动的活力构成了生命、宇宙、精神的两境,两境相入则有生生不息而又和谐有序的音乐化节奏化的文化精神,而音乐化和节奏化是中国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的特点。
40多年后,高尔泰先生也在“苦瓜和尚”的画语录之中读到“美是太一的光辉”,而“太一”并不神秘,正是个体生命在一瞬间所体验到的自由。高尔泰、宗白华一脉相承,以浪漫视野涵濡古典艺境,以古典艺境汇通现代精神。浪漫主义赋予自然以灵性,再现了西方哲学文化的另一种精神,一种同古希腊―近性主义相对立和补充的精神。这种说法触及了浪漫主义的灵性与灵知,但没有揭示这种灵性与灵知的渊源所在。诗人诺瓦利斯有一首名诗《夜颂》,其中尽情歌咏了忧伤。但是,诗歌在爱情与死亡、壮丽的光辉与恐怖的黑暗、灵魂的狂喜与肉体的战栗之间展开,我们分明感受到本雅明所说的“神圣救赎”与“世俗进程”之间整体偿还的节奏。但最让人提神的诗句是“在地面上漂着我的解放了的灵气”,这“灵气”之“灵”,便是灵知主义之“灵”。按照汉斯・布鲁门贝格的说法,中世纪基督教对灵知主义的克服以失败告终,灵知主义隐秘流传,终于在启蒙后的浪漫主义文学之中发展为波澜壮阔的废黜超验的思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灵知主义以审美主义为中介间接导致了基督教正统信念的解构。阿道夫・哈纳克断言,灵知主义从来就没有影息于思想历史,而是以文学形式、诗歌形式借尸还魂,复活在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以及俄罗斯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高尔基的作品之中。埃瑞克・沃格林则作惊人之论,说灵知主义构成了现代性政治的基础,而现代性就是灵知人对上帝的谋杀。灵知主义谱系班驳模糊,一时还不甚了了,但读浪漫主义诗人如诺瓦利斯、荷尔德林的作品,则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灵知主义把这个世界看作是异乡,因而诗人怀着巨大的乡愁寻找故园。
寻找故园,就是渴望拯救。这就是灵知主义的一种最低限度的信仰,其要义是人类心灵深处有一道神圣的闪光,这道闪光与至高无上的神息息相通。可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意识不到这神圣的闪光,因为我们沉沦于物质现实里面,而完全蒙昧于神圣。蒙昧于神圣,所以只有以孤独、忧伤的心灵去遭遇这个陌生、邪恶的世界。现代文学中的灵知主义与彻底摈弃世界的古典灵知主义略为不同,那就是更深地沉湎于自己的内心之中,以孤独的心去感受世界,渴望遭遇黑暗和穿越黑暗,获取那神圣的光。现代诗人失落自己于内心,“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化而出”,从紊乱之中寻求秩序,从罪恶之中发现美,在黑暗深处遭遇光明,这就是宗白华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审美主义。他还用王夫之“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来描述这种审美主义。由于他对宇宙人生怀有深挚的爱和广博的情,我把这种审美主义称之为“审美的世界主义”。我们在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诸神死了》的最终境界之中亦可体验到这种“审美的世界主义”:日暮黄昏,风起云扬,古希腊牧羊人低回哀婉的箫声与基督教堂里晚祷的钟声交相呼应,彼此和鸣,这象征着异教与正统、恶魔与圣洁的最后和解。石涛诗曰:“奇枝怪节多年尽,空腹虚心太古时。”于是,艺术家就臻于天地不言、花开水流之境,而这就是终极的实在,也是超越了审美的属灵的真实实在。(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R.耀斯著,顾建光等译《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②谢林著,邓安庆译《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7页。
③诺瓦利斯著,林克等译《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④Jacques Derrida, 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 Vol. II, ed. Michel Lisse, Marie-Louise Mallet, and Ginette Michaud,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Chicago and Lo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 190.
⑤布鲁门伯格著,胡继华译《神话研究》(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4页。
⑥伯林著,吕梁译《浪漫主义的根源》,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110页。
⑦蒂克《金发的埃克伯特》,孙凤城主编《德国浪漫主义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
⑧同②,第118页。
⑨Haynes Horne etl. (ed. ), The Theory as Practice: A Critical Anthology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 Writings,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ta Press, 1997, p.181.
⑩席勒著,张玉能译《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263页。
谢林著,梁志学译《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76页。
同②,第72页。
David Farrel Krell, The Tragic Absolute: German Idealism and the Languishing of God,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84-89.
同③,第134页。
同,第80页。
Beate Allert, “Romanticism and the Visual Arts”, in The Literature of German Romanticism, ed., Dennis F. Mahoney,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4, pp.276.
施莱格尔著,李伯杰译《浪漫派风格》,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布洛赫著,梦海译《希望的原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W. H.瓦肯罗德著,谷裕译《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