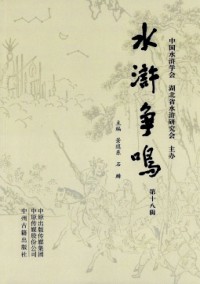描写父亲的诗句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描写父亲的诗句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描写父亲的诗句范文第1篇
说起诗歌,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无论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还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时的诗歌,就像如今的好歌词,朗朗上口又广为传播。
不过,斗转星移,随着诗歌的小圈子化和精英化,后来的个别诗作,在所谓后现代、先锋派等概念面前,越来越不接地气。不着边际的联想、语无伦次的呓语,使得其慢慢成了让人“高山仰止”的“稀世珍品”,无法被老百姓平凡的胃口接受。
此后的诗歌,通过音乐这个载体,歌词这种形式,在另一个层面复活。但是,仍有个别民谣歌手,他们就算写不出一句通顺的旋律,也要弄出一段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句,要不然就感觉没法在民谣圈立足。
这在后来便形成了一个有些奇怪的现象,即音乐创作中的诗歌体写作模式。故乡、远方、梦想、流浪、姑娘、理想、迷惘、挫折……诸如此类的词语大量出现,无疑也背离了诗歌那种充满想象力的创作意旨。
其实,诗歌的兴与衰,很多时候和现实有关。就像董玉方的这首《父亲写的散文诗》,它本身就是诗人根据父亲日记中的片断采撷加工而成,可以说是典型的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诗人没那么神秘,诗人应该先是生活的创造者,然后才是文字的编织者。根据生活中平凡又琐碎的点滴,加工出饱满又具有热情的文字,这才是诗人该做的事情。
如同《父亲写的散文诗》中描写的那样,“旧报纸,那上面的故事,就是一辈子”。没有一个生僻字,没有任何的文字游戏,都是你看得懂的话,却在字里行间,呈现生活的点滴。
S飞根据《父亲写的散文诗》谱曲,加工出新版本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时光版),同样也是贴合诗歌本身的情境,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将这些文字有韵律地表现出来。口语化的旋律,以及在口语化旋律基础上的节奏变化,让这首歌曲平实却不呆板,就像每一个平凡人在平凡的生活中,谱写在个人看来,未必平凡的命运一样。
《父亲写的散文诗》(时光版)里吉他与钢琴交织的简洁编曲,把现代乐器中素与雅的两面,很好地呈现出来。它们在音乐中,隐隐约约又无处不在,让一首娓娓道来的好诗,变得分外动人。
描写父亲的诗句范文第2篇
一、善于点拨学生向文学艺术作品学习丰富的想象
让学生多了解文学艺术作品对培养想象的作用。我告诉学生,诗人和画家常常被认为是具有最丰富的想象力的。诗人和画家正是用他们的想象力,为我们描绘一幅幅形象生动的画面。如我在教《汉江临眺》这首诗时,其中有两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两句时,启发学生:“诗人王维的诗被苏轼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那么,请你展开想象,在你的头脑中将会出现一幅什么画面?”这两句写汉江水流汹涌,似向天地之外奔流而去,远山由于被江面蒸腾的水气所笼罩,“若有若无,时隐时现”,后面两句“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写襄阳一带的城郭楼阁,远远望去似乎飘浮在前面的江面上,翻滚起伏的波澜好像撼动远处的天空也忽上忽下的。这两联突出地描绘了汉江水势的雄伟壮观。
诗人运用了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在这首诗中,王维把画家的观察、诗人的思考、绘画的技巧、诗歌的手法极自然地结合起来了。他巧妙地描绘了同时并列干空间的景物,生动地表现出自然界持续性的运动、变化。引导学生依据诗句想象并描述诗中所展现的富有动感的画面,在学生的头脑中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善于激发学生头脑中的记忆。让他们再现生活中的经历,以展开想象
如我在教朱自清的《背影》一文时,文中写“父亲为我买橘子”,有一段文字写到:“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下身去……用两手攀着上面……显出努力的样子。”我让学生在头脑中想象,父亲爬过铁道买橘子的情景。再想象一下自己的父亲在平时给自己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这样通过让学生想象加深了学生头脑中对父亲背影的印象,更能让学生体会出父亲对儿子的深厚感情。
三、善于通过点拨启迪来引导
描写父亲的诗句范文第3篇
于是我开始了对李汀的阅读,获知了他的更多的精神历程。他写诗、写戏也写散文,影视作品有《华都街口》、《彼岸芳草》、《再生人的秘密》、《走出雨季》、《舞萌》等等,散文我看到的有在《十月》上发表的《外婆的脸是一只摇篮》和在《中国作家》上发表的《九月逢冬》,两篇散文在美丽和平实的语言书写里都滥觞着怀旧和自省的魅力。《活的石头》则应该是他的第一部诗集,收录了他大约在1999年至2001年的136首诗,还有一些是过去写了又在这段时间里改动过的诗,这些作品被他分成各为“天渊”、“心篮”、“石忆”、“灵履”四个分辑,从分辑的取名上就能看出诗人是一个很注重意象捕捉和直觉抒写的智者,就象诗人在自己的文章里所写到的那样是“完全发乎于真诚的所思所想而形成的”。
李汀的他的书写方式其实是较为通俗易懂的,然而,要真正诠释他诗中焕发出的那种对一切富有生命力的事物的感悟,似乎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且因为身份和经历的缘故,使这种“不容易”凭添了一些朦胧曲隐的特性。比较而言,我更能亲近他2000年元月写的《活的石头》这一类的诗作,因为他在这些诗中充分表现了对意象艺术运用的娴熟和高超,让每一个阅读它的人都可以注入自己的生命之流,然后再去染成各自的颜色。诗的哲学意义就这样诞生了。
李汀诗中的意象之感动
诗的意象的首要元素,就是诗因意象而感动诗人自己也感动读者,这一点李汀做到了。
意象的感动首先是真情实感的抒写,李汀就是如此,他收拾着他可以收拾的包括出身、工作、迁徙、行走在内的所有财富,把那些思想的经历凝练为感动的元素,然后经过意象的孵化,再巧妙地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们可以看看诗人对父亲的描写:一首是《父亲》:“声音留给空白/凝结在永久的过去/伤痛依然相系/温暖和冰寒/对话常在梦里//我尚在前行/你却不是影子//在未知的所有时日/我都在承受爱的负荷/由你无由无碍的抚摸/遗憾无法偿还//爸爸/老父/我不能不噙着泪水/你是我生命之肩”诗人通过意象的孵化,使一个很具体很个例的父亲升华为一个也许人人都感同身受的父亲。同样,他在另一首《父逝》里对父亲又有如此描写:“大雪飘落在腊月/你突然降温/没有打招呼/血就成了冰//那一霎/我的血陡热/可灼烫的泪再多/也不能把你冰的肖像/融化一小块//血燃成火/把你烧作了烟/那时我突然长大/大到了头顶抵着你的脚跟”在这里,诗人把对父亲的情感和怀想,意象化地比作雪和血、冰和火,强烈的热与冷的意象把情感真实而又概括地传导给读者,让读者看一眼就砰然心动。
意象的感动又是激情的贴切表达。李汀的诗作大多是先把一种激动的情绪抓住了,然后沉淀,再酿造出炉。这样的诗一般来讲是高山平湖,把汹涌的波涛和跌宕的瀑布都留给了它的过去和将来,然而即使这样,读李汀的诗仍然会有一种冲动,这是因为诗人平静的表面是被潜在的涌动所托举起来的。如《晨》一诗中,诗人利用一个平凡的苏醒的瞬间,一场平凡的夏天的雨,写出了那不平凡的一阵隐伤,写得节制而沉郁,惆怅而深刻,仿佛伤感中夹带着对生命的感激和对时光流逝的眷恋,诗人一再地诉说“我是真心喜欢活着”!他高喊着“吻我 吻我/倘我不再复苏/就请抡起太阳的重锤敲响/灵魂的钟声吧”。
李汀诗中的意象之深刻
一个真正的诗人本质上必然也是一个哲学家。诗人的心灵、哲人的头脑,两者似乎永远无法分离,不世故、不务实,是诗和哲学的共同的特点。然而,诗人与哲学家的不同,就在于哲学家用逻辑说真理,诗人用意象说真理。李汀的诗有着无穷的哲学含义,有着平和的愤怒、荒谬的存在,有着无望中的渴望、微笑中的悲哀;同时,他又有意将这些深刻的哲思藏在他的诗的陈述中,这无疑令他的诗纯熟凝重而又带着苦涩。
意象的深刻首先表现在诗人的尊严。真正的诗人不会是起码不仅仅是物表特征和人情世故的描摹能手,他所见所思的一定是人类和宇宙共有的现实问题和精神事态,因此,他的所有努力和挣扎就是在坚守人类思想领域里高于一切的人格尊严。诗人在面对一张照片时这样联想――“看自己的昨天/证明今天/当自己成为昨天/就留给别人/看另一个人的昨天/还有前天” (《照片》);诗人在看见鸽子时会发问――“用多少鸽的飞翔/记一首五线谱/才能为和平/抒怀//用多少牺牲的白骨/作柴/烧一堆火/才能把烽烟/替代//回答/让所有的生者” (《问和平鸽》);诗人在看见流星时理解着人为了尊严不可以――“为一瞬华丽/丢了自己”又想到人为了尊严可以――“愿全部热恋/离经叛道”(《流星》)。
意象的深刻又体现在诗人超越自我的孤独。一个真正的诗人必定格外重视人类的孤独感,并把这种孤独感视作一种高贵的精神立场;一个真正的诗人必定是对孤独有着特殊敏感的人,他坚持不懈地向孤独的深穴摸索,坚信拥有孤独才拥有渴望和力量,坚信只有孤独的灵魂才会有崇高的大悲哀和大欢乐。李汀在自己的诗的解构方式和话语向度上都对孤独进行了终极讲述。为此我推崇他的《雪地》――“雪地是一面镜/会映出你模糊的肖像/不必惧怕寒冷/让温热的躯体与它重叠//雪地没有底片/只有冰冷的胸襟袒露着/期待你一颗无尘之心一如冬阳/丢下/它把全部的感动融化了/给你只给了你/纯泪的一片湖泊”雪地就是诗人自己,融化的都是诗人孤独的泪,他的爱因为孤独而没有底片,因为孤独不可以复制,也不可以存放储藏,他把自己对所爱的人所爱的物所爱的宇宙天环的那一份纯洁,毫不吝惜地一古脑地合盘端出,在孤独地渴望那颗冬阳的过程里也化作感激的泪湖。诗人的孤独是牺牲性的因而是崇高的,是无我性的因而是超越的。
李汀诗中的意象之恒久
万物都属于永恒生成的自然之全,诗也一样。诗人搁下了笔,思想却伴随他的诗句留存着,它激发出新的思想。周而复始,就进入了永恒。李汀的诗不光是写给今天也是写给未来的,这应当无庸置疑。我们在被李汀的诗所感动的同时,也会感受到那些诗句给我们的不能用时间限定的力量。
诗的永恒,首要的是那种排斥当下媚俗文化的非功利心境。《岩画》似乎就是诗人不齿于世俗和功利的写照――“那些粗砺的萌/不知道什么不朽/更不齿于名利//一斫一刻/全由心的真切情不自禁的/疯狂催生”。那么,诗人在《敦煌飞天》里所表现的非功利则给我们带来莫大震撼――“是一种灵魂描绘另一种灵魂/是一个空灵的梦把另一个更为空灵的梦托举/厌倦了地上苦难的/让天上的梦发芽/梦/无论谁做做些什么都不算奢侈”。
诗的平民思想的意蕴流泻,也是诗之永恒的保证。诗集里的《寒风中一个老妪前行》中诗人对人与岁月抗争、《一只天堂鸟――给H君》中诗人对生命处境的注解、《听唢呐》中诗人对农人情感的亲近、《拾雪的花袄》中诗人对贫瘠而不堕落的生活的呵护怜爱,无疑都折射出诗人平民思想的光芒。这种思考还表现在诗人对自然的理解和歌咏,如《雨燕》《海、船》《日子》等。诗人的平民思想也体现在童心上,《牵牛花》“很少见牵牛花了/小时候心爱的小喇叭/紫色的花冠白色的花尾/每看到它/就能听到/嗒嘀嗒 嗒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牵牛花/记忆的花/想起来眼泪会滴下”
描写父亲的诗句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体验教学;新课标;语文课堂
一、利用语言描述情境,实施体验教学
“以语言描述情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情境体验的方法。在体验式课堂教学中,运用语言描述创设情境主要表现在课文导语的设计和体味文本词语或语句含义两个方面。不同的课文由于有着不同的主题内容、题材特征和情感内涵,所以就应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设计导语,营造符合课文感情基调的教学情境,同时教师在运用语言描述创设情境时,要注意做到语言简练、准确、生动且富有感染力,在描述中要精选一些可以用感官体会的具象性词句,这样可以使知识信息真切而形象地映入学生的感知之中,给他们审美愉悦。
例如教朱自清的《春》时,教师满怀激情地说:“我们一提到春,眼前就仿佛展现出阳光明媚,东风浩荡,绿满天下的美丽景色;一提到春,我们就会感到有无限生机,无穷力量。”请同学们回忆一下你知道哪些吟咏春天的诗句?学生纷纷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说出“春来江水绿如蓝”“春风送暖入屠苏”“春心莫共花争发”“二月春风似剪刀”等诗句,这些诗句使学生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春意萌动的生动场景,通过诗句意境的引导,使学生置身于情境之中,学生们进入了春天的环境中,也就的自然而然地触动了学生心中对春天的喜爱之情。然后教师可以进一步引导:“课文中的这些自然景色,你是从哪里体察到的?”这样,学生的内心就会随着审美情景自然而然地打开,进入文章展现的情感世界,进而把课文中的“彼情彼景”转化为“我情我景”,更深入地体验文章的艺术真谛。
二、借助多媒体描述情境,实施体验教学
在语文审美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审美能力主要是通过语文教材,在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一系列审美体验的过程中逐步培养的。恰当利用多媒体来创设情景、组织教学,可以使教材这一静态客体,变得富有动态感,促使学生的审美活动向生命的深层次发展,从而使教学达到理想境界。
课堂教学中,可以根据教材的不同特点来创设新颖和谐的教学情境。比如在教授《春》中写“春雨”的那部分深情地朗读。听后,请学生描绘春雨的特征。在把夏雨和春雨的描写比对之后,提问:“为什么朱自清描绘的春雨那么美妙动人,而老舍写的夏雨却凶猛可怕?”学生联系课文思考,终于找到明确答案:朱自清描绘春雨的种种特点,是为了表达他对春天的无比赞美之情;老舍先生写夏雨是为了向读者展示骆驼祥子生活环境的恶劣,从而让人体会到祥子生活的艰难痛苦。这样,又回到了对作者思想、观点、情感的理解和感悟上。应引起注意的是,我们用多媒体辅助创设情境,应该辅助在学生经验的盲区、知识的盲点、思维的堵塞处、情感的模糊处。多媒体的使用绝不能成为一种美丽的“包装”,也不能用的过滥,而要坚持为学生的“学”服务,以起到启发、诱导、点拨、开窍的功效,追求点“石”成“金”的境界。
三、围绕问题描述情境,实施体验教学
在教学中,教师结合课文提出疑问,激发悬念,让学生在课堂的学习中心存疑问,以问题作为学习的载体,围绕问题的出现、提出、分析和解决来组织自己的学习活动,并在这样的活动中逐步形成一种强烈而又稳定的问题意识,始终保持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以激发他们的思考和讨论,在渴望答案的求知情境中学习。
创设问题情境,在需要讲授内容与学生求知心理之间制造出一种“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可以使学生的兴趣持续高昂,使课堂心理时间短暂而充实,使课堂心理空间广阔而丰富,使每个学生活动充分,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愤悱”的状态之中。问题情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学生所接触的学习内容与现有知识水平和结构发生冲突时,但却不知如何解决的心理困境。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依赖于问题情境提供的信息支持。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创设出能够引发学生认知冲突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产生认知需要,产生探索的心理意愿,使学生的认知过程置于特定的问题情境中,提高有效性。例如,在教学《背影》一课时,我围绕教学目标“学习在特定环境下抓住特点描写人物的写法”设置了问题情境:课文中四次写到“背影”,哪一次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为什么?并围绕这一问题设置了一组序列性较强的问题(划出四次背影的描写,看看哪次背影印象最深?引导到第二次“车站送别”场面上),适时追问:为什么买橘是集中体现了这种父爱?讨论交流后,进一步思考:其他三次背影与这第二次背影有什么关系?贯穿全文的主线是什么?最后让学生开展讨论: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这种感情?由于成功设置了问题情境,引发了学生认知冲突,学生在交流活动中,迸发出众多思维的火花。学生所作的回答,充分体现了思维的广度与深度:“父亲是在身心疲惫,承受着巨大的生活与情感压力的情况下,亲自为儿子买橘,这背影真正凝聚了父亲对儿子的慈爱之情,读来让人感动。”于是,我马上引导总结:“是啊,正是在如此特定的环境下,父亲买橘的一举一动,那‘蹒跚’的步履,那‘肥胖’的身影,那努力的一‘攀’一‘缩’,让儿子流下了感激的泪,也深深拨动了我们的心弦,对文中父亲的背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整堂课学生思维活跃,课堂气氛热烈,有效促进了学生的批判思维。这样的问题情境能把学生带入虚实相生,充满张力的思维情境中。
总之,体验使学生在语文课堂上拥有更多的机会去学、去想、去做、去说,我们教师宜鼓励学生生成积极的体验,学生如若产生消极体验,应加以引导,指引学生积极走进真实的生活,避开毫无价值的虚假、空洞、粗浅体验,启发学生在阅读及写作体验中不懈追求、感悟成长。
参考文献:
[1]黄仕秀.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情感[J].语文教研,2010(35)
描写父亲的诗句范文第5篇
[关键词]张守刚;诗歌;精神内蕴
一、张守刚打工诗歌的地层化
打工意味着一种漂泊,是一种被动的行为,饱含着一种无奈与辛酸,备受冷落与白眼,他们是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也是一种命运被迫式的不得已的选择。“打工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贴近时代,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存与命运。”拥有打工和写作双重身份的张守刚,运用他的笔记录下这段打工者的历史,让同时代和后来者更深刻、全面地了解这个身处社会边缘的群体。他的打工诗歌是对生活在底层民间的弱势群体的精神及生活状况还有内心的表达。
(一)漂泊主题
“身世浮沉雨打萍”是对打工者所处的状况的最贴切的表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差距拉大,很多农民被迫离开生养他们的故土,到所谓的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空间。这些打工者虽然进入城市,但是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制约,却没有城市居民的正式身份,只能被城市遗忘甚至于抛弃,成为处境尴尬的“漂流族”。漂泊是打工者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打工者的情感、体验在张守刚创作的打工诗歌中都能很好的表现出来。尤其是张守刚诗歌中所表现的打工人漂泊中的孤独感、失落感。
张守刚的打工诗歌,深刻地表现了漂泊着的打工者生命的孤独感和悬浮感。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根意识”是极其强烈的,“强根”才能“固本”的观念一直流传。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对于长期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来说,茫然去面对这陌生、无援的世界,他们割断了自己与亲人、与土地、与家乡的联系,就等于失去了多年来赖以生存的根本,不可避免地会有孤独和悬浮感去。这些必然带来焦虑感。对打工者而言,他们的焦虑主要表现在对自己身份的焦虑,以及对自身处境的焦虑。原因就是这些打工者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生存,难免由于社会的冷落,外乡的不适应而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而无所适从。如张守刚的《皮革厂的灯光》“它的白天是夜晚/它的夜晚是白天/那些迷惘的灯光/常常记不起/白天和黑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那样一直苍白着/苍白地映着它目光下/被流水线追赶的/单薄的身影/还有被那些愤怒的机器/不停谩骂的手/那些疲惫的手啊/摩挲着一张张高贵的皮/裁剪 缝合……”在这首诗里,张守刚把打工者无所适从的感觉,还有在打工时受到的压抑,不用很有力度的字眼表现出来,打工者身处异乡的困惑,对自己身份的茫然感也不言而喻。
张守刚的打工诗歌还表现出打工者时时刻刻在为自己的处境担忧的精神和一种心理状态。外在打工者与城市的关系非常的敏感,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疏离感,在这个大城市,他们没有家庭亲人,没有一个长久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固定职业,“租来的房子和高风险(或强竞争)的工作能够在瞬间将他们抛掷出去,使他们与这个城市的联结断裂。”城市生活千变万化,虽然打工者小心翼翼地经营着属于自己的每一份工作。但是面临的都是试用期,随时会被城市淘汰。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与处境很是迷茫。对他们而言生命与城市似乎总是陌生的,没有方向的,茫然的,虽然打工的目的地是南方,是外地,是城市,但是这些词语只化为一个指向、一个符号,未来是什么样子,梦想到底为何物,他们始终存在疑惑。“暂住证”、“身份证”一些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牢牢装在身上,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如果他们丢失,那么自己在城市中就更难立足,处境就会更加焦虑。如张守刚《我的身份证掉了》一诗中的:“我朴实的名字里/裹着新鲜的乡土/无论它掉在哪里/都会像一棵野草一样/生长”。张守刚的这首诗虽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生命律动,但是,其内因是打工者对自己身份、处境、漂泊不定生活的焦虑所引发的。
漂泊,打工者的一种存在、生活方式,其实是一种生存所迫,也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他们快速进入城市,却不能顺利融入城市,他们只是在漂泊。张守刚的打工诗歌,让我们听到了来自生活底层的无声呐喊,捕捉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城市的边缘线上颤动,也让我们对漂泊者的处境有深刻体会。
(二)主体痛感
所谓主体痛感,张守刚作为一个打工诗人,曾在多处漂泊打工,所以,他对身体与场所的漂移有深切体会,在换各种场地工作时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对主体的追寻与扣问都留在诗歌中,而其中显示出的一些或明朗或隐约的痛感也在诗句中彰显。
张守刚一百多首关于“坦洲”的诗歌,也突出表现了他对工作场所的敏感及对主体的重视。从他在坦洲打工的那一天开始,打工的痛感,打工过程中对主体的茫然与追寻就在心灵中生长。诗人诗歌展开的精神背景是工作场景的转换。他对大量生活细节的观察,都是由这种主体痛感而升华的,近几年,张守刚去过很多地方。这些地方,有的是南方的一个镇,有的是一个城中村,有的则是一条不过千米长的街道。然而就是这些镇、村和街道,它们在他的诗里却充满了主体的一种莫名的痛感。他说:“我必须记住这些地名/坦洲的平坦/南京的艰难/义乌莫名的短暂/这些我流浪的经络/打开我生活的苦难。”(《记住》)。一些空间秩序和有关事物见证了他的个人记忆:多少次我用笨拙的文字/写你/写工业区的密集厂房/写厂房里异乡人的遭遇/他们被工业吞噬的日子/他们被老板占有的青春/还有那些失魂落魄的颠沛流离/更多的是写我自己(张守刚《坦洲》)。它不仅仅是一个村/一个工厂连着一个工厂/这边的机器喧嚣着/一个出租房连着一个出租房/那边方言混杂/从十四围到十五围/从金斗街到又有巷/那么多拗口的广东普通话中/簇拥着更多的外地方言/……我所说的合胜村没有村庄/它的每一条道路/它的每一片钢筋水泥森林/都闪着工业的气息/就连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身上/也能看出工厂的痕迹/(张守刚《在合胜村》)。
细度张守刚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一条明显的线,那就是生存的现场,身体的现场,这些汇集在一起就是一个主体感,场景感,现场感都很强的诗歌。在打工过程中张守刚的身体在不停地“搬迁”和“停留”。但是在他的打工诗歌中,他不自觉地让每个小地方因为他的诗歌而有了一层更深刻的含义。那些地点已经不是简单的地理标志,而是身体的游走,主体情感在漂泊中的痛感,及不断搬迁的路线。在他的另一首诗中,不仅主体感强,疼痛感也能为人感知。“我的名字已经在工卡上注册/我的双手已被流水线操纵/我的身体已被签进合同/我找不到我的头/只看见那双朴素的大脚/每天走在上班和下班的路上∥身边的人都开始认识/工号A058是孤独的湖北人/阿平阿香互相暗恋/在机器轰鸣声中悄悄眉来眼去/住我下床的是我老乡/他每晚加班深夜后/仍辗转难睡/我知道他又在想谁了/1995年在坦洲/我是真正的打工仔了/我在工厂的员工登记表上/看见我名字/虽然它被工号代替/依旧飘着故乡泥土的芳香。”(张守刚《坦洲1995》)在坦洲这样的工业化乡镇,打工者的身体仿佛成了一个容器,把自我这个小小的身体毫不费力地装了进去,就连自我主体的灵魂肉体都消弭在其中,显得小小不言,一种在打工场景中不得已,无奈的感受浮出诗歌的文字层面,让人回味的是他对主体重视而无可奈何的痛感。
二、“异城”与“家乡”的对立
(一)对借居城市的悲痛展示
大批量的外来打工者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他们被城市的人们称为外来者、“农民工”,他们是城市的寻梦者,憧憬着美好的城市生活。他们干最苦最脏的活,拿最低的工资,而且地位低下,苦难的生活扭曲了他们的微笑,使他们在城市中始终不能真正融入,只是一个“借居者”,身心的背离与漂泊使他们只能成为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双重“他者”。“打工的”、“盲流”、“农民工”等都是他们的称谓,在城市追寻着他们淘金梦的过程中,时常被城市的富贵之门挤在门缝甚至于门外,他们经常被侮辱、损害,是一群被边缘化了的“借居者”。
张守刚的打工诗歌以直面打工生活的勇气和责任,描写了打工者作为借居在城市中的人的边缘性,体现了文学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也表达了对打工者借居在城市中的不知所措,精神与肉体的苦难疼痛。如他的《天黑了》:天黑了/她不知道/在工厂密密麻麻的机器声里/她不知道天是怎么黑下来的/这是否预示她的日子/长久地光明/白天和夜晚的灯光/是一样的/谁能将日和夜分得更清/偶尔眨眨眼睛的灯/虚构的白天/在她心里布下了多少阴影/她习惯了机器高分贝的争吵/习惯了锈迹斑斑的乡愁/习惯了主管轻佻的辱骂/可是啊那个刚满月就离开的儿子/六年了还是她的儿子吗/他的白天白吗/他的夜晚黑吗/怀揣着撕心裂肺的思念/她更像那台不堪重负的机器/在白炽灯漫长的/漫长的苍白里/身体里长满了黑。在张守刚的诗歌中,坦洲的工厂是一个监视者,密密麻麻的机器也是嘈杂的,它们与工厂厂主的谩骂一起成为黑暗中不能熟睡的罪魁祸首。而路灯在工厂中这些睡眠不足的打工者眼里成了罪恶之物,它是开工拼命劳作的昭示,是驱赶人死命劳作的象征,甚至比定时的闹钟还让人揪心。工业区,一个简单的词汇,可它在政府眼里是政绩,是GDP的象征,也因此遮蔽了外来打工者灰头土脸的真实生存状况。在这里成了张守刚以表达自己身居异乡,尤其是城市中那种不被接受的疏离感与痛苦感。
(二)对家乡的眷恋
张守刚生活在一个美丽而富有情韵的农村,他曾在几次采访中谈到自己对家乡的热爱。而在艰难的打工岁月里,无助、漂泊、疼痛、白眼等等,一切可以引起内心的孤独感的东西都遇到过,而这些远在异乡留下的痛楚,也更能让他加深对家乡的思念与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