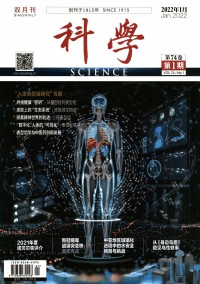科学理论的主要特征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科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科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范文第1篇
当代科学哲学的困境
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自W·塞拉斯算起,至今已有30 余年。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起因来看,它们主要是因为对早期形而上学实在论的不同看法引起,故本文就从形而上学实在论谈起。
所谓形而上学实在论是一种以绝对的真理符合论为基础的科学实在论,其代表人物是W·塞拉斯和澳大利亚哲学家J·J·C·斯马特。按照普特南的概括,该理论的基本主张是“世界是由不依赖于心灵对象的某个确定的总体构成的。只能有一个关于‘世界的存在方式’的正确而完备的描述。真理必须包括语词或思维记号与外部事物或事物集合之间的对应关系”〔1〕。按照该理论, 科学理论及其中心术语应作实在论意义的解释,即严格地按字面意义解读,因为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是对该理论取得解释成功与预测成功的唯一可能解释或最佳解释。
从科学理论及其发展史的角度看,形而上学实在论面临如下问题:第一,即使我们承认科学理论是对客观对象及整个世界真实而又完备的描述,科学理论中的理想实验和理想定律也无法按字面意义进行解读,如牛顿力学的第一定律;第二,从科学发展史看,历史上有许多科学理论曾取得实在论意义上的巨大成功,但最终还是被证伪,显然,成功的理论不一定为真,它所假定的实体不一定实在,或许只是理论的虚构;第三,对科学史上的科学革命,无法作出实在论的解释。
正是由于形而上学实在论无法对科学史上许多事实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一些科学哲学家就走上了反对科学实在论的道路,主张对科学理论作实用主义的或工具论的解释。不过,反实在论固然可以把科学理论归结为科学主体的信念或虚构,却又无法解释虚构的理论何以能导致科学理论的巨大成功,除非把它们说成是宇宙的奇迹。
在形而上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都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的情况下,一些科学哲学家从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基本立场出发,抛弃形而上学实在论中的超验因素,提出了“内在实在论”,其代表人物是H ·普特南。
内在实在论的主要特征是在理论内部承认理论实体的实在性,其理论基础是奎因的“本体论的承诺”理论。内在实在论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客观世界并不超验地独立于我们的认识和理论而存在,而是存在于我们的科学理论及其语言系统内部;第二,语言的意义并不在于指称着所谓“超验实体”,而在于指称着语言系统所涉及的实体,语言的意义是在语言系统内训形成的。普特南明确指出:“当一个记号使用者的特定共同体以特定方式实际运用一个记号时,这个记号就可以在那些使用者的概念构架内同特定的对象相对应,‘对象’不可能不依赖于概念构架而存在。当我们引入不同的描述构架,我们就把世界分割成一些对象,既然对象和记号对于描述来说同样是内部的,我们就可以说出什么对象匹配什么记号。”〔2〕第三, 科学实在论是说明科学成就的必要假定和最佳解释,否则只能用“宇宙的奇迹”来说明,这显然令人难以信服;第四,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不在于同外界对象的对应性,而在于系统内部的融贯性、 一致性, 在于系统内部的“可证实性”(provabilty)或有保障的可断定性(warrartable assertibility)。 第五,科学理论不断进步,不断逼近真理,真理作为人类思想的收敛进程的最终极限而存在于这个无限进展着的思想系统内部。
以普特南为代表的内在论因为主张逼近真理论,所以有时也被称作“逼真实在论”。这种内在实在论尽管由于抛弃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超验性和对应性,避免了一些理论困难,却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第一,内在实在论只在理论系统内部肯定科学实体的实在性,违背了大多数科学家的信念,为形而上学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所反对;第二,理论系统在逻辑上的融贯性并不担保该理论系统是真的,也不担保该理论系统假设的实体在客观世界确有指称。例如,许多错误的理论就可以自圆其说,具有逻辑的真值性,却不具有现实的真理性,没有客观的对应性;第三,假使逼近真理论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在认识论上也无法确认自己是否逼近了真理,何时达到了作为终极目标的真理;第四,从科学史角度看,一个理论的中心术语有指称,并不意味着该理论就会成功,反之,一个理论的成功也不能确保该理论的全部中心术语都有指称,相反,许多并非近似为真、其中心术语不具有指称的理论却经常是成功的,后继理论也并不总是先驱理论的极限;第五,“理论的成功”这一术语的含义比较模糊,科学史上有许多科学理论既可以解释为成功的,在另一方面又可以解释为不成功的。〔3〕
显然,以普特南为代表的内在实在论也没有达到对科学实在论作辩护的目的。相反,由于它的不彻底性,既遭到了反实在论的批判,也遭到了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猛烈抨击。不过,反实在论与形而上学实在论也因前述的理论困难而难以自圆其说。这样,科学哲学的研究就无所适从了。
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哲学家对科学哲学的研究价值提出了怀疑和批判。
在科学哲学内部,首先提出价值怀疑和批判的是A ·范恩(ArthurFine)。80年代初,他在有名的《自然本体论态度》一文中,公开喊出了“实在论已死”〔4〕的口号,宣告“后实在论时代”的到来, 一时间震惊了整个科学哲学界。
范恩是一个后实在论者,他对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都提出了批判,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进行了全面的价值否认。他认为,“如果说科学是一场演出的话,那么它也是一场观念与演员的联袂演出。解释表演的表明书也是表演节目之一,如果对这个或那个的意义或目的抱有疑问和猜测,那么这些疑问和猜测在表演中同样都有它们的地位。而且,剧本永远不会完善,任何过去的对白都不能决定以后的演出,这种演出决不会在总体上受到某种见解和阐释的影响,它要随着自身的发展找出与自身相适应的局部解释。”〔5〕也就是说, 科学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有着自身的内在趋势和动力,任何理论企图根据它以前的状况进行描述和说明,都是不完善的,对科学的发展也是徒劳无益的。
在他看来,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从表面上看有很大区别,其实不然,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最大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把科学真理置于“核心地位”,然后附加上他们各自不同的内容。范恩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这种把科学真理置于核心地位的作法本身是不对的,更不应该附加上什么哲学的说明和解释,应该让科学自己去判断。科学理论有着自身合理的发展程序,哲学家们应当充分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如果科学告诉我,真正存在着分子、原子以及Y/J粒子,甚至夸克, 它们就存在。我信任他们,因而必须承认果真存在着这类事物,以及伴随的特征和关系。”
范恩把这种对待科学家及其理论的“充分信任”态度称作“自然本体论态度”,他认为,随着科学哲学界对待科学理论这种新态度的兴起,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也就应该结束了,科学哲学研究也就进入“后实在论”时代。
无疑,范恩对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批判是有相当的合理之处,他对科学哲学研究价值的怀疑也是值得深思的。不过,他的“后实在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它没有解决“科学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他的潜台词中,科学哲学已没有研究价值,因为它对科学理论的发展没有益处,应当自然消亡,这种态度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其次,他没有解决科学理论的真理性问题,只是让科学自己裁决,包含有“科学中心论”的错误倾向。
罗蒂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大师,他从反基础主义角度看到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局限性,从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价值公开提出了否定。罗蒂认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争论假定了空洞而又令人误解的信念观:“被造成真”。其理论依据实际上是戴维森的这样一种看法,所有的证据就是使我们的句子或理论为真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东西使句子或理论为真:经验、表面磨擦和世界都不能使一个句子为真。按照戴维森的这个理论,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说,像经验采取一定的程式,我们的皮肤烤暖了和宇宙是有限的这样一些事实使相应的句子为真,但最好不要提这些事实,如句子“我的皮肤暖”为真,当且仅当我的皮肤暖,这里没提到任何事实,显然,戴维森·罗蒂所依据的还是塔斯基的真理理论。
在罗蒂看来,无论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都是企图建立一种绝对的科学真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的镜喻认识论基础上的,以为心灵是自然之镜,以为人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是一种典型的表象主义。然而,“事实上,只要停留在表象的思想方式上,你就仍然受着怀疑主义的威胁,因为一个人无法回答是否知道我们的表象符合不符合实在这一问题,除非他诉诸于康德或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6〕。 按照这种看法,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双方都无法对科学理论的实在性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因而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没有意义的。
无疑,他们两人的批判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范恩的理论包含有一定的“科学中心论”倾向,罗蒂的理论则由于达到了否认真理符合论的程度,这些都使得科学哲学家们感到难以接受。于是,许多人便走上了重构科学实在论的道路。
科学实在论的自然主义重构
阿姆斯特朗的“自然主义实在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阿姆斯特朗(D.M.Armstrong )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形而上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早年以倡导“心灵唯物论”而享誉国际哲学论坛,是有名的“澳大利亚唯物主义”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对心脑理论颇有研究,在心智哲学界与斯马特齐名。70年代以后,为建构他的物理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的需要,他转而对共相问题、自然定律问题和可能世界问题进行研究,以他的共相理论为基础形成了完整的“自然主义实在论”体系,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自然主义的重构,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摆脱困境走出了一条希望之路。他的自然主义实在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共相与科学实在论》(上、下册,1978,1980)、《自然定律是什么》(1983)、《共相》(1989)、《可能组合论》(1989)等著作中。
一、阿姆斯特朗首先是一个科学实在论者,与传统的科学实在论不同的是,他的实在论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是自然主义特征。所谓自然主义,在他这里是“物理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一个代称。阿姆斯特朗是一个坚定的、彻底的物理主义者,所以他把“自然主义”明确定义为一种认为“实在仅仅只是一种单一的、全体的时空体系”的学说〔7〕。在他看来, 所谓客观实在就是物理实在,就是具有时空结构的物理实在。凡不具有时空结构的存在都是超自然的、非实在存在,都是由人们的思想虚构出来的。因此,只承认物理实在,否认任何超物理实在,即使人的思想也只是大脑神经中枢的物理运动。这与传统的科学实在论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科学实在论者虽然都探讨物理实在问题,但大多数是不赞同彻底的物理主义的。
其次,它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征。阿姆斯特朗在心灵问题上的唯物主义立场也影响到他的科学实在论,使得他的科学实在论具有唯物主义特征。在《自然定律是什么》一书中,他曾写道,自然定律是“不依赖于试图理解它的心灵而独立存在的”,这一点与内在实在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再次,它具有后验特征。它承认客观实在具有一定的性质、关系和运动定律,至于这些实在究竟有哪些性质、关系和定律,它认为这不是哲学家们通过对谓词的理论分析就可确定的,有关性质和关系(即共相)是否存在的理论,被称为先验实在论,柏拉图的理念说就属于典型的先验实在论,这是阿姆斯特朗的科学实在论所坚决反对的。
最后,它具有可能理论的特征。阿姆斯特朗的科学实在论与前述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内在论不同,它是一种可能的实在论,而非狭隘的现实实在论。这主要表现在它对科学定律、科学理论作出了可能真理的解释。 二、阿姆斯特朗不自觉地突破了当代科学哲学所陷入的困境,把科学实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它实现了从现实实在论向可能实在论的过渡,这既为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立场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也解决了科学哲学存在的价值问题。
如上所述,阿姆斯特朗的科学实在论已不再是现实的实在论,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可能实在论,现实实在论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它对数学真理、逻辑真理所作出的可能真理的解释,为现代科学中的理想实验、理想定律也提供了实在论的解释。该理论虽然是一种可能的实在论,但它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可能实在论,它只承认现实世界的唯一性,因而它并没有违背科学实在论以现实存在说明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反倒为科学实在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科学实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尤为重要的是,他的这一转变也解决了科学哲学存在的价值问题。如前所述,传统的科学实在论企图从科学理论出发来确定相应实体及其规律的存在问题,正如范恩所批判的,这个问题不是从理论上可以解决的,它需要科学的实证研究才能确定。阿姆斯特朗也从后验实在论立场批判了传统实在论的先验性,指出,科学哲学并不能确定世界上究竟存在哪些性质、关系和定律,只能在理论上研究科学理论与科学对象、谓词与共相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以科学已确定的性质、关系为基础对共相理论进行概括,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对高度抽象的现代科学理论作出可能真理的解释,这些问题才是典型的科学哲学问题,它不是科学家经过实证研究可以随便确定的。这样,避免了后现代哲学的责难,既为科学哲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使科学哲学走出误区,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科学哲学的存在价值问题,使科学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它从理论上解决了传统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何以陷入困境的问题,也揭示了后现代哲学所存在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已陷入了困境,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都有自己的致命弱点,谁也不能说服谁,后现代哲学家范恩和罗蒂等人干脆从不同角度否认了科学哲学存在的价值,不过它们并没有解决科学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阿姆斯特朗虽然没有直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的谓词理论却给予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
按照阿姆斯特朗的理论,无论是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内在实在论,还是各种反实在论,都属于一种先验的实在论或反实在论。科学实在论强调理想的或成功的科学理论与其处在的指涉物具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反实在论则依据科学史否认其间具有这种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罗蒂和范恩则认为,人们在认识上无法判断二者之间否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因而干脆否认这种理论的研究价值;罗蒂甚至干脆否认它们有对应关系,走入了另一个极端。
阿姆斯特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介入这种是与否的争论,而是研究日常语言中的谓词与相应的客观共相之间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中。虽然他讨论的只是谓词与共相之间的关系,没有直接讨论科学理论与客观的指涉之间的关系,但因为科学研究可以在逻辑上还原为对事物的性质和关系(即共相)的研究,所以他的谓词理论可以推及整个科学理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按照他的研究,谓词与共相之间既不是处于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也不是没有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处于复杂的多元对应关系之中,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任何对应关系。日常语言涉及的是可观察物体和事件,它的谓词与共相之间况且处于这种复杂的关系之中,现代科学理论涉及的是不可观察或尚未观察的物体与事件,它的谓词与共相之间的关系无疑更为复杂。无论怎样,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包括后现代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都过于简单,都没有揭示出二者之间究竟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是它们的共同缺陷。
再次,他的谓词理论为批判绝对的真理符合论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也为真理符合论洗刷了清白,从而为克服科学哲学的价值危机甚至整个哲学的价值危机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正如澳大利亚另一个自然主义实在论者B·埃利斯所说, 传统的科学实在论所依据的是一种绝对真理符合论,其绝对性表现在要求真理是永恒的、超历史的,独立于人类的语言、思想、判断和价值观念而存在,其对应性表现在要求真理承受者(即观念、思想或理论,与客观对象具有客观的对应关系或符合关系,这种对应关系独立于人类而存在。这种真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就是罗蒂所分析和批判的传统的镜喻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实际上也就是哲学所批判的机械反映论,它不承认或忽视了人在认识过程中所具有的创造作用或主观加工作用。
由于这种真理所要求的镜喻认识论或机械反映论不符合人类的认识过程事实,所以,自18世纪以来,这种类型的认识论早就遭到了许多种类型的哲学家的批判,传统的科学实在论也属于这种类型。但是与以往的批判不同的是,罗蒂等人由批判镜喻认识论走上了反镜喻认识论的道路,由否认心灵是自然之镜,否认真理符合论,否认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追求,走上了否认科学哲学甚至整个哲学的道路。如果说罗蒂所强调的否认哲学的基础主义思维方式和那种追求终极真理、终极确定性的做法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从解构哲学角度所进行的批判则达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
德里达从语言系统的自足性出发,强调语义的内在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从而否认了在语言之外有某种为语言提供意义的基础。他认为,既然一个符号的意义只能通过它与别的符号的区别来确定(这是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那么,在能指及其关系之外就不存在所指,或者说二者在语言系统内部是不可分的。事实上,为了确定一个能指的意义(所指),我们只能举出与这一能指有关的若干其他能指,而它们的所指又牵涉到更多的能指,这一过程是无限的,我们决不可能达到一个本身不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语言就成了一种对立和区别的形式游戏,意义就成了这无始无终的符号游戏的产物。按此推论,哲学理论也就根本不存在任何客观性,真理符合论更是无稽之谈,这样,哲学研究也就成了纯粹的符号游戏,没有任何客观的意义和基础,整个哲学的存在价值也就成了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尤其是他的文本中心主义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他公然宣称:“文本就是一切,文本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这是一种典型的语言学的唯心主义,遭到了人们的猛烈抨击。
总之,后现代哲学家罗蒂和德里达等人从反镜喻认识论和语义的内在性角度达到了对认识的客观性和语义的单一性与外在性的否认,从而达到对真理符合论的否定,以至引起了科学哲学家及整个哲学存在的价值危机。不可否认,后现代哲学已成强弩之末,正在走下坡路,但它们对传统哲学、对真理符合论的批判所造成的影响很大,在许多哲学家的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成了一种心理障碍。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在理论上驳斥,这是一个令哲学家感到十分头痛的事情。
在直觉上,人们感到真理符合论应当是可以成立的,但后现代哲学家对真理符合论的批判也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出在哪里呢?对此,阿姆斯特朗并没有直接的论述,但是他的理论却给了我们极为重要的启示。
在《信念、真理与知识》一书中,阿姆斯特朗明确指出,真理符合论是可以成立的,所谓真理就是主体的信念状态与外在事态的对应或符合。不过,他认为,主体的信念状态与外在事态不是处于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二者经常是处于多元对应关系中,甚至不具有对应关系。他的这种理论又得到了后来的谓词与共相关系的理论证明。
由此可见,后现代哲学对镜喻认识论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们所批判的真理论其实是一种绝对的真理符合论,而非一般的真理符合论。罗蒂、德里达等人的问题在于他们把绝对的真理符合论与一般的真理符合论混为一谈,由反对前者达到对后者的反对。从认识论上讲,心灵固然不可能是绝对的“自然之镜”,但人的认识包含有一定的客体成份,包含有一定的客观性。人的心灵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自然之镜”的作用,换句话说,认识仍然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但不是机械的镜像式的反映,而是能动的反映。所以,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心灵不只是自然之镜,而非“不是自然之镜”。
既然心灵并非完全不是自然之镜,只是不能只归结为自然之镜,那么科学哲学以及整个哲学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的客观意义,并不是纯粹的符号游戏,其存在价值自然还是无法否认的。
显然,阿姆斯特朗通过对问题域的转换和对真理符合论的辩护,已不自觉地突破了当代科学哲学的困境,克服了后现代哲学批判所造成的价值危机,使科学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由于阿姆斯特朗的自然主义实在论具有物理主义的还原论缺陷,所以,本文认为他并没有完全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只是把科学实在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自然主义实在论阶段。
注释:
〔1〕H·普特南:《理性、真理和历史》,中译本,第62页。
〔2〕Brain Ellis: Truth and Objectivity, Blackwell, 1990 p.267—272.
〔3〕参见:Iarry Laudan: A Congutalion of ConvergentRealism, In Jarrett Leplin (eds) Scientifie Realism.1984. p. 218—245.
〔4〕Arthur Fine: The Natural Ontolegical Attituole. seeSeientifie Redism. edited by l.Leplin.p.83
〔5〕Arthur Fine: And Not Antirealism Either,in the sbakyGam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148.
科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足球运动员;体能训练;方法;原则
中图分类号:G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210-01
就目前我国足球运动员的状况来看,在多次与欧美强队的比赛中,仅仅只能坚持65分钟左右的比赛就会出现状态的下滑,而一场足球比赛,要求运动员必须和对手进行90分钟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的对抗,注意加强体能训练方法的研究,对于提高足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技术和战术水平很有意义。
一、足球运动员体能训练的概念
所谓“体能”,是指由人体各器官系统的机能在肌肉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从体能的概念我们可以得出所谓“体能训练”是一种以发展机能潜力和与机能潜力有关的体能要素为目的的大负荷训练,是指人体长时间、高强度、大负荷持续工作能力的训练。它突出对人体器官和机能系统的超负荷适应训练,旨在产生体能和心理适应以达到挖掘机能潜力,提高整体运动能力和培养顽强拼搏精神的目的。体能是影响足球技术水平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体能训练的作用就体现在对技术发挥好坏的控制上。
二、足球运动员专项体能素质特点
(一)针对性
足球运动员专项体能素质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和协调,针对足球专项运动特点,具有特定的要求。
(二)基础性
足球运动员专项体能五项素质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但结合足球运动的专项特点,五项素质中力量素质是足球运动中的首要素质,对其他素质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力量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其他素质的水平。在行进间跑跳过程力量的冲撞与对抗,对比赛争取主动、取得比赛胜利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足球运动员体能训练的特征
(一)先进的科学理论做指导
足球比赛越来越激烈,身体对抗程度越来越高,运动员的体能较以前有很大的提高,这与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推导分不开的。
(二)高科技设备作保证
现代足球体能训练是有科技含量很高的仪器设备和器械作保证的。如运用计算机监控运动员的身体指标的变化,运用新型材料制作合适的运动鞋,高科技含量的饮料和食谱等。
四、足球运动员体能训练的方法
(一)力量训练方法
力量的训练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提高运动员最大力量的训练,二是速度力量训练。训练中用运动员最大力量的80%左右,抓举、挺举、负重高抬腿、卧推等直到身体精疲力竭。
(二)速度训练方法
足球运动中速度主要取决于步频,在足球比赛中步长一般不能发挥出来,基本是步频在起作用,因此足球运动速度训练时,主要采用爆发性的动力练习。
(三)耐力训练方法
由于一场足球比赛的时间一般在1.5~2h,因此,长跑是发展运动员耐力的最好方法之一。在训练中一般采用重复训练法、间歇法、持续法等。
五、足球运动员体能训练的原则
(一)体能提高的刺激——适应理论与原则
所谓训练适应,是指运动员机体在训练负荷和外界环境、自然环境和比赛环境长期刺激的作用下,人体器官和系统所产生的结构与机能改善,这种机能改善能满足激烈比赛所需要的体能能力。
(二)训练量与训练强度统一的理论与原则
传统的训练理论在训练时处理训练量和训练强度这两个最基本的负荷因素时,把量和强度对立起来,注重训练强度时,降低训练量;增大训练量时,显著地降低训练强度,这种理论不利于球类运动员体能水平产生突破性提高。
科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解放思想 认识论 思维规律
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解放思想是实现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之一。一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历史命运是和自身思想解放的状况密切相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上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思想保守和落后的国家。任何落后,首先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落后;任何进步,首先都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进步。
解放思想是历史进步的要求。要解放思想,必须把握解放思想的规律。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三种关系或者说三个问题,对于把握解放思想的规律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观察的客观性和指导理论的正确性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要求,观察的客观性是解放思想的出发点、源泉和动力。解放思想的关键在于突破过时的、不适应当前状况的旧思想的局限。这就要求人们在致思趋向上必须破除“唯本本”、“唯古”、“唯上”等各种错误心态的影响,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面对客观事物。只有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突破自己思想中那些旧观念的屏障,才能把握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着的规律性,从而实现思想变革与现实变化的同步发展。进一步考察,解放思想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克服思想传统所固有的惯性,从而防止教条主义灾难发生的问题。要清醒地看到,思想传统自身是有局限性的。思想、思想传统一旦形成,其形式就有了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相对稳定性,一方面保证了思想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但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惯性和惰性。要解放思想,必须克服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这种惯性和惰性。所以,强调观察的客观性,通过观察的客观性克服思想传统的惯性和惰性,就成了解放思想的第一要求和首要原则。
但是,解放思想又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现代认识论的研究表明,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离不开具体理论的指导。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观察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和完成的。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无价值的观察是根本不存在的。解放思想离开了正确理论的指导,就会陷入盲目性和经验主义的泥潭。思想的解放,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实现。片面强调观察的客观性,同样完成不了思想解放的任务。真正的思想解放,是观察的客观性和科学理论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这也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要求。
我向思维和他向思维的关系
所谓我向思维,是指以主体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过程。他向思维,是指以获得事实真理为目的的思维过程。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考察,解放思想的过程又是我向思维与他向思维相统一的过程。
我向思维作为以维护和促进思维主体存在与发展为价值目标的思维形式,是引发思想解放心理动机的导火线,为思想的解放设置需要和欲望的目标。他向思维作为一种现实性思维过程,判定解放思想的现实情景和可能条件,为思想解放提供环境认知支持。在我向思维与他向思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问题情景与欲望目标不断得到调适,从而推动维护思维主体存在与发展的观念工具――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由此可以看出,解放思想实质上也是一种高级的适应性活动,是人类维持自身与外部环境平衡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工具,它的发生发展一方面要受自己需要的驱动,但另一方面又要受环境的制约。离开人的需要谈思想解放是不可能的,离开环境的制约谈思想解放同样是不现实的。只有将二者辩证地加以思考与运用,才有可能完成思想解放的任务。
作为我向思维和他向思维的结果,思想的解放应当体现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的统一,也即既是“应当”的体现,又是“是”的反映,是“应当”和“是”的统一体。“应当”和“是”是人类活动的两个基本原则。在人的思想解放活动中,自然也应该内在地包含自身活动的基本原则。所谓“是”的原则,是指我们的思想应该和客观事物的规律和性质相一致,不能借解放思想之名,用杜撰的观念虚构、许诺并不存在的东西。所谓“应当”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又要体现自身内在的价值尺度和需要,这是我们行为目的性的外在化。在解放思想的实践中,“是”和“应当”两个基本原则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作为解放思想的主体,一方面必然要承认客观规律的作用,要掌握和服从客观规律,而不是离开或背离客观规律去随心所欲地“解放思想”;另一方面,人又要改变和重建客体,使客体服务于主体的目的和需要。只有真正做到了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实现了“是”和“应当”的完全统一的思想和思想体系,才配称思想解放的美名。
解放思想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是人类智慧的主要特征之一。解放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过程,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
思想解放具有十分明显的时间特征。解放思想的过程是思维创新的过程,是旧观念逐渐消失和新观念不断涌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所表现出的持续性和顺序性,集中表现了解放思想过程在时间形式上的特点。从时间的持续性上来看,思想解放的过程是一维的不可逆的过程。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人、人类的思想总是不断更新、不断进步的。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有时也可能出现局部倒退或停滞不前现象,但总体上来看,思想、思想体系不断更新、不断进步,把握对象世界的范围不断扩大,这是基本的、不可逆转的趋势。由此可见,解放思想、思想解放其实是人类精神发展进步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现象,是人类精神活动内在的、必然的要求。从时间的顺序性上来看,思想解放在时间上具有十分显著的继起性。思想解放的过程在历史上是连贯的,任何时代的先进思想都是前一历史时期思想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思想观念作为传统,虽然给解放思想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阻力,但其迟缓性、稳定性和保守性,却恰好成了解放思想的对象,为解放思想提供了历史的出发点和逻辑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思想传统中的这种惰性和保守性,解放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创新与发展也就失去了自身的规定性,从而变成不可思议的事情。
思想解放还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解放思想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运动过程,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展开的,有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近到远的传播过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解放思想的过程,常常是从个人或社会的一个局部开始的,新思想的社会化要通过人际关系、社会组织机构和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的传播才能实现。新思想的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思想在空间中不断扩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的过程。新思想在空间上的扩散过程,从表面上看是文化交流或文化传播的过程,但在实际的历史运动中,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解放思想,不仅要扬弃自身的思想传统,而且还要敢于和善于接受外来先进的文化观念。
科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范文第4篇
“共性与个性”的问题
“究竟个性重要还是共性重要?什么叫共性?个性是什么?共性的基础是什么?”在课堂上曾经就这些问题做过一些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我有了以下一些认识。
共性的问题,深究起来应该是客观性与真理性的问题,有绝对客观的标准才能用于确定共性的问题。共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可以找到绝对客观的依据和绝对正确的理论(真理)。按照证伪主义的观点,所有的理论都不是绝对正确的,都会在不断的发展中被证伪,绝对真理不能达到,只能无限接近。而索罗斯则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存在偏差(彻底的可错性),人所认识的不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共性意味着绝对的正确,但是由于没有绝对客观的基础,绝对共性难以达到。从这一层次上说,绝对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现实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东西,比如两人对同一类问题有着同样的看法,两个国家选择同样的社会制度,对同样的社会问题选择同样的政策。这种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弱化的共性,因为它们产生的基础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里,只能说个体从各自的认识基础(对事物的理解)出发,得到了相同的观点。由于这种基础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客观的,所以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这种基础的不断客观化,这种相同存在的基础越来越牢固,越来越有意义。
一般的说,我们还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础是我们认为我们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识,比如自然科学理论(尚未被证伪的),社会科学知识(尚未被证伪的),历史、地理事实,道德伦理观等。虽然这些基础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绝对客观,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追求过于苛刻的绝对客观。过于苛刻的追求会让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恐慌之中。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态度应该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共性并非绝对真实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非绝对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
联系到范式的概念,处于同一范式的群体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对价值观、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体系等的认可),而处于不同范式的群体共性基础较弱,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差异和冲突。
个性应该是存在于一定的共性之上的。基于自己获取的一定的事实(不论是不是绝对客观的),每个人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也不能轻易的把一般性的差异和不同理解为个性,要注意追究这种差异产生的基础是什么。真正的个性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性的基础上,这种共性最好是比较严格的共性(接近绝对的共性)。对一些基本的客观事实、理论基础有着完全一样的认识和把握(即有相同的公理性知识),然后根据自身的认识水平,认真思考,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才可以称为个性。
个性的表现可以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次上来看。对于一个国家,只有深刻认识自身的客观基础,才可能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条件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解决本国的问题。虽然在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理论上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但是只有找到自己的个性方面才是真正有用的。随便引用他人的经验,效仿他国的做法,最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对于个人,基于不同的基础,在对待同一问题的时候,就会得出自己特有的结论。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特有的结论越来越有意义。比如很多学术大师,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认识水平非常高,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低层次的),他们会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对一些深入的根本性的问题(高层次的),比如真理观、人生观,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看作个性的方面。个性存在于共性之上,而且共性基础越深刻,所得到的个性越有意义。这里的个性已经没有对与错之分了,只有水平高低之分。这时的个性是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最有意义的,是最值得追求的。我们要尊重个性,在没有深入的思考与理解时,不能轻易的否定别人的个性。
从理论研究上来看,个性存在的基础在于理论研究的核心假设条件。核心假设条件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对象。理论研究最终是解决共性的问题,对理论的认可构成了共性的基础。但是这种解决并不是确定的解决,只是相对的解决。共性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随着理论的证伪度越高,用它作为共性的基础就会越牢固,共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从而导致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个性如果得到越来越普遍的理解和认同,也可能最终转化为共性。个性的层次的提高,最终推动共性层次的提高,推动整体的发展。这也许是每个个体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提高自身层次的意义所在。
我们所要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也许是:首先积累知识,加深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这样可以使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加接近真实(绝对客观),这是获得共性的一面;然后通过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产生自己的信念,这是获得个性的一面。要获得更高层次的个性,就必须不断积累知识,深入思考,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人们总是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然后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选择自己的真理观。这种层次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就如同选择了一种信仰,我们只能给与尊重。
范式的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
库恩从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的理解,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把科学的发展过程分为常规科学时期和非常规科学时期,认为只有在常规科学时期才能导致科学事业的确定性的进步,常规科学时期的特征才是衡量科学的主要特征。库恩最大的思想高度是把科学理论联系到历史、社会背景。范式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代表了一种共同的信念、价值观,对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认可,而不能将其缩小到一个具体的理论上。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应该是研究对象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世界,是物,这一对象最大的特征是不受人的主观意识的直接影响。自然世界具有独立于人的认识的客观运行规律,人类可以通过观察、猜测、实验不断的认识这些规律,但是却难以改变它。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对其加以利用,比如发电、发射飞船、太阳能技术、核工程技术。由于这些规律难以改变,因而按照这些规律往往得到一些确定性的结果,即:条件一定,结果一定。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比如粒子运动的测不准性,不确定性,混沌效应,复杂网络等,似乎破坏了传统的“确定性”,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这些复杂的自然现象仍然有它自身的特有规律,只是过于复杂,一时之间难以把握。而且这些特有的规律不会因为人的参与而改变,一种确定性似乎仍然存在。
自然科学的发展往往有很强的被动性。当一种新的自然现象被人们观察到之后,如果现有的理论难以给出令人满意信服的解释,就必然产生对新理论的需求,或者称旧的理论被证伪。比如原子理论、量子理论的产生。当然也有一些主动的创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有很强的主动性,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来源于自己的思考与兴趣。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非常的直接。这种联系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科研条件、仪器设备、技术条件,这些是由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会带来对技术设备进步的追求,从而导致对科学研究的需求,及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这里也存在某些个人完全处于对真理的追求而从事科学研究,不过仍然需要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才可以延续下去。在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存在更多表现为历史阶段性,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引起范式革命,新的范式的建
立和旧范式的摈弃。同一时期的范式冲突一般仅局限在科学研究本身,与社会活动的联系较少,表现出来时较为缓和,社会影响也较小。科学研究的范式与社会的联系往往在于社会对于科学的利益需求,这种需求受到历史社会情况的影响。
对于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自身。研究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具有一定认识能力的人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加大了人对世界认识的偏差(索罗斯的反射性概念),也改变了社会活动的本身。人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社会活动的把握,也许最需要注重的是对人本身特质的把握。人的本质特征也许是思维与心理活动在社会环境及进程过程中的波动特征。
在经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特别强调了“理性经济人追求最大化的效用”这一前提,这是对“资本主义行为”十分深刻的描述。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的理性其实就是一种逐利的精神,对这种精神的把握,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经济现象。每个人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西方经济理论认为这种追求可以导致整体的帕累托最优,从而鼓励个体对利益的无限追求,而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以保障个体的利益追求的自由为目标。然而又有理论证明,个体的理性可能造成集体的非理性。个体的逐利理性冲动始终引导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动,它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个体对利益的追求导致了资产价格的非理性波动,泡沫的产生,从而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理性预期又始终影响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在这些过程中,对人的特质的理解和把握,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一系列经济现象。
科学理论的主要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进化认识论/跨学科/实证科学
【正文】
一、进化认识论的崛起
“进化认识论”是西方新近出现的一股哲学认识论思潮,通常,我们将福尔迈(G.Vollmer)的《进化认识论》视作进化认识论诞生的标志。[1]福尔迈的书一经问世,便立即在德国许多专业报刊上激起热烈反响并获得高度评价:
“福尔迈的书给进化论、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认识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描述。它尤其阐述了遗传与环境影响的问题,语言问题也在其视野之内。仅仅凭借其对现代认识的清楚细致的描述,该书就很值得一读。”(《物理学报》)
“福尔迈的书为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重新对话作了准备。”(《哲学文献指南》)
“事实上,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不只是对各门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作描述性的总结,而毋宁是系统地重建生物学的认识论。它不仅运用广泛的经验材料作佐证,而且试图发掘这种理论的科学理论基础。由此,正像太阳中心说之对于物理学、进化论之对于物生学、比较行为研究之对于心理学一样,进化认识论也为哲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东西,它因此也标志着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变革……在认识论领域,福尔迈的书对于真正理解人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乃是一次决定性的突破。”(criticon)
在未曾了解进化认识论之前,我们无法知道上述评价是否准确。然而,福尔迈的书在哲学认识论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影响,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低估其价值。
仅仅以德国为例。七十年代初,当福尔迈的书刚刚出现时,进化认识论思想还普遍不为人所知。但是很快,情况便发生了明显变化。下面列举的论著证实了这一点:
1975年,舒里希:《心灵的自然史》(二卷)[2];
1976年,迪特符特:《精神并非从天降我们意识的进化》[3];
1977年,班内施:《精神的起源》;
布律施:《生命途中进化无目标?》;
伦 施:《普遍的世界图景进化与自然哲学》[4];
1979年,里德尔:《认识的生物学理性之种系进化史基础》;[5]
尽管上述著作的倾向性与侧重点各有不同,然而在下面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它们都论述到了人、人的大脑与认知机能的进化的起源。它们皆把人的认识能力置于种系进化的框架加以理解。人们可以根据上述事实断言:自七十年代以来,进化认识论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
二、传统认识论的局限与进化认识论的新尝试
进化认识论的崛起,当不是将生物进化论简单地运用于认识论研究的结果,但是从一开始,它就自觉地将进化的观念同传统认识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忽视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相对峙。
由于传统认识论通常将成年的文化人的认识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势必忽视以下若干方面:同一民族共同体中个体之间的智力差异(天才、智力衰弱者、精神病患者等);人种之间的差异;成长着的儿童的认识能力的发育,亦即认识能力的个体发育方面(今天,它是发展心理学,首先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对象);认识能力在人与动物身上的进化,亦即认识能力的种系发育方面(它恰好是进化认识论的研究课题)。
一般说来,古典认识论研究者虽然偶尔注意到了上述各种差异的个别方面(洛克就曾指出白痴与正常人的理智区别),然而,他们更多地是企图避开经验素材的各种细节,研究所谓“作为认识的认识”、“实质性认识”、“自在认识”(胡塞尔甚至提出了“自在真理理论”)、研究所谓“哲学意义上的认识”,研究个别知识的一般条件等等。这样一种“纯粹”的认识论曾经并始终认为:认识论的分析与反思从原则上应当预先综合专门科学的知识,反之,专门科学的知识就其意义与价值而言,必定在认识方面未能得到事先确证。因此,专门科学知识就不可能修正认识论或对认识论作出建设性的贡献。认识论与专门科学知识相互决定的观点,在传统认识论研究者看来,乃是一个必须抛弃的“循环论证”。
但是,进化认识论却宣称:这样一种循环论证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就完全没有必要固执下述成见,即认为认识论本身能够独立于各专门科学知识而一劳永逸地证实它的陈述。进化认识论认为:认识论的各种陈述与命题只能作为假设而进行演绎,因而一种要求它也至少能够将认识论的陈述作为“虚假”的而加以显现。因此,进化认识论的一个主要关切点,就是展示具体的历史性认识与认识论是怎样互为条件的。正如福尔迈所指出的:“无论如何,对于符合时代潮流的认识论所提出的要求,便是它与经验事实的相关性。进化认识论是满足这种要求的一种尝试。”[6]
这样一来,进化认识论就不能不具有如下主要特征:A.历史性:强调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的起源,认定历史与认识是互为条件的;B.实证性:强调哲学认识论与所有实证科学的相关性,并企图把不同的实证科学与元科学的观念组合成一个有牢固基础的认识论“玛赛克”(mosaik),在这个玛赛克中,认识能力的进化构成了中心;C.跨学科性:这是它同实证科学的相关性所直接决定的。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的副标题就是:“在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与科学理论框架中探究人的天赋认识结构。”
可以认为,进化认识论是对现代科学认识的一次新综合,它不仅力图克服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而且还想把各门自然科学中有价值的成分系统地综合起来。简言之,进化认识论是现代科学的高度分化与重新综合所导致的一种新的收获。正是在综合各门具体科学知识,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进化作系统研究的过程中,进化认识论尝试对经典认识论所要解决的一系列“经典问题”——关于人类认识的起源、效力,范围和界限等问题——重新作出解答。“例如,进化的观点,导致了一种认识立场,我们称之为‘投影认识论’。它特别说明了关于世界的客观认识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的,它虽然不能为许多有争议的哲学问题提供一劳永逸的解答,……但是却采纳了一种立场,或者作出了一种明智的判断。这一点,对于先天综合性问题,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争论,对是否存在认识的界限问题,都是有效的。当然,它也对语言哲学、人类学和科学理论问题也有效。”[7]
三、进化认识论思想的起源及发展
哲学家尼采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历史意义的欠缺是所有哲学家的遗传病……然而,万物皆变,不存在任何永恒的事实,也不存在什么绝对真理。——依此,从现在开始,历史性的哲学思考就迫切需要了,而且与此相关,需要培植谦逊的美德。”
虽然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一切皆变”的思想,在恩培多克勒那里甚至可以发现有关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的思考,然而,有关“人类认识能力不断进化”的假设,只有在十九世纪发展的观念孕育了生物进化论之后,才可能真正确立起来。譬如,我们知道,天赋观念的问题在认识论的历史发展中始终起着关键作用,[8]但是,“我们的认识结构是否具有一种生物学的意义?”这一问题,只有在建立了一种不仅是描述性的(如在亚里士多德与林奈那里),而且是说明性的生物科学之后,才能得到富有意义的讨论(因而这一问题只是在1990年以后才得到讨论)。
主体的认识结构的生物学条件是由下述人物所肯定的:
哲学家:尼采、齐美尔、斯宾塞、皮尔士、巴德文(Baldwin)、F.C.S.席勒、罗素、波普;
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彭加勒、马赫;
心理学家:齐亨(Ziehen)、皮亚杰、坎贝尔、符尔特(Furth)、赖尼贝格(Lenuberg);
生物学家:海克尔、V.贝塔朗菲、伦施、洛伦茨、摩尔、莫诺;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康茨(Katz)。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斯威德茨基(Schwidetzky)
然而,上述人物并非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并实际上采纳进化认识论的基础思想。六十年代之前,只有少数(主要是生物学家)研究了认识能力的进化问题。再者,尽管有些生物学家、遗传学家与行为研究者抓住了这一重要课题,但他们却不想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敞开并力图进入一种元科学的,即认识论的领域之中。相反,哲学家与认识论研究者只是很少或至多只是暗示性地考虑到认识能力的进化问题。西蒙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从进化的立场出发对知觉所作的研究在绝大多数认识论研究者身上没有产生影响,此乃哲学与自然科学持续分裂的许多症状之一。”[9]
诚然,人们可以从上述人物的论著中找到进化认识论思想的闪光,但是,在六十年代之前,人们毕竟未能结合各门具体科学的成就,在跨学科的框架中研究认识能力的进化问题。一般说来,在追溯进化认识论思想的历史起源时,人们都会提到下述人物及其著作:
1955年,V.贝塔朗菲:“论范畴的实在性”[10];
1959年,坎贝尔:“认识过程的比较心理学之方法论启示”[11];
1967年,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
摩尔:“科学与人的实存”[12];
1968年,伦施:“生物哲学”;
乔姆斯基:“语言与心灵”[13];
1969年,符尔特:“皮亚杰与认识”[14];
1970年,莫诺:“偶然与必然”;
西蒙:“从进化的观点来看知觉”[15];
1972年,波普:“客观的知识”[16];
1973年,洛伦茨:“镜子背后”[17];
1974年,坎贝尔“进化认识论”[18]。
可见,进化认识论在哲学中直到最近才得到认真讨论,特别是在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问世之后(参阅第一部分),才明确规定了进化认识论的研究重心,才能把诸多问题放在跨学科的框架中加以解答。对进化认识论的粗略回顾表明:进化认识论虽然与各门实证科学相关,但它却决不限于任何一门专门科学的单一研究。因而我们可以宣称:进化认识论是综合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行为研究、语言学、人类学、逻辑学、哲学认识论与科学理论等学科的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
四、进化认识论与其他学科之关联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断定,我们有必要指明进化认识论所研究的问题与其他学科所蕴含的根本难题之间的相关性。
逻辑学:逻辑学当中最为困难、最为关键的问题不外是:逻辑公理是必然的,抑或仅仅只具备一种心理学上的必然性?亦即:以约定论为基础的逻辑公理站得住脚吗?在回答这类问题时,人们诚然可以认定逻辑规律具有一种假设的性质,但是由此又会导致下面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恰恰按这些公设而不是按照别的公理进行推论呢?进化认识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立足于下述观点之上:我们的认识能力是在不断进化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逻辑公理之所以可以充当一切推论的前提,正是由于它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经受住了自然选择的检验。
转贴于 先验哲学:如果人们接受康德及康德主义者的根本观点,即认为认识主体的天赋认识结构在构造经验与现象世界时起着主导作用,主体的直观形式(时、空间)与思维形式(范畴、原理)使经验成为可能并限制知识的地盘,那么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些天赋结构究竟从何而来?它们为什么在所有主体身上皆同样有效?进化认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康德的先验哲学的立场上不可能弄清主体的认识结构的起源。这主要是因为,遗传进化的观念,就像当时的生物学一样为康德所不熟悉,康德仅仅满足于宣布主体的认识结构是“天赋”的,而这些结构的起源和进化问题却在他的视野之外了。
认识论:人类认识的最大的谜之一乃是:在我们的知识的可靠性与经验印象的偶然破碎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怎样才能填补其间的鸿沟呢?换言之,人与世界所发生的关系是短暂的、有限的与个别的,但是人们为什么却对世界有如此广博可靠的知识呢?要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设定:我们的大脑早就具备着某种“前知识”了,它们不断地组织我们的经验印象并加以说明。按照进化认识论的观点,这些“前知识”是在千百万年的人的持续进化中得到的,并经受住了不断的检验。
行为研究:今天,行为研究给予“本能”、“天赋”这些概念一种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在经验上有意义的解释。人们了解到:不仅感官亦即解剖生理学的结构具有遗传上的条件,而且各种行为模式,包括动物的较高级的能力也可以遗传,它们被当作脑功能而得到理解。但是,行为模式的生理学与生物学的条件也引起了对这类能力作自然的解释的问题。行为科学家K.洛伦茨卓有成效地从进化认识论立场出发给这些问题以自己的回答。
进化论:发展的思想早已普遍化了。从涡旋星系到太阳系,从宏观到微观,从无机界到有机生命界,从动植物界到社会文化领域,皆处在进化之中。因而很自然地会引申出下述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进化的原理用来解释人类认识能力呢?对该问题的回答势必推动进化认识论的形成。
神经生理学:感官与神经生理学指出了中枢神经系统的构造及其功能与认识的基本结构的关联。人们或许会问:神经刺激的传导过程中的"Alles-oder-nichts"(全收或全斥)的规律是否就是我们思维过程中的二元性(排中律)的根源呢?知觉的恒定功能对于客体概念似乎是构造性的;我们的空间直观至少可以部分地通过视知觉的深层结构并通过“内耳”才有可能;我们的时间直观离不开所谓“内在的钟表”……这许多现象都使生理学家感到奇怪,并促使他们去理解这类认识构造机制的合理性,最终从进化认识论的角度给予解释。
语言科学与语言哲学:现代语言学所讨论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语法”,亦即存在着基本的、所有语言共通的结构?这些结构是否可以遗传?乔姆斯基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强调指出:普遍的语法结构与普遍的认识结构是密切相关的,甚至是同一的。但是由此也就要求研究这些结构的历史的起源。
心理学:皮亚杰及其学派详尽地研究了儿童在其发育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阶段。虽然个体的发育秩序并不一定与人类进化的秩序完全相应,因为海克尔的生物遗传学定律——个体发育是种系进化的浓缩的反映——只具有一种启发性意义,然而,对个体的发育秩序的研究却极容易导向遗传学进化论乃至进化认识论。
人类学:与早期人类学、民俗学不同,现代人类学研究的重心已不再是各个民族或民族的特殊性,而是各种文化类型的一般特征,正如在语言学领域一样,人们也可以谈论文化的普遍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就深信:这种共性依赖着隐蔽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渗透在语言、亲属体系、神话与宗教、巫术与艺术等等的结构之中。所有这类结构皆是“天赋”的,并在人类精神的进化中得以塑造。“人类学的结构主义是否为认识的普遍结构寻找到了运用的领域?”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进化认识论的产生。
科学理论:古典哲学所肯定的见解——存在着确定的知识——已遭到现代科学理论的彻底否决。一切科学皆具有假设性!倘若事实上没有什么关于世界的确定无疑的认识,那么,科学理论如此富有成效的原因就必定在于:自然界当中存在着一些恒定(不变)的条件——科学描述接近这些条件,另外,不仅在规范科学中只有经受住不断检验的理论才得以保存,而且人们的经验认识也同样需要经受不断的检验。这种自然选择与淘汰机制与进化认识论的关联是饶有趣味的(进化认识论与波普的“试错论”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进化认识论的问题当然不限于以上所述。但是,仅仅通过对以上各种问题的解答就使得进化认识论具有高度的说明价值与启迪意义。上述各个方面既可以视作由各门具体科学进入进化认识论的通道,也可以当作进化认识论在各个具体领域中的运用。
五、简单评论
最后,我们还想就进化认识论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我们认为,进化认识论的确抓住了传统认识论的一些重大缺陷,诸如缺乏对人类认识能力作发生学的研究,忽视了人与动物在不同进化阶序上的认识能力的差异,忽视了各种文化与人种的区别以及同一文化共同体中个体智力上的差异,因此,当进化认识论尝试克服这些局限性时,它就是对一切自诩为“纯粹认识论”的倾向的反叛,就此而言,它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进化认识论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它与古典哲学(以黑格尔为代表)之抽象地强调认识的历史性不同,因而它坚决反对对认识的历史进化作抽象的思辨演绎,这就使得它站在坚实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
进化认识论的产生对当今中国哲学认识论的变革具有极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第一,进化认识论有助于克服当今中国认识论研究中认识论同自然科学相互分裂的不幸局面;第二,进化认识论的尝试促使我们重估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理论价值。由于对西方各种思潮缺乏全面了解,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偏重于个体发生认识论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并且与进化认识论密切相关,但是进化认识论却提醒人们:海克尔的遗传学基本定理只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对个体认识能力的发生研究不可能取代对认识的种系进化史的研究,进化认识论甚至试图把发生认识论综合进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诚然,由于进化认识论研究还刚刚开始,因此人们还不可期望它具备了完备的科学的形态,也不能认为它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可以指责进化认识论过分偏重了认识的生物学方面而忽视了认识的社会属性,还可以指责它过分强调了认识能力的遗传性而忽视了遗性的可变性,诸如此类,但是总的来说,进化认识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值得我们给予充分重视。
参考文献
[1] Gehard Vollmer:Evolutionaere Erkenntnistheorie,4Baende,Stuttgart Hirzel Verlag 1987.
[2] Schurig,V.:Naturgeschichte des Psychischen,2 Baende,Compus,Frankfurt 1975.
[3] Dithfurth,H.v.:Der Geist fiel nicht vom Himmel,Die Evolution unseres Bewuβtseins,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1976.
[4] Benesch,H.:Der Ursprung des Geistes,dva.Stuttgart 1977(dtv 1980).Bresch,C:Zwischenstufe Leben,Evolution ohne Ziel?Piper,Muenchen/Zuerich(Fischer-TB6802)1977.Rensch,B.:Das universale Weltbild,Evolution und Naturphiosophie(Fischer-TB6340)1977.
[5] Riedl,R.:Biologie der Erkenntnis,Die stammes-geschichtlichen Grundlagen der Vernunft.Parey.Berlin/Hamburg 1979.
[6] Gehard Vollmer:Evolutionaere Erkenntnistheorie,4 Baende,Stuttgart Hirzel Verlag 1987,212.
[7] 参见福尔迈《进化认识论》,舒远招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165页。
[8] 进化认识论所理解的“天赋观念”,指人的认识的先天结构。这样,“天赋观念”就有不同的意义:柏拉图(所有抽象理念);亚里士多德(逻辑公理);F.培根(各种假象);休谟(本能、推论规则);笛卡尔(第一原理);康德(直观形式与认识范畴);赫尔姆霍茨(空间直观);洛伦茨(行为模式、直观形式与范畴);皮亚杰(反应规则、认识结构);荣格(原型);列维-斯特劳斯(文化结构);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等等。
[9] Shimony,A:Perception from an evolutionary point of view,J.Philosophy 68(1971),571.
[10] Bertalanffy,L.v.:An essay on the relativity of categories,Philosophy of Science 22(1955)243-265.
[11] Campbell,D.T.:Methodological suggestions from a comparative psychology of knowlodge processes,Inquiry 2(1959)152-182.
[12] Piaget,J:Biologie und Erkenntn S.Fischer,Franfurt 1974(Biologie et connaissance,1967).
[13] Rensch,B.:Biophilosophie,G.Fischer,Stuttgart 1968.Chomsky,N.:Sprache und Geist,Suhrkamp,Frankfurt 1970(language and mind,1968).
[14] Furth,H.G.:Intelligenz und Erkennen,Suhrkamp,Frankfurt 1972(Piaget and Knowledge,1969).
[15] Monod,J.:Zufall und Notwendigkeit,Piper,Muenchen 1971(Le hasard et La,necēssitē,1970).
[16] Popper,K.R.:Objektive Erkenntnis,Hoffmann und Hamburg 1973(Objective knowledge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