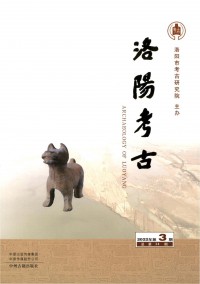考古学的概念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1篇
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
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2篇
地考古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在对于彔观及观测点的调查研究中什么才是重要的,并解释了哪牲数据,地理信息和环境是没有屮的。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以这些信息为基础,从挖掘者、环境学家或者土壤微形态学家的角度解释了过去环境的改变。土壤考古学包含诸多方面的研究内容,介绍如下。
(一)考古记录中的沉积物以及土壤和人产品。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沉积层中古代文物的发现,为地层年代、古景观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变换进程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和参考。从地质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考古学中的文物属于地质学上的一种特殊的沉积物。同样的特性也适用于沉积物,与这桦沉积物是否包括文物或者是具有考古学特性无关,我们需要理解沉积学的概念,这样有利于更好的评估采样点的环境条件,这些对考古学家的报告有帮助
(二)考古i己录中环境的形成研究人类活动和M他自然过程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助于全面的理解考古学的形成和结构。因为考古学中的物质被沉积的沉积物所覆盖,从地质学和沉积学的角度来ft对考古学中解释文物这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体现在考古学中的那些特別的行为活动的特点和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的柄息地。地面景观的分布也影响了报告的能见度。
(三)古环境的重建:人类、气候和古代景观。景观演变、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大尺度的联系是考古学解释中的重要方向。地考古学的一个根本标准是对于史前i己录的过去人类活动、K他有机体的柄息环境相互作)和关系的解释。古生态地质学这个方面是地质考古学的一个子集,这项研究着重解释史前生命和环境景观。
物理和生物环境中地域特性、域和全球性的变化影响着景观环境.然而气候的变化似乎更加直接的影响到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会导致区域性、全球性和地方性地质条件的改变,甚至会影响到大气和水文的流通模式。
在推断过去的环境条件和研究环境条件与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时候,反映沉积土壤过程中的侵蚀、沉积、景观稳定性同样也适用于古生态地质学的研究中。任何这牲学科单独研究只能建立一个有限的地冈图,然而将多学科结合nf以很好的建立一个域的甚至是全球的第四纪气候模式。
(四)原生矿物和资源。产生于希腊语.意思是石头和岩石)来命名那些用岩石和矿物制作的物品。考古挖掘得到的样品通常是丰富的社会物质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文物是是稳定存在于地球表面环境的碎片。大多数的地质学上的原生矿物衍生出无机的残骸许多现在使用的岩石矿物的名称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这里集中了一些地质考古学中在旧世界和新壯界环境中会涉及到的岩石和矿物,包括:角岩、玉髓等矿物、金属、矿石、岩石、建筑材料。
(五)物质起源的研究。起源是考古学中的一个常用术语.涉及到文物波掩埋的明确的地理位置。脱离了起源的相关资料,文物儿乎没有考古学价值。但是,地质考古学中定义的起源与之很不相同。地考古学定义的起源是从从地质-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组成这个文物的原生矿物,它是一个特殊的地质沉积。地考古学中定义的起源并不是指文物发现的地点位置,而是指原也矿物的成分大量的化学、物理、生物参数可以被川来定义向然物质的组成成分。地质学家使用元素追踪、同位素、等方法区別定义矿物和原始组分。
(六>考古记录中的年代估算。对于考古学中的物质和第四纪地层年代的估计是地质考古学中的主要任务。年代学提供了暂时尺寸从人种学、动物行为学等学科中将历史由然科学和地质学丨X:分幵来。理解了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解释过去的数据的重要意义fr:测年技术发展起来之前,我们许平代学测定技术有一定的不足。更好的定义年代在推测人类行为的研究上有关键性作用、实践中选择测定的技术受分析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受到考古学现象年代的约束。这桦限制条件多是根据样品的特征和技术情况制定的。
(七)质图、遥感和调查分类是制图的中心工作。信息的筛选已经是制图和地图内容中的一部分。因此,地图的制作者经常会使用已经分类的信息,分类,然后以点的形式集中反映那些数据并制图,许多种类的地阁可以运W到考古学上。K:中有2种.地形罔和地表地质地阁(有时候叫做第四纪地图mtL质考古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土壤学家制作的地图,建立在多种景观之上。他们的研究领域和地质学儿乎是相同的,但同时有一个增加的重要环节是土壤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打钻或挖掘(因为土壤的变化要比地质学特征和物质变化要迅速)。
二、土壤考古学的研究展望
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美术考古;叙事特征;宗教美术;学科关系
美术考古学的学术概念来自于西方,郭沫若1929年翻译的《美术考古学发展史》首次将其引入到中国。之后,学术界并没有关注学科定义、学科归属等方面的内容。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首次出现“美术考古学”的内容,以后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学》卷中也出现了“美术考古学”的词条。在专著中明确为美术考古学作定义的是刘风君1995年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孙长初2004年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不过,这些学科定义上的工作还只是停留于浅尝辄止的层面上,并没有专门的讨论。
学科定义涉及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时,一个学科性质的准确认识,也需要涉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通过学科之间的关系梳理,可以突出学科的特征,同时也可以完善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在关于美术考古学科关系的认识中,目前学者较多涉及的是与考古学、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图像学等学科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学科的本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的意义等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具体。遗憾的是,在这些关系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的特殊关系。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同之处,而且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上也有相同之处;同时,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上也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提出美术考古的叙事特征和与宗教美术的学科关系作为理论深入的探讨视角。
一、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叙事逻辑
这是一个关于叙事逻辑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如果作为分支学科看待,那么,从叙事逻辑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
首先,美术考古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美术史现象来描述的。“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1](P5)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在美术考古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美术遗迹和遗物转化为美术发展史上的叙事遗存,围绕美术遗迹和遗物展开的研究是关于构图、造型、色彩和主题、风格、艺术进步等美术学科范畴的研究。以我国西域龟兹石窟为例,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它是关于石窟的考古对象;而在美术考古的研究中,它就是石窟艺术的研究对象,研究者是将它作为美术现象来研究的,学者们从龟兹石窟感受到了多元化的艺术影响。比如,希腊艺术的影响:“在龟兹石窟的早期壁画中,人物显得非常突出,与后期山水鸟兽等附加景物的比例较大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受希腊以人为本艺术思想的表现。有些形象与希腊神话传说似乎也有联系,如克孜尔石窟新1窟中的人面兽身的金翅鸟,荷马史诗中也有生动的描写。被学术界所注目的龟兹壁画,显然也是有希腊艺术影响的痕迹。希腊艺术是推崇的,认为这是健康、力量和美的象征。龟兹艺术家接受了这样的审美观点,而且也对小乘佛教的禁欲主义给予了突破。”[2](P137)这些研究内容,已经完全是在美术学的学科范围中进行。其他著名的敦煌石窟艺术、汉画像石墓葬艺术等,在进入美术考古视野后,都是作为美术发展史上的美术现象、叙事风格和艺术成就来研究的。
其次,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的研究趋势。目前学术界中,不论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考古学学科还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美术学学科,学者们都希望美术考古拥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这种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要求。中国传统的田野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标型学、器物形态学),这两种方法都借鉴于自然科学的手段和理念。自然科学是以物为研究标的的特性,这一基本点决定了田野考古学只能是“见物不见人”。美术考古如被作为田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虽然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研究中的特殊对象——美术作品,但是它从属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决定了其在方法论上必然是以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为主要研究手段,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过程的客观性,禁止运用描述性语言,从而忽视了这种特殊人工制品所具有的主观性内容。有学者认为:“许多考古人不做研究,将考古发掘报告当作研究成果,那是不妥的。任何学科都离不开研究,否则就不是什么学问了。而且,考古界禁止用描述性语言也是错误的。”[3]在强调客观性的制约下,美术考古归于考古学缺少可操作性。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考古学前辈和权威性的观点中得到旁证。比如,前辈夏鼐认为:“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由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又由于作为遗迹和遗物的各种美术品多是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所以美术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4](P9)目前,“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已经不能覆盖美术考古的全部研究成果,相反,“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国目前美术考古取得的学科影响主要是在美术学领域。其一,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美术史的研究内容。在美术考古发挥影响之前,我国美术史的研究依赖于传世的美术作品和相关文献,这些作品和文献在传播过程中指导创作,形成流派,后人由此而产生的理解也直接推动美术理论的发展。但是,在美术考古学科形成后,情况发生变化,大量的美术考古作品进入美术史的研究领域,不仅增加了传统美术的作品数量,而且美术史的理论认识也得到了普遍提高。在目前流行的美术史教科书中,美术考古的内容已经进入到了所有朝代美术发展的认识中。其二,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美术史研究模式。对于传世美术作品的研究,美术史更多的是依靠传统的文化研究模式,比如知人论世的考释,比如师承关系的梳理,等等。对于美术考古作品,考古学的地层学方法和类型学方法则被学者们热情地引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也被学者们广泛地运用,目前甚为流行的图像学、叙事学等,皆为美术考古研究常用方法。其三,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影响。这一点最好理解,美术考古将美术史的研究进入到石窟艺术、墓葬艺术、岩画艺术等考古遗存的领域,美术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许多文化遗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术史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美术考古不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作为美术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我们提出一个求教大方的表述:美术考古是一门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在美术史层面上展开研究活动的美术学分支学科。
二、与宗教美术相关的叙事特征
这是一个从叙事特征角度讨论学科关系的问题。
首先,从逻辑关系上对叙事特征的讨论。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在概念上存在的关系是交叉关系。这样的关系与全同关系不同,具有反自返性、对称性和非传递性的性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学术界并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实际上,在它们的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宗教信仰有关,同时,它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通过考古手段获得的,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从叙事特征看,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为宗教信仰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古建筑遗址、被掩埋的艺术作品等。这两部分作品中,从目前的研究条件看,宗教信仰原因的考古对象占有着极大的比重。这一现象,也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延承有关。自三代开始,人们就将与自然、先人有关的祭祀活动和与自己有关的埋葬活动作为了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以后的各类宗教思想发展不仅没有降低这项活动的重要性,而且还从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不灭和生命的转化等方面予以丰富和细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宗教信仰深入于艺术活动之中,留下了丰富的美术作品。
宗教美术的研究对象也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第二部分则是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而保存、流传的传世作品。与美术考古一样,宗教美术的第一部分占有极大的比重,而且第一部分的作品与美术考古的第一部分作品完全重叠,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这些美术作品都是通过考古的手段而获得,这就使得这两门学科有了更加紧密的学科关系,我们因此而可以提出这样的关系命题:对于这部分作品,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是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活动。“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是主项,“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活动”是谓项,主项之间的关系是对称性的性质。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所具有的对称性关系,虽然是有条件的,不能覆盖两学科的所有内容,但是考虑到这部分重叠的内容具有很大的比重,而且这部分作品中优秀作品的比重也很大,所以这样的对称性关系使得两学科的共同性有了特别的意义。在建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关系命题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许多共同性的方面来深入思考它们的学科性质了。
其次,关于美术作品埋葬方式的叙事认识。
在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无疑问是美术作品完成叙事的重要内容,可是这一点目前没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研究论文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常常是侧重于从作品的发现角度来认识的,即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则认为,作品的埋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这是一个关于作品本体的角度。当然,作品埋葬和作品发现都是属于作品存在的范畴,作品发现也已经反映了作品的部分埋葬情况,但是埋葬的角度是一种直接性的观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收集和反映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就作品的流传而言,作品的埋葬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原作品所有人的主观愿望可以得到最大可能的实现;而作品的发现,则可能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其中的一些环节是原作品所有人不可预期、不可掌握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与原作品所有人的愿望是没有关系的,极端情况下还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作品的发现不考虑这些因素,那么认识原作品所有人的创作就有了一个信息损失、甚至歪曲的可能。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汉墓壁画,墓主人将反映自己社会地位、日常生活和对另一个世界想象的绘画作品置于自己的墓室之中,他的目的是表现自己的长生思想。对他而言,长生思想的表现是一个长生行为,是对长生信仰的体验,同时,这一定是一个个人的行动。他绝对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现象:考古学的发掘活动,发现了他的行为或研究了他的思想。也就是说,墓主人墓葬绘画行为的目的只是后人理解中的一部分内容,另外的内容为后人所加。墓主人的内容和后人的内容之间的叙事结构完成,在新信息得到的同时,也可能会因为叙事结构的转化而损失了一定的信息,比如误解,比如疏忽。所以,作品的埋葬与作品的发现,是一个存在一定意义差别的不同角度。
作品的埋葬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品为什么存在?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作品,其创作是在信仰的指导下完成的。作品的所有人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个人的魂魄并不随着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结束,而是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所以他要为那个世界的存在而作这个世界的准备,因此他的行为就涉及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研究对象——具有宗教色彩的美术作品。这样的美术作品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创作而直接参加宗教行为的作品,如石窟中的造像和壁画;一种是之前创作而间接参加宗教行为的作品,如墓葬艺术中的一些帛画、雕塑、冥器等作品。这两类作品就创作过程而言,有着不同的创作性质,第一种是宗教行为性质的创作,完全是在宗教信仰的指导下进行,为宗教体验服务是它的唯一目的;第二种是世俗行为性质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并不一定接受宗教信仰的指导。这两类作品能够有叙事上的同构,是因为埋葬活动提供了条件,为宗教信仰服务是作品完成整个叙事过程之后才得到的创作意义。这两类作品在考古学的活动中,都是以历史遗存的形式出现,就作品的发现而言,它们是以相同形式的遗存出现的,它们的主题也都是为墓主人或供养人的宗教信仰服务的创作行为。但是,宗教行为的创作行为和世俗行为的创作行为是存在着区别的,世俗行为成为宗教行为必须有一个结构演变的过程。
从逻辑关系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有着部分对称性的关系,其意义是肯定两学科的共同性,从共同性的角度出发认识它们的优秀作品;而从埋葬角度出发,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被考虑的则是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当然,这个差异性是部分的,而且是在共同性的前提下展开的,目的是从两学科的关系层面上思考学科性质。但是,如果我们在了解、分析埋葬美术作品时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学科之间的差异,那我们的认识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错误的。
再次,关于叙事意义的理论认识。
叙事作品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系统。[5]通过学科逻辑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认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通过作品埋葬角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作品存在的角度认识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两学科的结合思考还可以在操作层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论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认识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学科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两者结合思考后的指导意义,即强调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所具有的叙事意义。
其一,叙事主题的单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中,叙事的结构往往都显得非常宏大,几乎所有的构图都试图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间和世外,这是宗教信仰指导的必然结果。如我国最早的黄帝图像就出现在山东武梁祠的画像石中,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孔子等先秦圣人,他们之上就是西王母的图像,墓主人用这样的构图说明西王母对世界的控制和自己对西王母无所不及的期待。无所不及是一个多么大的结构,墓主人能够在有限的画面上和有限的手段等条件下完成这样大的结构吗?显然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要求,但是宗教美术可以很轻松和很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叙事主题的单一,或叙事主题的集中。在所有的宗教美术作品中,作品的主体都是至上神或主宰这个世界的神灵。在构图上,这个主体占据着作品的最重要位置和最大的比例,甚至是唯一的形象,比如我国四川和北方河南、山西的一些大型石窟中,常常主体就是一尊佛的造像。以单一的形象反映丰富的世界,在世俗美术创作中是非常难办的,似乎有悖于一般的艺术创作规律,但是这在宗教美术创作中却是普遍的现象。在宗教美术创作中,至上神与其所代表的世界表现的是终极关怀,艺术审美感来自信仰经验。如此,净化的世界也同时产生了简化的世界,叙事主题自然就显得单一,显得集中。当美术考古的作品涉及宗教美术的范畴时,相关的叙事同样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进行的,丰富的世界可以作为创作的背景存在,但就作品本身而言,其主题是单一的,是集中的。宗教美术作品的叙事主题单一、集中的特点,可以充分反映、同时也充分论证了宗教行为的性质和影响的存在。
其二,情节的真实性。
宗教美术是描写另一个世界的,与现实世界对照,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宗教美术作品能够存在的理由却是来自于宗教经验,即这些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现了情节的真实性。情节的真实性当然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宗教经验对这样的真实是支持的态度。宗教美术作品的构图体现着这样的“真实性”。在我国神话传说中,女娲是一个大神,有着极高的地位。我国早期的历史书籍中,几乎都有关于女娲的文字记载,在各地的民间传说中,女娲也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料。关于女娲神话的发展,学者们的研究是将女娲的神格分为始祖母神格和文化英雄神格两大类。为什么女娲在这两方面作出贡献?因为她是女神,这一点充分表现在艺术形象中。她能够如现实世界中的女性一样造人,而且她有着许多神奇的造人方法。主要有三种造人法,即化生人类、抟土作人和孕育人类[6](P29)。就神话的流传而言,女娲的这些情节都是真实的。汉画像石中,女娲所拥有的与生育有关的情节也是真实的。在汉画像石里,女娲的形象一般被描写为人首蛇身状,有着非常浓郁的原始气息。因为在原始社会,女性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生育,蛇是卵生动物,生育力特别强,女娲蛇身就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寄托。在原始神话中,蛇的生育本领往往要被移植于造物的神话里,许多造物的大神因为本领大、功劳大而与蛇产生联系。在造物的神话人物中,烛龙是个大神,他就有着蛇的形态。
因此,在宗教美术和美术考古的作品中,情节的真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特征,这一点与世俗美术有相似的地方,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宗教美术并不是依靠写实来达到真实的,也不一定是依靠夸张来达到真实的,更多的依靠联想,依靠联想来获得情节的真实,联系最直接的说明,就是物象的符号化。
其三,物象的符号化。
在宗教美术作品中,物象符号化的手法无处不在,每一个物象都拒绝随意的理解,必须从某一个已经存在的特定的概念来入手,从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义。一是因为宗教美术有着强大的象征体系,天边的云气是象征仙界的符号,飞翔的鸟是象征使者的符号,地面行走的神兽是象征宗教行为某个过程的符号,每一个物象都与象征体系有着对应的关系,有了符号化的运用,物象的意义不仅更加明确,而且接受也有了流畅的表达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宗教美术所包含的宗教仪式内容,仪式支持宗教美术,但对艺术创作有约束的要求,这个要求并不是生硬的,而是通过符号的联系来实现,这样的联系在宗教的象征体系中就产生了艺术的联想。当然,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世俗与宗教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象征体系,所以宗教物象与世俗物象是有区别的。比如蟾蜍,在宗教的象征体系中,它是长生的物象,使信徒联想到与长生有关的美好事物,于是蟾蜍就可以与嫦娥有了联系。特别是在汉代,画像石中有将嫦娥与蟾蜍联系在一起构图的现象,而且这种图像非常普遍。但是在世俗世界,因为形象的问题,嫦娥和蟾蜍是被分开的。如白居易的《虾蟆》诗,不仅对嫦娥与蟾蜍作了区别,而且还特别提出害怕将虾蟆拿来联系嫦娥,认为这样会玷污嫦娥的美名:“常恐飞上天,跳远随妲娥。往往蚀明月,谴君无奈何!”因此,物象的符号化不仅反映出宗教美术的叙事路径,而且也可以很好地说明宗教美术区别于世俗美术的艺术特征。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就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言,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两门学科的共性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学科性质上寻找到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上所存在的相同叙事结构,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学科定位。
[参考文献]
[1]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阮荣春,主编.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
[3]朱浒.全国首届艺术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国美术研究,2007,(3).
[4]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众考古 海昏侯墓 新闻 发掘
公众考古,也称为“公共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尚未对此有一个清楚的定义。
高蒙河教授在《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中认为公众考古是“意在通过向公众阐释考古、进行考古教育,来动员他们参与到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中。”姚伟钧、张国超则在《中国公众考古模式概论》中提出“公众考古是考古学的大众化”,而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也提出公众考古是考古学的社会化。简单地讲就是考古的大众化,核心思想是对考古相关者进行交流与解释。
中国考古学界对于公众考古学的研究起步早、成绩显著。原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苏秉琦老先生就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独到观点。然而,苏先生的公众考古研究基本上还是集中在理论的研究上,并未付诸专业实践。
一、新闻发掘的缺位和考古的“被娱乐化”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大量工程建设打破古人遗迹,使得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了黄金时代。与此同时,有关考古新闻的报道也日益集中。由于考古新闻的报道重在将考古发掘成果传播给社会公众,故而属于公众考古学的学科范畴。同时,新闻报道者对于新闻源的报道,是对考古信息的第二次“发掘”。因此,我们将与公众关系密切的考古新闻报道称之为“公众考古的新闻发掘”。
2009年末的“曹操墓事件”更是对考古学界敲响了警钟。由于学术界对于新闻渠道的不重视,导致了网络上甚至出现《曹操墓发现小孩尸骨,专家说是小时候曹操?》等一类假新闻,对考古学科的严肃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使得舆论场上产生“公众不明就里、考古学者百口莫辩”的窘境。
该事例也说明了社会公众与考古学界一直横亘着一道“知识鸿沟”。美国学者蒂奇诺曾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过一种名为“知沟”的理论,该理论主张精英和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知沟,并强调这个知沟是由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所造成的。而缩小知沟的解决方案也必须依靠大众媒介。
由此看来,利用公众考古的新闻发掘来向社会公众普及考古学常识显得尤为必要。唯有此,才能使考古工作者发现历史之时,历史得以公之于众。在深化考古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要通过文物观浸价值观,让决策者和公众形成对于考古资源的忧患意识。
当人们正在在如何把控公众考古新闻发掘的信息源而犯难之时,2015年末的“南昌海昏侯墓”以其开放的新闻公开机制、多元的新闻渠道、严谨的信息整合流程震惊了新闻业界和考古学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若考古学界还固守在学术的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而不愿意借助媒体为公众解释历史,那么考古学这门严肃的科学必将难以逃脱被娱乐的命运。
因此我们应该系统地对南昌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公众考古中合理运用媒介技巧、海昏侯墓报道对于公众考古新闻发掘的启示。
二、公众考古视域下的海昏侯墓新闻发掘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的南昌西汉海昏候墓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内涵最丰富、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西汉侯国聚落遗址。同时,经历过列侯、诸侯王、皇帝的角色更迭的墓主刘贺人生经历更是颇为独特。南昌海昏侯墓园由七座陪葬墓、两座主墓室、一座陪葬坑等部分构成,是西汉列侯丧葬制度的典型案例。
从2015年末至今,喜欢看新闻的朋友怕是都能感受到大众传媒对于南昌海昏侯墓的巨大热情。全盛期间,央新闻频道基本每天都把黄金时间留给了南昌海昏侯墓发掘工作的报道。
众所周知,南昌海昏侯墓自去年11月公布阶段成果以来,南昌海昏侯墓一直是文化圈的热词,独特的传播案例也使其堪称公众考古的典范。而下面,我将依据部分网络搜索数据对南昌海昏侯墓的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进行量化分析,以此来了解南昌海昏侯墓在不同时段媒体的报道重点、总体呈现的报道特点、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实际效果等具体情况。(全文数据基于搜索引擎“百度”,样本量截至2016年10月17日上午8点)
笔者首先利用百度搜索引擎统计海昏侯墓关键词的搜索次数。输入“海昏侯”这个关键词,最后得出的结果是:数据库中涉及海昏侯的搜索次数有将近四百万次之多。然后,笔者为了了解海昏侯墓各大新闻报道重点的具体流量情况,专门选取了海昏侯墓马蹄金、汉废帝刘贺、最早的火锅、孔子漆屏风、海昏侯墓黄金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海昏侯墓马蹄金为190万、汉废帝刘贺的相关结果为28万、最早的火锅为101万次、孔子漆屏风仅为3890次。
我们将通过搜索其它热门关键词进行新闻报道密度的比较。首先,搜索的范围还是在百度搜索引擎之中,搜索条件限定为“关键词位于全文中”,搜索得到“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有39万篇,搜索得到“曹操墓”的搜索结果有7620篇,“石渠宝笈展”有1980篇。我们再进一步把海昏侯墓的上一级概念“考古”作为检索对象,也仅仅得到了31万篇报道。而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政策热点’限购房政策’的新闻报道也仅为17万篇。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海昏侯墓新闻报道的集中程度远远高于文博界的其它新闻事件。比如曹操墓和石渠宝笈都是前期很火的文博行业新闻事件,但是它们的报道流量却连一万都不到,但是“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却有惊人的39万篇。
第二,海昏侯墓新闻报道的集中程度甚至可以比肩全国性的政策热点。“限购房政策”是一项关乎全社会公众利益的公共性民生新闻事件,其关注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海昏侯墓”却能超过这个政策热点,足可以说明海昏侯墓事件完全有能力跻身舆论场上的社会热点事件。
第三,公众在海昏侯墓报道中对于金器的热情远胜于其它。在海昏侯字概念关键词的搜索中,海昏侯墓马蹄金为190万、汉废帝刘贺的相关结果为28万、最早的火锅为101万次、孔子漆屏风为3890次。在拜金主义的浪潮之下,社会公众对于黄金的热情都盖过了墓主人自身的传奇人生的社会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三、海昏侯墓新闻发掘的现实启示
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不仅是一场世界遗产级的文保行动,更是一场各大新闻媒体的“大会师”。各级各类媒体的新闻记者齐聚豫章,有的在考古现场周围的宾馆安营扎寨,有的与考古工作者同吃同住,一起用新闻讲述着这段“过去的故事”。
在这场新闻追逐中,海昏侯墓考古团队以其严格的新闻机制、稳健的新闻把关能力应对媒体。虽然媒体蜂拥而至,但是考古发掘机构并没有口不择言,反而是在该沉得住气的时候越发稳健。
在南昌海昏侯墓的新闻报道中,考古团队为了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可谓是慎之又慎。盖棺定论的结论都是一直等到2016年2月末开完学术研讨会才正式确定。而新闻源的把控更是一直严守到了2016年3月2日在北京举行新闻会上。
确定墓主身份的关键证据“刘贺”印章早在2016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一直等到了2016年2月末_完学术研讨会才正式确定墓主身份。另外,其实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工作早在2011年业已开始,但是领队杨军等人把所有新闻线索都保留起来,等到2015年主棺发掘的时候一起公布,从而保证了海昏侯墓每天都有新闻曝光点,增加了公众对于南昌海昏侯墓的认知。
有效的宣传手段使这次考古发掘通过新闻媒体之手成了一场公众“追剧”的典型报道,并对日后深入挖掘“考古IP链”下的相关新闻报道产生了以下几点借鉴意义。
首先,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实现学科融合。正是由于对于新闻的稳健把控,才使得南昌海昏侯墓的报道密度如此集中。同时,由于考古学界与新闻业界存在的学科隔阂,记者因缺乏考古知识对某些新闻线索产生误读、考古学者因不熟悉新闻采写流程而惹出闹剧的现象时有发生。因而,从事公众考古新闻报道报道之时,将考古学知识和新闻学科理论进行整合显得很有必要。
其次,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客观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的职责就是客观地把新近发生之事实传播给公众。公众考古新闻涉及到的是我们祖先的文化信息,在公众考古新闻报道中做到客观真实,既是对先人的崇敬,更是对于历史的尊重。海昏侯墓中严格的新闻制度正是遵循该原则的具体体现。
最后,公众考古新闻发掘要以人为本。张忠培先生曾经说过:“考古工作者就是以物论史,透物见人。”这句话在新闻界中同样适用。一个完整的故事必定要具备新闻六要素,也就是“5W1H”,即:谁(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为何(Why)、过程如何(How)。而在这“5W1H”中,谁(Who)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海昏侯墓的报道中,“刘贺”一直是新闻媒体竞相追逐的热词。毕竟,没有人物,就没有笔尖的那一抹厚重,也不会有新闻价值的深度。
参考文献:
[1]杨军、徐长青:《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2]郭云菁:《公众考古传播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学位论文
[3]孙波:《新传媒时代的“公众考古学”与危机公关》,《中国文物报》2012-08-31-005.
[4]陈洪波:《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中国文物报》2005-08-12-007.
[5]付鑫鑫:《海昏侯墓具备申报世遗条件》,《文汇报》2015-11-16-005
[6]吴运亮、郭潇雅:《公共考古拓宽考古学社会职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4-09-A01
[7]高蒙河、郑好:《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
[8]高蒙河、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
[9]徐长青:《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撼世价值》,《江西日报》2016-1-22-C02
[10]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考古学的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相对年代,绝对年代,参照点
中图分类号:K85;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1-0039-04
On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of Archeology
ZHAI Shengli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relative chronology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is not the precision of time but the reference points. The reference point of absolute chronology may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specifically known; however, the reference point of relative chronology must be a time point or time zone which is not known by now.
Keywords: relative chronology,absolute chronology, reference points
考古学是一门关于时间的科学。在整理考古发掘资料时,最基本的环节就是对考古遗物和遗迹的年代加以判定,这就是考古年代学。年代学的研究涉及一对基本概念:“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对于这对看似简单的概念,学者在理解和使用的过程中却多有分歧。笔者不揣简陋,尝试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基本含义
对于“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基本含义,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整齐划一的定义。学者们对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争议,多体现在适用范围与精确度方面,主要观点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将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研究限制在考古学范畴之内,他们认为相对年代是考古学研究的一项特定内容。有学者认为[1]:相对年代是指各种遗迹和遗物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绝对年代是指遗物和遗迹形成时距今的具体年代。这也是多数考古学家的观点。
考古学上,人类的历史遗存按形制分类,形制相近或相同的遗存归为一类,以某一方面的特征为标准来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然后按照型式差异程度的递增或递减序列,排出一个“系列”,这个“系列”便代表该类遗存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各遗存在这个系列中的位置,就表明了它们的相对年代。“相对年代”的研究就是通过考察多个考古遗存在演变系列中的位置,来判定其相对早晚关系。
另一些学者则将相对年代的研究推广至历史学范畴。《辞海》认为:“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具体年代,称为绝对年代。不能确定具体年代而仅能比较和推定先后时序者,称为相对年代。”[2]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再限定相对年代的研究对象,他们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都是关于时间的科学。无论对于考古遗存还是历史人物、事件,如果只能比较先后序列而不能确定具体的年代,都可以称为相对年代。
刘华夏先生认为:“绝对年代是以现今或与现今距离可知的定点为起点,用公认的时间单位(如一年、一世纪等)计算的年代。相对年代则不同,其既无起点,亦非用时间单位来计算,仅仅指甲早于乙而已。”[3]刘先生对绝对年代的界定是比较中肯的,但其关于相对年代的看法却存在问题。遗存之间既然有早晚关系,那么至少是互为时间起点的。
也有学者从时间轴方面对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作出定义。曹书杰先生认为:“绝对年代是将历史事件置于时间轴上(例如公元前1975年)或时间区内(例如12 000~10 000年)的纪年法,年代可以直接测定并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所谓相对年代纪年法,就是把一段时间、事件或对象安插到已经确定好的时序之内的纪年法。”[4]这种说法较为形象,但其对于相对年代的界定却较为模糊。
以上几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然而又都存在不足。笔者认为二者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形式。从狭义方面:相对年代是指一系列考古遗物和遗迹的相对早晚关系;绝对年代是指某一个或某一系列考古遗物和遗迹距今的年代数据。从广义方面:相对年代是指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遗存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绝对年代是指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或者遗存之间距今的年代数据。
二 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相关论述中,不少学者都曾涉及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多将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的区别理解为时间精确度的差异。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不妥之处。
1.二者的命名与时间精确度无关
为了说明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的联系和区别,有学者曾经提出“具体年代”“精确年代”等概念。有人认为绝对年代就是具体年代,相对年代就是大致年代。曹书杰先生将历史年代分为绝对年代、具体年代、概括年代、稳定年代、约定年代等几种类型。他认为绝对年代是指那些已精确到某一具体年份的月和日的时间结论,而且是确定不疑的,也可称为精确年代[5]。
马承源先生提出青铜器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的区别在于时间幅度的不同。马先生认为:“绝对年代是青铜器铸造的年代,或非常接近于铸造的年代。相对年代是指用一定的时间幅度彼此对比而借以决定的期限。”[6]马先生所谓的绝对年代是指青铜器铸作于某一时间点,而相对年代则是指对比研究以后所能确定的时间段或时间区。二者精确度有所区别。
林先生曾说:“考古发掘中的层位,只能用以判断遗物的相对早晚关系,对遗物的具体年代则只能提供大致的估计。”所谓“相对早晚关系”无疑是指相对年代,那么“具体年代”应该是指遗物的绝对年代[7]。彭裕商先生则认为:“根据确切年代或其他有关内容的铭文资料和考古学地层关系,就可以知道某个型式的器物的绝对或大致的年代。”[8]此处的“绝对的年代”相当于确切年代,而“大致的年代”应该指相对年代。
以上专家所论虽不无道理,却有不妥之处。例如:“高卢人攻占罗马是在羊河战役后19年,留克特拉战役前16年,与斯巴达人批准同波斯国王签定的安达尔西达斯和约同年。”这些年代是通过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相互对比系联而得出的,显然属于相对年代,然而它们都是非常具体的数据。人类旧石器时代开始于三百万年前,虽然三百万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数据,但仍然属于绝对年代。所以笔者认为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二者精确度的高低。
2.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所选参照点不同
相对年代之“相对”,在于必须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考古遗存或历史事件相互比较才能得出其先后关系。而绝对年代之“绝对”应指某遗存或事件可以与今天的纪年系统产生关联,进而能表明它与今天的时间距离。正如李雅书先生所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直接的纪年方法只能是相对纪年:即把要记的事件同前后已知的著名事件联系起来,用它们之间的距离来标明该事件发生的时间。例如:“特洛伊陷落后六十年,彼阿提亚人定住于现在的彼阿提亚。再过二十年,多利亚人和赫丘利的子孙们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9]这里用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为纪年起点,显然是一种相对纪年。
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使用的纪年方法主要有帝王纪年、干支纪年、年号纪年、大事纪年等几种形式。帝王纪年以某一位帝王即位时间为起点,干支纪年以天干、地支组合为周期循环运转计算,年号纪年以某一帝王的年号为纪年起点,而大事纪年则以过去某著名事件为起点计算年数。这些纪年起点都是主观选择的结果,先民们将后来的事件与主观选择的起点相联系,所得即为相对年代。现在通行的西方公元纪年,以耶稣诞生为纪年起点,从科学上并无道理可言。其实公元纪年与其他纪年方式一样也都属于相对纪年,那么可以说,包括公元纪年在内的一切年代都可以被称为相对年代。
另一方面,一切被使用的纪年在当时人看来肯定都属于绝对纪年。因为被当时人选作参照点的事件或者时间在他们看来肯定是明确无疑的,这是该事件或者时间被当做参照点的前提。今天也是如此,公元元年即耶稣诞生的时间,这一点必须是公认的。假如由于历史的变迁,今天的人已经无法了解某种纪年的使用情况,历史上的绝对纪年就会变成今天的相对纪年。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进行年代学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历史遗存或者事件的相对年代,然后将相对年代转变为与今天相关联的绝对年代。
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都是将遗存或历史事件置于历史发展的时间轴之上,其区别在于参照点的不同。绝对年代以当下或其他能够与当下产生关联的时间为参照点,目的在于了解某一遗存或事件与当下的时间关系。而相对年代则可以用当下以外的未知时间为参照点,将数个遗存或事件联系起来,以标明它们的先后关系。每一个记录下来的年代,只有明确它们在今天的纪年体系中所占的位置,这个年代才有意义。也就是必须把相对年代换算成今天通用的纪年体系的年代,相对年代才能起到纪年的作用。这样,这个相对年代即变成了绝对年代。作为判定绝对年代的纪元,“公元”显然并非唯一可能的起点。公元起点是约定俗成的,因此最终推断出来的绝对年代可能有好几种表示方式[10]。
在进行考古学断代时,考古学家经常将遗存与某一王世年代进行拟合。彭裕商先生认为:“指出铜器的绝对年代,即将某器具体归入某王世。”[11]而杜勇、沈长云两位先生则认为,彝铭记事内容所在的王世即西周金文的相对年代[12]。
以上专家的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将遗存与王世拟合后的年代既可称为相对年代又可称为绝对年代。例如汉武帝元鼎三年,当我们对汉武帝或汉代一无所知时,它只表明该年比元鼎元年晚了三年,其实是一个相对年代。只有当我们弄清楚该年代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关系,或者汉武帝在位的大致年代,这个相对年代才能被称为绝对年代。当然,仅知道汉代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大致位置,也足以将元鼎三年称为绝对年代,时间精确度的高低并非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都是相对而言的,二者之间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它们都是将历史遗存或事件置于时间轴上,其区别在于所选参照点的不同。绝对年代的参照点是当下已知的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相对年代的参照点则可以是当下未知的某个时间点或时间段。
参 考 文 献
[1]段小强,杜斗城.考古学通论[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15-16.
[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历史\考古\世界史分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310.
[3]刘华夏.金文字体与铜器断代[J].考古学报,2010(1):43-72.
[4]王乃新.罗马年代学与卡皮托执政官表[G].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139-140.
[5]曹书杰.中国历史年代学若干问题思考[J].史学集刊,1991(2):1-5,76.
[6]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09-410.
[7]林.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C]//古文字研究(9).北京:中华书局,1984:148.
[8]彭裕商.组卜辞分类研究及其它[C]//古文字研究(18).北京:中华书局,1992:46.
[9]李雅书.古罗马的历法和年代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2):40-50.
[10]刘华夏.金文字体与铜器断代[J].考古学报,2010(1):4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