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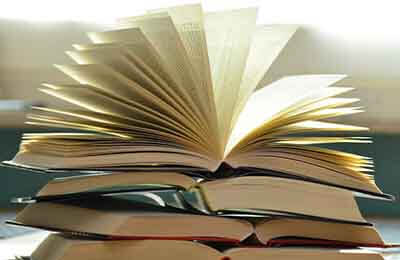
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范文第1篇
唐代诗人孟郊在《游子吟》中慨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生我养我,在我们生命之初都有“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之后我们成长中的每一天,都离不开父母为我们的无私付出,虽然对大多数父母而言,这种付出是不求回报的,但作为子女,却不能对父母的付出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我们所能回报的就是孝。
纵观华夏数千年的人文史,虽然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曾说过他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但那不过是在当时矫枉必须过正的特殊时期的一时激愤之语,当不得万世不变之圭臬。我们如有对传统的同情与关照,则当细心探究下何为“孝”?
孝的三个层次:尊亲、弗辱、能养
孝是人类最朴素自然的情感。同时,孝又是古代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标准甚至是根本大法。在《诗经-蓼莪》中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孝经》中有“古之明王以孝治天下”。
具体而言之,关于什么是孝,《礼记・祭义》中这样记载――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这是孝的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尊亲――发自内心的对父母的尊重以及因自己的行为使父母得到他人由衷的尊重。这里的“尊亲”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层面既包含了孔子在《论语》中回答孟懿子问孝时所说的“无违”,无论父母在世还是去世,都要用一种诚敬的心去做好生养死葬的每一件事,要依礼而行,不可轻忽。同时也包含了《礼记・曲礼上》所规定的“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这种做法,其出发点在于让孝子尽己之心去感受父母每一天的身体变化,通过几个特定的时段――严寒、酷暑、入睡前、起床时,来全面细致地观察父母的健康状况,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保证父母的健康长寿。
第二层面包含《孝经》中所说的“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的处事态度。在上位时有庄敬之心,在下位时有恭谨之心,与人交往时有谦让之心。这不仅能够让自己获得他人的广泛认同和尊重,更是使自己的父母、亲人也得到他人同样甚至更高的尊重的主要表现:他人会赞美你的父母教子有方并慕而效法;也会出于对你的礼敬而对你的父母礼敬有加。这就是孝。民间有一句俗语叫做――“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古人所追求的“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以及“身后哀荣”体现的同样是这种思想。这是孝的最高表现,也是我们当前认识孝道所普遍忽略的地方。
《孟子・离娄下》中记述了五种不孝的行为――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这五种行为除了让父母感到痛心之外,都会给父母造成来自他人的羞辱,违背的还是“弗辱”的思想。这是孝道的第二个层面。由此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父母的孝。
至于从衣食口体上赡养父母,也即孔子所言之“能养”,就等而下之了。《论语》中孔子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如果缺乏了敬意,即便做到“能养”,也不能称之为孝;反之,有敬意的养实为“尊亲”的大孝之举。
“能养”在孝行中是排在最后的,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对孝行仅及于此的肤浅认识,并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历经2500多年的风雨,当今社会依然有很多人所谓的孝子之行也都只是做到了这一层,这是我们时代的不幸,也是传统的不幸。
悌是儒家“推己及人”精神的体现
在儒家的价值中,与孝紧密相连的就是弟,现在也写作“悌”。
悌就是为弟之道,兄弟之爱一如父子之亲,也起于天性,是父子之亲的自然延伸,这同样体现了孝。这种关系在儒家看来也是相互的,“兄友弟恭”,而且“兄弟睦,孝在中”。兄弟和睦会让父母感到莫大的慰藉,这样他们才可能满心欢喜地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整个家庭才会有其乐融融的气氛。
有了孝悌之心,自然便会有爱心的扩充,对同龄人中的年长者以及无血缘关系的长辈的尊重也被称为悌,这既是儒家“推己及人”精神的体现,更是对“大孝尊亲”的具体实践。儒家文化的教育,就是要在生活中时时处处注重培固孝悌的根基。因为――
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孝经・广扬名章第十四》)
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孝经・广至德章第十三》)
以事兄之心去事长,以敬兄之心去敬他人之兄。这是悌的扩展和延伸,也是孝的扩展和延伸。同时,正是因了这种推而广之的敬,才使得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冷漠。
孝道根本乃在要人心存敬意
《礼记》开篇有言:“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孝道思想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人心存敬意。对人、对事、对天地万物,都要心存敬意,方可成就君子之德。“敬”是内心的道德修养以及这种修养的具体外化。
在当代社会,实珊涕道依然要和孝道结合在一起。当前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基本绝迹,居住环境呈多元化特点,故而维护小家庭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大家庭之间的和睦是孝悌之道的核心要义。同时,邻里和谐、尊老敬长也是孝悌之道的应有之义。
孝悌的外化,就是儒家“推己及人”的重要思想,也是正人心、化风俗的重要手段。事亲是孝,从兄是悌,孝悌是仁义的基础,有此孝悌才会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思想,才会有仁有义,才会有立人之道。礼乐以及智慧也随之而产生并赖以存续。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推恩”思想,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爱人”,而由“仁民”而“爱物”则是进一步的推及,是对天地万物一体之爱,就像北宋的张载在《西铭》中所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儒家思想的特质,立足于当下今生,从血缘亲情入手,培固孝心,弘扬孝道,并由此而扩充仁爱之心,涵养浩然正气。这种直人人心、直探本原的做法,在精神信仰层面必然成为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其他信仰并世而立的一种选择。在面对当前社会的信仰危机方面,应该是最具本土意识也最契合中华民族心理的解决之道。
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范文第2篇
一、问题指向:工夫而非本体
1.宋明道学话语体系中的礼理关系
在宋明道学家中,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都讲“礼者,理也”,区别在于对“理”的把握不同。周敦颐讲的“理”是可显可微,但又不是独立的精神存在。程颢、程颐以“理”为最高范畴来反对张载“气为太虚”之说,“指虚曰: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2],以“天理”否定张载的太虚之气,把“理”说成无形而实有之物,而且认为“理”乃天地万物之根源。朱熹已意识到“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行迹之可言”,“某之意,不欲其只说复理而不说礼字。盖说复礼,即说得实。若说人理则悬空,是个甚物事”。[3]之后王阳明在《礼记纂言序》中讲道:“礼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其浑然于其性也,则理一而已矣。”[4]王阳明将“礼”提升到“天理”的高度,认为它是事物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体现。尽管如此,他们仍有一个共性,即通过对“理”的意义阐发,将礼理关系的讨论提升到了伦理终极根据亦即本体的高度。
2.张载礼理关系的问题指向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从天理、物理、人理等各个方面为“礼”作论证,把“礼治”变成“理治”和“治心”,把封建礼教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使礼理相通更具有了权威性,对人们的思想引导变成了思想控制。与他们不同,张载借助于“天”而非“天理”或“心”来解释三纲五常和礼理关系。这也是张载礼理关系理论的重要特色。张载对礼理关系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通过对如何践礼的讨论来进行的。尽管与其他宋明道学家相比,张载亦有着宋明道学家企图为道德寻找终极根据的共同倾向,但在他那里,对于五代以来甚或孔孟以来伦理纲常丧失的状况有着更为强烈和独特的感知,其批判不止指向佛老对伦常的冲击,世儒、陋儒与现实政治的脱节更是其重要的理论批判指向。在张载看来,当时社会存在的最大问题即在于国家缺乏有效的礼制,而世儒和陋儒与社会脱节,导致“体用殊绝”,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使传统礼仪出现了形式化和去形式化这两种不良倾向。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改变儒者“不知择术而求”而只是重视内在修为的局面,还要走出国家制定礼仪制度“出于人”的误区。在张载看来,只有通过对“礼”的贯通理解与实践,这个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张载通过对传统礼观的重构,在新的意义上提出了礼理关系的新见解。他说:“盖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1](P326)针对世俗践礼过程中过分注重礼的外在化、形式化倾向,张载强调应该注重把握礼的内在精神,并批评在“礼出于人”理念指导下制定礼仪的行为规范。质言之,他所要解决的是礼的内外之辨问题,而非如何为伦理确立终极根据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张载是通过对虚气关系的深入探讨来完成的。
二、理论特质:礼本于天而非本于天理把握张载的礼理关系说,首先要澄清的就是张载关于礼的本原问题的探讨。
从学理上来说,考察张载的礼理关系说,既要考察其对“礼”的定位,亦要考察其“理”的涵义。在宋明道学的整体话语体系中,要把握张载礼理关系的特质,关键在于把握其“理”的涵义。在张载那里,除“顺而不妄”之“气之理”,还有“性命之理”、“自然之理”以及“天理”等诸多提法。张载所讲之“理”主要是指不得已而然的必然性,亦即规律。尽管张载讲“天理”之处亦不少,且往往将其与“人欲”置于一处而论。“徇物丧心,人化物而灭天理者乎!”“上达反天理,下达徇人欲者与!”[1](P18,P22)这两处的“天理”皆是就自然法则而言。张载亦讲:“所谓天理也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时义而已。君子教人,举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时措之也。”[1](P23,P24)这依然是从普遍法则的角度而非从“至静无感”的本体论角度来说“理”的。可见,在张载这里,“理”的提法尽管很多,但基本是从自然法则和规律意义上谈的,并没有上升到本体的高度。张载对礼的本原的反思并没有止于“理”,而是通过上达至“天”的思路而最终完成的。
首先,从张载应然的理论逻辑来看,礼当本于“天”。针对陋儒“不知择术而求”而“有有无之分”及佛老理论陷入虚空寂定的理论弊端,张载从“太虚”概念的引入入手建构起了新儒学的理论体系,为人和万物的存在确立了终极价值根据。“虚者天地之祖,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实也。”[1](P325)天地万物之“取足于太虚”,正说明太虚是天给予万物的内在禀赋;而从“天之实”到“心之实”,则是就太虚作为天人一性而言。“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从虚中求出实。……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1](P325)这也说明了太虚之天人一贯的性质,而天地以虚为德乃太虚之至善属性的表现。张载言:“虚者,仁之原,忠恕者与仁俱生,礼义者仁之用。”[1](P325)。从虚到仁、从仁到礼,张载实现了由“太虚”向“礼”的自然过渡,使得“礼本于太虚(天)”成为必然的理论归宿。
其次,张载曾明确讲过“礼本于天”。张载不认同前贤时儒“专以礼出于人”的观点。他在其佚书《礼记说》中提出:“大虚(太虚)即礼之大一也。大者,大之一也,极之谓也。礼非出于人,虽无人,礼固自然而有,何假于人?今天之生万物,其尊卑小大,自有礼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或者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5](卷五十八)张载曾明确讲到:“礼本于天,天无形固有无体之礼。……盖礼无不在天所自有,人以节文之耳。”[5](卷五十四)此处将礼的本根已讲得非常明确,将礼的地位提升到了天的高度。以此为基础,他为当时的社会危机提出了解决的方法:“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序天秩,如何可变!礼不必皆出于人,至如无人,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告子专以义为外,而不知所以行义由内也,皆非也,当合内外之道。”[5](卷九十七)此段话有三层含义:其一,礼不依于人而有,即使无人存在于世,天地之间所展现的秩序性即“礼”之展现。基于此可知,若礼不依于人而有,则礼之根源不在于人;而由“天地之礼自然而有”则可知,礼之本根实源出于天地。其二,人是通过顺承并取法天地所展现的整体秩序性而建立人间秩序之礼的。人通过与天地宇宙的“感通”来完成从天序、天秩向人间之礼的转化。张载哲学“以人合天”的思路得以充分展现。其三,礼虽为形上之理于存在世界所展现之整体秩序,但礼之实践需基于人之内在道德心性,方能体证取法天地大化所展现的秩序性。这样,从天道到人道的思维模式得以充分展现,“天”抑或“太虚”是最高的终极实在,不仅“礼”根源于天,“理”同样也根源于天。
若以“礼本于天理”来总结张载关于礼之本源问题的探讨,则不利于准确理解其“天理”概念及工夫论特色,也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关学与洛学的差异。
首先,该提法没有准确把握张载引入“天理”概念的意旨。在程、朱那里“天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张载这里却并非如此。如前所言,张载虽然在其着作中不止一次提及“天理”的概念,但并未超越《礼记》中的《仲尼燕居》《乐记》等篇的思想范围,仍然主要是从自然法则和规律意义而言的。借助于“以礼制心”的实践工夫,克治人心(人欲),以化解道心与人心之紧张关系,这是张载首要的观照点和引入“天理”概念的主旨所在。尽管其“天理”概念已包含着普遍之理的必然 性,但更为突出的应是其“所当然之理”的规范意义。张载曾言:“全备天理,则其体孰大于此!是谓大人。以其道变通无穷,故谓之圣人。”[1](P236)可见,张载并没有把“天理”放置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不可能用它充当礼的终极根据。这也正是“礼本于天理”的命题在张载这里不成立的最重要的文本根据。
其次,该提法不利于把握张载的工夫论特色。张载在宋儒中是比较早地将“天理”“人欲”和“道心”“人心”这两对范畴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的儒者。他说:“穷人欲则心无虚,须立天理。人心者人欲,道心者天理,穷人欲则灭天理。既无人欲,则天理自明,明则可至于精微。谓之危,则在以礼制心。”[1](P264)张载通过“虚心”、“反(返)天理”、“变化气质”和“以礼制心”等修身实践工夫将“天理”“道心”与“人欲”“人心”衔接起来,突出强调了超越人欲、返归天理的价值取向。他所提出的以“礼滋养人德性”、“得礼上下达”的提法都是在强调“克己”、“化性”的重要性。这也是张载工夫论的鲜明特色。而“礼本于天理”的提法,易于导出“先识仁”、“涵养需用敬”的修养工夫,与张载重视礼化而渐次提高修为工夫的特点不符。
最后,该提法不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关洛学派的差异。尽管在张载着作中也多次出现“天理”、“义理”和“穷理之学”等词语,但需要根据语境作具体研判。通过对散布在张载着作中“理”概念的综合考察发现,“理”在“天、道、性、心”的哲学总纲中与“礼”基本上处于同样的地位,即近于“道”。张载礼之根源在于“天理”的提法,将“先识造化”或“天”的关学特色淹没在“先识仁”、“先识天理”的洛学思路之中,具有鲜明的程朱理学本位立场。这在一定意义上降低了张载哲学的建构层次,若将礼之根源归于“天理”,无疑是将“礼根源于太虚(天)”的深刻性降低到了“道”的层次,也容易给人造成张载与二程本体论建构无差别的误解。这对于准确把握其礼理关系都是非常不利的。
三、理论归宿:“以礼合理”而非“以理代礼”或“以礼”张载对礼“本之于天”的认识和“得礼上下达”的贯通式理解,使得天序、天秩与人间社会规范有机结合,从理论上真正实现了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事的贯通。“以礼贯通天人”或“礼合天人”的理论,成为张载在修养工夫论中通过礼的实践而顺利完成“合内外”之目标的理论铺垫。
1.礼合内外
礼的内外之辩其实一直是传统儒家思想里的重要论题之一。对张载而言,有效协调礼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其礼学思想建构的重要目标。
首先,在张载看来,礼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内外合一的过程。张载认为礼并无所谓内外,“礼非止着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1](P264),主张“平物我,合内外”[1](P285)。在张载看来,践礼、行礼的过程就是内外合一、勉认成性的过程,“知礼成性”之要义在于将外在礼仪通过实践内化于主体自身。由此不难看出,集“合两”、“成性”于一体的张载人性论已经给践礼提供了内外合一的空间,为确保在重视义理即“理先”的前提下做到礼理融合贯通打好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礼理的先后问题也就是在礼化的实践中如何实现内外一致的问题。
其次,在张载看来,礼理先后问题实际上是对内和外的重视程度问题。翻检卫湜《礼记集说》会发现,张载对于礼理关系要义的阐发,来自于对《礼记·乐记》篇中“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一句的解释。《礼记》原文通过对“礼”和“乐”的不同意义的揭示,阐明了礼乐与人情之间的关联。张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礼者,理也。欲知礼必先学穷理,礼所以行其义,知理乃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今夫立本者,未能穷则在后者,乌能尽礼文残缺?惟是先求礼之意,然后可以观理。”[5](卷九十七)他明确指出,无论是学礼还是践礼,都需要先学理、穷理,而且认为“礼出于理之后”,并在此基础上批评当时建构儒家新理论的学者们不先穷理,尤其是不问礼之本意而一味效法古礼的做法。在《张子语录》中,他进一步指出:“礼文参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当。盖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礼,礼则所以行其易,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1](326-327)他认为礼的精髓在于礼义,而非在于礼文。对于盲目效法者,需要重视礼的内在精神;对于空谈天道性命者,需要重视礼的外在仪节。礼理的先后问题关键在于要实现内与外的“交相培养”。
2.以礼合理
首先,“以礼合理”是张载礼学思想的必然落脚点。张载反复强调要先穷理而后知礼:“今礼文残缺,须是先求得礼之意然后观礼,合此理者,即是圣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学者所以宜先观礼者,类聚一处,他日得理,以意参校。”[5](P327)礼本就是“天理之节文”,乃顺乎人情的产物,故而要真正理解礼,就需先得“礼之意”。所谓“合此理”、“他日得理”之“理”,实指综合考察诸种礼仪器物转自制度后所得礼仪上的条理或规矩。可见,张载之意,乃礼理二者兼容并包,而非相互取代。张载认为,礼之实践乃“合内外之道”,若人能守礼便是不背离天道。因此,张载认为礼能使人“持性反本”,即通过外在之礼的践行实现内外合一,此即“以礼合理”。
其次,张载“以礼合理”思路的中断是关学衰落的重要原因。朱子在《答陆子寿书》中云:“伊川先生尝讥关中学礼者有役文之弊。”[6]所谓“役文之弊”,即拘泥于形式上的仪节礼教。伊川弟子谢上蔡认为:“其门人下稍头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因,无所见处,如涅木札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厌倦,故其学无传之者。”[7] (卷上)指出张载后学之讲礼,只限于有形和外在的规矩,失去内在修养上的实践意义。在张载弟子的视野中,似乎张载仅重视外在仪节,对礼与道德实践在理论上的必然关联关注不够,甚至在理解中发生了从“礼”向“理”的自然滑转[8],从而导致其后学尽管能够秉持“崇礼贵德”、“学政不二”的宗旨,但理论建树非常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关学学派在张载之后同洛学及其他学派的学理讨论与沟通,导致其后学渐趋中绝的格局。
最后,“以礼”与“以理代礼”皆非张载的初衷。张载后学之所以遭到来自程朱学者的批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于道德实践中呈现出的“以礼”的思维导向。即便如此,朱熹本人仍对张载“以礼合理”的思想保持了几分自觉。朱熹在生前就曾针对学生提出的“以理易礼”说给予了激烈的批评,而且从其一生的理论建树来看,既有对儒家性命义理之学反复精研的《四书章句集注》等学术性理论着作,亦有对现实社会移风易俗发挥重要导向作用的《朱子家礼》,这使张载的“礼理融合”的思路得到充分展现,从而奠定了其在道学史乃至于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至清中叶,为了纠王学末流之弊,以凌廷堪为代表的清儒发起的“以礼”的思潮运动,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和学术指向,以此推定理学发展初期甚至包括从张载那里就已存在“以理代礼”趋势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9]
四、结语
“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10]这是皮锡瑞对经学史上汉、宋学各自学术宗旨所做的论断。就汉学与宋学在义理层面上“由礼转理”的思想史转型而言, 这一论断确为精辟之论;而就某一个思想家的特殊性而言,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礼”的定位问题,就政治层面而言,统治者关注的是如何达到掌控社会的目的,故易导发“以礼”的倾向;就学理分析层面来看,因儒者的着力点多在学术探析与思想阐发,故而易沦入“以理代礼”的泥潭。此两种取向,虽意义指向不同,但对社会的整合都非常不利;只有贯通学与政,实现“礼”与“理”在实践层面的融合与沟通,才是理想政治秩序建构的必然选择。本着“学政不二”、“天人合一”的思维,张载通过对“执于礼”和“执于理”的两偏之失的救治,以礼理贯通、“以礼合理”的思路重构儒家礼学,对包括朱熹在内的道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张载.张载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8.
[2]程颢,程颐.二程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118.
[3]朱熹.论后世礼书[C]//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2183.
[4]王阳明.传习录(上)[C]//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81.
[5]卫湜.礼记集说[M].宋嘉熙新定郡斋刻本.
[6]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559.
[7]谢良佐.上蔡先生语录[M].张伯行,辑.福州正谊书院.
[8]牟坚.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与辨析——论朱子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J].中国哲学史,2009(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