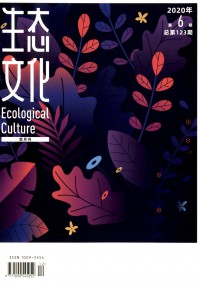文化典籍和文学艺术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文化典籍和文学艺术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文化典籍和文学艺术范文第1篇
我演讲的题目是:让书香为梦想插上快乐的翅膀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本书,自诞生之日翻开扉页,每一天都没有停止记录和书写。每个人的书页里,既有自身对于生活感悟的记录,又有通过读书与先知和历史交流的感言。芸芸众生,正是组成现实的浩瀚典籍的元素,把历史、把文明一天天承前启后,每一天都在续写着历史和文明。
读书,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在潜移默化中提高素质,提升人格。一本好书,能够告诉你许多做人的道理:告诉你宽容是对自己的慈爱;善待他人的是人生的美德;尊重别人是尊重自己等等。
读书,能够令我们充实,丰富我们的知识储备,从字里行间感受人间真情,从书中悟出人生的真谛,打开心扉,用心去感受生活。就不会因为生活的平淡无奇而麻木,也不会因为世俗的利益纷争而漠然,会以一种积极态度来感受并传递生活中的点滴快乐,也能够平和而正确的对待利益的得与失。
书就是这样的朋友。她不狭隘,不聒噪,一直守候在我的左右,伴我成长。寂寞的时候,她会用渊博的学识拓宽我的视野,告诉我世界其实很大;失落的时候,她会用真情实感、励志名言给我鼓劲,让我振作;迷茫的时候,她会用寓意深刻的哲理故事引导我走向新的旅程……她是海,包容着我的一切;她是树,为我遮挡风雨;她是风,吹着迷人的气息,抚慰我的心灵,感受着我的喜悲。
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有人问教育专家,为什么不能贡献一个爱因斯坦?专家回答: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造就一个爱因斯坦,除了需要超常的数理知识之外,还需要广阔的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丰富的文学艺术素养。 不错,文学艺术不能直接帮助爱因斯坦推导数理公式,然而它扩大了爱因斯坦的文化背景,强化了他的想象力,升华了他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境界。对他来说,两个世界同等重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可见,文学艺术素养多么重要!它可以成就一个人辉煌的事业!
如何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呢?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在书海中遨游,汲取营养。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充实,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多么深刻的感受!知识的力量无穷。我们是新世纪的学生,有着光荣的读书传统,在初中阶段认认真真地读上几本好书,你将终身受用。
文化典籍和文学艺术范文第2篇
关键词:藏族舞蹈; 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7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06-129-001
舞蹈艺术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最早形成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样,藏族舞蹈也在民族心理素质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伴随着藏民族的形成发展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意识形态。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一、探讨藏族舞蹈的文化特征,要搞清楚历史上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艺术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传统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学”中,把舞蹈归于“工巧明”(即工艺学),这就表明舞蹈艺术在理论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围之内,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论依据的艺术形式之一。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和众多舞蹈论述中,都出现了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论部分。这些文化遗产中首先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体所做出的各种动作,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情感。随着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藏族舞蹈也由起初的简单模仿、无意识的自娱性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一门艺术。藏族人民在萃取历史文化的精髓时时非常重视古今的文化意识相结合,以民族思想需要和创新精神创造了符合民族文化特征的舞蹈理论。
二、藏族人民都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一整套反映民族生活、思想情感并具备一定审美特征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且顺应自然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结合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政治历史、、民俗民风的不同,又形成了具有藏民族地方特色风格的“藏舞”。藏舞要求舞者在舞蹈时表现诗情画意,融诗舞于一体,载歌载舞,以词带情,以姿促情,使藏族舞蹈富有生命力和激情。从藏舞提出的基本要求不难看出藏族舞蹈的文化思想。藏族舞蹈非常强调舞蹈时脚、膝、腰、胸、手、肩、头、眼的配合及统一运用。例如,藏族众多舞蹈的“膝盖”动作就是一个最具典型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动作之一,也是最能表现内心情感和舞蹈动感的表现手法之一。
文化典籍和文学艺术范文第3篇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最新表述,“出版业以传统出版为主,数字出版为辅的发展阶段已告一段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并重发展的格局将逐步形成”。当下,业界人士、学者和政府官员,包括稍微敏感的老百姓言必云“数字出版”。俨然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业已经“并驾齐驱”。
国外的声音不比我们早,只比我们更盛。德国出版商称再用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普及数字出版;美国出版界直接用出版业的“革命”来表明它的来势迅猛。
于是,业界的人们开始坐立不安,忧心忡忡,担心传统出版被革命、被替代,担心自己再无立身之地,担心自身的文化价值不复存在。于是,著作界的一些人士也被“网络写作”的高效传播力和高额回报所诱惑。价值观和文化传播观发生了变化,实在令人迷离。
所谓传统出版的“传统”, 就是相对数字出版的纸介出版形态。跨过千年历史、蕴含墨韵书香的纸介出版物真的会被替代吗?面对新媒介的挑战和冲击,我和业内人士一样,有很多感慨,也充满危机意识。但是,在“热情”讴歌数字出版的时候,还要能够冷静思考、理性分析,不能乱了方寸、乱了阵脚, 不能无所作为。
传统纸介出版物的稳定、可靠、经久的性质,包括它承载艺术设计与创意的能力,以及独有的整体审美鉴赏性质,是新介质不可比拟的。任何事物的优与劣都是相对的,新媒介是有局限性的。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认识、把握介质特性,发挥、调动材料介质的优势,以自己的经典价值立于各种新老介质之林,保持身段,独领,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业界有识之士总是呼吁说,面对挑战要自信和淡定。我以为它不应当是一句空话,也不应当是硬撑着面子喊高调,它一定是理性而客观的举措, 是一条切实而有前瞻性的路径,这就是做传统出版“要讲究,不能将就”。
何谓讲究?“讲究”就是从内容到形式,传统出版所具有的个性品位。做经典,是那些秉赋学术传承、服务文化建设,古今中外典籍的整理、开发、诠释性的项目;做深度,是那些便于研读、推敲、比对、切磋、考量的项目;做文献,是那些国家、民族、地域、机构等单位组织用以保存重要资料、数据,要求载体物理性质稳定、“立此存照”、具有版本学意义的项目;做收藏,是那些以图书作为文化符号和独特文明标志、体现生活品位和历史责任,可以传之久远的项目;做审美,是那些反映、承载优秀而纯粹的文学艺术创作,声入心通、幽怀逸趣、文学有文、掷地金声的满足读者品位、批评、把玩和赏析等高端需求的项目;做从容,是那些对传统阅读情有独钟、养成依赖和习惯,追求纸版材料的亲和质感、易于翻卷和持握的自由形态、图文贴切搭配和整体装帧设计的艺术魅力,以及令人沉湎于墨韵书香的项目。
文化典籍和文学艺术范文第4篇
关键词:藏文古籍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141-04
藏文古籍是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有藏文长条典籍约1.5万多种,其中解放前写本、刻本藏文古籍4543种,内不乏一些珍本和孤本,如唐代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明代抄本《米拉日巴传》、清康熙年间朱、墨手抄本《大藏经·甘珠尔》等多种文献,皆为国内珍稀版本。2007年以来,文化部在全国开展古籍普查活动,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图十五)珍藏的藏文古籍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有15部藏文古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47部藏文古籍入选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以下将馆藏藏文古籍从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三方面做一评介,以飨读者。
一 藏文古籍的历史文物价值
藏族文化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早期的藏文古籍主要以佛经翻译为主,后随着佛经翻译的兴盛,有关佛教注疏、藏族哲学、历史、文学、医学、天文、历算、艺术等方面文字资料逐渐增多,成为今天藏文古籍的主要组成部分[1]。
藏文古籍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代表着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对研究藏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其受古印度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版本形式特殊,典籍装帧、装潢、书籍名称等都不同于汉文古籍[2]。如馆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唐代京拉喜、桑贡、李才红抄写,卷轴高31厘米、长136厘米,白麻纸,纸质较厚、纸面稍粗,有横划乌丝栏,经文字迹工整、清晰,藏文正体书写。文字从左至右横写,卷首在左,卷尾在右。卷子上下有天头、地脚,卷子左右有边距,宽度大约在1至1.3 厘米之间。每纸分左右两页抄写,中间留有0.8厘米宽的中缝,近似古籍刻本版式中的版心。卷末有抄写者的署名,经文由三纸粘连成一体(图五)。此经是公元九至十世纪敦煌藏文写本,浸染了千年光阴,其文物价值远不是宋刻本能比的[3]。
馆藏《大藏经·甘珠尔》(封面图),是由甘肃天祝天堂寺(图十三)解放初捐赠,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是清代藏文朱、墨写本,一百零五函,梵夹装,开本高25.2厘米、宽69.5厘米。字体苍劲,整齐均匀,校勘精良。全书所用纸张洁白坚韧、色泽鲜亮。夹板由高级红木雕刻而成,木质坚硬、雕工精美、古朴典雅,为存世珍稀版本。
馆藏善本中有珍贵文集36种,都是藏族历代著名学者的文集,如宗喀巴和其最著名的弟子克珠杰及贾曹杰的文集、布敦大师文集、第一代嘉木央错文集、历代高僧传记等。馆藏藏文古籍中还有一些医学代表作如《四部医典》,也有一部分天文、技术等科技类藏文古籍。总之,这些古籍以丰富的内容,充分反映古代藏族文化历史,具有无可估量的文献价值。
二 藏文古籍的艺术价值
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也创造出独特的民族艺术。藏文古籍是藏族千百年文化的结晶,代表了藏族文化内在的思想和艺术。
藏族是笃信佛教的民族,其文化艺术带有很深的佛教文化艺术烙印,其古籍的装帧和版本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藏文古籍的装帧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书籍呈长条形,活页状,梵夹装帧。藏族受佛教贝叶经启发和影响,创造性地将贝叶经的形式运用到书籍的装帧上,形成独特的梵夹装。同时梵夹装也适合佛教徒的阅读习惯,藏文典籍大多是佛教经典,佛教徒诵经要求正襟危坐,专心致志以表虔诚,经书的翻阅要求便于翻页[4]。这种装帧将印有文字的活页按次序重迭起来,不进行装订,在上下夹两张檀香木板作为前后封。夹板均为红漆描金,雕工精细,珍贵古籍的夹板上还有佛像、火焰及宝珠等彩色图案。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藏文古籍多在卷首绘有佛像插图或菩提塔图以及花纹装饰,一些藏族古代医学、天文科技的典籍内还绘有人体解剖图和动植物药科图、天体星象图,表现出藏族早期的绘画艺术。藏族的绘画是在本民族古有的佛画绘画基础上,吸收汉族、印度、尼泊尔的艺术营养,发展为具有鲜明民族艺术特色的绘画艺术。馆藏藏文古籍上的彩绘插图,使用藏族独特的矿物质颜料绘制,人物形象夸张,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色彩艳丽。古籍上的插图与内容相互呼应,互相衬托,将古籍内容、寓意明了解读给读者[5]。如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圣三宝念要经》为明本,突出表现了藏民族在文化古籍中的艺术形式。《圣三宝念要经》是一部佛教典籍,开本高9厘米、宽45厘米,全书采用金、银、玛瑙、绿松石、珍珠等珍奇宝石磨成贵重颜料与墨调和研磨成汁抄写而成,字体优美,字迹经久不变。书的夹板上有用矿物质染料调汁画的莲花,永不褪色,时隔数百年,莲花仍有一种含苞待放之感。莲花图案不仅是书的装饰,更是吉祥、神圣、智慧之物。封面遮幔是绣有龙纹的彩缎、璎珞,遮幔下甲板上塑有立体的描金题名,题名周围用黄金、贝壳等镶成藏族吉祥物日月、彩云、宝焰、金轮宝、宝塔、白海螺等标志,与佛陀和佛法息息相关,夹板图案精美、做工精细别致、技法高超、镶嵌图案错落有致,代表了藏族高超的雕塑和镶嵌艺术。《圣三宝念要经》还将藏族传统的唐卡制作艺术灵活运用到了古籍的装帧上,表现了藏族古籍独特的装帧艺术形式。夹板的两侧绘有释迦牟尼佛像和观音菩萨像,每页的空白处用彩色丝线堆绣出朵朵鲜花,版面看起来绚丽多彩,整部古籍无论内容还是装帧都突出代表了藏族古籍浓郁的艺术特色。
勤劳智慧的藏民族利用当地的野生植物,造出有独特工艺特色的古籍用纸。藏纸采用当地丰富的瑞香狼毒、登台树、野茶花树、瑞香等多种原料制造而成,质地厚实、洁白坚韧。由于原料中有狼毒草,藏纸不仅坚韧洁白经年不朽,且不被虫蠹。自唐代起,已能造出红、白、蓝、黑、紫、绿、藏墨等各色纸张。藏族喜用黄纸印经,并制作工艺精细的“藏青纸”用以书写金汁、银汁藏文经典。馆藏明写本《嘛尼全集》、《密宗五种》(图十二)、《般若波罗密多八千颂》(图六)等佛教典籍,用金汁、银汁书写在“藏青纸”上,版面庄重典雅,绚丽华贵。更为神奇的是馆藏印本清代《大藏经·丹珠尔》二百零五函,书籍纸张是在藏纸抄造原料中加入羊绒,历经数百年,纸张既柔软有韧性,又不会被虫蛀。馆藏藏文古籍无论内在的艺术内容,还是外在的装帧艺术形式和纸张、写绘颜料等工艺,均是学习研究藏文典籍不可多得的材料。
三 藏文古籍的学术资料价值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藏文典籍门类齐全,内容以藏传佛教教义为主线,是少数民族院校教学和科研重要的资料。
藏文写经与甲骨文、汉简、明清故宫大库档案并列为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馆藏藏文《大藏经》是由经(修多罗)、律(毗尼,又译毗奈耶)、论(阿毗昙)三部分构成,故又称“三藏”。“大藏经”一名实为汉语赋予它的称谓,而藏文大藏经则有它自己的称谓——《甘珠尔》和《丹珠尔》。馆藏《大藏经》由两套丛书构成,即清代抄本《甘珠尔》和刻本《丹珠尔》两大类,共有经典4570部,以论述内容分为显宗、密宗两类,显宗分经、律、论三部分,密宗分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分,加密宗总续共类。八类之外又按学科分五明之学列藏族学者的著作,大类下再分小类,按照佛教教义、戒律、修行、历史传纪、文学、音韵、工艺、医学等学科分类。由于藏文《大藏经》主要是由梵文翻译而来,许多经典甚至在印度都已经消失了很久,藏语又是模仿梵语创制成,可以说是一种标准梵文,保存了印度原典的旧观点。在梵文典籍不多的今日,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可翻译还原成梵文佛典,做梵文典籍的参考和校订,同时也是研究古印度历史、宗教、哲学、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大藏经》中还保存大量汉文、巴利文所缺的佛教经典,因而藏译佛典又是佛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相比,有译语统一和忠实原文、校刊精良的优点,可为新版佛教经典的对勘、校订提供资料。
藏文《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资料总汇,藏族文明史的发展总汇,也是藏族文化遗产的珍贵结晶。藏文《大藏经》作为藏人经籍文化的代表,其卷帧之浩繁,内容之丰富,门类之齐全,传播与影响之巨大,是其它文献资料难以比拟的,是研究藏族文化的珍贵资料。
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馆藏传世孤本《米拉日巴传》是宋代日巴吾琼著,明朱、墨两色抄本,长49厘米、宽7厘米,全书231页。纸张细腻光滑,笔迹生动优美,关键字全用朱笔书写,是一部藏族自己创作的传纪文学。《米拉日巴传》真实记述了11世纪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的人生经历,叙述了米拉日巴解脱和成佛的道路,采用散文、韵文相间文体,热情讴歌了藏民族坚韧不拔、聪慧向上的民族精神[6]。《米拉日巴传》书中文字多处为古藏文书写,说明此书的作者运用的藏文文字处于藏文厘定期间,新藏文文字还未完全成熟确立,对研究藏文文字的演变过程具有资料价值。已出版的《哲蚌寺藏文古籍目录》、《藏文典籍目录》、《拉卜愣寺藏文古籍目录》等整个藏区的藏文古籍目录中均未记载日巴吾琼所著的《米拉日巴传》。书后题记中明确注有该书资助人的姓名,左右双边、上下无边的特点是典型的明本,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是研究11-12世纪历史、文化、经济、宗教的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
馆藏藏文古籍还包括藏族文学的代表作《米拉日巴道歌集》,采用藏族传统的韵文和散文并举,将唱词加入到叙述中,通俗简洁、意境隽永。关注社会生活,教人处事哲学的戒言锦语《萨迦格言》、《格丹格言》;佛教教义经典《药师经》(图二,图十)、《药师尊经》、《普明经》(图七)、《俱舍善述》;用注释法依据实际的诗例解读藏族名家诗的《诗境释难·妙音欢歌》;以及著名藏族诗人仓央嘉措的诗,以清丽、朴素、细腻意境构思和形象创造,是研究藏族诗歌的最好资料。
馆藏藏族历史传纪以历代高僧大传为主,《百本生传》、《仓央嘉措传》、《仁钦坚参传》、《根敦嘉措传》、《根敦珠巴传》、《洛桑丹白尼玛传》、《东科努木翰传》等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历代高僧的生平、政治主张、传教活动及学术造诣等。
医学典籍《四部医典》、《药物分类用途详述》、《治病伏魔药物功能直讲·无垢晶球》是藏族医学的代表作。藏族天文历算学典籍《万年历表》、《韵律论》(图八)是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历法著作,在指导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涉及到人的生理、心理、本性、认识等方面的宗教学著作,以绝对的文献优势占馆藏藏文典籍的主要部分。
格萨尔王是藏族古老文化传说中的英雄,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他以慈悲、智慧和大力护佑着芸芸众生,使其脱离痛苦和灾难。馆藏有脍炙人口的藏族民间说唱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系列典籍《卡切玉宗》、《下蒙玉宗》(图九)、《娘林大圆满》、《地狱大圆满》等,是根据民间艺人的说唱记录整理成文的木刻本,有着一千多年历史,与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一起被誉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学校已故藏学研究专家王沂暖先生,专门从事藏学研究和藏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是中国最早翻译与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学者,被誉为格萨尔学奠基人。其论著有《藏族文学史略》、《藏汉佛学辞典》,译著有《米拉日巴传》、《王统记》、《格萨尔王传》(图一)。西北民族大学设有在全国民族院校中唯一一家以世界最长史诗《格萨尔》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建制级别最高的研究机构,为专门研究《格萨尔》的研究院,编纂出版有五卷本《格萨尔文库》(图十四)。
馆藏梵文翻译著作《绘画度量经》是印度古代艺术中最完美阶段笈多时代的造像规范。其对造像基本尺度,诸佛、菩萨等造型特征及身体各部位的度量比例都有详细的论述。《绘画度量经》也创造了适应的度量单位,把拃、平指、青稞粒等日常生活中熟知的事物作为度量单位,生动贴切,便于记忆和掌握。在描述人体各部位的形象时,采用大自然中动植物的造型特点来喻示,生动典型,一目了然,是论述藏民族造像艺术的代表著作。《戏剧论》是讲述农、牧、宗教三者为一体的藏族民间舞蹈、喜剧、演奏技法、风格的著作,生动描绘了千百年来藏民族在雪域高原形成能歌善舞的特质。
藏文古籍的整理与收藏既反映了国家对古籍文化的重视,也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发展原则。藏文古籍的整理,对于深入挖掘藏族文化的形成,推动藏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作为立足西北地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历史、宗教等综合研究的材料汇总库,承担着搜集、整理、研究藏文古籍的重要任务,并在六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整理古籍文献,将大量的零散的古籍串联起来,形成了研究藏族文化、社会、历史的主线,为深入挖掘藏族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藏文古籍的整理和研究的深入,一张张藏族文化研究的蓝图不断呈现,一条条指引挖掘藏族文化的路线图显现,为丰富藏族历史和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印证着搜集、整理、研究藏文古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断地印证着藏文古籍的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先巴.藏文典籍及其收藏[J].收藏,2010,(1):75.
[2]彭学云.试论藏文典籍文化[J].中国藏学,2007,(1):88.
[3]范开宏.敦煌遗书及其价值浅说[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3,(2):96.
[4]王鉴,安富海.地方性知识视野中的民族教育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12,(6).
[5]乃波·噶桑文.谢热译.藏族佛画艺术[J].研究,1989,(12):86.
文化典籍和文学艺术范文第5篇
文化符号学,龚鹏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符号。初文与字母一汉字树,饶宗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高友工,三联书店,2008
从“文”到“文学”的变迁表明,中国文学观念受到现代西方影响,逐步转换为对“心声”的诉求,强调文学作品与主体心灵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里的文学作品主要被理解为那种在场的声音语言,然后才是作为语言之记录的文字。但即便如此,百年文论进程中仍有不少学者尊重或坚持传统思路,看重文字(而非直接的语言)与文学的相关性。这种复杂的情况,最突出莫如鲁迅。鲁迅的新文化新文学立场非常鲜明,但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撰《中国文学史略》讲义(后改名《汉文学史纲要》),则以“自文字至文章”开篇,强调自古以来由文字而成就文章,以形声为主的汉字可“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以至“其在文章”“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对文学的理解上,鲁迅坚持“感动”的指标,但在相当程度上调整了早年的文学“心声”观念,即转而坚持文学与“文字”较强的相关性。这一思路既有西来影响,但更源自师辈学术及其背后的小学传统:章太炎《文学总略》有“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的说法,而刘师培《文章源始》则明言:“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百年文学中不少学者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周氏兄弟、朱自清、郭绍虞、台静农等,都一直深受“语”与“文”对待问题的缠绕。笔者以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文字性”及其现代际遇的把握。
,概括地说,“文字性”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很多深层方面的以文字为准、系于书面文字甚至最终归于文字化的特点。当然,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中,“文字性”的内涵可以不一而足。比如,就古典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而言,它可能体现在作为文学的语文层面上的“文字化”取向,也可能是文人雅士透过视觉化的文字艺术而突出出来的趣味情怀,更可能是整个文化传统所体现出的深察名号、专论字义的行为模式和潜在的文化意识。
首先看文学的语言文字层面。在中西文学传统的比较中,语言性取向和文字性取向的差异相当突出。西方因为拼音文字的关系,言文一致,大体均以语言为其基型。而汉文学在古代往往言是言,文是文,并且如章太炎在《书・订文》中所言的“文因于言,其末则言擎迫而因于文”。也就是说,古代长期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是,语言往往趋向于文字,才能更好地发挥影响,体现价值: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此中分析而言,所谓“文”,相当意义上即是指篇章文字的取向在文化整体中的规定性和影响力。“言”之“文”大抵即如孔子所坚持的“雅言”,或者是数千年来作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所采用或接纳的文字化传统。在特定场合说话写文章做事情,必须突破现场语音的具体性和随意性,而诉诸规范化的文化模式和语文样式,以实现某种超越和提拔,获得相应的普遍性。郭绍虞先生认为,长期以来汉语反过来受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连续性的文字的规定与影响,理应称为“文字语”。这是相当有道理的。由此看来,中国文学或汉文学与西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就有大为不同的地方,即文学在文化落熟的中国或汉文化圈,名为语言艺术,其实是文字艺术。
那么,古代民间就没有口传的文学吗?当然有。但在传统中国,总的情况是“言语文学,厥科本异”,民间风俗与书面雅言“沟分畛域,无使两伤”。并且“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可以想见,没有形诸文字,也往往在历史流传中消逝无形。而作为直接现实的,则是被纪录下来的、同时亦被文字化的文学。即就近世古典小说言,在唐宋以降,由讲唱变文和说话而来的小说其实越发文人化,“讲的故事”渐被“看的小说”取代,而就社会地位而言,过去的职业编书人或说话人也远不及吴承恩、吴敬梓、李汝珍、纪昀和曹雪芹这样的文人小说家。大的趋势即是:语言艺术变成了语言文字艺术,最后乃或变成文字的艺术了。
五四是个古今中外各种思潮交锋剧烈、文化方向纷纭的时代,如同在多重歧路口急于抉择。也正因此,对自己文化与文学的根性问题往往未及深入追问,文字性即是诸多问题之一。而在当代中文学界,相关追问和探讨日渐出现,并且这种追索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深层次的内在肌理。这方面目前看到的最为深广的研究,当数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在龚氏看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统的骨干即在“文”,“文是由文字崇拜、文人阶层、文学艺术等所形成之相关文化状况……不知此,即不能体会中国人的行动、思维与感情,亦不能切察中国社会之底蕴。”该著气魄宏大,内涵高迥,其核心观点即在强调,中国文化中无论是文人还是儒道释,无论各类文艺还是各家学术甚或文吏政治,都存在浓重的尊崇文字、文书化、文学化的传统。而这一点与西方文化重视语言、逻辑和(句子)文法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定势颇不相同。中国文化在语文训诂、思维方式和文学写作诸方面都突出体现出“专论字义”的作风和特点,“训诂明而义理明”的夸说更体现出深入骨髓的“深察名号”的正统名分意识和行思方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是颠扑不破的,“名”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当然可以是人们言语中的名号,但更可能是、并且一般都要落实到某种如同器物一般的“名字”:“名”在古代即训为“字”!通过这种“哲学文字学”对中国文化深层肌理的探讨和描述,龚氏宣称,由文字而文学进而文化,整个古典中国社会生活都充分地文字化、文学化,形成了一个以文字文化为核心的文学社会。
就不同角度和现象而言,“文字性”特点和取向并不容易捕捉,并且对其内涵的把握和理解也不一而足。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总是无可避免地涉入汉字、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域及其逻辑和历史根源的分析。这实在是一个幽微难言而不易把握的境界。其中的研究思路之一就是设想“文字性”特点有其文化基因上的特异性,亦即在世界范围内看来的汉文字的特异性。早期进入中土的传教士提供了初步的他者意识和语言学把握,但更多基于经验的认识和把握上的困难而对汉语文颇多恶声。目前看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确实需要很好的语言哲学(就汉语文而言或可称“语文哲学”)高度。比如德国思想家、教育家洪堡,他提出了迥异于时俗的理解:虽然中国人并不追求语法的精确概念和表达的清晰性与逻辑性,但这并不能排除汉语文在形式上没有的东西可能意味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所短之处实则优
势所在,现代人所熟悉的独体(实体)的分析的思维所不能把握的内涵很可能在中国人的关系化、结构化的思维和语文中包含着,并且中国思维和文化较多地带有审美和伦理的色彩。这些观点竟然成为相当多一部分中国文化学者的基本思路,至今仍然值得细细审度。
对这个问题另有一种探讨思路,就是具体化到语言文字之学的历史研究,或者从追源早期中国文字和文字文化的生成逻辑入手,并且必须在比较语言学的角度与其他早期文明进行比对。也就是说,需要经验的实证史学的印证。在百年相当实证化的学术传统中,人们对此相关的具体细节和科际整合的成果的期望非常之高,但是目前看来,这方面似乎成果也比较有限。饶宗颐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在穷诸方资源多方比勘后,有如是比对:“古代交通困难,人民各安其居,不相往来。我想每个地区可能有它自己的语言。观扬雄在西汉所调查,其复杂可见,三代以前更难以想象,由于方言的复杂,唯有用文字来作为控制工具,幸而汉语是单音语系,一字一音。文字主要作用在于记名(包括物名、私名、族属之名),在古代汉民族圈内,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不像西亚,文字必须与语言结合,为了方便才发明字母来记录口头语言,才可取得语、文必须一致的效果。”也就是说,其一,文字系统的生成及其使用状况也必须结合着古代经济技术基础及相应文化分层的状况,即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文字是属于上层阶级并且较多用于相应文化圈内的精英交流和外交鼎鼐的。正是这种在地的特殊性,孕育了前现代世界各大文明自身的特色、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字文化。其二,与苏美尔文明的文字文化注重财产记录和经济计算、古埃及文字文化注重年历记时和符咒通神不同,古代华夏民族直至汉代的文字文化从总体上看其主要功能在于记名,书以记姓名、主名山川。犹有进者,饶氏对汉字对文化的规定性状况及其历史演化有较为深入的辨析:“汉字属单音制,在形成的过程上,大体保持一字一音,文字的构造,以形声字为主,占最高的百分比,由一个形符与声符组成。形符主视觉,声符取其读音,与语言维持相当联系,前者保存汉字的图象性的美感,形符声符二者相辅而行,双轨并进,形成了文学上的形文与声文结合的文章体制,奠定汉字不必去追逐语言,脱离了语言的羁绊,在政治生活上,文字使用于政令上礼制上作为某种印信的工具,其名字可以识别,简单明了,不必与语言结合,所以我说汉字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这种观点看来是从另一个角度发明了鲁迅先生“自文字至文章”的思路。基于科际整合,进一步的梳理和深描汉字发生学的脉络和文字文化的生成缘由,需要更多平实征信的历史印证和文化比较,很值得期待。
也有不在文字文学和文化的起源学而从中国抒情文学传统之书写机制上着手,专力于探讨汉语文之“文字性”潜能及其利用的思路。在这方面探讨最深入和成果最细致的当数高友工的《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他认为,汉文字自有特点,但中国抒情传统之形成其实更多地在于中国人的使用偏好:由于中国的孤立语,由于中国的象意字,也许更由于中国人对内在意象的重视,竟能用我们最古老的文字语言来象征,舍细节而取主旨,轻实证而重印象,以至现实时间反而要通过心理空间来表现,“内在经验居然能用纯形象语言的象征来保存。这是文化史的一个关键。它奠定中国语言,甚至思想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文学和美学的理想。”与前一种思路显然相同,高氏不欲将“文字性”或“文字文化”这些范畴本质化,而专从汉语文的使用状况上来把握汉文字之艺术潜能的思路。他在文字使用或功能的角度上突出了“中国的文字语言”的潜能及其在抒情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的抒情美典不是建立在日常普通交流上的,只有“在语言的运用上着重文字的内涵,而忽视文字的外指,也就是在语言的运用上不取代表而走象意的路;使语言脱离实存,集中在它的性质、本性,也就是把语言视为和音乐、抽象美术一样的媒介”,正是在这种“文字语言”的基础上,复杂的抒情才可能诞生,中国特色的抒情美典才可能生成。西方美典从美感经验的条件上看以外观和代表为主,走向对单个艺术品的分析、解释和评价,而在中国抒情美典,则以内化和象意为主,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需由形窥神,趋向主体经验和理想。因此文学和文化(包括文字、诗文、书法乃至绘画一切文人施为)都特别重视一种有限制的艺术形式,很容易孤立地来看,而非融入人际活动的现实讯息的传达。独立的书语倒与个人内心情态、活动可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书写活动心态,进一步就成为更趋极端的艺术活动类型。“文字语言”已然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从总体上看,这种研究掘进到中西比较、史论相融而抽绎原理的理论化阶段,发人兴味,也难能可贵。
上述两种思路一者着力辨析汉字特性把握传统文章体制摆脱语言羁绊的历史演化轨迹,一者把握文字潜能和主体取向之两相契合造就民族文学抒情美典的审美机制。前者聚焦于在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的起源,后者突出了主体书写对文字体制及其潜能的利用。但显而易见的是,二者都突出了中国特色的“文字语言”相对于西方语文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中的基础性地位,都把握住了传统文人对“书面雅言”和“文字语”的重视。如果再考虑到传统文化落熟期唐宋以降如古文一派如桐城文人如何利用典籍文选大力诵读以“因声求气”等等诸种功夫,中国文学和文化及其文字书写的基本面貌也就呈现出来了――真正如徐梵澄所言在《澄庐文议》中所言“两千多年来知识分子的心力皆用在文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