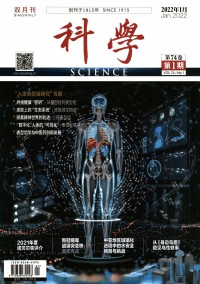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范文第1篇
较早对科学史做出层次划分并以此为基础探讨科学编史学问题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L.劳丹(Larry Laudan)。劳丹在其成名之作《进步及其问题》的第一部分中提出“研究传统”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科学进步的一种新模式。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劳丹对科学编史学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之前人更为系统、深入的阐述。劳丹在研究中发现,尽管包括阿伽西(J.Agassi)、库恩(T.S.Kuhn)和拉卡托斯(I.Lakatos)在内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都认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具有一定的内在统一性,即科学史为科学哲学研究提供思想材料,而科学哲学为科学史研究提供规范指导。然而,在对上述命题成立的分析论证中却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困难。这种逻辑困难的症结就在于,如果科学史的撰写预设了一种以其作为依据的科学哲学,而科学哲学又得依据它是否揭示出被认为是隐含于在它的指导下写成的科学史中的合理性得到证实,那么二者互为因果。劳丹认为,摆脱上述理论困难的唯一途径是对科学史做出“一种虽属基本,但却极为重要的区别,即科学史本身(可初步近似地看作是按年代排列的以往科学家的种种信念)与科学史的著作(即历史学家对科学所作的描述性和说明性陈述)之间的区别”[1]。他建议用HOS[,1]指谓实际的科学史(科学发展本体),用HOS[,2]指谓历史学家的科学史著述(写定的科学史)。劳丹进一步将HOS[,2]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历史描述的层次;二是历史说明的层次。描述性科学史主要着眼于科学事件的演变过程,是对科学家曾经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的记录、收集、整理和编纂。而说明性科学史所注目和思索的则是科学家如何去想,如何去说,如何去做。它所要回答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何以是”的问题[2]。基于上述划分,劳丹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科学思想史的性质、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层次性等重要的编史学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对科学史做出层次划分的是J.阿伽西和H.柯拉夫(H.Kragh)[3][4]。其中,后者的工作更具代表性。柯拉夫在1987年出版了《科学编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of Science)一书。在该书的第二章,他首先讨论了“历史”和“科学”的界定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科学史的层次划分。柯拉夫认为,历史[,1](H[,1])是指过去发生的实际现象或事件,我们只能有,甚至也将只能有有限的关于过去实在的知识。我们所知道的H[,1]的这部分不仅在范围上受到限制,而且还受到包括历史学家的选择、描述和假设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能直接接近H[,1],而只能接近由各种原始资料翻译过来的H[,1]的一部分。历史[,2](H[,2])是指历史研究及其成果。如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一样,H[,2]的研究对象是H[,1]。在柯拉夫看来,科学观是科学史观的基础。他认为,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对“科学”做出区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第一层次上,科学(S[,1])是指关于自然的经验或公式的陈述的集合,这种科学观强调的是科学是已完成的思想成果;在第二层次上,科学(S[,2])是指科学家的活动或行为。S[,1]是S[,2]的结果。在上述划分的基础上,柯拉夫对科学史做了两层次划分。他认为,HS[,1]是指通过对各种出版物内容的知识(技术)分析探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以及科学理论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HS[,2]是指那些把研究重点集中在科学活动同其它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历史研究,它不是以对以往科学的技术进展作为主要内容,而是要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下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5]。
劳丹对科学史的两层次划分对科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其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将科学发展本体(HOS[,1])仅仅理解为以往科学家的种种信念,即科学共同体的某种行为规范,容易产生科学史只是一部思想史的认识误导,从而使人们忽视对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思想演进与文化变迁的相关机制的研究;第二,对科学发展本体的狭隘理解使劳丹进一步认为,对科学发展动力机制的回答应从思想的层面展开,因而也就未对历史说明(说明性科学史)这一层次做进一步划分。柯拉夫坚持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统一性,并将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做了明确划分,这是对历史解释层次认识的深入。然而,由于柯拉夫对科学史研究进行层次划分时忽视了描述性科学史同解释性(说明性)科学史的区分,因此,在逻辑上缺乏应有的缜密性。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可将科学史作以下三层次划分。在第一层次上,即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将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发展本体(HOS[,1])和科学发展研究(HOS[,2])两部分。科学发展本体是指以往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全部活动或行为(科学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科学史研究是指科学史家或自然科学家对以往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活动或行为的认识、思考及其成果。该层次划分所明确界定的是科学史认识中的主体与客体,人们可以根据科学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特殊性探讨科学史认识活动与人类其它认识活动的区别与联系。在第二层次上,即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将科学史研究(HOS[,2])划分为描述性科学史和解释性科学史两部分。描述性科学史是通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按照编年的顺序描述在历史上“曾发生了什么”。解释性科学史是把科学理论以及科学活动放在特定的问题环境中和社会背景下,揭示科学理论嬗替的规律,阐明科学发展的动因和机制。该层次划分为探讨不同史学方法的功能以及各种方法之间的互补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研究成果不仅对科学史,而且对于整个史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在第三层次上,可将解释性科学史划分为科学思想史(内史)和科学社会史(外史)两部分。科学思想史重点研究科学概念、科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探讨科学思维的特点和规律。科学社会史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侧面揭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机制。该层次划分对于认识思想史与社会史在解释科学发展上的功能互补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 科学史层次划分的编史学意义
(1)科学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特殊性
受19世纪末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和人文史学中科学主义的共同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史研究中出现了唯科学主义倾向。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史家以及从事科学史研究的自然科学家认为,科学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在认识对象和方法上具有一致性,史学家通过对史料的深层次发掘和详细考证,就可以获得对以往科学发展历程的“客观”、“真实”的认识。这种实证主义的编史观主张科学史研究要效法自然科学,坚持科学史研究的惟一目的就是“如实地述说过去”,应该“述而不作”。
> 上述思潮的认识论根源是对科学史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科学史认识中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缺乏正确的理解。我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去把握:首先,从科学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区别上看,作为科学史研究对象的HOS[,1]是人类以往的科学活动,这些科学活动具有时间上的不可反演性,因此,科学史家无法直接面对这些科学活动,他们只能借助对历史遗物和作为科学活动结果的科学理论、假说的发掘、整理、分析而间接地推测和述说历史上曾发生了哪些科学活动,科学家又是如何思考的。与科学史研究不同,自然科学家能够直接面对自然界(无论是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还是借助科学仪器),而且多数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具有时间上的可反演性。它进一步保证了科学观察和实验的可重复性,从而使观察、实验既能为理论建构提供思想材料,又能为假说(或理论)的证实和证伪提供直接判据。其次,从科学史研究与其它史学研究的区别上看,科学史以以往的科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而科学活动是以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为主线而展开,其成果是科学概念的提出或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由于科学思想不具可观察性,科学史家只能依据部分占有的历史资料,在自己的思想中“重演”以往科学家的思想活动,这就更有可能使这种重演一方面夹杂着科学史家个人的思想色彩,另一方面又可能打上科学史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某些印迹。与科学史的研究不同,其它史学学科或是从政治活动、或是从经济活动、或是从军事活动的角度研究历史,这些研究虽然也要分析人们的思想动机,但思想并不成为研究的主线。认识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在科学史研究中主客体关系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由于科学思想发展是批判与继承的辩证统一,当代科学思想部分地包含以往科学思想的合理成份,这是科学史家在自己的思想中“重演”以往思想的基本依据所在,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以往科学家的思想”和作为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史家自己的思想在重演中必然要发生融合,因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科学史研究中主体与客体表现出更强的互动性与融合性。第二,由于史料的有限性以及科学史家重演结果的多样性,使史实对历史陈述或历史解释的检验具有更明显的相对性。
(2)“史”与“论”在科学史研究中的渗透与融合
将科学史研究划分为描述性科学史和解释性科学史并不是人为地将科学史这一有机整体分割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而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史实收集、整理的基础性,理论建构的必要性,以及在具体史学实践中二者渗透与融合的必然性。
描述性科学史的主要任务是发掘和整理历史资料,并按照编年的顺序对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进行客观描述。史实的收集、考证、整理是科学史研究的基础,只有掌握足够的第一手资料,科学史家才有可能按年经事纬的顺序较为完整地向现代人述说以往科学家曾经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同时,描述性科学史又为解释性科学史对历史发展中的“为什么”和“何以是”的回答提供思想材料。没有丹麦文献学家海尔伯格(J.L.Heiberg)对阿基米德手稿的发掘,当代人对古希腊数学就不会有现在的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的重大发现才改变了人们对中世纪科学的看法。在肯定史实的这种基础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历史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人们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而对历史设问的角度不同又决定了对史料的选择范围和对历史进行陈述的内容和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说,如同自然科学中“观察渗透理论”一样,在科学史研究中,“史料必定负荷规范”。因此,在科学史研究中,不受理论或规范影响的、完全中性的历史陈述是不存在的,而脱离史实的理论重建也没有任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解释性科学史存在的必要性与科学史的特定功能密切相关。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都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人们研究科学史不是“为了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它要为人类现实的科学活动服务。为此,科学史研究必须透过历史表象,探析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动力,揭示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以便为现实的科学活动提供启迪和借鉴。描述性科学史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嬗替的具体机制和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内容及方式,因此,必须在史实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理性重建,对科学与社会的作用机制进行全方位透视,以便使人类能更好地驾驭和利用科学。
(3)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在解释科学发展上的功能互补性
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它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演化、发展。因此,对科学发展的“为什么”、“何以是”的解释和说明就应从两个侧面展开。一是从理论嬗替、思想演变的角度探析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以便使当代科学家能更好地把握科学发展的趋势,合理地选择理论、方法创新的方向和切入点;二是以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为主线,研究科学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机制,以便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更有效地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在科学日益社会化,社会愈趋科学化的今天,思想史的研究和社会史的研究体现出越来越强的互补性。
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在批判历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思潮时曾指出,“对于科学来说,自然永远仅仅是现象”,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现象,而是要求史学家必须看透它并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6]因此,“史学的任务在于表明事件何以发生,在于表明一件事情怎样导致另一件事情。”他认为,在历史事件的这种“何以”和“怎样”的背后,就有一条不可须臾离弃的思想线索在起作用,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出贯穿其间的这一思想线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著名论断。[7]如果说人文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并非是已完结(死掉)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依然活着的过去的话,那么,对于科学史家来说,他所研究的思想在当代科学研究中仍在延续,科学思想史研究就更富“思想”的特性,而科学理论作为思想的直接成果又是分析以往科学家思想活动的“活化石”。因此,科学思想史研究是解释科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然而,思想的研究不能离开史实而专论思想。伽利略的思想是根据他的一系列科学实验的事实而产生的,我们可以重复他的实验,因而可以以自己的思想重演他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描述性科学史是解释性科学史的基础,而解释性科学史是对描述性科学史的提炼和升华。科学史家要从历史的残篇断片中再现以往思想的逻辑,就要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演(re-enact)他所要研究的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同时,他又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往水平上的重演,而是要提高到今天水平上的重演。也就是说,科学史家对以往科学思想的认识总是要纳入他自己的思想结构,而每个科学史家的思想又各不相同,其结果有可能(或必然)导致有多少理性重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科学思想史。实际上,就象描述性科学史不可能完全如实地述说以往一样,对科学思想的重演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科学史家个人的思想印迹或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否定科学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性。在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科学史进行重建,这些不同的重建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提供了多重视角。
科学的发展是内外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把对科学发展过程的解说仅仅局限在对思想逻辑的考察,而忽视科学思维结构、倾向同其它社会活动的作用与联系,那么,“科学史研究只能向人们提供一幅抽象的、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科学发展图景。”[8]因此,对科学发展过程的说明还必须从科学与社会互动的角度进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萨顿(G.Sarton)为代表的外史学派试图以整个文明发生、发展以及文化的演进为背景,研究不同学科间的联系以及全部精神活动与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外在论的编史观不仅批判了近代以记事为主的编史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内史学派历史视野过于狭隘的缺欠。默顿(R.K.Merton)则认为,按编年的框架,以纯经济、政治、文化要素为中心展开的研究虽然能向人们展示出科学发展中某些激动人心的历史画卷,却难以从微观层次和运行机理上阐明历史总体的深刻变动。他坚持科学发展的社会整体观,主张把科学史的探索领域拓展到社会结构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次,并将自然科学定量分析的方法和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对科学发展的研究,不仅拓展了科学史的研究视野,也实现了科学编史方法的重大变革[9]。
将解释性科学史分为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并不是说科学发展就存在两种动因、两种机制,它是科学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也是科学史研究的必经阶段。科学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科学史也必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科学史的整体性决定了对科学发展解释的内在统一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虽然在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各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对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科学史同科学哲学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尚显滞后,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学史研究的整体进展。[10][11]
参考文献
[1][2]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刘新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67-223.
[3] J Agassi.Towards an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M].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 2(1963).
[4][5] H Kragh.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Scienc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6][7]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9-42.
[8] 刘凤朝.科学编史学的思想源流与现代走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12):31-35.
[9] R K 默顿.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5-18.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科学史 科学知识社会学 内史 外史
abstract: since 1930s, most of chang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western history of science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di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about that problem, many chinese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ternal history”, and, even some scholars who focus the “external history” would insist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howeve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sk, the premise of these opinions and controversies is the opposi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t insists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sk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is view of science, there is no such independent “internal history” that is free from any social factors. in that way, the demarc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s eliminated.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ce ssk internal history external history
科学史中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已经是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十分熟悉的概念。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构成了科学编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对于一阶的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的立场出发,指出这种划分实际上是可以被消解的,而且这种消解又可以带来科学观和科学史观上的新拓展。
一、科学史“内外史”之争
在讨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内外史”划分的消解之前,我们先且按传统的标准和划分方式对“内史论”与“外史论”的含义及“内外史”之争做简单的回顾与分析。
一般而言,科学史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指的是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内史论”(in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只应关注科学自身的独立发展,注重科学发展中的逻辑展开、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论的阐述、实验的完成,以及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等,关心科学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后联系,而不考虑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默认科学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科学史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指社会等因素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外史论”(ex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应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认为这些环境影响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在研究科学史时,把科学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中。[ ](p24)
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科学史研究(包括萨顿的编年史研究在内)基本上都属于“内史”范畴。直到20世纪30年代默顿和格森发表了有关著作之后,科学史研究才开始重视外部社会因素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与传统“内史”研究不同风格的编史倾向。这才出现了科学史的“外史”转向,并引起了所谓的“内外史”之争。
具体而言,“内外史”之争的焦点在于外部社会因素是否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科学史的研究中,这些外部影响是否可被研究者忽略。其中,“内史论”者认为,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是不断趋向真理的过程;科学内在的认知概念和认知内容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且科学的真理性和内在发展逻辑往往使得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也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反,“外史论”者则坚持认为,尽管科学有其内在的概念和认知内容,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往往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其看来,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无一不对科学研究主题的变化和科学发展进程的快慢产生重要影响。
在20世纪30-40年代,因为格森和默顿等人的工作,“外史论”在科学史界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二战后期直接源于坦纳里、迪昂、迈耶逊、布鲁内和黙茨格的法国传统的观念论纲领开始流行。正如科学史家萨克雷所说,由于观念论的哲学性历史占主导地位,在50-6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很自然地注意远离任何对科学的社会根源的讨论。即使出现这种讨论,那也是发生在一个明确界定的领域,并由社会学家而非科学史家进行。[ ](p55)在这一时期,柯瓦雷关于伽利略和牛顿的经典研究奠定了观念论科学史的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外史论”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重新发挥了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势头,这与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的出现不无关系。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发展,对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开始兴起,其中,不但科学的形成过程和形式,连科学的内容也被纳入了社会分析的范围,科学知识的内容因其社会建构过程,也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科学既被看成是一种知识现象,更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可以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史家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是围绕着界定、区分和评价“内史论”与“外史论”,是在这两者彼此对立存在(虽然也有认为两者可以综合融通的看法)的前提下展开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内外史”研究的变化与争论进行分析,可以窥见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侧重点和范式变化的历史脉络。
二、国内学者的态度及其前提假定
对于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内外史”演变和争论,国内学者的态度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种是埋首于个人的具体研究,不去关心和讨论这个编史学理论问题,但潜在地却基本同意“内外史”的划分,这类学者占大多数;另一种是对该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和讨论,当然这些学者在人数上不是很多。在这类学者当中,通常极端的“内史论”和“外史论”都不被他们同意,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坚持的二者的综合运用。
具体而言,在第一类学者看来,具体的一阶研究更为重要,讨论“内外史”之争问题往往是“空谈理论”,对于实际的科学史研究没有多大意义。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国内科学编史学研究相对来说一直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其价值和意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值得注意而且也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这些一阶的研究中,“内史”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外史”。在许多学者看来,科学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科学史描述的就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少数“外史”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描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速度、形式的影响上,把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一个外在的背景环境来考虑,尚未触及到社会因素对科学内容的建构与塑型的层面。
在第二类学者中,80年代末就已经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指出科学中的多数重大进展都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促成的,认为在“内史”和“外史”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 ](p39-47)随后一些学者较为系统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外史”转向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通过对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自1913年到1992年的论文和书评进行的计量研究,发现科学史的确发生了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内史研究为主,80年代之后以外史研究为主。[ ](p128)此外,他们还就“内史”为何先于“外史”、“内史”为什么转向“外史”、“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究竟如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国外学者关于“内外史”问题的观点,并认为“内外史”二者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 ](p27-32)其理由在于“极端的‘内史论’会使科学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动力和基础,无法解释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极端的‘外史论’又会使科学失去科学味,而显得空洞。”[ ](p6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未对“内外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但从不同的关注角度出发,大多都认为科学史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必须进行某种综合。[ ](p14,p97-98)
无论是不去讨论“内外史”问题,还是总结国外学者的观点并主张“内外史”综合,第一类学者和第二类学者都默认了“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方式,且大多更为看重“内史”。如果对他们的观点做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在背后支撑着这种划分及侧重的仍然是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对实在的揭示和反映,它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不受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科学的历史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出现,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这种科学观指导下的科学史研究就必须揭示出科学发展的这种“内在”发展逻辑,揭示科学的纵向的“进步”历史。例如,有学者在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科学、科学史的发展来谈“内史”先于“外史”的合理性时,提到“科学史一开始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科学史事实在(包括科学家个人思想、科学概念及理论发展)的内部因素及产生机制的研究。而这一科学史事实在内部机制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区别于别的学科的特质和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石。也就是说内史研究是科学史的基础和起点;”“外史是在内史研究的基础上随着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增大而非研究外史不可的地步时才逐渐从内史中生长出来的。”[5](p28)这些观点大致包含了这么几层含义:首先,科学史事实在内部蕴含了科学发展有其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内部机制、逻辑与规律;其次,对这些科学发展规律、机制及内部自主性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学科的特性;最后,注重科学内部理论概念等的自主发展的“内史”研究先于“外史”研究,“外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内史”的补充。尽管一些作者坚持一种“内外史”相结合的综合论,但仔细分析起来,其“外史”仍然没有取得与“内史”并重的位置。而且,其强调的“外史”研究也只是重视“分析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如哲学、社会思潮、社会心理、时代精神以及非精神因素诸如科学研究制度、科学政策、科学管理、教育制度、特别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科学发展的阻碍或促进作用。”[5](p32)此外,从一些学者的总结性论文中可以发现,在那些围绕着“李约瑟问题”而讨论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诸多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p110-116)在这里,种种社会因素只被看成是科学活动的背景(尽管可能是非常重要乃至于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其构成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方法、程序以及科学结果的可检验性保证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对科学的历史的研究,必然要以研究科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发展为主要线索,科学史仍然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科学活动的历史。
由此可见,对“内史”与“外史”的传统划分的坚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综合”运用,都是以科学的的一种内在、客观、理性及自主独立发展为前提假定的,只有基于这样的科学观,才可能使得“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分别得以成立,“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才成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科学史界“内史论”与“外史论”的争论之所以长期持续,原因可能恰恰在于这种科学观本身。它使得研究者或者片面强调“内史”,完全否认“外史”研究的合法性;或者虽偏重“外史”,却仍只将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背景来考察;或者虽强调“内外史结合”,却仍以“内史”为主,“外史”为辅。要结束这种争论,就必须在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层面进行超越。科学知识社会学正是基于对这一科学观和前提假定的解构,消解了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内外史”划分的消解
科学知识社会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英国,它以爱丁堡大学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爱丁堡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巴恩斯、布鲁尔、夏平和皮克林等。ssk明确地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要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其中,巴恩斯和布鲁尔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尤其是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四条“强纲领”原则。除此之外,ssk的学者如谢廷娜、夏平和拉图尔等,在这些纲领下做了大量成功的、具体的案例研究。
“爱丁堡学派”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是为了与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相区别。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做社会学的分析的,因为它们只受内在的纯逻辑因素的决定,它们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 ](p68-69)在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中,科学是一种有条理的、客观合理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社会活动,科学的发展及其速度会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科学家必须坚持普遍性、共有性、无私利性等社会规范的约束。[ ](p267-278)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首先不赞成曼海姆将自然科学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的做法,他们认为独立于环境或超文化的所谓的理性范式是不存在的,因而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不但可行而且必须,布鲁尔对数学和逻辑学进行的社会学分析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p133-249)由此也可看到,ssk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进一步将科学知识的内容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范畴。在ssk看来,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它们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达,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局域知识。通过各种修辞学手段,人们将这种局域知识说成是普遍真理。科学知识实际上负载了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它往往是由特定的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它与其他任何知识一样,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9](p2)
ssk与传统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上述区别直接反映在其相关的科学史研究上,表现为对“内外史”的不同侧重和消解。传统知识社会学在自然科学史领域仍然坚持的是“内史”传统,科学社会学虽然开始重视“外史”研究,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时至今日它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社会分层、社会影响、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在其看来,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后者超出了社会学家的探索范围。[ ](p38-39)可见,传统的科学观在科学社会学那里仍没有被打破,科学“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依然存在,二者的界限依然十分清晰。但ssk却坚持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主张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12](p38)这样一来,因为连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那种纯粹的所谓科学“内史”便不复存在,原来被认为是“内史”的内容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因素无孔不入的影响,从而,“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就被消解了。正如巴恩斯所说,柏拉图主义对于科学而言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柯瓦雷本人的观点也含糊不清。[ ](p150)又如布鲁尔就开尔文勋爵对进化论的批判事件进行分析时指出的那样,该事件表明了社会过程是内在于科学的,因而也不存在将社会学的分析局限在对科学的外部影响上的问题了。[ ](p6-7))。
ssk关于科学史的内在说明和外在说明问题也有直接的分析。其重要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对“知识自主性”进行批判时,就对科学自身的逻辑、理性说明和外在的社会学、心理学说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讨论。他指出,以往学者一般将科学的行为或信仰分为两种类型:对或错、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并往往援引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原因来说明这些划分中的后者,对于前者而言,则认为这些正确的、真的、理性的科学之所以如此发展,其原因就在于逻辑、理性和真理性本身,也即它是自我说明的。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往往认为这种内在的说明,比外在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说明更加具有优先性。[14](p9)
实际上,布鲁尔所要批判的这种观点代表着ssk理论出现之前,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里的某种介乎于传统实证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科学编史学思想。其中,拉卡托斯可以被看成是一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将科学史看成是在某种关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理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的理论的框架下的“合理重建”,是对其相应的科学哲学原则的某种史学例证和解释,也就是说科学史是某种“重建”的过程,而非科学发展历史的实证主义记录或者某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历史;另一方面,拉卡托斯又认为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属于一种内部历史,其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只有当实际的历史与这种“合理重建”出现出入时,才需要对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出入提供外部历史的经验说明。[ ](p163)也就说,科学发展仍然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理性和真理性,科学的内部历史就是对这种逻辑性和合理性方面的内部证明,它具有某种逻辑必然性;而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仍然外在于科学的合理性和科学的逻辑发展,仍然外在于科学的“内部历史”,是科学史家关注的次要内容。但这种历史观内在的悖论在于,那种纯内史的合理重建,实际上又离不开科学史家潜在的理论预设,因而是不可能的。
正如布鲁尔所说,考察和批判这种观点的关键首先在于认识到,它们实际上是把“内部历史”看成是自洽和自治的,在其看来,展示某科学发展的合理性特征本身就是为什么历史事件会发生的充分说明;其次还在于认识到,这种观点不仅认为其主张的合理重建是自治的,而且对于外部历史或者社会学的说明而言,这种内部历史还具有优先性,只有当内部历史的范围被划定之后,外部历史的范围才得以明确。[14](p10)实际上,布鲁尔强调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建构性,恰恰是基于对这种科学内部历史的自治性和随之而来的“内史”优先性假定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又导致了科学编史学上“内外史”界限的模糊和“内外史”划分的消解。
四、其他相关分析与评论
ssk之于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以及随之可能带来的科学史“内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引起了国内少数学者的注意,但他们对此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sts研究,就其个人看法,缺乏思想的深度,偏重了科学外部的社会性分析,如能注入科学思想的成分和哲理性的分析会更好些。[6](p63-64)此外,还有些学者肯定了ssk研究的价值,并从中看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和默顿学派对待科学合理性和科学知识本性的态度的不同,但认为在一定意义上ssk是用相对主义消解了在科学理性旗帜下“内外史”观点之争。[ ](p47)实际上,认为社会学的分析缺乏深度,本身就是在对科学知识、科学理性与内在逻辑性不可做社会学分析的观点的一种认可,并潜在地赋予社会学的“外史”研究以较低的地位。认为“内史”与“外史”的划分必须存在,认为ssk对“内外史”之争的消解来自于其相对主义的科学观等等,实际上都反映了对传统的科学理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性、真理性与实在性的坚守,这种坚守又意味着对科学内在的发展逻辑做“内史”考察是可能的,并且是第一位的。
然而,在国际学术背景中,后库恩时期研究的整体趋势确已开始走向了将“内史论”和“外史论”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这种结合更多地是将“内史”与“外史”的界限逐渐模糊和消除。例如,除了ssk的理论可以消解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之外,类似地,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同样可以对这一划分进行解构。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被政治家误用或滥用,而是社会政策的议程和价值已内在地包含于科学进程的选择、科学问题的概念化理解以及科学研究的结果中。[ ](p81)因而,科学本身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为此也就不存在着对科学内在独立逻辑的某种真理性的挖掘,也不存在关于社会因素加于科学发展之上的某种作用关系的考察。正如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哈丁所认为的,“内史论”与“外史论”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两者之间的共同特点是赞同纯科学的认知结构是超验的和价值中立的,以科学与社会的虚假分离为前提,因此他们并没有为考察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和延续对科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留下认识论的空间。[17](p82)
这种整体趋势在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也有实际的体现。在李约瑟去世后,2000年,由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美国权威学者席文负责编辑整理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第6分册“医学”得以出版,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此卷此分册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其它已经出版了的各卷各分册有明显的不同。席文将此书编成仅由李约瑟几篇早期作品组成的文集。对于席文编辑处理李约瑟文稿的方式,学界当然存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席文的做法确也明显地表现出他与李约瑟在研究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他在为此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系统地总结了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的研究成果与问题,并对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综述,提出了诸多见解新颖的观点。在他那篇重要的序言中,席文明确指出:“由于对相互关系之注重的革新,内部史和外部史渐渐隐退。在80年代,最有影响的科学史家,以及那些与他们接近的医学史家,承认思想和社会关系的二分法使得人们不可能把任何历史的境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p1-37)
“内史”与“外史”的划分、“内史”与“外史”何者更为重要以及“内史”与“外史”二元划分的消解,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科学观,在这些不同的科学观下又产生了科学史研究的不同范式和纲领。“内史”的研究传统在柯瓦雷关于16、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人的研究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外史”的研究方法则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的互动方面,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而ssk的案例研究则充分体现了打破“内外史”界限之后,对科学史进行新诠释的巨大威力。尽管科学哲学领域对于ssk的“相对主义”、“反科学”以及围绕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仍在持续,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ssk对“内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可以被看作是打通了“内史”和“外史”之间的壁垒,形成了一种统一的科学史。在这种新的范式下,科学史研究能够大大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给予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诠释。
[1 ]刘兵.克丽奥眼中的科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2 ]吴国盛编.科学思想史指南[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3 ]邱仁宗. 论科学史中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间的张力[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1).
[4 ]魏屹东,邢润川.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1913-1992年)内容计量分析[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
[5 ]魏屹东. 科学史研究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
[6 ]魏屹东. 科学史研究的语境分析方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5).
[7 ]江晓原.为什么需要科学史——《简明科学技术史》导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肖运鸿.科学史的解释方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3).
[8 ]胡化凯. 关于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的几种观点[j].大自然探索,1998,(3).
[9 ]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0 ] r.k.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11 ]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m].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12]刘华杰.科学元勘中ssk学派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哲学研究[j].2000,(1).
[13 ]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m].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14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15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6 ]赵乐静,郭贵春.科学争论与科学史研究[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4).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范文第3篇
>> 理工科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探索 简论理工科大学生科技素养的培养 理工科大学生科技创新素养提升理论与实践研究 工科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理工科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探索 理工科大学生应重视公关素质的培养 论理工科大学生哲学素质的培养 浅论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理工科大学生写作能力培养的实践途径 理工科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 理工科大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的培养 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途径 理工科大学生科技英语翻译能力分析 基于问题导向学习模式的理工科大学生学习方法研究 工科大学生数学思维的培养 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创新模式构建 理工科大学生艺术素养教育创新模式构建 以创新基地为依托的理工科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研究 从就业探究理工科大学生培养模式 理工科大学生翻译能力培养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5] 耶鲁校长:本科教育核心是通识[EB/OL].(20150915)[20160116]. http:///a/20150915/065846.htm.
[6] M・尼尔・布朗,斯图尔特・M・基利.走出思维的误区:批判性思维指南[M].张晓辉,马昕,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7] Peter A Facione. 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M]. Newark: The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1990:2.
[8] 武宏志,周建武.批判性思维――论证逻辑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
[9] 文森特・鲁吉罗.超越感觉:批判性思考指南[M].顾肃,董玉英,译.第8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1.
[10] 钟启泉.“批判性思维”及其教学[J].全球教育展望,2002(1).
[11] 罗清旭.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4).
[12] 郑祥福,李润洲.培育批判性思维:大学教学的重要维度[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13] 布鲁克・诺埃尔・穆尔,肯尼思・布鲁德.思想的力量[M].李宏昀,倪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1.
[14] 庞思奋.哲学之树[M].翟鹏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5] 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M].张卜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6] 罗伯特・沃尔夫.哲学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0.
[17] 饶毅.缺乏科学精神是我们文化的重大缺陷[EB/OL].(20151218)[20160105].http:///mrdx/201512/18/c_134930602.htm.
[18] 桑新民,李曙华,谢阳斌.“乔布斯之问”的文化战略解读――在线课程新潮流的深层思考[J].开放教育研究,2013(3):31.
[19] 汤广全.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德里克・博克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J].教育学术月刊,2012(3):11.
[20] 桑新民.学习科学与技术――信息时代大学生学习能力培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1] 桑新民,谢阳斌.21世纪:大学课堂向何处去――“太极学堂”的理念与实践探索[J].开放教育研究,2012(2):921.
[22] 刘长锁.摒弃教育中的急功近利[N].光明日报,20120530(14).
[23] 拉塞尔・L・阿克夫,丹尼尔・格林伯格.翻转式学习:21世纪学习的革命[M].杨彩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
[24] 冯增俊.香港高校通识教育初探[J].比较教育研究,2004(8):68.
[25] 张志伟,欧阳康.西方哲学智慧[M].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
[26] 罗伯特・所罗门.哲学的快乐:干瘪的思考VS.激情的生活[M].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7] 伯特兰・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M].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8] 斯特拉・科特雷尔.批判性思维训练手册[M].李天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
[29] 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M].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565.
[30]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8.
[31] 林德宏.科学思想史[M].第2版.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379.
[32] 蒙艺,贺加,罗长坤.美国医学课程改革历程中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变迁及其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13(4):9296.
[33] 李喜先.21世纪100个交叉科学难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序言.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学 存在论 数学因素
abstract: have 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shown the intrinsic process of 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science? no. this essay tries to analyze science’s own intrinsic process of coming into being from the ontological viewpoint in accordance with heidegger's thinking.
key words: science ontology mathematical element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或者说近现代科学(modern science)。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讨论已使我们对近现代科学的产生过程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其中仍有许多难解之谜。“既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此发达,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个广为关注的李约瑟难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说明我们对近现代科学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详细了解科学史上的每一个事实并不能保证我们理解了科学史,从逻辑上严密精确地分析科学的理论结构、研究过程和认识方法并不能保证我们理解了科学,而对于科学的社会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把握也无法保证我们理解科学本身。
科学以万物为研究对象,同时又是人的特定的存在方式。科学体现着人与万物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存在自身演历的必然结果。从存在论的视角考察近代科学是理解它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是一种最为彻底的方式,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提供出对科学的内在理解,而其它的方式只是把科学作为一个外在的对象,对它进行外在的研究。
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虽然没有把科学作为他们特定的专题研究对象,却从存在论的层次深入地思考了科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克尔曼斯(joseph j. kocklmans)等美国学者沿着海德格尔等人的思路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把这类研究叫作“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现象学”(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of the natural sciences)或“自然科学的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在国内,吴国盛首先关注到对于科学的存在论研究,并把这类研究称为“科学存在论”(ontology of science)或“第二种科学哲学”1。由于现象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指的是思考存在问题的本源性方法,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是存在论层次上的解释学,所以上述不同的称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对科学的存在论研究或科学存在论尚未引起学人的足够重视,但它是真正理解能够标志我们这个时代本质的科学现象所必需的。科学哲学作为对科学的哲学探讨应该推进到科学存在论领域。本文试图在海德格尔等人工作的基础上,从存在论的角度对近代科学的产生问题加以初步的考察。
一、古希腊哲学为近现代科学所做的最初准备
近现代科学产生的存在论根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那里发生的思想转变早早地为近现代科学做了最初的准备。
1. 古希腊早期的思想家对存在有一种源始的领悟。他们对于世界的开启、万物的敞开深有感触,原来处于掩蔽状态的神秘的万物竟然去蔽而公开出来,存在者存在着。早期思想家惊异于存在者的存在,纵身其中,应和着世界的显现。他们把这种开启、显现和公开叫作physis(自然),他们的主要著作均以“论自然”(peri physeos)为名。
后来,罗马人把physis译为natura。natura又被译为英语的nature、德语的natur等。但今天人们理解的“自然”已与希腊早期的physis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我们把早期希腊哲学,即前苏格拉底哲学,叫作自然哲学,是有道理的。但那时的自然哲学还不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低级形态,与近代视野中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
古希腊早期的physis不是后来那种与人对立的“自然”,它针对存在者整体,包含着人和神,也包含着政治和伦理。physis的基本意思是“生长”。但并非指量的增加,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发展或变化。“生长”乃是涌现,即自行开启并驻立于自身,意味着进入无蔽境界,逗留于澄明之中,把自身展示出来。这是万物的现身。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干脆把physis与存在等同起来。作为存在的physis就是从遮蔽中绽出、公开而又持留、逗留,即现象,phainesthai,源始意义上的现象。作为现象的physis从隐蔽中走出,进入无蔽状态,这就是aletheia,真理,源始意义上的真理。
physis与存在的一致性能使我们很好地理解巴门尼德的《论自然》为什么以存在问题为核心。但是巴门尼德极力强调存在的不变性和永恒性。这一点为柏拉图所继承,并走向一个不同的方向。
2. 柏拉图用idea和eidos表示存在或physis。physis,涌现,现象,这个涌现出来的所“现”之“象”不就是事物呈现出来的idea和eidos(外观)吗?事物的外观就是它赖以显示自身于我们面前的“样子”,它赖这个“样子”并以这个“样子”而存在,而现身,而涌现(physis)。所以,physis必然连带出一个外观,idea。通过idea可以把physis讲得更清楚,更易于理解。
然而,physis是自行显现,而idea是显现出来的外观,即显现的结果。当柏拉图用idea代替physis时,就用显现的结果代替了显现本身。显现本身被忽略了。另一方面,我们极有可能看到同一事物的不同外观,但只能有一种外观与事物本身一致。idea当指这种真实的外观,而且它未必就是眼睛所看到的。严格来说,真实的idea,即通常译为“理念”的idea,只能通过灵魂才能把握。这种idea是事物的本体(存在本身),感官所感觉到的外观则只是本体的分有或模仿,或者干脆是假的,总之是有缺陷的。可感世界是与作为本体的idea世界相对立的。在physis变成idea时,phainesthai也就成为与本体(存在本身)相对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在柏拉图的idea中,数的因素特别地突出出来。可感世界只是意见的对象,idea作为可知的世界才是知识的对象。对idea的认识形成知识。知识是永恒的、可教可学的。在希腊语中,可教可学的东西又叫作ta mathemata,数学因素。毕达哥拉斯已经把数作为万物的本原了,当柏拉图把idea作为本体时,数的因素也进入了本体(存在)之中。作为本体的idea是数学性的东西,数学因素是事物的本质,是“存在本身”。同时,数学因素也是我们的灵魂本来拥有的,所以我们才可以不依靠感官就能把握它。这样柏拉图就把数学因素当成了人与万物的共同本质,只有依靠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3. 亚里士多德继续把追求知识当作灵魂的崇高事业。这种对知识的追求也同样改变了physis和存在的源初含义,不过与柏拉图有所区别。亚里士多德对存在和自然的考察过程是这样的:
⑴存在有多种意义,但最根本的意义是ousia,实体。
⑵自然(physis)有多种意义,但最源始的、最主要的意义是指,具有运动本原的东西的实体(ousia),自然就是某种ousia。
⑶ousia有多种含义:①是其所是;②普遍;③种;④hypokeimenon(载体、基质、主体、根据)。其中hypokeimenon最有资格充当ousia。hypokeimenon可能是质料,可能是形式,也可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结合,但它应该是内在于某物的形式。
这样,亚里士多德把存在和physis归结为ousia,把ousia归结为hypokeimenon。ousia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既保留着存在和在场者之在场的意义,又表示在场者在其外观的是“什么”中。亚里士多德在上述所列的ousia的第一种含义可以体现出在场者之在场的意义,而后三种含义都已经是“什么”了,是经常的、现在的、永恒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主要以hypokeimenon表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和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原因,而原因可以归结为四类,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其中后三类其实是一类,可以用形式因或目的因表示。hypokeimenon就是内在于事物中的形式因或目的因,是事物最重要的原因,是根据、主体。
柏拉图把存在本身和physis的本质理解为idea(理念),亚里士多德则最终归结为作为原因的hypokeimenon(根据、主体)。随着physis变为idea和hypokeimenon,希腊人把握它们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同步的变化。这种变化就体现在logos一词的演变之中。
4. 希腊词logos的最初含义是指万物遵循的尺度、比例或平衡关系,是一方对它方的关系,是事物把各种关系和比例聚集于一身从而呈现自身。海德格尔据此把logos的源始含义理解为“采集”,并在对赫拉克利特残篇的解释中印证了这种理解。作为采集的logos不是杂乱的堆积,而是相互协调使之和谐地涌现出来,“是把纷然杂陈与相互排斥者扣入一种归属一体的境界中”2。所以,logos最初与physis具有统一的意义。logos就是存在者的内在的集中和呈现,就是存在。
人在存在中建立自己的根基。人响应存在,与存在相和谐。所以人的本质就在于听从logos。听从logos就具有智慧。而听从logos就是以logos的方式行动,即以采集的方式行动。logos据此也指人的采集。人通过采集而承纳存在,展示存在,归属于存在。这就是源始的思,noein。当巴门尼德说“思与存在是同一的”的时候,他的“思”就是这种意思。
由于logos就是聚集而呈现,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以它又引申为语言。人与存在者以logos的方式存在,就是在语言中存在,“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对存在的响应就是对语言的响应,也是对智慧的响应。这种响应即爱,philo。对于存在、语言和智慧的响应或爱就是philosophia,哲学。
但是,以logos(语言)的方式的响应或爱,总要表现为人的说以及说出来的话。这种说以及说出来的话还可以被重复。在重复中就有可能失真,即仅仅是人云亦云,而没有真正响应存在。另外,说出来的话也可能与存在本身并不一致或自身相互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语言的保真,需要挽救对存在的响应或爱。于是,原来与存在自然而然的和谐一致就变成需要有意追求的了。logos在人身上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东西。
当存在和physis变成idea和hypokeimenon,当philosophia由与智慧和存在的源始协调变成对知识的有意追求之时,logos就由采集、说话、语言变成了逻辑或理性。源始的思在这时就成为理性思维或逻辑思维。另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由于存在、physis成为ousia和hypokeimenon,对应着实体的种种状态、大小、关联等,即对应着实体和主体的种种规定和属性,logos也就成了种种范畴(kategoria)。
从古希腊早期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的完成时期,原来相互统一的physis和logos分离成了相互对立的两种东西:一方是作为本体(“存在”)的数学性的idea或作为原因和根据的hypokeimenon,另一方是作为逻辑、理性或范畴的logos。原来作为响应存在的思(noein)也变成逻辑思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活动所引起的变化“是如此地具有决定性,以至于它表明了希腊思想的终结,同时这终结间接地为近代准备了可能性。”3 也就是说,这种变化从形而上学上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准备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二、希腊科学(知识)的演变
1. 近代科学正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所提供的视域之内逐步蕴育出来的。对于柏拉图,数学性的理念世界是要认识的对象;对于亚里士多德,原因和根据是要认识的对象。人的存在方式在这里突出地表现为求知,“求知是人的本性。”4 只有作为求知的人的存在方式才有可能创造出科学。
但古希腊的“知识”(episteme)与近代的科学(science)之间还有着本质的差异。尽管episteme已不同于古希腊早期的智慧(sophon),它“仍然以对存在者的希腊式的基本经验为基础。”5
episteme源于epistamenos,知其然的人,又指胜任、擅长某事的人。胜任即theoretike,能够思辨。思辨即theorein,指注视着某种东西并将所见收入眼帘。6 动词theorein的主词theoria,我们又译为“理论”。“理论”就是纯粹观照。亚里士多德把与存在者本身的关联称为theoria--纯粹观照。theorein由thea和orao构成。thea的意思是,在其中表现出某种东西的外观、外形、外貌,即柏拉图的eidos。orao的意思是观看某物,看到某物,观察某物。两者构成的theorein就指观看到存在者在其中显现的外观,并保持对此外观的看。theorein和theoria具有神秘和高尚的意义,以theorein规定自身并献身于其中,就是一种观看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观看存在者的纯粹显现。但是,这种观看、思辨的生活,就是最高的“做”。7
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知识和理论是与techne密不可分的。techne不是功利性的技术,而是获得真理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在取得真理的五种方式中,把techne列为首位。8 techne与知识、理论等都与实用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人的自由的求知,代表着人的完善状态,其中照射着诸神的在场。9 所以,从理论、知识和techne中仍可透露出人与显现的牵连以及人对显现的敬畏。它们与近代科学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罗马人以contemplari翻译theorein,用contemplatio翻译theoria,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contemplari意味着将某物划分成一块并在其中造起围栏,contemplatio则显示了切入、分割式的观看,针对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所做的那种有安排的干预性过程在认识中得以突显。10 近代科学的理论则进一步加强了对实在的加工、干预和支配。理论就是对象化:把实在纳入科学的视野,使之成为科学的特定对象。实在作为对象化的对象,就与古代知识的对象有了原则性的区别。
2. 希腊时代以后,先是关注彼岸世界数学性idea的柏拉图主义在基督教世界中占居统治地位,后来亚里士多德主义逐渐代替了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哲学更注重研究实际的事物,鼓励了经验的研究。但是,不断增加的经验知识又越来越与依附于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发生冲突,摆脱基督教体系之内的僵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显得越来越必要。这时已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发现和研究更多的希腊文献,人们重新发现了柏拉图。柏拉图主义再次流行起来。但这时的柏拉图主义不再否定世俗世界和可感世界,而是在肯定它们的背景下,追求事物背后的数理结构或数学规律。它最终伴随着人的本质的变化而导致了自然的数学化和知识的数学化。
人的本质在古希腊早期体现为承纳存在,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体现为追求知识的神圣的生活方式,在中世纪则由上帝规定着。它们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由人自身决定,而是另有所“本”。然而,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的本质逐渐由人自身规定,人自身就是人的“本”。而且人自身还成为一切存在者的根据,人的欲望和需求是最高的目的,人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准则。
普罗泰戈拉曾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但他的人是指具体的人的存在。人的具体的存在是对存在之无蔽状态的限制,这种限制性的“尺度”承诺“存在者的遮蔽性及存在者的在场或不在场面对任何决断都依然保持着的岿然不动性,也同样承诺持久在场之可见外观在决断面前的岿然不动性。”11 近代的人则建立起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必须服从的强硬的尺度。希腊人作为“尺度”表明了人的有限性和存在的无限性,而近代人作为尺度则表明了人的无限性和存在的受限制性。
人的无限性使人成为主体,存在的受限制性使万物成为对象。“主体”一词在拉丁语中是subjectum,它是对希腊词hypokeimenon的翻译,意指载体和根据。subjectum可以指称一切存在者。任何存在者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是subjectum,主体。但是,在人的解放的背景下,笛卡尔使人变成了唯一的主体。
三、笛卡尔哲学与近现代科学的产生
1. 我们如何确定自身与它物的存在呢?人的思维活动清晰明白地表明了人的自我的存在,思维和意识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它保证了作为思维和意识的主体(载体)的自我的存在。自我这个subjectum首先被确定下来,它的存在和如何存在也构成了其它一切存在者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示范。因为其它存在者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标准就在于,它们是否象自我的存在及存在方式这样清晰明白,亦即是否具有自我这样的确定性。
人对其它事物的感觉是不可靠的,思维必须同时担当起确定其它subjectum的重任。在笛卡尔时代,思维早已不再是与存在共属一体的对存在的承纳和应和。思维即理性活动,亦即表象(representing)。表象不是对在场者之在场(presenting)的直接领悟,而是在场(presenting)的一种变式,是对在场者的把握和掌握,是把存在者限定到面前来并对之发动进攻,是从自身出发并以自身为根据向着被限定到面前的存在者领域的进发。在表象中,存在者不再是在场者,而是被限定到面前的坚固地站立着的对立物,即对象(object)。因而,表象就是进攻并控制存在者的对象化(objectifying)。“表象就以这种方式把一切共同逐入被如此赋予对象性的统一体中。”12
自我通过表象活动使一切纳入其视野的存在者对象化了,存在者在对象化中得以确定。在这种确定过程中,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存在者作为自我的对象而存在着。不具有对象性的存在者,即没有被对象化的存在者,因其没有被表象而不具有存在的特性,亦即是不存在的。这样,其它的subjectum 就不再是subjectum了,因为它们的根据不在自身,而在于自我。它们只能是对象、客体(object)。原来宽泛的subjectum现在专指作为自我的人。人成为别具一格的优越的subjectum,并因而成为唯一的主体(subject)。笛卡尔使subjectum分裂为 subject和 object,导致了主客的二分和对立。这种二分和对立既是近代哲学的特征,也是近代的时代特征,并同时构成近代科学赖以产生的基础。
2. 万物作为对象,由人确定其是否存在及如何存在,人作为主体就成为万物的中心和尺度。但只有存在者的存在及存在方式具有可靠性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主体的中心地位。表象着的自我在实施对象化的过程中要求着可靠性,并指向可靠性,“这种可靠性就在于,有待表象的任何事物和表象自身一起被逐入数学性的idea的清晰明白之中并凝聚在那里。”13
自我作为主体在表象存在者时只有通过数学的计算才能使存在者的存在得以真正确定。只有预先计算出存在者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种种状态,才使存在者真正成为可靠的对象。计算是理性思维的本质所在,主体的表象方式就是去计算事物,表象活动的对象化过程就是数学的计算过程。如此这般通过计算思维而使存在者的存在在这种对象性中被寻求之际,就出现了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把对自然的研究变为固定的程序,预先要求着一种基本的敞开区域。通过对存在者的筹划(projection),研究程序就依附于并固执于这个敞开区域。数学因素是这个敞开区域的基本特征,特定的时空观、物质观和运动观是这个敞开区域预先规定的基本框架。对于任何事物,都必须从这种数学性的基本框架出发加以认识。这种数学性的基本框架使得对自然的认识具有严格性和精确性,使得自然在测量和计算中被表象。
近代科学的敞开区域预先规定的基本框架决定了近代科学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数学的方法。我们常说实验和数学是近代科学的两大基础,但近代科学的实验本身就是数学的,它是在基本框架的指导下,由数学因素要求出来的,因而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实验”。罗吉尔•培根的“实验”不属于近代科学,因为它不是数学性的。
数学因素的优势地位在17世纪正式确立起来,制造出主客二分的笛卡尔同时也赋予近代科学以数学本质。在笛卡尔那里,数学是指广义的数学理性或数学因素。它是普遍的、决定性的学科,“是一切学科的源泉”14 所以数学成为理性的代名词,理性就是数学理性或数学因素。它集中体现于对公理化知识的欲求之中。笛卡尔说:“方法,对于探求事物真理是绝对必要的。”15 而“全部方法,只不过是:为了发现某一真理而把心灵的目光应该观察的那些事物安排为秩序。”16 这种排序就是使之公理化,亦即首先确定最高的第一性的公理,然后从中引出各种事物的存在和属性,引出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数学因素不仅仅体现于一般的科学方法之中,它注定要转化成实在的数理规律,成为人和其它存在者的形而上学规定。只有数学性的实在才是可以接受的真实的实在。主体对事物的表象因数学因素而使事物的对象化得以实现。
数学因素的本质就在于预先开启一个事物在其中现身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公理性地筹划出对事物的设定,敞开事物的基本轮廓,并以此为尺度界定所有事物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确定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数学因素导致近代狭义数学的形成和发展,并使之应用于其它近代科学之中。实际上,“近代自然科学、近代数学和近代形而上学都是源出于广义的数学因素这个同一根源。”17
数学因素作为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在伽利略那里得到最终的定形,在笛卡尔那里又获得形而上学的形式,在牛顿那里则发展出完整的科学形态。牛顿力学作为数学因素在近代科学中的首次完整体现,标志着近代科学的正式产生。在牛顿定律的发现以及被确立为基本定理的过程中,“包含着一场革命,它属于人类思想的最伟大革命”。18
* * * * * * * * *
从古希腊思想的开端到近代,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化:从建基于存在者的自行公开、自身涌现,亦即与存在的源始协调,到“观看者的生活方式”,亦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纯粹求知方式,最后变成主体性的生活方式,亦即主体以自身的数学理性表象事物的对象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事物或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同步的根本性变化:从“存在”,physis, phainesthai到idea, hypokeimenon,再到被主体对象化的对象。这样的变化过程就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历史。
注释:
1、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又收入吴国盛《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沈阳)1998。
2、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第135页。
3、5、11、12、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harper & row, 1977, p143, p143, p147, p150.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北京)1991,第1页。
6、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597页。
7、10、martin heidegger, "science and reflection",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harper & row, 1977, pp163-4, pp165-6.
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第117页。
9、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二章。
13、martin heidegger,“the word of nietzsche:‘god is dead’”,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harper row, 1977,p89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自然观;形而上学;前提性知识
Abstract:The idea of nature is not a result of the science,but root in the social cultural field . It was the function of the prerequisite knowledge that it played science. The ideas, such as natural order, harmonious unifying, simplicity, etc. have influenced characteristic and form of science for modern times.
Key words: The ideal of nature, metaphysics, prerequisite knowledge
自然观由于其传统定义与自然科学的目的和内容有相当大的重合,人们又习惯于用自然科学的发展解释它的流变,于是给人们造成了一种“科学世界中的自然图景”的印象。在自然科学不断进步的今天,人们就对继续从事自然观的研究产生了怀疑。
在笔者看来,自然观的形成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自然科学成果的总结,自然观的内容根植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诸如自然秩序、和谐统一、简单性等观念都是对社会文化概念的推广,它们作为自然观的内容深刻影响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形式和特点,对自然科学起到了一种前提性知识的作用。因此,在自然科学不断进步的今天,不仅不能放弃对自然观的研究,反而要加强对它的内涵和功能的阐释。
一、 自然观的划界
为自然观划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涉及到自然观与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的关系。要澄清自然观的独特内涵,就必须追溯自然科学独立后,自然观又在自然哲学内部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的历史。
近代以来,随着实验科学的兴起和数学方法的应用,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探索自然的排头兵。哲学的研究重心也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但是,本体论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自然哲学仍然是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这个研究领域却在“自然观”和“形而上学”两条路线上前进。
就自然观而言,由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熏陶,逐渐形成了有关自然界的有序、和谐、统一、服从简单性原理等观念,这种自然观深刻影响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思维,特别是在自然科学进入新的领域、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科学家都要从这些观念出发寻求解决的途径,例如笛卡尔、康德、拉普拉斯有关星云的假说。而就形而上学来说,有些哲学家则孜孜不倦于追求“关于普遍性的、关于支配宇宙最普遍原则的知识”[ ]。与神学不同的是,这些哲学家选择了利用自然科学成果继续营造包罗万象的自然体系的方式,黑格尔就是他们的典范。但是人们通常不仔细区分本体论的这两条路线,而是一概地称之为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这种混淆就给自然观带来了 “连坐”的厄运。
19世纪,孔德和马赫开始反对形而上学;20世纪初,逻辑经验主义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认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都是无意义的,哲学对科学的作用仅仅在于对澄清命题。但是逻辑经验主义者也没有对形而上学进行详细分析,他们把自然观和纯粹的形而上学一起排斥在了科学之外。同时,他们对发现的上下文和证明的上下文的严格区分也使他们忽略了自然科学的发现过程和发现的机制,忽略了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观的作用。于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把婴儿和水一起泼出了盆外。
这一偏颇迟早要被纠正。20世纪40年代,W.V.O.蒯因恢复了本体论在哲学中的地位,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的概念。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在科学的发现过程中“形而上学”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库恩的范式、S.E.图尔敏的“自然秩序概念”、I.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L.劳丹的“研究传统”、麦克斯韦(N.Maxwell)的“形而上学蓝图”都不同程度地突出了自然科学研究中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因素的作用。
然而,这些“形而上学”因素并不是黑格尔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前面所划分出来的、与形而上学同处一室的另外一个部分——自然观的内容。这种自然观才是自然科学探索中、特别是科学发现中影响科学家思维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库恩的范式中就包含科学共同体的信念,L.劳丹的研究传统也是“一组本体论和方法论规则”[ ]。这种自然观才真正履行了W.V.O.蒯恩所说的“本体论的承诺”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所涉及的东西虽然与自然界相关,但却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一种关于自然的整体观念。它们通常不来源于自然科学、也不是主观思辨,而是根植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可以历数的自然秩序观念、自然的和谐统一观念、简单性原理等,实际上都是人对自然所做出的一种“规定”。
二、 自然观的承诺
人类开始探索自然的奥秘之初,其目的和动机也许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抱有的信念却大同小异,就是首先信奉自然是可以被认识或理解的,爱因斯坦就说:“……任何科学工作,除完全不需要理性干预的工作以外,都要从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这种坚定的信念出发。”[ ]相信自然界的存在和运动有规律可循、并且人类有能力认识和理解这种存在和运动,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首要观念。这种观念又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诸如自然秩序观念、自然律(因果律)、自然界和谐统一观念、自然的简单性原理等。
(一) 自然秩序观念和自然律
怀特海说:“……,我们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 ] 自然秩序观念应该是自然合理性的首要内容,但它并非源于自然科学,而是古代西方人把希腊神话、艺术以及中世纪神学等领域中所包含的秩序观念向自然界推广的结果。
在希腊神话中包含有一种宇宙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它是如何被安排的系统说明,也包含一套含蓄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法则和模式:从某种原初混沌状态和早期几代神为争夺统治地位的争斗中,浮现出一种秩序,各种事物按照一条其必然性是不可动摇的同一性规律被整理得出了秩序[ ]。希腊戏剧作品、特别是悲剧作者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其中驱使着悲剧性事件不可逃避地发生的思想也成为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 ]。
中世纪的神学家,例如奥古斯丁、阿奎那,都力图通过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认为自然界的和谐秩序最能证明存在着一种超人的智慧,因而最能证明存在着一位无所不能的有理性的上帝[ ]。但是神学家的愿望之树却结出了意外的果实,通过自然界或自然秩序去证明上帝存在的理想逐渐异化成对自然界本身的秩序的认识。因为中世纪以后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上帝造好了世界后就离开了,人们只能通过他的作品来认识他。斯宾诺莎就提出,不能通过奇迹认识上帝的性质和存在,而必须倒是由自然的确定不移的秩序来窥察[ ]。这样,自然秩序观念就演变成人们对世界的基本信念和从事自然探索的出发点。
与自然秩序观念密切相关的自然律概念也来自于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观念和中世纪的上帝创世说。
奥古斯丁最早提出了“自然律”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一切被造物都按照最初的原则,在恰当的事件中,在合适的时间里出现,并且每一个都按照它的本性衰败消亡。自然律概念又逐渐演变成自然规律概念,人们企图通过认识自然从而认识上帝的做法也逐渐异化成以认识自然本身为目的。笛卡尔就说:“神用他创造物质的同样方式继续保存物质。既然神保存物质,那就必然推出,在物质的各部分里应当有很多变化,这些变化我觉得真正说来是不能归给神的活动的,因为神的活动决不变化,我就把它们归给了自然。据以发生变化的那些规律,我就称之为自然规律。”[ ]
从此,认识和总结这些自然规律就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任务,其中一个完备的、有关外在世界的规律就是:如果客体在某一时刻的状态完全是已知的,那么,它们在任何时态的状态就完全事由自然规律决定的[ ]。牛顿说:“自然哲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界的结构和作用,并且尽可能把它们归结为一些普遍的法则和一般定律——用观察和实验来建立这些法则,从而导出事物的原因和结果”[ ]。经典力学体系恰恰就塑造了这样一个井然有序的自然图景。
(二) 自然的和谐统一
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观念同自然秩序观念一样,最初也来源于社会文化领域。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经把世界的本源归结为某种单一的东西;而在中世纪的神学中存在的普遍信念就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和谐、统一的,人们应该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中认识上帝。例如开普勒就认为他对天体和谐的研究、他所提出的行星运行三定律不过是对上帝创世过程的探索。而这一目的逐渐演变成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界本身的探索,并成为物理学研究的基本信念之一。
统一的目标在物理学史上为大家所熟悉。那时,每一种主要的理论都把物理学界当时所知道的主要事实统一起来,伽利略所概括的力学和牛顿用公式概括伽利略的理论就是这样;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和波尔兹曼的热力学也是这样。20世纪,爱因斯坦对突破了19世纪物理学统一的、突然反常的世界图景的解释做出了贡献——狭义相对论使经典物理学产生的谜得到了前后一致和精确的解答;广义相对论则出乎意料地把几何学和力学结合了起来。
要知道,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爱因斯坦一生的信念,他曾明确提出:“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 ]他没有满足于几何学和力学的统一,他还进一步寻求所有已知物理粒子和已知的时空力结合在自身没有时间性的统一场理论矩阵中。爱因斯坦生前只尝试了四种相互作用的普遍力中的两种(引力和电磁力)的统一,而没有考虑弱力和强力。其后,物理学家则把四种普遍力都包含在内,并把20世纪后半期发现的一大批粒子也纳入其中。[ ]欧文拉兹洛总结说,在20世纪后期,“现在正在进行的科学革命比哥白尼的革命发展得更快,比爱因斯坦发起的革命更广泛。它的典型特点是把范围广泛的发现都整合进一个高度统一的、简单的(即使是抽象的)理论框架。”[ ]
(三) 自然的简单性原理
爱因斯坦说,“从希腊哲学到现代物理学的整个科学史中,不断有人力图把表面上复杂的自然现象归结为一些简单的基本观念和关系。这就是一切自然哲学的基本原理。”[ ]他举例说,德谟克利特就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简单的粒子,称为原子。
简单性原理在近代以来曾被奥康的威廉、牛顿、马赫、阿芬那留斯、奥斯特瓦尔德等人反复讨论过。也许奥康的威廉没有说过“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话,但是他却表达过“能以较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较多者去做即是徒劳”的意思,因此罗素认为这是逻辑分析中最有成效的原则[ ]。
经典力学体系无疑是简单性原则的典范。从伽利略开始到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用不变的物体之间的简单的力解释了一切自然现象,并在天文学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
自然的简单性观念又逐渐发展成自然科学理论的逻辑简单性或数学简单性。在经典电磁学的创建过程中,法拉第在思考磁和电之间联系时,也曾设想过磁铁周围有磁力线,形成了一个磁场,导线周围有电场,它们之间是通过场相互作用的。但是法拉第的数学基础非常差,没有能力推导出这个公式。直到三十年后,麦克斯韦才凭借其数学天才建立了一组描述电磁场运动规律的方程,阐明了电磁感应的本质,最终建立了经典电磁学的理论基础。
而在现代物理学中,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也同样也遵循逻辑简单性的原理。爱因斯坦说:“广义相对性原理的著名的启发性意义就在于,它引导我们去探求那些在广义协变的表述中尽可能简单的方程组;我们应当从这些方程组中找到物理空间的场定律。”[ ]
K.波普尔曾经探问:“为什么简单性如此高度的合乎需要?”他给出了一种独断的答案:“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假定‘思维经济原理’或者任何这类原理。假如知识是我们的目的,简单的陈述就比不那么简单的陈述得到更高的评价,因为它们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因为它们的经验内容更多,因为它们更可检验。”[ ]
三、 自然观的前提性意义
综上,笔者探讨了有关自然观的一些理论问题,尝试着在自然观、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间进行了划界,并列举了作为自然观典型内容的自然秩序观念、自然和谐统一观念、简单性原理的来源及其对自然科学的重大意义。实际上,这些观念都被单独讨论过,只不过没有将它们统一在自然观的概念之下。因此,如果说笔者在这里的阐述有一点新意的话,那也是受到了以往研究的启发。
可以看出,本文的自然观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观不同。如果仍然沿用自然观的经典定义,即“对自然的总的认识,包括人们关于自然界的本原、演化规律、结构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总的看法”,那么这里所谓“总的认识”或“总的看法”就不是对自然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而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信念对自然界的一种想往或一种“承诺”,也就是康德所说的“人为自然立法”。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就对柯林武德的观点产生了疑问。柯林武德曾写道:“说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以自然的观念为基础,并非意味着自然的一般观念,或作为整体的自然观念,是在脱离对自然事实的具体研究的情形下首先产生的;也不是说当这种抽象的观念成形后,人们便在此基础上建立具体自然科学的上层建筑。它所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是时间关系。”但是,柯林武德在描述古代自然观的时候却又写道:“希腊自然科学是建立在自然界渗透或充满心灵(mind)这个原理之上的。希腊思想家把自然中心灵的存在当作自然界规则或秩序的源泉,而正是后者的存在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 ]显然,柯林武德的观点前后有点矛盾。应该说,自然观与自然科学既有一种逻辑关系,同时也有一种时间关系。从逻辑关系上讲,自然观对自然科学家的思维起到了导向的作用,同时自然科学成果的证实与否还会影响到科学家对他一惯所抱有的自然观的态度的取舍——要么更加坚信,要么予以放弃。从时间关系上讲,自然观则可能比自然科学更古老,正是在那些社会文化观念的驱使下人们才开始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诸如自然秩序观念、自然律、自然和谐统一观念、简单性原理都同古希腊、中世纪以来的法律观念和上帝创世说密不可分。
于是乎自然观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经验或理论就有了本质的区别,它作为一种元理论或者前提性的知识(或称“第三种知识”)对自然科学发挥着导向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有关自然观的研究就无法退出哲学或者其他有关自然科学的反思性活动。
除了划界问题外,有关自然观的其它问题,诸如具体探讨自然观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应用具有社会文化内涵的自然观概念重新梳理20世纪以来的自然观的发展历史,分析它与现代自然科学的新型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论题。
参考文献
[ ] [德]莱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J].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234.
[ ] [美]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第二版)[M].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81.
[ ]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C].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284.
[ ] [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4.
[ ] [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Z].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92.
[ ] [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10.
[ ] 吴忠.自然法、自然规律与近代科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6):29.
[ ] 王太庆等.西方自然哲学原著选辑(三)[Z].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35.
[ ] 王太庆等.西方自然哲学原著选辑(三)[Z].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90.
[ ]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Z].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519.
[ ] 王太庆等.西方自然哲学原著选辑(三)[Z].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76.
[ ]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Z].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379.
[ ] [美]欧文拉兹洛.微漪之塘——宇宙进化的新图景[M].钱兆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6-127.
[ ] [美]欧文拉兹洛.微漪之塘——宇宙进化的新图景[M].钱兆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5.
[ ]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Z].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285.
[ ]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573.
[ ]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Z].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376.
[ ]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Z].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31.重点处为原文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