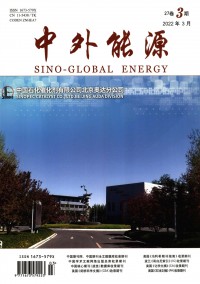中外文化交流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交流;广西;东盟;柳州
一、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从周边的国家开始,像朝鲜、日本以致东南亚,然后渐渐扩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而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则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前)时期,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曾说:“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
2009年1月31日,总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座谈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中非合作论坛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语言文化将逐步融人世界的发展趋势。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广西柳州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侬族、泰族、高栏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等,均起源于中国南方,与广西的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这些国家的民族对广西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这些都是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础以及优势。
东盟博览会不仅对广西的经济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促进了广西乃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广西充分利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的重要机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不断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次数和规模逐年增长。可以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与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也是第一个与柳州结成“友城”关系的东盟国家城市,随着近11年时光流逝,柳州与东盟各国之间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早已在东盟国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中,700名来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览了穿城而过的碧波柳江、欣赏了两岸斑斓旖旎的风景,参观了柳州市博物馆、柳侯祠、城市规划设计展览馆。而且在参观胡志明旧居时,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经历和在柳的活动,更是让越方代表团的青年们感慨万千。而作为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的分会场,柳州不但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同时,也让“山水柳州”的美誉通过活动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广西重工业城市的柳州,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日趋紧密,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以贸易合作良好展开为基础,柳州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也积极的展开来了。“自从东盟博览会召开后,东盟的留学生来到了柳州,到东盟经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来越多,双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从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也越来越为东盟国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外侨办国际交流科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矛盾的认知说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国。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21世纪是文化制胜的时代,保护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文化交流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展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选择、吸收、创新的过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生产力较发达,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文化势能也较高。我国在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积极吸取其文化的精华,自觉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应当坚持原汁原味,适当创新,切忌迎合,避免产生不中不洋的产品。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王韬 跨文化传播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柯文[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J].《德州学院学报》,2003(10)
③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⒇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0(3)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3篇
传统中国画的国际化是阳小毛教授必须面对的课题,阳小毛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早在2002年公派去法国学习期间,就有一个问题缠绕着他的思绪,偌大一个巴黎,几百家画廊、艺术馆、博物馆,却很难见到一幅地地道道的中国画,不是欧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感兴趣,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欧洲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段中不可能明白中国画的玄妙,文化的传播与文化的对接需要时间去磨合。
作为一个有民族责任心的画家,阳小毛十分清楚这一点,要让欧洲人看懂中国画,那么中国画的国际化,中国民族绘画与国际接轨是中国艺术家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中国画的绘画语境当随时生转型,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巴黎期间阳小毛与来自国内各美术学院的教授艺术家学者探讨这一命题。他欣喜地见到一些毕业于中央美院的留学生,在法国春季沙龙、秋季沙龙中所作的各种尝试,异国的环境迫使他们求变,他们汲取许多西欧艺术的元素融入传统的中国画,使之中国画更具现代意识,也就更易于让大胡子的老外大致明白,起码是先从视觉上产生共鸣。他开始以国际化的目光关注传统的中国画,如何让中国画走向国际,自觉地成为他的一份责任,青年时代他对西洋画的民族化进行过深入地学术探讨,阳小毛教授是在西方形式构成美学理论影响下切入中国画的,然后回归到传统。他发现中国传统绘画与现念是吻合的,只是如何丰富传统形式的艺术表现值得去尝试。他十分关注中国画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他要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画。自2001年他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之后,2010年到来之际画家阳小毛将自己的画展办到了韩国的国会,韩国的国会副议事长以及许多的国会议员观看了画家阳小毛的画展。画家阳小毛的作品被收藏,许多阳小毛早期的创作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些90年代的大量印刷品在收藏界流传,并有学术论文译成外文在一些国家与地区传播。
画家阳小毛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研修西洋画,随之公派赴法国巴黎深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阳小毛将传统的中国画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使自身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他走出了传统与地域的局限,与其他本土艺术家所不同的是,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投向了一个更加广大的视域。
艺术简介
阳小毛:中国著名画家,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百杰艺术家。大学本科攻读西洋画,先后于中央美术学院深造绘画艺术,公派赴法国巴黎研修欧洲美术,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印刷品和早期的水彩画在国内收藏界和海外广泛流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画家阳小毛对中国画新视域的拓展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全国许多媒体《中国画家》《当代名家》《美术时空》《书画名流》《文化娱乐》等专题介绍画家阳小毛与作品,专版介绍《画家阳小毛掠影》刊登于人民美术出版社《水彩艺术》丛书,曾多次荣获全国及省市各类奖项,两次荣获市政府奖。
1998年中国画《女性之光》参加日本东京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展
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并由《北京日报》《中国日报》予以报道
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并由《华盛顿邮报》《美术报》予以报道
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并由《欧洲日报》《欧州时报》予以报道
1989年《祖国在我心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三次再版
2007年《阳小毛中国画作品集》中国民族美术出版社出版
论文《陷入温柔泥沼的当代美术》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精神的追寻与放逐》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漂泊的家园》发表于《北京日报》
论文《水彩特质的雨雾欧洲》发表于《美术报》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4篇
历史上,中国大运河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走廊。在这条走廊里,交流是双向的:早期,主要是中国文化输出;后半期,则是外国先进文化输入。
大运河的输出
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1254-1324)描述了他看到的长江以北运河:忽必烈已经开通了从瓜洲到大都的水路。这条水路是一条宽而深的航道,把江河、湖泊连接起来。《游记》还记录了他在山东一带看到的运河城市如临清、济南和东平等地的情况。
近代西方人进入中国、并对中国逐渐产生影响,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明代。这个节点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关。史学家一般把哥伦布1492年第一次航海当作中世纪和现代的转捩点。此后,西北欧沿海强国通过战争、掠夺、贸易、传教、建立殖民地等方式逐渐向外扩张。至19世纪,欧洲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迅猛发展。而明清时期的中国早已繁华,举世闻名,引发了西方人的关注,当时外国人来中国,首先接触的往往就是大运河。前往北京的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大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作品中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西方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1488年,朝鲜人崔溥(1454-1504)在海上遭遇风浪,漂流14天后在宁波附近获救登岸。之后,他沿浙东运河、京杭运河前往北京,历时44天,成为明代走完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他用中文写下的《飘海录》成为弥足珍贵的大运河史料。
日本僧人策彦周良(1501-1579)于1539年和1547年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和正使来中国,在中国逗留5年多,多次沿大运河南来北往。他将两次来华经历写成《初渡集》《再渡集》。这两本记事性诗文集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明万历年间来中国。他从南京出发沿运河前往北京,沿途经过许多大运河城市。对明代运河漕运的有关情况,他甚感兴趣,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详细记载。
除了利玛窦之外,明清时期有不少来中国的传教士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书,在欧洲出版,其中不乏关于大运河的详细描述。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中国传统典籍经翻译而介绍到欧洲。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是牛津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他不仅翻译中国典籍,还著书立说,系统论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国的文学和宗教。在牛津任职之前,他于1873年4月从上海出发,坐船经大运河访问北京,回程时去了泰山和曲阜,之后经大运河返回上海。他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可以听到大运河的水声。
但外国人对大运河的描述,并非仅限于见闻。他们目的性很强,颇有系统性,撰写专门报告,研究大运河,研究大运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英国学者吉恩斯在1890年在伦敦出版《世界各国的水道和水运》中提到中国的大运河,认为“就许多方面来说,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运河。它也是所有其他运河中,我们了解最少的。”1895年出版的《时代世界地图集》中载有中国大运河的地图。1912年10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F.H.金的学术论文,题目是《中国的运河,人类的奇迹》,该文对江南运河地区河网密布做了详细的记录。1917年在伦敦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国》有关于大运河的词条。
大运河的接纳
通过大运河,西方对中国有所了解。而现代西方文化最早进入中国,所谓西风东渐,正是沿着大运河而播扬。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在利玛窦逝世后不久抵达北京,并发现了利玛窦的札记。明万历四十年(1612),金尼阁返回欧洲,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于各国公共场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并着手整理翻译《利玛窦中国札记》。该札记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当时,大批欧洲年轻传教士申请赴华,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即是其中的一位。汤若望历经明清两代,为西学东渐做出重大贡献。1618年,金尼阁离开里斯本第二次来华时,携带在欧洲各国募集的7000册图书和仪器,从杭州沿大运河抵达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国图书馆。金尼阁本人估计书籍和仪器在离开欧洲时价值1万金币。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金尼阁二度来华后,先在南方进行传教和译著工作,较长时间住在杭州,并以杭州为中心沿大运河到嘉定等地活动。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去世,把“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大部分书籍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残存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之后,外国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浙北的运河城市早已成为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基地和大本营。嘉兴的文生修道院西临大运河,1902年建成之后到1908年,它是天主教中国遣使会的唯一总修院。嘉兴的天主教堂在1930年建成,号称中国第一、远东第三大教堂。文生修道院和天主教堂均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在杭州。父母均是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的传教士。南长老会海外传教的第一个基地是杭州,以后沿大运河逐步向嘉兴、苏州、江阴、南京等地扩展。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结束学业,回到杭州开始传教,他的传教足迹正是沿大运河迤逦北去。
19世纪后半期起,大运河沿岸城市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经过多年经营,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13所教会大学和几十所教会中学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这些学校中相当一部分位于大运河沿线的城市或者与运河关系甚为密切的城市。
教会大学各校名师云集,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毕业于东吴大学。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以及齐鲁大学的医科,为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1901年,清政府废除漕运,大运河似乎失去了历史作用,但因为依靠大运河为广阔腹地而有机会迅速成为中国最大港口和最繁华城市的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在20世纪结出硕果。
很多人惊异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浙一带大量涌现文人政客这一现象,细究起来,却不难看出大运河的作用。正是大运河使得整个地区经济繁荣,积聚起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在各个层面广泛深入进行,人才辈出是理所当然的。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Grand Canal: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By Wei Daguo
Historicall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served as a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The exchanges were mutual: in the early centuries, Chinese culture went out to the outside world; largely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foreign cultures began to come in.
Prosperity of the Grand Canal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as made by Marco Polo (1254-1324), who traveled across China for years. He mentioned the Grand Canal that connect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Dadu, the present day Beijing,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There a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the travelogue about the canal towns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wa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westerners began to flood in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eir arrival in China followed Columbus’ epoch-making travel. Afterwards, the west expanded outward through wars, trade, religious missions, colonialism, profits through looting. By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world. Europeans came to China, allured by the legendary wealth of China. During these centuries,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missionaries, and travelers usually traveled on the Canal to reach Beijing. They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size and the grandeur of the Grand Canal. Their reports deepene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country in the orient.
The Italia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1552–1610)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chronicled his canal tour in detail in his book. In addition to Matteo Ricci, other missionaries also wrote books and introduced their China experiences to Europe. Some missionaries even provided Europeans wit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James Legge (1815-1897), a noted Scot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in Malacca and Hong Kong for 33 years and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Oxford University for 21 years. He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wrote books o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e took office at Oxford, he started in April 1873 in Shanghai to visit Beij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On his way back, he visited Mount Tai and Confucius Temple. Then he traveled on the Canal again on his way back to Shanghai.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had become a constant subject in encyclopedias, map atlases, and academic books published in the west.
Western Culture Came In
While information on the Grand Canal went abroad, westerners brought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In China scholars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Ming,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years in words “Western Winds Blow into East.” The Grand Canal played a big role in thi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arrived in Beijing shortly after Matteo Ricci passed away.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influential westerner in China. He toured China before going back to Europe to report to the Pope on missionary affairs in China. In 1612, he returned to Europe. He traveled across Europe, publicizing the 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nd raising funds. He appeared in public dressed in the Confucian gown. It was during his European tour that 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Matteo Ricci’s China Journal. The work was published in Augsburg in 1616 and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idely read. Twenty-two young missionaries followed him back to China.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was one of the 22 missionaries. He served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Nicolas Trigault brought 7,000 books and instruments to China and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all the way from Hangzhou to Beijing. He set up the first foreign library in China. He planned to translate the books into Chines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group of elite Chinese scholars. He died in Hangzhou in 1628 and he was buried in Hangzhou. His translation project aborted and most of the books dissipated. In 1938, hundreds of books were found in a library of a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These books were part of the 7,000 books Trigault had brought 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flood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al cities and towns in northern Zhejiang were home to headquarters of som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St. Vincent de Paul Seminary, a Catholic abbey in Jiaxing, served as the only seminary for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1902 to 1908.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iaxing, built in 1930, was the largest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Far East at that time. The two sanctuaries are now cultural relic units under provincial protection.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lat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China from 1946 to 1949. Born in Hangzhou in 1876, he was son of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parents based in Hangzhou and reached out to believers around Hangzhou and areas along the Grand Canal north of Hangzhou. John Leighton Stuart grew up on Hangzhou and spoke the local dialect. After he finishe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came back to Hangzhou and started missionary work in 1905. His constituents were residents in canal towns and villages.
中外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HTK]戏剧艺术;《哈姆莱特》;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中国接受史;路径整合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最近,《光明日报》(2013年9月20日)辟一整版篇幅刊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傅光明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的演讲《哈姆雷特:一个永恒的孤独者》。作为一个莎学学者,自然为此十分兴奋。但捧读之下,既为作者的斑斓文采所折服,为作者关于“生命的孤独者”的多维思考所触动,同时也感到深深的失望与无奈。作者是以老舍研究见长的当代中国戏剧文学史研究者,也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译者,同时也译有《观察中国》等书。如此良好的背景,在其演讲中却看不到《哈姆莱特》批评在中国近三十余年历史进展的信息。比如,作者斩钉截铁地断言:“莎士比亚的伟大恰恰在于,他把老旧的哈姆雷特从具有北欧海盗或中世纪色彩的复仇英雄,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文艺复兴时代温文尔雅的、高贵的人文主义者,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富于理性和启蒙的人性光辉,直到今天,还在熠熠闪烁。”“《哈姆雷特》的悲剧力量恰恰在于,莎士比亚要让所有这一切的爱,都因为那个最邪恶的人形魔鬼——国王克劳迪斯,被毁灭、埋葬。”这种绝对化二元对立式解读,使我们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证诸目前的许多涉《哈》文章和读物,这种恍若隔世的论述仍俯拾皆是,对于哈姆莱特形象在莎学界的演化,这些作者或者不曾了解,或者置若罔闻,难寻学术积累之痕迹,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林的一大奇观。当然,这种二元对立解读的生存权利自然不应被剥夺,但是对于哈姆莱特形象在我国莎评中的根本性转型可以不做任何回应和讨论而仍可在讲坛学坛畅行,显然是一种颇为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我认为,我国莎学在总体上尚缺乏明确的“接受史意识”,更缺乏莎剧接受路径互动与整合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或许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毋庸置疑,《哈姆莱特》是在世界上传播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文学艺术经典之一。自清末民初时期该剧传入我国以来,在我国文学艺术与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与广泛影响。该剧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既有与世界各国一样接受人类文学艺术瑰宝的共通性,也有基于我国特定文化背景与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是研究中外文学艺术与文化交流及其作用与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因此,莎剧中国接受史研究,当以系统研究《哈姆莱特》的中国接受史为重中之重。但是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在这种研究上虽有一定成绩但尚属初步,多维整合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尤其如此。鉴于戏剧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特殊性,一部戏剧在非同种语言之异域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史,涉及翻译、批评(含阐释、解读)、演出(含改编性演出及影视作品)、教学等诸多方面。传播者首先是接受者,而这些特殊的接受者又同时处于与广大受众的多层面互动之中。与此同时,上述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又呈现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这是戏剧接受史的系统研究难度较大的客观原因。就《哈姆莱特》来说,我国大陆学界在该剧的中国“批评史”研究方面比较着力,比如孟宪强《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2007)、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2006)等著作中对此有所总结;在“翻译史”研究方面,我国港台学界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体现在周兆祥著《汉译〈哈姆雷特〉研究》(1981)、彭镜禧著《细说莎士比亚论文集》(2004)等著作之中;在“演出史”研究方面有曹树钧、孙福良著《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1989)、李茹茹著《莎士比亚:莎剧在中国舞台上》(2003)等著作;“教学史”方面,除了一些零星的成果外,尚无系统性成果问世。而在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相互作用研究方面,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也有所涉及,加之一些戏剧家(如、、焦菊隐、林兆华等)有一些经验之谈。近年李伟民教授“多管齐下”的全景式努力尤为值得称道,这集中体现在其《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2002)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莎学知音思想探析与理论建设》(2012)两部著作之中。但真正的路径互动意义上的“接受史”研究的总体局面还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我国有关学界长期缺乏这种“接受史”研究视角相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学科、界别机械划分限制了这种跨学科、跨界别研究课题的展开。“接受史”研究视角与总体构想的引入,可以为上述诸方面互动研究的系统开展提供贯通性枢纽。这种研究的系统展开,可通过对《哈姆莱特》这部文学艺术瑰宝在我国(含台港)多层面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反思,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这部经典巨制的多方面现实功能提供启发与借鉴。
二 依据笔者的初步研究,中国《哈姆莱特》接受史可大致分为如下五个历史时期: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二、20年代至40年代;三、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四、“”十年;五、“”结束至今。其港学界的接受史分期又可相对独立。研究应以《哈姆莱特》在中国的“翻译史”、“批评史”、“演出史”、“教学史”研究为基础,改变将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分立研究的传统模式,着力考察该剧传入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历史发展与相互作用。在研究的总体路径上,可主要运用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兼采当代接受理论、历史情境分析及其他各种研究方法之长。可首先考察并确定各个历史时期的《哈姆莱特》之接受的标志性事件,继而围绕这些事件展开实证研究,揭示该历史时期《哈姆莱特》之接受的特点及发展趋向,说明其在中国文学艺术与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既通过深入分析把握各个阶段的特殊性,又在国外文学艺术之中国接受方面获得一些一般性结论。显然,这种研究的重心,当在于各个历史时期多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互动研究,但这种互动研究以进一步深入进行各种分立研究为前提,故需要进一步深入把握学界以往各种分立研究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史论两方面将研究推向前进。而目前研究难点在于学界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演出史”、“教学史”方面,需要组织力量展开规模较大的实际考察与系统分析。就戏剧文学与艺术接受史而言,局限于翻译史与批评史研究是具有片面性的,“演出史”(包括舞台演出与影视作品)和“教学史”在接受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下大气力改变在这两方面研究上的薄弱局面,从而为全面把握《哈姆莱特》接受史奠定扎实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应着力阐明我国各历史时期《哈姆莱特》之接受与我国各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层关联,揭示其在我国各时期产生独特影响的历史根据,充分展示出这部世界经典悲剧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与特殊机理。不过,这种研究不应对各个时期的接受史研究平均使用力量,而应在考察前四个时期《哈姆莱特》接受史的基础上,把研究重心放在改革开放以来多元认知背景逐渐形成的条件下对这部名作之接受史的多层面、多角度考察方面,力求加以立体、动态、整体性把握。除《哈姆莱特》本剧的接受史之外,同时亦应对其当代的一些衍生作品的中国接受史加以探讨,如后现代戏剧《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司吞死了》,《哈姆莱特》剧情延伸小说《葛楚德与克劳狄斯》等,因为这些作品代表了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哈》剧的新理解,它们传入中国之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研究《哈姆莱特》中国接受史所不应忽视的。作为一部悲剧文学巨制,《哈姆莱特》在中国的接受史既有其作为大悲剧的一般作用机理,即通过揭示人类在抗争各种生存灾难与不幸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有共通性的心理境况,使作品受众于震撼灵魂的悲剧中得到情感净化与心灵升华;同时,作为西方文艺复兴转型时期的一部人文主义名作,《哈》剧的传播与接受又适应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需要,发挥了其独特功能。我们应在对这种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功能转变给出有说服力的实然考察的基础上,加强应然视角的深入、系统探讨,为在“以人为本”已成为时代强音的新时期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挥这部人文主义名作及其他莎士比亚戏剧在我国的现实作用,为推动我国戏剧文学艺术的发展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的发挥,提供有益的借鉴。以“以人为本”为内核的广义人文主义理念,我曾概括为如下两个基本点:一、以人(而非神、物)为核心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二、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普适性肯定。而《哈姆莱特》的价值绝不是由于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而是由于通过对一系列圆形人物的精心刻画,最为集中、最为经典地体现了这样的人文主义理念,而这种理念在我国当下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具有极为重要与根本的弘扬价值。这是笔者长期致力于《哈姆莱特》研究系列工作①的主要思想诉求,也是提出《哈姆莱特》中国接受史研究构想的基本思想背景。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