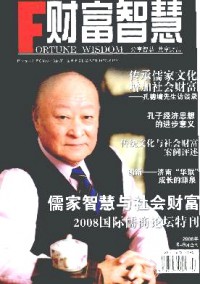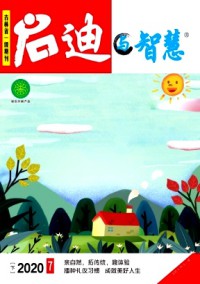智慧社区建设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智慧社区建设研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智慧社区建设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智慧社区 诚信商圈 社会关系网络 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8(c)-0068-02
通过构建智慧城市[1-2]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也是信息时代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3-5]的创新应用,在规划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带动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完善。智慧社区服务平台是社区服务体系中的核心平台,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平台。智慧社区[6]作为智慧城市的最基本组成单元,其建设优劣极大地影响着智慧城市的发展。智慧社区服务平台[7]的本质,是面向政府基层政务管理者、社区居民和本地商家的政务及生活服务一站式O2O服务平台,是电子商务向日常生活类本地化服务的延伸。智慧社区作为同时汇集政府基层管理者、社区居民和本地化商家的平台,是本地化口碑式社交网络的天然载体,即“诚信商圈”建设是智慧社区服务平台建设的核心问题。
为实现基于本地社交网络的O2O商圈诚信体系,在融合智慧社区服务的基础上,针对智慧社区发展过程中与诚信商圈建设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8-10]应用展开研究和技术攻关,利用智慧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建模、SNS应用、数据挖掘等核心技术,整合跨业务大数据系统,构建面向智慧社区诚信商圈平台。
1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商圈诚信体系建模
在面向智慧社区诚信商圈平台中,主要包括:(1)本地商圈社会关系网络模型;(2)社会关系网络与诚信商圈体系的关系模型;(3)诚信商圈体系的保障机制模型。
1.1 本地商圈社会关系网络模型
在本地社会关系网络中,以关系数据为对象,利用量化型数值来考察本地社交网络的属性和特征,对处于本地商圈中的个体属性和特征进行分析建模。模型的主要属性包括以下几方面。
(1)网络规模模型:本地商圈中行动/参与者(社区个体用户、销售者、供应商等)的总数,其表现在社交网络中的节点数,网络规模越大,其网络结构中的节点数也越多,结构也越复杂。
(2)网络密度模型:网络密度反映了本地商圈中行动/参与者客观实体之间关系的紧密度。通过带权有向网络中的弧及权值来描述,弧数越多,说明该节点关系越复杂、联系度大;权值越大说明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越紧密。
(3)中心及小团体模型:在模型中,节点的中心性及小团体反映了行动者在本地商圈中位置的重要程度。通过核心小圈的弧度(有向图中弧的数目)及权值、子群的数量、子群内部以及子群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度量其重要性。
(4)核心-边缘模型:根据本地商圈中行动/参与者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以弧、权值、节点数、子群数等作为度量)将本地商圈社交关系网络的节点划分为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
1.2 社会关系网络与诚信商圈体系的关系模型
通过为商家提供一个合理的诚信评价体系,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消费者,挖掘并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对其购买行为具有直接影响,而购买意愿又取决于消费者的信任态度。基于社会互动评价模型(评论、微博、说说、交互性留言等)、购买/管理行为模型(购买、销售、库存等)、技术接受模型、消费者行为模型、顾客价值评价模型等,建立社会关系、诚信体系、精准营销等三者关系的模型。
1.3 诚信商圈体系的保障机制模型
信用机制是电子商务和网络信用经济的制度基石。传统的信誉管理已难以适应电子商务市场的变化,将建模技术和分析方法应用到信用领域,形成开放式信用机制评价及保障模型。诚信商圈体系的保障机制模型的主要指标模型。
(1)委托及信息传递建模:委托者通过者依照其利益完成相关行为(调研、评价等),得到由者的行动以及其他外生随机因素共同决定的衡量值。
(2)商务过程中重复博弈模型:重复的博弈过程中,博弈各方会考虑各自利益的均衡,选择相关的策略以达到获取利益的目的。重复博弈次数会影响博弈均衡的结果。重复博弈模型中必须考虑:博弈参与方、长远利益、短期利益、利益权重、协商、决策等相关的技术指标。
(3)声誉模型:通过对本地社会关系的信息及相关数据的挖掘,建立一个基于经验和概率统计(由大数据的挖掘来获取)来度量信任关系的信任评估模型:基于本地社会关系的声誉模型的信任机制模型(局部、朋友圈、小团体声誉模型);基于第三方认证机构的信任机制模型(全局声誉模型);基于服务质量的信任机制模型。
2 面向智慧社区诚信商圈平台的实现
2.1 商圈诚信体系系统构成
在智慧社区中应用社会关系网络,以智慧社区诚信商圈为需求,建立多维的社会关系网络模型,设计并实现基于社会复杂网络的信息系统。通过建立起一套采集本地用户数据的系统,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下指的是通过政府提供的用户属性数据为本地用户建立个人诚信体系数据库,线上指的是通过智慧社区APP以及其他的电子渠道获得本地用户的线上行为数据,将这两部分数据作为“本地商圈社会关系网络模型、社会关系网络与诚信商圈体系的关系模型”、“诚信商圈体系的保障机制模型”的入口参数,构建面向智慧社区诚信商圈平台。
商圈诚信体系系统构成如图1所示。在数据采集中,主要的数据来源为:G端政府数据(基础脱敏数据)、B端商圈数据(商品、商家、服务等数据)和C端线上数据(线上交易、线上服务、线上社交等数据)。依据本地化的社交网络,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过滤:以C端基础属性和社会关系影响力评估模型为基础,完成本地社会关系量化计算。通过社会计算和数据挖掘技术,构建基于商圈诚信体系的三个核心模型的数据平台。
2.2 智慧社区诚信商圈平台系统实现
面向智慧社区诚信商圈平台主要由数据采集系统,数据分析引擎,引擎运行平台三大部分构成。数据采集系统包括:智慧社区中面向本地用户的各类线上的应用(如APP、PC网站等),用于对接政府数据的数据库建设;数据分析引擎主要包括:本地用户社会关系的分析引擎,商家诚信指标计算引擎,精准营销效果评价引擎等;引擎运行平台:需要开发一个基于多粒度应用资源分配系统,实现计算资源的高效利用。平台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面向智慧社区诚信商圈平台对外提供的服务是:社区政务管理和民生服务,主要服务对象包括政府基层管理者、社区居民和商家。平台的用户主要包括:城市基层政府组织、智慧城市投资运营商、智慧社区建设运营商、系统集成商等,服务于基层政府管理人员、社区民众和商家。在数据采集系统中,通过对物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在智慧社区中的应用,接入专业的服务商家,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生活服务,并以各种物联网设备即时感知社区管理对象数据,做到社区范围内各类信息资源的互联共享,结合政府各类相关业务信息系统,是实现直接面向社区居民、政府基层组织的可视化智慧社区服务平台。数据采集系统平台主要包括:“1个综合门户、2大专业子平台、8个应用支撑系统、1套业务协同体系、‘6+N’类服务渠道、1个社区综合资源库”,为数据分析引擎提供了大数据支撑服务。
引擎运行平台是一个支持诚信商圈应用的多粒度并行计算的资源管理框架,利用应用虚拟化技术,在服务器中通过技术规范建立适合多粒度应用服务运行的软件计算服务环境,为面向智慧社区诚信商圈平台提供计算资源支撑服务。
3 结语
以目前正高速发展的智慧社区及O2O电子商务领域为背景,研究智慧社区平台诚信商圈建设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模、实现与验证,构建面向智慧社区诚信商圈平台。该平台结合了智慧社区平台的本地化商圈特点,以“本地商圈社会关系网络模型”、“社会关系网络与诚信商圈体系的关系模型”、“诚信商圈体系的保障机制模型”为核心计算模型,将分析过程与数据采集过程并行进行以降低系统复杂性,确保数据处理的高效与安全,为社区政务管理和民生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 巫细波,杨再高.智慧城市理念与未来城市发展[J].城市发展研究,2010, 11(17):40-60.
[2] 杨再高.智慧城市发展策略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2,32(7):20-24.
[3] Armbrust M,Fox A, Griffith R,et al.A view of cloud computing[J].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2010,53(4):50-58.
[4] 刘强,崔莉,陈海明.物联网关键技术与应用[J].计算机科学,2010(6):1-5.
[5] McAfee A,Brynjolfsson E, Davenport T H, et al.Big data: The management revolution[J].Harvard Bus Rev,2012,90(10):61-67.
[6] 康春鹏.智慧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21(2):72-76.
[7] 宫艳雪,武智霞,郑树泉,等.面向智慧社区的物联网架构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14,35(1):344-349.
[8] 章成志,汤丽娟.基于多语言社会化标签聚类的潜在社会关系网络发现[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36(9):67-71.
智慧社区建设研究范文第2篇
空间是社会存在的重要维度,“当代许多社会科学都存在一个相当大的缺陷,即忽视了时间和空间。”[1]如今这一观点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界兴起的空间转向,针对这一缺陷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空间进行反思,探寻空间在社会运行中的模式和效用,以期修正传统的社会理论。与此宏图相反的是,空间研究对主流社会理论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对空间研究兴趣高涨的当下,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那些专注于空间的理论家为何未能对空间做出大量的讨论?空间研究之所以困难且进展迟缓,原因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社会空间研究的实质与误区,并对其做出反思。
一、社会空间研究的实质
自然科学的空间观是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空间概念的基础。自然科学认为空间通过接触产生联系并发挥作用,例如x影响y,那么x和y必须有物理上的接触,或两者通过介质联系起来。通过接触而起作用是空间发生联系的途径,但此观点没有说明空间相互作用联系得以发生的具体的因果和格局,因此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界的空间分析。社会科学界的空间观体现于空间的物质性和实践性,我们称之为社会的观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验研究
(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人类社会活动生产出房屋、道路、桥梁等物质设施及其组成的空间,它们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空间组织。社会关系决定了空间的结构、属性和形态,它在生产空间的同时也将自身铭刻进空间。我们可以通过空间来了解不同人群的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阶层,以及居民个体与集体的属性、关系。社会空间存在于物质构成它的地方,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成为空间的来源。社会为空间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以及本体论的依据,这使得社会空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唯物主义基础:空间只有依据构成它的对象和过程才能被理解。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以下字母之间的空间关系,来更好地理解社会空间的经验性。
A C
B D
从表面上看,我们将A和B换位,A和B各自所在的空间还会存在,并且A、B、C、D四者之间的空间模式和组合也没有改变。这也是单纯抽象出空间形式的合理性所在。但实际中,A、B、C、D这些字母代表着特定的对象,它们使各自所在的空间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属性,那么它们之间的移动会引发或阻碍彼此之间的某种因果机制,并且改变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因此,我们如果想了解空间对事件影响的实际方式、过程和结果,就必须将空间置于具体的社会过程中,进行经验分析。
(二)实现“社会―空间―时间”三者辩证
时间和空间并不是两个互不关联的“容器”,“每一项社会活动都沿着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展开。” [2]时空共同构成社会实践的情境性特征。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把时间看作是“瞬间”的集合,空间则是“地点”的组成。每一个事件和环节都必须置于瞬间和地点共同限定的位置上,以此与其他事件区分开来,例如,休息是在夜晚的卧室中进行;学习是白天在学校的上课活动,等等。这些“事件―瞬间―地点”组成的情景是社会实践的“节点”,又通过权力、管理等手段联系起来,楔入宏观制度的时空绵延中,社会系统正是通过此种方式凝聚了结构、时间和空间,实现了其在时空中的延展。
反观社会实践的时空过程,社会存在显然是在历史和地理的语境化中被安置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社会过程的发生需要占据一定的地点,并且经历开端、中间和结尾等不同阶段;我们将不同的社会活动分配于不同的地方,同时通过时间来测量、协调、管理、标准化活动过程。位置、场所、先后、次序,这些时空要素是社会存在和运行的必要条件。社会空间的研究目标是重构社会理论,那么它必然要实现“社会―空间―时间”三者的整合。
二、社会空间研究的误区
社会空间研究的实质是其展开研究的依据,但是在现实中,这一依据或者指向一些错误的倾向,或者没有得到落实,从而导致社会空间的实际研究出现了一些误区。
(一)物质空间分析导致空间模式化研究
空间的经验性指向这样一种理解,因为空间只存在于对象构成它的地方,所以空间可以还原为它的构成对象。社会空间依存于社会活动和社会过程,而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社会过程又体现于社区、土地、公共设施等物质要素的使用。例如,资本以及人员流动被理解为诸如工厂、邻里和城市这些表现为物的地方,这些现象最终和社会因果关系连接起来,观察它们,我们最终可以理解过程,那么社会空间就可以被看作是物的集合。然而当地理现象被替换成对社会空间组织的解释时,这种方法变得极具迷惑性。地理空间具有一定的形式和结构,它表征的社会空间组织似乎是自然距离和位置排序的产物,部分学者甚至提出一个大胆的主张:是否存在一些普遍的空间规律或空间过程。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作用及问题突出,为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证,因为城市确实具有一种明显的空间规则性。学者们热衷于识别空间规则,例如人类生态学派总结出的一些经典城市空间模型: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霍伊特的扇形模型等。空间是社会构造物,这是一种单向序列的解释,解释的关键(也是合理之处)在于空间变迁被理解成生成社会变迁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需要进一步阐述,因为它不是社会空间研究的全部。从社会变迁到空间变迁忽视了空间的组织作用,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也在空间中建构,空间并非由社会导出而从属于后者,相反,二者互为条件。按照这种思路,社会空间研究者提出了涵盖各种研究层次、不同研究领域的“社会―空间”辩证限定分析范式,即社会实践生产出了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又指导、制约着空间中以后的实践,维持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或者创造出新的社会空间。
表面上看,社会空间研究是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解释机制。实际上,这种模式化分析会使研究陷入一种抽象的空间理论建构中。事实证明,抽象的空间特性明显不同于具体研究的特性,空间和物质的重新再结合经常完全不可行。由于对城市生长模式的过分关注,古典人类生态学派在后期开始将空间分布作为研究中心,企图发展出普遍的城市成长模式,后来的学者很快发现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模式,哈特在1946年的研究表明城市模型分析方法不能应用到西雅图。城市确实拥有某种空间形式,但这种形式不是统一的,一旦我们开始用某个城市特殊、偶然的空间形式来推演其他城市,并因此把它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代名词,尽管某些关系可能是必然的,但混乱和错误必将会出现。“社会―空间”辩证分析同样对现实缺乏解释能力。首先,它没有揭示社会实践机制形成的原因,这种循环分析成为一种十分乏味的表述,认为社会关系发生在某种前构造的和静止的时空框架之中。其次,“社会―空间”辩证分析也无法说明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尽管它包含了生产和再生产两种变化,却没有指出这两种变化各自在什么条件和情况下发生。
(二)空间的社会性分析导致“去空间化”研究
空间的经验性还体现于空间具有社会性。在社会科学家看来,空间之所以能成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空间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这种认识暗含着一种假设:研究者可以通过观察空间来把握社会。其本质反映了自启蒙哲学以来一直支配科学思想的“实体―属性”观点。一直以来,空间和社会理论家不断从这个影响巨大的传统观念中寻求洞见和合法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直接合二为一的,那么一切科学就都成多余的了。”[3]任何社会科学的分析都是从明显的现象开始,最终认识事物的结构以及生成结构的机制。社会空间研究也是如此,开始于地理构造而结束于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空间其实成为了一种工具,也即是说,空间一旦被归结为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编码”和“映像”,我们会抛开空间本身的形式和结构去建构社会理论,这种分析与公然“去空间化”的理论建构模式不存在任何差别。
(三)采用无时间的静态分析
社会空间研究将共时与历时两种主要社会状态转化为空间结构和空间发展,但是在有关这两者的讨论中,社会空间研究几乎可以说是与时间无涉的,它将视角集中于静态分析上,更适合于称作“时间中的片段”研究。
空间结构分析强调的是同时性而不是纵向性,学者们描述的是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但这不是唯一的问题,即使理论家是以变化的视角来探寻事物的过程,这种分析也常常基于无时间的延伸,他们一般的做法是采取一种过去式的视角来比较此前、此后的不同,而不关注变化的过程。“多数描述和分析,通常以过去式来说明文化和社会,这种把经验直接地和规则地转化为已经完成产品的做法,是认识人类文化活动最大的障碍。关系、制度和形式是已经形成的结果而不是正在形成的过程。活生生的当下总是模糊不清。”[4]差异、转换、形变的过程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社会空间研究将结构或变迁理解为不受时间影响的互动瞬相,这种“瞬相定格”分析实际上根本无法揭示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因为社会系统仅通过其随着时间推移而进行持续运行而存在。“稳定意味着跨越时间的持续性,稳定的秩序就是事物现在的状态和过去状态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性。”[5]社会系统仅通过其随时间推移而进行的不断再生产而存在。
三、社会空间研究的反思
揭示空间探讨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非常重要,但我们更不能忽视这些错误的根源,以及避免这些错误的种种困难,这是空间研究困境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
(一)社会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的合理性
由于社会与空间的不可分割性(不论是空间是社会存在的维度,还是空间具有社会性),一些学者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融合为“社会空间”概念,并试图以社会空间为研究对象,建立起一门空间社会科学。然而社会空间真的可以成为某一门空间科学的研究对象吗?空间若想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它必须是一种原质或者实体。就物质由不同的原质构成,并且每一种原质的存在都不依赖其他实体而言,社会空间不是原质,只有当各种实体、关系存在于空间中,社会空间才存在。因此,尽管社会空间是由对象构成的,但它却不能还原为构成它的事物和社会关系,它在实际中更多是事物的环境和背景。
例如,像城市和城镇这样的社会空间单位传达出清晰的空间图像,然而,对城市化的分析却表明,这些定义不存在物质基础,因为在这样一些区域发现的社会关系和活动并非它们独有,城市影响社会过程运作的主要方面是其规模和形式要素。正如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所认识到的,形式不是一种根本的东西,能够影响到抽象理论所分离出来的基本结构和机制。因此,任何试图分析社会空间的尝试,最终都会出现前文所说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关注空间形式,企图建立一种空间科学。这正是地理学的科学目标,然而就像某些地理学家发现的那样,纯粹的空间过程并不存在,只有一些特殊的社会过程发生在空间中。空间显然并不是一种能够抽象化的对象,一旦从内容中抽象出形式,空间本身就会变成无内容的存在。二是关注社会要素和社会过程,研究最终指向发展社会理论。例如,卡斯特在其研究中提及空间和城市空间,但“他关注的是城市的构成要素,只是从空间布局角度对它们进行分类分析,实际上几乎没有真正地讨论空间。”[6]
(二)时空结合的困境
以索亚为代表的一些空间学者,认为空间应当并且也能够实现与时间的整合。社会空间“实际上产生于作为人类生活中一种独特物质性及符号性语境或居所的‘空间的社会性生产’中,因此,它兼有形式或形态、活动或动态两个方面。空间可称为历史发展着的特别地理志。”[7]社会空间将历史的发展维度纳入进来,便是实现了空间与时间的整合,然而在实际中,社会空间研究者仅仅在时长概念或者事件先后顺序方面考虑时间,简而言之,时间要么不被看作是一个分析性的变量,要么只是在随后的证明中才被引入。各种时间概念与社会形态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有得到详细的说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空间研究对于时间的误读。受自然科学时间观的影响,空间研究将时间问题归结为定量社会分析问题,更宽泛地说是实证社会科学的问题,这造成了社会空间理论对时间探讨的抑制。实际上,时间和空间一样都是秩序的核心,时间渗透于变化、稳定、秩序和计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时间都是社会时间。米德曾说,“必须至少有某件事降临到事物,发生在事物中,这影响了事物的性质,从而可以将一个时刻与另一个时刻区分开来,进而可以有时间。”[5](32)没有事物,就没有时间,甚至没有要被测量的数量。虽然自然、物理、机械的时间是实践活动展开的基础,但社会事件在时间中展开,事件对时间也有标识作用,不同的社会过程将其所在的时间标记为不同的“时段”,如学习时段、工作时段、休闲时段等,这些时段成为我们展开社会活动的指导和依据。如同空间一样,时间也既是社会的构造物,又是社会运行的媒介,时间的社会定义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之中。因此,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空间研究都不能回避时间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同时,时间又是一个系统整体,所有时段都不是孤立的实体,它们被整体的社会进程组合成一种时间节奏,并且象征着社会结构。因此,我们要以复杂关联的方式来考虑时间,不同时段的生成,相互之间如何实现转化,其过程又是如何,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时间与空间研究的分裂。目前,把时间与空间割裂开来仍然是学界流行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社会空间与社会时间研究的相互排斥与低估。首先,时间与空间不仅被看作是社会分析的不同维度,同时还以学科划分的方式将彼此分裂开来,一般来说,时间是历史学的身份表现,空间则是地理学的特权,学科以及视角的差异阻碍了时空的融合。其次,时间和空间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得到单方面的强调。例如阿维尼的《时间帝国》完全质疑空间的本质,即便构造时间所必需的空间化实际都存在着。厄里则认为“不论从最明显的过程来看还是从更一般的社会意识来看,空间而非时间才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独特重要性的维度。”[1](19)
智慧社区建设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旅游地;聚居空间;研究进展;述评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8-0040-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08.009
引言
希腊学者Doxiadis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人类聚居学”理论,指出人类聚居是“人类为自身所作出的地域安排,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其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的需求”[1]。中国学者吴良镛院士发展Doxiadis的聚居学思想,结合中国国情,将聚居定义为:“是人类居住活动的现象、过程和形态”[2]。1976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召开的第一次人类住区国际会议正式接受了人类聚居的概念。聚居既是一种空间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和发展过程。
旅游地是典型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特殊区域,旅游成为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聚居空间演变进程。随着人类旅游活动影响范围和强度的增加,聚居空间逐渐外向化并融入所在的旅游空间。聚居空间的演变过程是深入理解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演变机理与社会调控的关键所在[3-5]。因而,聚居空间构成了解读旅游地转型的重要和独特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人类活动过程对聚居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的改变方式、强度和影响机制 [2,6-17],聚居研究尺度已由最初的城市扩展到区域、乡村,从空间分析逐渐向社会和人文方向转变,更加关注公平性[15]。但目前研究较多集中在由城镇化、工业化等主导下的聚居变迁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旅游快速发展背景下聚居现象研究,深入探讨人类旅游活动因素与人居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揭示旅游地聚居现象、过程及形态背后所涵盖的本质特征与地域规律,为我国不同地域环境下人居环境建设与空间调控提供一定的参考。
通过系统梳理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Geographie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Journal of Rural Studies、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城市规划》《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旅游学刊》等国内外核心期刊的98篇相关文献发现,旅游地聚居已成为地理学、人居环境学、社会学等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进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过程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经历外部扩展和内部重组双重过程,分别以“增生”和“替代”的方式重构聚居空间。经历从非旅游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1.1 聚居空间从非旅游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
Nepal研究了昆布Namche Bazaar村的个案,分析发现:聚居地面积不断向外扩展、传统住房向旅游功能转型[18]。Nepal根据发展阶段、住房历史、聚居地规模、经济功能(依附于旅游或农业程度)、参与旅游程度、聚居点旅游区位优势等,对受旅游影响的聚居地进行分类,识别了安纳布尔那山地区5种类型的聚居空间,这些聚居空间已经历了几次转型,即从农牧村落到季节性旅游中心再到永久聚居地转型[4]。王茵茵等以大理喜洲镇为例,分析了旅游促进传统农业村落向旅游小城镇演变的进程[19]。席建超等分析了野三坡旅游村镇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传统乡村功能解构和村庄“旅游化”过程相伴而生,从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逐步向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住宿、购物、餐饮、娱乐等复合型用地转变[20-21]。
1.2 聚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空间分异特征
1.2.1 湖泊型旅游地聚居空间沿岸线逐渐递减
Dahms研究了多伦多安大略休伦湖乔治亚湾,发现湖区沿岸分布着大量别墅,并伴有游艇码头、退休社区、分时度假公寓和露营地[22]。其中Creemore、Meaford 和Thornbury等宜人的旅游社区沿河流和港口布局,Wasaga Beach 是安大略最古老农舍社区,而Midland和 Collingwood 是当地重要的中心地。Schnaiberg等分析了威斯康辛州韦勒斯县主要湖区聚居空间分布特征[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游憩活动增加,超过50%的新住宅小区沿湖岸被建成,中等规模的居住区离岸线不超过100 m,60.9%居住地位于岸线100m,69.9%居住地位于岸线200m。Winkler分析了布雷纳德湖区,该湖区吸引了旅游者、第二居所业主和退休移民等群体[23]。31%的住房主要被用来季节性居住和游憩居住。聚居空间呈现湖区旅游聚居、郊区聚居、工业小镇聚居、远离湖区的乡村聚居的空间分异特征。
1.2.2 山岳型旅游地聚居空间呈现水平和垂直尺度扩张
Nepal研究发现安纳布尔那山聚居空间呈现水平和垂直尺度扩张,聚居布局遵循徒步旅行线路扩张模式,服务导向聚居地超过了农业或贸易聚居地[4]。呈现核心-边缘等级结构特征,核心区旅游住宿设施占所有住宿设施的63%。Pawson等研究发现,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游客涌入尼泊尔昆布地区,南奇镇因旅游建设推动了城镇快速增长,而远离珠穆朗玛峰的村落逐渐萎缩[24]。Yin和Muller揭示了萨米特县山地滑雪旅游地新的聚居空间呈现水平尺度扩张[25]。Silberman和Rees运用GIS模型,以落基山脉395山区聚居地为对象,识别了受到滑雪度假胜地影响的24个聚居地,呈现以滑雪度假地为中心向扩张[26]。
1.2.3 村镇旅游地聚居空间沿道路线性布局、接近游憩宜居环境区域
Glibert在1930年代最早发现旅游发展正在改变英国海滨城镇聚居空间的形态,形成新的具有众多特征的海滨旅游小镇[27]。Kuentzel和Ramaswamy测度了佛蒙特州斯托每年的度假住房和永久住房数量[28]。斯托镇永久住房年增长率相对稳定,而季节性住房在过去51年内呈现快速增长。Muller等分析了鲁特县小城镇,发现29%的住房单元属于空置房或第二居所,39%住房住户为非当地居民[29]。Baski和Wesolowska调查了波兰卢布林2627户居民,发现聚居空间呈现明显的空间极化过程[30]。东部卢布林城市居住单元面积从1970年的50.2m2增至2002年的85m2。传统聚居空间主要围绕在卢布林城市30km范围内的区域,新的聚居空间沿主要交通线路附近和自然环境优美的旅游区。陈志钢和保继刚发现阳朔县1999年以前属于自然状态下的蔓延式扩展阶段,1999年以后则为旅游影响下的飞地式扩展阶段[31]。张译丹跟踪调研大理州双廊镇,认为聚居空间向扩展,但呈现无序开发和非理性发展状况[32]。杨俊等采用元胞自动机模型模拟与预测了三坡镇,发现:2005―2010年研究区城镇增长主要围绕现有镇区范围扩展;2010―2015年主要城镇增长区位于镇内距离景区较近的苟各庄村附近,其他区域则保持相对平稳状态[33]。
1.2.4 保护区聚居空间呈现圈层扩张
Gude等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测度了大黄石生态系统聚居空间增长速度[34]。从1970―1999年,案例地人口增长58%,而支撑聚居发展的用地增长了350%。20世纪以来,选择在肥沃土地和临水自然环境优美区域的居住比重占主导。Radeloff等编制了详细住房增长空间数据,定量分析了美国荒野地区、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等保护区聚居空间增长过程[5]。研究结果表明:1940―2000年,自然保护区50km范围内,建有2800万套住房,在国家森林公园内建有94万套住房。Mockrin等使用了聚类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了自从1940年以来,美国北方森林公园区域内及其周边地区聚居发展模式和分布特征[35]。研究发现:建立在旅游基础上的服务经济引起了当地聚居空间的变化,增长区域主要集中在接近城市和拥有丰富自然环境的区域。
1.3 利用主体聚居面临着分化重组的分布格局
旅游的活力在于外来投资与人口的进入,这种流动性导致社区内部相对同质,而社区与社区之间相对异质的分布格局,由“同质同构”向“异质异构”转变,推动了聚居空间的重构[36],且往往与当地社区发生较大冲突[37]。体现了大量中产阶级的注入改变了旅游地原本的阶层结构,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分 层[38]。Dredge认为旅游发展影响了许多城镇的增长或衰落[39],形成了Macquarie湖区西部旅游社区经济繁荣,而东部存在大量的与世隔绝的村庄[40]。旅游业发展使得中产阶级居住的邻里地区转化成为一个相对富裕和专有区域的过程[41-42]。Winkler研究得出布雷纳德湖区富有居民居住在湖区周围,中产阶级居住在Baxter或远离湖区村镇,贫困群体居住在工业区[23]。环境特权存在导致贫穷并没有减缓,而发生社区的置换和过滤[43]。Park和Pellow对阿斯彭研究发现:财产价值为富有的阿斯彭人提供了环境特权,造成了富有居民、低收入居民、少数民族居民的空间隔离,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群体居住在峡谷末端[44]。Cloke等指出城市中产阶级向乡村迁移,寻求居住与休闲空间,造成乡村地区的住房紧张与原居民的搬迁[45]。富有群体能够担负得起居住在环境富集区,而贫困群体选择相对偏远地区[46]。谭瑾和王晓艳分析发现旅游影响下知子罗怒族村寨经历了空间置换过程[47]。李鑫和张晓萍认为古镇居民生活空间置换成了旅游空间和商业空间[48]。何深静等发现广州小洲村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聚居空间形成了挤占、分割。同时,当地居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推动聚居空间的重构[49]。刘俊和楼枫烨发现案例社区在旅游大开发过程中日益边缘化的趋势难以改 变[50]。张焕指出舟山群岛部分人居环境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51]。陶伟和徐辰研究发现平遥外来资本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聚居空间扩展和置换能力,社会资本造成了当地居民的社会分层[52]。
2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理论解释
国内外关于逆城市化、旅游城市化和流动性转型等理论为旅游地聚居空间系统重构提供了理论线索。
2.1 逆城市化理论
尽管逆城市化研究较多关心城乡流动结果,但旅游在第三世界国家效应相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城乡关系变化主要表现在聚居模式变化和空间重构[28]、容纳服务业增长的乡村空间重 组[53]。Mitchell认为逆城市化体现2个方面:从城市到田园乡村的人口流动以及带来的聚居系统变 化[38]。逆城市化过程既是移民过程也是聚居空间变化过程。逆城市化的研究除了集中在人口流动外,还集中在乡村空间绅士化[57]、环境移民和生活方式移民等[58-59]。逆城市化研究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观点(构成、模式、形态)向人文主义解释演进(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重塑聚居系统)转型。
(1)功能主义观点。提供了聚居地演化、扩张过程以及空间形态变迁的解释[60]。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需求和环境移民不断增强[61]。这种需求导致了田园乡村人口和住房的去中心化、住宅数量增长、住宅分散化模式、区域分异和等级结构[62]。新增住宅包括了第二居所、旅游住宿设施、别墅等,形成了由旅游主导的聚居空间模式。
(2)人本主义观点。人文主义观点有助于理解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影响聚居空间出现和发展,主要涉及变化、过程和空间,乡村聚居受到居民的感知和决策影响[62]。空间转型导致不同类型马赛克空间和景观出现,如无地方性的空白空间,介于旅游、居住和其他社会行为之间的旅游空间,排他性旅游消费阶层专属空间[63]。人文主义观点提供了关于以下问题的解释:这些聚居模式为什么会出现,人们态度和决策行为、历史经验、政治和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聚居模式[4]。
2.2 旅游城市化
旅游城市化导致聚居空间扩张。在欧洲,旅游一直是许多聚居区发展的主导因素,被看作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推手[64]。旅游导致了以前乡村地区的城市化,促使欠发达地区的聚居功能和特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4]。旅游城市化起源于福特制时期的高工资和大众消费,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以独特的象征性符号以吸引旅游者,导致以人口和劳动力的迅速增长,人口集中于旅游服务业和建筑业、房地产业[65-68]。Yin和Muller通过聚居密度化过程研究解释旅游城镇化形成过程[25]。陈志钢和孙九霞对日照市乡村非农化建设中的旅游化现象进行典型案例研究[69]。李亚娟等研究发现北京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旅游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以旅游用地的递增、耕地面积的缩减和宅基地的流转为特征的土地非农化,以乡村人口的外流和乡村聚落的社区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解体化等[70]。黄震方等指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并探讨了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旅游城市化、旅游城市化现象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问题[71-72]。葛敬炳等认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将旅游城市化分为资源驱动型、经济驱动型、综合驱动型等不同类型[73]。朱f和贾莲莲辨析了“旅游城市化”和城市“旅游化”的异同[74]。李志飞和曹珍珍对近50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旅游引导新型城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集中在4个方面:发展特征与动力机制、发展模式与路径、效应与影响、管理与决策[75]。旅游引导新型城镇化是特色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提升,在不同程度上导致旅游地聚居空间的景观变化、新居民迁入和土地利用等变化。高品质集约发展的诉求为旅游地聚居空间发展带来了旅游地新发展模式[75-77]。
2.3 流动性转型理论
尽管逆城市化理论研究为聚居空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但逆城市化研究强调了人口从城市流向乡村的单向流动过程,掩盖了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性的复杂性。Milbourne指出较多学者专注于长距离的城市到乡村的流动性研究,导致了其他类型流动性研究被边缘化[78]。例如,乡村地域内部流动性研究、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流动性、基于乡村聚落等级向上的流动性。这些居住流动性研究有助于理解旅游地住房市场、当地住房需求或新房的潜在需求,而不是仅仅单向的城市向乡村的移民。Gkartzios和Scott认为关于乡村流动性和人口流动的相互联系研究相对有限[79]。文章重点讨论了案例地爱尔兰基尔代尔、南蒂珀雷里郡、克莱尔3个县,探索居住流动性这一维度对旅游地聚居空间重构过程的影响。流动性涉及逆城市化、农村向农村的迁移、当地内部流动性。许多偏远地区增长可以归因于宜居的自然环境,吸引人们(如移民、季节性居民、和/或游客)观光旅游和户外游憩[80-83]。杨钊和陆林认为异地购房往往是生活方式移民和退休移民的先兆,消费导向旅游移民已初显端倪[84]。张骁鸣和保继刚提出了西递村旅游发展对乡村外出劳动力向原社区回流并参与非农产业生产现象的社会经济解释[85]。饶勇认为旅游导致外来精英劳动者迁入,往往造成本地社区边缘化[86]。
3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
3.1 聚居空间演化的宏观机制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取决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30]。可进入性和宜居环境是独特聚居模式的重要要素[18]。大量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对聚居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一系列的因素:人口变化(例如老龄化、住房结构变化等);生产和消费模式变化;现代技术,特别是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87-88]。Gude等分析了大黄石生态系统生态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居发展模式的影响程度[34]。聚居模式主要受农业适宜性、交通和服务设施、自然环境舒适度、过去开发模式、附近小城镇的经济和游憩特征等因素影响。Gkartzios和Scott分析了聚居空间重构的原因涉及:经济需求――在目的地的经济原因(便宜的住房、低的生活成本、就业机会);社会和自然特性――社会因素(如更好地培养小孩、生活质量、没有犯罪)和自然因素(如旅游环境质量较高、较少拥挤);区位――强调区域或住房区位(如接近工作地点、交通线路或亲朋好友等);住房特征――住房因素(更大面积住房、更好住房或配套设施,建设或购买自己的住房);家庭构成的变化――如结婚、离婚等[79]。驱动机制呈现3个阶段的特征:自然资源约束、交通扩张、自然舒适度的追求[34]。
早期的农业社会聚居空间较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Dahms关注了多伦多周边的小城镇的居民点的变化[22]。最初,农业社区是典型短距离型社会,聚居空间主要集中在村镇服务中心及其腹地。土地利用为聚居空间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承载空间,土地利用在调节和控制聚居空间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传统聚居空间最明显地受制于土地质量和农业适宜性[89]。今天,自然因素逐渐减弱,社会经济因素(农业改革和人口移动过程)重塑聚居系统的空间结构过程增强。乡村聚居空间结构受到交通可达性和路网密度的影响[90],相对于大都市区的区位[91],基础设施的提供[30],土地价格、法律约束等[92]。
旅游是聚居空间增长和扩展的主要驱动力。旅游影响聚居系统社会、经济和空间特征。宏观经济和社会条件是居住变化的重要条件,旅游环境是旅游地居住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引致社区季节性和长期居住空间发展的最重要的诱因[93-95]。吸引游客的社区也进一步吸引了永久居民居住和居住投 资[93]。McGranahan研究发现:自然舒适度较高区域往往也是游憩活动集聚区域[80]。特定的宜居环境将导致聚居价格差异化[43,96]。Dredge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澳大利亚麦加里湖,认为旅游影响该地区聚居模式;反之,聚居地社会、经济和空间动力也塑造旅游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39]。Kuentzel和Ramaswamy研究了1950―2001年美国旅游发展、净移民和聚居发展的关系[28]。宜居的乡村社区鼓励旅游者的聚居/居住迁移,表明旅游发展与移民和居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Nepal研究发现:聚居空间和住房类型的增长由旅游者流动性及其需求所主导,而不是乡村聚居空间传统功能决定的[18]。Biagi等通过对居住特征和旅游宜居环境等系列解释变量,分析旅游对住房市场的住房价格或租金的影 响[97]。席建超等分析了三坡镇旅游用地的驱动机制,发现外部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和政府干预与调控等成为旅游城镇用地演变的主要动力[21]。杨俊等主要考虑两种演化动力,一是受地形条件影响,二是受旅游因子影响[33]。李亚娟等指出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便利的旅游区位导向、广泛的旅游政策支持和多元化的产业经济背景等是重要因素[70]。
微观尺度自然环境也影响聚居空间选择。Schnaiberg等采用住房密度作为因变量,设置4组自变量[3]。第一组自变量水质环境包括:湖区颜色、浑浊度、碱度和叶绿素;第二组变量为湖面面积;第三组变量是岸线特征,主要是土地覆盖和植被(湿地);第四组变量为社会变量:土地权属(公有、私有)、可进入性(旅行成本)。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湖区聚居开发密度主要受到湖区面积、可进入性(旅行成本)影响,湿地面积、公有土地面积比重也产生一定影响。Silberman和Rees选择年降雪量、潜在的滑雪季节、距国家森林公园距离、可达性指数、滑雪区距最近聚居地距离,分析了聚居空间区位选择[26]。
3.2 利用主体微观行为响应机制
不同利用主体在聚居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聚居空间重构过程起到重要的作用。旅游者、环境移民、房地产开发商、旅游投资商等,是住房设计、住房质量、聚居规模和形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98]。Gill根据住房权属关系、居住时间和住房类型,对住房市场利益主体进行了划分,包括:服务部门的住户(含零售和建筑工人)、当地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住户、宜居环境寻求者住户、周末旅行者4种类型[99]。Biagi等认为在旅游目的地存在大量的行为主体,涉及需求(当地居住使用者、投资者、租赁者和第二居住所有者)、供给和调节者(银行、当地政府)、供给者(开发商)[97]。Muller等认为度假社区正在吸引新的群体,包括游客、长距离的通勤者、退休人员、第二居所业主和服务从业人员[29]。Yin和Muller指出滑雪度假区和其他游憩山区创造了大量旅游就业,但大部分工作岗位是兼职或季节性的[25]。
不同利益主体或个体决策影响了聚居区位变迁。其中,旅游者仍然是聚居空间变迁的主导因 素[18]。此外,涉及当地企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政府土地利用决策、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早期的聚居地主要受到当地地主和富有的企业家,以及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影响[4]。人口流入旅游地归因于一系列因素,包括生活方式移民、退休移民、福利移民(主要是便宜的生活成本等因素)和度假移民[100-101]。Yin和Muller识别了山地滑雪旅游地服务人员、分时公寓所有者、第二居所所有者等利用主体,采用多主体模型,从不同利益主体或个体区位决策角度,调查了住房密度变化的动力机制[25]。许多美国退休人员、企业家、追求小镇生活方式和适宜的乡村自然环境的迁移者[102-103]。游憩生活渴望和不断增长的空间流动,导致资源利用的竞争进一步加剧[104]。Dahms指出乔治亚湾环境吸引了大量退休人员、农舍、住宅和分时度假别墅的所有者或租赁者[22]。Nepal识别了6个因素来解释聚居空间的变化[18],即早期来自夏尔巴人的移民、地方经济和服务中心的发展、登山者和徒步旅行者、来自珠峰低山地区季节性劳工移民、政府部门。“先锋农户”和“体制精英”的示范效应在乡村旅游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69]。席建超研究发现苟各庄乡村聚落空间扩展隐含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政府、农户、资源、市场等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调控渐进式介入和农户行为等要素在个体和群体间相互影响[20]。
4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社会效应
聚居空间变迁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随着旅游从业者、旅游移居者、游客 等的大量涌入,他们试图将原有的封闭式生活空间、社区公共空间转变为开放式消费空间[105]。随着不同社会群体对稀缺的住房区位的竞争,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对度假区产生了累积效应。围绕社会效应的辩论,主要集中在住房负担能力[106]和乡村绅士化等[54、56]。涉及是谁的空间问题(住房为当地或是新来者)[107]、提供或抵制新住房发展的社会冲突[108]。
4.1 社会关系网络变迁
聚居空间变迁不仅会反作用于居民对旅游从业者、旅游移居者和游客的态度,而且还能深入影响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倾向和行为表现,集中体现为地方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社会关系动态变化过程。Lynch对英国乡村家庭旅馆中主人对空间的使用以及空间利用体现出的主客关系开展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109]。不断度假和旅游服务的需求增加,吸引了大量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就业增加,冲破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结构[97]。住房是家庭过稳定生活最为重要的因素[23]。买房太贵,租房质量较差,导致房东和房客关系紧张。旅游房地产造成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对聚居空间利用的分异,形成不同社会关系网络,体现了功能和权力的分割[110]。第二居所深刻影响着迁移者的社会关系、地方依恋与身份感 知[111-112],社会空间的主体与关系网络呈现出了旅游开发前后的不同[113]。彭丽娟等指出在空间上游客旅游区与古村落建成区重叠,形成游客与居民对有限空间的争夺[114]。李王鸣等分析了杭州西湖龙井村在“景”“村”双重属性作用下土地使用、社会网络关系等方面的演变特征[115]。汪永青和陆林研究发现:大量的旅游者侵占了旅游地居民生活空间,造成旅游者同居民在空间上的冲突[116]。
[3] Schnaiberg J, Riera J, Turner M, et al. Explaining human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 recreational lake district: Vilas County, Wisconsin[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2, 30(1): 24-34.
[4] Nepal S. Tourism and rural settlements Nepal’s Annapurna reg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4(4): 855-875.
[5] Radeloff V, Stewart S, Hawbaker T, et al. Housing growth in and near United States protected areas limits their conservation valu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107(2): 940-945.
[6] Zhang Xiaolin. Rural Spatial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South of Jiangsu Province[M].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9: 55-85. [张小林. 乡村空间系统以及演变研究:以苏南为例[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55-85. ]
[7] Wu Mingwei, Wu Xiao, Cheng Maojie. The Morpholog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2-135. [吴明伟, 吴晓, 程茂吉. 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聚居形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M].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102-135. ]
[8] Li Bohua, Zeng Juxin, Hu Jua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n the research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08, 24(5):70-73. [李伯华, 曾菊新, 胡娟.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8, 24(5): 70-73. ]
[9] Lei Zhendong.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Guanzhong[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2-245. [雷振东. 整合与重构: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222-245. ]
[10] Li Xueming.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0: 13-45. [李雪铭. 地理学视角的人居环境[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13-45]
[11] Wang Chuansheng, Sun Guiyan, Zhu Shanshan. The main progress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western mountainous areas[J]. Human geography, 2011, 121(5): 9-14. [王传胜, 孙贵艳, 朱珊珊. 西部山区乡村聚落空间演进研究的主要进展[J]. 人文地理, 2011, 121(5): 9-14. ]
[12] Zhao Wanmin. Study of Settlement Space in Bayu Ancient Town[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1:35-58. [赵万民. 巴渝古镇聚居空间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35-58. ]
[13] Ma Xiaodong, Li Quanlin, Shen Yi. The form and its regional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 (4): 516-525. [马晓冬, 李全林, 沈一.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J]. 地理学报, 2012, 67(4): 516-525. ]
[14] He Renwei, Chen Guojie, Liu Shaoquan,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d the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 in China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 (8): 1055-1062. [何仁伟, 陈国阶, 刘邵权, 等. 中国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趋向[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8): 1055-1062. ]
[15] Zhang Wenzhong, Chen Li, Yang Yizhao. Research progress of in human settlement evolut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5): 710-721. [张文忠, 谌丽, 杨翌朝. 人居环境演变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5): 710-721. ]
[16] He Yanhua, Zeng Shanshan, Tang Chengli, et al. Rural settlemen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 (12): 1643-1656. [贺艳华, 曾山山, 唐承丽, 等. 中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J]. 地理学报, 2013, 68(12): 1643-1656. ]
[17] Yang Xingzhu, Wang Qun.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effect analysis in the Southern Anhui tourism are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 (6): 851-867. [杨兴柱, 王群.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分析[J]. 地理学报, 2013, 68(6): 851-867. ]
[18] Nepal S. Tourism and remote mountain settlements: Spatial and temporal development of tourist infrastructure in the Mt Everest region, Nepal[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5, 7(2): 205-227.
[19] Wang Yinyin, Cui Ling, Chen Xiangju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under the tourism influence to the small town: Dali City as an example[J]. Huazhong Architecture, 2013, 31 (4):156-160. [王茵茵, 崔玲, 陈向军. 旅游影响下村落向小城镇形态演变特征分析――以大理市喜洲镇为例[J]. 华中建筑, 2013, 31(4): 156-160. ]
[20] Xi Jianchao, Zhao Meifeng, Ge Quansheng. The micro-scale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use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of Yesanpo Scenic Area in Hebei provinc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 (12): 1707-1717. [席建超, 赵美风, 葛全胜. 旅游地乡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J].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707-1717. ]
[21] Xi Jianchao, Zhao Meifeng, Wang Kai, et al. Land use evolution of growth tourism-town from 1986 to 2010: A case study of Sanpo town in Yesanpo tourism attraction in Hebei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1): 1-19. [席建超, 赵美风, 王凯, 等. 1986-2010年成长型旅游小镇用地演变格局――河北野三坡旅游区三坡镇的案例实证[J]. 地理研究, 2013, 32(1):1-19. ]
[22] Dahms F.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the arena society in the urban fiel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8, 14(3): 299-320.
[23] Winkler R. Living on lakes segregated communities and inequality in a natural amenity destination[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13, 54(1): 105-129.
[24] Pawson I, Stanford D, Adams V, et al. Growth of tourism in Nepal's Everest region: Impact o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structure of human settlements[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84, 4(3): 237-246.
[25] Yin L, Muller B. Urbanization and resort regions: Creating an Agent-Based Simulation of housing density in “Ski County”[J].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08, 15(2): 55-75.
[39] Dredge D. Leisure lifestyles and tourism: Socio-cultural, economic and spatial change in Lake Macquarie[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1, 3(3): 279-299.
[40] Johnson K, Beale C. The recent revival of widespread population growth in nonmetropolitan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J]. Rural Sociology, 1994, 59(4): 655-667.
[41] Gotham K. Tourism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new Orleans’ Vieux Carre[J]. Urban Studies, 2005, 42(7): 1099-1121.
[42] Hines J. Rural gentrification as permanent tourism: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est Archipelago as postindustrial cultural spac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0, 28(3): 509-525.
[43] Nelson B.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 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4): 395-407.
[44] Park L, Pellow D. The Slums of Aspen: Immigrants vs. the Environment in America’s Eden[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89-102.
[45] Cloke P, Phillips M, Thrift N. The New Middle Class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s of Rural Living[A] //Butler T, Savage M. Social Change and the Middle Classes[M]. London: UCL Press, 1995:12.
[46] Jordan B. A Theory of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M]. Oxford:Wiley-Blackwell, 1996:45.
[47] Tan Jin, Wang Xiaoyan.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 community under the replacement of space: Based on the filedwork in Zhiziluo Village, Fugong Town[J].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2012, 30(5): 106-110. [谭瑾, 王晓艳. 空间置换下的民族社区重塑――基于云南省福贡县知子罗村的田野考察[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0(5): 106-110. ]
[48] Li Xin, Zhang Xiaoping. On the relation and impac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partial commoditization an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locals’ living space in old towns[J]. Tourism Research, 2012, 4(4): 25-31. [李鑫, 张晓萍. 试论旅游地空间商品化与古镇居民生活空间置换的关系及影响[J]. 旅游研究, 2012, 4(4): 25-31. ]
[49] He Shenjing, Qian Junxi, Xu Yuxuan, et a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midst rapi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44-1056. [何深静, 钱俊希, 徐雨璇, 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J].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44-1056. ]
[50] Liu Jun, Lou Fengye. On the marginal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drop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Liupan Li nationality resettlement area, Sanya, Hainan[J]. Tourism Tribune, 2009, 25(9): 44-50. [刘俊, 楼枫烨. 旅游开发背景下世居少数民族社区边缘化:海南三亚六盘黎族安置区案例[J]. 旅游学刊, 2009, 25(9): 44-50. ]
[51] Zhang Huan . Economic context of marin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island hollow and countermeasures: Take Zhoushan islands as an example[J]. Architecture & Culture, 2012, 9(6): 91-93. [张焕. 海洋经济背景下海岛人居环境空心化现象及对策――以舟山群岛新区为例[J]. 建筑与文化, 2012, 9(6): 91-93. ]
[52] Tao Wei, Xu Chen. The influe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idents' occupations in tourism destination Pingyao[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6): 1143-1154. [陶伟, 徐辰. 旅游地居民职业转换中社会资本的影响与重塑――平遥案例[J]. 地理研究, 2013, 32(6): 1143-1154. ]
[53] Butler R, Hall C, Jenkins J. Tourism and Recreation in Rural Areas[M]. Chichester: Wiley, 1998:25-36.
[54] Phillips M. Other geographies of gentrific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 (1): 5-30.
[55] Smith D, Holt L. Lesbian migrants in the gentrified valley and other geographie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5, 21(3): 313-322.
[56] Stockdale A. The diverse geographie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Scotlan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1): 31-40.
[57] Stockdale A, Findlay A, Short D. The repopulation of rural Scotland: Opportunity and threa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2): 243-257.
[58] Dam F, Heins B. Lay discourses of the rural and stated and revealed preferences for rural living: Some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a rural idyll in The Netherland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2, 18(4): 461-476.
[59] Curran N. The turning tide: Amenity migration in coastal Australia[J].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2008, 13(4): 391-414.
[60] Cowie W. Towards a normative concept of settlemen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problems in the “Lower Limb”[J]. Geoforum, 1983, 14(1): 55-73.
[61] Hall C, Müller D. Tourism, Mobility, and Second Homes: Between Elite Landscape and Common Ground[M]. Bristol: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4:16.
[62] Spencer D. Counterurbanisation: The local dimension[J]. Geoforum, 1995, 26(2): 153-173.
[63] Torres R, Momsen J. Gringoland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ourist space in Mexico[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5, 95(2): 314-335.
[64] Cohen E. Toward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J]. Social Research, 1972, 39(1): 164-182.
[65]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1, 15(3): 326-342.
[66] Mullins P. Class relations and tourism urbanization: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petite bourgeoisi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urban for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4, 18(4): 591-608.
[67] Gladstone D.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Urban Affairs Review, 1998, 33(1): 3-27.
[68] Lu Lin, Ge Jing-bing.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6, 25(4): 741-750. [陆林, 葛敬炳. 旅游城市化研究进展及启示[J]. 地理研究, 2006, 25(4): 741-750. ]
[69] Chen Zhigang, Sun Jiuxia.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 fringe[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cnce Edition), 2007, 28(3): 206-209. [陈志钢, 孙九霞. 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动力机制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7, 28(3): 206-209. ]
[70] Li Yajuan, Chen Tian, Wang Jing, et al. Research on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in metropolitan fringe: A case of Beijing City[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3(4): 162-168. [李亚娟, 陈田, 王婧, 等.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旅游城市化进程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4): 162-168. ]
[71] Huang Zhenfang. Study o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tourist resource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economy developed region: A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J]. Human Geography, 2001, 16(5): 53-57. [黄震方. 发达地区旅游城市化现象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问题探析: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01, 16(5): 53-57. ]
[72] Huang Zhenfang, Wu Jiang, Hou Guolin. Preliminary probing in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00, 9(2): 160-165. [黄震方, 吴江, 侯国林. 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0, 9(2): 160-165. ]
[73] Ge Jingbing, Lu Lin, Ling Shanji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of Lijiang City[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29(1): 134-140. [葛敬炳, 陆林, 凌善金. 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分析[J]. 地理科学, 2009, 29(1): 134-140. ]
[74] Zhu Hong, Jia Lianlian. The form of urban tourism based on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26(1): 151-155. [朱f, 贾莲莲. 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 桂林案例[J]. 经济地理, 2006, 26(1): 151-155. ]
[75] Li Zhifei, Cao Zhenzhu. Tourism-oriented new urbanization: A multi-dimensional comparative study[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7): 16-25. [李志飞, 曹珍珠. 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 一个多维度的中外比较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 30(7): 16-25. ]
[76] Lin Feng. Tourism- oriented New- type Urbanization[M]. Beijing: China Travel & Tourism Press, 2013: 136-155. [林峰. 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3: 136-155. ]
[77] Yu Fenglong, Huang Zhenfang, Cao Fangdong, et al. Influenc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o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 2014, 29(8): 1297-1309. [余凤龙, 黄震方, 曹芳东, 等.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J]. 自然资源学报, 2014, 29(8): 1297-1309. ]
[78] Milbourne P. Re-populating rural studies: Migrations, movements and mobilit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7, 23 (3): 381-386.
[79] Gkartzios M, Scott M. Residential mobilities and house building in rural Ireland: Evidence from three case studies[J]. Sociologia Ruralis, 2010, 50(1): 64-84.
[80] McGranahan D. Natural Amenities Drive Rural Population Change[R].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1999:5.
[81] Deller S, Tsai T, Marcouiller D, et al. The role of amenitie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economic growth[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1, 83(2): 352-365.
[82] Williams A, Hall C. Tourism and migration: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0, 2(1): 5-27.
[83] Johnson K, Beale C. Nonmetrorecreation counties: Their identification and rapid growth[J]. Rural America, 2003, 17(4): 12-19.
[84] Yang Zhao, Lu Li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research system and methods of tourism migr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4): 949-962. [杨钊, 陆林. 旅游移民研究体系及方法初探[J]. 地理研究, 2008, 27(4): 949-962. ]
[85] Zhao Xiaoming, Bao Jigang.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turn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Case study on Xidi Villag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29(3): 360-367. [张骁鸣, 保继刚. 旅游发展与乡村劳动力回流研究――以西递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09, 29(3): 360-367. ]
[86] Rao Yong. Elite labor immigr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local community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Sanya City,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13, 28(1): 46-53. [饶勇. 旅游开发背景下的精英劳动力迁入与本地社区边缘化――以海南三亚为例[J]. 旅游学刊, 2013, 28(1): 46-53. ]
[87] Knox P. 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M]. Essex: Longm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1993: 45-67.
[88] Bell M. Understanding Internal Migration[M].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6: 33-39.
[89] Sevenant M, Antrop M. Settlement models, land use and visibility in rural landscapes: Two case studies in Greec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7, 80(4): 362-374.
[90] Havbaker T, Radeloff V, Hammer R, et al. Road density and landscape pattern In relation to housing density, land ownership, land cover, and soils[J]. Landscape Ecology, 2005, 20(5): 609-625.
[91] Hammer R, Stewart S, Winkler R, et al. Characterizing dynamic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idential density patterns from 1940―1990 across the North Central United Stat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9(2): 183-199.
[92] Ihlanfeldt K. The effect of land use regulation on housing and land pric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7, 61(3): 420-435.
[93] Galston W, Baehler K.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necting Theory, Practice and Possibilitie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5: 123-138.
[94] Knapp T, Graves P. On the role of amenities in models of mig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89, 29(1): 71-87.
[95] Snepenger D, Johnson J, Rasker R. Travel-stimulated entrepreneurial migra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5, 34(1): 40-44.
[96] Taylor L, Smith K. Environmental amenities as a source of market power[J]. Land Economics, 2000, 76 (4):550-568.
[97] Biagi B, Lambiri D, Faggian A. The effect of tourism on the housing market[A]//Handbook of Tourism and Quality-of-Life Research[M].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2: 210-234.
[98] Howe J, McMahon E, Propst L. Balancing Nature and Commerce in Gateway Communitie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7: 88-102.
[99] Gill A. From growth machine to growth management: The dynamics of resort development in Whistler, British Columbi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0, 32(6): 1083-1103.
[100] Stimson R, Minnery J, Kabamba A , et al. Sun-belt Migration Decisions: A Study of the Gold Coast[M].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6: 44-57.
[101] Walmsley D, Epps W, Duncan C. Migration to the New South Wales North Coast 1986-1991: Lifestyle motivated counterurbanisation[J]. Geoforum, 1998, 29(1): 105-118.
[102] Rudzitis G. Amenities increasingly draw people to the rural west[J]. Rur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999, 14 (2): 9-13.
[103] Daniels T. When City and Country Collide: Managing Growth in the Metropolitan Fringe[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9: 99-123.
[104] Theobald D. Landscape patterns of exurban growth in the USA from 1980 to 2020[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5, 10(1): 1-32.
[105] Gosnell H, Abrams J. Amenity migration: Diverse conceptualizations of drivers, socioeconomic dimensions, and emerging challenges[J]. GeoJournal, 2011, 76(4): 303-322.
[106] Satsangi M, Dunmore K. The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provis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in rural Britain: A comparison of the Scottish and English experience[J]. Housing Studies, 2003, 18 (2): 201-218.
[107] Campbell H. Interface: Planning for the countryside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which and whose countryside?) [J].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03, 4 (1): 75-99.
[108] Murdoch J, Lowe P, Ward N, et al. The Differentiated Countryside[M]. London: Routledge, 2003: 34-38.
[109] Lynch P. Homing in on home hospitality[J]. The Hospitality Review, 2000, 2(2): 48-54.
[110] Wu Yuefang, Xu Honggang.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ocio-cultural impact of tourism real estate in the ancient of Dali[J]. Human Geography, 2010, 114(4): 67-71. [吴悦芳, 徐红罡. 大理古城旅游房地产的发展及社会文化影响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 114(4): 67-71. ]
[111] Xu Wenxiong, Bao Jigang.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vacation-oriented second homes: A case study on Sanya City[J]. 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6, 38(5): 63-67. [徐文雄, 保继刚. 度假地型第二居所空间分布和影响研究――以三亚市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8(5): 63-67. ]
[112] Wu Yuefang, Xu Honggang. A literature review of second residence tourism: Implication on mobility analysi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6): 799-807. [吴悦芳, 徐红罡. 基于流动性视角的第二居所旅游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6): 799-807. ]
[113] Fan Wenyi. Study on social space of tourism-oriented small town: Case of Yangshuo, Xing’ping and Daxu in Li River Area[J]. Study of Ethnics in Guangxi, 2010, 100(2): 192-196. [范文艺. 旅游小城镇社会空间问题研究――以漓江流域阳朔, 兴坪, 大圩调查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10, 100(2): 192-196. ]
[114] Peng Lijuan, Xu Honggang, Liu Chang. A social exchange approach to the mechanism of person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Xidi Village[J]. Human Geography, 2011, 26(5): 29-33. [彭丽娟, 徐红罡, 刘畅.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西递古村落私人空间转化机制研究[J]. 人文地理, 2011, 26(5): 29-33. ]
[115] Li Wangming, Gao Yichen, Wang Ying, et al. Spatial harmonization of village in scenic area: A case study of Longjing Village in the West Lake scenic area[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 37(8): 46-51. [李王鸣, 高沂琛, 王颖, 等. 景中村空间和谐发展研究――以杭州西湖风景区龙井村为例[J]. 城市规划, 2013, 37(8): 46-51. ]
[116] Wang Yongqing, Lu Lin. Residents’ construct space strategy of destination[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08, 24(11): 1038-1041. [汪永青, 陆林. 旅游地居民的再创空间[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08, 24(11): 1038-1041. ]
[117] Hammes D. Resort development impact on labour and land marke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 21 (4) : 729-744.
[118] Marks R.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The contradictions and ambiguities of tourism in the Stone Town of Zanzibar[J]. Habitat International, 1996, 20(2): 265-272
[119] Beyers W, Nelson P.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forces in the non-metropolitan West: New insights from rapidly growing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4): 459-474.
[120] Lindberg K, Johnson R. The economic values of tourism’s social impac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7, 24 (1): 90-116.
[121] Gallent N, Tewdwr-Jones M. Second homes and the UK planning system[J]. Plann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2001, 16 (1): 59-69.
[122] Hettinger W. Living and Working in Paradise: Why Housing is too Expensive and Why Communities can Do about It [M]. Windham: Thames River Publishing, 2005: 72-103.
[123] Chen Zhansh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wns and scenic areas: A case of study of towns in Gulin Lijiang scenic area[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5, 29(1): 84-87. [陈战是. 小城镇与风景名胜区协调发展探讨――以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内小城镇为例[J]. 城市规划, 2005, 29(1): 84-87. ]
智慧社区建设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智慧社区 智慧城市 需求分析 系统架构 运营方式
1 引 言
城市发展是世界文明进程的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社会的主题之一。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这种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百分比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等都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1]。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数量显著增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规模持续扩张,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经济蒸蒸日上,城市已经成为拉动中国GDP增长的火车头。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和消费的更集中、更大规模、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以及更大的资源需求、更复杂的城市管理和社会关系。然而,城市化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与威胁,包括城市人口密集、管理复杂,人与自然矛盾突出,城市经济发展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等。城市所面临的这些挑战,贯穿在城市的组织、业务/政务、交通、通讯、水和能源六大核心系统。为了使城市运行中所依靠的核心系统更充分并且有效地工作,迫切需要引入科学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技术。在此背景下,建设智慧城市已成为解决城市发展所面临问题的首选方案。
关于“智慧城市”,IBM公司曾对其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即“智慧城市”是指借助物联网、传感器、数字家庭、路网监控、票证管理、智慧社区等诸多领域,构建城市发展的智慧环境,形成市民生活、产业发展、社会管理的新模式的新城市形态[2]。在互联网、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等信息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智慧城市的建设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首席工程师单志广透露,我国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总数达到了154个,投资规模预计超过1.1万亿元[3]。
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建设中智慧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城市的建设不可能孤立于社区之外[4]。因此,以智慧社区为起点,采取“从下而上”的构筑方式,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智慧城市建设策略。目前,对“智慧社区”国内还无统一的定义,但概括综合各地正在进行的“智慧社区”建设,其具体内容大致是综合运用互联网、通讯网、物联网技术,将楼宇、物业、家居、路网、医院等诸多领域的信息加以充分互联,并基于社区公共数据资源中心,综合开发利用各类社会信息资源,从而实现社区管理、政府职能以及社会服务的智慧化。
2 智慧社区需求分析
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模组,它对外承载着社区与城市的信息互联,满足政府、企业和个人对社区内部信息的需求,对内承担着感知层信息的收集、转换、处理,并与互联层完全连接和融合,满足社区内“高效、节能和环保”运行过程中对信息的需求,以达到“安全、舒适、方便、快捷”的目的。
系统框架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第一步,近几年对中国如何构建智慧社区的架构问题也有许多探讨。大部分学者在社区信息系统的总体构架方面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社区信息系统应分为应用层、功能支撑层和数据技术平台层[5]。根据这个思路寻找解决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在部分地区试点成功。
但是本研究认为,对智慧社区建设不仅应考虑社区物管和居家的基本需求,还要立足于智慧城市、感知中国的层面去规划和建设。
据数字社区建设过程中的需求调查和智慧城市对社区的要求,智慧社区的需求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 智慧社区的基本功能需求。智慧社区有政府(政府机构、执法机构)、企业(物业、商业和服务)和个人(居民、来访者)三大类直接参与者,物业作为主要使用者,其功能需求单列,各方对智慧社区系统的功能需求不同:①政府:以“居民信息管理”为核心,关注环境、生态、公共安全、就业、社保、医疗等民生方面信息,并对其进行收集、处理和响应。包括社区经费管理、综治维稳、居民管理、计生管理、民政管理、劳动保障、党建管理、文教管理、志愿者管理、社会救助、平安社区等。②物业:关注治安、物业维护、社区环境、财产和人身安全、协调外部企业对社区的相关业务。包括保安消防、物业管理、物业档案、环境监测、电梯管理、停车场管理、垃圾回收清运、电子巡更、电子围栏、小区一卡通等[6]。③企业:关注企业在社区的服务、收益及设备维护,新产品、新服务的推广及商务活动。包括商户管理(商品预定、服务预订、积分管理、结算管理等)和面向服务(信息的、通知推送等)等方面。④个人:关注社区所提供的环境、服务、安全等方面的内容。包括居家、出行、安全、方便、信息服务、社区办事管理、家居智能管理等方面。
? 智慧社区的性能需求。①快速扩展能力:能通过应用模板、引擎,提供新功能、业务的扩展,以适应高速发展的技术政务、业务功能的发展与变化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为快速搭建各项业务应用提供保障。②应用集成能力:具有定义标准接口,支持第三方应用集成、数据集成的能力。③资源共享能力:向政府、企业提供社区相关资源,提高自身与城市、社区间、企业的数据交互。④系统应该具有安全、可靠、易管理、易维护、低成本的特点。
3 智慧社区建设中待解决的问题
智慧社区是在智慧城市构建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化而提出的,而智慧社区的建设领域零散、应用水平有待提高,尚未形成“面”上的整体推动态势,从而导致社区建设中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化。综上所述,要完整实现智慧社区的功能和性能需求,无论从现在或未来的角度看,不可能由任何一家供应商完整地提供所有服务,考虑到技术进步和管理的逐步完善,基于基本架构和架构的可扩展性来构建智慧社区,才能赋予智慧社区不断自我完善的生命力。所以,基本架构和架构的可扩展性成为智慧社区建设关注的焦点,其依赖于以下几个问题的解决:
? 有效的总体规划。在智慧城市的框架内,建立清晰的社区发展策略与规划:充分考虑居民、企业和政府的信息需求,进行全面的统筹规划;根据社区环境、定位、特色等要素量身定做规划;严格按照智慧城市对数据接入、数据处理、应用框架、业务接口规范进行系统规划和设计,避免信息孤岛出现。
? 建设可感知的社区。充分利用3S、3G等数字化技术和手段,对社区基础设施与生活相关的设施进行信息化处理和利用,将人与人之间的P2P通信扩展到机器与机器之间的M2M通信。由“通信网+互联网+物联网”构成充分互联的基础信息网络,发挥三网协同效应。
? 建设完整、科学的标准体系。从国家层面上,政府牵头主导,成立各专业领域的行业信息化标准组织,促进广泛的行业用户和厂家参与,形成完整、科学的标准体系。针对使用规模大、集中度高的行业,通过政府推动引导逐步形成完整、科学的标准体系,为智慧社区、智慧城市和智慧中国的建设奠定基础标准体系。
4 智慧社区系统架构的构建
合理的社区架构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向纵深发展的迫切需求。为使社区的信息资源有序、主动、高效,实现整合管理和深层次的利用,提高社区的运作效率和管理决策能力,实现社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与智慧化,使智慧社区真正融入智慧城市建设,本研究以智慧社区的功能需求和性能需求为导向,结合智慧社区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在基于4C技术(由计算机、自动控制、网络通信、IC卡等组成)及3S技术(由GIS、RS、GPS组成)等多种技术的基础上,对业务、标准、管理流程、应用和信息进行一体化设计,提出智慧社区系统架构[7-8](见图1),该系统架构由网络层、数据层、支撑层、表现层构成。
该架构从参与者的视角上关注表现层是否实现自身功能需求,而事实上,是由隐藏在表现层后面的支撑层、数据层和网络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满足系统功能需求和性能需求的。
4.1 表现层
表现层是智慧社区直接表现功能需求与性能需求、实现用户体验的软硬件系统。面向智慧社区三大直接参与者,通过不同终端,例如手机、PC、PAD、户外屏、IPTV等,提供社区应用的入口访问,然后根据可控性策略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9-10]。该层的具体实施策略包括:①各种感知设备、智能设备自动完成对相关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和利用,同时主动或被动地告知参与者。②为了实现与智慧城市、政府、企业、商业以及其他社区的通信,提供专门的访问策略和标准接口。
4.2 支撑层
支撑层是基本构架的核心。该模型不仅是为了满足智慧社区的功能和性能要求,同时也是系统可扩展性的实施者。该层主要由可扩展模板管理和系统引擎组成,功能有:
? 可扩展模版管理:是指系统完成后,可扩展模板可实现对新增应用系统或子模块的动态升级。只要符合数据标准接口和系统模板规范要求,就可将数据按数据库分类附加到数据层,应用子系统模板即可加入可扩展模板管理中,新应用或新功能即能实现与原系统的无缝集成,使软硬件均能即插即用。
由于系统面临技术的快速发展、管理方式方法的不断更新以及管理业务流程重组等实际情况,故要求其能快速升级,以保障整个系统正常运作。可扩展模板能管理和实现对不同供应商的软硬件产品的集成,有效地避免系统重建,达到支撑层能力及应用的扩展,使系统具有自成长的生命力。可扩展模板管理结构如图2所示:
? 系统引擎:对社区系统内部的数据进行分析、统计、过滤和挖掘等,内外数据交互和特定消息响应采用标准引擎(见图3),适用于更高层面(城市的角度)对社区资源利用,标准化引擎大大降低了系统投入和维护量。
4.3 数据层
数据层以数据交换、数据抽取的接口规范为标准,对不同应用子系统的数据采用集中、分类、一体化等策略,进行合理有效的整合,建立有序的社区数据中心,从而保障支撑层内各不同应用之间的互联。
数据层作为社区管理体系的数据中心,在开放网关环境下,主要的组成部分如下:
? 标准类数据库,包括涉及社区内业务、政务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数据库系统、数据交换标准等。
? 公用类数据库,包括社区综合统计信息库、社区空间信息库、社区服务资源信息库、社区人口资源信息库、社区物业名录信息库等。
? 社区数据:以满足用户信息交流、、沟通等需求为特征,处理和存储社区内的信息服务数据,包括收费服务数据、治安消防数据、日常行政工作数据、社区文档数据、图纸、多媒体数据等。
? 实时数据:以时间序列为主要特征,处理和存储智能设备运行过程中的实时数据。实时数据主要以社区内部使用为主,如社区视频监控、音频等数据,更新周期短,数据量大。
? 地理空间数据:处理和存储智慧社区网络拓扑结构数据、各类管线结构数据(小区平面、地下管线、楼层垂直管线等)、小区电子地图等数据。
4.4 网络层
网络层主要是实现将社区内部智能监控系统、感应设备设施、电信电视网系统、信息服务系统的信息接入城市通信网络的功能,实现数据在网络路由层的传输、交换以及支撑各子网络之间的信息传输。它是实现物联网、通讯网、互联网互通的物理保障。
如图4所示,网络层由物联网、通讯网、互联网构成,它们在信号传输上采用自己的端口接入各自的组网中,在网络路由层各自独立。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在它们之间设立隔离装置,一般通过有线的方式实现互联。
5 运营方式
我国基础网络的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无线城市)、中国电信(光网城市)和中国联通(智慧城市)已经为智慧城市建设进行了大量网络基础设施的准备工作。而在系统研发和集成方面,国内的华为等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尝试。
目前,学者们对智能社区的运营方式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供应商与社区物业在资金投入、后期运营和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多种组合的运营方案[11],就社区建设本身而言,它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案,也有很多成功案例。
但从目前城市具体情况来说,社区大小、档次相差很大,通过政府招标多家系统服务商、硬件供应商的运营方式,会造成物业投资负担过重,社区信息化参差不齐,无法与智慧城市的建设统一起来[12-13]。
智慧社区的建设作为智慧城市建设中惠民内容的一部分,要使其真正融入智慧城市,避免出现数据孤岛,所选择的运营方式不仅应关注经济、技术和局部功能,还应该注意智慧城市规划、集成能力、可扩展性、数据交互标准和信息安全规范等因素,考察运行机制是否有利于新技术有效、及时地应用,确保社区和城市建设融为一体。
采用按功能分层BOT(build、operate、transfer)的方式是一种值得尝试的运营方式。BOT方式在市政工程中应用非常普遍,在信息化建设中还是一种较新的尝试。基于BOT方式的智慧社区运营方式内容包括:①建设(build):政府牵头,参与制订应用准入制度,像城市建设规划一样审批复核智慧社区建设规划,确保社区建设中的软硬件符合智慧城市建设要求,从源头上杜绝软硬件重复建设的可能,指导智能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应用,通过契约授权运营商负责具体的建设实施。②运营(operate):政府负责运营监督,运营商拥有一定的期限专营权,负责运营管理。③移交(transfer):运营权到期后,运营商将运营权移交给政府。
该方式的优点在于:政府起监督、协调作用,物业所承担的投资和风险都非常小,可以保证智慧社区的建设有序运行与资金回笼,有效地促使运营商和相关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规避技术升级和自身需求突变风险,从而实现政府、物业和供应商多方的共赢。
6 结 语
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是智慧中国在不同层次上的组成元素,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标志,同样也是世界各国研究与发展的热门领域,是城市与社区发展的方向。智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用基本架构、集成能力、可扩展性、数据交互标准和信息安全规范等指标综合评估社区建设,将有利于规范社区和城市建设。然而,目前智慧社区的建设还面临着许多的挑战与威胁,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化。本研究针对现在智慧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从智慧社区直接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分析他们对系统的功能需求与性能需求,并充分考虑智慧社区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智慧社区的整体设计架构。此设计架构力求在功能需求、性能需求、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系统技术应用四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并对系统运营提出可操作的运营方式,从而获得一个先进、科学以及经济的智慧社区建设和管理方案。
参考文献:
[1] 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 IBM商业价值研究院.智慧的城市在中国[R/OL].[2012-09-02].
[3] 我国智慧城市达154个 投资规模将超1.1万亿元[EB/OL]. [2012-08-22]..
[4] 郭华东.从认识数字地球来认识数字城市[EB/OL].[2009-10-24]..
[5] 李焱. 中国社区信息化及其系统结构的框架研究[J].电子政务,2012(5):91-95.
[6] 王要武,李良宝.数字社区的功能需求与系统构建[J].哈尔滨建筑大学学报,2002,35(6):85-88.
[7] Sillence E, Baber C. Integrated digital communities: Combining Web based interaction with text messaging to develop a system for encouraging group communication and competition[J].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 2004(16):93-113.
[8] 刘春年,邹珊.数字社区市场的发展及探索[J].情报杂志,2007(4):132-136.
[9] 戴瑜兴,杨金辉,肖昕宇.数字化社区智能化系统一体化设计[J].低压电器,2007(2):19-23.
[10] 李端明 李宇翔.U型组织中信息系统扩展访问控制模型的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9,53(24):46-50.
[11] 吴余龙.智慧城市的投资运营与评估[EB/OL]. [2012-08-23]..
[12] Zeng Mingxing, Chen Qiang, Li Hongli. Research on innovation model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digital city[J]. Energy Procedia,2011(13):1804-1810.
[13] 吕剑亮,李伟.中国数字化城市发展模式研究[J].情报科学,2006,24(5):672-675.
[作者简介] 李宇翔,女,1964年生,副教授,13篇。
智慧社区建设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智慧社区;社区居民;移动网络
目前,全国很多城市开始智慧城市的相关建设,作为城市主要组成部分的社区建设也在持续进行。智慧社区的建设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础设施上智慧社区建设需要更多质量可靠、性能稳定、物美价廉的硬件产品;软件设施上智慧社区建设应打造适合城市发展的智慧社区平台。我国幅员辽阔、民族多样,不同地区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所以关于智慧社区的运营模式也不尽相同。
1智慧社区
1.1智慧社区的概念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科技越来越方便人们的生活。智慧社区是社区管理中的一种新的理念,是新科技下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型的管理模式。智慧社区是指充分利用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为社区的居民提供了一个现代化、智慧化、智能化的生活环境,从而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社区服务,形成一种智能管理形式的社区。从专业角度出发,智慧社区涉及到智能家居、网络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多种领域。智慧社区是一种在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产业下的新“产品”,该“产品”充分发挥了信息技术通信产业的高速发展、领先的RFID相关技术,以及电信业务中信息化基础设施良好等优势。
1.2智慧社区的作用
智慧社区可以平衡社会、经济和环境的需求,同时提供优化信息化资源,为各种流程、系统和产品提供城市智慧化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为城市化进程,以及经济化建设带来了很多利益。例如,某市的妇幼保健医院的移动医疗,已经可以实现患者提前预约门诊,在手机上查阅各项检查报告等功能。将装备了移动医疗设备的体验车开进社区,为社区居民上门服务,提供健康检查、疾病预防、现场打印体检报告等服务,并将社区居民的体检数据保存在医院的内网中,建立社区居民个人的电子医疗档案等。再如,社区居民如果在马路上发现井盖不见了或者是树被风吹倒了等日常生活常见现象,居民都可以利用手机拍照的功能,将照片以微信(彩信)的形式发送到应急联动中心,这样相关的各个职能部门就能实时地去解决,通过智慧社区平台系统,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共同创建和谐美好的新社区。
1.3发展现状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各地区、各民族生活方式不同的影响,智慧社区的建设并没有固定的商业模式。智慧社区的建设要综合考虑民族文化、社区文化、周边环境设施以及住户的生活习惯,要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于社区发展的商业模式,从而更好地建设智慧社区的新模式。智慧社区的建设是近几年刚发展的新项目,各城市大力扶植社区建设,也有许多物业公司、房地产公司以及风险投资公司,都在向智慧社区方向进行大量的投资和探索。智慧社区的经济投入并不能立竿见影地见到经济效益,这是行业回归理性发展的表现状态,需要从更长远的角度去观望经济收益。因此,合作共赢是智慧社区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企业以及民众应用共同参与到智慧社区的建设中,投入更多的物力、财力和精力去经营建设好智慧社区。如在智慧社区的移动网络建设中,可以更好地实现即定的具体目标,利用前沿的信息化技术,针对于智慧社区存在的问题,从管理、服务、通知等多个角度进行实践,以确保移动网络的智慧社区解决方案的实现。
2基于移动网络智慧社区的方案
2.1设计时应规避的问题
(1)智慧社区的建设包含的系统和产品非常多,负责运行整个社区平台软件的开发商,都不能提供完整的系统和产品。(2)智慧社区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各个开发商在进行开发时,由于产品和系统过多导致开发难度较大,而且各个开发商之间也无法实现互通互利,如果全都由一个企业进行开发,需要的时间和财力的投入难以想象。(3)虽然智慧社区的概念在逐渐地被人们所熟知。但由于拥有住房的用户都已经在对应社区生活一定时间,对所处的生活模式已经形成了固有的习惯。很多用户认为没有必要去接受这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改变自我已经所习惯的生活方式。(4)独立的开发一个新的APP,需要用户去学习许多新的功能,而这样的模式并不能使很多用户轻易接受。
2.2方案设计概要
2.2.1功能构架
围绕智慧社区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形成解决设计方案的思路。包括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与社区通告。社区用户在对社区内的移动终端专用的信息移动网络,对养老,医疗等数据进行采集,该数据在系统中形成电子化采集。政府通过专用的移动通信网络,对采集的数据通过推送页面,使社区的居民对该服务进行评价,充分地表达社区居民的想法和对智慧社区服务建设的建议。通过大数据的应用,将社区居民需求的信息通过电子化应用、电子化升级、电子化开发等方式,在社区展示牌进行展示。
2.2.2社区信息化功能
移动网络的服务端与数据业务服务的安全管理体系,在前端展现时要体现出服务对象,包括社区服务中心,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等。服务的渠道可以通过社区电子屏、飞信接口、平板电脑、个人电脑小助手、个性业务和市民主页。用户在接受服务时,包括的内容有工作协同,无线采集、服务支撑、综合评价、公告通知。该系统的核心应用层包括社区管理工作、协同系统无线信息采集系统、社区服务支撑系统、社区综合评价系统、以及社区公告管理系统。社区的信息接口包括虚拟服务层和核心数据层,通过虚拟应用以及数据处理,从而达到非结构化数据的采集、、管理、资源接收等核心数据层的应用。飞信网关接口,离线交互数据交换接口,可通过社区云计算系统、系统管理平台、安全管理平台、Web应用中间件信息支撑层来支持IT基础设施,服务器系统集中存储系统网络系统网络安全设备等信息基础层。
2.2.3智慧社区的内容
(1)协同功能。上门巡视工作的工作人员,可以提供随时随地的专用网络联系沟通。通过PC、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在移动网络支持的条件下,在移动设备的主页面上选择社区通信化软件,进入到社区信息化的平台中,用户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接收信息任务,在该软件的使用上加以计费。居委会的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后台登录,在网络上将飞信账号,授权账号进行捆绑。通过社区信息化软件中的企业飞信界面,指定工作给工作人员完成用户的任务,并且居委会管理人员还可以对完成的任务进行巡查和监督,以保证通信的实时沟通。(2)本地信息采集功能。通过PC和移动设备进行现场采集,将含有文字、数字、录音、视频、照片、电话、短信等信息收集在用户的存储数据中,将采集后的数据进行保存、分类,以便日后的使用。信息采集功能需要包括前端采集功能,社区居民可以到用户所在的家中进行日常的巡视,如发现家中有老人存在的情况,要对老人家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进行采集;信息采集功能在后端工作时,可以形成闭环,请社区居民进行评价。该功能对小区存在的安全隐患可以进行排查和处理,并采集相关的数据进行综合的处理。后端采集管理系统,对前端系统采集后的数据进行相应的管理,实现社区的管理人员在巡视过程中跟踪、监控和对采集的数据处理。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进行评价,可以通过移动公司自由的短信,网线、网站的方式填写综合的服务评价问卷。
3智慧社区设计方案的实现
社区信息的设立是为更好地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平台数据存储、大数据分析等融会在一体,通过服务自助化、运营自主化、决策智能化的方式,将社会通知、活动信息化、在线查看缴费情况、社会周边商家服务、物业服务统一化等归纳为服务自助化中;将远程统一服务、运营状态实时监控、广告自动播放等归纳为运营自动化中;将基于数据营销活动、精准社区业主服务、商业精准营销、智能数据分析等归纳为决策智能化中。移动互联网技术为社区带来了科技改革,可以享受到更为人性化的服务,使用智能设备可以降低运营成本。通过智能化的管理,可以拉近业主和物业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引入第三方的合作为物业管理增加收入。对现有社区的智慧化改造,是一个抛弃陈旧管理,打造新型的智慧社区管理的方式,业主通过新的信息化服务,可以接受社区新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还可以重新构建业主与物业之间的关系,而对于物业管理,这种新形势主动创造了社区服务管理的价值,为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智慧社区管理可以通过3方面来实现:(1)可以实现手机APP智能门禁,社区居民通过手机APP注册业主用户,经过物业管理办公室相关认证并授权后,手机APP账户就具备养的智能钥匙功能,可以通过手机APP自己开门或者是为远道而来的客人进行远程开门,社区居民与访客可以进行远程视频,业主通过APP内的访客留影,可查看开门记录;(2)可以通过智慧物业进行邻里互动,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由于信息时代的发展,邻里之间的冷漠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注册APP的用户可以通过物业的认证,享受到物业服务,如门卫接收快递、费用催收、维修通告等服务。社区居民也可以直接通过APP进行故障申报,社区内的用户可以在APP平台面进行信息交流,信息互动增加与邻居间沟通交流,促进和谐友好的社区关系。(3)还可以认证识别社区周围的商家。社区居民通过手机APP的网页,可以了解到社区周边的商家服务信息,可以在线直接下单进行支付,选择自己想要的个性化服务,对于感兴趣的商家也可以自行关注或入住该平台,实时掌握该商家的优惠促销信息。
4结语
智慧社区的设计与实现,方便了社区居民的现代化生活,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活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谢新翔,王驰,朱传华,等.基于移动网络的智慧社区解决方案设计和实现[J].电信技术,2015,(11).
[2]朱琳,刘晓静.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智慧社区服务公众采纳实证研究———以打浦桥街道“IN标签”为例[J].电子政务,2014,(8).
[3]冯亚飞,陈连刚,刘建华,等.基于移动GIS的北京市智慧社区研究与实现[J].地理空间信息,2017,(4).
[4]陈军.基于Oauth协议的智慧社区平台的设计与研究[D].苏州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