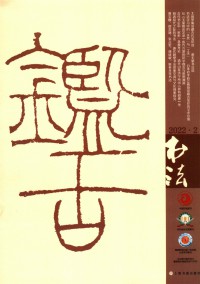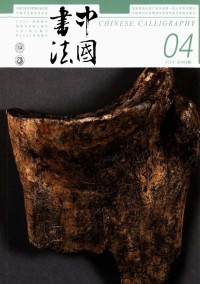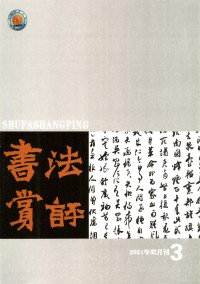书法艺术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书法艺术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书法艺术范文第1篇
关键词:书法艺术书法欣赏书法作品
书法的欣赏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眼高手低”的书法家从没有过。历代的书法家大多是具有高度鉴赏能力的书法评论家。他们都十分重视“读帖”。所谓“读帖”,就是通过观摩书迹和碑刻去领悟书法家所采用或创造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借以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对于一个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来说,同样需要重视读帖,逐步学会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的能力,取其所长,拼其所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如果毫无区分地加以一概兼收,则往往进步不快,甚至会走弯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来的说法各不相同,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欣赏标准。
康有为在《广艺双楫•十六宗》中,提出了十条评论标准,即所谓“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辉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发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郭绍虞在《怎样欣赏书法》中提出了六条标准:“一、形体,看结构天成,横直相安;二、魄力,从笔力用墨看;三、意态,要飞动;四、流派,不拘泥碑帖,不以碑的标准看帖;五、才学,书法以外关系;六、气象,挥朴安详。”
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欣赏书法作品时的参考。如果进一步加以归纳,则不外乎“形”、“神”二字。所谓“形”,指的是由特殊的笔画线条所构成的外形,包括字的笔画、字的结构、一幅字的布局;所谓“神”,指的是上述外形中内在的精神,包括笔力、气势神态、情感等各个方面。因此,欣赏书法作品,不仅要看一点一画、一字字和整幅字的外形,更要看它的笔力、气势、神态。如果外形美观多姿,内在奕奕有神,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形神兼备”的好作品。分析、欣赏书法作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字的笔画长短、粗细、浓淡是否多变而适宜
汉字是由若干个线条式的笔画有机的组合而成的,这若各个笔画,尤其是一字之中的相同笔画,在字中不能长短、粗细、浓淡一模一样,应该而且必须有所变化。如“多”字的四个“撇”画,唐太宗认为,应该分别写作,一缩,二少缩,三亦缩,四须出锋。这里所说的“缩”,就是笔势收缩而不伸展,含有“短”的意思:“锋”就是笔势伸展而不收缩,含有“长”的意思。“多”字的“撇”画是这样,其它的笔画也是这样,否则,字形就显得死板,单调,也就无艺术可言。
二、字的“重心”能否给人以稳健的感觉
字姿可以而且应该多种多样、千姿百态,但不可忽略必须把字的重心“稳住”。欧阳询的字,初看起来,有摇摇欲坠之感,但仔细一看,它犹似千年古塔,虽欲倾却“重心”不离地,依然稳健如新。有些书法欠佳的字,平躺在纸上似乎四平八稳,不偏不倚,但如果一竖起来,则往往东倒西歪,中心不稳。因此,要判别字的重心如何,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纸竖起来,看看它有没有“倒塌”。
三、字势是否自然
宋代王安石有一句论书名言:“不必勉强方通神。”所谓“不必勉强”,就是历来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们都一致强调的要“自然得体”。王羲之在给他的儿子王献之传授书法经验时说:字要“自然宽狭得所”,“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独擅一家之美”,关键在于“天质自然”。
四、看整篇书法作品的章法、笔势是否一气呵成、融会贯通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犹如一幅好的山水画,它必然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气势连贯,笔虽短而意却连。汁白以当黑,疏密得当,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书法作品中的落款、印章也是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注意是否用得恰倒好处,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若是画蛇添足,也会有损于整幅作品的艺术性。
五、看书法作品中的笔法是否有法度有新意
书法艺术具有极强的继承性,书写者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度。但是,仅有继承,甚至与古人写的一模一样,还称不上真正书法艺术,充其量只能是他人的“奴书”,还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因此,在评论和欣赏书法作品时,要看作品中能否正确的处理好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六、在欣赏书法作品时,要适当地了解其创作的时代背景
书法作品和文学作品一样,与作者书写时的心情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艺术风格常随作者的年龄和心情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个书法家可以由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心情而写出不尽相同的甚至截然不同的作品来,如颜真卿中期写的《多宝塔碑》,是在和平环境的得意之中写就的,字势端重浑厚,清晰悦目,成为楷书中的代表作;他晚期写的《祭侄文稿》则是在朝廷岌岌可危,侄儿不幸身亡之中写就的,悲愤之情夺腔而出,于是,出现了笔画浓淡、疏密、大小不一,甚至涂涂改改的粗犷、潇洒的风格,成为行书中的代表作。因此,一定要把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评论和欣赏,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七、欣赏书法要有一定的艺术想象力,要防止以实论实
书法艺术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和思想;书法艺术;《书法雅言》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4-0081-02
明代项穆的《书法雅言》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它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为立论基础,其中专立《中和》一章,集中阐述其书法美学主张。项穆提出中和的审美思想,正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他说:“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况夫翰墨者哉。”黄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中说:“项穆的《书法雅言》自始至终围绕中和二字论书,所谓规矩从心,中和为的。在文章中,他论‘古今、辨体、规矩、神化、取舍’……无不以‘中和’观照。”①我们从《书法雅言》的17章论述中都可以看到中和思想的影子。可见,中和的美学思想在项穆的书学思想中体现得极为深刻。
项穆的中和美学思想是在传统儒家中庸思想的基础之上提炼出来的。关于“中庸”一词,何晏注《论语》:“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郑玄注《礼记》说道:“明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可见,中庸思想的实质即为中和思想。朱熹《中庸章句》:“游民曰:‘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庸和中和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对于中和涵义的解释,朱良志先生说:“儒家哲学中的中和思想有三个要点:一是中体合用;从哲学基础上看,儒家和谐美学思想当以和谐二字为要。中是其体,和是其用。本立而道生,中在和谐思想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或许可以这样说,只有在‘中’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和’……”②这种中庸、中和的观念不仅反映在书法史的发展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书法艺术中本来就有来自文化层面的依托。丛文俊先生说过:“书法以文字的规范之美筑基,以艺术的个性之美为动力,二美有相通之处,但个性化的艺术创造往往带有摆脱文字社会化之共性美的离心倾向,由此产生实用与艺术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和的标准是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规范中确立起来的,它必然也要反映到书法活动当中,用以平衡、消解其实用与艺术需求之间的矛盾。”③在汉字的书写艺术成为独立的书法艺术的汉代,这种汉字实用与艺术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很明显了。之所以汉字书法艺术能够发展至今,这与中和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侯开嘉先生曾在其《俗书与官书的双线发展规律》一文中提出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官书和俗书双线并行发展的重要规律。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就是由于汉字发展过程中实用性和艺术需求之间调和、折中所呈现的规律。
在具体的艺术品评过程中,“中和”一词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为书法艺术的品评树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个标准对于古代书家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我们知道,历来书家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时都说其具有中和之美,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中和哲学思想,即强调其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的调和统一。孙过庭的《书谱》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时说:“王右军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④“志气和平,不激不厉”反映的是一种中和的美学观。同时,我们通过项穆的《书法雅言》可以看出其对王羲之的书法同样是推崇备至,他所言真正意义上的书法风格的美应该是“不激不厉,骨态清和”的美。《书法雅言・品格》中有这样的描述:“又书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则点画不混杂,整则形体不偏邪;第二要温润,温则性情不骄怒,润则折挫不枯涩;第三要闲雅,闲则运用不矜持,雅则起伏不恣肆。”他所认同的书法美的原则是清整、温润和闲雅,其实这正是中和之美的反映。对于一位书法家来讲,他们追求的标准应该是能够为书法作品赋予清整、温润和闲雅的美学特质,无论是点画用笔、结体取势、章法布局,还是书作整体的韵律感和美感,都应该把握住“不激不厉”的尺度,即中和的审美原则,这样才能使书作达到一种至高至深的境界。
当今书坛一些人强调书法艺术应该倡导狂、怪、奇的艺术个性,认为这样的书法作品才具有真正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太过偏激。从某种层面讲,它正好忽略了书法美存在的本质内涵。我们知道,中国的书法艺术是汉字的形体美基于正确的汉字书写上的一门独特艺术,它的本质离不开汉字的正确书写,换言之,离开汉字书写的书法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那么我们试想,要是一幅书法作品在形式上搞得有声有色,而汉字的处理古里古怪,那么它怎样让观者去进行品评和识读?这种风气从根本意义上违背了中和的审美原则,不讲究传统价值与精神境界,扰乱人们正确看待书法艺术的视线,麻痹了书法艺术的神经,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从事书法学习、研究创作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握住中和这一标准,认真地研习古代书家留下来的经典之作,从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改善和学习,这样才能渐入书法艺术学习的殿堂。对于学习书法的正宗观,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说:“会古通今,不激不厉,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矣奇解――此谓大成已集,妙入时中,继往开来,永垂模轨:一之正宗也。”由此可见中和之美对于学习书法的重大意义。
然而我们辩证地思考项穆所言中和,并不像许多人所理解的不偏不倚、调和折中,进而变成了保守落后和不思进取的代名词,被许多人所误解,认为其抹杀了书法艺术的个性,束缚了书法家的创新精神。实际上,在《书法雅言》中,项穆强调了“权变”与“时中”,认为处理书法中的各类问题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中”,并在具体情况下提出相应的具体原则。如古今、形质、品格、资学、规矩、正奇、老少、取舍等,这些不同的范围内都必须具有灵活多变的原则,这就是“权”。“权之谓者,称物平施,即中和也。”项穆中和观念里的时中精神既强调“中”因“时”而变,又强调因“时”而“中”。“中”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与多变性,体现出书法中存在的复杂性、运动性,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从书法美学的角度看,项穆主张的中和之美,并不是将书法诸多因素或对立的方面做无原则的折中调和,而是具有辩证因素的矛盾观。项穆在《书法雅言・古今》中说道:“不学古法者,无稽之徒也;专泥上古者,岂从周之士哉……宣圣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孙过庭云: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审斯二语,与世推移,规矩从心,中和为的。”由此可见,他主张书法艺术顺势而发展的过程中要继承传统,绝不能因古而失今,或因今而失古,这种积极的辩证思想贯穿于项穆书法思想始终。
中国书法受汉字笔画、结构的约束,并借助毛笔和宣纸来抒发书法家情感,传达艺术美的信息。线条形态变化万千,笔法丰富多样,书法家的书写节奏、艺术情感也都随时变化,但就书写线条的整体质量与整幅书作的韵律而言,又必须是无所不及、无所不戾、和谐统一的。这是评价一幅书法作品成败与否的基本出发点。孙过庭有言曰:“至若数画并布……合情调于纸上。”
中庸之道及中和之美是我国传统文化和思维的基本特点,被视为传统道德与艺术追求的法则与最高境界。纵览中国古代书法史,中和之美的审美思想一直贯穿其中,从有记载的商代殷墟甲骨文一直发展到各体皆备、书体演变已臻成熟的汉代,再从魏晋南北朝的书法一直发展到碑学复兴的清代,我们都能体察到中和之美的审美原则于书法艺术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审美个性,还从另一方面显现出中国书法作为东方艺术门类之中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艺术所绽放出的熠熠光辉。
[注释]
①黄:《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②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书法艺术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书法艺术;书法美学;境界;坐忘;艺术学;审美特征
中图分类号:J292.1文献标识码:A
正如数学是最纯粹的科学一样,书法也可以说是中国美术中最纯粹的艺术。书法不是通过“写实”或“写意”的“造型”来表达书家的情绪和感知,靠“字”的“间架结构”、轻重缓疾、抑扬顿挫的笔法,呈现出构图上的变化,让鉴赏者体察其中的“气韵”所在,从而引发精神上的感触。在书家、鉴赏者的创作、鉴赏过程中,自始自终都没有任何一种如“形”――自然形――的约束。在书家,那是在运笔之中,把自己的精神意念借助笔触、笔势化解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鉴赏者则是从这些“有意味的形式”中重新发现自我精神意念的空间,因而能够从平时俗务围裹着的意识世界中解脱出来。当俗务重负下的意识不再成为精神负担,精神就在新的空间中任意驰骋,绝无旁倚,而达到身心愉悦的艺术境界。
但是,这种对“有意味的形式”的感知,却是因人而异,毫无雷同的:书家的感触不等于就是鉴赏者的感悟;不同鉴赏者之间的感悟更是千差万别。尽管如此,他们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一流的书家和一流的鉴赏者面对书法艺术,其精神状态都是一样的处于“忘”的境地。
一、“忘”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至高境界
“忘”,本是中国先秦哲学的一个概念。有“物我两忘”之说。《老子•十三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有身”就是“有‘我’。”就是“吾”不能“忘我”的意思。人有“自我”的意识观念,就有“私欲”;有“私欲”就会妨害“公德”。所以先秦诸子不赞成人的“自我”意识太浓太多,否则就会天下不安宁。后来的佛学讲“心无所住”,“心”是“我心”。“无所住”就是“不著相”。此“相”含虚妄之“相”,也含“实相”之“相”。在这一派佛学说,“实相”也“无相”。既如此,“我心”也无“著相”,彻底否认了“相”的存在,“我”、“我身”、“我心”当然统统无相可见,无迹可求了:这是又一境界的“忘”(当然,在某些流派的佛教者看来,此非“忘”,乃是本无一物,固无所谓“忘”。此牵涉到“空”义理解,本文不予置评。)。
如果说老子的语言过于简约,佛学言辞趋于深奥;那么,简明生动的叙述就是庄子的“坐忘”之论了。
《庄子•大宗师中》杜撰孔子和学生颜回的对话,提出“坐忘”概念如下:
颜回曰:“回益矣。”
件尼曰:“何谓也?”
曰:“回忘礼乐矣。”
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
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
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
曰:“回坐忘矣。”
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
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这段话的前提是庄子提出的“真人”概念,“真人”是“其心忘”的,是“天与人不相胜”的,是与“自然”一体的。颜回为达到这个要求,在精神上做到了二个层面的提升。第一个层面是“忘仁义”。但在儒家立场,“坐忘”也有“同于大通”之外的意义。
众所周知,“仁”是孔子儒家学说的核心,“仁者爱人”,他的理想社会是按血统为纽带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社会。大宗子是共主,各成员按照宗法秩序安分守已的生活。在这个范围内,只要子民无非分言行,大宗子都会对子民充满恰如其份的“仁爱之心”,宗法社会无疑是其乐融融,上下和谐。颜回要做官而“忘仁义”,是因为“仁义”仍是执政者有“心”为之的东西,如果一直心中保存一个行“仁义”的“心”,那就是说他和“仁义”还有距离,还是一个脱离“仁义”的人。“忘”了这个有“心”为之的东西,是表明自己已经和“仁义”融为一体,不分彼此,没有了有“心”的距离。颜回自诩已“忘仁义”,却仍不得孔子(其实是庄子)首肯。于是有了第二个层面的提升,即从个人内在的修养扩展到宗法社会的制度层面。用颜回话说是:“忘礼乐。”
“礼乐”是宗法社会制度、规章,所谓“礼乐之制”。“克已复礼”是孔子一生的追求,是孔子心中当时第一等大事。颜回心中自然很明白。他回答说“忘礼乐”,和“忘仁义”同义,都是表白自已与“礼乐”的相融相渗,并不是靠“背诵”、“记录”礼乐规章制度的人。换言之,颜回强调自己具备“礼乐”素质,毋须去死记硬背那些条文。
精神素质达到这个层面,应该说已大大超越了宗法社会组织一般贵族官员,可是孔子(庄子)不认可,孔子说过,“先进于礼乐者,野人也;后进于礼乐者,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从先进”,就是从“野人”。“野人”相对于“君子”,“野人”非有世袭特权的“君子”,故先习礼乐,培养礼乐素质。君子世袭爵位,先有爵位,后习礼乐。所以孔子重视先具礼乐素质教育的人选。但这仍然不符要求,最终是颜回达到“坐忘”的程度,孔子才以为合格。如颜回说的“坐忘”,是“忘”了自身的存在。原来先前“忘礼义”也好,“忘礼乐”也罢,都还是有“自己”、“我”的存在。“坐忘”是“我”已不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唯有“无我”的状态,才免除老子“为吾有身”的感慨,才彻底与“仁义”同体,与“礼乐”相融。至此孔子才赞许“果其贤乎!”。
孔子的赞许,其实是庄子的意见。“仁义”、“礼乐”这些儒家宗法伦理道德观念,在庄子看来,都是“人为”的产物。模范的遵守这些“人为”的规定的宗法社会成员,庄子一概名之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如果有人不是按照这些“人为”的条条框框生活,而是顺应自己的自然需求生活,庄子称之为“人之小人”,却是“天之君子”,就是“真人”的状态――“真人”,真正的“人”。不论孔、老、庄的议论的归结有些如何不同,出发点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纷乱现象。都是认为人的“自我”概念存在,必有种种利益私心,在私心杂念下的人即使明白“仁义”之道,即使掌握“礼乐之制”,也会使“仁义”成为幌子,“礼乐”成为遮羞布。如此,非但不成其为真正的“人”,而且又成为“卑鄙”、“虚伪”的活体了。所以,他们要求“绝圣去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又要求“坐忘”,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筑一道堤坝。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形骸都不知所在了,也就是“吾身”概念消失,由之引起的种种私欲当然也不复存在,这就能达到庄子追求的“不以外物物于物”的“逍遥”境地。事实上在欲望横流的社会现实中,能做到“坐忘”、“逍遥”心境的人是极其有限的。先秦诸子“政治正确”的理念宣导虽然在历史上没有多少呼应,但“歪打正着”的在艺术领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坐忘”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艺术精神的境界。
二、书法善乎“忘”
书法艺术的大发展是在两汉至南北朝,其标志是解散篆体,出现的隶法、楷法。在这个过程中的大量书者是政府的吏员,繁忙的公文誊写,促使笔法向简约的方向推进。于是乎隶法夹带着篆法的各种书写风格,出现在大量竹木简帛书中。从出土的竹木简书看,竹木简的宽度有限,每根竹木简的直行字数相对固定,每根简片上部分的文字书写大都笔法严正,而下部分文字则趋轻松。特例是最后一根简片的末尾几个单字,笔法运用有放松夸张的特色。显然书者在单调乏味的公文写过程中,特别是在每枚简片起首行书写时都不得不整饬精神,敛神屏气。及至到每行末字,“精、气、神”才可以稍加舒缓。到了公文结尾的最后一二个字,“精、气、神”获得最后解脱,那一笔挥洒,仿佛能听到他的一声长吁。也就是这一声长吁,“精、气、神”大自由,随之而来的则是那更加解散的笔法和韵味独具的单字间架。可以推想,在当时这种解散笔法给书者带来可以自由发挥的精神空间一定是让人欣喜不已的,新的笔法、新的单字结构、新的整篇抑扬顿挫的节奏,都引导书者对这个纯艺术的境界感悟有更深入、更本质的探究。
这种探究很自然的沿袭着先秦诸子已经辨明的“精诚”历史概念而来。
拿前述庄子推重的“真人”来说,“人”有“真”、“假”之别,是因为“真”的人有“精诚”之质;“假”的人则非是,“假人”无“精诚”之质,故无论其外表如何“正经”,但均属“伪君子”之流,“伪君子”即非“真人”。在庄子看来,“真”有可检测的表征;在我们看来,这个表征就是“艺术”范畴。如《庄子•渔父》中说: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庄子提出的问题转化到书法艺术上,就是书家如果不以“精诚”之心对待艺术,其书法作品“不能动人”。鉴赏者如果无“精诚”之心面对作品,其欣赏、评论皆为“强哭者”、“强怒者”、“强亲者”流。“精”可通“神”,“诚”可达“意”。无“精诚”,书家所作就是徒有其势而无其神、意;无神意即无韵可求,未可以艺术言之。鉴赏者无“精诚”,所见所言必落入空泛套语,虚饰夸张而已,亦未可以艺术评鉴目之。
庄子强调“真人”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因了种种“人为”的“宗法伦理”观念的约束和“宗法社会”权欲、利欲的诱惑,能保持“人”的真性情不容易,“真人”日少,“假人”日多。这种违背“自然”的现象,当然是庄子最厌恶的事,所以他要张扬“真人”的“精诚”。有“精诚”,就有出于自然的“情”,“情”是外感于物的反应,是“真人”“精诚”的流露。汉代刘向撰《淮南子•齐俗训》说:
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
又说:
且人之情,耳目应感动,心志知忧乐。
这种耳目感官的“感动”,不说是艺术大师,还是职业艺术工作者,都内启心灵的感悟,使之上动天地,下泣鬼神。同书《览冥训》说:
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夫瞽师庶女,位贱尚,权轻飞羽,然而专精厉意,委务积神,上通九天,激厉至精。
特别要注意的是文中提出“专精厉意,委务积神”:这是艺术家创作时的“精气神”状态,“白雪之音”,无状可拟,无形可写。正如书法,无形可求,无色可侔。这种纯粹的艺术感悟,非“专精厉意”,非“委务积神”,不能在虚空中达到挥洒自由境地。
要达此境地,汉末蔡邕已认识到先要摒弃胸中一切桎梏,他说: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
如何“先散怀抱,任情恣性”呢?他说:
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
“如对至尊”,是“宗法伦理”的要求,外观上那是一种必恭必敬,不苟言笑,神情肃穆的状态。内在的精神意识却是“沉密神采”、“静思”、“随意所适”,这是艺术的要求。“静思”而“随意所适”,已经含有远离“理性”,释放潜意识的意味。因为“潜意识”,才能“随意所适”,信马由缰,独往独来,无所羁绊;才是独立特行,才能自由。这种精神状态,《淮南子》有更精采的妙喻:
夫工匠之为连运开,阴闭眩错,入于冥冥之眇,神调之极,游乎心手众虚之间,而莫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师之放意相物,写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
“阴闭眩错,入于冥冥之眇,神调之极,游乎心手众虚之间”。原来任一“手艺”之极致,皆须“放意相物,写神愈舞。”皆有此“艺术”境界:这就是“艺术”的共通之性。
达此共通之性,自然进入艺术的空间。这又是一流书家的必由之径,所以晋代王教导侄子王羲之说:
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
在达到“书乃吾自书”的认知程度后,对书法创作过程中的点划转折,也就另一番妙悟。王羲之的体会是“须得书意”:
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
到这一步,书法的艺术呈现完全在“转深点画”的“形式”之间展开,“形式”即如蔡邕《笔论》中的“须入其形”:
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这里说明“纵横有可象者”,就是“若虫食木叶”等等。“虫食木叶”,是自然成文的,所以,强调的还是书法创作中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就是上述“事事皆然”的“然”。显然,“自然”,就不能拘束,也就“自由”、“逍遥”。致此状态,书法艺术的“纯粹”性也展露无遗。
由是言之,书法艺术在书家,在鉴赏者皆以“精气神”相通融,“精气神”是可以游离于人自身之外的。书家、鉴赏者面对书法作品,须“忘”自身一切:从名利到种种概念的选择,直以“精气神”的感受为唯一性,方可有直入如来境地的机缘。南齐王僧虔《笔意赞》说:
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笔两忘,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这里说的“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笔两忘”,当然要求书者的静思默然须达到相当于“心斋”境地,“心斋”是“虚壹而静”的结果,并不能一蹴而就,有一个日积月累的渐悟过程。但从艺术境界说,“心斋”、“忘”的状态表征在不受理性意识控制,如上述是书者本身固有的潜意识的展露,由是发挥出艺术的“潜能”。在艺术家中,追求自我,应该是追求自我“潜意识”的充分展现,“潜能”的创造力,于是有“醉里挑灯”、“往往醉后”的艺术佳作问世。
可以说,到南北朝,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已经为书家道出,书法的艺术纯粹性也得到证明。
书法的纯粹性依靠笔法展现,所以也有“技巧”问题。这一点在汉代也有清楚的认识。《淮南子•修务训》说:
今夫盲者目不能别昼夜,分向黑,然而博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拂,乎若蔑蒙,不失一弦。使未尝鼓瑟者,虽有离朱之明,攫掇之捷,犹不能屈伸其指。何则?服习积贯之所致。
“服习积贯”,是艺术技巧训练的共通要求,书法不例外,在这方面,“术业有专攻”,就有精、疏区分。《淮南子》还指出: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修,贤者之所不足,不若众人之有余。何以知其然?夫宋画吴冶,刻刑镂法,乱修曲出,其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蔡之,卫之稚质,捆纂组,杂奇彩,抑墨质,扬赤文,禹汤之智不能逮。
这也是唐人所谓“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意思。所不同的是,这里说的“知(智)者”、“愚者”之论不可取而已。但就艺术技巧因人而异的情况说,仍然符合书法艺术的事实。(责任编辑:楚小庆)
On the "Forgetting" in Calligraphic Art
LIU Dao-guang
(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8)
书法艺术范文第4篇
一、书法艺术中优美的线条
1、矛盾的立体感用立体感来形容书法艺术,本身就是比较矛盾的。因为书法艺术属于是一种平面艺术,本身没有立体感。但是拥有优美线条的书法作品,却给人以形象的立体感。通过这种形象感,让人感受到了优美线条中的丰富内涵。对于书法艺术来说,需要很强的中锋技巧侧锋则需要与之相互替补。书法的立体感不是简单通过改变笔法就能达到的,因为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关于美的问题。
2、节奏感在书法的形式中,我们不难发现其节奏。因为在书法的家走中,又有一种生命的活力的感觉。通过墨迹在白纸上的行云流水,使得这两种鲜明的对比组成了一种节奏。通过笔的一松一紧、一轻一重、一快一慢造就了线条节奏的不同。正是有了不同之处的对比,才有了不同性质的节奏。
二、书法艺术的结构美
1、平正美书法美的基本要素就是平正,只有让人感觉到稳定和舒适,才能够让人感受到书法的平正美。由于书法出自人的手,所以书法的审美心理与人也是一样的,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审美观念。整齐有序的才是美。所以从古至今的书法家在作品中都比较注重平正美。《四体书势》中对于隶书就有这样的说法:“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正是说出了书法对于结构中平正美的要求。
2、匀称美书法要匀称在结构中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字的笔画之间要匀称适中,形成各个部分之间基本的整齐感。也就是说在书法的时候,应该注重实线的枢密程度,从而更好地保证匀称。有的时候,书法家比较重视没有实线的空白处来着手,形成具有美感的黑白匀称。尤其是在篆书中,特别注重书法的匀称和黑白适中。
3、参差美参差不齐之中方显事物之美。山峰之所以美,正是因为峰顶的参差不齐;海浪之美,正是由于浪花的参差所带来的美感;而云彩的秀丽之美,也是因为参差所带来的美感。所以在书法方面,有了结构上的参差,就出现了错落的美感。无论是在楷书还是隶书中,在构字和布局上都比较注重参差错落,这样也正是为了能够形成这种独特的美感。
三、书法艺术中优美的章法
1、贯通和承接谈到书法的章法美,首先应该涉及到其贯通和承接。因为只有书法的字句行篇中有秩序的贯通和承接,才会出现体势的美。正是在贯通处和承接处,我们才看到了书法的章法美。例如在《临池管见》中就说过“古人作书,于联络处见章法,于洒落处见意境”。说的正是章法美在联络处的最好体现。
2、虚实相成在书法中,虚实相成体现的比较明显。首先,有线条和字的地方就是书法中的实;字间或者其他空白处就是虚。通过这种虚实相成的章法,来更好地体现出书法的虚实相成美。作者通过手眼结合来确定黑与白的平衡布局,中间也体现出了作者书法艺术的高超。题识作为书法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正文的补充和发展,同时也起到了衬托虚实相成章法美的重要作用。虚实相成有的时候也会体现在题款上字体的不断变化,使书法的章法美好假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3、错落有致错落有致属于一种比较奇特的美。首先,在字之间产生一定程度的错位,可以是中轴线和中线重合,也可以存在一定的角度。通过这样错位的方式,能够体现出字李行间的不争气和不平衡。有的时候还会有作者刻意地进行一些修缮。这样就会使书法中的错落有致的美感更加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把错落有致章法运用的炉火纯青的人物当属唐代怀素,在其代表作《自叙贴》就有错落有致的变化美。
四、结语
书法艺术范文第5篇
1.用笔。
“用笔”,也称作“笔法”或“点画用笔”,是指运用毛笔的方法与技巧以及所写出来的点画形态及其效果。它是构成书法审美情趣、表现书法家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用笔方法,有起笔、行笔、收笔、提笔、按笔、转笔、折笔。用笔的不同,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从用笔方法上说,有快、慢、轻、重、藏锋、露锋、中锋、侧锋;从点画效果上说,有长、短、肥、瘦、曲、直、方、圆、俯、仰。要将不同的用笔方式在一幅作品中运用协调,变化有致,才会使通篇像一曲音乐一样婉转美妙。
2.结体。
“结体”,也称“结字”、“字法”、“结构”或“间架结构”,是将点画按照一定的法则组合成字。要成就一个字的美观,除了写好每个点画,还要注意点画之间搭配的稳妥,互相照应,要讲究比例协调,重心平稳,疏密均衡,向背分明,揖让得当,开合有致。可以说,结构是决定一个字好坏成败的关键。点画用笔好比是肌肤血肉,结构好比是人的筋骨。筋骨不立其形,则肌肤血肉难成其美。
3.章法。
“章法”,也叫“布局”或“布白”,就是将一系列文字组成一幅完整作品所进行的通篇安排。章法的具体方面包括字的大小、斜正、疏密等的变化与协调,也包括落款与印章的安排。书法艺术要求通篇的每行、每字以及一个字的各个点画之间都要搭配均衡,协调一致,同时还要体现变化莫测的神妙趣味。
4.用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