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家庭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张之洞家庭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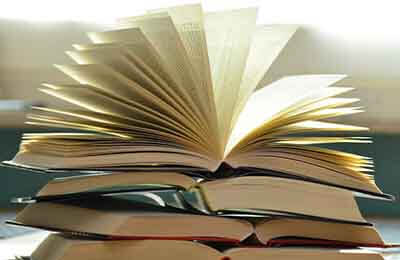
中国之弊就在于抱残守缺,囿于成法,不思进取,“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蔽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绌矣”[1](P9734-9735)。洞悉如此,张之洞试图采西法之精进,复中国旧学之精意,通过中西比较、新旧相参,“可引为外惧,籍以儆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1](P9735)。果真如此,中国摆脱西方的奴役而走向独立富强不是不可能的。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大厦将倾,张之洞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沉沦于社会的逆境之中,而是不断以此为激励自己进取奋斗的动力,“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2]。他勇于在末世之下承担起“持危扶颠”的责任,积极实施自己惊世骇俗、力挽狂澜的抱负。在近代中国社会巨变的大舞台上,实现其教育兴国、兴教图存的梦想,并以此教育后代子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是张之洞家庭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大背景。
张之洞的经历、学历和履历的作用和影响
张之洞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还与他的成长经历、学习过程和职业生涯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经历也促成了他教育思想的完善和成熟。
(一)张之洞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与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道光十七年(1837年),张之洞出生于其父任职的贵州官舍内,父张瑛,原籍直隶南皮,时任贵州兴义知府。张氏家族自明代迁至山西洪洞,至张瑛累世为官,祖上为官勤勉清廉,对幼小的张之洞有很大影响。其祖张淮,曾官至明朝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义有声于时”[3](P1)。高祖乃曾,清时为山西孝义知县,其子怡熊,官浙江山阴知县,“两世为县令,皆以廉惠闻”[3](P1)。祖父廷琛,题补古田知县,时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闽浙总督乌拉那贪污、纵盗窝案发,廷琛不仅洁身免祸,还多方“调护拯救”[3](P1),甚获时誉。家风的熏陶,使张之洞渐渐养成洁身清廉的习惯。这种良好的习惯也慢慢渗透到了他后来的为官和家庭教育中。张之洞的父亲张瑛,早年丧父,家境窘迫,但“食贫力学,艰苦卓绝”[3](P1),为官尽职尽责,呕心沥血。父亲树立的榜样对张之洞的成长起着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也影响到了张之洞对子女的教育。道光二十年(1840年)张之洞生母朱夫人病逝,年仅三岁的之洞由父亲的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无子,待之洞如己出。但张之洞幼小的心灵毕竟经历了幼年丧母的痛苦,后来以诗抒怀:“梦断怀木卷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儿嬉仿佛前生事,那忆抛廉理柱声。”[1](P10472)手扶生母留下的双琴,在母亲怀里的嬉戏欢闹仿佛离自己非常遥远,孤寂和无助时刻缠绕着他。这种经历更激起了张之洞对家庭天伦之乐的渴望,进而转化为对子女疼爱有加和无微不至的教育情怀。
(二)求学的历程与张之洞家庭教育思想的深化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张之洞从父亲张瑛那里得到做事、为人、处世的最早的启蒙。张瑛对子侄管教甚严,他礼聘远近名儒为子侄传授学业,又购书数十橱,“令于日课外,听以已意观之”[3](P2)。张之洞在严父的管教下,自小就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且终生受益。张之洞四岁发蒙,师从当地名儒研习“乾嘉老辈诸言”。做过张之洞业师的先后有十数人之多,“其中胡林翼、韩超十分器重少年之洞的才气,而之洞一生奉行经世实学,亦受胡、韩二人影响为最”[4](P22)。韩超“性刚直,有胆略”[5],时誉“血性奇男子”[3](P3)。胡林翼“于书无所不读,然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厄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6]。而其“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经济、军事,固无所不学,无所不至其用也”[7]。在鸿儒名师的教导下,张之洞不但扎实掌握了儒家经典,而且广泛涉猎名家所长,为日后的家庭教育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三)入仕为官的职业生涯与张之洞家庭教育思想的完善同治六年(1867年),张之洞任浙江乡试副考官,这是张之洞入仕以来第一个实差,也是他十年学官生涯的开始。之后张之洞历任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学官经历使张之洞认识到:“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字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1](P1833)其教育思想由表面的读书识字,上升到加强人生修养、“砥砺名节”的高度,把教育与个人前途、国家民族的兴废存亡结合在一起。“之洞为官一生,惜才、‘得人’是其始终不渝的风格,显然与他的十年学官经历密切相依,同时学官生涯也使他对于科场积弊之重,改革教育之切,有了较深刻的认识。”[4](P31)这种经历使张之洞重视教育,更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光绪三年(1877年)到光绪七年(1881年),张之洞多充在京闲职,也就是在此时,他入党清流。“虎豹当关卧,不能竭我言”[1](P10454)是这时的写照。指点流弊,愤世嫉俗,虽然物质境遇窘迫,但激励张之洞高远的抱负和耿直的性情。他屡屡以诗言志:“当代功名同气盛,蹉跎莫待鬓如丝。”[1](P10455)这段经历对日后张之洞品格和情操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光绪七年(1881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封疆大吏的生涯。他先后总督两广、湖广,两度暂署两江,虽位高权倾,但在清政府江河日下,列强步步紧逼,内忧外患相交而至之下,张之洞不屑与清末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文恬武嬉、尸位素餐者为伍,弃清流转而事洋务,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公忠体国,廉正无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而在实践中更注重实学、实干型人才的培养,张之洞的家庭教育思想日臻完善。
张之洞性格因素和学识素养的促成作用
与那些顽固守旧者和一味趋新者相比,张之洞的家庭教育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然不能说是最早,但确实起到了引领时代的作用。这种先进思想的形成除了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外,还与他的性格特点和学识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两种因素在其对西学的态度上表现的最为明显。清末,张之洞以“儒臣”著称,但他决非迂儒,其为官之道,颇精于谋略。究其根源,张之洞“性善变”的性格因素是原因之一。“性善变”,可以理解为见风使舵,也可以理解为善于审时度势,善于接受新事物,“之洞不愧一代能臣,工于心计,精于权变,善于转圜”[4](P254)。另外,张之洞“中庸”的人生哲学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曾言“废德为进退,相时为行藏”,“不痴不聋不能为公”,“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1](P10311)。静观其变,顺其自然,这种人生态度,利于顺应时代潮流地去接受新生事物,同时对于已经失去活力的旧东西,也会自然地去淘汰。张之洞的这种性格能够使他在学术上兼采汉宋,在实践中中西兼学。张之洞也力图使子弟认识到:“精于审时度势,以为进退之据;因时、因地制宜,以为行事之规;灵活变通,立于不败”[4](P256),“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1](P1001)。“张之洞的学风,亦大受时代熏染,以经世、务实为其特点。”[4](P286)正是这种“经世致用’的学识素养,使张之洞能够清醒地辨识传统的中学,同时又能客观地看待渐入的西学,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其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认为“术听人择,何为必通经乎?曰:有本,学人因谓之根底,凡学工根底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底在通经,读史之根底亦在通经。归其终也,在于有用”[1](P10075)。汉学和宋学都出自儒家之门,“不必强立门户,相互訾敖言”[1](P9794),“好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1](P9795)。汉学也好,宋学也罢,其存在和学研的价值都在于对社会的“经世致用”,西学对中国社会来讲当然也是这个道理。张之洞意识到传统经世之学不足以满足国富民强的目标时,便将眼光转向更为实用的西学,即“中学为治之具,西法为富强之谋”[1](P1412)。所以张之洞一生笃信的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不以中学排斥西学,“并最终为其大力倡导的‘西学为用’学说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8],成为其采西学的思想根源和内在动力。教育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发展决定了教育的内容及形式,张之洞的家庭教育思想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努力培养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但是社会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顺势的也有逆势的,张之洞极力克服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对子女进行有效教育。他力图保持合乎社会规范的成分,积极吸收、创新教育的内容,从而使自己的教育思想更趋完美。张之洞善于趋变,敢于创新,脚踏实地,使施教者的理念、行动尽量赶上时代的步伐,而且极力协调新与旧、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虽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也体现了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特点。
作者:杨庆博单位:沧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