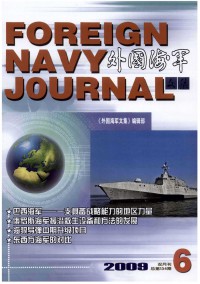外国犯罪体系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外国犯罪体系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对于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学界存在着主张维持现状的“维持论”、主张修修补补的“改良论”和主张推倒重来的“重构论”。目前,维持论日益式微、重构论逐渐有力而改良论可谓似是而非。与从正面论证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较之我国平面的体系所具有的优越性同样重要,就改良论者所提出的一些论断予以反驳,也是我们在正面主张重构犯罪构成理论时所面临的一个必需的理论课题。
关键词:违法有责类型实质的犯罪论刑法学说问题的思考体系的思考
Abstract
Astocurrenttheoryofcrimeconstitute,therearedifferentclaimswhichcancomeunderthreetypes:maintainingthecurrentcondition,ormakingsomeimprovement,orreconstructingcompletely.Nowadays,theclaimsofmaintainingiswastingwhiletheclaimsofreconstructingprospering,andtheclaimofreformationissoobscure.Asimportantasdemonstratingthesuperiorityofthethree-layeredtheoryofcrimeconstituteownscomparedwithourleveledtheoryfrontally,itisalsoanecessarytheorysubjectwhenwefrontallyclaimtoreconstructourtheoryofcrimeconstitute,namely,torefutingsomeargumentsexpoundedbyreformers.
Keywords
thetypeofillegalityandliability,materialtheoryofcrime,theoryofcriminallaw,considerationsonquestions,systematicconsideration
在对于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的研讨过程之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犯罪构成理论尽管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实质性、根本性的,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调整来加以改进,从而“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不必重构”。这样的主张,就对于现有犯罪构成理论所采取的态度来看,既不同于主张维持现有理论现状而无需做出改变的“维持说”,也不同于主张对于现有理论推倒重来、用另外的犯罪成立理论取而代之(典型的备选答案是德日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之三阶层体系)的“重构论”,表面上看来,既不保守也不激进,姑且将其称之为“改良论”。这种表现温和的所谓改良论,简单说来也就是对于现在的犯罪成立理论进行修修补补。而就改良(修补)的具体方案来说,又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区别。主张改良说的论者大有人在,而清华大学黎宏教授新近的论文[1]则可以说是改良说的最新代表。
笔者在几年前与梁根林教授合作的论文中,从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检讨和反思切入,已经初步表达了重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立场。[2]时至今日,笔者的立场更加明确,那就是,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应当重构。自然,系统的主张重构论既需要从正面具体论证作为重构之目标选择的三阶层体系所赖以依存的基本原理、重构犯罪构成理论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3],也需要从反面在对于现有的各种基本立场进行描述的基础上解构重构论与维持论特别是与改良论之间的主要区别[4],还需要在论证了阶层式体系较之平面式体系所具有的优越性的前提下,从侧面具体论证为什么我们应该选择的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体系而不是不法-责任的二阶层体系或者行为-不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或者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四阶层体系等[5]。在此同时,就重构论者的论争对象来说,应该承认改良论的主张较之维持论更为有力也更具迷惑性,因此,就改良论者所提出的一些论断予以反驳,也是我们在正面主张重构犯罪构成理论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
一、改良论者认为,德日犯罪体系论“体系上前后冲突”,“在有关违法性、有责性判断上,有先入为主的倾向。”[6]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论者得出上述的结论的论据,是认为“按照现在德日所流行的犯罪判断过程三阶段论,构成要件该当性是认定违法性和有责性的事实依据,行为只要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可以积极地推定其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而在违法性和有责性的阶段上,只要消极地探讨什么样的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和有责行为就够了。”因此,“由于构成要件是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类型,换言之,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可以说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在尚未说明什么是违法和有责之前,就说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是违法、有责行为,这样,在违法和有责这种本属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岂不是也存在先入为主的嫌疑吗?”[7]
在日本,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的观点大概是源自小野清一郎博士所提倡的构成要件论,而采纳这样的违法有责类型说的则有团藤重光、大塚仁、庄子邦雄、藤木英雄、吉川经夫、香川达夫、板仓宏、大谷实、西田典之、前田雅英、佐伯仁志等。[8]但是,日本刑法学者从来没有断绝过对于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类型说的批评。比如,将构成要件理解为违法·有责类型的话,将故意·过失作为责任要素纳入到构成要件之中就有疑问的。平野龙一博士对此批评道,“这样的‘构成要件’,已经失去了作为犯罪成立的‘一要素’的意味”,“可以说是构成要件的理论的崩坏。不仅如此,采纳这样的构成要件论的话,因为故意·过失这样的主观的要素从一开始就被纳入考虑范围,就会陷入‘全体的考察’,罪刑法定主义的机能就变得最小。而且要是故意本身属于构成要件的话,构成要件就不能成为故意的认识的‘对象’,由此构成要件也就失去了故意的规制机能。”平野的弟子、东京大学山口厚教授也指出,将构成要件理解为违法·有责行为类型的话,“这里,构成要件就成了犯罪本身,也就是犯罪的积极的成立要件的总体(犯罪的成立要件总体之中除去阻却其成立的事由),构成要件失去了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的意味。而且,这里违法要素与责任要素的区别变得非常暧昧,具有了将两者混淆而进行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的危险。这里,将犯罪的实质的成立条件分为违法性与责任,其各自的背后具有不同的原理,是一种分析的考虑,而将构成要件理解为违法·有责类型的话,则妨碍了这种初衷,会导致倒霉的‘全体的考察’,是不妥当的。”[9]同样持结果无价值立场的内藤谦教授也认为,将构成要件作为违法·有责行为类型的时候,作为有责行为类型,即便是故意·过失被包含于其中,责任能力、违法性的意识这样的责任要素也没有类型化到构成要件之中。从而,与违法要素被全面的类型化的违法行为类型同样的意义上,能否说与此对等的所谓的有责行为类型,是有疑问的。这样,大概也就不能说是构成要件像具有违法推定(推测)机能一样的意义上,也具有责任推定机能了。[10]针对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同样主张结果无价值的大阪市立大学教授浅田和茂提出了如下的批评。他指出,确实,“犯罪类型”虽然属于将违法·有责的行为予以类型化的存在,但是在作为刑法评价的第一阶段的“构成要件”来说,犯罪体系方面的从形式到实质、从客观到主观这一顺序是必须予以维持的。而且,在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的基础上,理论地说来,就变成了不仅肯定构成要件的违法推定机能、而且也应该肯定其责任推定机能,但是,连构成要件的责任推定机能也承认却是做得过头了(至少责任能力的推定是无法发挥作用的)。而且,在这一立场这里,由于将违法与责任同列予以触及,就使得责任的判断仅加诸于该当构成要件且违法的行为这一点,变得不鲜明了。[11]
事实上,对于此等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类型说的批判,不仅存在于结果无价值论者(如前引平野、内藤、山口、浅田诸教授的批评)之中,也存在于行为无价值论者之中。如有批评认为,将构成要件作为责任的类型几乎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与就违法性来说对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存否进行消极的判断同样,就责任来说,并不意味着责任只根据责任阻却事由的存否的判断来确定,构成要件该当性应该被视为不推定责任(福田平教授的看法);也有批评认为,构成要件,不具有与违法类型对等的意义上的责任类型的意义(西原春夫教授的看法)。[12]日本当代行为无价值二元论的代表学者井田良教授认为,确实,主张违法有责类型说,在构成要件之中,考虑责任非难的可能性以限定构成要件的范围是有理由的,但是,“第一,像责任能力这样的重要的责任要素,将之作为构成要件要素来考虑是不可能的,而且认定了构成要件该当性即可赋予责任以基础,这样的论理的推定关系也不存在。第二,要是也认可了构成要件和责任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犯罪的成否恐怕就存在接近于一揽子判断的危险,将犯罪要件予以三分的意味将大打折扣。第三,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阶段即不仅考虑违法要素亦考虑责任要素,就混同了违法性与有责性,在体系上,与责任的存否相独立的违法性之有无的确定(客观的违法性论)将变得不可能。这样看来,将构成要件理解为违法类型而不同时理解为责任类型的见解是妥当的。”[13]上述井田教授对违法有责类型说的批判与平野、山口教授等的批判理由大致类似,这形象而又论理地说明,无论是坚持结果无价值还是坚持行为无价值(二元论),将构成要件理解为违法有责类型的观点,都是有问题的。
回过头来再看我国学者(改良论者)对于德日犯罪论体系“前后冲突”、“先入为主”等的批评。无疑,这样的批评是建立在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类型说的基础上的。但是,第一,就对构成要件理解的学说史而言,是先有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说(贝林),后有违法类型说(麦兹格),最后才有违法有责类型说(小野清一郎)。违法有责类型说尽管在日本至今仍然十分有力,却并非学说中的唯一,甚至也未必能够称得上是通说。就是说,就日本来说,主张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类型说只是日本刑法学中的一部分学说(尽管有力)而非全部,以此一部分学说来论证阶层式体系“前后冲突”、“先入为主”,未免以偏概全。第二,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类型说已经受到了日本的不同时代(平野、内藤、福田、西原等为一代,山口、浅田、井田等为一代)、不同立场(平野、内藤、山口、浅田持结果无价值立场,福田、西原、井田持行为无价值立场)的多位著名学者的批驳。这些有识之士的以上对于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类型说的批评,足以引导我们走向对于德日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全面认识。第三,就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类型说与犯罪论体系的建构来说,即便这里改良论者的诘难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其诘难实际上与前述日本学者对于违法有责行为类型说的批评在路径上是一致的),这也只能引导我们放弃构成要件的违法有责类型说而转而选择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说(主张者如内田文昭教授、曾根威彦教授等)或者违法类型说(主张者如平野、山口等相当部分学者),而不能因噎废食地就此否定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本身。
二、改良论者认为,“可以说,国内一些学者所推崇备至的通过层层进逼的方式,缩小犯罪包围圈的理想,在德日国家,已经是昨日黄花,不复存在了。”[14]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笔者完全不懂德语,对于这样的“通过层层进逼的方式缩小犯罪包围圈”的犯罪论体系在德国的现状如何无从也不想借助翻译的资料作更多的评价,但是至少在日本来说,改良论者的上述“昨日黄花,不复存在”的论断恐怕是难以成立的。退一步说,即便是论者所举的前田雅英教授的“构成要件,从违法性的角度来看,必须是客观上伴有值得刑罚处罚的害恶的行为类型;从主观角度来看,必须是现在的日本国民认为可以谴责的主观事实,如故意过失或者特定目的等”这样的所谓的“充斥价值判断的论述”能够说明在他的教科书中“只是保留了一个当初的三阶段的大体框架,但是在内容上却完全偏离了当初的设想”,这也不过是前田教授等个别学者的论断,恐怕不能代表日本刑法学相应问题的全貌。实际上,前田教授所主张的体现于上述论述的所谓“实质的犯罪论”在日本不过是一种有力说而非通说,而且连前田教授自己都承认他的学说在实务界的影响要比在学界的影响大得多。日本的传统的犯罪论体系,在构成要件论、违法论的阶段不区别故意犯与过失犯(不承认构成要件的故意过失),而客观地予以判断(而就行为论是否前置于构成要件论来说,存在着见解的分歧),构成要件论是讨论事实(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的构成要件论;违法论则区别违法性阻却事由的事实的前提以及违法的评价,而责任论则以责任能力为前提,作为责任的种类区别故意和过失,并且作为责任阻却事由加上期待不可能性,就是这样的一种构成。坚持这样的传统的犯罪论体系的代表性学者,老一辈的有泷川幸辰教授、平野龙一教授、中山研一教授、内藤谦教授等,中青年的学者则有山口厚教授、浅田和茂教授等(在此行为是否属于独立的阶层的问题暂且予以忽略)。单说在日本非常有力的“结果无价值+构成要件的违法类型说”的大批论者那里,三阶层之间的分工是极为明确的,从形式到实质,从事实到价值,从客观到主观,这样的简明的和传统的犯罪论体系,不但没有成为“昨日黄花,不复存在”,而且是得到了有力的坚持和精当的发展。
三、改良论者认为,德日刑法学的教科书中,“各种学说,各种理论,铺天盖地地迎面而来,叫人眼花缭乱。”[15]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在这里,论者所说的德日刑法学的教科书中“各种学说,各种理论,铺天盖地地迎面而来,叫人眼花缭乱”的论断,在事实的层面上说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对于这样的事实应该如何作出价值上的判断?在我看来,论者对于德日学说“泛滥”的批判,其实反而映衬着中国刑法学累积不足的欠缺。中国刑法学对于各个问题,特别是总论问题的研究,惯常是常套的“主观说”、“客观说”或者标榜所谓主客观相统一的似是而非的“折衷说”,而往往缺乏对于相应问题的深入探讨。比如说在对待紧急避险的行为能否实行正当防卫的问题上,违法阻却说和责任阻却说的区分显然有助于对于对象的认识和对于结论的把握。紧急避险行为的正当化依据,在不区分违法和责任的体系中,也就没有所谓的违法减少说与责任减少说(以及违法责任减少说)之间的对立,这样,也就必然妨碍了我们对于紧急避险的法律评价之认识,从而也就妨害了对于紧急避险行为能否实行正当防卫问题的把握。而与此相对,在犯罪论体系中明确区分违法和责任时,将紧急避险区分为正当化的紧急避险(作为违法阻却事由的紧急避险)和免责的紧急避险[16](作为责任阻却事由的紧急避险)[17],则尽管两者都属于不可罚的行为,但是对于属于违法阻却事由的行为不能实行正当防卫,而对于属于责任则却事由的行为进行正当防卫则是可能的。可以说,这里,论者所批评的各种学说、理论的“铺天盖地”、“眼花缭乱”,恰恰是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诸多理论学说的存在,深化了我们对于问题的认识,也为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方案。这里,这个所谓的“学说泛滥”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刑法学理论学说的精致或粗放的问题。对此,笔者同意陈兴良教授的如下论断,“精细不是过错,过分精细才是过错。但对于刑法学这样一个关乎公民生杀予夺的学科来说,过分精细之过错远远小于粗放之过错。因此,没有经历过精细的我国刑法学,是没有资格指责大陆法系刑法学过分精细的。”[18]诚哉斯言。
四、改良论者认为,“有的日本学者就直接采用了和我国平面式犯罪构成体系一样的犯罪判断体系。”“这可以说是对德日传统的犯罪判断体系进行反思的结果。”[19]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诚然如改良论者所说,“有的日本学者就直接采用了和我国平面式犯罪构成体系一样的犯罪判断体系。”但是,事实上在日本采纳了“四要件的平面的犯罪论体系”的,不过是个别研究者出于个人的经历的一种学术偏好而已。的确,夏目文雄(1929-,曾任爱知大学法学部教授,现为该校名誉教授)、上野达彦(1947-,三重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合著的《犯罪概说》(敬文堂,1992年版)和此后的几乎没有明显变化的合著《刑法学概说(总论)》(敬文堂,2004年)确实采用了四要件的体系。但是,纵观以上两书,并非是在对两种不同的体系进行优劣评判的基础上作出的取舍选择,而是在介绍了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论历史之后,径直采纳了四要件的论说方式(其论说顺序两书一贯,是客体-主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对于采纳平面四要件体系的理由,只是在前言之中指出,这是因为“近年来的刑法学展开了基于极为绵密的规范论理学的刑法理论。但是,其过于形式主义的方向大概也使得刑法学的全体变得难以预料。现在,在讲解刑法学的时候,我们痛感到有必要能够俯视其全体。采纳像本书这样的犯罪论构成的教科书未必多,今后,至少,要是能成为针对规范主义刑法学的反省的话,就很荣幸了。”[20]实际上,这样的一种问题意识,就是认为分析的、论理的思考妨害了对于“刑法学全体”的认识,从而为了能够“俯视刑法学的全体”,而主张所谓的“全体的思考”,从而采纳了平面的四要件的体系。但是,如论者指出,这种“全体的考察”却内涵着将刑事司法直观化、感性化的危险,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21]
不仅对于分析的思考和体系的考察的青睐、对于全体的考察的警惕使得我们对于以上的采纳四要件体系的主张持排斥的态度,而且,坦率一点说,以上两位研究者在日本刑法学界更多不过是处在边缘的形态而从未对主流的日本刑法学知识系统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较以上两位更为著名的、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熟悉的著名的中山研一教授常年研究苏联刑法学[22],而自己在教科书[23]中仍然坚定地采纳了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只不过中山主张行为是独立的阶层,从而采纳了四阶层的体系)。以上事实也可以直观地说明,以个别的日本学者采纳了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来论证日本学界“尝试突破传统的唯体系论的马首是瞻的倾向,考虑建立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恐怕是难以立足的。[24]
五、改良论者认为,德日犯罪体系论“有唯体系论的倾向,偏离了现实的司法实践。”“在德日,刑法学者的研究精力,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投入到体系的建构上,而不是具体问题的研究上。”[25]对此,应该怎样认识?
这里,论者实际上提到了体系的思考与问题的思考的辩证关系问题。在建构犯罪论的体系之际,明确问题的思考与体系的思考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重大的意义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和认识呢?
一)对“体系的思考”的反省和“问题的思考”的提出
确实,偏重体系的话,就会过分拘泥于概念的明确化和体系的整合性,推导出不利于现实的结论来。这种倾向,在重视体系的德国刑法学中,尤为明显。因此,“二战”以后,德国的刑法学者中开始出现对偏重体系的倾向进行反思的见解。1957年,德国刑法学者韦登博格(Wurtenberger)指出,学术研究之中存在着体系的思考(Systemdenken)与问题的思考(Problemdenken)之间的对立,并且认为德国刑法学几乎是偏重于体系的思考。[26]在日本,也有学者在“从体系的思考到问题的思考演变”的气氛之下,强调同体系的整合性相比,应当更加尊重解决问题的具体的妥当性。如日本著名刑法学者平野龙一博士于1966年认为,日本刑法学之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27]平野主张,为了体系的体系是没有意义的,刑法学必须是对于现实的问题能够有效予以解决,也就要求从体系的思考到问题的思考的转换。[28]平野之后的学者也认为,“一直以来,‘是体系的思考还是问题的思考’或者‘从体系的思考到问题的思考’这样的问题被屡屡提及,促进了对于从来所偏重的体系思考的充分反省。”[29]人们开始对体系论思考的产物——或者说体系论本身——在理论刑法上应该具有怎样的意义进行重新反思。
(二)问题的思考不能否定犯罪论中的体系思考的意义与重要性
但是,体系的思考毕竟是必不可少的。将犯罪的要件分解为“行为、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大致上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对于这些要素如何进行体系化则存有争议。“就刑法学来说,可以认为,贯彻论理的整合性、树立没有矛盾的犯罪论体系是学者的使命所在。”[30]因此,就日本刑法学来说,继受缜密的理论刑法学在某种意义上就可谓是当然的归结。“但是,一旦将这样的思考极端地推进的话,就会成为追求‘为了体系的体系’,有陷入纸上谈兵的危险。是‘体系的思考’还是‘问题的思考’的见解的不同,就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但是,另一方面,将关乎犯罪成否的诸要件纳入到犯罪论的体系之中,在犯罪成否之认定的场合,从法官的恣意的判断中致力于对于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这绝对不是没有理由的。”[31]
就是说,问题的思考,并不否定犯罪论中的体系思考的意义与重要性。将和是否成立犯罪有关的问题全部列入体系性的框架之中以得出结论的方法,对于排除判断者的任意性来说,是最合适的方法。
就体系思考的重要性来说,首先,不以任何体系思考为前提就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再者,尽管不容否认,由纯粹的体系的论据出发的议论常常缺乏说服力,但是体系论层次上(比如一定的阻却事由是违法阻却事由还是责任阻却事由)的理论检讨还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在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的时候,对于类似的事例的过去的解决或者是将来应该的解决是否矛盾这一点也是必须考虑的。检讨事例解决之间的相互的体系的关系,对各自对事例的解决方案予以整合,力图使其不产生论理的、价值的矛盾,这也是平等原则的要求,是法治的精髓所在。所以说,由问题的思考出发,体系的思考仍然是不可欠缺的。[32]“当然,这里的‘体系’不是排斥问题的思考的,不如说我们是将问题的思考作为前提,根据新出现的问题(以及更进一步的价值观的变迁)不断的修正、补充原来的体系。对于全部的事例都可以演绎出妥当的解决结论这样的封闭的、完结的体系是不存在的……不但是现阶段的犯罪论的体系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将来的体系也是如此。”[33]犯罪论的首先的课题就在于,在对得以考虑的全部的事例的类型予以把握的基础上,探究其相互之间不矛盾的实质的解决的标准。所以可以说,问题的思考是研究的起点,体系的思考是研究的归结。从问题的思考到体系的思考的提升,就是相关者的讨论之介入以达成事件解决的合意的过程。可以说,问题的思考尽管是在既定的“体系”之内完成的,却又是在对这种体系试图纠偏、不断拷问的过程中进行的,最终得出的结论使得具体事例解决中综合了不同的讨论并且反馈于体系,对原来的体系修枝剪叶,并在一定意义上固定为新的体系。“从问题的思考到体系的思考”,“贯通问题的思考与体系的思考”这样的研究范式,是值得推而广之的[34],而且,“在体系性思考和问题性思考之间进行综合是富有成果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35]
(三)“唯体系论的倾向”?——对于改良论者的回答
对于改良论者提出的德日刑法学的犯罪体系论中存在的“唯体系论的倾向”,来看看当下的日本一线学者是如何看待的。立命馆大学法学部教授松宫孝明(1958-)指出,在日本的刑法学中,传统上,由于追求体系的、精致的理论构成,不太在意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乍看上去似乎是忽略了“问题的思考”的“体系的思考”。但是,概览有关日本刑法总论的理论,就会觉得得出前述的结论是有疑问的。在日本刑法中,体系的思考并没有妨碍问题的思考。[36]大阪市立大学教授浅田和茂(1947-)也认为,“确实,炫耀体系的美学绝对不是刑法学的任务。但是,对于犯罪的成立要件予以整序、构成不存在前后矛盾的体系,将犯罪是什么予以明确,对于各个犯罪的成立要件的内容予以确定,这是不可欠缺的工作,以此为前提,对于现实的问题的处理也是必要的。体系的思考与问题的思考不是相互对立的,经过两者之间的反馈与互动,大概也就能带来适切的体系和问题的解决。”[37]因此,概括起来可以说,没有体系就没有学问,另外,在重视具体的妥当性的时候,也容易忽视刑法的保障机能。解决问题的思考,应只看作为对偏重体系的学问倾向提出的警示而已。[38]
而且,在我看来,对于当代中国的犯罪论体系建构来说,问题不在于体系的思考之后出于问题的思考的反省,而在于体系的思考建立本身。就像一个已经现代化了的国家正在反省诸如老龄化、少子化等后现代的问题,而我国首先需要面对的,则是现代化本身的问题。这样来看的话,那么所谓的“唯体系论”的问题,和前面所说的对于所谓“学说泛滥”的问题一样,特别是对当下的我国学界来说,可以认为是一个伪问题。
[1]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梁根林、付立庆:《刑事领域违法性的冲突及其救济——以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检讨与反思为切入》,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0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以下。
[3]对此,请参见付立庆:《重构我国犯罪成立理论的正面展开:基本依托和意义所在》(未刊稿)。
[4]对此,请参见付立庆:《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改造研究的现场叙事——兼对一种改良论主张的若干评论》(未刊稿)。
[5]对此,请参见付立庆:《重构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目标定位——二阶层、三阶层还是四阶层?》,载冯军主编:《比较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9页以下。
[6]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39-40页。
[7]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39-40页。
[8]关于西田采纳了违法有责类型说,可参见西田典之:《刑法总论》,弘文堂,2006年版;关于佐伯采纳了违法有责类型说,可参见佐伯仁志:《构成要件论》,载《法学教室》2004年第6期,第34页;至于上述其他学者采纳了违法有责类型说,可参见山中敬一:《刑法总论І》,成文堂,1999年版,第151页。
[9]山口厚:《刑法总论》,有斐阁,2005年补订版,第28-29页。对于违法有责类型说,我国台湾学者蔡墩铭教授也认为,果然如此的话,“则构成要件已成为犯罪类型,而构成要件论几与犯罪论无异矣。”蔡墩铭:《刑法总论》修订四版,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138页。
[10]内藤谦:《刑法讲义总论(上)》,有斐阁,1983年版,第187页。
[11]浅田和茂:《刑法总论》,成文堂,2005年版,第116页。
[12]参见山中敬一:《刑法总论І》,成文堂,1999年版,第152页。
[13]井田良:《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成文堂,2005年版,第7页。
[14]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41页。
[15]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42页。
[16]紧急避险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保全法益与损害法益价值相等的场合,比如保全法益与损害法益都是生命或者身体的场合等等。与我国的平面式犯罪构成理论以及社会危害性理论相关,将紧急避险笼统地看作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可能是过于简单化的。
[17]这种区分可能是刑法规定上的区分,也可能是学理认识上的区分,但是都以阶层式地区分违法与责任为前提。需要说明,包含“构成要件”的此种“三阶层体系”在立法之中也得到反映的,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在德国明确地将可罚性阻却事由二分为“不违法”的场合和“无责任”的场合的,是始于具有将紧急避险二分之规定的1927年刑法草案,而实际上对之加以改正并且施行的则是1975年的刑法总则。而在日本,订立于1907年的现行刑法之中并未将违法阻却事由予以二分(这是因为作为其摹本的德国刑法典的立法者此时尚未掌握将可罚性阻却事由二分说的立法技术),此后一直维持此种状况至今,就连1974年的日本改正刑法草案之中,也未有这样的二分规定。松宫孝明:《关于日本的犯罪体系论》,《立命馆法学》,2005年第5号,第324-325页。
[18]陈兴良:《转型与变革:刑法学的一种知识论的考察》,载陈兴良、周光权著:《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代跋。
[19]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44页。
[20]参见夏目文雄与上野达彦合著的《犯罪概说》(敬文堂,1992年版)和合著的《刑法学概说(总论)》(敬文堂,2004年)两书的前言部分。
[21]参见平野龙一:《刑法总论І》,有斐阁,1972年版,第88页。
[22]其在此领域的代表作主要包括《苏维埃刑法论·第1分册·犯罪论》,宫崎升、中山研一译,法务省刑务局,1964年版;《苏维埃刑法:本质与课题》,中山研一著,庆应通信,1972年增补版;《马克思主义与刑法》,皮昂特考夫斯基著,中山研一、上田宽译,成文堂,1979年版。
[23]中山研一:《刑法总论》,成文堂,1982年版。
[24]黎宏教授还认为,前田雅英教授的“以构成要件为中心,首先论述客观的构成要件,之后讨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正当业务行为之类的客观的正当化事由,之后再讨论责任的犯罪论体系,实际上与我国的平面的犯罪论体系有相近之处。”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44页。对于这样的判断是否可以成立,笔者也表示怀疑。
[25]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42页。
[26]参见平野龙一:《刑法的基础》,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247页。
[27]平野龙一:《刑法的基础》,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247页。
[28]参见平野龙一:《刑法的基础》,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247页以下。
[29]仲地哲哉:“构成要件论”,载中山研一等编:《现代刑法讲座》(第一卷·刑法的基础理论),成文堂,1977年版,第231页。
[30]立石二六:《刑法总论》,成文堂,1999年版,第50页。
[31]立石二六:《刑法总论》,成文堂,1999年版,第50页。
[32]关于体系性思考的优点,可参见骆克信:《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28页。同时,骆克信教授也指出了体系性思考存在着多方面的危险。见同书第128-131页。
[33]井田良:“体系的思考与问题的思考”,载《法学教室》第102号,第83页。
[34]1995年,张明楷教授在评价平野龙一博士的刑法学术思想的时候曾经指出:“我国的刑法学体系并不完善,无疑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刑法学体系。但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的犯罪现象不断产生,刑事司法中存在许多现实问题。我们既需要‘体系的思考’,也需要‘问题的思考’。”参见李海东主编:《日本刑事法学者》(上),(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联合出版,1995年版,第293页。
[35]骆克信:《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36]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第3版),成文堂,2004年版,第298页。尽管此后松宫也曾认为“象征着‘体系的思考’和‘问题的思考’的分裂的日本刑法学的动向,可能会遗憾地被(中国的同行)作为‘反面教材’所接受”(松宫孝明:《关于日本的犯罪体系论》,《立命馆法学》,2005年第5号,第331页),但是,在我看来,那可能不过是在参加由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犯罪论体系的国际研讨会时,作为客人的一种谦虚的自嘲罢了。
[37]浅田和茂:《刑法总论》,成文堂,2005年版,第90页。
[38]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