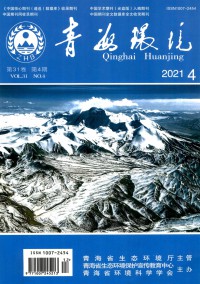环境NGO研究论文:国内环境NGO困境及策略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环境NGO研究论文:国内环境NGO困境及策略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本文作者:王德新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自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环境NGO的社会主体地位得到了承认,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仍然是当前制约环境NGO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NGO的成立实行“审批制”,准入门槛过高
目前,我国规范NGO设立的法规主要有三部:一是1998年10月生效的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二是同月生效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三是2004年6月生效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于环境NGO而言,既可以依法登记为会员制的“社会团体”,也可以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它们都不以营利为目的,只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虽然我国已建立起一套登记制度,但实践中环境NGO获得登记的还占不到总数的一半。据统计,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环境NGO只占总数的38.9%,在工商机关登记的占4.4%,另约有56.7%的处于没有登记的状态。[1]环境NGO的登记率偏低,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登记制度不合理。首先,我国实行混乱的双重审批制。在NGO的设立方面,两部法规都实行“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和“登记主管部门审查”相结合的双重审批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审批登记制阻碍了环境NGO的登记。一方面,不少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门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模式,对NGO抱有高度的不信任感和怀疑眼光。主管部门在审批设立NGO的申请时,如何降低政治风险和规避责任往往是首要的考量因素,而NGO的发展被置于次要的目标上。另一方面,条例虽然对登记机关的工作流程有详细规定,但对于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批义务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业务主管部门由于肩负对所属NGO的活动的日常监管职责,但又不能从中受益,故在当前强调“维稳”的大环境下很容易使其滋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对设立环境NGO的申请经常采取“推脱”的态度。这两方面的原因的综合作用使得实践中设立环境NGO的申请很难获得批准,申请者不得不转而求助工商登记,甚至冒险不登记。其次,我国设置了苛刻的成立条件。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0条设置了苛刻的社团成立条件。比如,在会员数量方面,要求至少有50人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人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在物质条件方面,要求有合法的经费来源,其中全国性社团要有10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地方性的社团要有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基金会管理条例》虽然没有会员数的要求,但对原始基金额度的要求高得惊人。根据条例第8条的要求,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且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相比而言,NGO的成立条件比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成立条件还要苛刻很多。对于从事公益活动的环境志愿者来说,在NGO成立之初就要求达到上述会员和资金条件,显然存在困难。苛刻的成立条件,降低了环境NGO的登记率。再次,我国实行严格的年检制度。无论是社会团体还是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于5月31日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年检主要审查遵纪守法、章程变动的等情况,本无可厚非。但在实践中,某些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在审批上体现了从严的精神。比如,“不听话”的不批,从事了“干扰地方经济发展”活动的不批,有疑问的不批等。年检审批机关的随意性,导致环境NGO获得合法身份的门槛太高,于是越来越多的NGO转而采取工商注册的形式;另有一些NGO寻求中国特色的变通方式如通过部门挂靠、媒体报道、领导出席、名人挂帅等方式,以使自身的存在获得合法性;还有一些NGO干脆游离于法律之外,我行我素地从事环保活动。
(二)实行“限制竞争、抑制发展”的政策,制约了环境NGO的规模效应
我国对NGO却采取了一种“限制竞争、抑制发展”的政策,其表现就是法律规定的限制分支和非竞争性原则。例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登记。第19条规定:社会团体经审查批准,可以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社会团体不得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13条更进一步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限制竞争、抑制发展”的政策有利于避免NGO之间的无序竞争,也保障了政府对NGO管控的有效性。但是,这一政策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限制竞争会导致个别NGO的垄断,这反而会危及环保公共利益;抑制规模在实现政府管控有效性的同时,却牺牲了NGO从事环保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活动能力的增强。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环境NGO是在相互竞争中成长和壮大的,而且其能力往往与其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例如,美国环境保护基金协会(EDF)成立于1967年,最初只有10名会员;由于其工作卓有成效,现在已经发展成拥有30万会员的庞大组织,其150名全职人员中有一半是科学家、律师、经济学家等专业人员。再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1961年成立时只有几个创始会员,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一个由27个国家级会员、21个项目办公室及5个附属会员组织组成的全球性网络,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非政府环境NGO。截止2009年,该组织共资助中国开展了100多个重大项目,投入总额超过3亿元人民币。[3]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其庞大的规模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会产生这么大的积极作用。
(三)财政资助少,税收优惠制度不健全,危及了环境NGO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环境NGO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要维持自身生存和活动能力就需要外界的资金资助。资金来源大体有三个途径:一是政府的资助,二是社会各界的捐赠,三是会员的会费和投入。统计显示,我国74%的环境NGO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在拥有固定资金来源的NGO中,政府发起成立的环境NGO占到了42.1%,高校环保社团占到了36.8%,草根环境NGO仅仅占10.6%。就草根环境NGO的资金来源看,59.6%的资金为会员捐赠,48.8%为企业捐赠,64.6%为私人捐赠。而在美国,在NGO资金来源中社会各界的捐赠占20%,会员投入占49%,有31%的资金来自政府基金或政府合同,其中联邦政府是美国NGO最大的资助者之一。[4]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环境NGO的资金资助简直少得可怜。除了政府财政投入较少外,我国NGO整体上获得社会资助的规模偏少。统计显示,中国的NGO总支出只占GDP的0.73%,既低于发达国家7%的水平,也低于4.6%的世界平均水平。[2]究其原因,与我国NGO税收优惠制度的不健全不无关系。这突出地表现为三个方面:(1)我国尚未出台系统的NGO税收优惠法,相关规定散见于各有关税法中,立法不够系统、明确和具体。(2)NGO的特殊税法主体地位没有得到突出,在财产税、商品税方面缺乏专门的优惠措施。(3)对捐赠人的税收减免制度不合理。例如,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企业的捐赠财产可以从应税所得额中抵扣,但是作了如下限定:一方面,内资企业抵扣所得税时要求必须是间接捐赠,直接向NGO捐赠的财产不能免税;另一方面,实行抵扣最高额度限制,即不管企业捐赠多少均只能免应纳税款的3%。这种立法现状,大大降低了企业向环境NGO捐赠的热情,也是导致不少NGO死亡的重要原因。
(四)环境NGO从事环保活动的方式,受到了配套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制约
国外成熟的环境NGO从事环境保护活动的方式往往是多元的,常见的有四种:一是影响政府决策,即反映公众环保呼声,从事环境研究和调查,对政府制定环保法规和出台环境政策施加影响。二是介入企业生产,即与企业合作开展环境科研活动,促进企业推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三是从事环保实践,如推动和践行绿化造林,保护和提升环境质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等。四是环保宣传教育,如通过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介和举办演讲会等方式进行环保知识的传播,推动公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我国目前而言,环境NGO虽然在四个方面都有所尝试,但配套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其从事环保活动往往力不从心。例如,赋予环境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在世界各国几乎是通例;但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当一起环境公害事件发生后,环境NGO自身的财产利益不必然受到直接损害,它往往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立法设定的“直接利害关系”的原告资格条件,显然成了环境NGO提起公益诉讼的直接障碍。在实践中,我国最大的环境NGO即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于2009年7月6日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法院受理该案后以调解的方式结案。[5]此案成为我国环境NGO提起公益诉讼“破冰”第一案,但此前和此后鲜有NGO起诉成功的,法院经常以原告不适格为由拒绝受理。配套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给环境NGO从事环保活动造成的消极影响,由此可窥一斑。
推动环境NGO繁荣发展的法律对策分析
(一)转变“政府管制NGO”的陈旧观念
任何法律制度的改进,都是从观念的转变和革新为先导的。完善我国环境NGO相关法律制度,应当从转变传统的“全能政府”观念和“管制型”社会治理模式开始。首先,改变“全能政府”观念,确立“公民社会”理念。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建立了政府统合一切社会领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唯一合法管理主体,同时也是公共产品的唯一合法供给主体。1978年以后,正是认识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不足和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我国才开始了绵延至今的改革开放。此后,整个社会逐渐分化成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公民社会”三元并立的结构。相应地,社会主体也分化成三个部门即第一部门(Publicsector,即政府)、第二部门(Privatesector,即企业)和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即非政府组织或非盈利组织)。[6]公民社会的精神,是倡导公民和NGO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关注和解决慈善、环保、教育等公共问题。历史经验表明,政府在处理环境公共问题方面经常力不从心,环境ngo是必不可少的社会依靠力量。其次,更新“执政安全”观念,确立“风险分担”理念。我国环境NGO遭遇法律困境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问题。有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对NGO的心态极其微妙:一方面,对于环境NGO在公益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表示赞赏,因为政府在解决某些环境问题(如保护野生动植物、绿化等)时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力量来弥补其不足;另一方面,又对环境NGO的发展壮大心存疑虑,担心其维权活动影响党和政府的执政安全,也担心NGO的“风头”过大而影响党和政府的群众威信。所以,就对NGO登记成立、开展活动等诸多方面设置门槛和限制,导致NGO要么无从获得登记、要么发育不良。笔者认为,影响执政安全和群众威信的根本因素是环境公共问题能否得到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才是最大的隐患。与政府把所有问题都拦在自己身上又解决不好相比,给环境NGO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其分担处理环境公共问题的社会责任,更有利于实现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安全。所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执政安全观念,这一点非常必要。最后,改变“管制型政府”观念,确立“服务型政府”理念。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一种管制色彩浓厚的行政管理模式。管制型政府的特点,以高度集权、政府全能为观念前提,以行政审批、行业准入为制度特色,以行政介入、业务干预为执法特色。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等法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制定的,体现了较为浓厚的政府管制色彩,如登记审批制、年检审批制等。这些做法显然已经不再符合时展的需要。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服务型政府”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政府、职能有限的政府、依法行政的政府和公众参与的政府。[7]根据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政府与NGO不再是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而应该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在尊重NGO独立与自由的基础上合作服务社会人群、推进文明进步。
(二)完善我国环境NGO相关法律制度的思路
我国现行的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为代表的NGO相关法规,大多是由政府自己而不是立法机关制定的,且大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这些法规的某些指导思想已经过时,已不能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政府组织基本法》。我国当前关于NGO的相关规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法律位阶低,主要是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难免体现行政部门利益,缺乏立法机关统一的权威立法;二是相互协调性差,由于行政机关管理权限的分工,导致NGO法规政出多门,为数众多、且协调性差;三是实体规范少,制度有盲点,现行法规往往只规定登记审批这些程序问题,忽视了NGO的组织建设、日常监管和服务保障等配套制度,不利于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规范。为此,我们呼吁全国人大根据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享有结社自由”为基础,尽早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政府组织基本法》,以基本法的形式对环境、教育、慈善等领域的NGO共性问题做统一规定。第二,改革现有的双重审批制,实行单一政府部门形式审查的登记制。在西方国家,公民成立NGO被认为一项宪法自由,政府对NGO成立申请不实行审批制,而实行注册登记制。NGO的成立门槛也很低,如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小规模的NGO只需缴纳89美元的注册费,成员人数只须1个人,就能合法成立;而且,成立后也没有在该州从事活动的要求。[8]但是,登记机关、税务机关、审计机关经常派员到NGO办公地进行检查;有33个州由司法机关负责对NGO组织的财产进行监督管理,他们拥有仲裁权、处罚权和起诉权,以确保NGO行为符合规范。[4]相比而言,我国现行法律对NGO带有较强的管制色彩,设立条件过高,重设立审批、轻日常监管。这种管理体制一方面阻碍了NGO的成立,遏制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和权利,另一方面也不利于NGO活动的规范化建设。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对现行的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主管部门“双重审批制”进行改革,降低成立条件(2人以上、5000元资金即可注册);同时,明确审计、税务、司法等机关的日常监管职责。第三,完善NGO资金来源和捐赠制度,规范其资金使用行为。NGO最大的挑战不应当是登记,而应当是如何提高工作绩效,以吸引捐赠者、扩大影响力。这需要从三个方面完善相关制度:一是政府对NGO的资金资助制度。以美国为例,政府不直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而是以招标的方法委托给NGO;因此NGO可以从政府那里申请得到社会公益事业的项目资金,但同时其工作完成和资金使用情况要接受政府的监督。二是完善NGO税收优惠制度。一方面,凡是企业和个人向NGO捐赠的,捐赠的财产免征个人所得税;另一方面,NGO自身财产免征所得税和财产税。三是完善NGO盈利资金管理制度。西方经验表明,NGO可以存在商业行为,其商业行业并不必然影响其公益属性。在美国,NGO的资金平均有50%来自经营,2002年全美NGO的总资产达到24000亿美元。为了保障这些资产使用的公益性,美国各州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在法律上明确NGO的财产所有权归社会所有,个人不得侵占;经营全部所得必须用于与宗旨相关的事业,任何人不得分红;机构解散后,剩余财产转移给同类机构,个人不得瓜分。[4]这些做法在规范了NGO的经营活动的同时,也保证了其非盈利的组织性质,值得我国借鉴。第四,完善NGO活动途径的法律保障机制,规范其活动的公益性。如果说前述三方面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各类NGO的共同需要,那么对活动途径和内容进行规范则涉及各类NGO的特殊性。就环境NGO而言,其在从事环境公共利益保护活动时,最迫切需要法律保障和规制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修改诉讼法的方式,赋予环境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让环境NGO拥有利用司法途径对任何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的权利。对此,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法律修改动向,让我们看到了环境NGO通过司法途径制止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的希望,但环境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仍需法律的进一步明确授权,其提起诉讼的程序也需做进一步的详细规定。二是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或者制定环境NGO法规的方式,规范环境NGO与企业的合作行为。在现代社会,企业是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主要主体,造成环境污染与破坏的原因往往是企业缺乏环保意识和环保技术。在西方国家,环境NGO与污染企业合作是促进环境保护的常见手段,即企业出资、环境NGO提供专业知识,为企业员工开展环保培训、进行环保技术科研项目等。但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即如何保障环境NGO的公益性而不使其与企业结成利益集团?这就需要对环境NGO与企业的合作、及其资金流向进行法律监管,以规范环境NGO与企业的合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