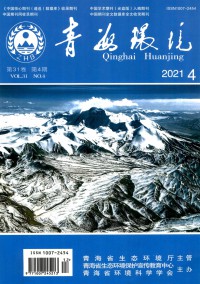环境尘暴管理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环境尘暴管理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就在自南而北的SARS恐慌肆虐着2003年春天的北京城时,近年猖獗的沙尘暴却差不多销声匿迹了,往年满世界的尘土飞扬一变而为似乎让人有些陌生的和风丽日。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也以异常醒目的标题,隆重推出了关于沙尘暴问题的一组文章,如《沙尘暴——地球不可或缺的部分》、《沙尘暴的杰作——黄土高原》、《沙尘暴:抵抗全球变暖的幕后英雄》、《被媒体“妖魔化”的沙尘暴》等。这些文章根据环境化学、海洋生态学、大气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世人“一步步勾勒出沙尘暴的另一幅面孔”即“生命万物的忠实朋友、改善环境的可靠帮手”,所以,对人类而言,沙尘暴“也是大自然的一种恩赐”。这些文章还进一步把沙尘暴提到“自然规律”的高度来看待,认为沙尘暴“不但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而且无法根治,大的气候趋势不可违背”。
此情此论,客观上使去年8月份出版的美国环境史名著《尘暴:19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生态与人译丛”,夏明方、梅雪芹主编)显得姗姗来迟,而且有点不合时宜。那么,在诸如沙尘暴这类自然灾害的形成过程中,人类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由美国学者唐钠德·沃斯特倡导的有关环境问题的历史研究取向,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关注这些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迫切需要作出自己的回答。
最近,在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的一次座谈会上,包括北京大学、青岛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以及三联出版社等单位在内的十多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围绕着尘暴问题及《尘暴》译著,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并希望藉此给当前中国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增添一点历史意识和人文气氛。
作为一种自然过程,尘暴的发生确实有着不容否认的自然原因。与会学者对此并没有任何疑义。《尘暴》的译者侯文蕙教授(青岛大学法学院)还特别指出,我们在分析今年北京没出现尘暴的原因时,就不能单纯地将其归功于人工治理的成就,还要看到今年的雨水确实多于往年,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忽视自然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问题片面化、极端化、淡化甚至无视人类的影响和作用,恐怕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长期从事中国沙漠考古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景爱研究员(中国文物研究所),对这个问题,乃至更大范围的土地沙漠化问题进行了更为概括性的论述:“土地沙漠化,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沙漠化的二重性。长期以来,许多科学家着重强调沙漠化的自然性,而忽略了沙漠化的社会性,很少从社会的角度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结果治理沙漠化的成果往往又被人类活动所抵消。这是过去治沙活动没有扭转沙漠化恶性发展的根本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沙漠研究中心主任邹学勇教授,则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尘暴的二重性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详细解释了风洞实验的原理与操作过程,指出在风的作用下,对草原的人为破坏(如过度畜牧、开垦田地等)必然加重扬沙现象。他还指出,沙尘暴的产生固然有自然的原因,但也是人的因素所致,近代工业化以来则尤其如此。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人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了缓解因人口增长造成的人地紧张关系,中苏两国在上世纪中叶都曾大幅度开荒,出现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一是迷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自然规律,只看到短期利益而盲目建设。这是当前应该吸取的教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国荣先生指出,正是这种生态视角和文化批判构成《尘暴》一书的两大鲜明特色。与其他学者相比,沃斯特的研究凸显出白人到来前后发生在美国南部大平原上剧烈的生态变化。而这场由白人主导的改天换地的生态革命,对印第安人来说固然完全是一次毁灭性灾难,对急功近利的白人而言也同样是一场大悲剧,因为生态秩序的崩溃使得白人最终也成为受害者。而且在沃斯特看来,这场伴随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生态悲剧,并不限于大平原和北美大陆。这样,他就给陶醉在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繁荣中的人们敲响了生态的警钟。沃斯特还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美国,不要盲从和追随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沃斯特通过对尘暴的具体研究,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是靠大规模地吞噬自然资源而发展起来,其进程沾满血腥,所有这些都可以归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劣根性。因此,他的研究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他的环境史研究是对资本主义和对现代化理论的有力批判。
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宏副教授进一步指出,《尘暴》的理论基础有两个来源,即卡尔·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他把两者结合起来,并最终归结为文化。但他对沃斯特在《尘暴》中文版序言中所谈到的美国尘暴的世界意义表示质疑,因为至少前苏联和中国的荒漠化问题就与美国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在从事非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史问题时,我们需要反对和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
侯文蕙教授补充指出,中国传统的自然观明确地分为两种。除了“天人合一”之外,还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而“天人合一”思想,更主要的还是一种人生哲学。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和天的关系当然更近些,但是农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着和自然作斗争的问题。16世纪以来,中国环境加剧恶化,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人口的迅速增加带来的生存压力所致的。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完全可以为其他国家和自然科学学者的研究提供借鉴和补充。
夏明方指出,就中国史学界而言,环境史研究虽然只是在近几年才逐渐开展起来的,但是具体的工作很早就有人在做了。远在19世纪晚期,著名的维新思想家陈炽就曾经从历史上森林变迁的角度对中国南北两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解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各个不同专业的许多学者,开创性地运用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气候变迁和地貌变迁,以及环境变化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民族心理的影响,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迄今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有关气象、水利、地震、农林等各级研究机构,对中国历史上各类自然灾害史料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并以此为基础,对几千年来中国的气候变迁和自然灾害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以史念海为代表的一大批历史地理学者,则以其艰苦细致的史料考证工作和田野考古,为我们揭示了历史时期森林、植被、沙漠、河湖水系等时空变迁大势。所有这些工作,无疑为我们今天的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夏明方进一步指出,过去的研究当然也有局限,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离。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更深入地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是未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鉴于中国相关历史资料的连续性和丰富性,以及当代中国生态环境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相信中国环境史研究一定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