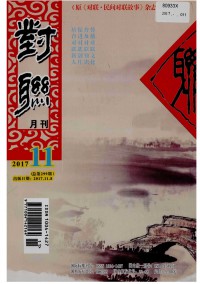民间叙事论文:民间故事语境及逻辑探究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民间叙事论文:民间故事语境及逻辑探究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本文作者:丁晓辉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巧女故事的荒唐
对巧女故事中的细节稍作推敲,就会发现处处充斥着不合理的情节。如《幺媳妇》⑤:三个媳妇回娘家,婆婆说:“大女玩四六天,二女玩三七天,三女玩二八天。三个人要一天去,一天回来……”三个媳妇为难了,不过问题被路遇的巧女解决:四六天是四天加六天,是十天;同样,三七天、二八天指的也都是十天。所以大家可以同一天去,同一天回来。这个情节只不过是以故意制造的语言含混列出了一道低级算术题。现实生活不是游戏,婆婆不必以低级无聊的文字游戏刁难媳妇,媳妇也不必接受这种荒唐的游戏前提。又如《巧媳妇》①:财主对巧媳妇起了歹心,派人对巧媳妇的公爹说:“限你家三天后交出公鸡下的蛋,山头大的猪,路长的一匹布。交不出就要巧媳妇抵。”三天后财主来要东西,巧媳妇说:“我爹刚生小孩,躺在床上。”财主问:“男人怎么会生小孩?”巧媳妇反问:“公鸡又怎会下蛋?”巧媳妇拿出秤对财主说:“请你称称山有几斤,我们好给你养猪。”财主没有办法。巧媳妇又拿出尺子给财主:“请你量量路有多长,我们好照着给你织路一样长的布。”财主张口结舌,灰溜溜地走了。此类故事属金荣华编纂的类型索引中的类型“875巧女妙解两难之题”。《巧媳妇》的情节分别对应此类型下的875B.1和875B.5,875B.1为“姑娘巧解公牛奶(以不合理喻不合理)”,875B.5为“巧姑娘以难制难”。②按金荣华的理解,巧媳妇反问公鸡怎会下蛋是“以不合理喻不合理”,巧媳妇让财主称山有多重和量路有多长是“以难制难”。财主的要求是荒唐的,巧女以荒唐应对荒唐,竟致财主灰溜溜地逃走———社会地位悬殊的两类人,以浅薄的口舌之争作为胜负依据,这似乎是更大的荒唐。康丽将巧女故事的叙事结构描述为:“‘困境’、‘考验’、‘破题’和‘困境解除’”,认为这一序列构成了巧女故事的核心形式。③这个结构可以简化为“困境—解困”。困境必须由巧女解决,那么困境如何由巧女解决?这时,民间故事的主体,也就是讲述者和听众的制造能力和欣赏品味受到了考验。何为难题,如何解决,这些具体情节的安排都受到故事所有者文化水平不高、思维能力有限等多方面的限制。故事需要具体的事件来展现巧女之巧。困境是必须的,巧女解决困境也是必须的。困境是预设的,即便总是荒谬,也要用婆婆和财主的貌似精明、其他几个媳妇和公爹等人的愚蠢笨拙来衬托,使之成为困境;解决困境的方法也常常是荒谬的,但不管巧女的解决方法有多牵强,也要用巧女的胜利,来展示巧女的机巧。钟敬文曾在1955年说:“单就情节说,这种故事所具有的,也有些并不合乎常情的,例如我们在巧女故事、侥幸成功故事等里面所看到的。”④巧女故事中的细节在研究者看来多无聊荒谬,经不起现实逻辑的简单推敲。但讲述者津津乐道,听众如醉如痴,如果仅用讲述者和听众的愚蠢来解释,显然不够公允。中国传统道德以敏于行、讷于言为贵,品评女性更以端庄稳重为美。机巧泼辣、巧舌如簧的快嘴李翠莲固有其美,但终究难与“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刘兰芝相提并论。但是,如果讲述者和听众都希望女性充当民间故事的正面角色,除了表彰其忠孝、贞节、能干等传统美德(这是故事常见的内容)之外,也只有通过讲述女性的机巧(如前分析,往往以拙劣的方式来表达)来展开故事了。巧媳妇故事赞美女性的方式是,把正面的女性设置成了有好结局的胜利者。还有一些巧女故事在表现男人欺侮女人的同时,也会出现两厢情愿的男女调情、猥亵对白。⑤本尼迪克特认为,民俗常常会违反文化标准,以此来满足人们的幻想、表达对文化束缚的愤怒。民间故事构成了一个来自文化现实的幻想世界,如果在平原印第安人文化中没有禁止与岳母性交的禁忌,那么故事里郊狼对这一禁忌的违反就不会引发听众的笑声。①从故事的拥有者来分析,无论是讲述者还是听众,似乎都愿意从此类巧女故事的男女调笑当中获得解禁的快感。这些故事讲述巧女是虚,借机发泄欲望是实,所以,他们根本不愿去追究巧女是否真的聪慧过人、巧女故事的细节是否真的符合常理。还要注意的是,女性在充当负面角色时,其特征也比男性更为突出。两兄弟故事中嫂子比哥哥更狠毒,懒惰夫妻故事中妻子比丈夫更脏、更懒,甚至在笑话中,女放屁手的放屁能力也胜过了男放屁手。如果以男尊女卑、心理投射等社会原因、心理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就与巧女故事中对女性的赞美形成矛盾。其实,从讲述者的叙事角度看,如果以女性为叙事中心,就只能有表现女人美好和刻画女人丑恶的两种选择,故事中的男性作为次要角色,需要发挥对比和衬托的功能。女人或被称颂赞美,或遭谴责嘲笑,体现在巧女或恶妇等角色身上,都是以女性为叙事中心的不同表现,二者并不矛盾。
智慧与愚蠢的混同
巧断连环案故事中出现的几起案件都是偶然事故,国王或官员的判决都出人意料。如:判定压死妇人婴孩的人把妇人领走,与该妇人一起生一个孩子,作为对妇人的赔偿;判定原告把砸死原告父亲的人领回家,当成自己的父亲赡养,作为对原告的赔偿。一些新奇的判决被设计成主事者超凡智慧的表现。然而,刘守华发现,这些情节也出现在贪财的判官、昏庸的县官断案等故事中,主事者并不智慧,而是被认定为愚蠢,②如《昏县官断案》③。金荣华把这类故事命名为“似是而非连环判”④。同样的内容,价值判断却截然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该故事的结构属于“难题———意外的解决方式”这一模式。难题最终会得到解决,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但同时,解决问题的方式应该是意外的。故事讲述者要通过出乎常理、出人意料的解决方式在模式化结构内部制造新鲜内容,这也正是听众的心理期待。此类故事往往归类到机智故事或愚蠢故事之下,与笑话、骗子故事紧密相关。邓迪斯在评论哈里•B•韦斯的《关于傻瓜西蒙》⑤一文时说,有时民间创造的角色是智慧和愚蠢的矛盾综合体。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聪明的傻瓜是土耳其的霍加(Hodja)⑥,在中东和阿拉伯北非,几乎每个文化中都有同样的角色。美洲印第安人的傻瓜通常也是骗子,他欺骗受害者,但也常为受害者所骗,只不过他欺骗别人的次数稍稍超过他被别人欺骗的次数而已。⑦一方面,这种聪明又愚蠢的判决可以用普洛普的理论来解释,即同一行为(功能)可以由不同的角色来完成。⑧故事讲述者既可以把功能相同的角色设置成有智慧的王者、清官,也可以设置为愚蠢的昏官。这就是令人困惑的现象:智者与愚者混同。另一方面,对于已经事先确定身份的角色而言,各种相似的行为逐渐汇集到一人身上,形成箭垛式人物。聪明的傻瓜身上集中了各种笑料,只要引人发笑,无论主角是欺骗还是被骗,行动的功能都得以完成,所以,聪明的阿凡提也常常受到捉弄,显示出愚蠢的一面。这两种现象说明,在此类故事中,角色相反的人物可以具有相同行为,同一个角色也可以有相反的行为。角色与行动的组合有很大的自由,但必须满足故事的内部叙事逻辑,即故事内部会在不合常理的颠倒错乱中制造新奇,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故事的总结局不会改变,依然是智者聪明判决,昏官胡乱判案,骗子即便愚蠢被骗仍被指定为机智人物。参照另一个故事《奉节县的来历》。这个故事的附记里说,该故事的异文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故事的主人公许尤是清官,主动给刘备墓万年灯上油;另一种是,许尤是贪官,诸葛亮罚许尤给刘备墓万年灯上油。①两种异文都是解释奉节县县名的由来,即“奉公守节”。这个例子为智慧与愚蠢的混同提供了佐证。为了达到预定的结尾(即“奉公守节”一词的出现),清官是彰显其奉公守节,昏官是警告其要奉公守节,相反的事件具有了相同的结尾。同一情节可以有相反的结局,相反的情节也会有同一个结局———这印证了邓迪斯的判断:同一母题也可以使用到不同的母题位上,同一母题位上可以使用不同的母题。②这并不意味着民间叙事的混乱,而是更进一步地凸显出一条重要的叙事逻辑———为了令人满意的结局,过程的合理性让步于结局的合理性。可以补充说明的是,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决定了产生变异的可能。因事论事来评判智或愚,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主观性。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当一代代的传承人按自己的理解重述故事、完成故事的再创造时,对聪明的赞美就有可能变成对愚蠢的嘲弄,反之亦然。这样,故事的角色就自然发生了变化,直至截然相反。民间叙事,尤其是其中的生活故事,有很强的娱乐性。讲述者使出浑身解数令听众解颐一笑,为日常生活的无聊注入生气,这是故事讲述的目的之一。他们称故事是“瞎话”,称讲故事为“日白”③,称故事讲述者是“日白佬”,这说明他们未必真的相信故事。所以,他们关心故事结局的合理性远远胜过关心故事发展过程的合理性。生活现实不是游戏,但人为制造的故事可以通过游戏的叙事形式讲述。
总结
(一)民间故事的叙事逻辑
弗莱认为传奇故事有“高度程式化的模式”,它“与游戏类似”,人们“期望每局棋都不相同,但并不期望棋的规则本身改变”。④这同样适用于高度模式化的民间叙事。民间叙事的外部形态类似于每一局棋,内部结构类似于下棋的规则。作为民间叙事的所有者,讲述者和听众既希望每一局棋都有新意(这要求文本有新鲜的内容),又不希望改变下棋的规则(这要求文本有稳定的结构,遵循一定的叙事规律)。民间叙事在模式化框架内的有限变化既是讲述者的叙事需要,也是听众在不愿改变“棋的规则”的前提下期望新奇内容的心理需要。回顾对这几个问题的具体分析,我们发现民间叙事的叙事规律受一定的叙事逻辑的支配,其目的在于必须要满足讲述者的叙事需要和听众的叙事期待。试将叙事逻辑归纳如下几点:第一,故事要便于讲述。故事必须简单,简单到便于讲述人记忆,便于听众理解,同时不致故事尚在讲述而听众已经遗忘讲述过的内容。这需要故事有最优化的情节,即固定的模式。第二,故事要有足够的趣味。故事需要复杂,复杂到具有强烈的对立和冲突,波澜起伏,引人入胜,这样才能吸引听众。所以故事的讲述者必须在叙事方式的简单和复杂、叙事内容的熟悉和新鲜之间寻找平衡。第三,故事要有一个满足听众心理期待的结局。这需要讲述者事先设定好故事的结局。开端到结局之间的过程往往有分属不同层次的、细小的叙事环节,这些环节本身可能并不巧妙,但结局必须令听众满意。讲述者和听众对结局合理性的关心超过了对过程合理性的关心。第四,故事的讲述要达到具体目的。故事的讲述目的决定了讲述内容和讲述形式。如果要消磨时间,故事就东拉西扯;如果要振奋精神,故事就曲折动人;如果要心理释放,故事就涉及到男女调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奥尔里克的叙事法则、拉格伦的英雄模式、汤普森的母题、普罗普的功能、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素、弗里的大词、邓迪斯的母题位……,无不是这些叙事逻辑的外在体现。
(二)从文本到语境中的文本
早在1914到1918年间,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调查时就发现,自己难以理解土著人对一次沉船事故的描述。这是因为讲述者和当地的听众已对故事耳熟能详,所以很多重要的内容都被省略。这样记录下的故事当然是不连贯的、混乱的,民族志学者只有多次倾听并在事后直接向讲述者询问后才能真正理解故事的含义。①因缺乏语境而导致误解的类似例子不胜枚举。邓迪斯认为,“某项民俗的语境就是该项民俗被实际使用时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②就传统民间叙事而言,它的产生和传承既涉及故事的讲述者、故事的听众、故事的讲述场合等共时性因素,更涉及到文化传统等历时性因素,如此众多复杂的要素共同构成了民间叙事的语境。美国民俗研究的“文本—语境”之争从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持续不断;③国内学者就民间文学研究的“文本—田野”关系也展开过热烈讨论。④这些争论都从最初的方法论的探讨走向本体论的思索。如陈建宪所说,“‘回归文本’命题针对的是民间文艺学因研究对象与目的泛化而导致学科特性消解的现状提出的。它不是一个要不要做田野作业的方法论命题,而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回归文本’并不反对走向田野,但认为走向田野的目的也是为了作品……”⑤不过,就民间文学的文本研究而言,没有人会反对在语境中理解文本的研究方法,把二者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将文本还原到语境,目的在于尽可能全面地理解文本的原貌。叙事文本应该回归到语境当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过程,邓迪斯把它分为两个步骤:识别⑥和解释。⑦识别是解释的基础,解释是识别的目的。研究的具体对象是文本,这需要识别;研究终极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人,这是解释。语境中的文本,无论是作为概念还是作为方法,都并不新鲜。对民的理解,即对民间文学拥有者(民间文学的讲述者和听众)的理解,更能深入对文本的理解;反过来,对民间文学文本的解释,终极目的在于对民的理解。在民间文学研究中,文本与语境,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关系,指向的都是人,并不矛盾。时至今日,民间文学的文本研究日渐萧条。一方面,当前对语境、表演理论的提倡,使民间文学研究在过分关注语境的前提下走向另一极端,舍本逐末,流于空泛。另一方面,因不重语境而流于浅显的识别随处可见,导致缺乏阐释力的分析(甚至是误读)泛滥成灾———这也是一些研究者弃文本、奔田野甚至鄙夷文本分析的重要原因。
(三)民间文学的价值
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拿“一般文艺学”的原理去解释和评价民间文学,往往就有些行不通,或不免“削足就履”②。董上德评论中国古代民间叙事时认为,“往往有程式化的故事,无稽的表述,还有东拼西凑的情节”,但是,“如果一本正经地以历史学家的学识修养去看待民间系统的历史故事,就只会看到一堆一堆戏说的垃圾,而就领会不了戏说背后的民间文化密码”。③研究者看到民间叙事的荒诞而对民间叙事价值产生怀疑,根源在于忽视了传统民间叙事与书面作家文学的本质区别。所以,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对口头传统的偏见的纠正。如民族志诗学的产生就与此直接相关,反对用作家文学的理念来看待口头传统。④与书面作家文学不同,传统民间叙事的产生、传播和变异都离不开故事讲述者与听众互动的具体语境,它得到听众认可后被反复讲述,民既是故事的创造者(讲述者)又是故事的欣赏者(听众),故事的讲述和欣赏成为民众内部的集体自娱自乐。民集创造者与欣赏者于一身,能够体验到创造与享受的双重快乐,故沉浸其中,乐此不疲。民间故事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荒诞的,其核心叙事逻辑是合理的,不能强求也无法强求内外一致。热情的研究者为了彰显民间故事的价值,往往会失之偏颇,片面强调其合理性,如强辩巧女之“巧”(此种现象居多);而持书面作家文学标准衡量民间文学的研究者往往为斥之荒诞不经,片面否定其价值。二者结论相反,实则一致,都是忽视了语境而从客位研究的角度得出的局外人的结论。这如民间故事中的呆子,遇到娶亲他哭丧,遇到失火他道喜,遇到打铁他泼水。虽然处处卖力,却因不分场合处处挨打。如果研究者一定想在同一层面上论证民间故事是合理还是荒谬,就无异于呆子故事里的主人公,只会遭到民众的嘲笑。从民间文学的热情的爱好者到怀疑其价值的研究者,再到回归文本语境的分析者,我们对民间叙事的认识经历了有理———荒谬———有理的双重否定阶段。这是因为我们的立足点经历了从客位到主位、从外来研究者到内部的民间叙事拥有者的改换。对民间叙事按照不同的层次分析,其外荒谬,其内合理———这不过是民间叙事的口头性、叙事性、实用性、文学性等特点既相结合又相背离的复杂产物。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