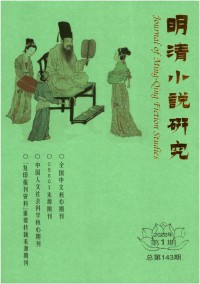明清小说花园意象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明清小说花园意象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关键词:《聊斋志异》“文化资本”“文化效忠从属关系”
摘要: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主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商贾阶层地位日盛,形成了对“士子”阶层的强大冲击。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当代大众文化学者约翰·菲斯克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理论,对深入研究《聊斋志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本文意图通过“士子”与“商人”间的“博弈”或“角力”关系研究,将“蒲学”研究由单纯的文学文本研究,拓展到社会文化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之中,为传统的研究方法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近年来,《聊斋志异》研究日趋活跃,研究范围涉及《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创作动机和人物形象等,而对蒲松龄创作思想研究一直是“蒲学”研究的重镇。这些研究的中心大多集中于蒲松龄的哲学、宗教、鬼神思想、孝文化传统、“绮思遐想”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已有论者将研究的主体拓展到了蒲松龄及《聊斋志异》中所透露的商品经济思想的领域,这种研究虽然是刚刚起步,但确实为“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开阔的文化社会学视野,而且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明清之际,正是中国社会主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余英时先生曾指出:明清之际“商人在中国的社会价值系统中正式地上升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渐渐转变为士、商、农、工的新秩序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六世纪以来,许多‘士’竟成为‘商’的代言人;所谓商人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通过‘士’的笔或舌而建立起来的”①。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同时也是建构性(Constructed)的,其必然反映在蒲松龄的创作思想中,众所周知,蒲松龄的父亲就是当时“弃儒从商”的一员。本文运用了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当代大众文化学者约翰·菲斯克的“文化效忠从属关系”理论,展开对《聊斋志异》中“士子”与“商人”关系的研究,通过二者间的“博弈”或“角力”关系解析,将“蒲学”研究由单纯的文学研究,拓展到社会文化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之中,这种研究不仅会有许多饶有兴味的新的体验,而且也为传统的研究方法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
一、“文化资本”和“商人”形象进入文本
当代法国文化社会学巨擘布尔迪厄在其代表作《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文化资本”,他指出,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一,经济资本,它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二,文化资本,它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三,社会资本,它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三种资本分别存在于不同的领域,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布尔迪厄还指出在各种鉴赏趣味和社会等级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上的同源关系,但这种同源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完全一致或对等的。“所谓‘同源’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场域都体现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每一场域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每一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等级秩序。”②
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对于研究十五六世纪中国社会结构及蒲松龄创作思想特别重要。首先,“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并不是“经济资本”越多,“文化资本”就越多,也不是“文化资本”越多,“经济资本”就越多。这一点在蒲松龄身上有着真实的反映,蒲松龄因其著述而与刑部上书、诗坛领袖王士祯,当朝名士李渔都有交往,王士祯还为其多篇小说作过序,可以说拥有相当丰厚的“文化资本”,但其一生贫困潦倒,教书为业,“经济资本”无从谈起,这些人生际遇都必然反映在其创作之中。
其次,“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和家庭环境、学校教育有密切联系,拥有雄厚经济资本的家庭可以将一部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即通过良好的家庭、学校文化教育,可使其子女或家庭积累起丰厚的“文化资本”,反之亦然。十五六世纪中国社会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实际就是这种转化的表征。明清之际,儒家和商家都已重新估量了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明末何心隐在《答作主》中说:“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③,即明确厘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等级,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商人是士以下文化教育水平(“文化资本”拥有)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科举竞争的无望,部分士人转投“商贾”,另一方面“商贾”本身的兴起,也成为了“士子”阶层的最大竞争对象。《聊斋志异》中有大量的篇幅揭示了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聊斋志异》全书“士子”形象最多,达300多个,其次是女性(狐女、闺秀、侠女、村姑、妓女等),再次是“商人”。“士子”形象最多是因为蒲松龄的士人身份,女性形象是源于作者创作中寄托感情的所谓“绮思遐想”,“商人”形象在书中的大量涌现不能不说是时事使然。
二、“士子”、“女性”、“商人”的三角叙事结构
因为蒲松龄本人的“士”的角色和立场,面对“异端蓬起”的商人集团,其内心感受必然流露在笔端纸上,我们看到蒲松龄在作品中不自觉地将“士子”与“商人”摆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展开德性的“博弈”和财富的“角力”,而这种“博弈”和“角力”都是经由“女性”这个特殊的纽带来实现的。在一场场或凄美、或悲壮、或团圆的种种悲喜剧中,实际上潜藏着一个基本恒定的叙事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三者的关系并非局限于传统的三角恋爱的俗套,而是朋友、知己、腻友、恋人、情敌等错综复杂的结构呈现。
举例如图:
《连城》故事梗概:乔生,少负才名,为人有肝胆,史孝廉有女,字连成,征诗择婿,女得乔生诗喜,对父称赏,父贫之,生叹曰:“连成我知己也!”倾怀结想,如饥似啖,无何,女许字于鹾贾王化成。未几,女病,沉痼不起,需男子膺肉合药,史告王生,王生不允,笑曰:“痴老翁,欲我剜心头肉耶?”于是,史对外称:“有能割肉者,妻之。”乔生舍身以膺肉送上,连成服药痊愈,乔生欲娶连成,王生怒而不允,欲告官并要娶连成,史乃重金谢乔生,乔生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连城不久即死,生往临吊,一痛而绝,二人九泉之下,得故人相帮,相与重返人间,王生无奈何,二人终成眷属。
《黄英》故事梗概:马子才,世好菊,至才有甚。陶姊(黄英)陶弟,应马邀约,居其地南荒圃,为马治菊。陶弟视马家不丰,欲为马卖菊为生。马闻言,甚鄙之,曰:“仆以君风流雅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为求贫也。”自此,陶弟、黄英种菊为业,一、二年间,村外治膏田二十顷,甲第益壮,后马妻死,娶黄英。初,马耻以妻富,于园中筑茅茨自居,不愿以裙带而食,久之,终复合居。一日,陶弟豪饮,醉化为菊,黄英拔置地上,复归人形,马方知陶弟乃菊花精,一日,陶醉卧,又化为菊,马如法拔之,却根株已枯,痛绝而死。九月化为菊花,名曰“醉陶”。
《细侯》故事梗概:昌化满生,设帐余杭,偶遇娼楼贾氏女细侯,终宵冥想,往投以刺,相见言笑甚欢,相与私订终身,即叮咛,坚相约,然满生贫困,往湖南寻友相助赎金,因故被逮囹圄,三年未归。细侯自别满生,杜门不纳一客,有富贾慕细侯名,求见不得,细侯曰:“满生虽贫,其骨清也,守龌龊商,诚非所愿。”富贾使人诣湖南赂当事吏,使久锢满生,并欺瞒细侯满生已死,细侯不得已,遂嫁贾,年余,生一子。无何满生还,细侯大悲,方知贾之诡谋,乘贾他出,杀抱中子,携所有以归满。
摘要:意象批评多用于诗歌,在小说方面则相对薄弱,事实上意象的使用亦是古代小说中常见的叙事手段,文章尝试以明清小说中的花园意象为例,解读该意象的审美意蕴,分析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在明清的小说创作中所形成的叙事模式及其独具的艺术功能,以期对该意象在明清小说中的使用情况有一较为全面的把握,并由此略窥意象的使用对于小说的重要意义。
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复合体,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既是有意义的表象,又是有表象的意义,是对作品有着整体性意义的美学范畴。①在明清小说中,花园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场所,涉及到情爱的作品往往伴随有花园的出现,在这些作品里,花园或作为叙事的背景,或作为抒情的触媒,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方”,而几乎是一个结构性的意象,以至于一提到花园,常会令人联想到才子佳人、密约偷期、私订终身等情节,花园与情爱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一种意象的形成必然要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生成,“它往往连同既往主体对特定物象,情景表现的‘有意味的形式’,神韵风味,一并扎根,且在一次次重新体验及欣赏创作时增加”②。花园意象亦是一个在传统文化的演进中得以不断充实并不断更新的审美范畴,这种历史继承的结果使得花园意象的文化蕴涵日趋丰厚,从而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作为一个整体意象,常出现在园中的有花草、山石、流水、亭台楼阁、短墙园门等,这些都是花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花园所拥有的各种象征意义,均离不开这些根植于各自的文化土壤中的具体意象,它们以其自身蕴涵深厚的文化能量,共同建构了美丽的花园意象。
花园虽然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地方,但又与残缺混乱的现实不同,它力图摹仿自由的大自然,让园中景物保持着自然的形态,它把自然景物中能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完美的理想之地。而“花园之所以能成其为花园意象,就在于它与实际生活的分离,其实质就是要创造出一个可以卸载或逃避沉重的尘世生存的飞地”③。因此花园意象的审美意蕴在园中各种景物的交互作用下,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花园内外的对比中得到呈现。尽管自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出来之后,商讨质疑的呼声从未消歇,但大观园的理想性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它未必如余先生所言那般,是“清、情、真”的乌托邦世界,但与园外的庸俗丑陋相比,已堪称是理想世界了。作为贾宝玉和众女儿的理想栖息之地,这里成了他们展现至情至性的理想天地,只有在这里,宝玉和众女儿们才得以自由呼吸,个性才得以彰显,她们通过结社吟诗、赏花填词展现她们的才气性情,追求真实的生命感受。相比之下,园外的世界则充满了肮脏与堕落:男子或求仙访道、或僵化腐朽、或恣酒纵欲以至通奸乱伦、无恶不作;女子则忙于家族事务,工于筹划算计。第四十九回湘云曾告诫宝琴:“你除在老太太屋里,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这种告诫确实让人触目惊心,但它足以说明大观园内外两个世界的对立与冲突,《红楼梦》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既写出了大观园的理想性,也写出了它的现实制约性以及它的毁灭,这才使这部作品在理想和现实的两个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④。
相比之下,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花园尽管也充满了诗情画意,园中之情也可谓风雅缠绵、浪漫多姿,然而正是由于对浪漫诗意的过度追求,描绘的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理想蓝图,完全忽略了花园的内外之别,使得本来蕴涵深厚的花园意象在其中也只沦为了一个功能性的符号,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量失败的记录。至于《金瓶梅》中的西门花园,因其强烈的讽刺意味而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但人们从张竹坡对月娘未能履行正室职责过问园中事务的指责中,多少也能得到这样的印象:花园是正常的社会伦理约束力鞭长莫及的地方。
在花园意象的生成过程中,戏曲花园的作用显然是无可代替的。元明戏曲中,作家常设置花园作为背景,以园中美景引发女子的伤春情感,使之不由得悲叹自身的青春易逝红颜易老,渴望早日遇到如意郎君,于是便有英俊书生出现在花园中,或有多情才子倾诉爱慕之情,接着便是花下结盟、私订终身等情节,花园在这些作品中,往往象征着青春、自由和爱情,是“与人现实中审美意识,人们感物而发、物我相生的艺术思维及与较直接的生活感受相关的意象”⑤。它对青春少女的启悟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西厢记》、《牡丹亭》均堪称此类作品的代表。在传统戏曲小说里出现的花园,大都是作为男女相爱相恋的背景,其中出现的景物像游鱼戏水、鸳鸯、并蒂莲等,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园中的这些具体事物往往能以其独具的文化意蕴激活人们的联想,成为男女相悦的独特言说体系,因此园中景物常以意象的方式暗示着人的情感欲望:“园中盛开的花朵象征着女性柔弱的美,奇异的山石则隐喻着男性阳刚的力量,而那小桥流水的雅致、清风拂面的甜美、月色溶溶的静谧,以及特殊情境下暗香浮动的神秘气息……后花园的气质是复调式的层层叠叠的完美,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爱与欲的场所。”⑥因此在戏曲和小说里面,随着这一意象的反复出现,花园实际上已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成为人的原始欲望生发的隐喻式场景。《牡丹亭》、《西厢记》、《娇红记》、《刘生觅莲记》、《飞花咏》、《快心编》、《定情人》等诸多作品里面描绘的情人盟誓相爱都发生在花园,不仅是因为地点的相宜,还在于花园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赋予问题上的话语有着密切的联系。二
花园意象的运用,在元明文言传奇和明末清初兴起的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往往是才子因某种机缘得以在花园中结识佳人,之后历经磨难,终得结成伉俪,所谓“私订终身后花园,多情才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已成为此类小说情节的一般模式,花园常是这三部曲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钟情丽集》、《平山冷燕》、《玉娇梨》、《两交婚》、《锦香亭》等。
《钟情丽集》叙述琼州才子辜辂奉父母之命谒见祖姑,被安置在西庑清桂轩下。见姑之女黎瑜娘“颜色绝世,光彩动人”,不禁怦然心动,写诗赋词向她表白心迹,瑜娘有词和曰:
娇痴倦极,御柳因花柔,东风无力。桃记得此去,早筑盟坛,共定风流策。也不难愁,更休须梦,务要亲身经历。欲使情如胶漆,先使心同金石。相期也,在西厢待月,蓝田种璧。⑦
抒发了面对满园芬芳桃李而恨青春易逝的伤感,流露出对辜生的一片深情,从中不难看出《西厢记》、《娇红记》等花园私订终身故事对她的影响。但瑜娘的爱情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并将她另许他人,瑜娘以死抗争,终于得偿宿愿。小说刻画了封建礼教禁锢下青年男女大胆追求爱情的复杂心理和艰难过程,写得可谓风雅缠绵,婉丽多姿。
明代中篇传奇的才子佳人大多以貌互相吸引,对才情尚不太重视,至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则极力张扬才情观,才子佳人们多是才、情、貌兼备,才子为得到才情相匹的佳偶,或托身为仆进入女家花园以寻求机会,或男扮女装以接近对方,或直接进入花园与佳人赛诗唱和。作为佳人才子“巧遇”或“私订终身”的场所,花园景色多充满诗情画意,服务于主人公的才学性情及爱情氛围,如《平山冷燕》写燕白颔和山黛、平如衡和冷绛雪两对才子佳人思慕爱恋的故事。才貌双全的小才女冷绛雪所居住的浣花园风景清幽,位置全无俗韵:
山铺青影,水涨绿波。密柳垂黄鹂之阴,杂花分秀户之色。曲径逶迤,三三不已;穿廊曲折,九九还多。高阁留云,瞒过白云重坐月;疏帘卷燕,放归紫燕忽闻莺。青松石上,棋敌而琴清;红雨花前,茶香而酒美。小圃行游,虽不敌辋川名胜;一丘自足,亦何殊金谷风流。⑧
而山黛所居之梅园,在燕白颔眼中则是另一番规模宏丽、制度深沉的景象:
上下尽秦砖碧瓦,周围都是红墙。雕甍画栋吐龙光,凤阁斜张朱网。娇鸟枝头百啭,名花栏内群芳。风流富贵不寻常,却有侯王气象。⑨
所绘景致不仅与山黛的才学性情相得益彰,亦与她的宰相千金的身份地位极相符合,为山燕二人的初相遇设置了美丽的场所。
然而,众所周知,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因其较为固定的程式化的叙事模式而遭到了世人的批评,虽然花园意象在早期纯正的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平山冷燕》中尚有较为成功的运用,但伴随着这类小说叙事模式的逐渐稳固定型,花园在其中也日益沦为一个符号性的场所,仅成为作者们习惯应用的一种道具而已,花园意象本身所具有的丰富蕴涵也随之被逐渐消解,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量失败的记录,如《锦香亭》、《宛如约》、《生花梦》、《飞花梦》、《锦疑团》等。此类作品中的花园明显具有类型化特征,它们更多的是充当一种道具,一种符号,仅成为为主人公提供一个活动的地点而已,尽管不少作品也对花园布局进行详细的描述,但描述本身并无多大意义。
明代中篇文言传奇中不少作品渲染情欲的成分明显增多,如《寻芳雅集》、《天缘奇遇》、《花神三妙传》、《怀春雅集》等,这些作品的花园里,“情”的成分减少而“欲”的成分增多,花园往往成为肉欲和欢乐的屏障,这与后来《金瓶梅》中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李瓶儿在花园中寻欢取乐的情节应是一脉相承的。
《金瓶梅》里西门庆家的花园是一个充斥着肮脏淫欲的污浊场所,生活在里面的人争风吃醋、纵欲淫荡、通奸乱伦,根本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和人心善良可言。小说中大量的篇幅均是用来描写花园中的生活琐事的,园中充满了妻妾之间的争风吃醋与勾心斗角,飘荡着乱伦通奸的污浊气息,如潘金莲为了报复李瓶儿从自己身边夺走西门庆,专门喂养训练了一只凶狠的猫将李瓶儿刚满周岁的儿子惊吓致死;又如西门庆与仆人来旺的媳妇宋惠莲通奸、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乱伦等,花园里的这些罪恶行径决定了他们毁灭的必然性,而人的毁灭也注定了花园不可避免的败落。西门庆死后,第九十六回作者通过庞春梅最后一次来到园中,看到往日喧嚣繁华的西门花园已是今非昔比,只见:
垣墙欹损,台榭歪斜。两边画壁长青苔,满地花砖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毁不显嵯峨;亭内凉床,被渗漏已无框档。石洞中蛛丝结网,鱼池内虾蟆成群。狐狸常睡卧云亭,黄鼠往来藏春阁。料想经年人不到,也知尽日有云来。⑩
昔日的繁华盛景已烟消云散,园中花草荒芜,亭台楼阁成为野兽出没之地,一派凄凉惨景,花园的这番衰败景象恰与建成时的热闹繁华形成了鲜明对比。花园意象显然是作者有意设置的,花园连同它的主人们一并消逝,李瓶儿死于血亏,潘金莲被吴月娘卖掉,花园最终成为西门庆、李瓶儿等人的葬身之地。淫欲无度而缺少人心善良,最终只会将人埋葬,这应是西门花园留给人们的警示,这里的花园意象显然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大观园作为《红楼梦》环境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初是为元妃省亲而建,但作者的真正目的却是为展示美好青春、共演红楼悲剧而设的。大观园不仅是宝黛爱情滋生、发展的场所,同时也是真挚爱情、美好世界的象征,然而随着大观园的毁灭,他们的爱情也最终虚化成为镜花水月,“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只不过是缥缈虚无的太虚幻境罢了,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它的立足之地。大观园竣工后,脂砚斋曾有点评道:《红楼梦》“深得金瓶壸奥”{11}。这似乎在暗示人们:应把这两部小说对比来看。《金瓶梅》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家庭为中心、反映世态人情的长篇小说,其刻画人物在家庭中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西门庆家的花园中,使花园具有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红楼梦》学习借鉴了《金瓶梅》以花园组织结构全书的框架,把人物集中在花园里加以刻画展示的技巧,使花园具有明显的寓意。第十七回作者清楚地告诉我们:大观园是建立在秦氏的会芳园和贾赦的一座旧花园的废墟之上的,因此,从一开始这座花园就被淫欲所污染,使人把大观园同乱伦和死亡联系起来。作者通过对大观园基础的描写所暗示的这一点,比任何批评家指出的都简明扼要,这不免使人想起《金瓶梅》中西门庆合并李瓶儿的园子重修扩建花园的情节。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沿用了明清园林建造的特点,用园林、房屋结构比喻文学作品的构架,寓深意于其中。而且类似于《金瓶梅》中“春梅游玩旧家池馆”的构想在《红楼梦》中也应存在,虽然现在已看不到曹雪芹笔下的萧条景象,但从脂批中,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昔日“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潇湘馆后来变成了“落叶萧萧、寒烟漠漠”的一派凄凉惨景,“系玉兄与十二钗太虚玄境”的大观园也最终归结于缥缈的太虚幻境。
曹雪芹虽然在《红楼梦》开篇即批评才子佳人小说“千部共出一套”,之后又借贾母之口作了进一步的批判。曹雪芹的批评是尖锐的,但应该说他所针对的是这类小说风行一时后所形成的人物、情节大同小异的公式化倾向。事实上,才子佳人小说张扬女子才情的传统对《红楼梦》的影响是不应否认的,所不同的是《红楼梦》虽也运用在花园中展开男女爱情的创作模式,但能力纠其弊,一改之前“一见倾心”的爱情方式,极力摹写宝黛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才子佳人小说在花园中描绘的是风雅浪漫的爱情喜剧,而在大观园中上演的却是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
此外,《红楼梦》所谈的“情”,则明显受益于《西厢记》、《牡丹亭》等戏曲。这在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有着细致的描绘。花园的中心意象虽然仍与男女情爱息息相关,但这得之于大自然的启悟并非如戏剧花园的启悟人性那样完成于瞬间,作者将男女主人公对自我生命的警悟、彼此爱情的滋长放置在生活化的自然时间里任其缓慢演进,大观园的四季美景则以它们各自的情韵默默应和着人物的情感气韵,在季节的变换与时间的推移中变幻爱的节奏与色彩。这样,“既突破了戏曲舞台上花园时空的拘囿,又极大地拓展了才子佳人小说花园意象的蕴涵,在意象沿用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从而蔚为古典文学花园意象之大观”{12}。
三
花园作为小说中常出现的场所,往往成为作品空间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金瓶梅》中西门庆营造花园,实际上可看作是创造故事的“戏台”,第十六回中西门庆对李瓶儿说:“我那边房子盖了才好。不然,要你过去,没有住房。”由此可知他营造花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安置妻妾。花园的建立为描写西门家庭的奢华淫逸,妻妾争宠,享乐污浊的现实提供了场所,并逐步对其豪华外表下内部的庸俗无聊进行披露。至于大观园的营造,应可看作是对这种手法的模仿,营造大观园的目的本为迎接元妃省亲,至于后来给宝玉和女儿们居住,大可看作是一种叙事策略的动用,大观园为红楼人物悲欢离合的上演建构了叙事的空间实体框架,每一处亭台轩榭、厢房楼廊的空间转换,都伴随着人物的脚步,推动着情节的演进。
花园环境作为叙事的空间背景,常为作品意境的营造提供特别的审美效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曾论及戏曲意境:“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是也。”{13}事实上,不论在戏曲还是小说中,以上三者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优秀的作品尤其如此。那些体现着作者整体构思和艺术审美的景物描写,常能给作品增添诗情画意,而单纯的或与主题无关的景物描写无论怎样美妙如画,也难以成为意境。如果讲融情入景,通过人物的感受和抒发使人物形象与环境互相映衬,浑然一体,从而构成如诗如画的浓郁诗境,《红楼梦》在这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堪称典范,脍炙人口的篇章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龄官画蔷”等不胜枚举,作者借用对大观园中各处优美景致的描写,创设出了一个个优美的红楼意境,这些虽是生活中的画面,却也是诗的意境,王国维关于戏曲意境的三个标准于此亦是最好的注脚。
环境描写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有着直接的作用,花园作为人物居住的环境或活动的场所,往往可看作人物性格的象征或延伸。如《花月痕》中,名士韩荷生的寄园“因山而构……园中亭台层叠,花木扶疏,池水萦回,山峦缭绕”{14},是一座景致绝佳的名园,与主人的高雅风度相契合,恰如主人公韦痴珠所言“这园落在你两人手里,才是园不负人,人也不负园哩!”{15}与此相反,《金瓶梅》中的花园不仅是西门庆社会地位的标记,在这个花团锦簇的园林里,分明透出一种以文人学士自命的得意劲儿,特别显眼的是西门庆那间摆设华丽而庸俗的花园书房,那是他依仗金钱而跻身于上流社会的见证,在书中对花园的大段描绘中,张竹坡曾有夹批曰:“写西门市井入骨。”{16}这座看似应有尽有却毫无章法的花园正适合没有文化、眼光低俗的西门庆居住,明眼人从宅院和花园的暴发式的浮华中不难看出这种权势的脆弱性,正如其中透露出的人物性格的丑陋不堪。至于如何融汇多姿多彩的园林景物以刻画纷繁复杂的人物性格,使人物与环境在相互映照中显示其丰满的形象和鲜明的个性,《红楼梦》在这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亦是无人能及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花园意象在明清小说中的使用情况,基本把握了五彩缤纷的花园背后所蕴涵的特殊审美价值,同时也从中窥探到了意象的使用对于小说的重要意义,它与作品中的其他要素交融互渗,共同构筑了叙事文本,成为小说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花园意象则以其独特的韵致与美丽得以反复出现并不断被拓展出新的蕴涵,从而成为小说中具体可观的叙事手段。
①参见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3;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75.
②⑤王立.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9.
③咸立强.中西文学作品中花园意象的审美意蕴比较[J].中华文化论坛,2006,(2):152.
④詹丹.红楼梦的物质与非物质[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03.
⑥周宁.花园:戏曲想像的异托邦[J].戏剧文学.2004,(3):25.
⑦[明]吴敬所.国色天香[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392.
⑧⑨李致中校点.平山冷燕[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59.148.
⑩[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香港:香港太平书局,1993,2849.
{11}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M].济南:齐鲁书社,1986,189.
{12}俞晓红.《红楼梦》花园意象解读[J].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323.
{13}王国维撰,马美信疏证.宋元戏曲史疏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77.
{14}{15}[清]魏仁秀.花月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80.182.
{16}王汝梅,李昭恂等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91,282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
文档上传者
- 明清之际几何原本内容
- 浅议明清文学演变
-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加强
- 明清小说花园意象
- 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纲
- 明清易代的思想史探讨
- 明清满汉女子发型形制演变
- 明清君主专制历史教案
- 明清以来广东生态农业类型
- 明清少数民族经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