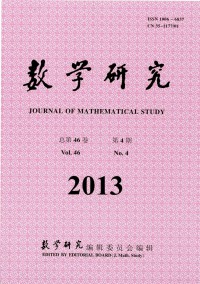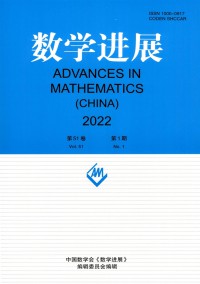数学精神教学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数学精神教学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篇这样的文章了。一方面,就我自己观察来看,很多非数
学专业的朋友甚至包括一些数学系的本科生对究竟什么是数学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
。这种流行的理解就是,数学是一种为其他科学服务的工具或者说语言。数学的任
务就是把已经列成式子的现实问题算出一个用数字表示的结果而已。我经常在我们
系的StudyingHall被一些外系的学生搞得哭笑不得,在他/她的眼里,我们就是一
群比别人算得快的奇怪动物。然而在我看来,数学无疑是具有自己独立精神的一门
科学,或者说是艺术。但是这一点往往只是在数学的教科书中被泛泛而谈,并不真
正让人信服。另外一个动力就是我想人的思想可以说九成九被他所占有的知识所决
定,读不同的专业的人很可能会有对世界的不同看法。这篇文章肯定是戴着我自己
的眼镜写的,正好衮衮诸公分析一下我的思想的缘起,俾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英国大数学家G.Hardy曾经说过[1],对于一个数学家来说,不去证明任何定
理而只是泛泛而谈数学实在是令人感到悲哀,因为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一个因为年
老(对于数学家来说,四十岁就已经是老人了)而不再具有年轻时的创造性的人身
上。一个拥有创造力并正在改写当代数学的年青人不会屑于去向外行“谈数学”。
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学生,在数学上和Hardy比只不过是个三岁毛头。按照中国古代
的说法小孩是不必忌讳的,所以就不必为泛泛而谈数学而感到任何不适。再说这个
世界上有许多的“外行”拥有比我更好的数学功底,还有更多的人其实比我更加具
有学数学的天份,我实在不敢有“不屑一顾”的傲气。
(一)数学对历史的两次推动
这篇文章到底要怎么下笔,我想了很久,最后还是认为该从历史谈起。西方有
一句形容古板学究的话,叫做言必称希腊。好吧就让我们从头谈起吧,从这个科学
皇后在希腊当黄毛丫头的场景开始吧。
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自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就有了世界上第一所大学,第一座图
书馆。欧洲的战乱并没有怎么波及到这里,所以这里也成了当时西方世界第一流学
者的天堂。就是在罗马征服埃及以后,学术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当时的罗马皇帝
在各行省征苛税,但对其它方面并没有干涉的兴趣。在科学和文学?,征服者是
崇拜希腊人的。罗马士兵在战乱中杀死了阿基米德,当时的统帅Marcellus垂胸顿
足,后悔莫及。后Henllenistic时期学术气氛仍算是宽松,Apollonius系统地研究
了圆锥曲线,托勒密等人对三角学推动很大,而丢番图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纯数学
中的难题。
主历三二五年,罗马康斯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为国教。那时希腊的最后一块属
地埃及也已经陷落三百五十五年了。从这以后曾经备受压迫的基督教(天主教)开
始成为压迫异端的急先锋。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在北方各蛮族的不断打击下
毁灭。但是就象入侵并占领了汉族中国的满族人最终被同化一样,强大的基督教战胜
了罗马兵团所没有战胜的敌人----古罗马帝国垮掉了,他们的宗教思想却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胜利,基督的威势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建立起来。公元五二九年,在狂热
的天主教信徒不断的压力下,雅典学院因转播异端思想被关闭。在此之前亚历山大
大学和图书馆已经焚毁,整个古希腊数学时期就此结束了。
从此中世纪的阴影就一直在分笼罩了一千年左右。要等到一五一七年马丁路
德在维滕贝格发表反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正式向教皇挑战并成为新教创始人
后欧洲的宗教垄断才被打破。在路德改宗前欧洲还发生了一些影响世界的大事情。
一四九二年一个叫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的意大利人发现了一个他称之为印度的庞大
新世界,以后各国特别是英伦三岛受宗教迫害的人们就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地,在这
之前在繁荣的意大利已经开始了文艺复兴,各种各样的新思潮和新技术伴随着新的
资本都在蠢蠢欲动。
这时候还有一些不是那么为正史所看中的人物在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只有靠人
类抽象的思辩才能够达到的世界里努力地耕耘着。他们是伽利略,开普勒,哥白尼
,帕斯卡,笛卡尔,莱布尼兹,牛顿.....特别是牛顿和莱布尼兹所发现的微机分
,整个地改写了科学史。通过数学工具的极大改进,一系列原本用初等方法无从下
手的问题迎刃而解。一个对社会的影响当然是提高了当时的生产力的需求,从而孕
育出最终埋葬神权和君权的资产阶级,另外一个更加直接的影响却是从天文学上来
的。这个天文学在中世纪经院哲学里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为按照基督教教义,天
体是天使和圣灵运行的轨迹,是完美的。天是圆的,地球在这个圆的最中心。当这
些观念被科学一个个地打破以后,教皇的权威,甚至说圣经本身的权威,才真正受
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对于牛顿到底有多重要,下面这收诗大概可以反映一下吧:
“NatureandNature''''''''slawslayhidinnight;
Godsaid,''''''''letNewtonbe,''''''''andallwaslight."[1]
信仰这个东西是非常奇怪的。和狂热的信徒谈天你会发现你几乎无法用另一套
信仰来改变他。这不仅仅是几百上千年以前中世纪的事,也不是只有西方民族或者
有宗教的地方才有。今天的朝鲜和昨天的民柬在信仰狂热的程度上绝不亚于费迪南
德和伊沙贝拉治下的西班牙。毕竟在那里宗滩门兴三个半世纪才烧死了三万两千
人,加上其他刑罚处死和间接死亡的,不过百万之数吧,而他们在亚洲的同仁们却
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达到了这个目标。其实就在几十年前我们的国家在思想领域又
何尝不是如此?七八年邓小平说出了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过多
久全国人民突然就发现了过去的荒谬----怎么会是那样呢?怎么会那么笨呢?在这
里皇帝的新衣一旦被揭下,谎言就变得一钱不值。今天的西方世界在回想起中世纪
的一幕幕场景时恐怕也和我们一样会觉得荒谬大于恐惧吧,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会为
对圣经上某一句话的不同解释如此愤怒,以至于非要把同样是信奉上帝的兄弟姐妹
送上火刑架呢?甚至在英国有很长一段时间里竟然要在全国找最美丽的女人来烧死
,只因为当时那里的神学家确信这些美人是撒旦的化身!
路德和加尔文站起来挑战罗马教皇的权威了,但丁更早些在《神曲》里把教皇
判入了地狱,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单凭文学和神学的革命并不能够改变上帝独一
无二的地位,人本主义并没有因为《神曲》而成为主流。甚至新教首领加尔文在教
皇鞭长莫及的日内瓦还烧死了塞尔维特,而且足足把他烤了两个小时。历史的车轮
似乎又在向着循环往复的轨道上滑去。靠神学本身的辩论只能够产生新的神学;靠
文学的启蒙可以产生怀疑,却无法最后战胜神学;靠地理上的发现可以解决一时的
压迫,但是一个清教徒的天堂依然让人们嗅到了旧世界信仰之争的味道;靠美学
----达·芬奇的名作并没有改变天主教堂的图案,再说这世上还有比那些送上火刑
架的“撒旦”更美的作品么?
只有真实和时间,才是战胜精神强权的终极力量。西方有一句话,说是(强权
)可以短时间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是它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象317是个素数这样的真实,就是再坚强的神学信仰也只有在这个事实面前底头。
而物质生活的真实呢,一旦产业革命的机器开动起来,田园诗
似的贵族们又如何抵
挡呢?打败旧制度的归根到底是靠以微机分为代表的理性击败了神学和以机器为代
表的新生产力战胜了贵族势力。如果没有这些,一切革命都将重复类似于中国农民
革命的老路。
牛顿和他之后一个世纪的科学家们生活在一个背靠绝对真理挑战世俗神权和政
权的伟大时代。在马斯顿荒原,英国革命军战胜了保王党的反动势力;在美洲,八
年艰苦的奋战打跑了日不落帝国的总督;在巴黎,第三等级废除了欧洲最顽固的君
主制。在那个时期的主流科学家头脑里,一个来源与物质世界,却又比它更加完美
的理性取代了华丽的拉丁文圣经。人作为上帝的影子的日子过去了,任何权势在真
理面前必须是平等的。微机分之后的科学文明中心在法国。那时全欧的人文主义旗
帜在以狄德罗和达郎贝尔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手里。达郎贝尔对发展方程,
函数论和代数都有重大贡献,他有一句名言:“代数是慷慨的,你从她那里得的总
是比你想要的多”,另外他还说过,“几何上的真理是物理真理的渐进形式,就是
说后者无穷地逼近前者但却永不相交”[2],这大概更加接近现代科学家们的想法
吧。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却又是无可抗拒地从中世纪走到了十九世纪末。科学学飞
速地发展着,正如当时的资本主义一样。神权和君权一点一点地退出了舞台,科学
和经济的力量似乎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上帝死了”,人作为主体出现在那个
喧嚣的世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的时代”[3]。世界似乎是永
无休止地被开采着,人几乎可以凭机器做到一切想做的事。在自然科学上,一个与
这种自大相对应的是在那时,主流物理学家们认为这个世界的规律已经被发现完毕
了。一九零零年,英国的开尔文勋爵在皇家学会的新年致辞中自负地宣称,物理学
的大厦已经完成,今后物理学家的任务只是把实验做得更精确些(当然那时他并没
有料到,他眼中小小的“两朵乌云”——黑体辐射的理论解释和迈克尔逊——莫雷
实验对以太观念的冲击——引起了现代物理学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的,社会的
终极真理似乎就在人们手边。随后文明世界却遭到了空前的打击,那就是两次世界
大战。在那些年现实中的文明世界秩序已经在意大利,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
国主义的冲击下荡然无存了。
两次次世界大战,全人类为此付出了近亿生命的代价。科学的标志既不是体现
在治病救人的青霉素上,也不是体现在纯粹数学和理论物理的完美结合广义相对论
上,而是体现在可以一次毁灭一个城市的原子弹上。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让位于民
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二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敌对,势不两立。社会主义阵营的
故事我就不说了,美国的麦卡锡先生对美国共产党(毋宁说是同情共产党的左派知
识分子)的迫害也足以名垂青史。与中世纪不同的是,现在没有一个极权愚蠢到敢
于宣称科学在自己之下了,相反地这个权力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合法性,往往宣
称自己是“科学”的。就算它还要迫害知识分子,也是用别的方法来进行。这种迫
害进行的方法说来也很简单,那就是先宣称自己是科学和正确的化身,然后让每一
个公民都相信,不“科学”不“正确”的人或者思想就必须予以消灭。最后给异端
贴标签的工作就比较容易了,各个不同的国家自有不同的方法和习惯。
好吧再让我们回到数学吧,回到这个比现实世界优美的避难所吧。让我们从本
世纪的最初看看数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数学学上出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在正史
中当然没有推倒柏林墙那么重要,但是其内在的意义,也许将比那个政治事件更能
让我们的后代共鸣。
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于一九零零年在巴黎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上作了一次演讲
[4]。在演讲中希尔伯特提出了二十三个公开问题,这些问题后来主宰了二十世纪
(至少是前五十年)的数学研究,几乎所有的第一流数学家都在为攻克这些难题而
奋斗。在这次著名的演讲中,他还说到:“.....每一个确定的数学问题,.....无
论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多么难以解决,无论在这些问题面前我们显得多么无能为力
,我们仍然坚定地相信,它们的解答一定能够通过有限步纯逻辑推理而得到。”这
一说法后来被称之为希尔伯特纲领,是人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看馑辩领域的缩
减版本。这二十三个问题如今大部分已经被解决或者部分解决,剩下未被解决的问
题是如下几个:
第二问题:算数公里体系的相容性;
第六问题:物理公理的数学处理;
第八问题:素数问题;
第十二问题:Abel域上的Kronecker定理的推广。
这里面后两个基本上是独立的技巧性问题,而前两个却事关整个数学物理的基础,
进而对整个人类科学和逻辑产生影响。我不是搞物理的,就物理公理的数学化不好
作深入的评论,但是这无疑是希尔伯特或者说任何一个相信希尔伯特纲领的科学家
的一个“野心”吧,先在数学领域建立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信心,然后再把物理
数学化,进而推广到一切人类的科学领域。就象运用数学归纳法时我们要证明两件
事:“对最基本的出发点成立;假设对n成立,证对n+1也成立”相仿,第六问题更
象是后一步,而第二问题则更象是前一步(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前一步走不通
,后一步也就失去了意义。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我想我不得不讲点专业化的东西了。大家都知道所有的
自然数{1,2,.....}是个无穷集合,而且肯定也知道全体实数,通常记作R的也是
个无穷集合。直观告诉我们,虽然都是无穷集合,后者比前者应该要“大”[5]。
数学怪才康托(Cantor)第一次给出了一个严格的证明,这个证明我想在实变函数
的第一章就可以找得到。康托还证明了一个和一般人直观很不一致的结论,那就是
一个正方形或者正方体的点数和一条小得可怜的一维线段的点数是“一样多”的。
这样一来一个自然的问题就出来了:有没有一种无穷大,它比自然数(数学上称之
为可数集)的无穷大要大,却又比实数(数学上称之为连续统)的无穷大要小?这
就是有名的希尔伯特第一问题,连续统假设了。
一九六三年美国的PaulJ.Cohen以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
题:连续统假设和实数公理体系(Zermelo-Fraenkel公里系统)是相互独立的,也
就是说,我们既不可以用实数公理来证明它,也不可能证伪!希尔伯特幸运地在这
个消息之前很早就去世了,但是不幸地是,在他逝世前十二年(一九三一年),一
个叫哥德尔[6]的年轻人已经彻底击碎了他的理想:在任何一个数学体系里,一定
存在既不能能够被证明,也不能够被证伪的命题[7]。那一年希尔伯特已年近七旬,
而哥德尔二十五岁。在这里理想国里老派学者的纲领被年轻人彻底给击败了。和我?
们骄傲的宣言正好成对比的是,数学的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无知。
时间似乎又回到了两千年前的古希腊。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无
知。”两千年来我们的智力不断地在发展,我们的科学不断地在完善,我们比起任
何一个时代都更有资格判断对错。我们甚至想要运用逻辑去证明一切事物都可以贴
上“正”“误”的标签。然后达到一个正确的天堂。而这时数学又一次改变了人类
的哲学,当人们盲目地崇拜上帝时她用锋利的矛挑战神性,而当人们把“正确”当
做新的偶像来崇拜时,又是她告诉人们,人类任何对真理的认识总有不足,地上不
仅仅没有神的天国,也没有绝对真理的标准。只有对不同的哪怕是错误的思想的包
容并蓄,只有放下打击“错误”的执着,凭着对异端的宽容,我们才能真正接近真
理。
“所有的动物生而平等,但是有些比别的更平等[1]。”在数学里也一样存在
这个现象。如果只是要合乎逻辑的话几何可以有很多种,代数也一样。就算动用美
学的标准,也很难说我们的数学就比它的这些兄弟们更好一些。那为什么我们今天
见到的数学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我想,原因在于我们总是用现实世界的眼睛去
观察和发现数学。欧氏几何之所以有这样的公理而不是别的,是因为它最符合当时
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观察。这样一来它就比别的几何在数学里具有更高的地位,拥有
更多的关注。
伟大的苏格拉底曾经向普罗塔奇思(Protarchus)问道:“是不是有两种数学,
一种是平民百姓的,一种是哲学家的?.....(平民)在建筑和作买卖时运用的算
法和测量的技术与哲学家们的(欧氏)几何和极为精细的计算比较如何——我的意
思是,它们是一种还是两种?”
普罗塔奇思:“.....我认为是两种”。[2]
这段对话其实反映出数学自降生以来,就被分成从目标上来说截然不同的两部
分: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我认为这种分类并不能严格地从内容上进行,比如说属
于应用数学的微分方程理论就有很多定理十分优美和抽象,当年被证明出来大概也
还是出于认识真理的动力;而以前非欧几何完全是在纯数学的小圈子里面流通的,
后来也在二十世纪成了描述现实宇宙的重要工具。最有意思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在
一九一零年左右,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数学家和一位物理学家在讨论课程表的时候,
物理学家很有把握地声称,他们无疑可以去掉抽象代数,因为它绝不会对物理有用
的[3]。结果是没出几十年,不懂群论就已经无法进行基础物理的研究了。在数学
的发展史上,“纯粹”往往在多年以后找到“应用”,而“应用”也常常成为理论
研究的动力,它们二者与其说成是两个不同的数学分支,不如说成是统一的数学的
两个侧面。就象在希腊神话中,雅典娜不仅有俏丽的面容,也有强大的力量。纯粹
思辩的数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极有力的工具,以至于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科学只有
当它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算作发展成熟了。[4]
然而为什么数学是如此地有用?这本身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哲学问题。就象我
在前面两章里所阐述的,数学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公设在逻辑推理下可以得到的所有
命题的总和。如果把“真理”理解为在现实世界里行得通的某种“法则”,那么正
好和常识相反,数学里不包含任何“真理”。在物理,化学,生物里我们经常可以
看到这样的论断:A具有性质B。验证它的方法是实验C。和这种毫不犹豫地求助于
实验的风格不同的是,在勾股定理的命题描述后面,你绝不会看见验证它的实验是
什么什么,取代这一步骤的是从欧几里得几何的几条公理出发,通过清晰的逻辑把
它证明出来。按照罗素等人的解释,“正三角形的直角边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这个给人以“客观真理”印象的命题是过于简化了,它应该被说成:“从欧氏几何
的公理和实数的策墨罗-富兰克尔公理体系出发,推出勾股定理的逻辑值为真”。
后一种说法其实就和客观实践无关了,如果我们把前提修改一下,后面那个符合实
践的结论很可能就不成立。比方说在非欧几何里,这条定理就行不通。这两个不同
的结论可以很好地共存,而且还不象经典力学和相对论那样是彼此近似的关系。
原
因是单从逻辑的角度上讲,只要它们各自的前提不存在内部矛盾就是平等的。而前
提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我们这个自然世界的性质?数学家们狡猾地笑笑,说:这就
是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们的事情了。
一个现实问题的数学解法之合理性是出自近似性。从应用的角度讲,我们从来
就不需要绝对的精确,恐怕永远也达不到它。根号二是个无理数?那不要紧,反正
我们连有理数长的尺子也造不出来。exp(x)=x没有“解析解”?这也不要紧,要紧
的是我们能够想出一个逼近的方法,有多精确的需要,就能够通过有限步运算达到
多么精确。
回到几何和数学本身,它们是有限步逻辑的产物,哪怕最接近“现实”的数学
也已注定了是这个无限复杂的世界的某种近似。那么真实世界中任何问题都能够被
某种数学所渐进描述么?学过一些比较专业的数学就知道,这个问题等价于“全体
数学空间”在“全体现实问题空间”里稠密,而这一般来说并不是显然的。好在我
们的科学发展暂时还没有碰到这些问题,多么复杂的物理问题最后总是找到相应的
数学工具,而且在很多时候这件事情还富有戏剧性:物理学家们有时发现,他们需
要的工具,很早以前一小群纯粹数学家们就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应用在数学界的影
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它把某种“没有用”的纯粹数学隐含的应用性揭示出来,从而
强烈地暗示,任何抽象的数学研究终归会被派上用场,成为应用数学。这也是非欧
几何创始人之一的罗巴切夫斯基的信心,而且我们还知道,爱因斯坦没有让他失望
。“所有数学都是有用的”这个命题大致是前面“所有现实问题都有数学模型”的
逆命题。很可惜,就和前面那个命题一样,这也是难以证明的。困难来自于无限,
希望却也来自无限。数学的发展与人类对无限的挑战和超越密不可分。
在上一章里,我已经提到所有的数学都是研究涉及无限的模式,哪怕最简单的
自然数也不例外。现在我们更进一步,看看我们是怎么解决由数本身所构成的无限
命题。第一步我想我们应该看看最为简单的无限:自然数所产生的无限(这种无限
有个学名,叫做“可数无穷大”)。在近代数学定义中,这个无限可以通过“给定
一个自然数n,总存在n+1比它大”这一事实来描述。这些语言本身仅仅涉及有限,
因而是我们可以把握的。由此我们还得到数学归纳法,它可以处理含有这种无穷大
的命题,比方说“1+2+……+n=n*(n+1)/2”。步骤是先证明最开始的一个情况是对
的,然后证明第n+1个情况的正确性可以由第n个情况所推出。这就象是在搭梯子,
只要第一下踏中了,而且保证一脚踏实后就可以踏第二脚,那么哪怕这梯子有无限
多级,我们也满可以登上去。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逻辑。事实上它违反了一个“常识”:如果真有
无限级的梯子,就算一个人结结实实地踩中了第一脚,并且保证下一脚永不踏空,
他也没有办法爬完全部梯子。不过好在我们谁也没有真正见到过无限级的梯子,真
正的无穷是不为人所见的。世界是那样的复杂,我们把它叫做无穷;而人却是渺小
的,我们只能感知到有限。无限如果不和有限结合起来,就是对我们毫无用处的无
限。这条想象中的“无限梯”是那样真实,以至于我们已经忘了它其实来自于“非
常长”然而仍然是有限的梯子的经验。我们不必为那条无限梯永远爬不到顶而烦恼
,我们的胜利来自于每一级被征服的有限,和不断延续的过程。过程!是的,无限
不是静止的体验,无限来自不停息的过程。每一个被征服的具体的n+1都是有限,
归纳的过程却意味着我们征服了第一个无限。
谈到过程,就要谈谈时间了。和自然数不同,时间是连续的。换句话说,在万
分之一毫秒中我们还可以插入许多亿分之一毫秒,而且这一分割还可以继续下去,
要多细有多细。在现实生活中,人对“微小”的认识水平是有限制的。所以无限可
分并不是直接的经验,而是和可数无穷大一样,是有限经验的一种抽象。这种无限
可分的性质不光时间有,空间也是有的,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宇宙的框架
。最早对这一框架的数学描述是欧氏几何,通过笛卡尔等人的努力,实数和这一几
何通过坐标系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几何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点”,“直线”等概念,这些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
不存在的。确实,有谁能够见到一个没有任何大小的“点”呢?又有哪一条“直线
”不是弯曲的呢?然而今天对于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讲,这些奇怪的人造动物
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们把力学问题抽象为几何,通过数学来推导,运算,得到
一个数字或者图形,然后再把它的力学意义解释出来。而这个结论总是对的,这可
以从无数实验中看出来。可是这种正确,却是基于在现实生活中谁也没有见到过的
“点”和“线”的看逻辑推理。
解释它的办法仍然是用过程的概念:比方说一个“点”或者说一个实数不是个
固定的概念——无限小的“存在”,而是一个可以不断逼近(缩小)的过程。一颗
质量为3.75公斤的石子在113.14牛顿的推进力下沿直线运行了3.03秒,那么它的轨
迹就有138.50米。这里的任何一个数字都不是对现实实验的真实描述,而是近似。
随着对3.75公斤,113.14牛顿,3.03秒近似水平的提高,轨迹也会越来越接近
138.50米。这个“越来越接近”又是一个涉及无限的过程了,它被有限的逻辑以
F=ma,S=a*t^2/2的形式表达出来。其中第一个式子来源于物理经验,第二个式子
则是微积分的一个结果。
微积分和它所生成的分析学是近代数学最值得铭记的里程碑,它在数学中的重
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可是它竟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数
学——因为它的基础要到很晚以后才被建立在坚实的逻辑之上。天文学家开普勒尝
试着做最早的积分,被叫做“dolichometry”——小桶的量度——即量度由曲面包
围起来的物体的容积。这是非公理化的,经验的几何学,而不是欧几里得以后的那
种几何学[5]。牛顿发明的“流数”运算,不仅是为了研究物理提供工具,连陈述
都是物理化的,而这种不精确性,来源就是把无穷小量当作静止的恒量。在牛顿时
代的微积分运算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用这个无穷小量做分母(这意味着它不等于
零),而在随后的乘法中和它相乘的量又都被消去(这时它就是零了),从而得到
结果。这个矛盾当时无法解决,而且它并不是象虚数那样完全是形式上的问题,那
种推导方法还有可能会得出象0=1这种荒谬的结论。以前曾经是如此严格地合乎道
德的数学也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这为它开辟了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谬误的
道路[6]。
现在我们高等数学/数学分析教科书上已经找不到这个象幽灵一样的无穷小量
了,取而代之的是柯西和魏尔斯特拉斯所发现的极限思想和用来描述它的ε-δ法
则。无穷小量现在被看成某个函数的极限过程,精确的描述如下:对于任意ε>0.
存在δ>0,当|x-x_0|<δ时|f(x)-f(x_0)|<ε,记为当x→x_0时,f(x)→
f(x_0)。
这里ε和δ都代表了有限,“任意”和“存在”是集合论或者说是逻辑运算的
语言,通过它们把代表无限的无穷小量刻画出来。看似笨拙的描述中透露的还是那
个思想:如果不能够从有限出发刻画无限,那样的无限就毫无意义;如果一种计算
不能
写成标准的逻辑语言,它就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数学。数学的力量表现在丰富多
彩的应用上,但更是出自它无比的严密。在历史上应用很多次走在了严密的前面,
就象微积分那样,但最终数学总可以为它们建立严格的逻辑,尽管有时不得不付出
直观性和有效性的代价。后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概率论。古典概率的直观体系很
早就有了雏形,而且被实践证明是管用的。然而要到本世纪柯尔莫哥洛夫(
Kolmogorov)突破性的工作后它才谈得上有一个严格的数学基础。这套体系是建立
在测度论上的,而在现有的体系下一定有很多事件是无法定义概率的(不可测),
所以概率的定义域就从来自经验的“全部可能的事件”缩减为一个纯粹为满足数学
严格性而建筑的δ-algebra之上。这种不自然多多少少削弱了概率论的力量(尽管
几乎所有我们见过的集合都是可测的),因此直到现在还有人反对它,试图建立一
套更加完美的理论。
不管新的体系会是什么样子,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一定是保证了逻辑严密性后
的推广,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充分的信心去运用它。可是逻辑又为什么会适用于我
们这个世界?这是还未得到解决的哲学问题。抽象的逻辑其实一样来自于重复足够
多次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则是视觉,听觉,触觉,嗅觉——通过机器可以把它们延
伸,通过思考可以间接地感受它们,然而归根到底它们还是基于这些感觉。也许
1+1=2不是感觉,可是它也是从一大类我们感知得到的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规律
。这个规律,就我们过去的经验所知是正确的。之所以我们要去(通过研究过去的
经验)追求规律,是为了把握我们难以把握的未来,如果历史对未来毫无影响,如
果宇宙随时间的变化完全不可知,我们还有研究科学的必要吗?我们的信心只能建
立在宇宙的规律性上,这种规律性也许永远不能够为人类所完全认识,但总是在某
个地方“存在”着,全部自然科学包括数学不是创造它,而是发现它。然而即使全
部的过去都支持某一种规律,这种规律就一定会在将来永远地成立下去吗?太阳明
天还会升起,这可以通过物理定律来证明,可是物理定律恰恰是从象太阳无数次有
规律的升起这样的大量经验中得出的,这就象是自己证明自己,并没有产生新的信
息。
到这里我打算停下来,把问题交给搞自然科学的同仁们。归跟到底,那些建立
模型解释模型的任务不在数学家身上。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就象是下围棋,给定了规
则(逻辑)后就演绎出许多推论,在数学上的“正确”意味着合乎这种规则,和现
实生活中的“正确”具有不同(然而非常相关)的哲学意义。由此可见,数学不是
具体科学,更不是“客观真理”的总汇。
[1]《动物庄院》,GeorgeOrwell
[2]《AppliedMathematicsIsBadMathematics》,P.Halmos
[3]《MathematicsinthePhysicalScience》,F.J.Dyson
[4]《马克思回忆录》,拉法格著,转引自《数学与人类文化》,孙小礼著
[5]《论数学》,冯·诺伊曼
[6]《反杜林论》,恩格斯
迦罗华小传
E·迦罗华(EvaristeGalois),法国数学家。一八一一年生于巴黎近郊的
Bourg-la-Reine。他父亲当时是那里的镇长,他母亲是知识妇女,她在家里一直教
小迦罗华到十二岁,到那时他才开始上正规的学校。但是由于不喜欢学校正规教育
的僵化体制和一成不变的教材,迦罗华在学校的成绩很快就从刚进去时的名列前矛
跌到了谷底。有一次他偶然找到了一本勒让德写的几何学专著,这个成绩一塌糊涂
的小家伙很快就全部看
懂了。学校的代数课本对他来说实在太boring,他于是就去
找数学大师拉格朗日和阿贝尔求学。然而在大师们那里他也表现不好,得到的评价
是该生十分古怪,喜欢争辩,老是惹麻烦。
十六岁时他投考闻名全欧的EcolePolytechnique,结果考官根本不能理解他
的答题,因而被拒。后来Terquem是这样评价的:“Acandidateofsuperior
intelligenceislostwithanexaminerofinferiorintelligence”。后他再
次报考该校,又碰到一帮这样的考官,在复试(面试)的时候,他甚至愤而拿粉笔
擦扔中一名考官。这一扔,也就扔掉了他读Polytechnique的希望。不过他虽然这
两年没有读大学,却还是找到了一个能够容忍他的数学老师,LouisRichard,自
此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数学研究。他的第一篇论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十七岁时)发
表的。就在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影响他人生观的事情,他的父亲,因为受到当时
法国天主教会的迫害而自杀了。
十九岁(一八二九年)终于上了另外一所学校EcoleNormale,然而不久(一
八三零年)法国发生革命。当时EcoleNormale的校长把所有的学生都锁在学校里
面,只除可怜的迦罗华以外----他因为怀有民主理想,写了支持暴动骂校长的公开
信而被开除了。在EcoleNormale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迦罗华发表了三篇关于代数
方程的论文,并寄给法国科学院。当时科学院的秘书把它们带回家准备去读,不过
他在写出评价之前就死了,那些论文再也没人找得到。
开除以后二十岁不到的他试图开办他自己的数学学校,结果是没有人肯当他的
学生。然后他就加入了国民卫队,并且说了一句对于我们中国人或多或少熟悉的话
:如果必须用尸体来激励民众,拿我的去好了。具有戏剧性的故事还在后面:他这
个危险分子似乎是不可避免地被抓了起来,罪名是“试图谋害国王”。这本是求仁
得仁,但在法庭上法官不知为什么却又判他无罪。最后他还是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
,罪名是“illegallywearingauniform”!
当他刑满释放后,他这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卷入了爱情纷争。就象他
一惯的不走运,他这一次也没有好多少。性子火暴的他很快就对爱情,他的女友和
他自己完全厌恶了。几天过后情绪低沉的他接受了他的政敌的决斗挑战。他自己知
道他不会有什么机会赢,于是整晚就在写数学手稿,那是他短暂不幸而又闪亮的一
生唯一能够给他安慰,体现他的价值的东西了,也是他不愿随自己的生命带走的。
他把这些新的结果,连同那次被法国科学院弄丢的论文的结果寄给了他的朋友
AugusteChxxxxier,然后在一八三二年五月三十日依约前往决斗场。
在那里他被射中腹部,一时断不了气。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他对他兄弟说:“别
哭,我可是要鼓起全部勇气才能在二十岁去死呢。”痛苦结束于第二天,然后他被
安葬于一个连标记都没有的墓穴里。
二十四年以后,刘维尔整理并发表了迦罗华的一些文章和传记。而真正理解他
的成就,还要等到1870年约当写出Traitedessubstitutions,或者更晚一些,到
二十世纪克莱因(FelixKlein)和李(SophusLie)把他的理论系统地运用到几
何上去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他们曾经拥有过一个怎样的天才。迦罗华只活了二十岁
,写的全部论文只有六十页纸。在他生前他的数学思想不为人所理解,政治主张也
大逆不道。然而在他死后人们称他是现代代数学的开创者,而他的祖国,再也不会
有“谋害国王”这条罪名了。他真正当得起Bell的评论-----
Inallthehistoryofsciencethereisnocompleterexampleofthe
triumphofcrassstupidityoveruntamablegeniusthanisaffordedbythe
alltoobrieflifeofEvaristeGalois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