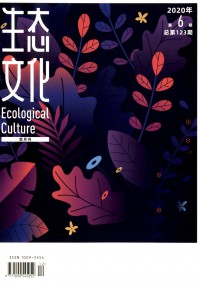文化多元结构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文化多元结构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我的基本策略是:通过总体文明进程,并20世纪中国历史的相关断代,来关涉当代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事实前提,显然,在“社会分工”这一历史机制的驱动下,职业化进程已然形成人文化之惯性。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针对其正面/负面作用进行合式的评估。由此事实,作进一步的具体化,在总体关系上,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发展,基本呈现为:一个中心(中西音乐文化发生关系)/两个基本点(发生两代历史断层/现代专业音乐成型,并形式体裁的多样化取向)。由于这一关系的极度突现,并占有核心位置,与此相平行的古今、雅俗关系,尤其,是其中的古乐与俗乐,似乎就自然隐退到了当代中国主流音乐文化圈之外。而处于其中心位置的,则更多是接受职业教育、经过专业训练之后,所成就了的音乐文化当事人,及其创造结果——即由分工后、专门化、职业性了的知识分子,及其由之统制的艺术音乐。
在人类总体文明进程中,(按不同分类依据)已经经历或者正在成型的各种方式,大约有——
一、世界性一般方式:原始农业,手工业,大工业,商品国际化,信息,大农业(以水土为主的传统绿色植物农业,以微生物资源为主的白色农业,以海洋生物资源为主的蓝色农业,统称“三色农业”)。
二、以资源配置为依据的产业方式: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
三、以主体输出或者投入为依据的生产方式:(古代)体力产业,(近代)资本产业,(现代)知识产业。
四、以人本参与或者拥有为依据的文化方式:(古代)感性范式,(近代)理性方式,(现代)非理性方式,(后现代)超越感理性方式。
五、20世纪中国音乐思想断代(或者仍然有局部笼罩与弥漫的并存地带);西方文化尚未大规模进入本土之前的古代中国音乐思想代/带,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本土之后的近现代中国音乐思想代/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为主宰型意识形态之后的当代中国音乐思想代/带(仅限于大陆地区)。
六、将上述历时关系横架过来进行共时定位的学术范型:(古代)混生形态的叙事品位,(近现代)分离形态的学理样式,(当代,尤其近十年间)综合上述两者形态的复合范型(具有学理推论与人文叙事的双重品式),并处于各种关系(中西,古今,雅俗,内外,是非,阴阳,等等)的“多元边缘”与“众声喧哗”状态当中。
七、未来世界发展的标准化进程:经济一体化,民主政治,自由人权。
八、不同层级的价值指向:乡土价值,民族价值,全球价值(自由,平等,社会公正)。
除以上之外,我想从一个新的视角,提供另一种人文景观(以20世纪中国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为基本依据的界划):(1919)可谓:地域文化碰撞,中西文化发生关系为标示;(1949)可谓:制度文化成型,以共和国成立为标示,并其意识形态的“制度化”意义;(1979)可谓:个性文化复原,以“改革开放”为标示,意识形态的“制度化”意义在相当程度上被消减;(1989)可谓:轴心文化颠覆,以知识分子从社会发言中心退降下来为标示,意识形态“制度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得到强化;(1992)可谓:经济文化铺张,以经济建设的再度启动为标示,一大批原先从事人文意识形态建构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变社会性角色,下海经商一度成为时尚;(1998)可谓:生态文化警钟,以全球性金融危机与中国南北大洪水为标示,生态问题(包括人文和自然两部分)以极其“残酷”的方式直接插入历史进程,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强迫一种“人文记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并将列入人类的跨世纪议程……
依此方式,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人文化的持续发展进程,总是或多或少地要受到非文化因素的干扰甚至堵截。况且,在经济运营的阶段与场合方面,又十分有限;而相应的知识分子文化的发展进程,则又极度地缓慢,甚至疲软,以至于总体人文资源的积累与储备,都显得非常的贫弱与匮乏。
“冷战”结束之后,大约最最令世界喧哗和骚动的一个声音就是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所说的“文明冲突”了。姑且不说这一声音是否得当,或者能否成为国际性话题。但至少,已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人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被视为具有跨世纪意义的一个行动策略。然而,这一预言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我认为,则是“后冷战”的历史态势与世界格局:不同区域文化(依地缘而构建之),不同族类文化(依血缘而构建之),不同形态文化(依物缘而构建之),以及各自之间:分立/相间/互动/制衡。之所以如此断言的别一种依据,则正好与“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形成“对应/对映”的架构形成复合。“当代”是一个问题,它并非仅仅日常语义之单纯时间概念,显然,已被赋予相当的文化涵义,是“历史/当下”的复合,并具有跨世纪的长远意义。对此,请注意一系列历史形态的转换:历史—→当下/由持续不断的深度叙事模式,向琐碎繁杂的平面叙事模式的转换;古典—→今典/由前人(别人)所作所为并可模之本,向“作者当日之事”的转换;正史—→稗史/由朝代更迭与皇家国事,向逸文俗事与凡间俚习的转换;书面文本—→口头文本/由知识阶层创制,向平民阶层诠释的转换;思想史—→学术史/由改变世界,向解释世界的转移;……。由此,通过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合理引申,“知识分子是第一生产力”命题不乏具有合理的存在意义,其前瞻性在于:不仅有足够的可持续发展的人文资源后助力,并可充分关注人文化的全面发展。
通观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状况,尤其在中西关系含量骤然增加的情况下,首先,可有以下三种定位:话语系统无序(失语/不可识别母语,无从选择,拆解本位文化),意识形态非位(无语/被动认识,无奈接轨,拼贴剪接,拆解主体文化),叙事结构失范(空语/什么都行,不用对策,拆解自在文化)。由此,则直接导致不同文化的并存和多种音乐样式的共在: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经典音乐,民间音乐,流行音乐,实验音乐,宗教音乐。其次,之所以如此看重中西关系在其中的分量,至少有两个潜在的极端姿态:一是过于推崇西方,一是过于排斥西方。但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尤其在“大洪水”面前,东西方生存策略,其实已然处在同一个起点和平面上。为此,对中西两个天然不同文化者的关系,不妨作如是调整,也可说是一种理想方式(只需动四个字):变本原对立为本原分立,变异质相融为异质相间,变耦合互补为耦合互动,变权力制约为权力制衡。于是,在并存共在的前提下,通过各自地道的作业,以确立自身价值。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吃不掉谁。
就此,在充分尊重“文化多元”的前提下,对“全面的现代化/充分的世界性”的命题而言,则“严格的传统化/极端的本位性”是否同样不失为一种选择?对“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而言,则文化保守主义(重建终极关怀和护存文化认同)是否也可有相应的历史承诺与文化担当?对“向西方乞灵”命题的人本主义呼唤而言,在充分守护其人文符号意义(西方文化的人本主义内涵)的同时,是否也可对其历史标示尺度(西方文化的科技进步标尺)提出怀疑?于是,关键在于:道路能否多元?方式是否多样?进而,“民族”与“世界”能否等同,以及“传统”与“现代”能否接续?
至此,似乎有必要将属意识形态的“是非”悬置起来,而采取“不争论”姿态,以直接面对文化,进而音乐本身。把对“音乐发展道路”的诘问,自觉转移成对“人究竟需求什么样的音乐”的追问。因为,在“文化多元”的前提下,人的需求必然是多种多样的。那么,什么是自觉的文化选择?协调,得体,妥贴,合式,进而,合情合理。
诚然,文化选择的现实处境并不单纯。以与艺术(音乐)最为接近的意识形态来说,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裂变,并有明显的分岔,比如:作为官方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形态”,作为大众或者边缘意识形态的“意象形态”,作为知识分子或者深层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态”。很显然,处在如此的意识形态新型整合格局当中,选择的空间就十分有限,为此,在提出“资源共享”的前提下,再提出“知识安全”的问题(包括:坚固知识产权的归属,遏制知识垄断的蔓延,防范知识霸权的威胁,加速知识结构的更新,推进知识整合的完形),乃是一个恰当的防范策略。如果说,人类停止进化的一个前提,是过于封闭自己,并过度安全保险,那么,“知识安全”必然关涉“知识间性”及其互向关系。对传统和国际的过度依赖,则个人知识极不安全。于是,最后的整合意义何在:传统,价值,文明,文化?无理僭越或者无法僭妄,其结果,都只能是肢解主体。于是,在艺术(音乐)领域,感性作为人最初的本原驱动,是问题的关键。同样,也是实现“知识安全”的必要保障。
音乐是人的创造。作为其当然结果,对以何为本的识别就很显然:天本,神本,物本,人本。如果以“人本”作为主要部件的话,则价值轴心的定位或者位移,将必须面对。无疑,理性并认知方式,及其终极依据(确实:实在+精确),是为当今主要价值轴心(作为历史辨认与文化识别的基本标准),并有大面积的覆盖与弥漫(包括此次会议发起单位散发的思考题,基于一种单一的真值逻辑:是或者非;其实,文化问题不仅仅:是或者非,还可能有:是并且非,不是或者不非,不是并且不非,等等)。尤其,需要充分地注意到,由于理性过于凝聚,以至全面格式化,进而,导致“初通音律”进程的中断。对此,不妨关注一下“完形人本结构系统”——感性/感受,知性/体验,理性/认知,灵性/觉悟;并置于人的“艺术/审美”方式及其语境当中,进行必要的轴心位移与定位。依照经济学“通过生产推动消费”或者“通过消费拉动生产”的原理,显然,基点应定位在:人的感知结构的合式合理(本原)驱动。进而,通过拉动技术,一方面推动乐音构成元素及其相应方式的增长与扩张,另一方面,引发人的音响感受方式的转换,再而,改变其先在意义指向。与此同时,其终极关怀也在于:感知结构在人的总体音乐文化历史进程中,不仅驱动,而且仲裁。
无疑,相比以往的历史,20世纪音乐一个空前的突现方面在于:音响媒体被极度关注。进一步的问题是,音响结构行态的人文意义如何“给出”?我认为——以感性为基础先导,设定“六合”底边:高低,长短,厚薄;以知性为经验中介,实现“两象”叠合;意象(构象、运象、品象之象),易象(简易、变易、不易之象);以理性为操纵路径,拉动“四素”张弛:音高,音长,音强,音色;以灵性为完形整合,在功利度量之后祛除精神遮蔽,在科学唯一与理性至上之后敞开人本原真,在认知承诺之后诗意地居住;再加上“3+3”外在关系之界约:古今/中外/雅俗+内外/是非/阴阳(尤其注意世界性女权主义思潮对音乐文化领域的渗透),以及在此之上的【生/死】关系之整合;进而,螺旋循环,周而复始……。其“底牌”就在于:音乐是人的创造。于是,“六合”之内外:生“物”由天,成“象”在人。不管是对声音的无穷探索,还是直接面对音响本身,其底线或者根源,只能是——人与人相关。作为人文前提,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早在二百多年前,通过对人类“部落自然法”(或者译为“氏族自然法”)的考察,认为:人类的需要和效益就是部落自然法的两个根源。质言之,“利益”就是人的感知结构的本原驱动。然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这一“利益”的性质归属,毫无疑问,处在“审美语境”当中。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言“无利害关系”,不失为一个合式的历史参照,至今依然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
诚如音乐起初仅限于向自然的表达,随后扩大为与人的交际,再后作为一种只供感性愉悦的生产与消费,如此的音乐文化历史进程,绝不仅仅是一个终结,而且,也将是一个开端。因为,面对极度人文化了的音乐和极端肆虐着的大自然,人类又将开始其最初的表达……在一种无穷无尽的文明进程当中……。也许,这就是最最简单和最最本原意义上的——文化多元与人的音乐感知结构完形合一。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