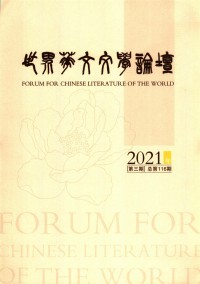语文文白之争教学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语文文白之争教学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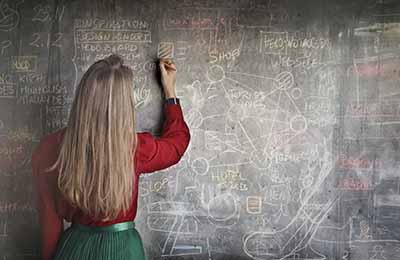
历史上的文白之争
文白之争,在1949年以前,大的、公开的论战大约有过两次,小的、私下的就难计其数了。
五四前后的大论战,使白话文得到全面推广,并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
20世纪30年代关于大众语文的论战,进一步巩固了白话的地位,使白话更加接近大众的口头语言。这两次大的论战,都以文言的节节败退而告终。鲁迅于1927年曾言,“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然而,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年那些攻击文言的大师级人物,莫不是受了文言的熏染,无一不旧学深厚。
近日,韩军先生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时间硝烟四起,引发了众人的争议,这场争议,使我们得以在鲁迅宣告“已经过去”将近八十年后,又躬逢了文白论战的盛事。
我们选编韩军先生的文章并组织这场讨论,希望能够引发人们对于文言和白话的矛盾、以及文言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应该占到多大的比例等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
沙龙·观点
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顿失光彩”、“暗然失色”,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譬如社会政治动荡等等,但一个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最根本的解释,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即13岁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在语言“敏感期”所接受“语文教育”,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是在废除文言的背景下,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人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
文言是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语言,而白话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白话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一母一子,一本一末。人们在孩童的“语言敏感期”,从“根源处”学习语言,阅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古诗、古文,打好文言根基,再运用白话来表达,那么,写出的文字就比较简洁、干净、纯粹、典雅、形象、传神;相反,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写出的文字,就难以达到以上境界,而可能拖沓、冗长、繁琐、欧化、罗嗦、抽象。几十年来内地文人的整体文字面貌是越来越“水”,越来越“白”,越来越“俗”,越来越“痞”,失去了纯粹、古雅、洁净、朴素。不可否认,这正是所谓内地“现代语文教育”斩断了“文言”血脉的结果!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汲取,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我绝对不是主张在中小学阶段全面恢复文言教育,全面实行“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我主张白话、文言,各占半壁江山,适度加大中小学阶段文言的课文比例,而且是小学、初中、高中循序渐进地增加,至高中阶段在课文篇目数量上应当略高于50%;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标,也绝不是放在培养“白话大师”上,我们着眼于奠定一代几代“现代人”的“白话运用”的根基,提高“现代语文教育”“学习运用白话”的效率。
现代汉语等于“现代”“进步”,文言等于“非现代”和“落后”,用啥即学啥,不用啥就摒弃啥,这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思维逻辑。
鲁迅、胡适、郭沫若反对文言,更多是从政治、思想、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的。而他们自身的文言素养,却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成年后,无论怎样大张旗鼓地反对文言,而自身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自身的文言功底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基,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而如果出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语文教师们”,自身文言根基很浅,却也跟在大师后面,齐声附和“废掉文言”,那么,我们可能“废掉中华文化灯塔”,废掉几代人“文化根基”,同时废掉“白话的根基”。使几代人的“白话”成为“浮萍”!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代内地文人的文字正在出现“粗鄙化”趋势,广大青少年的语言也正在“网络语言”、“商业语言”的冲击下,出现“垃圾化”趋势。
我必须声明,我主张在当今语境中重视文言教育,但是,我却极力反对让青少年读“经”。(本文作者:韩军)
沙龙·回应[一]
回“家”的路不在“文言”
近日拜读了韩军老师的《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文,笔者对文中的有些观点不敢苟同。我认为学生只有在现代语文的听说读写活动中才能真正生成现代语文的语文素养。冷了加衣,饿了吃饭,这才对号。
就必要性来看,要学好白话文并不必要一定学好文言文。文言与白话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白话从文言中吸收了大量的词汇,现代文章里常常引用一些文言成语或文句、诗句。学点文言文对于现代文肯定是有些益处的,读一些文言文对于学生的发展当然有帮助。但是,能否学好现代文,首先决定于学了多少现代文,是怎么学的。这种帮助、这种益处对于学生现代语文素养培养和提高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决定性的,而只是辅助性的。汉字是从甲骨文而来,汉字是中国人必须学的,但是从来没有人为了能够听说读写汉字而去学甲骨文,并把甲骨文作为能够运用汉语言文字的基础。同样的道理,为了学好现代文、白话文,我们没有必要把学好古代作品和文言文作为前提。而且,客观事实也证明这种理论只是一种臆想而已。
再就可能性来说,视古代语文素养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现代语文素养的前提,这是不现实的。学生在学校要学的课程极多,每一课程所学习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如古代那样只学一门课程。高中语文所有授课时数少于400个;初中和小学更多些,以韩先生所主张的,“通过文言”学习“运用白话”,“白话、文言,各占半壁江山……至高中阶段在课文篇目数量上应当略高于50%”,先不说学习白话需要占用一半以上的语文学习时间,仅就从教学时间上来说,中小学文言文教学已不可能成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现代语文素养的前提。
同时,中小学生对于远离他们生活的文言文极难有正确而深刻的理解。有的论者认为,现代汉语的应用能力是不必在学校中进行专门学习就能具备的,这种观点无视已经趋于成熟的自成体系的现代语文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高度,更是不敢苟同。使用现代语文即使仅仅要求达到“文从字顺”的初级水平,也非付出极大的努力不可。如果中小学语文教学文多白少或文白参半,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要找到回“家”的路,是不可能通过学量的文言文的。面对这种根扎于‘文’,语发为‘白’的“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法则,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中小学文言文教学是当前语文课程改革中需要认真看待和慎重对待的难题,我们应该站在现代语文课程服务于培养现代人的高度去审视它。(本文作者:刘梅珍)
沙龙·回应[二]
文言和白话宜分两科
文言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应该占到多大的比例,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它涉及普及教学的目标,甚至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应该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学好现代汉语,具备比较熟练地应用现代汉语的能力更有其迫切性。如果连现代汉语也学不好,甚至做不到起码的文通字顺,这样的受教育者在社会上将无立锥之地。从语文教学的实际效果来说,这个要求我们并没有完全达到。我做了十五年编辑,接触的大多是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受教育程度是偏高的,然而,能够完全做到文通字顺的,实在不多,一些专家、教授的文章竟是满篇不通的。所以,我觉得普及教育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提高受教育者现代汉语的程度。否则,就是教育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