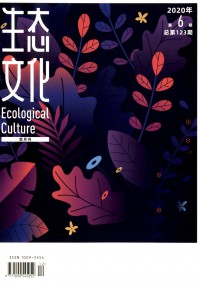文化哲学形上建构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文化哲学形上建构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文化哲学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从文化角度看待人类生存问题的一种方法论视角,在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哲学界颇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学者们对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相同或不同的思考结果。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不断出现的新的文化现象、生存方式和问题,对文化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促使我们对文化哲学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本期学术笔谈发表的三篇文章,是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哲学的思考和阐发,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迪。
一
我国整个人文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对文化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间的“新文化运动”起,对“文化”的研究就被作为一种以整体论、主体论的“哲学方法”解读当时的“中国问题”的思路。自此起近百年间,这种研究借鉴和吸收了不少西方学者的思想资料和研究构架,同时也承接和延续了中国近代学术传统,形成了自身的哲学特色,诸多先贤的这种努力已有累累成果。现在回头静心细读,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当具有“重新装备”和“重新奠基”的意义。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文化眼光”考量社会现实,以“文化战略”筹划社会发展,已经蔚然成风。正是上述两种历史性的文化学术条件,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新起的研究潮流中,各家的“学科”依据不尽相同,视角和方法也各有异样,但大多都注重从哲学层面对国人当代十分复杂的思想情绪和文化执着进行学理分析和心理“制引”,确也显出有效有益的业绩。各家论著的被引用和被关注或是明证。
面对目前我国社会的文化思想态势,我认为,文化哲学研究者的学术任务,应该主要着力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文化哲学形上建构的进一步探索;另一个是对解决当前文化现实问题的探索性的哲学式尝试。
在前一个问题上,我们似乎还是应该“再一次地”回到我们的核心主题词——“文化”上,对它进行新一轮的“哲学复述”。
关于“什么是文化”,我们不必再重复泰勒等的几百种“文化学”的(其实大多都是“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文化定义。从哲学的高度,我们可以以对象化的思维方式直觉到文化是一种“存在着的”精神“氛围”或者“弥漫”。而对于“他在”的观察者来说,我们(作为刚才的观察者)实际上也是他(周围“场”中)的氛围和弥漫。我们与他者的“共在”就这样在互置和互融中构成一个统一的“场”。这就是我们与他者共同形成的“更大的我们”的“存在”之场。这“存在”包括了下述五个“领域”(或者组成部分):1、作为我们的“原初的氛围”的自然界;2、我们在自然界养育下所创造的“文化的物质世界”;3、我们在自然界的昭示和支撑下所建构的我们的“社会”(即各个级别、不同规模和不同模态的人类文化共同体);4、我们不断培养和教化着的人的“自身的身体和心灵”;5、人类不断扩展着的共同的整个精神世界。这个存在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它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所依”,也就是我们“生命自身”。这个“存在”就是“我们的文化”,或者说,这个“文化”就是“我们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存在哲学”就是“文化哲学”:就我们的生命本身及其氛围而言,没有任何“存在”不具有文化的性质;没有任何存在在我们谈及它的时候可以不谈到文化。文化就这样“覆盖着”我们的生命,它就是我们的“存在之场”。它就是“存在”。
更重要的是,文化在其具体内容上把形上的存在开显为“此在”。此在就与生存(或者“实存”)在“形”的层面具有了同样的意义。所以,文化本身兼具存在与此在的两种性质。它既具“生之变道”,又显为“万象之形”。
所以,以文化哲学对形上的研究,导致对“存在”的进一步解释。存在就是生命;而生命具有两个相互制约、而不可对任何一方做任何弃舍的方面:“生命之动”与“生命之形”。
“生命之动”就是生命活力。它就是生命由于“生”(“活着”并“活得更好”)的欲望和追求所表现出的“活生生”的朝气蓬勃的样子。它是一切人的(民族的)文化运动和“存在”样式变动不居的“原动力”。人(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正是人(民族)的活跃着的“生命力”在创造历史;如果人(民族)的生命力萎缩了、衰弱了,甚至连“活着”的兴趣和勇气都没有了,他就不可能创造历史。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进步的”历史。反之,只有那些具有生命朝气和对生活有更好、更高追求的人(民族),才是文化的人(民族),才能创造历史,使自己生活得更好。
“生命之形”就是生命通过自我意识的自我教化塑造自我实体形象和活动的实体制度。也就是说,生命是活动的,而活动必然要落实到“形式上”,即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进行,同时,生命活动也必然以外在的形式(质料之物或者符号之物)为其活动的直接目的,或者为其活动的工具。也就是说,生命本身必然要用“形式”把自己“表现”出来。在严格意义上说,任何生命本身都是“形式的”,个体的生命形式就是“身体”。没有无形式的生命。生命以自己的“生命力之动”永远在“为自己塑形”,这“形”就是处于历史流变“不定”中的暂时的“定”,由于“定”都是由生命自己规制(建构规则和制度,或者按照生命心灵的外在性活动规则设置)出来的,所以就叫做“规定”。
所以,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人的存在就都表现为人把自己文化(向文雅、文明而变化)的过程。之所以形成连续不断的序列,就是因为人的生命欲望和对生活得更美好的从不间断的、且日益强烈的追求;而这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都无一例外地是以人类的各种暂时性的制度和“创造物”(形式)的不断新旧更替所表现出来的。一方面是文化活力,另一方面是不断更替的各种各样的实体的文化形式。历史的发展在其实质上就是文化生命力总要以其前所未有的活跃和力度(在发生学意义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制度和符号),或者(在历史学意义上)否定和摧毁旧有的“文化形态”(制度和符号)而创立新的“文化形态”。
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两种相互联结、且相互作用的特点的表现:以生命力的活跃来推动和实现自己的发展,而以对实体的文明形式的创制来一步步把自己的发展“落到实处”。历史就是人不断鼓舞、激扬自己的生命的“文化活跃性”并同时也就以此来为自己创建新的“文化形态”、文明的总体过程。
二
生命力的活跃和旺盛,靠的是人(民族)以一种“狂欢”和“冲动”的态度来激发自身。中国文化的“乐”中包含了这种态度,而西方文化中的“酒神精神”直接就是这种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狂欢的态度伸展人(民族)的可能的“自由”程度,冲决一切对人(民族)的“生命优化”欲望的限制性形式。这就是人(民族)的“文化创造精神”,它是一种相对于固定成型的文化形式来说的否定性力量、批判性力量。人正是靠生命的这种活跃性来不断发展和提升自己的。
而生命的形态化(即文明化),靠的是人对制度和符号的自我创设能力。这种创设在最初的意义上有两种方式:被动的创设和主动的创设。被动的创设结果就是“禁忌”的形成,这就是人为自己规定“不应该做什么”;而主动的创设结果就是图腾的形成,这就是人为自己规定“应该做什么”。在此基础上,文化史形成了这两种创设的漫长系列。泛而言之,中国文化中的“礼”与“教”和“为”与“不为”,西方文化中的“阿波罗精神”和“理性”精神等,都与这种创设能力及其成果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创设能力建构人(民族)所赖以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界(天地)环境“框架”、社会(共同体)“制度”、人(民族)自身的行动和思想“规范”,以及人(民族)的精神生活“境界”。人正是靠生命的这种创制能力来筹划、落实自己的人生愿望和理想。
应该说,文化活力和文化创制能力是描述人(民族)的文化样态和探讨人的文化(存在)进步可能性的两个重要的基本范畴。“生命之动”就是文化的“动力学”,而“生命之定”就是文化的“形态学”。“文化”就是处于生命之动与生命之定二者的激荡和和谐中的生命不断升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文化史。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人的生命的活跃性,即没有文化创造力,那么,任何既有的制度、规范和“纲常”再好、再完善,都不过是死水一潭。而要使人“有精神”,使民族“有生气”,就应该重视激发人的生命活力,重视培养人的生活情趣,调动人的创造性思想和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性,给人的创造性的展开提供尽可能大的文化社会空间;同时,在人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时候,要善于引导人们进行制度创设和规范的建设,而不要盲目崇拜人的本能的“自发性”。要把人的自发性区分为“积极的自发性”和“消极的自发性”。对积极的自发性进行促进,而对消极的自发性要用“现代禁忌”加以抑制和消除。总之,要使一个人(民族)有文化,就应该对“激发活力”与“创设制度规范”并重。当然,不同时期文化发展的这两个方面,都面临着由历史所奠基的、实际所昭示的时代任务。在不同时期文化任务各不相同甚至很不相同,因而,到底是应该更侧重激发生命的活力还是应该更重视制度创设能力,要视时代任务而定。这也是很自然的。但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在不同“度”的侧重的前提下,随机地协调文化之动和文化之定,使二者形成一种动态的均衡,这也可以被称作“文化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文档上传者
- 地域文化旅游文化品牌
- 文化资源建设文化思考
- 市文化局文化总结
- 文化翻译和文化传真
- 文化冲突和文化震荡
- 文化局文化艺术安排
- 后殖民文化音乐文化
- 文化局强化文化服务讲话
- 传统文化中的廉文化研讨
- 产业文化创业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