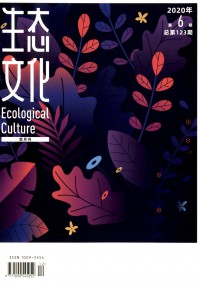文化散文哲学追求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文化散文哲学追求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20世纪90年代文化散文较多的吸收了古典哲学中道家“逍遥以游”的旷达超脱和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千秋情怀的精神内核。在行者的路上或者“神游”的历史情境展开与先哲、与历史、与文明的审美对话,思索着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从而达到一种宗教式的人生体悟,体现了人类对精神家园的执著追寻。
[关键词]90年代文化散文;古典哲学;精神家园
Abstract:The1990sprosesassimilatetheintrinsicbroadmindednessofTaoismandtheConfucianistclassicalphilosophyofresponsibility.Onthewayoftravelingorpatrolinthehistoricalsituation,authorsofthe1990’sproseslaunchaestheticdialogueswiththesages,thehistoryandthecivilization,thinkingdeeplyaboutthevalueoflifeandexistenceatthesametime,thusachievereligiouscomprehensionoflife.Itmanifeststherigidpursueofhumanspiritualhome.
Keywords:the1990’sprose;classicalphilosophy;spiritualhome
20世纪90年代文化散文(以下简称90年代文化散文)较多的吸收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内涵,不仅与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有关,而且还在于他们自觉的借鉴和追求。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在游历山水、瞻仰古迹和思索历史时往往能透过物象达到一种哲学的感悟和体认,表现出对哲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内在价值取向上的趋同性和承传性。对古典哲学吸收较多的是道家“逍遥以游”的旷达超脱和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千秋情怀的精神内核,体现了知识分子内心割舍不断的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脉系。在与先哲、与历史、与文明的审美对话中,作者也形而上地思索着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从而达到禅宗“瞬间永恒”的宗教式人生体悟,体现了人类对精神家园的执著追寻和永恒的存在之思。
一、逍遥以游的人生理想
中国古代哲学在90年代文化散文作品中最明显的体现是道家“逍遥以游”的思想和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作者将自我生命的存在形式,与山水、历史和文化进行主观想象性的天人合一,在山水和历史中畅神达意,逍遥以游,获得审美形式的生命体验,达到对个体自由生命的提升。因而,达到“独与天地来往”的绝对心灵自由是道家最高的人格理想,这也是摆脱世俗人生千般无奈万般不幸和生离死别的刻骨铭心之痛的最好方式。在90年代文化散文作者的笔下,映现了这种人格理想的光辉。
在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中,王充闾是受道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代表,在他所钟情所描写的山水风物和历史故事里,充盈着对道家思想的痴迷、执著和继承。《寂寞濠梁》通过寻找庄子与惠子同游时发出游鱼之乐的故地——濠梁观鱼台,以现代人的审美情怀与这位伟大的先哲展开穿越时空的对话,通过大量的故事系统展现了庄子思想中的超人智慧和深刻蕴含,直接表达了对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向往和迷恋。《存在与虚无》以洛阳古都为背景,以一曲名士悲歌、千古绝唱《广陵散》为线索,串起了十三朝古都的历史风云,表达了对放荡不羁、蔑视礼法、超然遗世的魏晋风度的向往和赞赏,高度褒扬了深受道家影响,有着“越名教而自由”思想的旷达洒脱的魏晋名士留给后世的文化、精神和人格财富,表达了对他们命运的深切同情和由衷敬仰。王充闾的散文深得庄子思想的真谛和精髓,不仅在写作风格上显示出博大庄严的艺术气度,上下几千年、纵横开阔、气势恢弘、游刃有余,而且内容丰厚、思想深邃、意境高远,显示出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少有人企及的大家气象。
除了王充闾之外,最典型的代表还有在佛宗道源的发祥地,显示着大仁大智的仙山——天台山养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刘长春。作者用饱含诗情的语言与天台山的一景一物畅谈对话,声声呼唤着天台山的远年灵魂。“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仰天大笑出京城的李白在天台山重新找回了飘逸的诗魂和奔放的诗情,所以李白抒发了“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的豪放情怀和人生愿望;隐居在天台山的诗人寒山子在这里找到了与他那颗易感的心灵相接通的原始的野性的静美,独行于山林,探问于天地间,追索着生存的意义和无意义,也渐渐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深思;由于“安史之乱”被无辜流放至此的郑虔,思想在天台山山水的滋养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以一种安于现状、豁达超脱的处世态度面对所经历、所面对的官场失意和人生挫折,兴办学馆,广收学徒,发展教育,以他的真诚和儒雅与一方水土一地民众建立了血肉联系,成为世代后人感激、怀念和敬仰的文人。刘长春着力描写天台山优美的景观和寄情于此的有着道骨侠风的文人骚客、道人隐士,体现了他作为文人对山水的天性向往,渴望在山水里“逍遥以游”返朴归真的愿望,借人杰地灵的天台山达到了寄情山水,“乘物游心”的思想净化和升华。
“游”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是精神绝对自由的终极向往,而“心游”和“神游”是道家最高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境界,也是最高的生命境界和哲学境界。作者通过“心游”和“神游”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精神境界。“天人合一”是一种绝对超脱绝对自由精神的高扬,也是一个有关中国智慧和生命存在的哲学命题。在悠然玄远的处世态度中,在物我相忘的人生超越中,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找到了排遣现实烦恼的方式和途径,找到了个体精神的独立和自由,找到了生命的韧性力量和内在激情。
二、积极入世的处世态度
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精神内核深深地浸润了几千年中国文人的内心。90年代文化散文延续了儒家的精神内核,在观鉴山水、冥思历史、体察文化时,寄予了积极进取、兼济苍生、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和人文精神,体现了文人根深蒂固的鸿儒之气和千秋情怀。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带着深沉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文人的忧患意识书写历史反思现实,体现出了俯仰天地、超乎时空的大气和慷慨,具有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沧桑感和战栗感。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和素素的《独语东北》便是其中最出色最典型的代表作品。
在《湮没的辉煌•东林悲风》一文中,作者夏坚勇以东林书院及它的创办人顾宪成为线索,叙写了书院在风雨飘摇、天崩地坼的晚明年代坎坷的遭遇和灾难性浩劫。东林书院的文人以顾宪成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联为处事原则和做人标准,讽议朝政、指陈时弊,在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指鹿为马的黑暗晚明时期为百姓疾呼,为国家呐喊,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标独立的人格精神。这些充满血性和阳刚之气的文人的高标独立、积极入世、天真自信终于引来了惨重的浩劫。他们指陈宦官魏忠贤的专权误国,直接导致了以杨涟、左光权为首的“东林六君子”的惨死,场面之壮烈惊天地泣鬼神,令人惨不忍睹、扼腕叹息。权势者虽然能够摧毁有形的书院和文人的肉身,但是东林精神已经汇入中华民族的浩浩长河,一代文化精英为后人所感叹所怀念的正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道德良知。夏坚勇以知识分子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和文人的文化承担意识对民族精神进行了探幽发微的深入挖掘和思考,在为古人的伟大人格和精神意志歌颂、感叹的同时也寄予了对当代人的警示和厚望,为当代人指明了一条精神自救和灵魂净化的道路。
在《独语东北•笔直的阴影》一文中,作者素素通过参观旅顺口万忠墓陈列馆和祭祀广场的行踪,真实再现了旅顺口大屠杀的血腥场面,思绪绵延万里,纵横古今中外,反思了古印度河文明的衰落、中世纪十字军东侵、日尔曼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对中国的侵犯等无数次造成文明戕害和摧残、对原始纯真人性践踏和破坏的非正义战争都是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这种残杀是毁灭性的,是人类万劫不复的灾难,作者也以迸发式的激动语言喊出:“我的悲哀已不只是为中国人,而是为整个人类。人类惧怕死亡却发明了屠杀,人类亲手制造的死亡的阴影,从未离开过人类自己的头顶,它笔直地穿过历史的时空,也穿过人类的心灵,垂落下来……人类总有一天要灭绝。但我希望,人类的灭绝最好是由于火山爆发或洪水漫流,而不是人类自己的残杀。不要屠杀。这应该是人类共同遵守的诺言。”[1]作者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反思人类文明和异化人性,体现了博大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徜徉在布满史迹的土地上,游览在厚重的中华文明的历程中,置身于一个凝重厚实的历史、现实和艺术世界,用心去体悟跨越千年的历史时空,使活跃的情思获得了一个当下的定位,使人文精神、民族精神和传统文明重新扎根于当代人干涸焦渴的心灵中,以作品体现出的美感和哲思,引领当代的每个人反思自我的行动和灵魂,思索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三、精神家园的执著追寻
“寻找精神家园”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而且纠缠着每个时代整体灵魂的基本问题,散文一直以来也与精神家园的寻找有关,力图在作品中寻找和建立精神家园。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以自觉的文化承担意识来探求人类灵魂的皈依,在寻找中逐渐达到与宗教相接的最高艺术境界。这种宗教境界的抵达便是作者苦苦寻觅的能够实现心灵和思想诗意栖居的最完美最稳定最终极的精神家园。
宗白华先生曾经把境界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和宗教境界,宗教境界主于神,是人类最高层次的艺术境界。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除了在自然和历史中,更多的是在宗教里寻找精神家园,这才是人类最终极的归宿和最理想的皈依。张承志的文化散文不仅体现了自然的真实、酷烈,更显示出了宗教的伟力:“我知道冥冥之中的那个存在让我进入西海固,并不是为着叫我礼全天的Farizo拜。一切天命都包含着对天命——Farizo的顺从……”[2]张承志的宗教情怀是源自本心的永不停息的精神追求,是真正纯粹意义的宗教,在“哲合忍耶”苏菲主义那里,他获得了璀璨的智慧之光和深邃高远的神明心境。余秋雨的散文也往往会在不经意间达到一种宗教境界和抵牾。作者拜谒莫高窟是为着宗教而来的,在这里,可以体会到一种圣洁的沉淀,可以体会到一种超越了宗教的宗教,作者也在这震颤的刹那间获得宗教式的感悟并畅达的释放出灵魂的声音:“蔡元培在20世纪提出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或许,人类的将来,就是要在这颗星球上建立一种有关美的宗教?”[3]西湖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在《西湖梦》中作者指出西湖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的体现,一切的宗教都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山水走向了宗教,宗教也走向了山水。中国的原始宗教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文化人格和民族精神的抽象和象征,余秋雨的宗教意识不如张承志来得浓烈来得直接来得纯正,而是一种广义的混沌的原始性的自然情绪,是对真理信仰、存在价值的终极思考和宗教式的审美超越。作者在面对宏大而苍茫的历史和人文、自然景观时,内心往往充满孤独感、虚无感和荒谬感,感到一种无形的、不可名状的力量尤其是死亡形成对自己的威胁,进而思考个人“存在”的问题。余秋雨的散文中多荒原、废墟、坟堆等意象,他多次追问“我们从何处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何处”,多次思考前世和今生,“如果真有前世,那我一定来过这里,住过很久,我隐隐约约找到自己了。”[4]他也多次反思死亡和毁灭的存在命题,走在苍凉的废墟和茫茫的大漠中,感到每一步都牵连着最纯粹的死亡和毁灭。这种个人的孤独感、畏惧感、死亡意识与禅宗的逻辑因果关系和生死循环原则有一定的心理感应和亲在联系。王充闾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等散文集既书写了历史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客观规律,也书写了其难以预料的偶然性,呈现了人文情怀的魅力和非理性的荒诞与虚无,在历史的烟云中领悟个体生命存在的宿命和悲剧。《陈桥崖海须臾事》以意识流结构全篇,时空交错,将整个宋王朝的沧海桑田汇聚于短短几千字中,作者以禅家拈花微笑式的生命体悟,呈现出对历史悲剧循环的超然理解:宇宙万有,沧海桑田,不过只是心灵幻象式的反映,历史像一个玄妙幽深的谜语,留下的只是精神世界的永恒追索和诗意情怀。王充闾的散文,以一种具有想象力的视界去重评和审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对历史和人事照以虚空,然而也不乏逻辑真理和道德良知,理性中隐含着诗情,运思中潜隐着禅理。
90年代文化散文作家在对苍茫原始的自然和悠远深邃的历史的思考中,寻求独立自由和自在自为的精神家园,实现重建价值体系,重塑人格风范等超越形而下层面的精神愿望和诉求,以知识者的生存体验、生命感悟与人格智慧分析、批判和再建理想的精神世界,进而思考人的生死和存在问题,达到与宗教接近的艺术高峰和澄明的禅意境界。
[参考文献]
[1]素素.独语东北[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95.
[2]张承志.荒芜英雄路[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302.
[3]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15.
[4]余秋雨.山居笔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106.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