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鉴泉先生人道思想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刘鉴泉先生人道思想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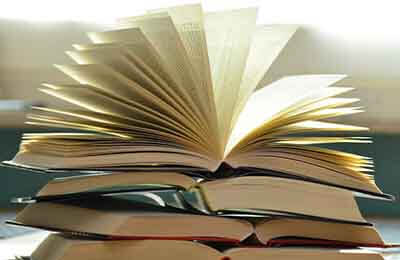
1923年,中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除了主将张君劢、丁文江外,梁启超、胡适、梁漱溟、陈独秀、王星拱、唐钺、张东荪、范寿康、林宰平、吴稚晖等人都卷了进去,事后由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先生搜集了论战各方的文章,总名为《科学与人生观》于1923年12月出版,其后多次再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地处西蜀成都的刘鉴泉先生也参加了这场论战,他写了一篇题为《人道》的文章,初稿于1923年,修改、定稿于1929年,历时五年,应该是一篇在思想上深思熟虑的作品。其文与《推十书》[①]中《内书》的《群治》(1923)、《故性》(1921)、《善恶》(1928-1930),《外书》的《进与退》(1925)、《动与植》(1925)诸篇在思想上有深刻的照应,首先批判胡适先生的“功利主义”,然后批判梁启超、梁漱溟二位先生的自由主义,最后发扬其祖父刘止唐先生“吾以圣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谬溷圣贤”[②]的学术思想,显示了刘鉴泉先生作为一名后五四时期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一
对胡适先生在评价墨子时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观点,梁启超、梁漱溟、刘鉴泉三位先生,均持反对、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三人各自的理论出发点却是不一样的。二梁在“科玄论战”中被吴稚晖等人斥为保守主义,[③]但是,在刘鉴泉先生看来二梁的思想中已经裹挟了很多有违“吾华先圣”的糟粕。所以《人道》一文批判胡适的“功利主义”只是一个铺垫,批判二梁的思想才是梁鉴泉先生的真正目的。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道》一文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科玄大战”的范围,刘鉴泉先生从来都不是一位凑热闹的人。
以“西洋的哲学”为“比较参证的材料”而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胡适先生十分欣赏墨子。胡谓:“墨子的根本方法,应用之处很多,说得最畅快。”“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④]这种“应用主义”为上的观点遭到了梁启超与梁漱溟二位先生的反对。梁启超先生云:“墨家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吾畴昔亦颇喜其说,细而思之,实乃不然。人类生活事项中,固有一小部分可以回答出个‘为什么’者,却有一大部分回答不出个‘为什么’者,‘什么都不为’,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⑤]梁漱溟先生将孔墨之争向上提升了一层,直谓:“大约这个态度问题不单是孔墨的不同,并且是中国西洋的不同所在。”并且进一步分析说:“将整个的人生生活打成两断截,把这一截完全附属于那一截,而自身无其意味。如我们原来生活是一个整的,时时处处都有意味,若一分,则当造房中那段生活就全成了住房是那一段生活的附属,而自身无复意味。若处处持这种态度,那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为手段——例如化住房为食息之手段,化食息为生殖之手段——而全一人生生活都倾欹在外了。不以生活之意味在生活,而把生活算作为别的事而生活了。其实生活是无所为的,不但全整人生无所为,就是那一时一时的生活亦非为别一时生活而生活的。平常人盖多有这种错分别——尤以聪明多欲人为甚——以致生活趣味枯干,追究人生的意义、目的、价值等等,甚而情志动摇,溃裂横决。……,这彻底的理智把直觉、情趣斩杀得干干净净,其实我们生活中处处受直觉的支配,实在说不上来‘为什么’的。”[⑥]
刘鉴泉先生在批胡的态度上与二梁完全一致,鉴泉先生曰:“胡氏持实验主义功利之说,二梁驳之是也。顾有当分析论者,人生行为固显有目的手段之分,安可皆混?积财以养生,而反舍生以守财,人莫不笑之;设兵以卫民,而反脧民以供兵,人皆恶之。本末之间,岂可无辨?顾凡诸意义,推论至人生而止,更求生之所为,则用无答案,此本无有,非求者之不力而未工也。西方之人,多求生之目的意义,价值终结,求之不得,遂成悲观主义。”[⑦]刘鉴泉先生在二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语言犀利、尖锐,切中要害,强化了梁漱溟将儒与墨的争议引向中国与西洋的争议路径。所不同的是,刘鉴泉先生在《人道》中大量引用了柏格森、托尔斯泰、叔本华等学者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言论来说明,西方文化务求于外的人生观最后必然导致“物物而物于物”,人生所以倚赖的精神必将丧失的悲观主义。用刘鉴泉先生所引托尔斯泰的话来讲,就是“吾觉吾前此所借以立足者,今已破坏。两足空无一物,吾遂无以为生。”[⑧]在笔者看来,这些材料的引用,并不仅仅说明刘鉴泉先生在反对西化的层面上认同梁启超、梁漱溟二位先生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它说明了刘鉴泉先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论视野宽广,对相关的各个方面的情况相当了解。换言之,文章将要提出的重要观点,实际上是刘鉴泉经过反复斟酌,认真思考之后取得的思想结晶,是有厚实的资料作为论证的基础的。
不过,在刘鉴泉先生看来,二梁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早在朱元晦那里就已经进行过讨论:“朱元晦门人常问六合之外。元晦曰:‘人生天地间,且只理会天地间事。’此语妙矣!柏格森何来何去之问,可直答之以来自天地间,去向天地间而已。且即以所见察之,天止一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固不见其有他之目的在也。朱元晦常令门人思天地有心无心,而谓以生物为心。实则此亦以人推天之言耳。谓天有心,天亦生也。谓天无心,天亦生也。生是事实,要不可改。故吾华圣哲殊不问天之生何为?即使天可问,天殆亦当答之曰:‘吾亦不知吾何为而然也。’天地之何为而生不可问,则人之何为而生固不可求矣。”[⑨]这是顺着朱元晦“以天推人”的理论推出来的不可问、不可求的结果。
但是,刘鉴泉先生认为,朱元晦的这种说法是需要进一步商榷的。刘鉴泉先生云:“若于生之长途中求其价值终结,固非无可言也。生有高下,是价值也;生有始末,是终结也。价值之不同,即在于意义。既有终结,亦未始不可谓有目的也。二梁之驳胡氏有太过者。利者,义之和。以义为利,圣人固非不言效果。使不言效果,则毁瓦画墁,亦可无讥,一切生活,孰非精神?皆可以常务所为而废其选择耶?梁氏之驳托氏,又有太浑者。”[⑩]批评朱元晦,意在批二梁。刘鉴泉先生的意思是,完全说人生没有任何目的,梁启超之“什么都不为,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梁漱溟之“生活是无所为的”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人生有价值的高下,否则“毁瓦画墁,亦可无讥”,人生有始末,必然要有精神的追求。什么都不为,从价值观上来讲,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刘鉴泉先生在其《人道》中对他与二梁的思想分歧,只是说了“什么”,没有说明是“为什么”。笔者在此略作说明。众所周知,严复先生以进化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曾经对梁启超先生产生过深远影响,逃亡日本之后,梁启超先生接触的都是诸如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江中兆民、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德富苏峰、加藤弘之等在日本具有卓著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学术思想,成了一名地道的自由主义者。有学者甚至称他为“典型的唯意志论者”。[11]他曾经说:“我既为我而生,为我而存,以我之良知别择事理,以我之良能决定行为,义不应受非我者宰制,蒙非我者之诱惑,若是者谓之自由意志,谓之独立精神。”[12]对墨子的评价,梁启超先生十分欣赏《庄子·天下篇》中的评语:“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实际上也是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分不开的。诚如蒋广学先生所云:“梁启超自由观是以近代进化学说为背景、以近代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知识为基础”的一种“新民说”[13]这与刘鉴泉先生“任天”、“圆道”,“以圣人之道定百家”的学术理路是大相径庭的。
梁漱溟先生是一位深受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生命哲学影响的思想家,因此在其批胡的表述中,始终强调人生的“直觉情趣”。“直觉”一词是梁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虽然梁氏本人可能自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的概念,并且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解释,但是,它直接来源于柏格森的“内感直觉”则是肯定的。刘放桐指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是“师承意志主义者布特鲁,综合吸收了生物学进化论、心理学、细胞学等现代科学理论,使生命哲学作为一种有影响的非理性哲学在20世纪初进入全盛期。”[14]有了这种思想作为基础,梁漱溟先生关于人生意义的一些解释就不可能不打上非理性的烙印:“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可指,如其寻问,就是在人生生活上而有其意义;人生没有什么价值可评,如其寻问,那么不论何人当下都已圆足无缺无欠(不待什么事业、功德、学问、名誉。或什么好的成就,而后才有价值)。人生没有什么责任可负,如其寻问,那么只有当下自己所责之于自己的。”[15]在刘鉴泉先生“以圣人之道定百家”的眼光看来,梁漱溟先生用柏格森的“内感直觉”来解释人生哲学,比梁启超先生走得更远。
不论是梁启超先生还是梁漱溟先生,都侵润在“欧风美雨”的话语背景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了中国固有文化精神的。刘鉴泉先生还专门撰写过《进与推》、《动与植》两篇重量级的文章,痛批西方“以物道概人道”的“进化论”,对当时所谓的科学主义、个人主义之类的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西方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打破了“任天”、“圆道”,天人合一的“人道”境界,给人类的未来只能带来永不停息的争斗。鉴全先生在其《变歌》中写道:“……千年笼络一旦脱,豺狼狐狸同邀嬉。千钧百喙唾陈迹,鲁变齐楚华变夷。我生恨晚乱耳目,纵观忽笑思忽悲,漫言醒眼看沉醉,独患坦道成嵌崎。世间万事尽虚诳,胶柱刻舟吾固痴,古今茫茫哪堪数,谓我哗众将何辞。长歌之哀过痛哭,听我藐藐空於戏……”[16]所以,二梁与刘鉴泉先生都反对胡适先生在杜威的影响下标榜的“实用主义”,归根结底,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二梁与刘鉴泉先生之间关于人生目的的不同看法,同样可以归结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本来,“五·四运动”以来,学术界实际上是把梁启超先生与梁漱溟先生当作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来对待的,可是现在看来,刘鉴泉先生实际上要比梁启超、梁漱溟二位先生“保守”得多。但是,笔者以为,刘鉴泉先生的学说之最大的特点就是“考镜源流、明统知类”,不仅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发展了如指掌,而且对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把握得相当准确。从《推十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他吸收西方新学说的速度与深度是令人钦佩的,在批判西学的缺陷时,也往往击中要害。然而,刘鉴泉先生的最大特点在于不人云亦云,始终坚持中国文化的“原典”立场,从学术的灵魂深处捍卫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是刘鉴泉先生思想的最动人之处。有诗为证:
自笑年来为底忙,痴情谁共俗人商。摊书顿喜贫儿富,落笔都成老汉狂。
侈口迂儒无剑气,秃头道士有丹方。生涯说与秋风听,故纸堆中是乐乡。[17]转二
刘鉴泉先生的人道观是植根于他的宇宙观的。他认为人在宇宙之中,不仅是宇宙中的一部分,而且与宇宙相续相联,是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一个环节。他在《群治》一文中写道:
夫孝弟仁义之义,岂独人道之必然哉?远原于宇宙分合之天理,而近基于人心爱敬之良能。盖不止为群之自然,抑且为天之自然、人之自然也。分合之义详于《易传》、《乐记》;爱敬之义详于《孟子》。吾常持以推说,已散见于各篇矣,兹复总述其略,以述天人群己之一贯焉。夫宇宙万象之则,惟调和与秩序,一则合之趋于同,一则分之趋于异。《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易传》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礼运》曰:‘连而不相及,动而不相害。’皆是义也。盖宇宙无过二态,一为动,二为静。动则发而行以成和,静则敛而止以成序。故《易传》曰:‘天行健,地势顺。’《记》曰:‘不息者天,不动者地。’宇宙即如是矣。人居宇宙中,亦顺是道,其和合也以爱,其序别也以敬。爱,恩也;敬,义也。盖人之心亦无过二态,其发也,趋于合,没人我而交通;其敛也,趋于分,定彼此而各守。发者,爱也;敛者,敬也。”[18]
此一段表述植根于相续相摩、不离不流的先秦礼乐精神是肯定的。但是,刘鉴泉先生具有超乎寻常的整合、超拔之功却又十分明显,第一,整合了孔子、孟子与《易传》、《乐记》由人道而天道,由现实践履而形上超越,在至俗至常的人间现世追求至神至奇的功夫。第二,把宇宙的生生不息、於穆不已概括为“动”、“静”二态的流转、互动,实际上就是整合了整个儒家与道家的思想资源。这种整合本来在《易传》、《乐记》中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是,鉴泉先生的整合是基于人生观的,是在讲宇宙万物与人类之生老病死相续相联,因此,践履中透出了高远,凡俗中透出了弘大。其理论目的是要矫正中国学术史不离则流,分崩离析的状态,是要批判五·四时期很多人执一而废百的偏激行为,这当然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第三,将宇宙分合之天理与人心爱敬之良能整合起来,实际上是将先秦原典的精神与陆、王心学理论的成果融会贯通。所以,笔者以为,鉴泉先生的思想始终继承了其祖父刘止唐先生立足于孔、曾、思、孟,吸收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思想资源的理路。萧萐父先生说:“鉴泉先生之学思脉络淹贯经史而以史为重,兼崇儒道而以道为归。”[19]如果把这个判断置放到中国宋明以来学术发展融合儒、释、道的情势之中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萧先生所说的这个“道”其实并不是先秦时期原汁原味的“道”,而是宋明以降经过了几番风雨、无数历炼的的“道”。因此,鉴泉先生云:“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纵能久而横能大。纵能久者,父子祖孙百世不忘,是以有史;横能大者,远近亲属分殊理一,是以有群。人居宇宙间,纵横系属,不可以离。仁以胹合之,义以序列之,而其本在于孝弟。诸德由是而成,百体本是而制,皆因其自然之情而定为当然之则。”[20]先秦儒家的孝弟仁义之道既久且大,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异于禽兽者,是系属于宇宙的自然之情,里面确有吸收了道家思想的陆象山、王阳明的影子。“诸德由是而成,百体本是而制”,体现了天与人的高度统一的精神。这种精神既符合宇宙生生不息的规律,也有利于人之所以为人,植根于善性的自然发展,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逆天之“妄”。因此,这种天道人道一以贯之的理论就不是学派的固执己见,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所以刘鉴泉先生在其《人道》中写道:“凡人生观必本于其宇宙观。盖凡言人道者,无非求合于大自然而已。吾华先圣之道不过曰:‘尽人以合天。’天者,宇宙之总名也。人在宇宙中,固不能超之,亦不能变之,彼持斗争分别之态以对宇宙者,妄也。”[21]“求合于大自然”,在鉴泉先生的观念中就是求合于宇宙、天人的世界中唯一的“善”,所以在其“性说”中,他不仅反对告子的“生之谓性”、荀子的“性恶论”,也反对世硕、宓子、漆雕子、公孙尼子,再到董仲舒、王充、韩愈、李翱、程朱、戴震、陆世仪、陈澧等各种有关“性说”的偏误,他只认同孟子的“性善论”,因为只有“性善论”遵循了宇宙自然之情的根本法则。[22]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建立在“适者生存”,“以物道概人道”的“进化论”基础之上的西方近代文化就是“持斗争分别之态以对宇宙”的“妄”者。鉴泉先生云:“自由平等之说倡,而人伦孝弟之说弃。”虽然“适者生存”、自由平等之说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学说“矫枉过正,因噎废食。自由之极裂其合,平等之极混其序。自由平等之极,欲并纵横之系属而绝之。而生物家等观人物之说,适盛于是。舍人从兽,倡言不耻,标野鸭之放逸,慕蜂蚁之均齐。如其所见,人之自由平等乃不如禽兽远甚矣。”[23]鉴泉先生的意思是,以“适者生存”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倡导的是人的生物性、兽性,它违反了“尽人以合天”的自然之道,违反了宇宙万物浑然一体的中合之德。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与告子的“生之谓性”之间有内在联系,它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导致人的兽性,因此,孟子的“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上》)的圣断在这里仍然可以起作用。毫无疑问,这种批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面前,是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的。
在这种理论背景下,鉴泉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人道”理论:“圣人知宇宙之相续相联,故其言人道曰:‘上事天地父母而下传子孙’,全其所得于天地父母之性命,而与天地父母同其久大,是为大孝。此即人生之目的意义。”[24]这段表述指出了人生的目的实际上可以化解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事天地父母”,第二个层面是“下传子孙”。鉴泉先生的这一重要的总结,来源于《曾子》记载孔子的有关论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说的是“上事天地父母”,“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说的是“下传子孙”。所以《曾子》云:“君子一孝一弟,可知终矣。”“知终”,就是说的人生目的。《曾子》又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由此可知,在《曾子》中,“孝”实际上是一种宇宙观、天人观,是人的自然情感的泛化,是“塞于天地,衡于四海”的一种宗教精神:“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乎身,敢不敬乎?”这与《孝经》“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的超越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鉴泉先生的“孝道”思想注重儒家与道家的融合:“《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吾华先圣之观宇宙,不于现象之外更求本体,盖知更求之徒劳而不可得也。故曰‘道法自然’。自然者,有二象焉,纵之宙则生生不已,横之宇则万物一体。夫弥异宙者,变也;弥异宇者,异也。变之中有不变焉,故不已,异之中有不异焉,故一体。不一者,相续也。道家之言循环,精于是矣。一体者,相联也,佛家之言因缘,精于是矣。其在《周易》以‘咸’、‘恒’为首曰:‘咸,感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久也。观其所久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宇也;恒,宙也。庄周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知其使。’”“故圣人之言造诣曰:‘久与大。’《易传》曰:‘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大根于久,惟久乃大。’《中庸》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易传》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地化成。’……皆言久大也。”[25]鉴泉先生的意思是,久,就是“下传子孙后代”,大,就是“上事天地父母”,“纵之宙则生生不已,横之宇则万物一体”。“大根于久,惟久乃大”,“上事天地父母”是以“下传子孙后代”为基础的,只有子孙万代不息不辍,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才能真正做到“博厚悠久高明”。这就是鉴泉先生效法自然、宇宙,天道人道一以贯之的人道精神。从宇宙天地的广阔视野来把握“孝”的精神,是刘鉴泉先生“人道”的最大特色,他从根本上抓住了《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宣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26]的表述中所显发出来的宇宙精神,天人群己一以贯之,既继承了“吾华先圣”的思想,也回应了“鲁变齐楚华变夷”的颠覆局面。
因此,刘鉴泉先生十分注重《孝经》。他认为《孝经》是先秦原始儒家哲学的精华与理论结果。在其《〈大学〉〈孝经〉贯义》中,鉴泉先生写道:“《论语》、《大学》、《礼运》、《中庸》、《孟子》之言,不可以不互证,缺其一则不贯,非独句义之多显同而已也。《论语》发其端,《大学》纵贯其次第,《中庸》横包其范围,《孟子》直指其要领,而《孝经》则定其会归。此诚儒家之大义也。”[27]这实际上给予了《孝经》极高的评价,这也正显示了鉴泉先生的理论归结。
在《人道》一文中刘鉴泉先生提出的“孝道”理论虽然之根于孔、曾、思、孟的原典,声称是“吾华先圣”的绝学,但是,由于鉴泉先生面对的是“持斗争分别之态以对宇宙”的现代生活,因此,从思想的统系来看,鉴泉先生走的是其祖父刘止唐先生整合儒家与道家,二者融通为一的道路,所以其“人道”的精神境界与宇宙相续相联,天地为大父母,父母为小天地,博厚高明悠久无疆的导向之中透着一种天人合一的萧朗、自然和了无挂碍的洒脱;从思想的方法上来讲,鉴泉先生走的是章实斋考镜源流、明统知类的道路,推十合一,两而能一,御变用中,“纵之宙则生生不已,横之宇则万物不息不辍”,其间蕴含了鉴泉先生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深层忧虑和无限憧憬。有诗为证:
人海风涛总未平,萧条秋气倍凄清。挑灯忽忆兴亡事,闭户难禁淅沥声。
晦景鸡鸣悲乱世,故庐蠖屈幸吾生。年来已断沧桑感,但视银河洗甲兵。[28][①]刘鉴泉,名咸炘,别号宥斋,生卒于1896-1932。祖籍成都双流,家世业儒,为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与著名学者蒙文通、唐迪风(唐君毅之父)等为知交。武汉大学萧萐父先生在其《刘鉴泉先生的学思成就及其时代意义》一文中指出:“刘鉴泉先生玄思独运,驰骋古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兀,堪称近世蜀学中的一朵奇葩。”(见氏著:《吹沙二集》,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454页)萧萐父先生又在刘鉴泉先生《推十书·序》中写道:“《推十书》,乃英年夭逝的天才学者刘鉴泉先生之重要遗著,是其所撰哲学纲旨、诸子学、史志学、文艺学、校雠目录学及其他杂著之总集,都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卷。”(见氏著:《吹沙二集》,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460页)刘鉴泉先生的学术成就还受到过陈寅恪、梁漱溟等先生的欣赏和赞誉。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刘鉴泉先生的学术成就湮没无闻,没有得到当代学术界应有的重视。《人道》一文,居《推十书·内书》之首。萧萐父先生在《推十书·序》中还写道:刘鉴泉先生“面对‘五·四’新潮及开始向后‘五·四’过渡的新时期,中西文化在中国的汇合激荡,正经历着由肤浅认同到笼统辨异,再向察异观同求其会通的新阶段发展。在其重要论著中,已有多处反映了这一主流文化思潮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人道》中体现得特别突出。
[②]刘止唐,名沅,生卒于1767-1855,祖籍成都双流,被列入《清史·儒林传》。其著作有《槐轩全书》(四川省图书馆有线装本),其中哲学方面除《四书恒解》、《周易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春秋恒解》、《周官恒解》、《礼记恒解》、《孝经恒解》、《大学古本质言》外,还有《正讹》、《子问》、《又问》、《约言》、《拾余四种》等,其学业多受自其父刘汝钦先生(精于《易》学,洞彻性理)。止唐先生认为,真正的圣学圣道至汉代以后,已被弄得面目全非,并且认定韩愈、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朱的思想都歪曲了孔子孟子的真义,致使圣学不传。他在其《槐轩约言》中说:“吾以圣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谬溷圣贤。”这种精神完全被五四时期的刘鉴泉先生继承了。
[③]深受胡适欣赏的“科学派”战将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中辛辣地讽刺了梁启超、梁漱溟二位先生,并且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一文中说,二梁的“谬误,乃是完全摆出西学古微的面孔,什么都是我们古代有的,什么我们还要好过别人的,一若进化学理直是狗屁。惟有二千年前天地生才,精华为之殚竭。无论亿万斯年,只要把什么都交给周秦间几个死鬼,请他们永远包办,便万无一失了。你想他如此的向字纸簏里,掏甘蔗渣出来咀嚼,开了曲阜大学,文化学院,遍赠青年,岂不祸世殃民呢?这是梁先生走去那条路上,走得太远了,所以陷入迷魂阵。”(张君劢、丁文江等著:《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
[④]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39、136页。
[⑤]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梁启超先生在其《人生观与科学》评判张君劢、丁文江的论战文章中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人生问题有一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见《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⑥]梁漱溟著:《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0-461页。
[⑦]刘鉴泉著:《人道》,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419页。
[⑧]刘鉴泉著:《人道》,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417页。
[⑨]刘鉴泉著:《人道》,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419页。
[⑩]刘鉴泉著:《人道》,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419-420页。
[11]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
[12]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之32,第75页。
[13]蒋广学著:《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14]刘放桐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15]梁漱溟著:《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88-689页。
[16]刘鉴泉著:《变歌》,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2227页。
[17]刘鉴泉著:《自笑》,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2225页。
[18]刘鉴泉著:《群治》,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429页。
[19]萧萐父著:《刘鉴泉先生〈道家史观说〉述评》(打印稿,第二届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摘要)。
[20]刘鉴泉著:《群治》,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428页。
[21]刘鉴泉著:《人道》,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422页。
[22]参见刘鉴泉著:《故性》、《善恶》,见《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
[23]刘鉴泉著:《群治》,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428页。
[24]刘鉴泉著:《人道》,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423页。
[25]刘鉴泉著:《人道》,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422-423页。
[26]此一段表述与小戴《礼记》的《祭义》一篇有雷同的地方:“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
[27]刘鉴泉著:《〈大学〉〈孝经〉贯义》,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60页。
[28]刘鉴泉著:《夜听雨》,见氏著《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版,第2225页。
文档上传者
- 刘鉴泉先生人道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