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蕺山无善无恶思想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刘蕺山无善无恶思想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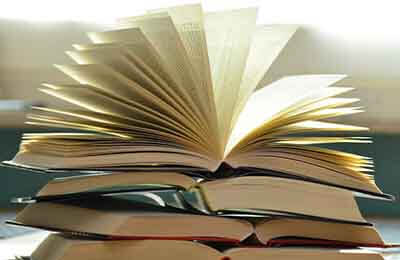
[提要]在王学中,“无善无恶”之说有两义:一是对本体“至善”之遮诠,一是指化境上的无执。以此两义来衡量蕺山的思想,可发现蕺山具有丰富的“无善无恶”思想。虽然他有不少言论是批评此说的,但若对其进行仔细审视,可知它们均未切中“无善无恶”说的本义。这些批评是在王学末流之弊的当下刺激下有为而发的,而非称理而谈。若称理而谈,蕺山是极力主张“无善无恶”之说的。此点可以印证蕺山与其师许敬菴及东林诸儒不同,其学在性质上属王学。
王学中的无善无恶之说发自王阳明,其高弟王龙溪及其后的周海门又对此说作了进一步的推阐,遂使此说成为王学的特色之一。倾向朱子学的学者多不以为然,如许敬菴、顾泾阳及冯少墟等皆辨之不遗余力。蕺山早年曾师事许敬菴,并与冯少墟及东林人士论学,其言论中也多有指摘无善无恶之说者。乍看上去,蕺山似与此说无缘。然而,如果抛开表面言辞上的龃龉而察其实,蕺山并不能反对此说。不仅不能反对,而且实质上是主张此说的。本文即欲对蕺山在此问题上产生的纠葛加以疏理,以见其思想之底蕴。
一无善无恶说在王学中的本义
仅就语词而论,“无善无恶”一语之义一目了然,即“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属谓词范畴。但是,在哲学上,随其指谓的主词之不同而在义理上产生的重要分际却是不能望文生义而明的。
若溯其源,具有哲学含义的无善无恶说当始发于告子。告子说: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
“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语义上等于“人性无善无恶”。这里主词是告子所理解的人性。孟子主性善论,告子主性无善无恶论。但告子所说之人性与孟子所说之人性完全不同。孟子讲人性,是就人的先验的良知良能而言;而告子主张“食色,性也”(同上),其讲人性,仅就人的自然生命而言。在告子看来,不论是善抑或是恶,均是人为的、外在的价值标准。人性如湍水、杞柳一样,只是一种自然材质,是中性的,不可以善恶言。这里,“无善无恶”指谓的是人的自然属性,其特定含义是人性论上的自然主义。
宋代的胡五峰,也有性无善无恶说,但又与告子之说迥异。五峰《知言》载:
或问性。
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
曰:然则孟轲氏、荀卿氏、杨雄氏之以善恶言性也,非与?
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哉?
或者问曰:何谓也?
曰:宏闻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独出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请曰:“何谓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也,不与恶对。”(《胡子知言疑义》,《胡宏集》附录一,页333。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1]
五峰承其父胡安国之说,认为善恶不足以言性。这也是一种“性无善无恶”说。这里,“无善无恶”指谓的是“天地之所以立”、“天地鬼神之奥”的天命之性,即性体。在五峰看来,性体是超越的、无对的本体。它是万善之源,超于善恶之表而为善恶判断的准则,因而,不可以经验中的善、恶观念指称之。“恶”当然不可以言性,即使“善”也不可以。如果一定要以善言之,那末,“善”的含义也就发生了变化:其义不再是“性有善的属性”,而是对性体之玄奥崇高而发的感叹,如“善哉!善哉!”这样的说法一样。[2]言下之意即是:对作为“天地鬼神之奥”的性体不能用表诠,只能用遮诠。因而才说性无善无恶。这种意义上的“无善无恶”是表示超越的天命之性之“至善”,与告子之说正相反对。
王阳明的无善无恶说当以“四句教”中所说的为代表。四句教说: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页117。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下同。)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这第一句。告子以“无善无恶”指谓人的自然属性,五峰以“无善无恶”指谓天命之性,结果使得其两人的无善无恶说的内涵大异其趣。而阳明又以“无善无恶”指谓“心之体”,其义又当如何?为把握其无善无恶说,有必要对“心之体”一语的含义先予衡定。
“心之体”,是宋明儒的惯用语汇,也称“心之本体”,有时简称“心体”或径称“本体”。它当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心之主宰者,即性;二是指心之自体,即抽象的心之本然状态;三是指工夫践履纯熟后自主观而言的心灵境界,即具体的圣贤之心。
先看第一种用法。朱子说:“心以性为体,心将性做馅子模样。”(《朱子语类》卷5。第1册,页89。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又说:“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朱子语类》卷119。第7册,页2867。)在朱子哲学中,心不即是性,心的活动要依于性,性是心的主宰。“心之体”即是性。在阳明哲学中,“心之体”也可指性。如阳明说:“心之体,性也。”(《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页33。)又说:“性是心之体。”(同上,页5。)但是,由于阳明主张“心即理”、“心即性、性即理”(同上,页15。),则心之主宰便是心之自我主宰,也即良知。第二种用法,即“心之体”指心之自体。朱子说:“此心之体,寂然不动,如镜之空,如衡之平,何不得其正之有?”(《朱子语类》卷18。第2册,页423,朱子门人转述《大学或问》中语。)其意为:心的本然状态是清明的,能精察理之所在。将此用法纳入阳明哲学中看,“心之自体”即是心之本然之善。其所指之实也落在良知上。如阳明说:“至善者,心之本体。”(《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页97。)“良知者,心之本体。”(《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页61。)这样,“心之体”的前两义在阳明哲学中都落在良知上,其区别无实义。第三种用法指具体的圣贤境界。阳明说:“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页30。)又说:“《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同上,页34。)此种“心之体”的用法与第二种用法是有不同的:第二种用法是抽象地就一切人而言者。说人心的本然状态是清明的或善的,这是从本源上、客观上作的先验肯定,并非是说人心在具体活动上已经真能如此。而第三种用法是就经过一定的工夫历程而复得前两种意义上的“心之体”后的心灵境界而言的。境界是具体的生命感受,是实存的,因而无所谓对其作先验肯定。“廓然大公”、“无有作好、作恶”都是对主观的、具体的心灵境界之情状而下的描述语。前两种用法是自客观上、体上说,第三种用法则自主观上、用上说。角度有别。
由以上分析可知,阳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语中的“心之体”只能有两种意义:一指良知,一指境界。与此相应,此语也当有两解:一是良知无善无恶,一是境界无善无恶。
“良知无善无恶”显然不能取告子解法,只能解为“良知是至善的”。在阳明哲学中,良知虽然属“心”,但又是超越的、纯粹的道德意志和明觉,是判断是非善恶的终极标准。因而,不可以善恶言。良知也是天命之性、形上本体。如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页104。)又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同上,页107。)这与胡五峰把性说成是“天地之所以立”、“天地鬼神之奥”思路一致。良知作为超越的形上本体,也不可以善恶言。阳明明确说过,“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同上,页115。)总之,阳明无善无恶说的第一层意义是以“无善无恶”来遮诠良知本体之“至善”。
境界上的无善无恶,其义为在最高境界中为善无迹、从容中道。由于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因而其“良知者,心之本体”这类说法就不单是一个本体论上的论断,它同时也是工夫指南,具有规范性,即指导、要求人们针对良知本体去做致良知工夫。从实然角度看,经验世界中的个体总有程度不等的气拘物蔽,在生命存在上并不能完全彰显良知本体,而是于本体有程度不等的缺失。欲使本体完全落实,须有复性的工夫。在做工夫的过程中,必须择善固执、为善去恶。待工夫臻于成熟时,心之本体完全恢复,实然之心纯化为良知本体。随之,主观境界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境界中,心的活动纯善无恶。既无恶可对,则善名也无以立,结果是善恶双泯,故称“无善无恶”。由于无善无恶境界中,心体毫无执著,随感而应,随感而化,故又可称此境界为“虚”的境界。这层意义上的“无善无恶”与第一层意义上的遮诠有不同:遮诠终究是对超越本体的一种特殊肯定,而就境界说“无善无恶”时,并无肯定之义,也无所谓超越问题;“无善无恶”纯然是对心灵状态的描述。这种描述语也可换为其他说法,如“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心所欲不逾矩”等等。
在无善无恶说的两层含义中,后一种,即自境界而言的无善无恶当是阳明的主要意思。[3]王龙溪在“四句教”的基础上提出“四无”说,使境界上的无善无恶说更为明朗。龙溪说:
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页117。)[4]
龙溪的“四无”,只能是境界上的“无”,不能解为对本体“至善”的遮诠。因为龙溪是将心体的无善无恶与意、知、物的无善无恶一体平视的。“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这句话即是明显的证据。意属经验层,其有善有恶并不能影响到作为超越本体的心的无善无恶(至善)。然而,若从境界上说,意有善有恶,则心须对不善之意加以对治;要对治,便不能不思不虑而从容中道。这样一来,心便从无善无恶之境上滑了下来。
龙溪主顿悟。顿悟后,意之发动纯善无恶,意所在之物也无不正,知也无善恶可知,心也无所对治。心、意、知、物皆纯善无恶,则善也不立,全是天理之如如呈现。这便是“四无”。[5]其实,在最高境界中,心、意、知、物一体而化,并无四者名目可指,故“四无”实即一“无”。龙溪只是顺着“四句教”的句式说而已。若单就境界而论,“四无”说并无不是,且很能描绘出透悟本体后儒者境界之实相。阳明对“四无”说并未否定,且颇有赞赏之意,故也可视为阳明本人的思想。[6]
综上所论,王学中的无善无恶说非告子“性无分于善不善”之义。其本义一为对本体至善的遮诠,一为对化境的描述。若紧扣此两义而不滑转,即可发现蕺山也有王学意义上的无善无恶思想。
二蕺山论本体无善无恶
蕺山认为超越本体是无善无恶的。他说:
后之言《大学》者曰“无善无恶心之体”,盖云善本不与恶对耳。然无对之善即是至善;有善可止,便非无善。其所云心体是“人生而静”以上之体。此处不容说,说有说无皆不得。《大学》言“止至善”是工夫边事,非专言心体也。必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乎!(《大学古记约义》,《刘子全书》卷38,页6。《刘子全书》以下简称《全书》。)
此语出自《大学古记约义》。成此书时,蕺山思想尚处于尊信阳明学阶段[7],故其所说“心体”也当指良知而言。“后之言《大学》者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显然是指“四句教”中的第一句。蕺山认为,“心之体”作为超越的本体,是“人生而静”以上的性体,“说有说无皆不得”。这与明道“才说性便亦不是性”之义相同。为强调本体不可以善恶言,蕺山认为《大学》“止于至善”一语是就工夫而言的,并非专言本体。意即“止于至善”只是为设立工夫而权称本体为“至善”;若就本体自身而言,说“无声无臭”方最恰当。“无声无臭”是对超越本体的遮诠,其义与阳明无善无恶说的第一层含义相当。
五十九岁时,蕺山提出“意者心之所存非所发”的主张(《学言》上,《全书》卷10,页26。按:蕺山《学言》有上、中、下三卷,分载于《全书》卷10、11、12,以下只注明《学言》卷次和页码。),创立诚意学体系。在诚意学中,“意”转而成为本体,其地位相当于阳明的良知。此时,蕺山又转而就“意”说无善无恶。他说:
意无所为(谓)善恶,但好善恶恶而已。(同上。)
心无善恶,而一点独知知善知恶。知善知恶之知,即是好善恶恶之意。好善恶恶之意,即是无善无恶之体。此之谓无极而太极。(《学言》中,页6。)
意是心之体,是超越感性经验的纯粹道德意志,故能好善恶恶。意之好恶并非盲目的,其自身具有辨别善恶的能力,故能知善知恶。既然意是好善恶恶的纯粹道德意志、知善知恶的明觉之体,所以其自身不受善、恶的限定。因而是无善无恶的。正如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之于推理,推理有正误,而推理能力则无所谓正误。[8]意之于善恶亦复如是。蕺山所说“心无善恶”一语,其实是说“心之体”无善无恶,也即意无善无恶之义。他并借濂溪“无极而太极”一语来表明“意无善无恶是至善”之义。《人谱》是蕺山反复改订过的精心之作。此书说:“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又说:“万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无善也。”(并见《人谱》,《全书》卷1,页2。)于此可见,无善无恶的确是蕺山的真实思想。
既然蕺山认为性体是无善无恶的,则其不惬意于孟子性善说是很自然的。他说:
孟子道性善,盖为纷纷时人解嘲,以挽异端之流弊,其旨可为严切。然他日立言,并未轻惹一善字。“人性之善也”一语稍执,亦承告子之言而破之。(《学言》下,页27。)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此言似之而非也。夫性无性也,况可以善恶言?然则性善之说盖为时人下药云。(《原旨×原性》,《全书》卷7,页1。)
告子的无善无恶说把性当作中性的自然材质,从儒家立场看,这根本是不识性。“似之而非”:只是表面言词上相似,其实质内容与儒家无善无恶说根本不同。孟子针对告子的发难而道性善,可堵住自然主义的流荡,故称“其旨可为严切”。但蕺山又认为,以善说性,于性之超越义有碍。“性无性”,不可以善恶言。所以,又认为孟子“人性之善也”一语稍执。也即:蕺山认为孟子道性善只是为时人“解嘲”、“下药”的权说。若称理而谈,则当说“性无善无恶”。他并认为孟子“他日立言并未轻惹一善字”便是佐证。就此点看,蕺山与五峰看法一致。
蕺山对孟子道性善的理据的解说未必切合孟子本怀,但可以从中反显出蕺山是主张性无善无恶的。蕺山又说:
子思子从喜怒哀乐之中和指点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即在其中,分明一元流行气象。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全不涉人分上。此言性第一义也。至孟子,因当时言性纷纷,不得不以善字标宗旨,单向心地觉处指点出粹然至善之理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全是人道边事,最有功于学者。虽四者之心未始非喜怒哀乐所化,然已落面目一班,直指之为仁义礼智名色,去“人生而静”之体远矣。(《证学杂解》十九,《全书》卷6,页9。)
蕺山对《中庸》“喜怒哀乐”的看法很特别。与以前儒者不同,他不把四者看成是人的感性心理,而是直视之为天命之性的内容,与仁义礼智同质。他明确说过:“喜怒哀乐中,便是仁义礼智信。”(《学言》下,页21。)儒者一般承《易传》“元者善之长也”这一说法,以“元”来代称仁。因此,蕺山“分明一元流行气象”一语当指生生不已、润物不息之仁体而言。也即,指的是天命流行之体、天命之性,非指宇宙论意义上的自然气机之流行。明乎此,则蕺山这段话便不难索解。
与前面一样,蕺山仍是先称道孟子道性善“最有功于学者”;但又认为,以“四端”指点性善,性体便落“面目”,不能保住天命流行之体应有的超越崇高义,所谓“去人生而静以上远矣”。因而,蕺山认为性善论非言性之第一义。第一义当如《中庸》那样,从“不识不知”处、“全不涉人分上”去理会。以善字标宗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便说法,正宗的说法当是无声无臭、无善无恶。
以上所论表明,蕺山思想中具有阳明无善无恶说的第一层含义,即以无善无恶遮诠本体之至善。下面再论其境界上的无善无恶思想,即阳明无善无恶说的第二层含义。
三蕺山之境界上的无善无恶思想
蕺山认为虚无之境非释、道两家专有者。他批评朱子“将吾道中静定虚无之说,一并归之禅门,惟恐一托足焉”。(《与王右仲问答》,《全书》卷9,页8。)一般说来,在宋儒中,濂溪和明道是最能体现“无”的境界的儒者,后人多议其杂禅。而蕺山断之曰:“儒而不杂者,自周程而后,吾见亦罕矣。”(《学言》下,页17。)或疑阳明是禅,而蕺山折之曰:“文成似禅非禅。”(《与王右仲问答》,《全书》卷9,页8。)蕺山甚至认为只有儒者才能真正具有“无”的境界。如他认为“虚无空寂吾儒所有而二氏不能有”这样的判断是“勘到语”。(同上,页9。)又说禅家是“窃吾儒之说之精者以文奸”。(同上。)此类说法当然不确,但从中可以看出蕺山是坚持认为儒者具有虚无之境的。
“意”在蕺山哲学中具有根本地位。他说:“意根最微,诚体本天。”(《学言》下,页18。)又说:“心之主宰曰意,故意为心本。”(《学言》下,页13。)因而,蕺山反复强调诚意是根本工夫,说“诚意一关为《大学》全经枢纽”。(《学言》下,页16。)意之根本特性是好善恶恶。蕺山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盖言独体之好恶也。原来只是自好自恶,故欺曰‘自欺’,谦曰‘自谦’。既自好自恶,则好在善,即恶在不善;恶在不善,即好在善。故好恶虽两,意而一几。”(《学言》下,页8~9。)“独体”即指意,是纯粹的道德意志,其见善必好,见恶必恶,恰是其至善之表现。蕺山还说:“意还其意之谓诚。”(《学言》下,页8。)也即诚意便是如其意之好恶而好恶之,也就是择善固执、为善去恶的意思。
可见,在做诚意工夫时,要着实去辨别善恶、为善去恶。但是,当诚意工夫臻于极致时,不需勉力而意自然能作主宰,不必有意去诚意而意自诚。这便是“无意”的境界。诚意是辨别善恶、为善去恶;既无意,则亦无所谓诚意、无所谓为善去恶了。因此,“无意”之境即是无善无恶之境。蕺山说:“其实诚意则无意,无意则无心。”(《商疑十则》,《全书》卷9,页19。)意即:诚意工夫纯熟后,便达至“无意”、“无心”的自由境界了。蕺山还借《论语》“子绝四”一节阐发其无善无恶思想。他说:
意与必、固、我相类。因无主宰心,故无执定心,故无住著心,故无私吝心。合之见圣心之妙。(同上。)
朱子将“毋意”之意解作“私意”,而蕺山将其解为正面意义的“心之主宰”,说:“毕竟意中本非有私也。有意而毋意,所谓有主而无主也。”(同上。)“毋”作为禁止词,本与“无”有别,但可通用。[9]即使强调其意义上的分别,但由于蕺山把“意”当成正面意义的主宰心,则“毋意”即化去主宰心之义,与“无意”的含义也通而为一。上段话中,蕺山正是把“毋意”解为“无主宰心”的。蕺山所说之“无”显然是指境界上的无善无恶。单就境界而论,蕺山所说“无主宰心”、“无执定心”、“无住著心”与《坛经》所言“无念”、“无相”、“无住”是很难区别的。蕺山又说:
子绝四,首云“毋意”。圣人心同太虚,一疵不存,了无端倪可窥,即就其存主处亦化而不有,大抵归之神明不测而已。(《学言》中,页16~17。)
“存主处亦化而不有”,即是“无意”,即是“心同太虚”的虚无境界。“了无端倪可窥”,即是境界上的无善无恶。龙溪说:“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天泉证道记》,《王龙溪先生全集》卷1,页1。清光绪间翻刻明本。)此四语可用作蕺山此处所说“神明不测”四字的最佳注脚。下面一段文字更能反映出蕺山的无善无恶思想:
知其为善而为之,为之也必尽,则亦无善可习矣。无善可习,反之吾性之初,本无善可习也。知其为恶而去之,去之也必尽,则亦无恶可习矣。无恶可习,反之吾性之初,本无恶可习也。此之谓浑然至善,依然人生之初,而复性之能事毕矣。(《习说》,《全书》卷8。)
“反之吾性之初,本无善可习”,“反之吾性之初,本无恶可习”,这是说人之本性是至善的,不受经验中的善恶的封限,这是无善无恶说之第一层意义。“为之也必尽,则亦无善可习矣”,“去之也必尽,则亦无恶可习矣”,这是说“人生之初”在生命实存上的彰显,是“复性之能事毕矣”之后的境界。这是无善无恶说之第二层意义。
下面两轮问答将境界上的无善无恶表白得淋漓尽致:
问:心有无意时否?
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著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然定盘针与盘子终是两物,意之于心,只是虚体中一点精神,仍只是一个心。本非滞于有也,安得而云无?(《心意十问》,《全书》卷9,页10~11。)
问:从心不逾,此时属心用事,还属意用事?
此个机缘正是意中真消息。如定盘针在盘子中,随盘子东西南北,此针子只是向南也。圣人学问到此,得净净地,并将盘子打碎,针子抛弃,所以平日用无意工夫,方是至诚如神也。无声无臭,至矣乎!(同上,页12~13。)
前轮问答中,蕺山将意与心的关系比作定盘针与盘子的关系。意是超越的纯粹道德意志和明觉,不滞于经验事物,故说“本非滞于有”。意又是心之所以为心者,并非空无,所以又说“安得而云无?”这是强调意作为心之主宰的重要性,相当于阳明所说“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一语之义。(《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页124。)[10]后轮问答中,语义急转,新意别出。孔子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后通常用以指圣人境界。蕺山此处所说“净净地”即指此。此境界中,动容周旋自然中节,犹如指南针总向南指一样,绝无走失。心体如太虚,心、意皆冥于无声无臭之天理流行中,因而,便谈不上“属心用事还属意用事”了。所以蕺山说“并将盘子打碎,针子抛弃”,颇类禅家棒喝的架式。其实,蕺山所言只是形象说法,强调“无意”境界中不再有任何执著而已。此时不必有意去打盘、抛针,而是盘不打而自碎,针不抛而自弃。进而言之,也无所谓“碎”、“弃”,只是盘、针皆冥于无形无象而已。阳明“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同上。)一语可作蕺山“无意”境界的简明概括。“平日用无意工夫方是至诚如神”,其义为在“净净地”境界中,平日所用工夫都是出于无意的,也即为善无迹之义。其实,在“净净地”说“工夫”只是方便说法。此时并不需要什麽特别工夫,也无本体、工夫可分。用蕺山自己的话说,“此中自著不得一毫思虑,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思而无所思,虑而无所虑。”(《与门人祝开美问答》,《全书》卷9,页20。)蕺山说:“学始于思,而达于不思而得。”(《学言》上,页18。)因而,“净净地”非凭空而来者,而是思诚工夫纯熟后致得的。所以说“此个机缘正是意中真消息”。“真消息”即指无善无恶之妙境。所差只是“无善无恶”这样的字面而已。
此种“打盘”、“抛针”的“净净地”指的是无善无恶之境,显而易见。[11]这种境界之“无”与本体论上的“存有”之“有”毫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有此“有”,方有是“无”;有是“无”,方能尽此“有”。“有”就本体而言,“无”就作用、境界而言;“有”与“无”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常人不免滞与“有”[12],而释、道中人又不免沦于“无”。所以蕺山申论道:
此个主宰(本文按:指“意”而言。)要它有,又要它无。惟圣人为能有,亦惟圣人为能无。有而无,无而有,其为天下至妙至妙者乎!(《心意十问》,《全书》卷9,页13。)
蕺山之意并非说常人绝对不能“有”,绝对不能“无”;而是说常人不能尽“有”之全,不能尽“无”之极。“有”、“无”之间不免有程度不等的紧张。而圣人可将“有”、“无”之对立辩证地统一起来,使“有”、“无”泯合无间,即“有”即“无”,即“无”即“有”。蕺山认为这是“天下至妙至妙者”。阳明曾说:“有而未尝有,是真有也;无而未尝无,是真无也。”(《见斋说》,《王阳明全集》卷7,页262。)蕺山所言与阳明之意若合符节。
有、无双泯,则心中“些子”不留,所以蕺山说:
本体只是这些子,工夫只是这些子。并这些子仍不得分此为本体,彼为工夫。既无本体工夫可分,则亦并无这些子可指。故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学言》上,页36。)
“这些子”实指蕺山常语及的“心中这一点生意”。(《学言》上,页29。)蕺山并认为,“生意之意,即是心之意”。(《学言》下,页30。)意是心之主宰,因而意是本体;意好善恶恶,诚意工夫不外乎如其意之好恶而好恶之,因而意也是工夫。所以,蕺山说本体、工夫都不过是“这些子”。不明说“意”而转说“这些子”,是因为在无善无恶境界中,意藏体于寂,不显主宰的痕迹,无相状可指,不得已而强指点之曰“这些子”。即如此指点,也落言诠了。因为,实在“并无这些子可指”,必用“无声无臭”遮诠之方庶几近之。心中“些子”不留,则虚而无滞,妙应无方。所以蕺山说:
虚者,心之体。(《周易古文抄》,《咸》卦大《象》注。《全书》卷33,页2。)
“天下之道,感应而已矣。”随感而应,随感而忘者,圣人也。(《学言》下,页1。)
圣人之心,如空中楼阁,中通外辟,八面玲珑。一气往来,周极世界。天地之体皆我之体,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只是一个虚而已。(《学言》下,页24。)
在此虚圆不测之境中,用蕺山自己的话说,“人心浑然一天体”,(《学言》中,页5。)“不是我不可须臾离道,直是道不能须臾离我”。(《学言》中,页22。)一切皆遁于无形,故蕺山又说:
心与理一,则心无形;理与事一,则理无形;事与境一,则事无形;境与时一,则境无形。无形之道,至矣乎!吾强而名之曰“太虚”。(《学言》中,页18。)
心、理、事、境皆无形,则冲漠无朕,廓尔忘言,更有何是非可分、何善恶之辨?故蕺山又说:
程子曰“无妄之谓诚”——无妄亦无诚。(《学言》上,页17。)
“性即理也”——理无定理,理亦无理。(《学言》中,页12。)
无妄之天理,是本体上之存有。但是,待“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时,则也无诚可言、无理可指。这是境界之“无”。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一诗句差可比况此中意思:“真意”可指无妄之天理,“忘言”可指“无诚”、“无理”之境界。
儒家讲虚、无,只就境界言。蕺山说:“禹治水,是极大事功,只是行所无事而已。”(《学言》上,页21。)[13]“行所无事”,并非无所事事。这是儒家与释、道的不同处。然单就境界论,又与彼家相通。蕺山尝用《庄子》中颜回坐忘的寓言来比拟儒家无善无恶的虚无之境,称“庄子寓言,亦表其实”。(《周易古文抄》,《益》卦六二爻注。《全书》卷33,页24。)玄学家以无为本,蕺山也仿其语形容儒者境界,说“非惟得意而忘言,抑亦冥心而忘象,则君子体道之极功也”。(《周易古文抄》,《系辞》注语。《全书》卷34,页19。)周海门曾说:“维世范俗,以为善去恶为堤防。而尽性知天,必无善无恶为究竟。无善无恶,即为善去恶而无迹;而为善去恶,悟无善无恶而始真。教本相通不相悖,语可相济难相非。”(《九解》,《明儒学案》卷36。《黄宗羲全集》第8册,页122。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下同。)蕺山所言与海门之说可谓后先呼应,别无二致。
无善无恶之境是心灵获得自由的境界,因而也是乐的境界。有人疑蕺山“拘谨”,或悯其“太清苦”,[14]其实,蕺山也有洒落、乐易的一面。他称道王心斋的《乐学歌》颇足发明孔颜之乐(参《学言》上,页13。),并自道学中之乐说:“一日二日不放过,即此一日二日便是圣人。以此积累渐深,不忍抛弃前功,自然歇手不得。明无人非,幽无鬼责。达则共由,穷则独善。何等浩落,何等坦荡!虽有至乐,弗与易也。(《师说》,《祝月隐先生遗集》卷4,页13。《适园丛书》本。下同。)他描绘学臻于成时的从容气象说:“优焉游焉,弗劳以扰也;餍焉饫焉,弗艰以苦也。瞬存而息养,人尽而天随,日有孳孳,不知年岁之不足也。”(《证学杂解》二十一,《全书》卷6,页10。)可见,蕺山对深湛无待的境界之乐感受极切。心无挂碍,自然洒落。晚年在致其高弟祝开美的信中说:“静观造物之妙,化育流行,傍花随柳,惟我适意而已。”(《答开美四》,《全书》卷19,页56。)这煞有风沂舞雩的曾点气象。
蕺山一方面反复指点无善无恶之境,也不讳言境界之乐;一方面又强调工夫纯熟后方有此境。他说:“学焉而后不学之知无不知,虑焉而后不虑之能无不能。”(《学言》上,页2。)又说:“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必由择执纯熟来,才有此意。”(《师说》,《祝月隐先生遗集》卷4,页15。)否则,即是“绝类离群,妄希神化”。(《周易古文抄》,《升》卦六五爻注。《全书》卷33,页32。)《刘子全书》中讲戒慎恐惧的慎独工夫最为精切详备,这样,蕺山就在强调下学与指点上达之间保持了合理的平衡,所以虽言无善无恶,但无虚荡之嫌。这是他与龙溪等人的真正分歧所在。
蕺山个人的为学历程,便是其思想的最好见证。其子刘汋说:“先君子盛年用工,过于严毅。平居斋庄端肃,见之者不寒而栗。及晚年,造履益醇,涵养益粹,又如坐春风中,不觉浃于肌肤之深也。”(《年谱》下,《全书》卷40下,页51~52。)蕺山晚年所造,实已逼近无善无恶之境。绝粒之际,“胸中浑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同上,页48。)其《绝命辞》也颇能透显此中消息:“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亦何易。”(同上,页47。)致命遂志,何等慷慨,何等艰难!然蕺山蹈之,从容流易,如“了我平生事”一般。近世章太炎也认为蕺山所造已接近“无我”之境。(参《与徐仲荪书》,《文献》1993年第1期。)而黄梨洲称其师“从严毅清苦之中,发为光风霁月”,可谓点睛之语。(《行状》,《全书》卷39,页36。)
四不可因蕺山有指摘无善无恶的言论便否认其有无善无恶思想之实
上文根据阳明无善无恶说的本义,对蕺山思想进行了考察,发现蕺山的确具有阳明意义上的无善无恶思想。但是,众所周知,蕺山也发过不少批评无善无恶之说的言论。如何看待此问题,是深入了解蕺山思想的关键之一。
明代后期,王学末流之弊在浙东表现得尤为明显。或离笃实践履而希羡妙境,或不事消欲而冒认自然。阳明以良知教挽圣学于词章训诂之中,蕺山称其“一时唤醒沉迷,如长夜之旦”。(《证学杂解》二十五,《全书》卷6,页13。)但同时又对其末流之弊痛惜不已,说:“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同上,页14。)黄梨洲也说:“风俗颓弊,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不复知有忠义名节之可贵。”(《行状》,《全书》卷39,页45。)这真的是“无善无恶”了。于是有东林之学,起而排之,并疑阳明“以无善无恶,扫却为善去恶矣”[15],认为末流之弊是阳明无善无恶说导致的结果。当时之大儒如许敬菴、冯少墟等也龈龈辨之不遗余力。蕺山与东林人士过从颇密,并师许敬菴、友冯少墟。处在此种现实背景下,蕺山难免会对无善无恶这样的说法产生某种忌讳,以致非难。并进而牵及阳明,怀疑末流之弊“亦新建之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有以启之”。(《行状》,《全书》卷39,页39。)加之“无善无恶”一语不止有一层含义——既可解为对道德价值之否定,如告子之说;也可解为对性体至善之肯定,如五峰之说;还可解为道德践履纯熟后心体妙用之无滞,如龙溪、海门之说——的确易启争议。因而,如果出现既主张无善无恶,同时又反对无善无恶这种情况——主张此种意义上的无善无恶,反对彼种意义上的无善无恶——也就并非不可思议了。
蕺山的情形正是如此。王学末流“不分是非,不辨曲直”,把阳明的无善无恶说抹上一层不光彩的色调,使得在阳明那里本来是胜义的“无善无恶”滑转为劣义的无善无恶,甚至使此说成了放僻邪逸、恣意妄为的理论依据。蕺山对此深恶痛绝,于是在现实刺激下发了一些指摘无善无恶说的言论。但是,由于蕺山的诚意学与阳明的良知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蕺山是造诣深微的儒者,对阳明无善无恶说的实质内容、本然之义理,不可能无所心得,因而,虽然有批评,但其思想中又有阳明无善无恶说之实。不过,蕺山因痛恨末流之弊而牵连到阳明无善无恶说,对其加以指摘,这便有“择焉而不精”之嫌。阳明当时若避开易启争议的“无善无恶”这一字面,改用其他语辞来表达同一意思,比如说,改用蕺山自己常用的“不思不虑”、“虚”、“无”这些词句,也许会更好些(其实并不见得好多少),但不能因此就可以保证末流之弊不再出现。下面即对蕺山指摘无善无恶说的具有代表性的言论作一分析,以见其指摘未能切中阳明的本义。
蕺山说:
心可言无善无恶,而以正还心,则心之有善可知。意可言有善有恶,而以诚还意,则意之无恶可知。“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以为桮棬也?”(《学言》下,页9。)
这段话中,蕺山显然把阳明的无善无恶误解为告子的无善无恶了。告子把性比作杞柳,把仁义之善比作桮棬,认为人性中本无仁义之善,犹如杞柳本非桮棬一样。孟子反诘之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今蕺山举孟子辟告子之语转而对准阳明,显然文不对题。因为,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不论是指“良知至善”也好,还是指“为善无迹”也好,均与告子“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之意大相径庭。
蕺山说:
王门倡无善无恶之说,终于“至善”二字有碍。解者曰:无善无恶,斯为至善。无乃多此一重之绕乎?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无善”之善,古人未之及也。即阳明先生亦偶一言之,而后人奉以为圣书,无乃过与?(《学言》下,页6。)
蕺山此处所辩也欠恰当。“有善”之善是经验中与恶相对的善,“无善”之善是超越无对的本体之善。对本体用“无善无恶”遮诠之方恰当。即使改用“至善”以言之,也是为了表示两种层次不同的善的区别。当然,依“体用一源”之理,本体之善与经验中的善,从根本上讲,的确可说是“一善”。但在解说义理时,仍需把握其分际。因而,“多此一重之绕”不仅不为过,而且是义理之实所要求的。“后人奉以为圣书”,这可能是蕺山不满“无善无恶”之说的真正原因。末流不做为善去恶的工夫,而奢谈无善无恶,流弊丛生,的确可忧。但总不能因流弊而放弃义理之当然。其实,当就义理本身而言时,蕺山是极力主张无善无恶的。《人谱》开篇一句就是“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这与“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实无区别[16]。而且,当有人怀疑此句话中的“无善”二字不当时,蕺山还郑重地解释说:
人心止有好恶一机(《明儒学案》作“几”。),好便好善,恶便恶不善,正见人性之善。若说心有个善,吾从而好之;有个不善,吾从而恶之,则千头万绪,其为矫揉也多矣。且谓好恶者心乎?善恶者心乎?识者当辨之。(《会录》,《全书》卷13,页27。《明儒学案》卷62《蕺山学案》中也有载。)
“好恶者心乎?善恶者心乎?”意即心之体不可以善恶言,是无善无恶的[17]。《人谱》是蕺山临没前不久尚在改订的精心之作,于此可见,当蕺山撇开现实的纠葛称理而谈时,是坚持无善无恶之说的。只是当面对当境的周遭学风时,末流之弊更具切肤之感,笼罩了他的头脑,因而有感而发了一些批评无善无恶的言论。
蕺山又说:
先生(本文案:指阳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体”。又曰“至善只是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录》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时言“无善无恶者理之静”,亦未曾径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本文按:黄梨洲引作“何处起”。见《刘子全书》卷39所载黄撰《行状》。下同。)?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来(梨洲引作“何处用”。)?无乃语语绝流断港(梨洲引“港”下有“乎”字。)?快哉!“四无”之论,先生当于何处作答?(《阳明先生传信录》三,《刘子全书遗编》卷13,页34。清道光间刻本。也见于《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中。)
此段话是批评龙溪,回护阳明。蕺山认为“四句教”是龙溪自作主张,非阳明本意。蕺山在他处说得更为直接:“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于龙溪。”(《明儒学案》卷首《师说》中论龙溪语。)“四句教”无疑是阳明的思想,即“四无”也并非不是阳明之意,蕺山所说自然不确。此点无须赘论,只论其对“四句教”和“四无”的指摘。
若心体指良知而言,则说心体“无善无恶”,只是表明作为超越本体的良知是“至善”之意。在阳明哲学中,“意”属经验意识,由于感性之作用,发有中节与否之别,其有善有恶与良知之无善无恶并无矛盾。知善知恶之知就是良知本体,不是外铄而有者。良知虽是超越的无善无恶之体,但又内在地具于本心,见善必好,见恶必恶,正是为善去恶之功所用处。并非是“语语绝流断港”。若心体指工夫纯熟或顿悟后的化境,则说心体无善无恶只是表明为善无迹,虚圆不滞。此境界中,意之发动纯善无恶。恶既不存,善也不立,故意也归于无善无恶。意所在之物也无不正,也同样归于无善无恶。既无善恶,则知无所知、知无知相,也同样归于无善无恶。心、意、知、物一体而化,最终归于“四无”。这样,则有善有恶之意无自来,知善知恶之知无自起,为善去恶之功无处用。也非“语语绝流断港”。“四无”之论,阳明也已作答,并非无处作答。不过,阳明将“四无”当作接引“利根人”的教法,也有失当处。因为,“四无”并不成其为“教法”。阳明自己也承认,“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工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页118。)这样,“四无”实际上已失去“教法”的意义。
龙溪之“四无”只是指境界上的“无滞”、“无相”,蕺山斥之为“蹈佛氏之坑堑”、“操戈入室”(《明儒学案》卷首《师说》。),是失当的。龙溪的确有虚荡之嫌,但其病不在“四无”说之提出,而病在将“四无”境界的达成讲得太徒捷、太轻松,对悟本体的工夫强调不够,对工夫的艰难性认识不足。[18]若对“四无“谈不离口”[19],便会启躐等之弊,诱使学者希羡妙境,忽视当下的道德关切,严重的话,便会真地脱离儒家本色,滑向释道。批评龙溪应在此着力,“四无”之说本身并无不是。因为儒者的最后境界与禅家的悟境,在表现上的确有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在根本上无所分别。这一点,蕺山本来是能辨别的。如他说:
心体浑然至善,以其气而言谓之虚,以其理而言谓之无。至虚故能含万象,至无故能造万有。而二氏者,虚而虚之,无而无之。是以蔽于一身之小,而不足以通天下之故;逃于出世之大,而不足以返性命之源,则谓之无善也亦宜。(《学言》中,页5。)
“心体浑然至善”,当解为“心体臻于泯绝一切差别的最高境界”。“浑然”是说无善恶之相,无品类之别。“至善”是指至妙之境而言。在此最高境界中,心体感应无方,遍润无迹,故说“以其气而言谓之虚”。此“气”与前文引及的“圣人之心,如空中楼阁,中通外辟,八面玲珑。一气往来,周极世界”一语中的“气”的含义一样,指心灵的感通。此境中,天理流行而无天理可以执持,随心体之虚而泯于无形,故说“以其理而言谓之无”。但是,这种“虚”、“无”只是就主观境界而言,万物万象仍是实在的存有,所以说“至虚故能含万象,至无故能造万有”。而释道是“虚而虚之”,即虚而不能含万象;“无而无之”,即无而不能造万有。蕺山既明白儒者之虚无与释道之虚无在背景上有不同,便不能因龙溪提出“四无”而目其为禅了。
下面再看蕺山的另一段言论:
阳明先生言“无善无恶者心之体”,原与性无善无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无不善,安得云无?心以气言,气之动有善有不善。而当其藏体于寂之时,独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谓之有善有恶乎?(《学言》中,页6。)
按:在《明儒学案》中,梨洲曾搬用蕺山这一整段话来解“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20]。他还根据蕺山的这一说法来分别蕺山自己的“无善而至善”之说与阳明的“无善无恶”说。他说:“《人谱》谓‘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与阳明先生‘无善无恶者心之体’之语不同。阳明但言寂然不动之时,故下即言‘有善有恶意之动’矣。”(梨洲在《蕺山学案》中的案语。《黄宗羲全集》第8册,页925。)还说:“(阳明)所谓‘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无恶也。”(《明儒学案》卷58论顾泾阳之学处。《黄宗羲全集》第8册,页732~733。)梨洲是承其师蕺山之说,而蕺山又可能是承其师许敬菴之说。因敬菴曾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盖指其未发廓然寂然者而言之。”(《明儒学案》卷36。《黄宗羲全集》第8册,页128。)下面参以梨洲之说,对上面蕺山这段话加以分析。
在这段话中,蕺山又改口说阳明所说与告子之意不同。不过,仍然有误解,只是误解的角度有不同罢了。
蕺山认为,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中的“心”并非指性、理而言,而是指气——心气——而言。或据梨洲所说,指经验心理上的念虑而言。当心气或念虑发动时,有中节不中节、合理不合理之别,因而有善不善之分。但是,当心气或念虑不发动时,则气、念“藏体于寂”——回归于纯粹意识之自体中而不向外表现,因而也就无善恶可见。因其藏而不露、不可见,即说“无善无恶”。梨洲说“无善念恶念耳”,其义即是“无善念恶念可见耳”。他们两人将阳明四句教中的“心”和“意”看成是同性质、同层次的范畴,皆视之为经验心理上的心气、念虑。“心之体”指气、念之寂、不发,“意之动”是气、念因外感而发动。寂则无善恶之念可睹,故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感则有善念恶念可察,故曰“有善有恶意之动”。梨洲“但言寂然不动之时,故下即言‘有善有恶意之动’矣”一语,将此一意思透露得明白无疑。
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在阳明那里,心即理,心即性,心并不以气言。“心之体”既可指复得性、理之全后的境界,也可指良知本体,它就是“性”、就是“理”。它是不动于气的,与意和念的性质不同、层次不同。蕺山和梨洲等而视之,显系误会。阳明论未发、已发,一般也就良知自体言,并无时间上的动静之分。如他曾以扣钟来比喻已发未发,说:“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既扣时也只是寂天寞地。”(《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页115。)阳明有“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之说(《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页29。),但这里的“理之静”与“气之动”是不同层面上的动静。静不与动对,“静”只是形容理之活动绝无偏颇,指“静定”而言,并非时位中的“静”。这种静定之“静”与蕺山所言“藏体于寂”、梨洲所言“寂然不动之时”根本不同。蕺山、梨洲此处虽借用了《系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成话,但所指内容全然不同。在《系辞》中,“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就“天下之至神”的易道言,而蕺山和梨洲在此仅借以指念虑言。也即,一指理言,一指气言。此外,上文蕺山所说“独知湛然”,与其所说“藏体于寂”同义,仅指寂而未发的经验意识,非在阳明那里指良知而言的“独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指摘也好,回护也好,蕺山均未能切中阳明无善无恶说的本义。此类言论是在王学末流之弊的现实刺激和压迫之下有为而发的,并不是就义理而论义理。因此,不可因蕺山有此等言论便遽下结论,认定蕺山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与阳明无善无恶说相悖的。事实恰与此相反,与其师许敬菴和东林派学者之学有不同,蕺山之学性质上属王学,也有王学意义上的无善无恶说,并且相当丰富。就思想实质而言是如此;就表面资料而言,也是信而有征的。
[1]五峰这段话本为《知言》中语,因朱子以为“有病”,遂不见于今传本《知言》正文。但从《朱文公文集》卷73所载《知言疑义》中可考见。
[2]孟子即心言性,并未明确说性是超越的形上本体,因而其讲性善并非“叹美之辞”。此处只取五峰本人对性的看法。
[3]陈来认为“四句教的思想与性之善恶的问题是不相干的”,意即“无善无恶”仅指境界而言。本
文则兼取二义。参《有无之境》页217。人民出版社,1991年。
[4]关于龙溪之“四无”,也可参《龙溪全集》卷1中的《天泉证道记》。
[5]龙溪“四无说”,牟宗三先生剖析最为精详,可参《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一书中的有关章节。
[6]牟宗三先生认为,龙溪讲“四无”,并“非不相应于阳明之义理”。陈来认为阳明“在内心对四无之说更为欣赏”。参《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页267,台北学生书局民国七十九年再版;《有无之境》页203。
[7]蕺山子刘汋说:“先生于阳明之学凡三变:始疑之,中信之,终而辨难不遗余力。”《年谱》下,《全书》卷40下,页24。据《年谱》崇祯十二年(己卯)“古学经成”条下追述,《大学古记约义》成于己巳年。己巳年蕺山五十二岁,尚未自立诚意学。
[8]此说取自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第三卷下册。三民书局增订七版。
[9]蕺山常通用“毋”、“无”二字。除此处外,他处还曾引《礼记》“毋不敬,俨若思”作“无不敬,俨若思”。见《大学杂言》,《全书》卷38,页18。
[10]阳明此语,若纳入蕺山诚意学中观之,可改为“有意俱是实,无意俱是幻”。不过,因意属心,不改也可。下同。
[11]劳思光认为此处“其说欠明”。《中国哲学史》第三卷下册,页596。
[12]与境界上的“无”相应,也当有境界上的“有”。境界上的“有”指道德践履上尚有执着,未臻于无善无恶之化境。本体上的“有”是指对天理的肯定;对本体之“有”有执着,便是“有”的境界。儒者不否认境界上的“有”的价值;相反,境界上的“有”是达成境界上的“无”的必备工夫。王阳明“四句教”之所以称“四有”即以此。
[13]蕺山之说本之《孟子×离娄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之说。
[14]容肇祖在其《明代思想史》中称蕺山之学是明代“拘谨的学者的思想”。牟宗三先生在《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中曾说蕺山之学“太清苦”。
[15]顾泾阳语。见《明儒学案》卷58。《黄宗羲全集》第8册,页752。
[16]黄梨洲认为两者不同,但其辩解失当。详下文。
[17]此可与五峰之说相参。五峰说:“好恶,性也。”而朱子认为,这就是“性无善恶之意”。《知言疑义》,
《胡宏集》附录一,页330。
[18]龙溪并非全然不言工夫,观《龙溪集》卷2中之《滁阳会语》即可见。
[19]许敬菴说:“其后‘四无’之说,龙溪子谈不离口。”见《明儒学案》卷36,《黄宗羲全集》第8册,页129。
[20]见《明儒学案》卷36论周海门之学处。《黄宗羲全集》第8册,页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