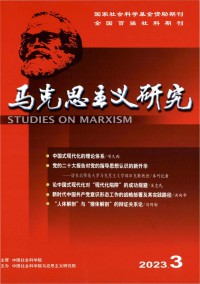马克思辩证法哲学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马克思辩证法哲学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论文关键词:辩证法;本体论承诺;本体论批判;实践批判
论文摘要:辩证法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思维,有其存在的“本体论承诺”。辩证法也就生成于对其“承诺”的“本体”的寻求、批判之中,因而辩证法总是与本体论纠缠在一起的。批判性是辩证法的内在本性,但这一批判本性,决不是一种对事物的简单否定和反驳,而是对其所承诺的“本体”所内含的“矛盾”的反思和批判,正是这一反思和批判,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以人的生存方式为“根本”的实践批判的辩证法的本体论革命。
对于辩证法,可以说一直是哲学史上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基本哲学问题,所以有人把辩证法戏称为“变戏法”,但不管对辩证法作何种理解和解释,其内在固有的否定的批判本性是不变的,这也正是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辩证法的这一批判本性,并不是对事物的简单否定,在其根本涵义上,是对哲学所“承诺”的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最高支撑点的“本体”的反思和批判。
一、辩证法的“本体论承诺”
辩证法作为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是有其存在的理论前提的。不可否认,邓晓芒教授对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存在的两个前提——“语言学起源”和“生存论起源”的揭示和阐释,是很富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语言学起源导致黑格尔辩证法的“逻各斯”主义、理性主义和方法论倾向,生存论起源赋予黑格尔辩证法以“努斯”精神、历史主义和能动的本体论特征。由此可见,辩证法天生就具有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向度。但“语言的逻辑本能恰好是出自于语言中所积淀下的生存论(或目的论)本能”,也就是说,方法论往往又内在地受制于本体论。所以。对此作进一步的追问,我们又可归结出辩证法存在的一个前提——最深层、最根本的前提——本体论前提。而辩证法自古希腊萌芽以来,就一直是与“本体”纠缠在一起的。在这一意义上,阿多诺认为,“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而这种“肯定的东西”,就是辩证法所“承诺”的“本体”。
按照美国当代哲学家蒯因的观点,在讨论本体论问题时,要注意区别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一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前者是关于“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后者则是语言使用中的所谓“本体论的承诺”问题。“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问题,就是按照那个理论有何物存在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本体论本质上不是“何物实际存在”的“事实”问题,而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承诺”问题,根据这一理解,“由于人类意识本性的意向性”,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应的本体论设定和承诺”,而辩证法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论言说,同样蕴含其特有的“本体论承诺”。无论是认定事实上何物存在,还是说何物存在,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最高支撑点的“本体”问题是哲学必须回答的。传统形而上学是在“何物实际存在”的意义上寻求和回答本体的,总是把本体实体化,是一种“实体本体论”。而辩证法却是在“说何物存在”的意义上反思和寻求自己所“承诺”的本体的,总是对本体进行反省和批判,是“承诺的本体论”。所以我们可以说,辩证法实质上是一种“如何”去寻求、反思和批判哲学所“承诺”的本体的理论思维。传统的哲学家们总是把“说何物存在”的“承诺”问题,视为“何物实际存在”的“事实”问题,也就是把自己的“承诺”当作毋庸置疑和不可变更的“独断”,从而走向了非批判的形而上学。而现代本体论的真实意蕴,决不是去独断何物可以作为“本体”,而是“承诺”我们有本体论的“意向性追求”。这样,本体论就由“独断”走向了“承诺”,而与之相应的辩证法也就取代了形而上学,从自发地断言本体,走向了自觉地反思、批判本体。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发生“本体论革命”的实质。
由此可见,辩证法在理论本性上也是一种“本体性”的理论,它与其相应的本体论承诺是内在统一的:“辩证法”是其“本体”所蕴含内容的内在展开,“本体论”是一种被“辩证”地理解了的“本体”;本体论构成了辩证法得以立足和生成自身的载体和依托,辩证法是根植于这一本体而展开的关于这一本体的思想逻辑;辩证法是本体论基础上的辩证法,本体论是一种辩证的本体论。离开其相应的本体论前提,辩证法就失去了其“真理内容”,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依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沦为纯粹形式化的“外延逻辑”和任意化的“概念游戏”,真,正成了“变戏法”。因此说,辩证法在本质上就是“如何”对待“本体”的一种理论思维,它的存在和生成是与其所“承诺”的“本体”密不可分的。
二、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
辩证法与其“本体论承诺”的内在关联性,决定了辩证法的生成即是源于对“本体”的寻求。但对本体的寻求即是矛盾: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所“承诺”的本体及其对本体的理解和解释,都只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而哲学本体论却总是要求最高的权威性和最终的确定性,把自己所承诺的本体视为毋庸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绝对”。因此哲学本体论从其产生开始,就蕴含着两个基本矛盾:其一,哲学本体论指向对人及其思维与世界内在统一的“基本原理”的终极占有和终极解释,力图以这种“基本原理”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永恒的“最高支撑点”;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却总是不断地向这种终极解释提出挑战,动摇它所提供的“最高支撑点”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这就是哲学本体论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其二,哲学本体论以自己所承诺的“本体”或“基本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以自身为根据,从而造成自身无法解脱的解释学循环。因此,哲学家们总是在相互批判中揭露对方的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本体论的解释循环跃迁到高一级层次。这又是哲学本体论的自我矛盾。这样,在对“本体”的寻求过程中,如何对待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本体论从原则上区分为“传统本体论”与“现代本体论”;而与之相应,作为对“本体”所蕴含的内在矛盾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辩证法也就有“自发形态”和“自觉形态”的区别。
古希腊哲学以寻求万物的“本原”、“始基”的方式,开始了对“世界何以可能”的哲学本体的寻求,从而形成了“宇宙本体论”。但古希腊哲学对本体的寻求,基本上是通过直接断言的形式,还是一种直观经验的猜测。不过这些对本原(本体)的“断言”和“猜测”,“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已经“处处、到处都是辩证法的活的胚芽和探索”,从而形成了古希腊时期自发的朴素辩证法。在这一意义上,苏格拉底追求普遍概念的“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确立理念的“通种论”,亚里士多德的“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四因说”,都是追寻“本体”的辩证法。但是,当哲学家们把万物的“本原”、“始基”独立出来并加以绝对化和人格化时,便演化成西方中世纪哲学的“上帝本体论”。在上帝本体论中,“上帝”成了万能的造物主,它既是宇宙的原则,也是人的尺度,人们对上帝只能绝对地信仰和服从。这样,上帝本体论就以“神”的形式,抛弃了辩证法,变成了一神教,在这一时期,古希腊哲学“一切探索、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甚至连自发的朴素辩证法也没有了。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西方哲学在近代实现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也即开始了对“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从表面来看,近代哲学关注的已不再是“本体”问题,而是“认识”问题,并且得出了“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的论断。但从深层来看,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实际上是以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可靠性来保证自己所“承诺”的本体的有效性,在本质上还是对“本体”的寻求和反思。所以说,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既是对本体的寻求过程,也是对本体的反思、批判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离开本体论批判的认识论哲学。其“转向”的根源在于要求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归还给人本身;其“转向”的实质在于把自发的本体论批判和非批判的本体论转向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因此,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把中世纪哲学的非批判的本体论转向本体论批判;二是把古代哲学自发的本体论批判升华为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即对本体论的认识论反省。这种近代水平的对本体论的认识论反省、即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同时也把辩证法理论由自发的形态升华为自觉的形态,并使之获得逻辑学形态的系统表达,从而达到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融为一体的辩证法理论。其最高表现,就是黑格尔所创建的“概念辩证法”体系,但正是在这种通过反省人的认识能力来探索“本体”的近代哲学中,出现了批判的辩证法与非批判的形而上学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对立和冲突。而这一冲突和对立,一方面使被中世纪哲学所抛弃的辩证法得以复苏,并开始逐渐由自发形态走向自觉形态,从而为黑格尔创立完全自觉形态的概念辩证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由于这时自觉的辩证法不具有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使近代哲学对本体的追寻变成了对本体的信仰,自觉形态的辩证法最终让位给非批判的形而上学,造成了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猖獗”。
正是由于西方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猖獗”,使西方近代哲学在批判的辩证法与非批判的形而上学的冲突中,形而上学占了上风。也就是说,西方近代哲学在寻求、反思和批判“本体”的过程中,缺乏应有的自觉辩证法。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是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通过康德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对认识能力加以区分和考察,确立了“先验逻辑”,揭示了“二律背反”,说明了矛盾是人类思维规定的本性,辩证法是理性的必然——“有一种纯粹理性之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与人类理性不可分离之辩证法”,才重新恢复了辩证法的合法地位。而这又直接导向了黑格尔在康德基础上对康德二律背反的批判和超越,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绝对理念”为本体的表达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的自觉形态的“概念辩证法”。对此,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通过一种想把希腊开端处的全部真理都囊括于自身中的思辨辩证法,完成了他对形而上学遗产的异乎寻常的综合。”而这种“综合”,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黑格尔真正实现了辩证法对近代形而上学“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而黑格尔的这种“复辟”,在阿多诺看来,实质上是一种本体论的“纯粹的恐怖”,所以阿多诺甚至有些极端地认为,自己否定的辩证法“在批判本体论时”,“并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甚至一种非本体论的本体论”。而作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的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的辩证法,也正是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在寻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实体本体论”批判而形成的。
三、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批判
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也即实现黑格尔所谓的“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而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是通过运用“把实体了解为主体”的概念的辩证法,构建了“绝对理念”的精神本体论来完成的。“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所以黑格尔强调,“要这样来理解那个理念,使得多种多样的现实,能够被引导到这个作为共相的理念上面,并通过它而被规定,在这个统一性里面被认识”。而黑格尔这一“绝对理念”,既是“实体”也是“主体”,能够自己二元化自己,自己乖离自己,自己发现自己,自己恢复自己,已经超越了康德的不可捉摸的“物自体”。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就是“绝对理念”自我对置、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历史展开过程。对此恩格斯指出:“要知道,当这个黑格尔发现,他借助理性不能得到另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真正的上帝时,他是多么为理性而感到自豪,以致他干脆宣布理性为上帝。”但黑格尔宣布理性为上帝。决不是理性向中世纪上帝的回归,在这里,代替上帝的理性(精神)本体论,也是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二者在黑格尔哲学的逻辑里是统一的。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精神本体论,只是对世界作了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人及其实践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不具有真正的自主性和现实性。所以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经过一切矛盾和差异化重又建立同一性”,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仍保留着“本体论上的自我驯服”,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而马克思则认为它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只是达到了辩证法的形式的自足,仍然是“头足倒置”的,还必须对其进行批判和拯救。
其实,早在马克思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费尔巴哈就以他的“人本学本体论”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精神本体论”进行过批判,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关于人、自然、社会等为理念所建立的学说,只是用理性的说法来表达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物质实体为非物质的、亦即抽象的实体所创造的神学学说,所以“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而在黑格尔的这种理性神学中,人的本质被“异化”了。因此,应该对黑格尔哲学加以“颠倒”,不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而是把“主体理解为实体”,破除人在宗教神学中的自我异化,颠倒人与精神的关系,把人的本质还给人,确立感性存在的人与自然的本原地位,遗憾的是,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话,不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实践性。人虽然获得了本原地位,但并未表现出作为现实主体的丰富性与能动性,人仍然是抽象的“无人身的感性”。费尔巴哈只不过是用抽象的“人和自然”取代了同样抽象的“绝对理念”。所以,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实际上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都是从一个抽象的“实体”出发,都以“还原”的方式把世界归结为一种实体性本质,都在建构一种“实体本体论”,都是一种传统的本体论思维,只不过费尔巴哈重“直观”,而黑格尔重“思辨”而已。这样,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本体论同样需要批判和超越。而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哲学的出发点,则奠定了马克思实践批判的辩证法的坚实基础。
正因如此,马克思展开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双重批判与超越:既是借鉴费尔巴哈来批判黑格尔,也是运用黑格尔来超越费尔巴哈。当时,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质就是“个人”受“抽象”(资本逻辑)统治。而其导致的结果就是“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所以马克思要做的就是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而这实质上就是确立“人”作为主体(本体)的合法地位,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在马克思眼里,人自由解放的“根本”就在“人本身”。而这里作为“根本”的“人本身”,既不是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无人身的感性”,而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强调: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作为根本的人本身的“人”,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的制约:“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正是如此,我们说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和论证了“人本身”的真正本质及其作为“根本”的合法性:“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可以说,马克思在这里所揭示的是“人本身”的特殊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实践是人的本源性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也是人作为“根本”所构成的人特有的“历史”的辩证法——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它表达了“人本身”作为“根本”的真实内涵。这种“历史的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的“实践”的本体论,而这只有以“人本身”作为历史的“根本”为前提才成为可能。在这里,马克思真正颠覆和解构了一切先验的、非历史的、非现实的、非具体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本体”:“传统哲学中那种形而上学的逻辑本体论,第一次在这里被宣布为非法的”。无论这种“本体”以什么形式出现(抽象的“精神”或抽象的“人”),只要它还在制造一种外在于人的抽象的主体本质,都是非科学的。正是如此,我们说马克思哲学是以现实的“人本身”为“根本”的“实践批判”的辩证法。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思辨的精神本体论和费尔巴哈直观的人本学本体论,既锻造了具有彻底批判本性的辩证法理论,又以这个革命的、批判的思想武器去批判“现存的一切”,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而为无产阶级及整个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开辟出了一条现实性的道路。所以马克思强调:自己的“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人的恼怒和恐怖”,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精神,其终极旨趣在于批判和否定一切阻碍人的自我发展、妨碍人的生命自由的异化力量,以实现人的不断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所以说,只有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的辩证法,才根本改变了哲学对所“承诺”的本体——“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绝对确定性和至高权威性的逻辑寻求路向,形成了对“本体”的实践性、历史性理解。在马克思这里,实践批判的辩证法不是“实践的本体化”,而是“本体的实践化”,这样,马克思实践批判的辩证法,就是一种以人的本源性生存方式和生命活动为“本体”的关于人的存在的自我解放学说;而马克思的本体论也就是运用实践批判对资本逻辑统治人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加以批判的“否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本体论与辩证法才真正实现了在瓦解资本逻辑的内在过程中的否定性的统一。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阿多诺作为“瓦解的逻辑”的“否定的辩证法”、海德格尔的“生存本体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话”、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德里达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和“延异”,以及罗蒂的“偶然”与“反讽”等所谓后现代脉动。其实都是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的内在意蕴的时代显现。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