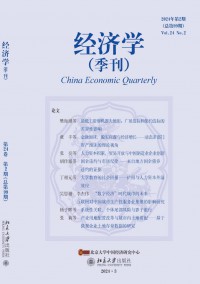经济学关键词管理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经济学关键词管理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在《经济原理》开篇中说,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极其繁多,但是只有两种力量是最持久和最普遍发生作用的。其一是宗教的力量。其二,是经济的力量。他是经济学可数的几个父亲之一,我念书的时候总想读他的原著却总也没有时间好好读。现代“工业生产式”教育体系的悖论之一是学生匆匆忙忙读最晚近的文献,揣摩老师要考的题目,拿到找工作必须的文凭,到头来对其所学茫然.香港是个忙碌着挣钱的地方。香港大学是为香港政府和商界生产文凭的地方。我常常对教室里学生身上突然发出的传呼机或手提电话的尖叫感到茫然,先是觉得有些伤心,觉得费好大的心力备课不那么值得。然而这是香港,在港大就读的大学生通常已经可以凭兼职挣到七八千港币一个月了,硕士研究生在大学里兼职可挣一万五千以上,而我的研究项目里有个博士生,按照学校规定我必须付给他两万一千元港币一个月的薪酬。即使这样也很难找到合格的研究助理。学生们喜欢穿和玩儿,挣得的钱大都花在这上面。港大的学生常以“走堂”(就是缺课)为荣。学得特别好的“走堂”,学得不好的,为了“追女”也要显摆一下自学的能力,走走堂,生活内容太丰富,每个人都有太多的选择,把时间搭在听课上就很昂贵了。经济力量真的是最经常起作用的力量。
“成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就谈不上成本。这个道理让经济学家找了至少一百年才找到,这还不算哲学家们在寻找“绝对价值”和“永恒”上面所花的时间。李嘉图被最聪明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好象从月亮上下来的人”,有着极不寻常的思维。尽管如此,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表明他仍然没有找到我们今天普通经济学课本上讲的关于成本的“庸俗”的道理。对永远不变的价值准则的追究毕竟是最具诱惑的一件事,就好象数学家至今还会被“无限”这个概念迷惑得废寝忘食一样。难怪黑格尔说,世界上若有“无限”的话,也只有“恶无限”。相对论以后,事情终于变得好一点,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价值”就因此而死了。找到目前这个“成本”概念并且作了最系统解释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其实并不是经济学家,他们自称是“学者”(scholar),是著名的“维也纳小组”里的学者,恩斯特。马赫、米塞斯、石里克、庞巴沃克、维特根斯坦、哈耶克等等。后三个人甚至还是亲戚。奥地利学派发动了经济学里的所谓“边际革命”,这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一场革命,我想我拿它引出这篇文章的主题,读者不会觉得乏味吧?!
古典经济学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寻找“财富”的来源。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威廉。配第,他说:“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而土地是它的母亲”。他的公式没有提供价值的衡量标准。生产一蒲式耳小麦耗费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还有土地的地力,土地折合成劳动力是多少呢?问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一个苹果加一个梨等于什么一样,得不到解答。李嘉图认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结论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实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连定义也还不十分清楚。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名噪一时的亨利。乔治写了《政治经济科学》,才明确定义了诸如“财富”、“价值”这类名词的经济学涵义。但那是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革命稍后,而且是为了反对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而写的一本书。“价值”的严格定义要等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法国数学家被他的法国导师推荐给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一般均衡”理论研究时才得到解决。这三个人先后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亨利。乔治明确但仍不严格的理论体系中,什么是“财富”?财富就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价值”?一个事物,只要它可以减少人在获取同等幸福时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它就有了价值。这个人能够节约的努力程度就是这件事物的价值。例如某甲允诺某乙在明天做某事,乙于是可以节省自己做该事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甲对乙的承诺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一种财富。当然,在一个言而无信的社会里,承诺的意义和价值就成了大问题,这也就是我在“金融热”(《读书》一九九五年四月)里讨论过的问题。但是甲对乙的承诺在完全不相干的某丙看来有没有价值呢?由于丙不能靠甲的这个承诺减少任何他明天为自己获取与今天同等的幸福的努力,这个承诺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价值。这是主观价值论的开始。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个主观价值论一定是荒谬的。我们怎能否认月亮在我们闭上眼睛的一瞬间就不存在了呢?同样地,我们怎能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以我们主观感受为转移的客观价值呢?我得承认,在贝克莱主教的“月亮”和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思想联系,那就是休谟的怀疑论。这个问题我在《主义与科学》(《读书》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和《传统与乌托邦-永远的徘徊》(《读书》一九九五年三月)里提到过,是理性的哲学基础问题,在这儿就没法多说了。主观价值论大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例如余秋雨写的“天一阁”主人范钦的儿子,面临两个选择,一个继承天一阁全部藏书,一个是继承万两白银。大儿子的选择是天一阁藏书,选择的代价是一万两白银,所谓“机会成本”,放弃的“机会”所值。如果他的选择是万两白银,则选择的机会成本或成本就是天一阁全部藏书的价值。同样的道理,一个中学毕业生如果面临两个选择:上大学,或就业,那么他上大学的成本就是他上学期间所放弃的工作收入的全部所值。类似地,自杀的成本是继续生命所值的全部;活得太痛苦就会想到自杀。可供选择的机会越多,选择一个特定机会的成本就越高,因为所放弃的机会,其所值随着机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港大的文凭随着香港的大学数目增加而贬值,同时,学生的时间随着香港劳工的日益短缺而增值。结果课堂里文静的气氛开始染上手提电话和传呼机的商业紧张。经济学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么个成本概念。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或哲学家(或人们加给他的其他什么家),但不是经济学家。据说他有一次“挤兑”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全部的内容可以在两星期内掌握。我猜他指的是“机会成本”的概念。说实在的,一门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掌握的科学,一定是简练到优美地步的学问,其基本定律一定如此有效以致根本用不到更多的假设和辅助定理,就足以解释整个世界了。如果我是赫赫有名的萨缪尔逊,我绝不会为此去和乔姆斯基辩论。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向经济学看齐,把理论提炼到可以在两星期内让一个清道夫掌握。这正是现代数学的“教父”,大卫。希尔伯特对数学的要求。
主观价值论的一个更深层的看法是,没有选择就谈不上有价值,没有选择余地的“机会”就不应当叫做机会,也谈不上机会成本。“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因此“身世”是没有价值和成本的。社会常以一个人的“身世”来判断其价值,那是因为伴随着他的身世,也许有一笔财富可供支配,而可供支配的财富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可以选择放弃这笔财富。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他“不得不”享受某种幸福,他不会感到“幸福”。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是因为他身不由己。绝望的人不会知道理想和美梦的价值。我曾经感叹北大荒我身边的那些“二劳改”的吃苦精神,却不曾意识到,对他们那没有选择的生活而言,“痛苦”是没有意义的。而我之所以感到了生活的困苦,是因为我还有选择的余地,我至少可以逃回北京。“不自由,毋宁死”。盛洪在他自己书的自序里提到经济学的人文精神,提到经济学不仅是学问,而且是做人的方式,对此我是有充分理由给以支持的。在主观价值论者看来,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当我们提到劳动的价值时,必须指明是谁的劳动,对谁而言的价值,以及价值判断的主体有什么样的选择。如果读者留意,可以发现我在《经济学的关键词》(《读书》一九九五年五月)里谈到分工可以节约劳动时间时,刻意避免使用马克思的“抽象人类劳动时间”。我只使用了具体劳动时间的概念。
基于选择的成本,现代经济学研究选择的“效率”。这个概念是可以直接从选择的成本概念推导出来的。说一个选择是有效率的,是说这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说一组选择有效率,是说这一组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既然是机会成本,就一定是和其他选择或其他组选择比较而言。香港人到“街市”(相当于北京的农贸市场)买海鲜,例如一百元一斤活虾,他们一定要挑个儿大的,因为一斤个儿大的虾比一斤个儿小的虾价值高些,放弃个儿大的虾相当于提高了买虾的机会成本。追求有效率的选择是自利的人的天性,有的人,例如我,从来不挑,买了就走。那不是因为缺少自利心,而是因为一来语言不通,二来时间“金贵”,三来毕竟还不习惯言利,有心理上的折磨,四来也许“面子上”的价值放不下来,全加在一起,讨价还价的机会成本就上去了。
说一组选择是有效率的,是相对于其他组的选择而言,这一组选择所放弃的价值最小,比方说在一顿白吃的午餐上人家告诉你可以随便选择任意数量的虾和梨,只要不超过一百条虾和一百个梨。在正常情况下,你没有胃口可以吃下一百条虾,或一百只梨,你的选择大半是若干条虾和若干只梨。这是有效率的选择,因为如果你非要选择不吃梨而吞下第二十条大虾时,你会发现梨的价值随着你对虾的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你会越来越觉得吃虾的成本太高。这里有一条经济学上的生理学韦伯定律:“单位时间内,一个人所消费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越大,这种物品对这个人而言的价值就越小”。人是生物,生物感觉基于神经,神经受到同等强度的刺激多次就不再感到刺激。神经不再感到刺激生命就嫌乏味,乏味使人追求。微观经济学家直到去年才有人写了篇论文说明这个道理的前半截,这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追求效率的理论。这道理的后半截到现在也还没人说过。总之,有效率的一组选择就是美国一本畅销书里说的,我们从小到大所学的道理之一是“什么都干点儿,什么都别干太多”。林语堂喜欢引李密庵的“半半歌”,记得其开头四行是“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优闲,半里乾坤宽展。”又记得最后四行是“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如此的闲适哲学,正是效率的真义。效率是选择的结果。选择是在可供选择的多个行动方案中择一而行。所以哈耶克的老师冯。米塞斯写了一本书题为《人类行为:一个经济学的论文》(vonMises,HumanAction:ATreatiseonEco-nomics),讲的是人类行为的通论,经济学是捎带着推导出来的。经典名著,可惜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的启蒙老师的著作,国内长期看不到。而在西方,奥地利学派的“中兴”也只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事。这一学派的人物,自二次大战以后“作鸟兽散”,撒的满世界都是,被人们遗忘了。一个行动方案包括三件事:(1)行动的目的,(2)可用的技术,(3)现有的资源。其中“技术”就是以各种方式储存起来的知识(我在《怀着乡愁,寻找家园》,《读书》一九九五年四月,详细说过了)。用大陆时兴的语言来区分技术和资源,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没有硬件的软件就是“无米之炊”。当然,没有软件的硬件只不过是一堆没用的“米”。不论怎样说,软的毕竟是软的,知识一旦被人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因为你知道了一件事以后,你就不可能再选择“不知道这件事”。选择是对未来行动方案的选择,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无法再选择。所以在选择行动方案时,所用可以使用的技术都是没有成本的(还没有买到的技术不是“可用的”)。选择只是对资源和目的的选择。
用上面的例子说明这件事,关于虾和梨的味道,吃法,以及他们可以提供的其他方面的享受,所有这些都是知识,现在已经没有成本。可以选择的是虾和梨的数量,但这是免费午餐,所以虾和梨对你而言也是没有成本的。你在乎的,在这里是稀缺的“资源”的,其实是你的胃口的容量。胃口成了达到你的“自我”(self)的目的的唯一资源,是“自我”目的的手段。于是有效率的选择是:这个容量的若干部分应当用于产生“吃虾的享受”,其余则用于生产“吃梨的享受”。“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嫌纠缠”。说知识没有成本,是说一旦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不知道的知识是要费高昂代价才可获得的。美国为“知识产权”四处与发展中国家打架,当然是为了让人家补偿知识所有者获取知识的代价。在没有分工的时候绝不会有这类的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知识的所有权是分工的产物。分工的好处是节约劳动时间。分工能够节约劳动时间是由于专业化和知识积累。这些我在《经济学的关键词》里说过了。分工越发达,每个人的闲暇时间就越多。可是怎么大家都越来越忙了呢?我这么写的时候,就看着屋角那只一寸见方的巴西龟,它可是不计较时间。《大英百科全书》(儿童版)说:“turtlestaketheirtime”。它不在乎时间一定是因为它天性缓慢呢?还是因为它
道得太少?不管怎样,我觉得我们人类的忙碌首先是因为知道得太多,其次是知道我们还有太多的东西不知道,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的知识使我们意识到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越多。就这句话而言,我想英语一定更清楚同时涵义丰富:“knowingmoreandmoreaboutlessandless”。忙,是因为时间金贵。时间的成本就是选择如何使用时间的成本。分工固然节约了很多时间,可是分工的重大代价是没有人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另一方面,我们一定愿意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因为“知道”就是知道机会的存在。机会越多,选择的空间越大,选择的价值就越高。如果你是人类学家发现的那个非洲土著,觉得吃虾简直匪夷所思(相当于我看人吃白蚁的感觉),你在上面那顿免费午餐里的选择的价值自然因此而大大减低。所以,分工越发达,人们越有动机去知道别人知道的事。上面说的第三点最重要。知识最显著的特点是全部知识的“互补性”,大学生具备小学的知识和中学的知识会学的更好。工程师知道经济学知识可以更有效地设计项目。经济学家知道哲学或心理学,可以成为更好的经济学家。正是由于知识的互补性,当一个学者在单一方向上探索了很远的路程后,会感到有必要在其他相关的(互补的)方向上也往前推进。这个道理在博兰倪看来就是原创性思考所需要的“隐秘的知识”(tacitknowledge),他是指存在的思考者脑海中的不被注意但对思考有潜移默化影响的知识。(见MichaelPolanyi,PersonalKnowledge:TowardsaPost-CriticalPhilosophy,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8)这个英文词直译应为“沉默的知识”。我们知道得越多,凭了知识的互补性,我们知道存在于我们脑海之外的应当被存入脑海的“沉默的知识”也就越多。所以苏格拉底说他只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香港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面临太多的诱惑,因为香港聚集了如此巨大的信息,当然主要是与商业有关的。随便你花一点时间,知道一点商业信息,就可以赚一笔钱。赚一笔钱之后想知道更多的商业信息,赚更多钱。于是你意识到有更多的信息(和赚钱的机会)需要去获取……这样一来,你就专业化了,也就异化了。异化意味着你变成了“它”的奴隶,是“我”之不欲成为“我”而要成为“他我”。为什么自利的人追求效率的结果反倒个个都走专业化的道路呢?不是应当“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吗?这个问题真是对经济学的挑战。就我所知,只有斯坦福大学的老经济学家西多夫斯基写了一本书叫《没有欢乐的经济》试图解答这个问题。(TiborScitovsky,TheJoylessEconom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真正求解还要从社会经济制度中去寻。这也许是《三谈经济学的关键词》的主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