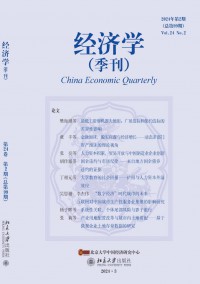经济学道德基础管理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经济学道德基础管理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与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如果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law),来解决日常的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bycase。法官遇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如果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当与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如果他不知道提出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告诉你,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像公民权利是什么意思,法制是什么意思,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在此我们强调的是作为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我们中国人处理问题有不同的影响。当我们处理道德共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什么是自由这个概念。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卢梭当然很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非常羡慕这些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发展到黑格尔极端的状态,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关于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用立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手段,解放你自己的一个手段,这就很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个人所主张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这样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边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非常地想控制别人,你向右边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部分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人是希特勒,大部分人也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分,态度区分非常重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理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from,我避免事情的自由,我不愿意去干扰别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避免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一定会承认他对别人同等的消极自由的责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这里有个度的问题,那么为了维持这个自由的度,你将对其他人的自由负担你的义务,你只有这样按基本的对等原则(道德黄金律)做才能够有你的自由。否则我们之间就是野蛮的、互相杀戳的关系。所以消极的自由态度包含着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你的隐私、小天地(privacy),别人不来干涉你,另一面是别人不来干涉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比如像认为不应该闯入别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别人不干预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别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我们谈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我们迫不得以,非要加入这样一个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承担着对这样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意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的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因为抽象的宪法不能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宪法的政府。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社会的结构——每个人都在服从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如果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如果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承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如果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如果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如果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如果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特殊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研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特殊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特殊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与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认识,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与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与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特殊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特殊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断,理性的判断,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断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断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时代人们所遇到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这样行事,因为这是在特殊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很多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时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很大,例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与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我们又没有,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如果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特殊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与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Benedict)观察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的人为英雄人物的标准,就是大家都服骗术最高的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在目前的时刻,我并不是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一个人来考虑道德问题,但我觉得道德的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处理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发展都很困难了。
很可惜,对目前的状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办法。我在香港除了制度经济学,就一直都是研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制度创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我总用这样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守规则,那你就死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那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这是一种希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我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没有一个人满意,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是我们得到好的制度,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要允许我们自由交往,也许就可以建立规范及道德共识。
但是,现代经济学还不现代,因为它没有思考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现代问题,或上面我们说的现代危机这个问题,我们声称现代只不过是数学用多了点。因此,为了使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必须首先回到古典,处理古典的问题。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正是启蒙时代,正是那时候人们认识了现代危机。所以我们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重新梳理出现代传统,这才可以继续往前走,进入现代。如果缺乏这种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思考现代经济学,我是从存在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来从新写经济分析。实际上我们做的任何一项经济分析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断,我们的价值判断最基本的就是从生存哲学、从生存论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角度,来给出我们的价值判断。在这个判断基础上,才可能有类似效用函数,博弈均衡的选择这些能动的选择,去改变传统、去改变均衡、去进行制度创新,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才现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义考虑进来,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所表现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控制。现代经济学无非做得动态化一些,像最优控制理论,但我们只要问人在哪里的问题,就会发现现在经济学的缺陷。我想中国人如果说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能够继承它并超过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我们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中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