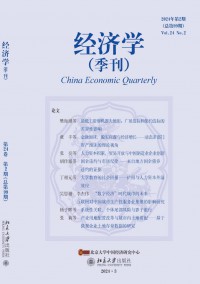经济学文化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经济学文化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