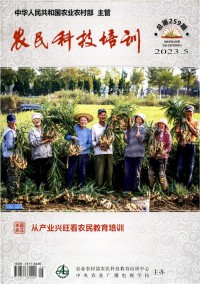农民离村社会经济效应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背景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农民离村社会经济效应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背景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内容提要】本文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背景,概述农民“离村”的社会经济效应,认为,“离村”现象主要是农村经济衰退的产物。农民大量“离村”,对农村经济社会影响至巨:精壮劳动力流失“不仅减削生产力,而且失去优秀人才以为农村改进之基本”;造成耕地撂荒和“有地无粮”现象的严重化。尽管农民离村对农村社会经济不无小补,但总的来看,积极影响微乎其微。
【摘要题】现代社会史研究
【英文摘要】Thearticlegeneralizesthesocialandeconomiceffectsofpeasants"leavinghome"bytaking1920''''sand1930''''sasthebackground.Itthinksthatthephenomenaof"leavinghome"resultedfromtheruraleconomicrecession.Themostpeasants"leavinghome"affecthugelytheruralsocietyandeconomy.Therunningoffofstronglaborsnotonlyweakenedproductiveforces,butlostthefundamentalpowertoimprovetheruraleconomy.Itaggravatedthephenomenaofthelandlyingwasteandtherebeinglandbutnogains.Thoughthepeasants"leavinghome"didalittleusetoruralsocietyandeconomyingeneral,theactiveeffectsareunworthyofmentioning.
【关键词】“离村”/流民/社会经济
"Leavinghome"/Refugee/Socialeconomy
【正文】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如鲁西奇先生的《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王文昌先生的《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彭南生先生的《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以及本人的《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等(注: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光明日报》1993年7月19日。),都作了有益的探讨。但对农民“离村”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尚无专文探究。本文的研究,可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离村”就是农民暂时或永久地离开自己所居住的村落。“离村”情况复杂,流亡、逃难、参军、求学、投亲访友、出嫁、作官等,均在此列,但在“流民的国度”里,“离村”人口中,流民居于绝对多数,正因为如此,人们把“离村率”作为检视流民问题严重程度的一根标尺。农民的“离村运动”,尽管有多种因素的合力驱动,但农村经济的衰退是至关重要的,对此,笔者在《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中作过探讨(注:《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这里拟梳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有关资料,概述农民“离村”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被强制脱离物质生产资料的流民“已普遍于全国的任何穷乡僻壤,并且日益严重化了”(注: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第72页。)。流民问题的严重性,用“离村率”衡量,表现在农民离村人数的明显增加上。根据时人的抽样调查,可以计算出20年代中国农民的离村情况:
表120年代中国农民离村情况表
资料来源: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中译本),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第111~113页;另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6~637页;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第71页。
据上表所示,2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的离村率,从1.44%~8.72%不等,平均为4.61%。历史进入30年代,农民“离村率”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列表如下:
表230年代中国农村离村率表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第173页。
显而易见,“离村率”较之2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份统计资料是综合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几千名分布在各地的报告员的上报材料得出的,虽然未将辽宁、吉林、黑龙江、蒙古、西康、西藏、新疆等地离村情况统计在内,但仍具有普遍意义。据此,22省全家离村的农家数为1920746家,按一家五口计算,则为9603730人,加上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如果一家仅一人离村)3525349人,便大大超过了1000万人,而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农民离村问题之严重,今人瞠目结舌。
对同一地区的“离村率”进行追踪调查,更能显示出流民问题严重性的“动态”。这方面的例子也有很多(注: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其中定县最具有典型意义。根据李景汉的调查,定县历年外流人口有如下表:
表31924~1934年定县历年外流人口统计表1931=100
资料来源:《民间》第1卷第7期;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882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定县历年外流农民有增有减,有升有降,但总的趋势是逐年递增,从1931年起,即扶摇直上,增至1368人,1932年再增至3367人,1933年更增加到7849人,而1934年第一季度农民离村人数竟一跃达到15084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3.771%,为1924~1933年十年中离村人数(18149人)的82%。这个统计令当时社会各界颇感震惊,这是因为,在全国1900多个县中,定县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生存环境比较稳定,更重要的是,它是“平教会”“复兴农村”的实验基地,每年有固定的投资(20万元左右),用于改良农业,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定县作为全国的“模范实验县”,农民离村问题尚且如此严重,其他各县不待言而知,无怪乎有人惊叹,定县“农民离村的高度,一至于此!至于其他贫瘠的西北各省,几年来的天灾人祸,弄得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农民离村的现象,更是报不绝书,大有‘旭日初升,方兴未艾’的感慨!”(注: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第72页。)
二
农民“离村”现象是农村凋敝的产物,农民的大量“逃脱农村”,对农村经济社会影响至巨。在“离村”的农民年龄构成中,青壮年——农村主要劳动力——农业生产的中坚,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根据李景汉的调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年龄构成如下:
表4离村农民年龄结构表
资料来源:《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第76页。
上表大体反映出离村农民年龄构成的基本面貌。从表中不难发现,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另据陈翰笙、刘宣、卜凯的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而年龄在20-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注: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第55~68页;刘宣:《二十四村离村人口分析》,《统计月报》第9号,第10~11页;卜凯:《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金陵大学,1929年,第143页。),流出去的差不多都是农村劳动力的精华,而留在农村的,“不过是老弱无生产力的人们”(注:康诚勋:《经济恐慌下的河北正定县农村》,《新中华》杂志第2卷第16期,第86页。)。这表明,在流民大潮中,精壮劳动力是主流。精壮劳动力的流失,对农业生产影响至巨,“强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谋糊口;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日见摧毁”(注:胡希平:《徐海农村病态的经济观》,《农业周报》第3卷第47期,第994页。)。这对于农村,“不仅减削生产力,而且因此失去优秀人才以为农村改进之基本”(注: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22、23、24号合刊,第98页。)。流民主要是农村经济衰退的产物,流民“逃脱农村”又加速农村经济的衰退,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中,因精壮劳动力流失造成农工缺乏,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记载普遍存在于全国。如“京畿一带以及城内无业贫民虽称众多,但……乡间之农作尤有缺少农工之叹。日前(一九二四年六月间)田间忽得透雨,地皆湿润,农民等以播种谷稼时机已到,于是咸皆雇觅农工,忙于耕种。不料农工竟不敷需要,以致大好良田,因乏工人不能耕种者,为数甚广”(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650页。)。再如河南杞县,“迭遭灾害,无地农民皆就食他方,农工缺乏,概因于此”;虞城县“近几年来,颇感农工缺乏。因兵燹匪患,水旱虫荒,天灾人祸,继续不已。青年壮丁散至四方,奔走生活”(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第68页。);淮北萧县“年来天灾人祸兵匪交乘,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工多视农村工作苦且不安,又常终岁勤苦,不免冻馁,故多另谋出路,……以致农工极感缺乏”(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03~904页。)。
另一方面,有时我们又可以发现农工过剩的情况,这同样是农村经济衰退的反映,如在淮北泗阳县“近三年来感觉农工太多。其原因大多由于前年大水为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一般平民为维持生活计,不是卖地,即是借债,以致多数自耕农及佃户变而为农工,以谋生活”(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第77页。)。农工缺乏,或农工过剩,与农村经济衰退、流民众多互为因果,使农村社会陷于无以自拔的困境。流民的流出与回流呈现出循环流动的状态。这种循环,固然有益于乡村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但对农村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著的,时人注意到,“都市人口或工业化人口,是经常不断地和农村农业人换流动,从而吸收农村精良性质的人口入于工业;又把劣质的人口复返于农村的”(注:汪疑今:《中国近代人口移动之经济的研究——江苏人口移动之一例》,《中国经济》第4卷第5期,第5页。)。下表所列上海某纱厂一年中工人退职情况,或能说明一些问题。
表5上海某纱厂一年中工人退职情况表
资料来源:《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1编,第371页;《中国经济》第4卷第5期,第6页。原表中数字有误,今照录。
从这份抽样资料显示的情况看,因家事、归家、结婚、生产等退职,当然不能谓“劣质人口还于农村”,但以怠慢、成绩不佳、身长不足、淘汰人员、及负伤还诸农村者,“则无疑地是劣质的人口”,仅此几项,即超过了退职总人数的30%。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仍滞留于城市,其余大部分回流,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流出的是精壮劳动力,回流的却是因各种原因淘汰的“劣质的人口”,如此循环流动,其恶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如时论所评,“这种疾病、伤残、成绩不佳的人口还于农村,是使农村农业劳动生产力退步的。在他方面,工业化人口,又在年龄精壮上吸收农村劳动人口,留老弱的劣质人口于农村,以抑压农村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注:汪疑今:《中国近代人口移动之经济的研究——江苏人口移动之一例》,《中国经济》第4卷第5期,第6页。)。这是不能忽视的。
三
农民,特别是精壮劳动力大批“离村”,不仅“致生产力日益减少”(注: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中译本),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第139页。),而且给土地的开发利用带来严重后果,土地撂荒,显然成为流民“离村后之必然重要影响之一”(注: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22、23、24号合刊,第97页。)。如山东省在“兵祸、土匪和红枪会扰乱之后,又继以天灾,不仅地主阶级脱离农村,就是农民也都逃亡了。最剧烈的如沂县,全县人口,残存的仅有三成,耕地也都全部荒废了”(注:长野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中译本),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第206页。);四川安县等地因“政治不就轨道,兵匪蹂躏乡间,贪污土劣敲剥地方。一般农民或被迫而为匪为兵,或跑入城市作工。乡村农民太少,田地荒芜甚多”(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第67页。);甘肃“临泽的县城,还不如内地的一个市镇,但是这个弹丸之地的县城的农民,每年却要负担着六万元的烟亩罚款,这里的官吏和土劣,差不多是操着生杀之权。况且各方的军队在这里都是长年累月的住着,一次又一次的无限量的提取‘摊款’,农民一年忍饥耐劳的一些收获,统被取去不算,还时时要挨打挨骂!可怜这大批的农民处在这水深火热的厄运中,只好离开他们的破陋的房屋和祖宗的坟墓向别处跑!好好的田地也一天一天地荒废起来了。
据统计第四区,民十九年共上粮一千四百四十五石,到二十三年只上八百八十一石,减少了五百六十四石,按平均每耕地十亩承粮一石计,五年之内,荒去耕地,已占原来耕地面积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比例可以普遍的说明甘肃河西(甘肃西北的一部分,河西——包括永登、古浪、武威、民勤、永昌、山丹、民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等十六县)各地的耕地荒废的情形”(注:余源昌:《甘肃的农村经济》,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11页。);在宁夏,“出灵武北门,有几里的小沙窝,……由此向西北行三十里,所过皆为肥沃的荒地,原有的阡陌痕迹,与村落废址,至今仍历历明现于大道两侧荒野之间。现存村舍,寥若晨星之落落。本来所谓‘塞北江南’、‘鱼米之乡’之宁夏,因变乱与征敛的结果,人民逃散,若干地方已渐即荒芜了!”(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12页。)他如绥远、陕西、河北、湖南、江西等省耕地,“无论就固定基期或移动基期比较,均有减少之趋势”(注: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第45页。)。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土地弃耕与农民大量“离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农村“离村”,未垦之荒地,固然难以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就是已耕熟田,亦任其荒芜。统计数字最具有说服力。据农商部统计,1922年全国荒地面积计为896216784亩,占全国耕地和园圃总面积的半数以上(按农商部1915-1921年的统计,在中国21行省间,耕地和园圃总面积计为1745669003亩)(注:董汝舟:《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东方杂志》第29卷第7号,第15页。)。10年后,据1934年土地委员会的调查资料,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宁夏等20省572县,荒地计有1179201357公亩(注:参见拙著:《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6页。)。由此可见,“我国荒地面积仍在增涨之中”(注: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第48页。)。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一大要素,它的变动,当然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农民的无地化历来是流民涌动的一大源泉,近代亦然。农村中虽然多数农民没有脱离土地,但同时没有充分的土地可以利用而不得不受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这半封建性的农村土地关系,耕地的面积日渐的减少,而荒地的面积,反日益增加。这就可以证明中国农村半封建性土地关系的恐慌性”(注: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37年,第13页。)。近代以来,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人多地少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另一方面,全国各地“农工远逃,荒田无人种者太多”(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第69页。),耕地撂荒,农业生产每况愈下,造成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反常现象,不能不说是对近代中国病态社会的深刻反映。
“离村”农民,流离四方,造就出大批政府无法控制的流动人口,增加社会管理的负担,同时也使政府的田赋征收额大打折扣,如河北静海县,田赋实征额与额征数之比率,逐年俱减,1927年为87.15%,1928年为77.47%,1929年为76.45%,1930年为73.90%,1931年为70.20%,1932年减至69.69%(注:《大公报》1935年3月27日。),颇有江河日下之势。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全国。田赋征收额趋减,当然与农民无力缴纳、抗缴、逃粮、地权转移、死亡逃户等因素有关,但“有地无粮”现象日趋严重,是值得注意的。
关于“有地无粮”现象,据称,“普通多指下列数种情形而言:第一,农村秩序不安定,时遭匪祸,致农民在乡下不能安心耕作,逃难于都市,而坐使土地荒芜,田赋无法征收;第二,因天灾人祸与苛捐杂税之压迫,使全国农村,多濒破产,一般农民每日劳苦所得,普通常是不敷支出。在这种情形之下,一般农民多愿出卖其田地,而就食都市。但一方因田地出卖者过多,而土地之收买者又毫无利益可获,结果,农民往往以极贱价出卖其土地,而仍常苦买主无人。如此,农民除了弃地出走之外,别无他法。但把大好田地,弃之又甚为可惜,所以,有些农民,多把田地借给或托付其亲友代耕。而弃田不顾,离乡他往者也甚多。弃田他往者,田赋固无从征收;即借托其亲友代耕者征收也甚困难,因土地原主既出走,无法追究,而代耕者又非物主,常不肯代为完粮也;第三,地方不靖,一般大地主多逃居都市,田赋无法追究而其佃户又每每不肯代为完粮;第四,土地产权转移,而买主又非本地居民,致经征官吏,无从催收。这四种情形,也便是形成‘有地无粮’现象之要因”(注:程树棠:《中国田赋之积弊与其整理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7号,第90页。)。由此可以看出,出现“有地无粮”的原因虽复杂,但农村社会不安、农民“逃脱农村”是符合事实与逻辑的重要因子。
四
农民大量“离村”成为流民,毫无疑问,对农村经济产生许多负面效应,但不能谓毫无益处,除开非常因素如兵燹、灾荒等引发的流民浪潮外,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有利影响可以在“打工族”身上得到体现,无论他们流向何方。
摆脱经济上的窘困是一般农家子弟外出“打工”的原动力。他们无论是漂洋过海,还是流向中心城市,还是在农村地区横向流动,一旦谋到适当的职业,从小处讲,可以贴补家庭生活之不足,从大处观之,对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亦不无裨益。就拿“洋流”来说,他们弃故土,离家室,远涉重洋,闯出一条沿海农民公认的追求生活的海上之路。他们的辛勤劳动,不仅推动着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缓解流出地经济困顿局面不无小补,他们的汇款源源地流入故乡,虽然为数不巨,但犹如给衰竭的农村经济注入“强心剂”,使之虚撑起超负荷的经济运转。这种情况,在平时不易为人察觉,但当“强心剂”缺乏,农村社会的不安立刻表露无遗。
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流民在海外谋生艰难,纷纷回国,加剧流出地生存竞争,而汇款大减,当地农村经济陷入泥潭,社会危机严重化。在广东,“有许多地方的离村人数,最近五年内不但没有增加,骤然间还要收容失业返国的华侨。……不经办事处而直接回乡的,当然更要来得多。所以像潮安农村中,这两年来农民人数反而增加了五分之一。广东的农村一面因为华侨汇款减去十之七、八而更是急剧地贫穷化;一面又因为华侨返乡而更要增加许多无业的游民”(注: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第66页。);“汕头经济恐慌,银根竭蹶,由来已久。溯其远因,始于民国二十年间,南洋工商业受衰落影响,失业华侨,回乡日众。往昔华侨每年汇款回乡约有五千万元,此项现银经过汕头,银业界运用此项资财,作活动流通金融,农村购买力,亦因而增加。此为过去潮汕金融之活跃情况。二十年以后,归侨既众,生利者变为分利之人,……所以潮、梅少壮青年,在生活上、经济上,毫无出路”(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484页。)。在福建,“自一九三○年,南洋经济衰落后,莆田出外谋生的侨民,一批一批的失业回国。不独华侨的汇款来源枯竭,社会上反添了很多失业游民”(注:朱博能:《福建莆田的农村金融》,《东方杂志》第32卷第8号,第86页。)。在广西,“岑溪和容县是广西出洋侨工最多的地方。容县华侨人数并无可靠统计,大约两户中间有一人以上在海外做工。以前每年华侨汇回款项约有三百万元;十八年起因受经济恐慌影响,汇款锐减;去年(一九三四年)汇款只有十余万元,仅及十六、七年的百分之五。近年华侨纷纷归国,使容县乡间骤然增加千万失业农民;依靠汇款补助家用的千万农家,更陷入朝不保暮的困境”(注:农英:《容县玉林两县农村调查日记》,《东方杂志》第32卷第18号,第107页。)。这些例子,可以反证“洋流”对于流出地农民生活及农村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补充”之效。
流向中心城市的流民,在外有所储蓄,同样可以增加农家收入,贴补农村经济之出超,法国著名学者谢诺就注意到,中国“大家庭消失的另一因素是在城市谋生的和留在农村的彼此分了家,有时是妻女在城里丝厂、棉纺厂、火柴厂或烟厂做自由工或包身工,有时是男的扔下家到城里工作,每月寄一点钱回去。一九二五年久大盐厂五百工人中有二百十一人给家寄钱,一九二六年有一百二十三人。汇款总数相当大,一九二五年平均每人每年寄二十三元,一九二六年三十九元。但低工资的不能坚持长期汇款,久大盐厂住塘沽的家属从农村迁到城市,因此在上海经常带家同住的,正是那些工资最低的,特别是由江北来的工人。只有有点钱或可能有相对稳定职业的,才能保证养活留在农村的妻儿,或至少可保证基本生活费用”(注: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见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561页。)。这种将“打工”所赚“每寄归老家”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注: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22、23、24号合刊,第98页。)。就连广西这样的边远省份也不例外,据载:“近城市的农村中男子许多跑到城市去做苦力的,到农忙时有些是转回农村耕田,有些则全年做苦力。他的家庭仍在乡下种田,他做苦力所得的钱拿回去帮助他们的家庭生活。这点情形,在苍梧地方最容易看见。苍梧县属七区当中,离村男子数为一六○九二人,占男子总数的百分之八,占壮丁总数百分之一八点四。梧州共有苦力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很多是由农村来的。他如南宁、柳州、桂林等比较大的城市所附近的农村,这种情形是一样的有的”(注:晶平:《广西的农村副业》,《中国经济》第5卷第3期,第107页。)。这是值得注意的。
在流民浪潮中,“闯关东”最引人瞩目。闯关的流民,特别是单身流民,无论为农、为工,抑或为商,只要有所收益,总是尽其所能,接济远方的家庭。“闯关”的山东人最具有典型性。不妨举出几个例子:
个案1郭宝孟口述:“我是1943年去东北凤凰城干小炉匠,时年二十三岁。那时家有祖父、祖母、父、母、兄弟五人,共计九人,因家庭生活困难,父亲让我去东北,希望能挣些钱回来。当时我还没有结婚,又有打铁的手艺,所以我答应去东北。同我一起去的共有四人,他们都结了婚。清明节起身,挑担步行到青岛,又坐船到大连再转旅顺口。我们四人,又步行到凤凰城,找到了老乡张学福,在他帮助下安了身干小炉匠。每年春节回家一次,带些钱来,当局不准多带,只准带五十元。”
个案2高绪远口述:“我上过六年学,1930年我去东北时,那年我十六岁。我舅舅在长春开副食品商店。舅舅回家把我带去。因为我有文化,就在他开的商店里当计帐会计。每月工资五十元。我每年都给家捎回些钱,是通过黄县福顺德钱庄寄回的,汇费百分之二十。”
个案3刘长泰口述:“我家世代很穷,在我小时候,家里只有一间房,一分地也没有。父亲十六岁(1894年)从蓬莱坐风船到辽宁营口。开始到店铺学生意,因上几年学,当会计,以后店家看着他有能力,便让他当采购,当时叫跑经济,经营烟土,来往于营口——上海——厦门之间,串通交易,能挣不少钱。他每年回家一次,捎回些钱来。
我上学六年,十五岁(1922年)跟着本村一个邻居到营口去找父亲。到那里开始学生意,……五年之后,……又去投靠表兄,在他那里挣钱也不少,常通过私人的钱庄往家寄钱”(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92、130、133页。)。
汇兑的需要刺激了银行钱庄业的兴隆,据称,“当时私人的钱庄,也叫私人银行。……这些钱庄在关内外两头都有人。在东北的收钱,并不往关内汇,而是就地搞买卖,靠关内各地的分钱庄付款,利钱很高,汇费要达百分之二十。莱阳人田和兴搞的私人钱庄就很厉害。他们总钱柜设在烟台,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分钱庄,关内的北京、济南、青岛都有他们的钱庄,各县有他们的联络户。他就是靠这套组织替闯东北的山东人汇款”(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第123页。)。
东北的汇款对山东的农村经济,同样具有“强心剂”之效。“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丧,汇款锐减,山东经济顿形竭蹶,濒于破产,时论有评:“农村经济恐慌为近日我国普遍现象,其重大原因,不外谷贱伤农,人民负担太重,及外货侵入农村等等,有以致之。惟山东情形特殊,除以上各种原因以外,另有一特别致命之伤,即东北汇款断绝是也。盖山东农民有勤苦耐劳之特长,历年来赴东北各地开垦,已有悠久之历史,其人民移于东北者,几占东北人口之半数,故东北三省不啻鲁人第二故乡。每年山东农民,由东北银行汇兑庄邮政局等汇兑机关,汇至山东农村之款,可统计者,在五千万元以上。农民由东北回鲁自行带来者,尚不在内,故东北汇款,实占山东农村收入之最大数目。据调查,大县每年收入皆在一二百万,小县亦在二三十万,故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山东农村情形颇为安定,纵间有水旱之灾,农田损害,亦可赖东北汇款之收入,以资挹注,不致感受若何困窘。自东北失守之后,山东农村骤蒙五千万元以上之巨大损失,以致经济周转不灵,入于死状,为农民者,咸叫苦连天,复以世界经济不景气之影响到达山东,谷贱伤农,粮价跌落,农民辛苦终岁,所得者,不足抵衣食及捐税之负担,再益之以土产滞销,及外货倾销之原因,农村出多入少,遂呈破产之现象”(注: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台湾华世出版社,1978年,第217页。)。这个评论虽然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足以证明流民“离村”外出谋事对流出地经济生活之影响了。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流民离土离乡,对农村经济不无小补。但所应注意者,农民“离村”的这种良好效应,正如吴至信所言,须先具备两个条件而后能实现:(1)离村者是个人而不是全家;(2)离村以后可以得到相当的职业。然而,“今日之中国,逃荒失业各地皆然,殊未足以言农民离村之利也”(注: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22、23、24号合刊,第98页。)。农民“离村”的积极影响,总起来看,实在是微乎其微的。农民“离村”的社会经济效应是复杂多元的,以上所述只是问题的几个侧面而已,是否得当,尚请学界同仁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