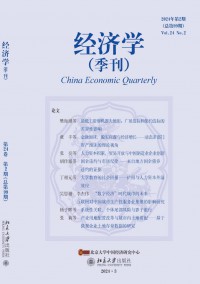经济学的道德思考与交易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经济学的道德思考与交易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最近笔者在自己的经济学专业中涉及到风头正健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不是中国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交易费用经济学中一些与政治经济改革有关的研究,希望与读者分享。笔者细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与温格斯特一篇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的精采文章。此文从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英国十七世纪光荣革命前后的政治制度变化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此文指出光荣革命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虚君宪政,议会民主制度使政府对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和法律制度的承诺成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对今后世界的变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一,这种对宪政秩序承诺的可信性使得政府不再利用其对政治的垄断来垄断经济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来追求执政者的利益。在没有民主宪政的制衡机制时,执政者"为社会服务"和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都是不可信的。他们会为了一党之私利,损害社会利益。这种"国家机会主义(Stateopportunism)行为"主要有如下几类严重恶果。第一,政府会借口特权垄断经济利益,窒息民间企业家的创业行为,扭曲价格。中国历史上学者称之为官营工商业与民争利造成的恶果。中国历史上也有学者看出这种政府从商有更严重的恶果,那就是海耶克所说的,制定游戏规则和参予游戏的政府角色的混淆。政府的功能本来是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及担当执行游戏规则的裁判。如果裁判也可以参加游戏,游戏哪还有公平、公正可言?中国史家历来鼓吹政府应该是清水衙门,不能从事工商业,这应该是与海耶克的主张一致。
其次,如果政府的权力没有可信的制衡,政府会追求一党之私利而损害社会利益,造成苛捐杂税,贪污和其它寻租行为。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间接后果比直接后果更为严重,因为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moralcode),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
这里有两点值得澄清。第一是法治和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第二是是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少中国人批评传统社会太重传统道德,而不重法治。但以我们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经验,和读到的法律教科书,我们可以体会到道德准则是英美普通法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比法律更原始更根本。在西方社会,各种不成文的道德准则起的作用非常重要,也更受人重视。很多从大陆去香港的新移民的行为特点足以说明此点。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他们在香港时行为非常有礼貌,不乱扔纸屑,但一旦过了罗湖关到了大陆,就像是另一个人,言行变得非常粗鲁无礼。这中间的差别不一定是法律的原因,而是每个人对不同社会群体对自己的道德期望有不同期望而造成。而这种对社会认可的行为的期望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行为的影响。如果政府言而无信(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公然违宪判王丹、魏京生的刑),甚至在"宪法"中公然鼓吹追求一党之私(四个坚持),则整个社会的行为会非常机会主义,社会认可的道德准则也会非常低下。这时纵有漂亮的法律条文,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可言。
下面我们再考虑国家机会主义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经济学中近年对此问题有不少有趣的研究。其中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各类寻租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包括资产特异性和议价过程造成的钓鱼行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欺骗行为等等),这类研究有时会得出一些民主和市场失败的结论。例如当一个划船比赛的团队中,各人划船努力的测度和节奏的协调费用很高时,用市场来协调划船可能比不上一个人下命令协调划船,下命令有可能犯错,划船节奏可能太快或太慢,但用市场价格来协调可能根本得不到节奏而使各人努力互相抵销。又例如两类生产活动,一类活动的投入产出容易测度,另一类却不易测度,则按市场原则论功行赏就会鼓励人们只生产前类东西而不生产后类东西,这时企业内的计时工资(不完全论功行赏)反而优于计件工资。对这种观点的批评以张五常,杨小凯,黄有光为代表。他们认为,划船的例子并不能说明命令经济优于自由价格制度,而只是说明与劳力市场有关的企业制度在一定条件下会比产品市场更有效。
另一个例子是各种活动的效果都不易测度时,强调论功行赏可能会使人们在寻租上投入太多精力,在评级升级上浪费很多精力,这时,反而日本式的按年资升级能减少寻租费用。这种看法被有些经济学家"论证",民主制度会使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制度化,因而反不如东亚的一些非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更有利,不少公司里因为很多活动的绩效不易测度,所以老板认为按绩效升级评等反而会刺激寻租行为,所以乾脆千方百计封锁信息,使雇员互相不知道各人的工资,而老板按他对综合效果主观判断来定工资。最近有不少这类经济模型"证明"过多的信息分享是有损效率的,而有效率的市场会使人们不去追求他们不应知道的信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指出,民主制度虽可能使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制度化,但它也会鼓励私人企业家活动,这些活动却会限制寻租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
这类对内生交易费用的研究并不能用来给我们前文中关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另一类"承诺对策模型"(以马士金,钱颖一等人为代表),却支持我们前文的观点。这类模型强调,内生交易费用的主要来源是承诺不可信问题。特别是钱颖一和温格斯特最近一系列文章用承诺对策的概念论证国家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分税制)是使各个地方政府在互相激烈竞争时使他们追求地方公众利益的承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其实是中国改革的动力。按他们的逻辑,当然民主宪政是使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负责和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成为可信的条件。
政府对宪政秩序承诺目前还只有在民主宪政制度下才可信。没有权力制衡,自由公平选举和政党自由,一个执政党保证在公平政治竞争下输了认输,怎么可能令人相信?如果政府对公众负责,不在损害公众利益时追求一己之私的承诺不可信,则会有如下恶果。首先,社会道德准则会江河日下,国家机会主义会为全社会所有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树立一个榜样,一个偷抢横行,不尊重私人财产,为人不厚道的社会就会出现。当大多数停在家里的自行车至少被偷过一次时,这个社会还有何道德准则可言。当执政党公开宣称其最终目标是一党之私(四个坚持)时,社会怎么可能太平?更可怕的是,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会使所有政治人物的行为非常机会主义,因此执政党不可能为社会提供长期的稳定秩序(’安定团结’)。中国一九四九年后每次社会动乱都是上层内斗造成的。高棉的动乱又一次说明,如果军队国家化,民主选举决定权力分配这些游戏规则没有稳定下来,则社会不可能安定,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地发展,一时上去了,也会掉下来。这当然不能只怪这些"政治野心家",主要问题在于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不公平时,政治人物争夺权力造成社会动乱就不可避免。政治人物会为了权力不惜将社会拖入动乱。为社会提供长期稳定的秩序是政府的首要功能,但至今为止,能提供长期稳定秩序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制度和君主世袭制度。君主世袭制度曾有提供三百年稳定秩序的纪录,但大多数君主世袭制都没达到这个纪录。民主宪政制度打破了这个纪录,但很多国家在立宪过程中陷入动乱(俄国一九一零年代的立宪和中国上世纪末的立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列宁式的非世袭非民主政治制度无法达到君主世袭制和民主制的纪录。
君主世袭制为什么能提供长期稳定秩序?因为世袭制是种部份满足布坎南"模糊面纱"的游戏规则,皇帝的位子是可遇不可求的。特别是在英国光荣革命后有了王位继承法,王位的得失变得完全无法由个人努力争得。所以人们也死了争王位的心。用经济学家的话而言,就是减少了寻租的投入,因而使内生交易费用大降。这有点像用年资制限制寻租行为的功效。民主宪政在高层次上有同样功效。竞选中的激烈政党竞争使得输赢不可能由个人努力来控制,很多敌对的个人努力互相抵销,使选举的胜负变得象随机事件。这不但容易形成各方对游戏规则的承诺可信的局面(因为游戏参加人不确定将来他会在朝或在野),而且这游戏规则比君权世袭要公平得多,即完全满足模糊的面纱原则。这原则声称,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可能是当权者,可能是在野,可能是被告,可能是原告,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囚犯),他认为在任何位置,游戏规则都是公正时,此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按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满足这种原则的社会秩序有可能长期稳定,超过君权世袭提供长期稳定社会秩序的纪录。
一个国家是否能走上这样一个宪政秩序的轨道是每个真正政治家首先要关心的问题。这个宪政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像高速公路网与汽车的关系,没有高速公路网,汽车越多反而可能越没有效率。
但是立宪过程中由于人们对新游戏规则没有信心,会出现输了不认输,因而动乱发生的局面。这种局面在俄国最近的立宪过程中没有出现,但却可能在中国即将发生的立宪过程中出现。其原因是中国人比俄国人个人主义色彩更重(此处并无褒贬含意)。因此,我们有必要记取过往的激进变革的种种教训。
对激进变革的批评是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以海耶克为代表)的传统。此传统就笔者的知识至少可追嗍到伯克(EdwardBurke)。他在一七九零年有名的"法国大革命反省"一文中就提出了自发秩序的观点。他认为激进变革的鼓吹者自以为他们了解现有制度的运作和缺失,以为用激烈的社会变革可以改进人们的福利。但是一种能运作的制度往往不是少数人能设计的,而是千万人交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它包含了千万人的个别信息,而这个别信息只有当事人了解,因此,没有任何个人可能完全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如果任何个人妄称他了解整个制度的运作及其缺失,而想用激烈的社会运动来改造制度,则他一定会把那些他不了解的奇妙机制破坏掉。他强调社会制度的功能是任何单个人(即使是天才)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就像蚂蚁不可能完全了解它们的蚁窝是按什么力学原理设计的一样。有人据此把这类思想称为人不能了解的宗教迷信。但是我却相信这类思想很有道理,因为它说明群体中个体的交互作用自发产生的东西,可以用一种群体智慧(看不见的手)达到个体智慧不可能理解的奇境。用这种看法来观察中国的政治制度演化,我们会更慎重对待一些中国发生的事,不轻易对制度的演变下结论,对自己个人的无知保持一种警觉。
为什么第一个民主宪政制度产生于英国?我认为英国人由伯克代表的思想传统是一个重要因素。政治领导人物对群体智慧的尊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看彭定康领导的香港的政制改革,我们对中英领导人的素质差别略有了一点了解。从最近的"末代港督"电视片中,我们了解到彭定康在决定是否政改的立法会前夕,对胜负还没有把握,但他不是让制度由个人胜负的利益来决定,而是在给定游戏规则下,尽最大努力与中方和其它各方玩一场公平的游戏。而中方却相反,一切制度安排完全以中方的胜负利益为准则,为了赢,避免输,可以把一个公平游戏规则下(中方和其它各方都积极参予了)产生的立法局废掉。
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后患无穷,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对公平游戏规则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极难建立的。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渐进的过程。不要以为英国人几年建立这套制度很容易,没有香港政府一百多年来在香港的令人尊敬(decent)行为,谁会相信香港政府对公平选举规则的承诺。中国政府的类似承诺从来就不可信,它在香港的不道德和自私行为再次证明它的承诺不可信。而中国近百年来的动乱都是因为政府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引起的。辛亥革命是因为维新党对皇室承诺立宪的不信任引起,二次革命是国民党对袁世凯对宪政的承诺不信任引起的。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不可信,其实是现代中国政治动乱迭起的根源,它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使中国失去了步明治维新后尘的机会,而人民对这种承诺的不信任当然是当政者不道德和自私行为日积月累造成的。中国政府在香港的行为再次将这种"动乱病毒"带到了香港,使香港人民对政府对宪政秩序和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信任。中国人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解散香港立法局看似事小,实则是伤了香港法治社会这棵大树的根,创立了一个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先例。如果香港政府在明年选举时,又以中方赢为标准来设计选举制度,那香港就完全倒退到中国式的反宪政制度去了。
而经济发展像宪政秩序这棵大树上的枝叶,它再茂盛也不能与树根相比。西方的经济发展都是宪政在先,经济大发展在后。英国光荣革命前,政府的贪污和人民的寻租行为(走后门)与中国目前一样。正是光荣革命创立的虚君宪政代议民主,提供了一种机制,使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变得可信。因而政府对财产的尊重和保护成为可信承诺,寻租行为受到限制,有了这些宪政环境,才会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大发展。
同样道理,美国的民主宪政秩序也先于经济大发展,它也是美国两百多年来强盛的条件,而不是反过来。但是人们常用东亚一些国家不民主也能发展经济的例子来反驳以上看法。这种反驳看似有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东亚经济发展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竞争压力下产生的一种不得不模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模仿经济制度可以在政治民主和宪政架框构不成熟的情况下成功(但不成功的例子多的是),但成功的原动力是西方靠宪政秩序取得经济实力造成对其它国家的压力。没有英国的宪政秩序,哪有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五十年代初贪污的情况与今天大陆差不多,但有宗主国的宪政架构,才会有可信的肃贪承诺,才会有香港的经济成就。
前文中提到的一些内生交易费用模型,论证企业内的独裁和计划经济可能减少内生交易费用。这也可能是种片面的观点。因为自由市场中的企业都要面临劳力市场,资本市场的竞争,麦当劳的内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但人们却有买或不买这计划的自由,计划不赚钱,则分店老板(Franchisee)就不会有人愿意当,也就是无人买这指令计划。正如海耶克所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也不是效率的差别,而是制度形成机制的差别。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由政府或哪个人设计的,而是千万人在自由选择合约和制度的条件下,无意而自发形成的。美国宪法就不是由哪个人设计的,而是由很多州的代表吵架吵出来的。所有人都不满意那个宪法,又不得不接受这种折衷。宪法并没有政党政治这一类设计,但在根本权利问题上大家达到了折衷,政党政治就自发地从宪政秩序无意地产生了。
有些后进国家即使有人为设计的政治制度能生存的情况,但在更高的层次,这些制度必须在国际竞争中经受适者生存的考验,因此最终也不能由个别人设计。由此来看中国最近的私有化改革,政府如果又用政治力量,人为设计私有化改革运动,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中国已有了公司法,在公司法秩序下,案例的积累,自然就会形成新的秩序,并不需要私有化运动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能运行,一定有一些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道理。例如国有企业不但有无效的一面,也有保险合约使人们专业化没有很多风险的一面。突然搞私有化运动,又不提供自由创业,资本市场自由化和保险业市场自由化等条件,就意味着违反当初的保险合约,这其实可能是种不公平的反市场行为。威尔士王子与王妃离婚还要给她大批补偿费,中国政府怎可突然违反当初的各种保险合约而大肆无偿裁人呢?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行为,不但是种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因为不了解保险促进贸易和分工的功能而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最近笔者与程文利和刘孟奇博士发展了两个数学模型。其中一个证明收入分配不公时,从分工没得利的一方会拒绝参加分工,因此使市场缩小,形成南美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局面。从这点而言,美国六十年代的’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可能有其经济效率方面的正面意义。当然这如果做过了头也有福利上的损失。另一篇文章说明完全保险制度(铁饭碗)一方面造成道德风险(moralhazard)及相关内生交易费用,但也有为一个复杂的分工网络保险增加分工协作可靠性的功能。竞争的保险市场能有效折衷这种两难的冲突达到均衡。但在保险市场不发达时突然废除完全保险,会使很多部门串联在一起的分工网络可靠性直线下降,一个专业部门失灵使得整个经济瘫痪,出现负增长。这就是东欧俄国的教训。
所以完全保险(铁饭碗)和完全无保险都是无效率的两个极端。竞争性市场上自发出现的不完全保险比这两个极端都更有效。最近出版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英文的首推Milgrom和Roberts的Economics,OrganizationandManagement(1992)。此书的特点是既涵盖大多数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深入浅出,非常切合实际。比如上文提及的寻租问题,此书用多个模型说明,寻租的交易费用有两种,一种是寻租的投入,另一种是测度投入和产出不精确时产生的信息歪曲。这二者之间的最优折中在不同条件下不同。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高时,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好,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很低时,绩效工资反而会使大量资源浪费在评级升级上。因此年资工资反而更有效。中文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首推张维迎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1996)。此书既涵盖大多数对策论中的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涵盖了大多数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adverseselection)模型。例如书中的鞭打快牛模型就非常切合中国实际。笔者和黄有的SpecializationandEconomicOrganization(1993)也用很多模型研究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和市场网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