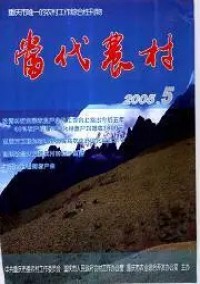农村婚姻状况计量分析论文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农村婚姻状况计量分析论文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利用族谱资料和计算机对明清以来的农村社会进行探讨,已经有若干学者做了开创性工作,特别是台湾的刘翠溶女士,卓有建树[2]。对江西地区,刘女士也曾对宜黄北山黄氏家族做过计量研究[3]。但仅此单一的个案当然远远不够,且单纯的族谱计量统计若无其他文献和实地调查相配合,也难以深入认识地域社会的真实内涵和运动过程。作为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笔者以民国二十五年(1936)底刻印的《抚乐流坑董氏复彦房谱》为基本资料,将该谱全部人口记录输入电脑,进行统计,再结合以往调查研究所得加以分析,这里是其中的婚姻部分。希望这能够深化我们对明清以来江西农村的认识,并对有关研究有所助益。
材料与方法
关于流坑村,几年来我们已经发表了多篇文章[4],故这里不重复介绍。本文所使用的基本资料──《抚乐流坑董氏复彦房谱》,是流坑董氏第三级宗族组织中最大的一房──复彦房的房谱。流坑现能看到的20余种族谱中,唯一的大宗谱修成于万历十年(1582年),早期的记载也并不完整,用于计量研究不够理想。而八个二级宗族组织的宗谱,最后编修时间多属清代,只有文晃房谱成于1936年,历时最长,内容也很充实,可惜我们未能借出复印,暂时无法使用。故只好退而求其次,根据成谱时间、内容和保存情况,以流坑董氏八大房之一的胤隆房下之复彦房房谱作为研究对象。
复彦房的房祖,是流坑董氏第19代的复彦公,由此下至第36代,共18代。该谱记载的人口历时跨度,从明中期的1436到民国的1936年,正好500年。由于记载开始时流坑宗族组织已经高度发展,按时修谱有制度保障,本房士绅亦比较多,故内容较为翔实和完备。另外本房是流坑诸房人数最多者之一,又绝大多数居于流坑,在外者很少,所以数据更具完整性。
本谱样本总数为7083人,其中男性4349人,女性2734人(均为男性配偶)。男性生年记录可确知和大致推出者4260人,占男性人口的97.95%;女性则为2297人,占女性人口的84.02%。男性有卒年记录以及修谱时尚存活者2510人,占男性人口的57.71%;女性为1956人,占71.54%。生卒年记录均详的,男性1969人,占男性人口的45.27%;女性1530人,占55.96%;如包括修谱时尚存活者,则男性为2509人,占57.69%,女性1915人,占70.04%。
由此可见,复彦房谱的人口记录不仅数量较大,而且相对而言也较为完整[5]。特别是3499个生卒年俱详的记录,对我们分析人口状况及其变动,尤为重要的资料。
这样一个有30个字段的数据库,基本可以全面反映该谱的所有人口信息,并较为方便地编制程序进行各种统计和检索。
婚姻基本状况
一、婚姻缔结
*比率此项,所统计仅为22代至34代,而略去了基数太小的19、20、21代和修谱时年龄尚小的35、36代。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复彦房男子结婚人数(等于全部配偶数)只占全部男子数的57.8%左右。这个比例,在已有的统计数字中是比较低的(如刘翠溶对南方23个家族的同一统计数字是65.9%[6],而毗邻的宜黄北山黄氏则为71%。)。由于本数字已经略去了修谱时年龄普遍尚小的世代,且漏载数量不会很多,所以导致其偏低的可能原因只有两个,即早卒未婚和成年未婚的人数较多。据上表,50岁以上未婚而卒的男子为66人,占1.5%。因这个数字仅是有生卒时间者,故偏低;如与生卒时间俱全的男子总数相比,则上升到2.6%。笔者另统计了30岁以上到50岁以下死亡的未婚男子,结果是占男子总数的2%和生卒时间俱全的男子3.4%。但二者相加最高仍不超过6%,说明男子30岁以下未婚而卒的达34%以上,即未婚的主要原因是早卒,排除这一因素,结婚是极为普遍的。然而男子未婚数量之大,毕竟值得注意,这将对生育率产生直接的影响,也从一个特定方面证明流坑未成年男性死亡率较高的事实。
第二,该房男子有较高的再婚率。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死亡率高,较高的再婚率乃是普遍的事实。但是流坑继室与元配比为22%,不仅大于宜黄黄氏家族的15.5%,也大于刘翠溶调查的23个南方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以下所称南方家族,均指此),并比其平均数字高出近一倍。本谱中妻子被丈夫生出的情况极为少见,不构成再婚的一个要素。求其缘故,当地童养媳较多似为一重要原因。道光年间,流坑一位老儒提到家族中“童养之妇,世俗动以未合不成妇而为辞,往往兄亡
弟收,弟亡兄收”;又反对溺女,赞成“与他姓童养为妇”[7],可证当地有此习俗。检索本谱有确切生卒时间的成员,有13位夭亡于10岁以下的男孩是已婚之身,另有9位元配死亡年龄在10岁以下,因本谱对配偶未过门即死亡的均有说明,则这些男孩的妻子和早死的元配属于童养媳无疑。而下面我们会看到,流坑元配妻子的结婚年龄明显低于其他地方,说明童养媳可能非常普遍。由于她们具有更多的死亡历时,所以童养媳多必然导致男子的再婚率高的事实。再看这里的男子三婚率和四婚率,分别为18.3%和18.6%,也高于刘氏的数字,似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第三,复彦房男子纳妾的现象较少。妾只占全部配偶的0.6%,在刘氏研究的南方家族中居于非常低的水平而大大低于平均数(3.7%)。从另一个角度看,纳妾男子只占结婚男性的0.89%(21位侧室分属19位男性),也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据刘氏的研究,城镇家族的纳妾比例较高,以江西本省的南昌东关甘氏为例,其比例为8%,13倍于复彦房。流坑基本上属于农村聚落,低于城镇家族亦在情理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宜黄黄氏家族的纳妾比例也比较低,为2.3%,这也许示意着赣中农村的共性;第二,复彦房纳妾行为始于27代,其时间大致为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正好是该房竹木贸易大发展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再看表二:
*此二人均纳二妾。
从表二可知,取妾者近70%为有各种身分之人,平民只占31.6%(纳妾数则为28.6%)。而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些有身分之人除儒士(童生)和秀才外,全是通过捐纳取得地位的,且几乎全是商人。即使是表二之平民和童生、秀才中,也有若干商人子弟。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流坑士绅特别是商人家庭,纳妾的可能性远大于一般家庭;也就是说,流坑清代纳妾现象的发展,和当地竹木贸易的发展直接相关。这和刘翠溶的研究有一致之处。
二、初婚年龄、夫妻年龄差和平均年龄
初婚年龄,族谱中均不记载,但可以通过父母(元配)与长子的年龄差大致加以推断。笔者将复彦房无女儿的家庭挑出,统计得到该房长子出生时夫妻的平均年龄,夫龄为28.70岁,妻龄为23.12岁。而刘翠溶对南方十五个家族的统计数字是,夫龄在27至31之间(笔者据以计算其平均数为28.56),元配年龄为24至25岁(平均数24.76)之间。两相比较,流坑男性在长子出生时的年龄非常接均数字,但女性则低于平均数1.64岁,也低于十五个家族中的任何一个,说明流坑女性婚龄显著偏小。如果我们按照刘女士的推算方法,假定由结婚到长子出生间隔为三年[8],那么流坑的平均初婚年龄大约在男25.70,女20.12岁左右。这组数字的意义在于,虽然大量存在早婚的事实,但男性平均婚龄并不太小,也就是说实际上仍有相当多的人是在比较大的年龄上才结婚的。而女性婚龄偏小,可能印证了当地收养童养媳之风较甚,这在上面已经提到了。
依据族谱中每一对夫妻生日(如果有记载的话),即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表三的第一栏即是元配、继室和侧室与丈夫的平均年龄差。丈夫比元配要大近5岁(这和上面根据长子生育时间计算出来的初婚年龄差5.58岁相近),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数据[9],再次证明了女性结婚年龄偏低的事实。而且显然,随着婚姻次数的增加,丈夫与配偶之间的年龄差距也逐渐拉大。这表明,流坑男性在妻子死后再次结婚时,更倾向于选择较年轻因而可能未婚的女性。而比较年轻女性的家长愿意把女儿嫁给董氏年龄较大的男子,则可能是董氏在当地有较为突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致。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女性年龄大于她们的丈夫。元配组为五分之一强,这个数字在北方地区无足称道,但在南方就是特别高者。就是继室组也高达8.68%,接近于南方地区一些家族元配的水平[10]。甚至再继之中,她们也依然存在。故而流坑男子娶妻并无男必须大于女的约束。但检索的结果表明,极少有妻子比丈夫大10岁以上的事实(元配亦只有0.14%),而且还有一部分大妻其实与丈夫为同年出生的同龄人(元配3.01%,继室1.74%),这与丈夫常常大于妻子20、30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根据生卒时间俱全的记录,统计得到复彦房男性平均年龄为42.84岁,女性为47.04岁。女性寿命长于男子,这是一般的通例,可是这里女性平均年龄超过男性较多,原因在于女性多为成年嫁入,不像男性有许多夭殇者进入统计。
三、守寡与醮出
由于复彦谱对女性生、卒记载不如男性详尽,特别是醮出者的卒年一律阙如,表四a、b的守寡数字,只是配偶双方有明确生、卒时间记录从而可以判定的寡妇和有“出”即醮出记载的寡妇数字,很不完全。尽管如此,其仍然可以帮助了解流坑女性守寡和出醮的一些情况。本表只列出数据较充分的元、继配的数字,再继和三继因数据较少从略,但保留侧室的数据以为参照。
复彦房的妇女元配守寡的比例为43.89%,继室为45.59%,总比例为47.28%,接近半数。虽然明显低于刘翠溶的南方15家族57.9%的平均守寡率,但也还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元配45岁以上的守寡人数少于45岁以下者,与南方诸家族情形完全相反,只有继室是45岁以上组大于以下组。如果不是因为有大量无法归属的数据存在影响了计算精确的话,则首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复彦房未成年男性的死亡率较高,这对元配45岁以下守寡比例较高是有影响的。而且刘氏的45岁以下组只包括20到44岁的妻子,没有计入事实上并不算少的20岁以下的寡妇(如上面提到的童养媳中的一些人及其他低龄妻子)。复彦房元配中20岁以下的寡妇为43人,占总数的6.07%,减去她们后差距就有所减少(46.61对33.90变为40.54对33.90)。从理论上说,该房妻子的平均寿命是47.04岁,丈夫的平均寿命为42.84岁,由于妇女婚龄偏低,夫妇之间有约5岁的年龄差,故妇女37岁时就有极大的守寡可能性,所以45岁以上者守寡比例有限。
另外从总体上看,随着婚姻次数的增加,续娶配偶守寡的比例也有所提高,这显然是因为继妻与丈夫的年龄差越来越大的缘故。
再看醮出。复彦房共有元配女子235人醮出,是所观察的元配寡妇总数的33.19%。即是说,大体上守寡的元配里面,每三个就有一个改嫁。而在总体上,大约每四个寡妇会有一人改嫁。所以,宋代以来理学家们和政府努力提倡的极度贞节观,在赣中农村和许多地方一样,实际上并未能成为支配的观念。当时流坑的一位士人说:“守贞难得三从,自是经常;逐物易移再醮,亦属权变。与其淫奔而玷户,不如改节以栖身”[11],这很可以说明当时社区精英们对此也是持宽容态度的。当然,流坑至今还能发现一些清代官员表彰节烈女子的牌匾,族谱里面也不乏类似的文字和榜样,但这种极力的赞美与提倡,恰恰说明当时社区中大量存在的,其实是相反的事实(复彦房谱的《贞节传》收入33人,仅占妇女总数的1.21%而已)。
再一个明显的情况是,45岁以下寡妇改嫁的比例远远超过以上者。表中元配是15倍,继室则是8倍。计算两组寡妇改嫁的比例(醮出人数/守寡人数),45岁以下组为26.05%,以上组则为2.32%。前者也是后者的11.23倍。因为有大量不详归属于何组的寡妇和醮出者,这两个比例肯定都偏小。如果将不详归属的寡妇按1:1分到两组,即使按照2:1的比例分配不详归属的醮出者,45岁以下者仍将达到43.83%,以上者则为17.97%;如按3:1分配醮出者,这两个数字则为46.60%和11.89%。可以认为,复彦房的妻子如果不到45岁死去丈夫,近半数甚至更多会改嫁;以上组就少得多,最多不会超过20%。
复彦房娶进女子与女儿所嫁姓氏极其近似。前十位中有9个相同,而且位次和总比例也很接近。前二十位中则有18个相同,即90%保持一致。这说明,该房无论嫁娶,通婚对象均很一致,而且主要是固定在一二十个姓氏上(按:通婚姓氏总数为107个)。这种通婚对象的相近有诸多原因(详下),其中亦包括“亲上加亲”的传统习俗,以及在社会交往较少的情况下出嫁女性在助成婚姻方面的重要作用。能够说明这一点的一个现象是,谱中母亲和女儿出嫁对象的姓氏往往相同。房谱共计949位女性有生女记载,生女2243人,内1240人有所嫁姓氏记载,而与母姓相同的为135人。可知14.23%的母亲至少有一位女儿会嫁给自己的同姓;10.89%女儿的夫君与母亲同姓。如果说这一比例还不算高的话,房谱还表明,有更大数量的女儿出嫁后婆家之姓与其继母、嫂子或婶子相同,这更能反映同样的事实。
根据梁洪生对流坑其他房支明中期到近代婚入姓氏的统计,胤明房前15位依次为王、陈、曾、黄、丁、张、胡、谭、吴、邓、詹、徐、袁、乐、邱;坦然公房为王、陈、曾、丁、邱、黄、谭、张、詹、元、邓、阙、刘、谢。比较起来,复彦房前15名与二者相同的均有10位(66.67%)。这说明整个流坑的通婚对象有很大的共同性。但某些姓氏的出入,特别是某些房位置在前的姓氏在另一房可能位次很后,如复彦房列第九的谢氏在胤明房的的前15名中踪迹皆无,而胤明房的乐氏和坦然房的阙氏在复彦房的通婚对象中仅都只有0.32%,仅在30位左右。个中差别,说明各房的通婚对象亦具有一定的特点。
复彦房90%以上的通婚对象在本县范围内,这是传统农村社区带有普遍性的现实。但有两个现象应该关注:一是仍然有一定的跨县甚至跨省的婚姻,主要是入嫁女性有11.34%来自县外;二是娶入和出嫁,亦即男女两方面之通婚地域有微妙的差异,男子在外县娶妻的比例大大高于女儿出嫁到外县,且有1.14%的跨省婚姻。这表示,当地婚姻并不是完全封闭的,男性获得配偶的范围尤较女性为大。仔细观察上述地点可以发现,县外婚姻较多地集中在永丰和赣江、长江水道上(湖北一例为小池,江苏一例为南京)。流坑所在的“下乐安”地区本属永丰,南宋才分出,但历来方言、风俗一致,交通便利,至今居民心理上仍很亲密。而恩江经永丰下注赣江,经吉水、樟树、丰城、南昌、鄱阳湖到长江中下游的水道,则是流坑竹木贸易的主要路线。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上述地点的分布。另外跨省婚姻中湖南和浙江两例,都是外出做官者娶的侧室,乃是男性社会政治活动的结果。所以,这里传统社会中主要由男子进行的各种超越社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行为,是部分打破通婚圈的封闭的主要原因。
同姓氏一样,在复彦房100个左右的通婚地点中,有一二十个最集中的地点,而全部又都在乐安南部的恩江流域即所谓“上乐安”地区,具有非常高集中性。从地图上看,这块地域南北约50公里,东西40公里,即董氏的主要通婚圈。由于大族聚族而居,所以这和上面姓氏的集中实际上是相通的。虽然同地未必同姓,但同姓的比例很高。以几个大姓为例,见表十:
上表是根据谱中出嫁地和所嫁姓氏俱全的记录,统计得出的从十大通婚姓氏主要居住地婚入女子在所有同姓配偶中所占比例。其从近80%到20%不等,成为相同姓氏中的主要通婚对象。其实,有不少同姓本为一支所孽,如谭港、员陂、官庄等处的黄氏,水南和莲河等处的丁氏,将他们合并计算后,黄、丁二氏的比例即上升到53.85%和97.22%。所以流坑董氏的通婚对象,实际上主要为一些类似董氏这样在当地有地位和影响的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当然,也有的地方杂居程度很高,如县城21个婚入的女子分属10个姓氏,这是城镇的特别之处,体现了流坑董姓在县境内的地位及其与县城士绅的较深关系。
流坑的婚姻,确实存在着一个空间狭小、大家族之间世为婚姻的固定圈子,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种圈子的形成,除了是上面指出的历史、风俗和交通、商贸等因素的产物,还与乡村宗族成员和精英人物试图获取和保持社会声望和地位,维系宗族组织的稳固与和谐相关联。明代中、期以来一批董氏士绅不断地在加强宗族的制度化,其中就包括加强婚姻限制。由知县董极撰写的万历大宗谱之祠规,明定可以通婚的若干“乡中世姓与凡清白守礼之家”。有敢于“开列之外,乖乱成法,”“贪利忍耻,将男女约婚小姓”者,处以“罚银十两”和“追谱黜族”的严厉处分[13],在若干族谱里我们看到一些具体事例,证明这一规定曾确实得到执行,其对世婚的确定和维持作用,自不待言。所以,至少在较早的谱牒中,出嫁地和嫁入地的明确记载,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然而也需看到,复彦房存在着不少与小姓结婚的例子,约40个仅一、二见的婚入姓氏,恐怕多属于此。其中如芜头的周氏,烧元的李氏,在其他房谱内明见娶而受罚的记录;又如蓝、钟、赖、雷之类的姓氏,应为客家山民,也不属于世族。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族人娶了本村的外姓女子(一姓李,一姓罗),我们知道,村中极少数的外姓人均为董族的佃仆贱役,其为严禁通婚的对象无疑。可是复彦谱中竟无一人因此而有受处罚的记录,令人嘱目。这些现象较多发生在29代也就是清代中期以后,可能表明随着乾隆以来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商贸活动的发展,流坑通婚世姓的传统规条有所松动。这对于我们研究流坑董氏家族的解体过程,有一定的意义。不过,某些房这一时期制定的家法还在强调“娶必相当,先分良贱;配非其偶,重玷门楣。如果贪财辱宗,定行削谱黜族”[14],并且确有具体记载,表明各房之间这种松动的程度是不同的。
进一步观察复彦房绅士家庭的婚姻情况,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认识。这里所说的绅士,是指包括童生以上有科举名分或通过捐纳、军功等途径得以取得散官或实职者。请看表十一和表十二:
比较表十一、十二可以看出:复彦房的士绅无论娶妻嫁女,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追求门当户对,所以该房绝大多数对方为绅士的婚姻(婚入为93.75%,出嫁为82.35%)都发生在这个圈子里头,普通成员极少。反过来说,对方之所以愿意与其通婚,也是因为其社会地位相近。表十三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由表中可见,复彦房的士绅主要是两类人,一是低级的科举功名的获得者,一是捐纳人员(本表国学以下至议叙全为捐纳所至),二者的地位都不高。他们的亲家,也完全是这两类低级士绅。但他们之间同一身分者数量多较悬殊,则表明他们在结亲时并不要求绝对对等,两类人员间也没有明显的隔阂。超级秘书网
但是在另一方面,事实上他们也远远达不到真正的门户相当。只有7.59%的士绅在娶妻时、7.09%的士绅在嫁女时能够如愿以偿,大部分则只能与平民通婚。从全房的范围来说,在婚入和出嫁的两种场合,董氏的亲家中绅士都只占1%多一点,所以实际上,当地社区中士绅通婚的次数,在总数中是不足道的。复彦房的绅士人数该房是男性成员的9.08%(395/4349),其和亲家的差距也许反映了流坑绅士比例较高的特点(流坑董氏利用族大人繁、控扼河流,垄断流域的竹木贸易后,大量捐纳职、监和资助子弟读书,形成了较大的商人和生、监群体,这方面深入的计量研究,将另文探讨),这也是他们会较多地与平民通婚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平民可能较为富有,而不是下层的贫民。
注释:
[1]本文是流坑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该项研究工作主要由江西师大历史系的梁洪生副教授和我进行,并得到了周銮书研究员、郑振满博士的指导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资助。本文计算和写作过程中,又得到了曹树基博士和胡振鹏博士的热忱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刘女士有关研究成果很多,最集中和完整的见《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8年6月。
[3]《宜黄北山黄氏之成长与社会经济活动》,《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以下有关这个家族的情况,均据此文。
[3]梁洪生:《家族组织的整合与乡绅──乐安流坑村“彰义堂”祭祀历史考察》;邵鸿:《竹木贸易与明清赣中山区土著宗族社会之变迁──乐安县流坑村的个案研究》,俱见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梁洪生:《社区建设实验──江右王门学者与流坑村》,1995年香港“经营文化:中国社会单元之组织与营运”学术讨论会论文。梁洪生:《流坑村何杨神崇拜考述》;邵鸿:《明代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俱见《南昌大学学报》赣文化专号,1996年。
[4]刘翠溶上揭书中所研究的族谱,知道生年者为80-68%,卒年为40%左右,见该书第一章。又刘氏研究的北山黄氏族谱,生年详知的男子占97%,女子占72%;卒年详知者男子占56%,女子占43%,刘氏已认为“此谱对于成员的生命日期记载相当完整。”
[5][6][8][9]刘翠溶:《明清人口之增殖与迁移──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之分析》,《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3。
[7]董泰然:《家戒八条》,道光十九年(1839)《乐邑流坑董胤明公房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