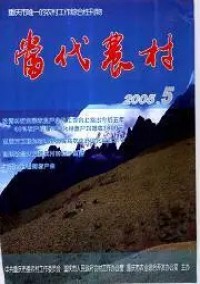农村社会资本路径选择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农村社会资本路径选择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与建立在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上的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新农村建设有利于重建农村社会资本,而农村社会资本的重建又可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从对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梳理中,我们发现,体现在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上的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面临着匮乏的状况。为此,本文着重探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如何针对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存量匮乏的状况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相关问题。
一、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的缘起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就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把它界定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1]布迪厄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社会学的解释,开创了社会学也能研究资本的先河,从而使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了进行对话的可能。但是,这种解释仅仅将社会资本局限于网络这一种形式,缩小了社会资本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只是对某些特殊的活动而言,它可以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2]然而,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这如同用其结果给社会现象下定义一样,混淆了前项和后项。我们知道,不同的前项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或者说,同样的前项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不幸的是,许多研究者都错误地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从其结果来理解,或者认为社会资本总是导致“生产性”结果,即社会资本总是起积极作用,而忽略了社会资本也会带来“破坏性”结果,即社会资本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美国学者亚历山德罗·波茨正是持着对科尔曼的批判态度来界定社会资本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3]正是由于侧重从网络的功能意义上界定社会资本的概念,波茨进而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概念,他在总结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最近的研究至少已经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内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秀异。”[4]可见,提出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是波茨对社会资本理论的一大贡献。但波茨和科尔曼都没能把自我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作用恰当地表述为影响创造、维护和破坏社会资本的因素。而区分开自我实现其个人特征的重要性的力量和自我实现其网络地位的重要性,是十分重要的。美国社会学教授罗纳德·伯特在总结科尔曼、波茨等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5]可见,伯特是从结构的观点来界定社会资本的,他注意到了自我凭借在网络中的地位拥有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网络结构形成的过程及其分配结果,而不是组成网络的个体自我。
上述学者都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的,而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也有译作帕特南)是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的第一人。普特南与同仁花了20年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研,他在这项调研的基础上写成的《使民主运转起来》(1993)一书,则成为美国当年的最畅销书之一,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在这本书中,普特南是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6]在此定义中,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对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现实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办成事情。
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和规范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构成社会资本的三大基本要素。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因血缘、地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参与网络体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从而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资本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政治稳定等现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范式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社会资本这一范式可以帮助我们考量转型期政府的绩效、农村社区的效率与社会活力,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的现状分析
从上文有关社会资本概念的梳理中我们可以认为,社会资本特别是农村社会资本体现在以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上。这是因为,与“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对自家人和外人的信任既会受人与人之间先天血缘联系的制约限制,也会受血缘关系泛化后所形成的各种拟亲属关系如同乡、同姓、哥们甚至亲密情感关系的影响,从而使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家属、亲戚和家族成员,也会包括一些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其他外人。因此,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越强。可见,血缘家族关系是制约人是否信任他人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关系(包括血缘家族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中所包容的双方之间的情感内涵对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具有明显和重要的影响作用;中国人根据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所确定的有选择倾向性的相互信任即特殊信任,与根据有关人性的基本观念信仰所确定的对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两者之间并非相互排斥或相互包容的,而是各自独立、无明显关联的。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
可是,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农村社会原来丰富的社会资本开始变得不足甚至出现了匮乏。
1.生产过程中的互助与合作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互惠互利”取代。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易遭损害性特点使得一般个体家庭很难抵抗自然界各种不可抗力因素的袭击。因此,在春播、夏收、秋种等农忙季节,农户难免要向亲属和社区邻居寻求互助合作,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这种基于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交往与合作关系,本身就反映出一种经济活动中的网络关系特征。然而,调查发现,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的生产活动逐步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生产活动“讲效益”的观念开始为个体农民所重视。如今农村生产生活中的许多人情交往都是以货币这种交换形式出现的。比如盖房子时请帮工要付工钱(以前吃顿饭即可),搭村子里的个体运输车进县城要付车钱(以前口头致谢就行),连带有“互助”性质的随礼都出现了货币化的倾向,且随礼的数量越来越大。因此,农户在经济活动中的互助合作关系,不再仅限于一种传统道义上的“无私”帮助,而是更多体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交往中的“互惠互利”的原则。正如李守经所指出的,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其深层结构是人们之间相互的利益关系”[7]。
2.网络性社会交换逐渐被非网络性社会交换所取代。
徐晓军(2002)曾将乡村社会的交换分为网络性交换和非网络性交换两种形式。[8]网络性社会交换指的是发生在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交换,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包括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这些关系是按照“差序格局”构成一个同心圆式的网络。而非网络性社会交换是指发生于上述“差序格局”网络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交换,即陌生人之间的交换。这两种交换具有不同的交换模式,遵循着不同的交换法则。
第一,网络性交换的特殊主义交换模式被非网络性交换的普遍主义交换模式所取代。
网络性社会交换是在熟人之间相互信任基础上进行的。正如费孝通所言,“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9]。然而,乡土社会中的信任是“差序”的,在同心圆式的网络中,每个人的位置是固定的,相应地具有不同的信任程度。网络性社会交换正是依据信任程度而具有个别性、选择性和特殊性。对于不同的对象或者买卖公平或者给多取少甚至分文不取。可见,网络性交换是特殊主义的交换模式。而非网络性交换则突破了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网络范围,因而其交换不存在“熟人之间的信任”基础,可见,非网络性交换是普遍主义的交换模式。
第二,网络性交换的人情原则/感性原则被非网络性交换的经济原则/理性原则所取代。
在网络性交换这种交换模式中,赊欠是常有的事,往往是何时有何时再还上,也就是说,网络性交换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终极动因,而是表现为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取向和费孝通概括的“人情”原则,或者说感性原则。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不是为了获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也不是某种权力,而往往只是为了维持自己已有的社会关系网。因为对于一个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来说,关系往往要比金钱更重要。而在非网络性交换这种模式中,不存在赊欠,奉行的是“一次交清”。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中,取而代之的是理性选择和价格机制的结合。因此,经济原则而不是人情原则成为非网络性交换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非网络性交换是一种理性工具,它追求的是货币,而不是社会关系;它关心的是权利和利益,而不是交换的对象。3.和睦友好团结的农村人际关系日益淡漠化。
农村人际关系日益淡漠化,具体体现在家庭、邻里、村庄成员和村际等不同层面。[10]第一,传统的农村家庭结构是一种成员长幼有序的“差序格局”,其家庭内部关系是角色规范、分明: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则出现了父子不亲、婆媳不容、夫妇不和、兄弟不睦、老无所养的问题,这实质上破坏了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与人最亲密的关系,离散了家庭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内部的亲和力。第二,邻里关系在农村社会中具有生产上互济、生活上守望相助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作为唯一的政治、经济、生活共同体的农村,这些职能即使使社会担负得更多也不能在农村完全丧失。但在社会转型期,邻里由于利益得失引发矛盾和摩擦冲突不断,邻里功能大为削弱,使邻里关系更多地成为“地理”上的关系。第三,村庄成员传统上以质朴真诚情感和诚信有序好礼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友好、无私、团结、互助的良好人际关系体现在村庄成员之间。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村庄成员之间那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不断淡化,村庄成员之间的角色行为、思维方式、社会心态、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村庄成员之间交往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越发浓厚,心理交往距离扩大。第四,毗邻的村庄在传统上由于通婚圈狭小大都有姻亲关系,因此村邻间的交往是和睦、恭让、友好的。即使人际关系有时出现不和谐的因素,那也是单一化的。在社会转型时期,村际关系裂变的因素复杂化、多样化,使人际关系裂变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影响,甚至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总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出现了普遍的下降趋势和负面影响。农村社会资本的这种匮乏状态已妨碍了农民利益表达、利益平衡、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有效实现,降低了社会的整合能力,对政府治理与农村社区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制约。
三、新农村建设与重建农村社会资本
如何才能改变当下农村社会资本的匮乏状态,如何才能使农村社会仅有的社会资本发挥出其正面的效用呢?我们认为,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举措,应该是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一种理想的路径选择。
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发展”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和实质所在,因为老百姓只有“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廪实而知荣辱”。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和主体,所以,农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团结、协作的程度,也就是说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是否能够集体行动起来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为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中,我们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重建农村社会资本。
1.通过教育手段,尤其是利用在农村切实实施义务教育的机会,在青少年中不断加强德育教育,培育一种超越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广泛的信任与合作意识。
社会资本的获得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忠诚、诚实和互信等美德。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是基于道德习俗建立起来的,具有“路径依赖”性,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在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重建的关键是要超越血缘关系和家庭意识,克服现有社会资本封闭、分散和规模小的弱点,积累信任、合作、创新和规范等现代意识。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从青少年抓起,从德育教育做起。因为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教育给人们传输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从而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我们要制订出一套适合青少年的德育原则,针对农村社会资本缺失的具体问题,使青少年从小就懂得理解和运用信任、公平、平等、合作、勤劳、创新和博爱等理念,以达到对现有社会资本存量(即文化、习俗、规范、信仰等)进行改造。并通过加强农村中人们之间的认同感,来弘扬将社会资源共享和互助互爱的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念,批判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唯利是图的思想,为农村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奠定文化和伦理基础。
2.加快经济发展,为建立农村新型人际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基础是农村人际关系协调的构成条件。通过深化改革,提高生产效益,使农民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勤劳致富;加大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和科技培训的力度,使农民能够运用先进的手段进行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提高农业的技术含量,以促使其向现代农民的转变;通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合理收费项目,做好帮扶工作,从而解决农民的一系列生活问题,促使人际关系与经济发展向着同一个方向变迁;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要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等手段,正确引导、科学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营造优化群众交往环境,建立和完善促进人际关系健康有序发展的经营机制。
3.加强村委会的建设,提高农民参与集体事务的意识和能力,为促进民主政治的现代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提供组织平台。
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公民参与能够巩固国家制度,意大利的经验表明,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社会实践,地方政府的民主改革给地区政治社会生活带来了看得见的、大部分是有益的影响,改革转变了旧的权力模式,创造了意大利统一后从未有过的真正的地区自治。[11]中国的村民自治与意大利地区改革也有类似之处。从1987年《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通过算起,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推行也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了,虽然这一制度变革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但是村民自治倡导的农村群众自主管理农村事务的精神,以及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行,村民自治总体上改变了以前农村基层干部由上级任命的传统。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选举参与、依法抗争等政治参与活动,正在把老实巴交的“顺民”、爱顶撞权威的“刁民”塑造成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12]村民自治运动和自治组织的发展,在客观上会促进适合民主政治的现代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也实现了新农村建设中的“管理民主”的要求。因此,在中国推行村民自治就是一项能够创造现代社会资本的制度改革,这在一些村民自治规范运作的乡村地区已初见端倪。只有真正地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才能够发挥家族等农村原有的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实现家族、民间宗族组织等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现代社会资本。
物质与精神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只要在农村村民中间建立起一种能够理解和运用信任、公平、平等、合作、勤劳、创新和博爱的理念,也就是说培育了村民的“公民心”,即村民集体行动的意识,这样才能形成发展农村经济的“合力”,这种公共精神又会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正如普特南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即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与分布均衡,政府工作运行效率就高,这个社会就有效率和活力;反之,社会资本缺乏或下降与分布不均,政府工作运转就效率低下,社会就没有效率和活力。[13]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2]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54.[3][4]Ale-jandroPortes,“TheEconomicSociologyofImmigration:AConceptualOverview."InPortes(ed.)TheEconomicSoci-ologyforImmigration:EssaysonNetworks,EthnnicityandEntrepreneurship,NewYork:RussellSageFoundation,1995.[5]RonaldBurt,StucturalHole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2,P9.[6][11][英]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95,中译本序(P1-2).[7]李守经.农村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70.[8]徐晓军.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J].社会科学辑刊,2002,(1):45.[9]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10]胡飞.试析转型时期中国农村人际关系的变迁[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7):114.[12]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J].社会学,2003,(9):80-81.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
文档上传者
- 农村
- 农村离婚
- 农村文化
- 农村讲话
- 农村讲话
- 农村选举
- 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
- 农村改革及农村城镇化
- 农村土地流转
- 农村会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