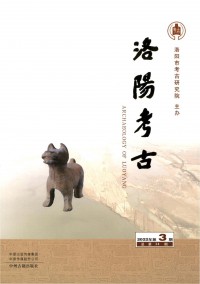考古范文精选
前言:在撰写考古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作品,小编整理了5篇优秀范文,希望能够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古铜矿遗址考古研究
岩阴山脚遗址考古成果
2011年12月,考古队调查发现了岩阴山脚遗址。遗址南北长约150m,东西宽约100m,面积达15000km2(如图4所示)。遗址所在地现已规划成铜绿山遗址博物馆新馆建设场所。由于自清代中期以来,当地村民在此开荒改田,修坟立碑,尤其是近几年滥采铁、铜矿石,遗址遭到了严重破坏。为配合新馆建设,2012年6月至今,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前,对遗址进行普钻,掌握了遗址范围和文化堆积情况;然后选择适宜地段布置探方发掘,以尽可能了解遗址的功能布局及文化面貌,重点在遗址南区和北区布5×5m探方26个,面积650m2,现已基本完成发掘工作(如图5所示)。暑去冬来,发掘工作精细严谨,初步了解到遗址功能分区和文化内涵。文化遗存的时代主要为东周和清代。在遗址南区和中部已揭露冶炼场和选矿场2处,北区发现圆形探矿井1座。出土了一批矿冶生产和生活遗物,尤其以东周遗迹较为丰富。发现的主要遗迹如下:1)南部发掘区。揭露一处含选矿的冶炼场,遗迹十分丰富。其中有选矿场铁矿石堆积遗迹1处、硬壳状遗迹1处、炉基遗迹1处、和泥池2个、脚印35枚、工棚柱洞8个等(如图6所示)。选矿场位于冶炼场东边缓坡地带。在东西长15m、南北宽约10m的红色粘土上,遗存有1处铁矿石堆积。经地矿和选矿专家共同鉴定,铁矿石多属品位较高的“平炉矿铁”,目测含铁量可达40%~60%。由于选矿场遭到晚期人为严重破坏,故铁矿石堆积厚薄、平面密疏程度不一(如图7所示)。工棚遗迹位于选矿场西边,有8个柱础洞,排列有序,据推测是当时冶匠为避雨防晒用木料搭建的工棚。灰坑(垃圾坑)2座,叠压在选矿场下。灰坑形制规整,平面为圆形,坑底呈锅底状。灰坑内堆满灰褐色土,土质较为致密,含有较多的木炭颗粒和小块铁矿石及少量东周陶器残片,陶器类见有罐、甗。硬壳状遗迹残存范围达48m2,疑似炼渣(如图8所示)。地层断面可见该炼渣有3层叠压,每层渣体呈大面积的薄形硬壳状,厚0.6~1cm,质地坚硬,灰褐色。3层之间或夹有浅黄色土或灰黑色土,这种硬壳状“炼渣”为首次发现。经鄂东南地质大队实验室对这种硬壳状“炼渣”进行初步检验和光谱分析,发现它以硅化铁物为主,还含有铝、铜、磷、钛、钙和其它微量元素,其中铜含量0.8%。为了弄清疑似“炼渣”的性质和成因,我们多次请矿冶专家进行现场分析鉴定,但对其认识不一致,主要有人工形成说和自然形成说二种。结合地层等关系,我们认为是人工形成的可能性大。和泥池平面为圆形,呈锅底状(如图9所示)。清理时,池内堆满揉和过的高岭土和红色粘土的混合土,土质粘性大,并夹杂2块东周陶片,初步推定该粘土用于涂抹炼炉缸内壁,为一种耐火材料。在冶炼炉基旁边超过10m2的黄土面上,先后发现足迹35枚(如图10所示)。其中,既有完整单个脚印(如图11所示),又有多个相互踩踏的脚印,弥足珍贵。为了确定足迹真实性,进一步弄清足迹的类别、人体身高、行走姿势、保存环境等历史信息,我们邀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主任法医师张继宗教授、足迹学专家刘伟平、武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刑侦专家郑道利等携带专业器材赴现场,共同对考古人员发现的足迹进行检测鉴定。专家们为了尽量原地保护足迹现状,首先非常谨慎地对考古方法标记的27枚足迹随机选取4枚(足迹编号为16、25、26、27),刮除考古方法刻划的足迹轮廓线条,均露出原始足迹的面貌,结果证明,考古方法发现的足迹真实可信。接着,专家们还在已发现的27枚足迹之间的空白地带轻刮足迹承载体(即黄土界面),再次发现8枚足迹(编号为28~35),足迹总数达35枚。经对上述12枚足迹现场取证,室内对比分析鉴定,确认12枚足迹皆为古人赤足脚印。其中部分赤足脚印完整,部分只能显示赤足轮廓,有的仅存前掌或足后跟。完整的赤足印痕长者26cm、短者25cm,从而推测12个足迹中起码为2人所留存。专家们还根据现在群体足长与人体身高关系推断,赤足中一人身高为1.72m,另一人身高1.52~1.54m。结合部分赤足有重压痕偏外、横向移位等痕迹,确定此类赤足者有负重特征反应,反映了当时冶匠搬运什物的劳动场景。2)中北部发掘区,已揭露面积达58m2的冶炼堆积1处,土色呈黑灰色,从发掘探方之外的田土和以往村民乱挖铁铜矿石废弃的断面观察,这层堆积从岩阴山腰向山脚延伸,如此大范围的堆积绝非偶然,应是若干炼炉长期生产所致。在所发掘探方之中,这种黑灰色堆积层较厚,包含有较多的木炭颗粒和少量的红烧土颗粒,局部堆积还含有一层铁矿粉和较多经人工整粒遗弃的小块铁矿石。此外,还发现有少量的炼渣(如图12所示)、氧化铜块(如图13所示)、炼炉残块及东周陶片等,说明黑灰色堆积层应为东周时期的冶炼后废弃堆积物,可佐证此地应是冶炼区。3)遗址北区。发现圆形探矿井(编号J1)1座,圆井开口略大,往下渐渐变小,至井底收缩成近长方形(如图14所示)。圆井口径1.90m,井深4.62m,其中,井口至井深2.9m厚开凿于高岭土层,其下1.72m深则开凿于高岭石化层。井口周壁有古人凿井提升土石留下的绳槽痕。井内填土可分为3层,出土遗物十分丰富,主要有东周时期陶盆、罐等残片,还有数十块铁矿石、石块,木炭、竹器残片、横向支撑木(如图15所示)、木器柄及果核等(如图16所示)。由于该矿井中的石质层未发现铜铁矿脉,推测是当时的矿师果断放弃了探矿井。探矿井遂成为垃圾坑,不久,因某种原因对探矿井又进行一次彻底填平。我们挖掘探矿井时,在相距古井口西边约25m的高坡处,适逢鄂东南地矿大队的一座探矿钻塔正在机械作业,钻孔编号为2303,最终孔深达1086.52m。据说,钻孔岩芯因一直未见铜铁矿层而停钻撤离。比较古今探矿井孔,勘探结果如此相同,充分反映了古代矿师高超的探矿技术。
对遗址保护区考古成果的初步研究
1)首次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区内开展专题调查,发现了12处冶炼遗址,不仅填补了保护区文物点的空白,而且初步认识到这里的冶炼遗址都分布于采矿点附近的山腰或山坡下,频临溪湖之畔的特点,这为探讨古代采冶结合、就采冶炼、临水选址的理念提供了实物资料。2)岩阴山脚遗址的初步发掘,发掘出一批东周灰坑、选矿场、冶炼堆积、灰沟等遗存,丰富了对遗址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在遗址上所发现的选矿场遗存,大批高品位铁矿石及废石有序的堆积在一起,揭示了在冶炼之前,古代冶匠就近对矿料进行过一次初选,这样做不仅减少了矿石搬运成本,而且确保了矿料的质量,反映了古代冶匠严谨的选矿程序和娴熟的选矿技术。3)遗址东北部发现一口圆形探矿井,增添了以往发现探矿井的种类。尽管仅发现一口探矿井,井周壁没有以往发现的方形竖井常常采用较密集的竖向支撑木加固井壁的方法,但圆形井壁对外形成张力的安全性,可节省支撑木用料的认识和快捷凿井方法均为古代工匠所掌握,反映了古代探矿技术的变革和探矿水平的提升。4)多学科协作成为本次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一个亮点。尤其是岩阴山脚遗址的抢救性发掘超出了预期收获,许多遗存为首次发现。其一,岩阴山脚遗址发掘出土最多的是各类矿石及废石,生活陶器残片极少,经地矿专家对出土的矿石进行鉴定,以铁矿石为主,可作为确定遗址性质、功能的参考物;其二,对新发现的2种疑似炼渣,委托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秦颖教授等进一步做成份分析,其鉴定意见一旦给出,可作为判定遗存性质的重要依据;其三,在岩阴山脚遗址南区选矿与冶炼场所发现的35枚足迹,弥足珍贵。经公安部物证中心权威法医师和足迹专家现场勘测和鉴定,获得大量古代冶匠足迹信息,这批足迹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冶炼(或选矿)遗址上首次发现数量最多、保存状况最好、足迹者身份最明显、时代最早的古人赤足印迹,填补了矿冶考古空白;其四,发掘中十分注意对每个遗迹收集土样,并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植物考古的博士来现场进行浮选,对少数出土的植物标本做初步的鉴定工作。浮选植物样本是一项基础工作,可进一步研究古代岩阴山脚遗址乃至铜绿山一带的气候、农作物、植被种类和人们食物组成等方面的内容,可从一个侧面揭示当时活动在遗址上的人类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便于全面深入了解遗址的内涵。因此,下一步计划将浮选出的样品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做成份分析。以上多学科合作的考古成果,为深入开展矿冶史研究、科学制定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保护管理计划,提供了新的基础资料。同时,为了保护好揭露出的各类遗迹,以便将来展示,推进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申遗”工作,经专家论证,现已暂作回填保护处理。5)结合以往资料和新获矿冶考古成果,还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本地区古代矿冶遗存的宏观探究内容应包括铜、铁等资源开发的源流、工匠族群来源、掌管铜、铁的政治集团及铜、铁资源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贡献等;除矿冶遗存是我们保护、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外,遗址区域内及鄂东南地域的同时性和历时性,古代工匠居住废墟、农业生产区、燃料生产地、城址、水运码头、墓葬及粗炼铜、铁输出地等如同一根根交错的链条节点,都应列入古矿冶调查、发掘和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些都是复原和展示矿冶文化不可忽视的对象,也是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建成独具特色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申遗”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遗产资源。
本文作者:陈树祥冯海潮席奇峰张国祥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科技考古助推考古学新发展浅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考古学界针对“中国考古学向何处去”产生了激烈讨论。其中,如何看待自然科学的作用是这一讨论的重要内容。按照夏鼐的定义,考古学是一门利用实物遗存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科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其研究对象是反映古代人类活动的实物遗存,不只限于古代器物,还包括人类居住及其他活动的遗迹和反映古代人类活动的自然物。遗存的自然属性,决定考古学必须要借助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展信息提取和价值挖掘工作。作为获取资料的技术和研究问题的方法,科技考古应运而生,逐渐发展成为考古学重要的分支学科。30多年过去了,中国考古学发生了巨变。除了新发现、新认识之外,科技考古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并大力推广的研究范式,也成为考古学的二级学科。
一、科技考古世纪沧桑
20世纪早期,地质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航空遥感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便逐渐用于考古调查和研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碳十四测年、分子生物学等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考古学注入了更多科技元素。北美新考古学派的兴起及其对实证主义的推崇,更是加速了科技考古的发展。1924年,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就提倡“除考古学家外,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学、动物学、化学……各项专门学者,与热心赞助本会会务者,协力合作”。当此之时,王琎对五铢钱等进行了成分分析,杨钟健对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动物遗存进行了专门研究。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之形成》的主体部分便是体质人类学的测量与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夏鼐为代表的新中国考古学家对于自然科学方法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动植物残骸、人类遗骸、冶金遗物、陶瓷制品等相关遗存的收集与研究工作,还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碳十四实验室。20世纪90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模式。进入21世纪,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第一至第五阶段的推进,科技考古逐渐走向深入。
二、承担更多学科责任
这是对科技考古的肯定,激励着科技考古工作者承担更多的学科责任。近些年,随着科技考古相关方法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考古逐渐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念之一。相关案例不胜枚举,河南二里头遗址与陕西血池遗址的相关研究即是典型代表。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伊洛河交汇之处,是东亚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重点,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中国考古学学科范畴内科技考古研究力量介入最全的一处遗址,研究团队集结了碳十四测年、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人骨考古、食性分析、冶金考古、玉器与陶器科技考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这些研究揭示,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当时伊河与洛河汇合于遗址以西后,流经遗址以南,形成了二里头依山傍水之势。二里头文化继承了龙山文化晚期粟、黍、稻、麦、豆同时种植的谷物农业和猪、狗、黄牛和羊共同饲养的家畜饲养业。其中,粟作农业是二里头先民的主要生计,也是猪、狗、黄牛主要的饲料来源。作为王都的二里头,存在高比例的外来人群和家畜,这应与人群、动物资源向都城汇入有关。二里头遗址手工业生产需要的金属矿产、玉石资源、白陶等原材料与产品皆有复杂的资源网络,相关产业链和核心技术则主要由服务于王权的贵族与专业化工匠所掌控。概而言之,二里头遗址的科技考古综合研究丰富了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历史内涵,实证了二里头王国坚实的经济基础、发达的资源网络和高超的政治文明。血池遗址是陕西凤翔秦故都雍城西北郊的一处大型祭祀遗址。据考证,该遗址与秦汉时期国家级祭天场所“雍畤”有关。司马迁曾随汉武帝前往雍畤祭天,并在《史记》中记载“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如今,与祭品相关的文献早已散佚湮灭,要复原这段历史,只有考古学能担此重任。2016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一系列田野发掘出土了大型宫殿建筑、祭祀坛场、祭祀坑、附属道路系统等祭祀设施,玉器、木质车马与青铜车马器等祭品,以及大量马、牛、羊等动物牺牲残骸。其中,祭祀坑所用马牲的综合研究涵盖了动物考古、食性分析、锶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科技考古方向,集中体现了科技考古对考古学研究的巨大贡献。研究发现,马牲的年龄基本在2岁左右,相当于《说文》中“驹”的年龄。颜色以栗色为主,运动资质较为平庸。马牲来源地较广,应是依托当时的马政系统,主要由分布于西北边郡的牧师苑征集而来,在杀祭之前它们曾被用粟、黍及谷草集中饲养过一段时间。这些工作实证了《周礼》“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则系于牢,刍之三月”记载,为研究“祀贡”制度提供了证据。二里头遗址与血池遗址的研究是科技考古助力考古学实证“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代表性案例。近年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项目的推动下,碳十四测年、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古DNA研究等科技考古研究领域均取得了较大突破,在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未来的科技考古还将在书写人类历史的考古实践中肩负更重要的学科责任。
三、推动“三大体系”建设
亚洲动物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进入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1867—1919年,自此进入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美国人庞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珍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世纪40年代—1919年),戴尔(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1919年—20世纪4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前一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研究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性行为、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考古研究成果讲话
各位专家、朋友们:
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家文物局向获得第四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的学者和单位表示衷心的祝贺!向精心组织此次评奖活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来自国内考古学界的专家评委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夏鼐先生是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学养深厚,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在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的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生前以学风严谨、实事求是著称,促成了一大批优秀考古学成果的面世。以夏鼐先生捐献的稿费作为基金,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继承了夏先生生前的优良传统,该奖自设立以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日益成为国内考古学最具学术权威性的奖项之一。该奖项的评选对我国考古学的学风建设、提高考古学研究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已经举行的四届评选活动中,共有37项考古成果获奖,其中包括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殷周金文集成》等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获奖的成果中,田野考古报告达33项,约占获奖总数的90%。获得本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的《郑州商城》、《桂林甑皮岩》、《西汉礼制建筑》、《舞阳贾湖》、《盘龙城》、《马桥》、《河姆渡》等都可以看作是高水平的田野发掘和高质量的发掘报告相结合的典范。另外一项获奖成果——《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虽是出土文献的整理,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类型的田野考古报告。由此可见,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一直是评委们关注的重点,这与夏鼐先生生前十分注重田野考古基础工作的作法是一脉相承的。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一直把提升田野考古工作质量和科技含量、加强考古报告的整理出版、促进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列为工作重点,积极推动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我们注意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的一批考古研究机构,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一批较高水平的发掘工地和高质量的发掘报告不断涌现出来,最近我们对考古报告出版情况做了一个初步统计,仅近三年国内出版考古报告专刊就达120余部,近五年考古报告出版的数量已占到建国以来的考古报告数量的40%,与此同时,考古学相关研究和科普著作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为了适应新形式下我国考古发掘管理的需要,进一步鼓励广大考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国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进步与发展,从今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将在田野考古奖之外另设立优秀考古报告奖,旨在进一步推动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和出版工作。这一奖项将两年评选一次,它应该和“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文物考古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八十余年的辉煌历程。今天,考古学这一人民的事业,更得到党和国家、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各界的空前关注。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新时期中国考古学的繁荣和发展共同努力,共同开启考古学发展的新篇章!
考古雕塑管理
摘要:王子云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载入法国《现代艺术家辞典》的唯一中国画家;四十年代举办了我国第一次敦煌艺术展;建国后,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雕塑史专著《中国雕塑艺术史》。把考古和雕塑结合在一起深入研究,是现代考古和雕塑的奠基者之一。
关键词:考古雕塑艺术结合研究奠基者
原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美协陕西分会名誉主席、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王子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雕塑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教育家。1990年,先生以93岁高龄寿终,将近一个世纪致力于美术教育、考古和雕塑,一生甘为人梯、甘做铺路石,为重振中国的考古和雕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我国现代考古和雕塑艺术的奠基者之一。
王子云,1897年出生于安徽萧县,1916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0年后,在北京从事美术教育和“五四”新美术活动;1926年任中山大学民众教育馆艺术部主任,任职期间,发起了“南京美术展览会。”1928年受聘为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讲师,曾协助学校在上海、日本东京举办国际性的美术交流活动。
王子云一直注重提携、奖掖后进。在北京从教期间,他发现北京美术学校学生、萧县同乡刘开渠精于绘画和雕塑的特点,了解到他因为经济拮据,难以继续读书的情况后,便慷慨解囊,并积极联系萧县同乡基金会对他施以救助,帮助刘开渠走上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上世纪七十年代,已进入暮年的刘开渠深情地回忆说:“二十年代,我在北京读书时,只有十几岁,举目无亲,生活难以为继,王子云老师接济我、鼓励我、帮助我寻求半工半读的办法,并联系萧县同乡基金会援助我。毕业以后,又鼓励我到法国学习雕塑,使我对自己的追求充满了憧憬与渴望。我1933年回国以后在国立杭州艺专任雕塑系主任和教授,他1937年留学归来,立即到杭州艺专任教,支持我、壮大我所在的雕塑系,和我一起共同培养雕塑人材。他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帮助我,我无法忘记他对我的栽培和支持。”
在他的帮助下,还成就了著名花鸟、篆刻艺术家王青芳。王青芳是他的堂弟,在王子云先生的资助下,1923年入北京美术学校学习,并根据他的特长,引荐他拜国画名家陈师曾、萧谦中、王梦白,国画学会的金拱北和国画大师齐白石为师。后来,王青芳集中精力向齐白石学习花鸟画和篆刻治印,并在篆刻基础上研究木刻版画,曾刻有屈原、司马迁、杜甫、王维等古代文学艺术家画像存世,号称“万版楼主”,求刻、求画者不绝于门,是名动京师的著名花鸟画家和篆刻艺术家。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