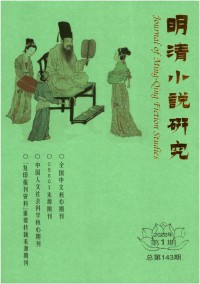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加强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加强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历史上,宗族制度和宗族思想,对徽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诸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因此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的真实状况做一深入的探讨,是很必要的。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时期。宗族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族人的言行限制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族产的设置和迅速扩展,发展到后来,在乡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形成“穷村乡,富祠堂”的局面,使族人从经济利害关系上与宗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得不俯首贴耳听命于宗族的权威,而这种“听命”,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甘情愿的。关于以上几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说,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拟着重讨论宗族对乡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影响力,和在乡村事务中的仲裁权问题。
元末明初人朱同,在谈到休宁潜溪汪桂编修族谱,并在祖墓前构筑“永慕亭”拜祭祖先之事时,联想到当时社会的一般风尚,慨叹地说:“宗法久弛,姓氏混淆,……亲尽然后为途人乎。”[(1)]可知元末明初,徽州的宗法关系处于“久弛”的状况。弘治十六年,祁门三四都凌氏族丁凌友宗,因“家中屋宇狭窄,人众难以住歇,前往本府婺源县迁居”。由于“本年系凌友宗应门户官差”,如果他甩手一走,这些差役税粮由谁承担呢?他的兄侄们不许他就此迁走,于是订立文约,将承租开垦的荒田其本人的分籍尽数拨给子侄凌胜宗等人名下,由他们耕种、收租、管业,并“供解门户差役税粮等项”。如果将来凌友宗的子孙回宗,“听照管业,同管门户”[(2)]。此文约牵涉到宗族内的纠纷,照理应有族长、房长、家长出面签押,然而文约中没有出现族长、房长、家长的字样,说明弘治时期,在有关族内纠纷事务中,族长、房长、家长尚不能发挥较大作用。正德四年,祁门十五都郑狮与族弟郑琼,因山场“互界不明”,引起争执,二家讦告到县。县官批示排年康续韶、里老汪永良等到山场踏勘,此间“二家思系亲族,不愿终讼”,于是撤讼,凭排年里老劝谕作中,订立合同,解决了争执。这件讼事实际也是宗族内部的纠纷,不在族内解决,而是到县衙去解决,从整个讼事中看不到族长、房长、家长的影响和权威,反而是排年、里老的劝谕调解起了决定作用,说明明中期前后,族长等尚没有很大权威,宗族对乡村的统治还比较薄弱[(3)]。
明中叶以后,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逐步加强,到清前期,则达到其鼎盛时期。太平天国之后,宗族的统治有所削弱,但余威仍不可忽视。顺治十三年,祁门六都善和里程氏宗族打算重修窦山公寝庙,由于经费缺乏,欲从众存族产的一千五百秤租中提出十分之二“众贮公支”,递年积攒,即可弥补修祠之不足。于是订立了《众立提轮谷重造窦山公寝庙并祠旁庄屋合文》。虽云“众立”,但押约者并不是众多族人,而是两位家长,可见提取众存产业租谷补作修祠费用一事,主要出自两位家长的意志。合文中有“有敢徇私破公强梗拗众者,即准不孝论,声罪鸣官,仍依此文为准”的字句,可以看出,由于众存族产族众拥有分籍,即可分到经济实惠[(4)],提走一部分,族众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因此一些族众会有不满情绪,但如果不服从家长的意志,“强梗拗众”,则会背上不孝的恶名,受到声罪鸣官的惩罚[(5)]。可见清前期,宗族中族长、房长、家长的权力很大,可以自行决定宗族中的大小事务,无人敢违拗反抗。嘉庆二年,休宁县官府指令一都八图王姓族长王惇裕等写立甘结文书,证明本族人捐职从九品的王荣锡“身家清白,以及三代出身并无违碍等情。”[(6)]官府需证明乡民的身家是否清白,三代出身是否有违碍,不委托里甲出面调查办理,而是指令族长和邻居写立证明文书,说明清代徽州的乡村,很多事务主要是由宗族在把持,里甲的权力和作用有所削弱。宗族的权威,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也得到官府的认可。乾隆年间,休宁县宰靳宗著,初到休宁时询问民间疾苦,了解到社仓的弊端,“胥役因得渔猎其间,甲户贿脱,又及乙户,流毒蔓延,四乡为之不安。”靳宗著洞察其弊,周咨士民,决定采取借用宗祠的力量管理社仓的措施:将管区内的族姓祠堂列名,设立名*,凡祠堂充管三年,再轮别族宗祠充管,按名*的排列顺序轮流管理。他并将此一措施“详明上官,永为定例”。据说此方法实施的结果,“邑民便之”[(7)]。政府官员和当地士民对宗祠管理乡间事务的信任,远远超过对胥役等人的信任。宗族不仅控制了本族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插手如社仓之类的地方政府赈济机构的管理,深刻地反映了徽州宗族在清代对乡村统治的有力有效。
一、宗族的统治渗透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徽州的宗族提倡“骨肉亲情,同族为一家”,宗祠往往置有义仓义宅、使贫乏的族人不至饿死沟壑,也使族众能安然渡过灾荒。如歙县潭渡黄天寿,晚年“割田百余亩以赡族之贫者,故建义仓以为出入之所。且请于官,别立户收税,以为永久之计。有司上其事,抚台锡扁嘉奖,鼓乐导送,以为里俗之劝。”以后族人塑其像于义仓内,岁时祭祀[(8)]。嘉靖十年,歙县郑贵孙在郑家埠头上郑氏宗祠之左建郑氏义宅,使族之贫者有了安身之处[(9)]。这样的事例在徽州可以说不胜枚举,宗族将他们作为族人的榜样,在族谱上大书特书,地方官和缙绅士大夫在修地方志时,也对此大加褒奖,一些动人的事例在当地世代流传着。明初,婺源理田李氏宗族有三兄弟,欧鹄溪驿卒死亡,长兄被怀疑是凶手,官府要捉拿他,长兄逃走了。两个弟弟挺身而出,赴官衙为哥哥洗清罪名,官府对他们施以酷刑,二人百刑备尝,被关押了四年。幸亏新上任的县宰李公成,疑心此案有误,重新提审他们,老二李士昌说:“兄逃我长,我当其辜。”老三李士昭说:“帮助长兄逃走的是我,我愿以身代。”弄得县官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想方设法为他们平反冤案时,恰遇大赦,县官放他们出狱,并赐与孝友的匾额使其荣归,以褒奖他们的崇高品德[(10)]。不仅一家之中互相友爱关心,一族之中,一人有难,众亲援手。潘氏篁洲公任仙居令时,因逋赋被罢官,上司仍严令追缴。潘氏兄弟纷纷典衣质产,并力集资,代为完缴,使篁洲公免于追呼[(11)],体现了族人之间忧乐相共、有无相济、相扶相顾、相恤相助的融融亲情。康熙年间,徽州张姓户丁张得育离开家乡到外地买地造屋,二十年后,因在外地生活艰难,又回到家乡。张姓宗族为此商议,认为“当思一脉流传,各全孝义,和睦为上”,因此订立了《孝义合同》,张得育可以住进原先的房子,管理旧时的产业[(12)]。人们在外经营失败后,回到家乡仍受到宗族的欢迎,得到原先的财产和权力,确实体现了宗族社会中族谊的温暖。这种族谊,增强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使族人自觉自愿拥护宗族,这恐怕也是宗族能长期存在的魅力之所在。这种传统,使中国的下层社会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然而,当族人之间的互助成为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时,也不能不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明清徽商崛起,当某人在外经商成功时,亲族人等蜂拥而至,或到他那里找点事做,或依赖他养活,史籍中不乏“赖以全活者数千指”、“赖以举火者何啻数十上百”的记载。如明代徽商方大经,经商致富后,他的三叔父经商破产,方大经解囊资助。二叔父落魄,他资助以本钱,二叔父又再次破产,他再次资给,多次资助毫无怨言倦色。亲族之中,很多人依靠向他借贷本钱去经商,有些人根本不还本钱,甚至有累借数百金而不还者,他毫不放在心上。依赖他而生活的亲戚,仅母族方面就有数十上百人[(13)]。他的友爱互助行为,固然被作为“义举”、“善行”而载录于族谱等史籍中,但也不能不令人产生忧思,一个商人刚刚发财,马上有上百的亲族人奔来依赖他生活,无形中使某些族人产生依赖他人的思想,不肯自立,丧失了进取心,也势必造成商人的沉重负担。如果形成风气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为了团结控制族人,宗族还插足民间的宗教活动。雍正年间,徽州胡氏宗族在修葺家庙之事告竣后,又认为“祠右古刹为一村香火,如雄殿山门将岌岌乎不可支,”修葺古刹之事刻不容缓。于是鸠工庀材,用两年的时间将古刹修葺一新。又感到应在其中供一长明灯,使香烟不绝于宝殿,钟鼓嘹亮于梵宇。为能留住僧人,使佛灯长明,胡氏宗族建立了佛会,佛会会员“每名输租二秤,递年照时交银,积贩置田”。三年后,就置买了田租达十余[石]的田地,每年轮派二人管理田租收支等事[(14)]。反映了宗族积极掌握民间宗教活动的情况。
宋元以来,徽州一些世家巨族流行修建寺庵道观,委托僧道人等代为祭祀祖先的风气。如唐宗室后裔、婺源严田李氏宋元时建立九观十三寺祭祀祖先,世承香火,奉祀不懈。其中仅“思显庵”就设置庙产三百余亩,两房火佃供僧管解[(15)]。祁门十一都盘溪吴氏,于宋代修建“永禧庵”,设置庙产百亩,以供僧人梵修日用。僧人刻吴氏五二公像,设神主牌位,岁时有祭祀之仪,朝暮有香灯之敬[(16)]。这些寺庵道观实质上成了变相的宗族家庙。徽州明清时关于大族之间争夺寺庵的案例记载,说明某些寺庵确实是由宗族掌握的。大族之所以要争夺寺庙,一方面,它是宗族地位和权势显赫的标记,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庙产的丰厚。
社祭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祭祀土神、谷神,祈祷丰年的敬神活动。洪武三年,皇帝诏天下乡民立社,普遍施行社祭。由明至清,徽州的一些宗族积极插手社祭活动,大多数的社为宗族所掌握,逐渐演化成宗族性的社。休宁茗洲吴氏,在明正统十二年以前举行社祭时,尚有别姓一同参加。在正统十二年的社日,宗族将四户别姓人“尽绌之”,增人吴姓族户如其数,自此,社就应称为吴姓的族社了[(17)]。村社演化成族社,反映了宗族统治的加强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徽人有建立各种会社的习俗,明清时期,宗族成立或掌握了各种形式的会社组织:有的属于祭祀祖先的;有的属于祭神、迎神赛会以及驱鬼禳灾弭病的;有的属于同年会性质的;有的属于文人结社性质的。通过众多的会社活动,宗族组织、影响、控制了族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历史所保存的清道光年间的《舒氏收租簿》,其中“众存神会、祀会租谷”项下列有:
(1)祭祀祖先性质的:咸宜堂宗祠冬至会、大虎形清明会、蟹形清明会、伯兴公清明会、志道公冬至会、始祖德舆公冬至会、红钱清明会、暾公会。
(2)属祭神迎神赛会等庙会性质的:土地会、东山庵仙帝姑会、兴裕堂天川会、咸宜堂天川会、周王会、上帝会、关帝会、琉璃会、麒麟会、张康会、高芹桥会、旗伞下元会。
(3)属敬老同年会性质的:祖父同年会、春老社会[(18)]。
可以看出,宗族掌握的会社,类型杂、数目多、涉及面广,深入到族人生活的不同方面。
宗族对传宗接代、继承宗祀十分重视,为保证宗族源流清白,决不允许非本宗族之人承继族人为后。规定早殇之子或无子之族人,应在侄辈中立嗣过继一人以接奉香烟,只有已立有嗣子,才能保持应继承的祖产份额。在立嗣过继时,往往事先要与宗族商议。写立的承继文约,一般也有宗族人等押约。在有可能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宗族要出面加以干涉。明代,黄氏宗族黄琼显老人育有五子,他在生前亲自将家产裁搭阄分给五个儿子。他去世后,五个儿子各管各业。万历年间,第五子去世,没有孙子继宗,“理合议立继祀”。长房的孙子嘉瓒、次房的孙子嘉瑞均年长于他们的五叔,“理不该继”,但由于当时五儿媳的坚持,因而以长房孙辈嘉瓒过继给五房。不久,五房孀媳改嫁,长房大孙子又去世,长房仅剩嘉瓒一个孙子,已过继给五房,因此长房又成为“故绝户”,“嘉瓒不能绝亲父祭祀而续五房香烟,而五房也不能因嘉瓒归宗而乏祀无依”,出现承继矛盾后,正当亲族内还未商议出个结果时,二房之子嘉瑞突然递呈到县,县主祝爷公断说:“嘉瓒继(五房),不独年长于继父,而自绝以他人之绝,天理人心何在?”批示族长、保约黄燮、黄潭等商议个合适的解决办法立即回报县主。族长等人商议结果,让嘉瓒归宗,“以三房以恩次子嘉璘承祀(五房)”。县主予以批准。嘉璘“思念父祖一脉,不忍相残”,因而“继义而不继利”。也就是名义上过继,奉祀五房香火,但并不继承五房财产,将五房财产“义与四房均分”。于是在族长等人的主持下,将五房的田土、山塘、房屋、佃仆等作四股均分[(19)]。当继承出现矛盾争执时,是二房的嘉瑞挑起讼端。族长等人在息讼劝谕过程中,主要是在做财产的重新划分工作。从订立的《义祀合同分单》看,五房被其他四房瓜分的产业颇丰,有六十八号田地、山、园、塘、伙佃庄屋等,还有三房仆人。可见,嘉瑞明里提出过继不适当的问题,挑起讼端,实际上是对五房丰厚的财产虎视眈眈。在众亲族如狼似虎的环视下,被推举出的过继人嘉璘“思念父祖一脉,不忍相残”,说明隐伏着“相残”的危机,他自动放弃五房的财产,实在是不如此就不得安生的无奈。这里,因为立嗣分产是宗族内的事务,因而县主批示族长等人去商议解决。可知万历时,当立嗣过继发生争执时,不经宗族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道光二年,黄浩科夫妇六旬无子,族中房侄黄可灌愿过继给老人做儿子。于是向宗族提出申请,并与母亲、伯叔、兄弟等亲属商议,最后订立《承绍继文约》,可灌过继并承接黄浩科夫妇的各项产业财物,同时为老夫妇养老送终,承担百年后的拜扫祭祀等事,也要承担老人各项门户差役钱粮等事。所立文约中说,黄可灌将过继之事“向族并身亲母、伯叔、兄弟、又兼友邻亲眷”商议,把宗族摆在第一位。文约后有几位族老作中的押约签名[(20)]。道光五年,黄泰晨因年老无子,托凭亲族商议,将弟弟的二儿子过继过来为嗣子。在写立的《承继文书》上,也有宗族中的四人押约签名[(21)]。可见在过继立嗣问题上,宗族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徽州风习,父亲在世时分析家产,一般由父亲主持阄分即可。但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不是按照传统均分惯例的话,有时不经宗族认可,分产合同就难以成立和持续有效,因而当出现不均分产业时,往往要请族长、房长等出面押约签字,才能使分产合同真正有效。万历四十六年,祁门十五都奇峰郑氏宗族郑三元老人,生有四子,前三子均已为他们婚配多年,只有四子年幼尚未成婚。老人已六十七岁,患有重病,身无余积,担忧四儿子将来娶妇艰难,因此托凭族长郑懋官等为中见证人,写立分产合同,将“住后山场并在山杉松各样杂木花利及山骨,尽数津贴”小儿子,“以为娶亲之资”。又将另一处山场阄分与其他三个儿子,要他们“各凭埋石疆界管业,无许侵犯混争”。如不听,则按“不孝论罪”[(22)]。因为不是平均分产,所以特请族长出面作中,押约签字,使分产能被承认有效。可见在分析家产的事情上,宗族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徽州各大宗族对教育都十分重视,希望族中不断培养出举人、进士。徽州明清古建住宅的马头墙上,大多筑一个形似方印的东西,据说是因为徽商虽然很有钱,但仍认为只有做官才是最高理想,只有走科名之路才能光大本族,保持家族的声望财势经久不衰。黟县宏村的古楹联有:“万世家风惟孝悌,百年世业在读书”。许多宗规家训鞭策族人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大吾门,亢吾族”,维护张大本族的社会地位。各宗族都拿出部分族产为子弟读书赶考提供学费盘缠。休宁茗洲吴氏的《家规》中说:“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之膏火。”[(23)]后岸柯氏《族训》中有:“奖励科贡诸生,有花红银两等事。”[(24)]歙县潭渡黄氏《家训》中说:“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劝,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还说:“广储书籍于济美祠中黄山楼上以惠宗族。”[(25)]潭渡黄氏德庵府君祠的祠规还规定:“俟本祠钱粮充足之时,生童赴试应酌给卷赀;孝廉会试,应酌给路费;登科、登甲、入庠、入监及援例授职者,应给发花红,照例输赀。倘再有余,应于中开支修脯,敦请明师开设蒙学,教育各堂无力读书子弟。”[(26)]婺源芳溪潘氏在修建宗祠后,“诸废并兴,聚书千家,择善而教,弦歌之声不弛昼夜。”[(27)]徽州地区在明嘉靖万历时,“十户之村,无废诵读”[(28)]。到清代,“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29)]明清徽州文化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曾居全国之冠。康熙时,全府有社学562所,书院54所,至于义塾、家塾、蒙馆不可胜计[(30)]。据《紫阳书院志》的统计,从明洪武四年至清光绪三十年,歙县籍士人乡试中举人者计1552人;春闱中进士者计525人[(31)]。如“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同胞翰林”,传为一时美谈。徽州一些宗族还建立了文会,一方面祭祀文昌帝君,祈求他保祐族中子弟科举中式者连绵不断。另一方面,借文会的形式聚集一笔资金,以提供族中子弟的学费和赴考盘缠。康熙年间,歙县张姓宗族认为,本族“自大三公以来沿及昭代,人文蒸蒸蔚起,瓜瓞绵绵不替。虽曰祖宗之功德使然,但也有文昌帝君的施恩与佑荫。今叔侄兄弟推诚输资共成胜会,逢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诞辰,共祭文昌帝君。”会费除建会始初的乐输之外,以后会友得子、入泮、补廪、岁科考、乡试会试中式者、出仕者均需交纳不等喜银或俸金。会费除用于祭祀文昌帝君外,会友的会文活动可以支取,会友应试盘缠也由此支出,“以为鼓舞人才之意。”[(32)]雍正十三年,徽州汪姓汪本立公秩下汪士礼等人商议,将承祖田租碓业,共计租七十余秤,用于建立文会之资,“以启秩下有志读书者。”凡赴县考者给卷资银一钱;赴府考者给盘费银四钱;赴院考者给盘费银六钱。余下田租按照进院考人均收,以为灯油之资。未进院者不得混争,否则,准不孝论罪。此外,“入泮者公出费用。”[(33)]有些宗族在祭祀文昌帝君的文昌阁旁,设一龛,供奉族中大力捐资文会者的神位[(34)]。
明隆庆前后,在全国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区很多宗族借机建立宗族性的乡约,所立乡约规条与族规家法合二为一,从而使宗族控制了乡里教化机构[(35)]。
徽人生活中的娶妇、嫁女、诞子、做寿、盖房、乔迁、丧葬等等大事,可以说都离不开宗族。宗族要求族人婚配看门第、辨良贱。歙县潭渡黄氏《家训》中说:“婚姻乃人道之本,必须良贱有辨,慎选礼仪不愆温良醇厚有家法者。不可贪财慕色,妄偶滥配,聘娶优伶臧获之女为妻。违者,不许庙见。”[(36)]婺源严田李氏宗族也规定:“婚女不计良贱者,”在宗族修订族谱时,要“泯其名号、行等、卒葬,示黜之以垂戒也。”[(37)]举行婚礼三天后,新人要到宗祠拜宗认祖,行所谓妇人“庙见礼”。新娘要给亲族中的长辈叩拜请安,明确尊称,须合乎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封建礼教清规。亲族长辈则对新人“各授以家庭规矩,嘱其谨守勿失。”[(38)]娶妇嫁女往往要使用宽敞的宗祠大厅以行礼宴客,须给宗祠交纳公堂银[(39)]。此外新娶者还要向宗祠交银若干作为新娶输赀银。诞子者也要交纳输赀银[(40)]。一些宗祠还备有娶亲用的轿、灯、团衫等等,供娶亲者使用,只须交纳少许税金。族人娶亲行嫁,可使用宗祠的佃仆充作乐人和轿夫[(41)]。徽州的一些宗族还规定:“族人大寿,身五十岁起,宗祠首人要备果酒恭贺。族人监造大厦、乔迁、葬祖等,首人亦要备果酒恭贺。”[(42)]徽州地区,嫡庶之分极严,很多族规中都规定,决不允许“尊庶为嫡、跻妾为妻。”明代汪子木“以母贱不得附其祖父墓,悲愤莫知所为。”[(43)]庶母死后不仅不能附葬祖父墓旁,而且“神主均不得入祠享祀。”[(44)]宗族通过插手族人娶妇、嫁女、诞子、盖房、乔迁、丧葬等事务,来增强族人的宗族观念、贯彻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封建礼教清规。
中国的农村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在乡村修桥、修路、修筑水利设施等项工程上,依靠一家一户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组织动员全村甚至数村人的力量。明清徽州地区的宗族,正是承担起了这种组织者的责任。歙县潭渡黄氏宗族的《家训》中说:“村前村后桥圯路倾急当倡众捐修,以便行旅。”[(45)]嘉庆年间,歙县十六都丰乐水芝河一段的雷[原字土加曷],附近有三个村庄。由于雷[原字土加曷]与胡姓一块地内的旧围墙相邻,每逢三个村庄的人“挑[原字土加曷]做工”,对雷[原字土加曷]进行修整,难免有“损动畔脚”的事,“胡姓虑墙颓卸”,每每引起口舌。为免“村邻结怨”,临河值司管[原字土加曷]人程景贤“邀同三村管[原字土加曷]商议”,认为“息事为贵”。于是凭各村族长、保长等作中,出面清理公查。结果看明旧围墙离雷[原字土加曷]中间尚隔有路。遂订立合同,规定以后“不论何分何祠支裔,值司开挑,不复再生事端。”合同的签押,除值司管[原字土加曷]人员排名在前外,每一村均是族长排名在前,保长排名在后[(46)]。中国人在合同文约上的签押排名是有严格顺序的,列前者表示身份地位尊贵,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能起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在解决水利设施的纠纷等事务中,宗族的权威和作用实际上要大于保甲。水利设施的修筑和养护,也主要由宗族来负责组织协调等工作。
限于篇幅,许多方面的事例不可能一一列举。总之,徽州在明中期以后宗族的影响无处不在,几乎渗透到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研究明清徽州的历史,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宗族状况,许多事情就无法理解,很多问题将得不到全面正确的解答。
二、家法大于国法
明代中叶,徽州婺源县有个居乡的富人,将其从兄殴打致死。他用重金贿赂官府,从而逃脱了刑法的惩治。当时居住樸溪有一位做过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的潘公,正好致仕乡居,闻听此事,义愤填膺,毅然率众向官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杀人者抵命[(47)]。殴打从兄致死,严重践踏了宗族倡导的“孝悌”、“骨肉亲亲”的精神,如果发生在明末清代,则先由宗族内给予严厉惩罚,甚至可能沉塘或令其自尽。但这里没有看出宗族有何反应,只是致仕居乡的官僚率乡人请愿,要求官府惩办。说明明中叶时,牵涉乡村司法事务,主要由官府主持审判仲裁。
明中叶以后,随着宗族权势的日益加强,某些宗族组织逐渐控制了乡村的司法仲裁权,形成“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徽州宗族大都规定,当族内发生纠纷争执等事时,由宗族族长、房长等主持的审判,是解决争执的首要必经程序。族人不许不经宗族,径自向官府投诉,也不许自行解决,要一听宗族裁判。歙县南屏叶氏“祖训家风”中规定:“族内偶有争端,必先凭劝谕处理,毋得遽兴词讼。”并自豪地说:“前此我族无一人入公门者历有年。……族中士庶以舞弄刀笔、出入公门为耻,非公事不见官长。或语及呈词讼事则忸怩不宁,诚恐开罪宗祖,有忝家风。”[(48)]祁门县二十都文堂陈氏“家法”中也有:“各户或有争竞事故,先须投明本户约正付理论。如不听,然后具投众约正副秉公和释。不得辄讼公庭,伤和破家。若有恃其才力,强梗不遵理处者,本户长转呈究治。”[(49)]文堂陈氏建立的乡约,属宗族性的乡约,因而乡约规条与族规家法合二而一。如果宗族内有人发生纠纷争执,先要向本户所属门、房系统建立的乡约负责人——约正、约付报告,由他们仲裁处理。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再投诉到全族系统建立的乡约负责人——众约正、众约付那里,由他们作出仲裁。可见牵涉到乡里族人间的纠纷争执,主要由宗族加以处理解决。当出现“强梗不遵理处者”,宗族无法解决时,才允许投官,而且要由户长(家长)出面,一般情况下不许自行投官。巨族大家以“无字纸入官府”、“无一人入公门”而自豪。这种不劳官府而自治的作法,有防止族人打官司而破家的隐忧。徽州有句俗语:“气死不打官司。”历来官府视百姓诉讼为“金穴”,趁机大捞昧心钱。清初休宁县令廖滕煃⑦在谈到他之前的县令时说:“皆以词讼为生涯,计词讼一年可得暮金(贿金)万有余两。”休宁“大约民风尚气好讼,讼必求胜,必不惜钱由来。宦于其地者类,取资词讼以自肥,”视词讼为“金穴,任意干没。两造之下,只视钱之多少,不分理之长短。锻炼深文,高下其手,受其害者愤气填膺,无从控诉。”经常是因为打官司,富家巨室的资产“顷刻销落殆尽”。致使“百姓视县堂如虎口”[(50)]。另一方面,也有宗族权势扩大后,力图控制垄断乡间诉讼的意图。凡涉及到宗法伦理、尊卑名分和破坏宗族内部秩序的“不法行为”,族规之罚往往超出国法之罚。崇祯年间,徽州胡姓宗族族丁胡五元、胡连生,一贯从事小本走贩,踪迹不定。后因詹三阳被人偷去财物,怀疑是他二人所为,官府差捕快捉拿他们,他们在被递解的路上,用小利贿赂公差脱放逃回。清明时节,族人齐集拜扫祖茔,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大家,宗族要将他二人捉拿送官,他俩连夜逃走。于是宗族连名歃血,众立文书,约定:“如有见者并知信者,即报众捕捉送理,家口遵祖旧规赶逐出村,庶免败坏门风,枉法连累。如有知信见者不报,亦赶逐出村,不许在族坏法。”[(51)]小偷小摸之事,在官府看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重案,因而公差才胆敢卖放。但在宗族看来,则认为“败坏门风,”“枉法连累”,不可容忍。不仅动员全族人捉拿违法族人,而且还要株连他们的家属,将他们赶逐出村。宗族的惩罚确实远超过国法的惩治。清代徽州柯氏“族训”中规定:族内若有忤逆父母长辈、奸淫、盗窃等,“往往勒令自尽”[(52)]。明末祁门文堂陈氏“家法”中也说,族中若有盗贼或素行不端,可令其“即时自尽,免玷宗声”[(53)]。小偷小摸等便要处死,家法惩治的严厉确实达到了极点,宗族对违法族人不仅拥有审判仲裁权,而且也拥有生杀大权。歙县潭渡黄氏,明隆庆年间,族人黄德涣持刀杀父,被族长及诸门长知道,将其“缒之将军潭”,然后将其罪行呈报县里。到清初,又有族人“以乱伦故为族从缚而沉之于水”。清初歙县稠墅汪氏宗族族人某“有奸情事为众人双获,于奸所遂聚薪活焚之。”此事被官府闻知,追究主谋者的刑事责任,也仅仅是使其“破家乃己”[(54)]。国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不准许宗族绕过国法,自行惩治和处死族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族的处罚是秘密执行的,族人守口如瓶,官府难以察觉。即使闻知一二,但面对的是整个宗族,审理追究起来都极为棘手。因而在国家需利用宗族加强地方管理时期,官府对宗族的一些无视国法的家法,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当国家与宗族有矛盾,政府采取打击削弱宗族势力政策时期,对于宗族的一些法外之法的举动,则采取坚决追究、毫不留情的态度。笔者在徽州祁门六都考察时,当地农民告诉我,村后有座山,五个小山包联在一起,形状象老虎的爪子,当地称为“五爪山”,此山象征明初程氏窦山公的五个做了大官的儿子,因而是风水山,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清末有人在山上砍了一棵小树,被族长知道,命人将他捆起来,鞭打致死。当问到历史上宗族内有没有沉塘之事时,当地人说:“沉塘的事是有的,不过不会写在族谱或其他什么书上。”我问徽州一些老人:“从前人们怕不怕族老(族长)?”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怕啦!族老权力很大,他要你死,你就不能活;他要你活,你也不能死。在我们这里是家法大于国法。”封建时代的乡村,普通农民离官府很远,而宗族则时时刻刻都在眼前,因此农民只知有族规家法,不知有国法。此外,在族人的心目中,族长除了是宗族领袖外,也是祖宗的代言人,在族人看来,遵守祖宗遗规、服从族长的管教,听命于家法的惩处,乃天经地义之事,从情理上就不容违抗。因此,不管官府怎样追究,在徽州的乡村依然是家法大于国法。
中国历史上的宗族,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事物,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宗族通过办学、祖训家风教育,将中华民族古老灿烂的文化一代代传下去,发扬光大,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材。中华民族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勤劳俭朴的美德,也通过这种途径世代继承。宗族社会造成了融融暖意的亲情、乡情,亲族间相助相扶,成了人们自然的生活信条,使中国的下层社会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不管你飘泊到天涯海角,仍忘不了故乡的亲人。中国人暮年时要“叶落归根”,扑回祖先曾流过血汗的故土,即使一把白骨扔在异国他乡,也要想方设法弄回故乡埋葬。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制的加强,恰恰与徽商的崛起同步发展。族产的庞大给徽商初期发展以很大支持。然而宗族的负担又在某种程度上拖住了商业资本进一步扩大和向产业转化的后腿。
宗族统治与封建政权统治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使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补、自我完善的机制。宗族统治,比较单纯封建政权的统治更细密、更有效,而且乡人在思想感情上更易于接受。清代曾历任多省巡抚的陈宏谋,曾评价宗族说:“立教不外乎明伦,临以祖宗、教其子孙,其势甚近,其情较切。以视法堂之威刑,官衙之劝戒,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实效。”[(55)]宗族有效有力地控制了某些地区的乡村,成为那里实际上的管理者和统治者,维护了封建秩序,使封建社会的基础更加强固。这恐怕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难于瓦解,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覆甄集》卷五《永慕亭记》。
(2)《洪武——乾隆祁门三四都凌氏誉契簿》中《又加一○五号凌友宗迁居婺源文约》。
(3)《正德四年祁门十五都郑狮等立合同》。
(4)参考拙文《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第四届明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5)《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
(6)《嘉庆二年休宁县一都八图族长王惇裕等甘结文书》。
(7)《道光徽州府志》卷八之二《职官志·名宦》。
(8)《潭滨杂志》中编《义仓》。
(9)《岩镇志草》元集《郑氏义宅》。
(10)《(理田重修)李氏统宗谱》,《理田李氏二孝友传》。
(11)《奉思录》。
(12)《康熙二十五年张福光户人等立孝义合同》。
(13)《大泌山房集》卷八七《征士方君墓志铭》。
(14)《雍正胡氏佛会收支簿》。
(15)《严田李氏会编宗谱》卷八《李氏寺观记》、《记传》。
(16)《吴氏祊坑永禧庵真迹叙录》、《永禧庵碑文》、《赎田碑文》。
(17)《休宁茗洲吴氏家记·序》。
(18)《道光舒氏收租簿》。
(19)《万历二十二年黄以恩等人议立义祀合同分单》。
(20)《道光二年黄可灌立承绍继文约》。
(21)《道光五年黄泰晨立承继文书》。
(22)《万历四十六年郑三元立分产合同》。
(23)(26)《茗洲吴氏家典》卷一《家规》,卷六《祠记·附康熙已亥公立德庵府君祠规》。
(24)(52)《民国新安柯氏宗谱》卷二四《后岸柯氏族训》。
(25)《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四《家训》。
(27)《樸溪潘公文集》卷五《芳溪潘氏宗祠记》。
(28)《嘉靖婺源县志》卷四《风俗》。《万历休宁县志》《舆地风俗》中有:“虽十户村落,亦有讽诵之声。”
(29)《道光休宁县志》卷一《风俗》。
(30)《康熙徽州府志》。
(31)《紫阳书院志》。
(32)《康熙张姓文昌会根源》,有张姓三十一人在文书上签字押约。
(33)《雍正十三年汪本立公秩下汪士礼等立清白合文》。
(34)(45)《歙行日记》。
(35)请参考拙文:《明清徽州的乡约》,《中国史研究》一九九○年第四期。
(36)(38)《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四《家训》。
(37)《嘉靖严田李氏会编宗谱》,《凡例》。
(39)(42)《金氏仁明祀簿》。
(40)《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五《黄氏大宗祠初刻祀产簿序》。
(41)《尊美堂条一本》。
(43)《大泌山房集》卷三五《方长公寿序》。
(44)(49)《文堂陈氏家谱》,《外编·永锡祠庶母神主祠享祀议约预知》;《陈氏文堂乡约家法》。
(46)《嘉庆十三年歙县程景贤等立合同》。
(47)(53)《朴溪潘公文集》卷六《显考封中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参政潘公行状》。
(48)《歙县南屏叶氏族谱》卷一《祖训家风》。
(50)《海阳纪略》卷下。
(51)《崇祯十一年胡义和堂本族人等立文书》。
(54)《潭滨杂志》,上编。
(55)《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八,《礼政》。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