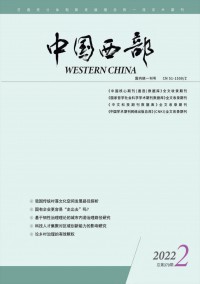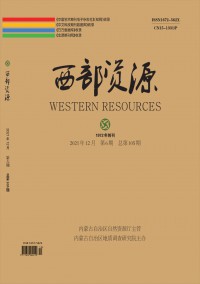西部民间艺术构建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西部民间艺术构建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西部曾经是中华文明的最早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曾经是中国文化政治的中心,而且由于这些地区多元化的地理环境和多元化的自然物产,孕育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历史与传统,这些都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席卷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今天,它也成了一种可供开发和利用的人文资源,在这种开发和利用中,许多的传统生活方式、乃至传统的民间工艺,都被提取出来成为一种可以作为文化商品出售的民间工艺品、民间美术品,或可以在舞台、旅游景点表演的民间歌舞。于是,一时间,在西部的农村出现了许多的民间艺术家、民间剪纸能手、民间歌王等等;还出现了许多民间艺术村、文化生态村、民族风情保护村等等。昔日在人们眼中落后的西部,开始成为一个个风情万种的文化大省,神秘的、遥远的、原生态的这些关键词,将西部建构成一个“异地”的“他者”的文化空间。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力量和哪些因素,在为我们建构这些让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向往的“异地”空间?笔者在考察中发现,这些空间的构成无一例外都是借用了民间艺术这一形式。在人类初期的文明中,人们用艺术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巫术的、宗教的、充满象征符号的意义世界。今天,人们仍然在用艺术建构一个可以供人娱乐的、观赏的、游玩的、可以得到经济收益的文化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从事文化产品和艺术产品的制造。
尽管在人们眼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滞后,由于地处偏远,文化封闭,传统保存相对完好。但在今天,已不再会有任何一个还保持着传统的、自然的、从未受过现代侵染的地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地区都已经开始生活在人工创造的“第二自然”中。在弗里德雷克•詹明信看来,“后工业化社会”根本标志就是“自然”已一去不复返,整个世界已不同以往,成为一个完全人文化了的世界,“文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所谓自然已经消失,指的是世界上再也不存在没有被人染指过、没有受过“文明”点化的净土了,一切都被纳人了人的视野、人的认识,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整个被知识化、话语化了①。以往人们是通过自然来创造文化,而现在的人们则是通过“文化”来“重构文化”。我们发现,西部也是在利用以往的文化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文化,而这种新的文化是以广泛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来表达的。
为了论证这一看法,在文章中,笔者将采用一些学者,以及笔者自己在这几年里考察的一些案例,来描述西部文化的重构过程,并以艺术人类学的视野观察民间艺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一些普通的农民为什么在今天成为了民间艺术家;一些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家庭,在今夭为什么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而成为了民间艺术或民间工艺生产的专业户;一些为人们日常生活服务的传统产业在今天为什么萧条,为什么他们其中的一部分只有变成了艺术才能生存下来;为什么一些为民间信仰和民间习俗服务的祭祀仪式和道具,在今天变成了可以表演的歌舞和可以出售的民间美术品等等。在学术上的“宏大叙述”理论体系遭到质疑以后,人们越来越重视地方性知识和个别经验的研究,越来越认识到许多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许多文化的重建与重组,都绝不是由单一的因素所促成的,里面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在相互纠结并形成一股合力。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地方,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艺术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新塑造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了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种现象在西部也不例外。在研究当今西部民间艺术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各种知识的形成,已不再是过去的那种被看成是自然现成的、理应如此的,而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势力交锋之后形成的表述方式。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促使西部民间艺术当代构成的各种“权威”或“权力”。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对于当今西部民间艺术的研究就不仅要把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视为已知的话语建构,把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看成是当下的一种话语建构,还要自觉地把关注的焦点调准到“当代西部民间艺术”与促使其形成的各种“力”的交互影响上,着重考察为社会所接受的“当代西部民间艺术”—即表达或体现当代西部民间艺术的“话语”—是如何形成,又如何变化的。虽然我们对于以往西部的民间艺术已经有了许多深人的研究,但对于它的现状,对于它在当代社会中的构成形式,认识仍不够完整和深刻。
人们只是认为:商品经济对西部的许多农村、牧区的渗透和冲击还相对薄弱,传统的农耕方式或游牧方式给予老百姓的影响还相对牢固,民族的“文化记忆”和“口头传统”在这些地区和民族中还相对丰富而完整。许多在沿海地区或其他文化圈内已经消失了的民间文化事像,如某些神话、传说,在西部一些地方,可能还相当完整地保存着。这种认识有一定的依据,但事实上,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能够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只要不是封闭,只要与各种“外力”不断发生联系,它就不会是处于静止的状态,而是在不停的建构和被建构之中。首先是电视机的普及,使即便生活在偏远西部的人们也能在不出家门的情况下,知道天下大事。
笔者在2001年到陕北考察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有了电视机,这些居住在深山里的人平衡的生活开始被打破了,生活在这里的许多人也许连西安都没有到过,但通过电视,他们却看到了整个世界。看到了繁华城市中的生活和他们所在的贫困中的乡村生活有多么大的距离。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寒酸和落后,同时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被颠覆,以前被认为是美好的东西,现在变得一文不值。于是,以前认为‘可好看’的剪纸画被迷人的明星照所取代了,以前曾把他们迷恋得要死要活的山歌—信天游,也被现代流行歌曲所代替了。他们为自己的贫穷而感到羞愧,在这羞愧中,也从此否认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审美习俗,认为那是一种落后和简陋,他们要奋起追求和城里人一样的时尚,一样的漂亮’,②。的确,大众媒体正在把不同地区人的文化拉平,在这一过程中人文资源便开始流失。
当然,许多的民间艺术仍然存在,还可能在蓬勃的发展,但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已经有了许多的改变。其次是旅游业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们对于精神的需求正在逐渐增加。同时,随着环境污染、自然生态平衡破坏的加剧,人们出现了一种怀旧、寻根、回归自然的心理,在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下,人们开始热衷于了解各民族的文化历史,热衷于收藏各种文物、艺术品,热衷于用民间的手工艺品和自然材料来装饰和布置自己的家居等,热衷于到与自己民族不一样的地区和国家去旅游、去体验文化的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原先被认为是封闭落后的地区,由于尚未被开发,保持了较好的自然环境和较完整的民族习俗与传统,开始成为旅游的胜地。西部的许多地区一也一样。旅游业对这些地区的介入,一方面给当地带来了经济增长,同时也给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而且还迅速重组了当地的文化传统,新的文化在这重组中得以再建。
一位摩梭族的学者在考察了他的家乡沪沽湖畔的两个村庄后,就旅游业对当地文化介入后的状况作了很详细的描述。在他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开发旅游业以后,当地的民族不仅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生产方式,甚至家庭的构成形式与人们的经济观念也因此改变。作者在文章中写道:“落水人过去以农业为主,劳动力主要从事种植及畜牧业,而现在,年轻人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旅游业上,从事牵马、划船、歌舞或摆摊,设立商铺等工作上”③。同时,人们还开始用民族艺术的手段,重构自己的家乡文化,于是,“摩梭风情园”、“女儿国饭店”,“女神酒楼”等充满了诱惑和招徕意味的旅馆、饭店,在沪沽湖边四处可见。
白天,打扮得花花绿绿的马匹和牵马的小伙子姑娘在村边排成队列等待游客的到来;晚上,摩梭人在院坝内燃起簧火,跳传统的舞,唱当地的民歌;一种既真实又虚幻的民间艺术风情油然而生。此情此景,使人们认识到,有关“现代”的诊释,可以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西方文明史阶段的“现代”,另一种则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在工业化发展的后期,工业化的组织管理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农业、商品流通的领域,使这些领域实现了工业化,进而渗透到文化生产、娱乐消遣的领域。文化生产和娱乐消遣,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美学意义上的“现代”得以生成的基础。另一位学者曾到中国最西北的小村庄—白哈巴村旅游,在村庄里,她看到了在内地小村庄从未见过的最整洁实用的卫生医疗站。所以她认为“这是一个美丽安宁又相当开放的地方”。她在文章中写道:“但是,自从内地的旅游公司‘发现’了这个地方,并且自以为是地赋予这里‘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色彩,大批游人便纷至沓来。美丽、神秘、边睡概念、异族风情,这些已经足够吸引大批游客,但旅游公司认为还不够。他们要提供更多的感官刺激,以刺激和满足游客快速消费、即时享受的欲望。各种新的旅游项目被开发出来:游船、游艇、直升机;马上、水上和空中体验。于是,这里的湖水不再平静,山林也不再安宁,传说中的湖怪杳无踪迹。
伴随着快艇、轮船和直升机的马达声,旅游公司纷纷宣传造势,把当地风情和民族文化浅薄地包装起来再出售给大众。在哈纳斯湖边,旅行社搭起一个固定的夜间活动场地,中间是一个簧火晚会台子,配有重磅音箱。一到夜里,这里就开始了哈纳斯湖边最喧嚣拙劣的所谓民族表演。这些表演一如内地某些场合的歌舞表演,声嘶力竭的喊叫和震天动地的音响伴奏是其特色。在阿尔泰深山哈纳斯湖区的夜色中,这种歌舞和喧闹特别触目惊心。在传统社会,髯火是人们在野外露营、游牧或者用炊、取暖甚至威吓野兽时使用的方法。而在这里,簧火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它变成了一道风景,一个符号,一种招徕游客的廉价而有效的手段。它可以用来刺激游客们已经麻木的感官,满足他们即时的欲望。而在这样的场合,鲜艳的民族服装、带有地方风情的表演,夹杂着英语和当地民族语言的节目是必不可少的道具”④。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西部大开发而蓬勃兴起的旅游文化,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地民族和族群的文化⑤。西部民间艺术在新时期不断被利用和被重新建构的过程中,政府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从上世纪so年代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兴起的革命化的秧歌、剪纸;后来在政府倡导下发展起来的户县农民画;各县级文化馆辅导出的农民画、剪纸、刺绣、泥塑等曾风行一时的民间美术,包括一些民间歌舞。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后期,中国美术界曾发起过一场民间艺术热。它与各地文化馆干部的工作有着直接的联系。就是这些文化馆的干部们,培养出了许多闻名中外的民间艺术家,国家为这些民间艺术家在美术馆办展览,在京城的舞台上演出,还派他们出国表演、参观、讲学。这些民间艺术家们的技艺是精湛的、传统的,但也无不充满了文化馆干部熏陶和指导的痕迹。
安塞县的农民画家基本是女性,这些农村女性大多数本来并不会画画,只是从小剪剪纸和绣花,有一定的造型能力和基础,正是在文化馆老师的培养下,她们才学会了画画。《安塞民间绘画精品》中介绍说:“妇女们画画,每一个形象都要画完整,不喜欢割裂成局部的片断。薛玉琴的牛画得很好,辅导员鼓励她试试只画几个牛头。薛玉琴画了牛头还是坚持要画出腿蹄。‘没有腿把子使不得,谁家牛不长腿把子?’辅导员来了点强迫性,硬是不让她画牛腿,薛玉琴无奈画成了第一幅局部特写作品。”由此看来,这些民间艺术的创作发展,并不完全是自主性的,一方面是政府的倡导,另一方面也是文化馆辅导员的引导。如果说,最初政府主导民间艺术的发展,是为了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含有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意义,那么后来政府扶持民间艺术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发展经济的含义。上文提到的农民画家薛玉琴住在离县城还有四十多公里的村庄里,陕北的沟沟筛赤,非常难走,所以,一般不会有旅行者进人这样的村庄。她是当地有名的农民画家和剪纸能手,但在她家的墙上和窗户上,没有贴一张她自己画的画,而是像所有的陕北农民家一样,贴满了明星照。笔者问她为什么,她说,明星照好看,而且真实,她自己画的画和剪的剪纸则很土,很难看。笔者再问她,既然不好看她为什么还要画、还要剪。
她说,是因为城里人和外国人喜欢,她可以将这画好的画和剪好的剪纸,送到县文化馆出售。县文化馆为了创收,他们收购农民们的剪纸、绘画和刺绣等,然后以展出和长期陈列的形式出售给游客。薛玉琴所在的村庄很穷,村里每户人家的年平均收人才几千元人民币,薛玉琴因为会画画和会剪剪纸,已经成了村里的首富。她不再从事农活,真正成了一个画画和剪纸的专业户。而另一位农民艺术家侯雪昭,她家就在安塞县旁边的一个村子里。窑洞里贴满了她剪的剪纸,窑洞的门脸上窗户旁,挂满了一串串红艳艳的辣椒、一串串白生生的大蒜头、一根根金黄色的玉米棒子,完全是陕北人家的风光图景,那是因为她家已被批准为可以接待外来游客的接待户。她的丈夫是当地远近有名的腰鼓手,现在他们夫妇俩基本不种地了。
还有一个事例似乎也能说明这个问题,2002年,笔者到陕西迁阳县的一个村庄做考察,正好遇到省妇联的几个干部也在村里,他们为了帮助当地农村妇女脱贫,带领文化馆的干部来免费培训村里的妇女,教她们刺绣,教她们做布玩具。本来这应该是当地妇女们熟习的本行,但她们告诉笔者,她们自己制作的这些手工艺品,不如文化馆老师教的有市场,无论是配色还是造型,她们都喜欢接受文化馆老师们的指导。这个案例说明,发展民间艺术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帮助农民脱贫的一种方式。更令人深思的例子是,一位妇女是村里最有名的刺绣能手,被国家授予民间艺术家的称号。笔者看到在她家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满了电话号码。经了解才知道,因为她是名人,客户总是指名要她的刺绣品,但她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做得了那么多活。于是接到订单,她就打电话给村里的妇女们,大家一起帮着做,她从中抽钱。
她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文化名人”,进而又成为一个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品牌”。现在她一家人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专搞布艺的制作与销售工作。在西部民间艺术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股我们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许多做民间艺术研究工作的学者在里面起的推动作用。笔者在去年春节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民间艺术村考察,那是一个坐落在黄河岸边、据说伏羲曾在那附近做过八卦图的村庄。到那里才发现,当地民间的文化传统,在解放以后的移风易俗和“”的“破四旧”运动中,早被冲刷得所剩无几。现在所有的网上和报纸上宣传的当地的民间文化和艺术都是近几年重建与恢复的,是美院的一位教授到这里画画,发现这里自然风光很美,同时也有很多的历史遗迹与神话传说。在他的帮助下,村里建起了民间艺术学校,请来文化馆的人训练当地农民唱民歌、跳秧歌、剪剪纸。为了挖掘当地更多的人文资源,教授请来了考古学家,对村里一座谁也说不清来历的古窑进行了考证,把这座窑的建筑年代确定为北魏时期。同时,他让村里人将他们耕地时翻出的汉唐时期的陶罐,宋元时期的画像石等古物都贡献出来,放在窑中,准备建一个有关这个村庄的历史博物馆。
在这座窑的墙上,贴着一张有关村子的介绍文章:小程村,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与山西吕梁山脉交界的黄河大峡谷西侧,黄河以雷霆万钧之势,蜿蜒展转行进于黄河大峡谷中,在这里形成时称“乾坤湾”的著名天文景观。山西永和县向一把利剑直指小程,因此,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冲,小程东有雄伟的汉代夯土古城遗址、碾畔汉墓群(距今约两千年),西有牛尾寨与战国古墓和清水关古渡口、古村寨遗址。这里自古就是汉民族与匈奴、月氏、羌族等内迁北方民族文化的交融之处,匈奴赫连勃勃建国的大夏,与古羌建立的西夏都活跃在这里。小程村至今仍然保留着刻有胡人服饰形象的千年石刻接口遗址,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古窑遗址和胡人门神艺术。村里人告诉我说,这段介绍是那位教授写的。在这之前,村里人除了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在明永乐年间由山西大槐树下迁移过来之外,其余的有关村庄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一概不知。
是那位教授让他们在众人面前有了些许的自豪感,知道了自己村庄与众不同的一面。村民们看见我们对老窑感兴趣,他们又向我们推荐了更让他们自豪的另一个景观—“乾坤湾”。在村民们的相拥下,我们来到了村头的一座黄土高坡上,向下俯视,黄河在这里形成了两道S形的大湾,中间有一座伸进弯道的小岛,酷似“太极图”,因此,这座岛的学名叫黄河太极晕。相传这里是风华青履大迹感生伏羲,姜媳履迹感生后樱的风水宝地。那个在黄河中央的小岛前有一片很大的河滩地,据说这块河滩地就叫“在河之洲”,夏商周三代君臣于每年的仲春二月,在这里聚黄河庙会,唱青阳歌,奏立基乐,跳宿夜舞,献牛犊祭,供九河神女,颂人民之祖。“关关雌鸡,在河之洲”就是产生于此。我不知这些说法是否正确,因为这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所说,至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历史,也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些历史。在学者们的帮助下,人们充分地利用和挖掘了当地的民间传说资源,并通过历史遗址和文物来重新确证当地的历史与文化,与此同时还展开了系列的传统民间艺术活动,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和重建当地文化,为外来人描绘甚至虚拟了一个新的似乎有着浓郁的地方风情的文化空间。当然,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文化在其中的变异,这里的秧歌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传统秧歌里的所有禁忌与章法在这里全部消失,有的只是娱乐,只是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这里的剪纸也不再有祈福、辟邪以及做鞋样、绣枕头、贴窗户的功能,它成了“剪纸艺术”,表现的功能变了,其剪纸的内容和形式也改变了。
没有了传统的民间宗教色彩,反映的都是农民们的现实生活,为了便于装饰和更有视觉上的冲击力,其外形更大,也更完整;同时还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民间艺术形式,如民间绘画、布贴画等;民歌中也夹杂了不少延安时期和以后的革命歌曲。现在这一地区已经被国家批准为黄河流域原生态文化保护区。随着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和开展,许多地方会越来越意识到地方人文资源的重要性,类似这样的挖掘、利用乃至重构当地文化的现象也会越来越多,所谓的原生态文化也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地方文化的名词中,尤其是在国家保护试点和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材料中。在西部民间艺术的重构和变异中,新技术的介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有关现代技术所带来的传统文化的变迁是多年来笔者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几年前,笔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西部一些偏远地区保留的较原生态的文化,往往是一种较古老的文化,它的动力模式来自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状态。而现代文明对于当地文化的浸染,就是首先要根据现代的技术要求来调整其文化,同时也就意味着要采纳现行技术的‘动力模式’,抛弃那种如今已找不到现实基础的传统‘动力模式’。这也就是说,技术动力有时会领先于社会动力,并将自己的动力强加给社会,造成社会变迁的加速化。从这种角度来看,技术是组成文化的一个部分,但同时它们又常常脱离文化,构成完全独立的系统。
它们和文化系统相互影响,又相互对立。正因为如此,在本土文化正走向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今天,考察技术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模式就非常紧要,尤其是要考察现代技术将如何影响本土文化的未来:或者逐步地造成地区性的旧文化的解体,或者建立新的文化形式。我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的技术模式不仅迅速地取代了各地方性传统技术的合法地位,导致了传统技术的崩溃,也使许多地方性的原生态文化遭到了破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甚至消亡。当然,这只是我的设想,我要到西部去考察的目的就是要证实我的设想是否正确,也许在考察中还会发现第三条路,那就是地方性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继续发展和再生。”在考察中笔者看到了第二条路,也发现了第三条路。笔者一直对传统手工艺的研究有兴趣,曾在景德镇做过有关民窑陶瓷业的研究。在对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中同样也作了类似的系列考察。
比如对陕西省铜关地区陈炉镇的考察。陈炉镇坐落在黄堡镇附近,黄堡镇是宋代著名的耀州窑瓷区。元代由于战乱,耀州窑衰败了,陈炉镇继黄堡镇后,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产瓷集散地。镇子里H个村庄,上千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做瓷器,他们祖祖辈辈以此为生。解放后,每家每户分散的手工业作坊,合并成了一个陶瓷厂,于是村民们由亦陶亦农的手工艺人,变成了“吃国家粮”的国营工厂的工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的产品不怕没有销路,作为大众服务的方针,一些传统的工艺瓷和陈设瓷不再生产,只生产一些日常用的杯碗盘碟,因为面向整个西北的市场,所以产量很大,工厂非常兴旺。当改革开放后,各种工业制品充斥市场,陈炉镇半手工半机械化的陶瓷业很快就在市场上败下阵来。我在考察时发现瓷厂已经关闭,镇上的青壮年劳力都到外面去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而另一个现象出现了,镇子里开始出现了几家陶瓷手工业作坊,人们开始恢复了传统工艺瓷的制作,已经失传很久的耀州窑青瓷制作的工艺,也在不断的研究中被成功试制出来。这种工艺瓷和仿古瓷的产量虽然很低,但和日用瓷相比,其附加值和利润却要高得多。
另外,由于瓦斯窑的引进,炼泥机的利用,使一个手工艺作坊的存在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可以使从事这一项手工艺劳动的人,把精力放在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上,余下的可以交付给机器。于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的手工艺却得到了恢复,又由于新技术的介人,使手艺人的工作具有了更多的艺术创造的成分。手艺人们也在开始争取一个艺术家的地位,他们希望获得“民间艺术家”或“工艺美术师”的称号,这和他们的经济收人划上等号。人们买一件这样有地方特色的陶瓷工艺品,目的不是为了用,而是因为它有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而这种价值往往是和作者的名气挂在一起的,作者的名字有了含金量,就是一种文化品牌。手工艺的恢复好像是一种传统的回归,但实际上已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虽然还保留了手工艺的形式和手工艺的部分技艺。而传统的手工艺时期的文化早已丢失,如行业的组织形式、行业崇拜、行业规矩、行业传承方式、行业流通方式等,连销售对象与市场范围,都发生了种种变化。这其中最重要的变量除了新技术的介人之外,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传统的手工艺文化到哪里去了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们全部流失了吗?是的,在解放后,从我们将其视为落后的生产方式以来,它们正在迅速丢失。而且因为它们只是普通手艺人的文化,没有人去记录它们,所以,在文献材料里也很难找到详细的有关资料。但作为历史的记忆,他们还储存在一些老陶工的脑海里。正因为如此,在我的考察中,通过对一些老陶工们的访谈,我们还能了解到一些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原生状态。而现在的手工艺则是在国营工厂垮台后的基础上建起来的,是一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融后的衍生物。也许人们不太会注意手工艺文化,其实它们是农业文明的基础,应该是农业文明的核心部分,核心部分的变异是最根本的变异。
在笔者的考察中,一些与生活联系紧密的手工艺消失得非常快。如农村中的铁匠、木匠、石匠、铜匠等,他们曾经因为有一技在身,受到村里人的羡慕。如今这类工作几乎消失了,从事这一行当的匠人们,也逐渐成为过时的人,在一步一步地退出历史舞台。有意思的是,有些手艺消失了,有些手艺却发展起来了,他们不再被人看成是普通的手艺,而成为了民间艺术。比如说泥塑、雕刻、编织等。笔者在2002年曾到陕西省关中一带考察,到了凤翔县的六营村,那里以泥塑的制作而闻名于全国。这些泥塑本身是农民们利用农闲做的一些泥塑,是农民们在节日庆典、人生礼仪中使用的一些道具,与当地的民俗生活息息相关。而六营村的村民们世世代代,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则做泥塑,然后,将做好的泥塑拿到集市上出售。随着现代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本认为随着传统生活的改变,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会受到冲击。
但事实恰恰相反,六营村的泥塑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前所未有地发展了起来。许多村民开始成为泥塑制作的专业户,这些本来是农闲时做的泥活,开始成为他们的主业,也成为他们赖以谋生的主要手段。现在,这些农民已经成为民间艺术家,同时,重要的是他们还懂得了作为一个民间艺术家的重要性。在每一位专业户的家中,都会得到一份介绍作者的简历文字。比如说自己是第几代传人,自己的作品在什么时候得了奖,在什么报纸杂志上登载过,什么时候到美院讲过课,上过电视,甚至出过国等。这些都是他们提高自己产品附加值的重要资源。本来民间艺术就是一种集体创造,这些作为农民的业余民间工匠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署名,要申请作品的专利权。但在今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2002年发行的邮票选择了凤翔的泥塑马。立刻,每一家专业户几乎都在自己的简历里写上自己就是邮票上的泥塑马的作者。笔者觉得很奇怪,打听后才知道,在六营村大多数人只会在铸造好的模子上印坯,印好后再加彩。大家印的都是同样的模子,而这模子是上一辈的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正因为用的是同样的模子,所以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马,而且都是这一作品的专利持有人。生活中的常见之物,如今却成了艺术品。正因为知道了名气的重要以及创造新技巧的重要,一些年轻的农民艺术专业户,便想办法到中央美院等一些艺术院校学习。六营村一位叫胡新民的青年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雕塑,他告诉笔者说,村里人基本上不会自己搞创作,所有的泥塑品种都是因承袭旧,包括一些最有名的艺人。而他因为在美术学院学习过,有一定的造型能力,所以,很多新的品种都出自他手。他说,在村里基本没有什么专利权,谁家有了新品种其他人就会来要,乡里乡亲也不好不给。集体创作,这也是民间艺术的特色。为了市场的需要,除了传统的泥塑,六营村的艺人们还创作了许多新的品种,如在马勺、斗、织布的梭子等农家器具上绘制社火的脸谱,以迎合城里人追求乡土风味的心理。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力”,那就是市场之力,是市场的需要促使了农民艺术家们不断地创新,不断地产生新的民间艺术作品。在与六营村相邻的一个村庄,长期以来以编织业的发达而闻名于周边地区,这个村的传统产品是草席、草帽、篮子等一些农家的实用品。
编织的材料大多是当地产的麦秆,现在这些传统的产品已萧条,但另一种更具艺术性和装饰性的麦秆编织品出现了:用麦秆编成的各种花色漂亮的门帘、墙上的挂饰、桌上放的各种装饰品,甚至还有麦秆画、麦秆雕塑。这些产品并不是提供给当地农村,而是国外的来样定货。是当地一家商到广交会订的货,有了订单,商就将活分配给村里的一些妇女编织或制作。这些新的手艺活,不仅改变了村里的副业生产结构,给村里人带来了新的手工艺技术,同时也让村里人跟世界拉近了距离,因为这些产品都是为了出口欧洲,这里的销售链是漫长的。一边是生产者,一边是消费者,他们之间并不能直接见面,但在生产的过程中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也在影响着生产者的审美观,激发出他们新的想象力。笔者在考察中发现,除了这些外来的力在重构西部的民间艺术之外,当地传统的“力”,仍然在起着作用,在努力保持着民间艺术中那种原生的种种因素。2(X)4年春节,笔者在小程村过完年后,来到了陕北的榆林地区,通过当地学者的介绍,笔者跟着保宁堡秧歌队走了十几天,每天到一个村庄演出,晚上就和秧歌队员们一起住在村里农民的窑洞里。这是一支从明代就有的秧歌队,保宁堡不是一个村庄,而是一个祠庙群,它们独处于陕西与内蒙交界的半沙漠地带,由保宁堡庙会掌管,而秧歌队则隶属于庙会。庙会管辖着周围七十多个村庄,秧歌队每年腊月就开始集训,正月初二开始到各村演出,到正月三十几才结束,每年跑二十个左右的村庄,三年轮一圈。每到一个村庄,秧歌队首先是拜庙、敬神,在榆林地区的每个村几乎都有庙,有的是龙王庙,有的是牛王庙,还有的是土地庙,总而言之都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庙宇。秧歌队信的是山官爷,拜完庙后,就到村里找个地方供上山官爷的神像,上香朝拜。然后再到各家“沿门子”,所谓“沿门子”就是挨家挨户跳秧歌,其目的是,为主人家驱邪去灾,祈福求吉祥。舞步是规定的,而歌词则是按照主人家的情况,触景生情临时编的。跳秧歌时,锣鼓喧天,歌声僚亮,按当地的习俗,过年时家里一定要有响动,要红火,这样邪气才不会侵人,鬼怪也会望而生畏,不敢作祟。正因为如此,秧歌队来到每一家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沿完门子,到晚上让歌队到村里的操场上,摆开场子,开始为全村的村民们跳秧歌。
和安塞的秧歌一样,开始是跳大圆场,这是为娱神而跳的。在伞头的带领下,秧歌队变换着各种队形,先走大圆场,再变换各种队形,组成各种图案。常见的有“踩四门”、“卷菜心”、“扭麻花”、“蛇盘九颗蛋”等。大场子走完后,即为小场子,这是为娱人而跳的,因此有着更丰富的内容。有腰鼓、旱船、跑驴等轮番上场,以腰鼓队最受欢迎。接下来是演小戏,这是真正的农民们自娱自乐的演出。小戏里有媳妇虐待婆婆,后被大家教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有因赌博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后浪子回头,破镜重圆的;也有近亲结婚,生下了弱智孩子后悔不已的。这些演出都是出自于业余演员之手,水平不太高,但因为演的都是自己的生活,所以农民们还是很爱看。笔者在农村考察,发现农民们平时是不习惯用文字的,即使许多的农民读书读到了初中,他们平时也是不太看书看报的,久而久之他们很多字都写不来了。农村的人,他们习惯的是面对面的交流,在一个小的区域范围内大家都彼此熟悉,可以用语言来交谈,并不需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在他们的群体教育中也是用小戏或其它类似的民间文化符号来进行的,这些民间艺术从其原生的意义来讲,还担负着农民们认知世界,传承道德的功能。至于秧歌队员们的构成,大多数是十六七至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和小伙子。只有几个骨干队员年龄比较大。
笔者很好奇这些秧歌队员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于是对他们作了逐个的访谈。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大多数队员都是为了给神还愿而来的。在这一带的农村,当家里遇到困难或生病,还是习惯到庙里求神,并向神许愿,如果为家里解了难或治好了病,自己或者孩子就要参加秧歌队,为神跳几年秧歌。秧歌队的队员们基本上都在城里打工,跳秧歌结束后他们都要返回城里。笔者问他们,明年还会来吗?他们都茫然地摇了摇头,因为跳秧歌从组织到演出,差不多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这么长的假期,一般老板都不愿意给。另外,进城后,看到城里人并不敬神也能生活得不错,那份虔诚之心也就淡了不少。还有一些人进城后,安下家,也就把父母接进城,过年就不再回乡了。这样的情况虽然不是太多,但也不在少数,笔者跟随秧歌队走了七八个村庄,每个村庄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再回乡下过年。因此,传统的力量还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城市化、现代化以后的农村人口疏离化的问题。当然,这里有趣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进城,西部的许多民间艺术也随之进人了城市。在北京的一些市场里,有卖贵州苗绣的,有卖西藏佩饰的等等。正如萨林斯所讲的:“地理意义上的村庄是微小的,而社会意义上的村庄则是绵延数千里”⑥。在城市里贩卖家乡民间艺术品的农民“部落”,不仅将乡村的民间艺术品提供给城里人,同时也会改变家乡的符号象征的形式与意义。
从而使民间艺术发生进一步的变异。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部新的民间艺术在各种不同力量的主导和推动下正产生着种种的变异,在这里,传统的力量虽然不可忽视,但其所具有的抗争性还是有限的。当然,也许像萨林斯所认为的那样,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应。因此,这种文化才被我们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的本土化”。而这种本土化是在各种民间艺术的粉饰下存在的,民间艺术就像一个美容师,它将一些传统的社区笼罩上充满各种民族风情、民族文化的光环,将其塑造成一种神秘的、虚幻的、美丽的、奇异的令人向往的文化空间。让人们去考察、去旅游、去体验不同文化的奇风异俗。但事实上,在大众媒体、互联网已经遍布世界的今天,早已不存在真正的自然,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原生态文化,正如萨林斯所说的:“矛盾的是,几乎所有人类学家们所研究和描述的‘传统的’文化,实际上都是新传统的(newtraditional),都是已经受西方扩张影响而发生改变的文化。”同时,他还说道:“民族学如不是处于一种悲剧的位置上,便是处于一个荒诞的景况中。
当我们开始把这门学科的车间安排就绪,当我们去为它锻造合适的工具,当我们开始为约定的任务做好准备工作,其研究的材料就已经以令人无望的速度迅捷地融化了。恰是现在,当科学的田野民族学方法和目标初具形态,当人们在受过全面田野工作的训练之后开始到另一社会中去研究他们的居民,这些东西就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⑦。他的体会和笔者在西部所做的田野考察的感觉一样。虽然他指的是西方世界眼皮下的田野,但其实中国的西部也一样,西部的文化田野也在迅速地重构着和变迁着,它的传统也许正在迅速逝去,但它的现状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让我们从中观察到,我们所进行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正在变成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的保护,一种民间艺术的表演,并以此形成了一个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文化空间。如果比喻为整容的话,西部的民间艺术正在为西部的民族民间文化整容。整容后的西部文化会更美丽,但它已经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的了,就像文化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能指的符号形式还仍然存在,而所指的位置却被移动和置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