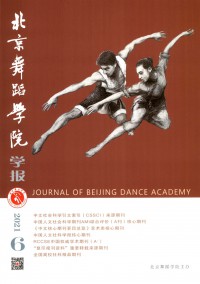舞蹈文化融合管理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舞蹈文化融合管理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文化冲突”与“文化震荡”
文化冲突与文化震荡就逻辑而言是两种文化互动的结果。可谓有“矛”才有“盾”,有“碰”才有“撞”。并且由文化碰撞形成文化反弹的文化震撼,使文化互动的双方受到影响。然而,目下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奇怪的景观是:虽然东西方文化是互惠互利,而冲突与震荡只存在于东方——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汇中深受的困挠,西方舞蹈家则毫无感觉。例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先锋派舞蹈家默斯·坎宁汉得到一本英文版的中国《易经》如获至宝。他从这本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关于世界万事万物不断变化的辩证思想中获得了艺术变化发展的重要启示,同时他把易理爻卦算命的原理用于他的舞蹈创作,形成“机遇编舞法”,坎宁汉先生似乎从未感觉到过东方文化对他的震荡问题。70年代,另一位先锋舞蹈家特丽莎·布朗的现代舞蹈团一边打着中国的“太极拳”,一边创造她的“放松技术”时,布朗女士亦从未困扰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他们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力创造了美国最先锋的艺术,并且,从本土到世界没有人对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美国化”问题提出任何质疑。显然,文化冲突与震荡好像一副“剃头挑子”——只存在于东方舞蹈家感觉中的“一头热”。追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现代东西文化发展强弱不均,带来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流中心态失衡:或者为西方现代舞蹈文化以势如破竹风靡世界之势所慑,以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而丧失本土的立场;或者苦于自身文化的羸弱所囿,尚无拥有足够的文化积累以超越他文化的影响。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视:冲突确实存在,并且,我们自身的现代舞蹈文化亦正是在解决这种冲突中不断建立。为此,我们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清醒地意识到冲突是怎样发生的。
静心梳理东方现代舞蹈文化的发展,全面地受到西方舞蹈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首先不在于西方舞蹈文化的强大而在于东方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的需要。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所说,一种真正重大深刻的外来影响被一个民族接受,必然因为前者与后者的某种内在要求相吻合。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就应该主要不在于前者的影响,而在于后者的接受。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方文化在近现展中处于相对滞缓状态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一种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经验需要新的艺术语言及其方式表达传递,而文化发展的羸弱与积累的匮乏,东方现代舞者在西风东进中借力而行便成为必然——借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的封闭状态,用外来的身体语言符号表达和揭示自我新的感觉经验。那么,成在于此,败即于此。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感觉和经验的传达方式,语言符号赋予我们周围世界的经验以形式及其色彩。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认为,人类建构真实的世界是通过他们对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特别选择。他的学生本杰明·L·沃尔夫亦认为,说话的语言不同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具有语言共同特性的身体语言——舞蹈语言成形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以特定的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着特定民族生命生存的状态。因此,东方舞蹈家借鉴他文化他民族的生命经验来表现本文化本民族的生命经验之时,两种文化,两种环境,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经验之间的距离必然十分鲜明地凸显出来。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距离和差异缺少足够的认识,在文化借鉴中对语言系统不进行应有的必要的转换,由于二者间的不兼容性带来的文化冲突便不可避免。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是当下现代舞蹈家挂在嘴边上的两个口号。就其总体意义而言,前者是寻求外来文化“民族化”的一种努力,后者是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种追求。毫无疑问,两者方向的正确性都无可厚非。就其特定意义而言,这两句口号折射着东方的现代舞者期待被认同的心态,前者在于希望得到国人的认同,后者在于期待世界认同。从某种角度来说,或许出于走出本土文化困境的急切心情,或许国际认同更具有权威性,对接踵而来的本土认同更具有说服力,“与国际接轨”成为东方的现代舞者更心仪的目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种心仪之后悄悄发生的立足点的偏移,恰恰容易使我们背离现代艺术创造的初衷。
问题绝不在于“与国际接轨”将艺术创造的标尺瞄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而在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世界文化格局往往使我们的价值尺度依然指向西方。而在事实上,与国际能够接轨的现代重大艺术节日和活动几乎均以西方背景为“麦加”,东方的舞蹈家常常处于被选择的地位。这样,与国际接轨所采用的价值判断的尺度不在东方文化而在于他者文化。在被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选择下的与国际接轨的东方艺术,尤其是为了“走向世界”而迎合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的东方艺术,很难说有多少东方民族文化独立的品格。
身体的语言作为人类最早的语言形态是对生命进行诗意的表达,舞蹈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态的本质在于对生命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一些伟大的艺术创造往往不是诞生于艺术家刻意追赶时尚之中,而诞生于艺术家不失时机地关注和及时地提供了如何解决民族的生命的问题思考之中,当代东西方现代舞蹈家的重大成就亦产生于此。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和欧洲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生活变得复杂和严峻,面对这样一个变化了的世界,美国现代舞的奠基人玛莎·格雷姆认为她的艺术不可能像前辈艺术家那样去做一朵花,去成一片浪,或像古典芭蕾那样关心美的线条,她的舞蹈是要使人体成为能量发动机,表现人类有机的行为。玛莎·格雷姆以伴随着呼吸的强有力的腹部收缩和脊椎伸展,揭示人的欲望的人性的内在风景。为美国现代舞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石。
70年代德国现代舞蹈家皮娜·鲍希一跃成为世界现代舞蹈剧场的先锋与核心人物,她那破碎、压抑并充满暴力的舞蹈剧场或使观众一头雾水或使观众趋之若鹜,但她受到人们仰视的决不是表面的破碎、压抑和暴力的形式,而是在这之后所呈现的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状态和两性之间或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本质,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对德国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鲍希艺术的价值在于她负荷了整个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破碎和沉重。
20世纪,西方现代舞蹈艺术向东方文化渗透一直是单方面的,然而在70年代,日本现代“舞蹈”则一反常态将其影响向西方回流。“舞蹈”震撼和影响了欧美剧场大约不在于它那黑暗、畸型、丑和死亡之美的形式,而在于日本舞蹈家对日本战后文化的深入反思——尤其是对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精神肉体的畸型发展的揭示,对不断制造垃圾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的揭露。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艺术的先锋性和艺术的国际定位都不仅仅在于艺术家刻意追求的形式,而在于在这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之中的生命与情感的内涵,尤其是对于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对其现存问题的考索与解决。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属于世界的往往是民族最好的,这一观点的价值不在于它对民族文化本身的强调,而在于它指出民族文化中那些解决特定民族生存问题的成功经验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
由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我们应关注的是东方的接受而非西方的影响;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本土定位而非与“国际接轨”。当我们把艺术的触角切入民族生存最敏感的神经,我们的艺术才会具有冲击力与震撼力,我们只有背靠着民族文化的、哲学的和美学的坚实基石,我们的现代艺术无论批判还是建构,才会有文化的广度、美学的高度以及哲学的深度,我们的艺术的本土定位才能成为现实。而当我们成功地解决本民族生命生存中的艺术方式对他民族提供了经验之时,东方民族艺术的国际定位亦成为不争的事实。
“现代派”与“现代性”
关于“现代舞”亦是我们争论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概念。对于这个说不清的问题还必须说的原因是由于它直接关系我们前行的方向。现代舞虽说对其认识众说纷纭,但从表象上总括起来其基本特点主要与以下几方面概念相联,一是与过去时所对应的现在时的时间概念相联;一是与传统相对应的现展的历史概念相联;一是与现实主义相对应的现代主义美学概念相联;还有就是和古典芭蕾所相应的风格类别的概念相联。可是有人却狭隘地把东方的现代舞看成是西方舶来的一个现代派舞蹈流派,或仅把它界定为与芭蕾相区别的一个舞种风格,其结果是从本质上忽略了现代舞是一场实现舞蹈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艺术革命和艺术运动,从而未注意到现代舞蹈家们对“现代舞”的“现代性”的体认与强调。即便西方现代舞蹈家本身亦不强调“现代派”的派别,而强调现代舞是一种观点,一种对当代世界中艺术功能的态度(塞尔玛·珍妮·科恩语)。把现代舞理解为是一种心态,一种对舞蹈艺术与时代同步的必要性的认识(霍塞·林蒙语)。因此,淡出“现代派”,强化“现代性”是在文化融合与文化借鉴中,东方舞蹈家解决文化冲突问题的一个思想方法的关键,亦是使现代舞蹈文化牢牢地建构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石之上的关键。
所谓“现代派”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化艺术发展到20世纪的特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可以说,它是形形色色的标榜反传统的文学艺术家的总称,它是对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传统美学的一次彻底的反向运动。而“现代性”则应是指“现代人最深刻的本质,它即为现代思辨所揭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是那种超越自身,无限发展的精神”(丹尼斯·贝尔语)。在这种精神引领下建构起来的具有“现代性”的舞蹈艺术一是具有现时代的独创性;二是具有现时代的经典性。如果这两者均属于一切优秀艺术品的标志的话,那么,对于现代舞而言,它还具有和一切传统艺术相区别的“实验性”——为艺术与为生命的发展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而作出的超出传统价值判断的种种探索。因此,作为一个现代舞者不仅应该具有批判旧传统中的僵化成分的勇气,亦应具有超越旧传统建设新文化的能力。因为只具有破坏力而缺少建设性的艺术行为较少具有说服力。另外现代舞者还应具有坚强的神经,去迎接旧习俗的攻击与挑战,承受失败和环境的重压。并且以健康的心态,不急功近利,不媚权媚俗,不取媚西方。因为,现代舞的艺术尺度永远存在于它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特定的文化“角色”之中,永远存在于一个民族的现代审美理想之中。从另一方面而言,整个社会应对现代舞蹈的“探索性”与“实验性”具有足够的认识与理解,并对其敞开更宽广的怀抱。注意不要教条地以传统与主流艺术的标准来要求与规范它们,防止在这种要求和规范之中使这种探索与实验精神萎缩,而这种探索与实验精神萎缩所带来的不是作为现代舞一种舞蹈风格种类发展的滞缓,而可能将是一个民族舞蹈文化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的丧失。因为这是由于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在现时代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差异所致。前者代表着一个时代和民族已认同的价值标准与审美尺度,它以一种艺术的和谐维护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定。而现代艺术则代表着对传统秩序的一种突破力量,对旧有文化中不适应时展的部分提出质疑,以一种新的可能性取而代之,试图将艺术推向前进。
关于现代艺术的标准,有学者曾提问:大众的口味,官方的尺度,专家的判断,学院派的规范,到底哪一个是艺术的最高尺度呢?并且现代舞、古典舞,民间舞到底哪一种更重要呢?本文再次重复著名理论家约翰·罗素的话语以为作答:作为真正的艺术,是何种类都不重要,“在伟大的艺术家看来,所有艺术标榜的标签都是可笑和无聊的,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沉潜到他的艺术生命的底层,去开拓全新的生命意义和真正的艺术瑰宝。”并且如果我们坚持用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艺术精神建构我们本土的现代舞蹈艺术,东方现代舞蹈文化摆脱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走向融合,并在全球化的世纪里使自己的舞蹈艺术纳入世界民族舞蹈文化的轨道一定成为历史的必然。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