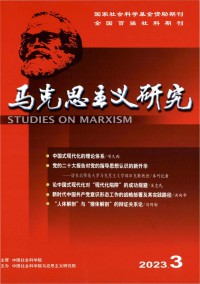马克思时代观和知识经济对知识经济一种时代观梳理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马克思时代观和知识经济对知识经济一种时代观梳理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内容摘要】以“五形态”论为主体;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层面的考察;全面把握时代的性质和特征间的关系,正确昭示时展的总脉络;科学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和复杂性,这四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决定了其特有的方法论功能。在我们所处的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必须要确立科学的时代观。在目前学术界关于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中存在着一种背离科学的时代观的倾向,即把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把握。因此,对“知识经济”做时代观上的梳理,便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时代观的一个重要契机。
从社会认识的表层上看,“时代”是人们对一定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变动的度的范围的一种称谓,但从社会认识的深层上看,“时代”是人们认识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系。这样,就产生了历史哲学视野中的“时代观”。然而,“时代观”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正因为如此,在人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重大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有不同的“时代观”碰撞。在对知识经济的认识上也概莫能外。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不少关于知识经济的“时代提法”,如:“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等。我以为,这类“时代提法”,如果仅用于具有“普及”意义的一般宣传上,或仅用于对我们所处时代一定阶段上科技和经济生产发展的某些特征及其趋势的称谓上,似乎还无可厚非,但若将其泛化,视为时代性质的根本变化或时代性质即将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那就值得推敲了。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时代观”的考察和对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的辨析,试图说明我们在现时代应确立和发展什么样的时代观。
一
科学的时代观有两个重要且相互联系的方法论功能:一是从静态上把握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历史时代中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揭示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或时代的性质;二是从动态上把握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历史时代中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演变发展,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规律。但科学的时代观是如何实现其方法论功能的呢?我以为,必须首先认识和把握科学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科学的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图式说”中,搞清楚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图式说”,也就明确了科学的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从而也就探明了科学的时代观是如何实现其方法论功能的。
1.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
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与“社会形态”是属于同构的范畴。(参见拙文:《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世界历史”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空间规定性,“社会形态”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而具有特定的空间规定性和一定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就是所谓的“时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五形态”(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论就是从总体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演变发展规律的逻辑论证。可以说,没有“五形态”论,就谈不上对“时代”的科学把握。当然,仅确定上述之点还不足以说明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五形态”论。笔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是“五形态”论,还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由。
首先,唯物史观在“时代”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就是科学的“时代观”,故唯物史观最核心的理论也就是科学“时代观”的最核心的理论。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唯物史观最核心的理论,而马克思的“五形态”论正是依据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的演变发展的规律的。所以,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构成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历史学笔记》等著作中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大量有关论述中得到印证,当然,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也有其他种类的划分(见下文),但这些划分并不能构成科学的“时代观”的主体。因为,以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为基础的“五形态”的演变发展是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毫无疑问,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直接、全面地昭示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从而在总体上把握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过程。此外,科学的“时代观”必须能够把握一定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作用,确定一定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指有阶级存在的时代)。显而易见,只有“五形态”论才能把握一定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作用,确定一定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其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观根据也正在于“五形态”论。因此,无视“五形态”论在马克思“时代观”中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在“时代观”的层面上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在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这又等于在逻辑上否定了马克思“时代观”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主旨就在于为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五形态”论则是这一主旨的“时代观”层面上的集中体现。由上可见,马克思“时代观”的主体只能是“五形态”论。至于如何理解“五形态”论普遍的方法论意义的问题,笔者已在有关论著中作了比较充分的阐释,故不赘言。(参见拙作:《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第四、七两章,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版)
2.以“五形态”论为主体的科学“时代观”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层面的考察
由于社会是多层面的,放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可从不同的视角上来考察,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除了“五形态”论以外,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还有其他种类的划分,如:两阶段划分:必然王国→自由王国。三阶段划分:(A)人的依赖性(自然经济社会)→物的依赖性或人的独立性(商品经济社会)→自由个性(产品经济社会);(B)个人从属于共同体→个人与共同体对立→共同体从属于个人;(C)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未来的社会形态;(D)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同占有制;(E)带有共同体外观的私有制→“纯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共同占有生产力总和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四阶段划分:(A)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自动化时代,等等。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上述划分形式与“五形态”论究竟是什么关系。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包括“五形态”论在内的“各种划分形式之间不存在哪种更根本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划分形式在认识对象上各有其限定的范围,而针对不同对象的认识角度是不能相互取代的”。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即看到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方位的考察,但却忽略了他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多种视角是有根本和非根本或主导和非主导之分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我以为,在马克思那里,既然“五形态”的演变发展是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主线,那么“五形态”论就必然是马克思科学地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逻辑视角。只要仔细揣摩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其他划分形式的“文本背景”,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他划分形式”都是在马克思考察“五形态”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们不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故对它们的论述在马克思那里也就不具有系统的形态。只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即生产方式为“划分标准”的“五形态”论,才能在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时代的演变发展规律。笔者的这种认识丝毫不意味着否认“其他划分形式”特定的方法论功用,而是强调:“其他划分形式”都只是在某个社会层面上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故它们在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中不可能与“五形态”论处于相同的地位。那么,它们与“五形态”论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在笔者看来,“其他划分形式”是对“五形态”论的逻辑补充和扩展,而“五形态”论则在逻辑上规定和包容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层面的考察。其“文本”根据是:首先,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第一个阶段,大都或是专指原始社会形态及其某一特征,或是指包括原始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如原生的社会形态、原始公有制、采集和渔猎时代、人的依赖性、个人从属共同体等。再者,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最后一个阶段,都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或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某一特征,如未来的社会形态、自由王国、自由个性(产品经济社会)、共同体从属于个人。自动化时代、共同占有制、共同占有生产力总和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等。其次,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某个阶段,大都或是专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某一特征,如物的依赖性或人的独立性、个人与共同体对立、纯粹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工业时代,或是指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两阶段划分”中的必然王国、“三阶段划分”中的次生的社会形态和私有制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其四,在“其他划分形式”中每一序列的某个阶段,大都或是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某一共有特征,或是指包括这两个社会形态在内的社会历史发展一定过程的某一特征,如带有共同体外观的私有制、农业时代、人的依赖性、个人从属于共同体、次生的社会形态、私有制等。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主要是为了全面地把握人类社会五形态的演变发展,特别是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历史性及其向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包括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和复杂性。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构成马克思“时代观”主体的只能“五形态”论。当然,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我们只有在搞清楚“五形态”论与这些“划分形式”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这种方法论意义。
3.马克思的“时代观”科学地昭示了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的关系,从而全面地把握了时展的总脉络
实际上,在考察“五形态”论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其他划分形式间关系的过程中,笔者已从一个侧面论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所谓时代的性质是指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力量或因素对时代的规定性。对此,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了它们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4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一种一定的生产”,指的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力量或因素”。对于马克思的“时代观”来说,确定一定的时代的性质是考察一切重大社会问题的逻辑基点。离开了这一逻辑基点,对任何重大社会问题的考察都无从谈起。与“时代的性质”相对应的是“时代的特征”。“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无疑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决不能因此而把它们混为一谈。
与“时代的特征”相比较,“时代的性质”有着更为稳定、单一的特点。而“时代的特征”则是复杂多样的。它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一定时代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其内容如该时代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特点等。这方面的提法有:采集和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自动化时代;原始公有制、私有制、“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共产主义的“个人所有制”等。二是,一定时代的某一发展阶段的特征,其内容如该时代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导向等。这方面的提法有:“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等。三是,一定时代某一发展阶段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其内容如在该时代某一发展阶段中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其社会生活影响的特点等。这方面的提法有:“蒸汽革命时代”、“电力革命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等。因此,具有特定的空间规定性和一定性质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即“时代”会呈现出多种特征,人们可以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来把握“时代的特征”。但“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毕竟不是一回事。19世纪的马克思既经历了以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为特征的时代,又经历了以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为特征的时代,同时还经历了“蒸汽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和“电力革命时代”的初期(他为“电力革命”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即将产生的深远影响而欢欣鼓舞),但他关于时代性质的观点(即他所处的时代仍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自20世纪初以来,人类社会开始由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过渡,当代社会主义处于这一过渡的整个过程的起点上。不过,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历史时代过渡是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将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所以,更确切地说,人类自20世纪初外来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多种特征都是由这个时代的根本性质所直接或间接规定的。
我以为,马克思的“时代观”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我们所处时代及其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既然“时代的特征”不等于“时代的性质”,那么,用“时代的特征”来直接界定“时代的性质”或把“时代的特征”视为“时代的性质”,就必然会把“时代的性质”搞得模糊不清。例如,无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提法,还是围绕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都不是对我们所处时代性质的界定。如果用上述这两类时代提法来直接界定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关于时代问题的研究中就会出现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此外,把“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时代的性质”,在方法论上把时代的某一方面、某一时期或某一时期的某一社会层面的特征绝对化,还会导致实践中的重大错误。对现时代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考察(包括重大的战略方针的正确制定过程)必须以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的正确界定为基点,因此,对“时代的性质”的界定出现了偏差,就会导致实践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从而也就必然会导致实践中的重大失误。例如,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曾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提法绝对化,从而在国内外形势、战争与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的编差,这就使得我们的实践活动往往受“左”的倾向的干扰。再如,近些年来,一些人又把“和平与发展”以及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绝对化,而忽略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以及科学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面,发达国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剥削和控制的一面,这种错误的倾向也同样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损害。4.马克思的“时代观”科学地揭示了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
从逻辑上看,以“五形态”论主体、科学昭示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的相互关系,从而全面把握时展总脉络的马克思的“时代观”,当然内在地包含着对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的科学揭示。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及其复杂性的论述上。鉴于人们对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必然性的论述较为熟知,放在此笔者仅简略地谈谈马克思关于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复杂性的认识及其过程。
19世纪50年代中期,在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考察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将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过程中,马克思作出了这样预测:“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球。”“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引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264页)可见,马克思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在20世纪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即美国的出现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性;人类将经历一个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并存、竞争,且资本关系仍占据统治和优势地位的发展阶段。虽然当代两种社会制度存在的“地区界限”并不是象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但这毕竟说明他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上把握了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代过渡的复杂性。此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展的复杂性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19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马克思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围绕着限制和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过程及其复杂性;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马克思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状况,围绕着限制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问题,从科学的时代观的角度昭示了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过程及其复杂性。关于马克思在上述这两个时期对“复杂性”问题的具体论述,我曾在有关文章中作了详尽的说明,故不赘述。(参见拙文《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综上所述,马克思时代观的基本逻辑框架决定了其特有的方法论功能。这种方法论功能使当今人们能够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他们所处时代的性质、演变发展的总脉络及其向更高一级时展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二
我以为,从方法论上看,目前学术界出现的把关于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如:“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泛化的倾向,与长期以来学术界不少人把从传统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转变一般过程的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有直接的关联。以下,笔者拟从对这一逻辑“描述”的局限性的剖析人手,对有关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作时代观上的梳理,旨在搞清楚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时代观的问题。
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般过程机为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必经的社会发展道路,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即:试图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但也有其明显局限性。首先,这一发展图式舍去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把并存的不同社会制度(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纳入同一发展序列,这就必然易于在方法论上导致把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简单化,忽略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参见拙文《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21第2期)因此,如果把这一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就会直接得出“趋同论”(指在方法论上抹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区别的“趋同论”)的结论。再者,即便从“技术经济”的角度上看,这一发展图式也仅是比较适合于20世纪以前的世界发展状况,而不适合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状况。如果硬要把这一发展图式“严丝合缝”地套于现代,那么就会产生“历史的虚构”。帕特(AlejandroPotters)在从方法论上分析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演化分化理论的弊病时指出:“现代化理论与演化分化论一样迷信于发展是从一初期的传统时代走到一前进的终点,如果把传统视为与现代在逻辑上相对立的状态,当代存在的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一个是‘传统的’这种过程中初期阶段的虚构性,归咎于它的观察完全不凭据社会事实,却凭据"最后"阶段的性质臆造出来。用OwenLattmore(1962)的话来说,是‘文明造就了野蛮’。”(转引自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版,第46页)同时,把这一发展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还易于在方法论上导致把西方国家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或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泛化”。众所周知,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迄今为止,能够被人们通常称之为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的国家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见,看不到上述逻辑“描述”的局限性,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化,即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就必然会在方法论上导致种种错误的出现。同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般过程的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一样,近些年来学术界所出现的把“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提法泛化的倾向,在方法论上也是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目前学术界为这种倾向的合理性作论证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人类科学现在已从传统的小科学进入大科学阶段”,“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历史的潮流”。所谓“大科学”即是指当代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越来越广泛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态势。应当承认,这种态势的确存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也的确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是否能由此得出可以直接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的层面上确定时代的性质或社会历史整体发展阶段性的结论。我以为恐怕还不能。首先,科学技术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中介环节实现的,而不是直接的或“立竿见影”的,无论科学技术和所谓“大科学”发展的程度有多高,这一点都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由社会“组织一结构”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所谓“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指的是“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社会分工、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文化传统、-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如果这些社会环节不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社会历史或时代的整体的质的变化就是不可能的。再则,科学技术对社会其他各个层面的影响又是复杂的。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比较快,如“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部分的社会分工形式、一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而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则比较慢,如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特别是上层建筑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同时,即便是接受科学技术影响比较快的社会层面,其深层也不会立刻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构成了科学技术作用的不均衡性。其三,上述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的重大变化不仅仅取决科学技术本身的作用,而且取决于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自身的发展状况。进而言之,上述每一个社会中介环节都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科学技术对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作用的程度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自身发展的程度。最后,科学技术作用的本身又受其他社会层面的制约。例如,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被赋予了“正负”双重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不少人把科学技术称之为“双刃剑”,虽然这种称谓并不很准确。
可见,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确定时代的性质,抑或说,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层面上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这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科学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也在一再向人们印证这一点。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创造一个“网络世界”,使“地球村”真正成为现实,但它在给人们的经济生产、社会交往关系等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使人类同临着前所未有的种种困扰:经济生产中泛起“新型泡沫”;泛滥着的无政府主义猛烈地冲击着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经济安全)受到严峻挑战;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通过网络世界大肆推行精神霸权主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高科技犯罪不断“花样翻新”;网络关系中道德相对主义愈来愈盛行,道德人格严重扭曲,从而道德失范现象愈演愈烈;私人生活领域和个人的权力被严重侵犯;人与人之间产生新的隔阂①,等等。学术界有人乐观地断言,“网络曾以前所未有的优势造福于人类,消除人的异化现象”。在这里笔者试图“修正”和“补全”这句话,即:网络在以前所未有的优势造福于人类,消除一些旧的人的异化现象的同时,也对人类构成了新的威胁,造就了新的人的异化现象。
虚拟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原有的主一客体活动方式,提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然而,只看到这一点就显得太“单纯”了。虚拟空间的主体及其活动归根结底是由现实生活中的主体来“虚拟”的,虚拟技术是“不管”谁来虚拟和虚拟什么的。这里就有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阶级观的冲突。众所周知,目前虚拟犯罪、虚拟战争(包括地球上的战争和星际战争)、虚拟“三角”恋爱、虚拟“同居”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家庭关系等,已向人类的政治、法律、文化和伦理提出了的挑战。学术界有的人说,“数字化生存”能使人类抽象的思维直接转化为“数字化”生存空间的真实,这并不错,但要加以说明:正是因为出现在“数字化”世界中的真实是由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抽象思维转化而来的,所以,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美的东西与丑的东西、富有朝气和创造性的东西与腐朽的和情性的东西都会在“数字化”世界中以各种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和“发挥”出来。
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现时代人在更大的程度上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无疑为人的多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不过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伴随着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而来的还有:“无解”的结构性失业的规模越来越庞大;患有“信息综合症”的人日益增多;“信息垃圾”对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年的污染日趋严重;人类生活模式特别是语言模式日益单一化;信息程序使人越来越陷入了一种“由电脑世界带来的新的孤独之中”;个人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丧失了“文化直觉”,等等。在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是,微电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只是为人的多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是否所有的人都利用闲暇时间来在各方面提高自己,这则是另一个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闲暇时间的增加也可能导致更多的社会的矛盾、冲突或紧张关系。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群”的一个重要环节。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应是不言而喻。可是,如果因此而认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将会直接导致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那似乎又颇显得幼稚。首先,通过应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人类大规模制造或合成的自然界没有的物种、生命和各种消费资料将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至今仍是需要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此外,至少在可以预料到的将来,人类还不能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使用加以有效的规范。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既能用于有益的生产上,也能用于武器的制造上。目前,由于种种利益上的需要,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或集团正在大力发展生化武器特别是基因武器。从长远来看,这类武器对整个人类生存的危害将会比核武器要大得多。二是,“科隆”技术的发展方向难以控制。我国有的科学家就此指出,在缺乏伦理探讨和技术保障的现阶段,要严格区分治疗性科隆和生殖性科隆。生殖性科隆将会对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产生极大冲击,其恶果难以预料。目前,尽管主流生命科学界反对科隆人,但仍有人在实施科隆人的计划(如意大利医生塞韦里诺·安蒂诺里就正在实施有5000人参与的科隆人的研究计划)。学术界不少人认为,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十大高新技术的发展使知识资源成为人类的共享。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只是在一定的层面上即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是正确的。所谓“一般知识传播”至少不包括世界性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技术资源的传播。如果超越了一般知识传播的层面,上述观点就会变成为谬误。因为,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资源,从而也就不可能均等享受知识“爆炸式”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收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一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能够分取到多大份额,与一国原来拥有的知识资源优势以及认识与利用知识的速度、规模、范围和效果直接相关。显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资源方面的巨大历史差距,故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高新技术所带来的全球利益分配明显不利于缺乏知识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当然,笔者的这种看法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资源不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而是说发达国家的尖端技术或最先进的技术资源是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共享的资源(如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至少在发达国家已有十年以上的周期)。正因为以上所述,在所谓“信息时代”,世界性的两极分化日益加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力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激增,但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受益。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贸易、劳务和金融市场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它们每年损失金额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每年接受外援总额的10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已下降到0.3%,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人口占世界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1%。两年之后(即199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继而又在《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的国家20%的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人在1994-1998年使自己的资产增加了l.2倍,总收入占全球人口收入的41%。1990--1998年,世界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收入之比,从30:l上升到74:l。
……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笔者的以上分析,并不是要简章地印证科学技术作用的“双重性”(法国的启蒙学者早在几百年前就印证了这一点),而是旨在说明:把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或即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囊括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提法中,这至少在学理上是很不严肃的。当然,“知识经济”、“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和“新经济”等,的确是对我们所处时代一定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某些特点的种种概括(姑且不论是否准确),但决不能将它们“泛化”为我们所处时代性质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标志”。否则,一个与此相关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无法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包括所谓“全球问题”在内的主要社会问题至今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不能脱离开对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的科学分析,直接从现代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中推导出人类文明和现代社会即将发生质的变化。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时代观”为后人树立的典范。
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75页)
就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关系的复杂性而言,马克思的以上论述至少说明了科学的时代观的一个重要特点: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及其作用,但不是“唯科学技术”论。马克思曾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对这一论断是有限定的:科学技术不会直接导致社会的整体进步,它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与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这是就其作用的最终意义而言的,而不是就其作用的具体过程而言的。如果就其作用的具体过程而言,至少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科学技术的作用仍然是双重的,即如诺伯特·维纳斯所说:“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马克思从科学时代观的高度把科学技术的这种双重作用归结为“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并进而指出,“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而这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历史时代取代资本主义历史时代来实现。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如前文所述,人类自20世纪初以来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虽然近百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不过时代的这一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对现代科学技术及其作用的具体过程的科学考察必须基于我们对所处时代的性质的正确认识才有可能。
科学的时代观的上述重要特点也表明: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直接确定时代的性质,这既不能昭示人类社会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层面与其他社会层面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确定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或时代的性质,也不能正确认识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间的关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脉络,揭示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规律及其复杂性,从而也就更不可能合理地解释科学技术与社会整体发展间关系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目前学术界关于“知识经济”的种种时代提法中所反映出的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直接确定时代性质的观点,其方法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技术经济形态的分析取代社会形态的分析,把时代的特征等同于时代的性质,把历史时展的某一层面等同于历史时展的总体,忽略由较低一级的历史时代向较高一级的历史时展的复杂性,从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关系简单化。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在我们所处的风云变幻时代中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时代观。
(该论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项目--“对知识经济的历史观透视”(项目编号02BZX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
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叶险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
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